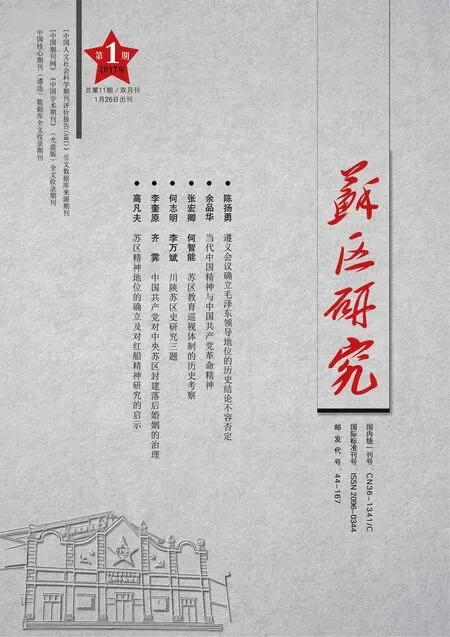群众教育阵地:中央苏区俱乐部研究
2017-01-28邱泉
邱 泉
群众教育阵地:中央苏区俱乐部研究
邱 泉
俱乐部是革命年代中共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土地革命战争环境下,俱乐部工作成为了中央苏区社会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在中央及各级党政机关尤其是教育部的领导下,俱乐部由偏娱乐的群众组织逐渐演变成面向群众的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俱乐部积极参与苏区建设,密切了与其它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最终成为中央苏区一个重要的群众教育阵地。
俱乐部;中央苏区;社会文化教育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为了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各连队都成立了军人活动室,这是中央苏区军人俱乐部的前身。*汪木兰、林碧珍:《中央苏区文艺运动大事记》(1987年12月30日),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老年文艺家协会编:《江西文艺史料》第2辑,江西文艺印刷厂1988年版,第138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土地革命形势逐渐高涨,红四军随后进军赣南、闽西,推动了这些区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1931年底中央苏区建立,各级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逐渐意识到群众组织的重要性,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则重视以俱乐部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教育组织的建设。苏区俱乐部规模不断扩大,工作不断向基层延伸,制度不断规范,有力地推动了苏区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丰富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支撑了革命战争的进行。关于苏区俱乐部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学界对苏区俱乐部的专门研究论文主要有祝也安的《闽浙赣苏区的农村俱乐部》(《江西文艺史料》第13辑,江西文艺印刷厂1992年版),庞振宇的《论苏区文化建设中的乡村俱乐部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刘魁、江明明的《革命性与娱乐性:中共与民众互动视野下的苏区戏剧》(《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陈始发的《试析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与深刻启示》(《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涉及俱乐部考察的苏区文化与教育研究的论著有万叶、吴邦初的《中央苏区戏剧史》(收录在刘云主编的《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董源来的《中央苏区教育简论》(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李国强的《中央苏区教育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王予霞的《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汤家庆的《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史》(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等。但以中央苏区俱乐部这一重要群众文化教育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央苏区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俱乐部作为中央苏区时期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教育组织之一,对其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准确认识中央苏区时期社会文化教育组织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准确理解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教育的群众性、革命性特点,正确把握革命年代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探索之路。
一、中央苏区建立前俱乐部的初步发展
俱乐部起初是中共借鉴苏联经验进行群众工作的一个载体,它是伴随着土地革命形势发展而不断兴起的。中央苏区建立前,闽西、赣西南等地的俱乐部已逐渐建立起来,此时俱乐部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军队俱乐部,一是群众俱乐部。
(一)红军内俱乐部的兴起
俱乐部最初主要是在军队当中建立和发展。在赣、闽、湘、粤交界的广大区域里,则是以红四军等军队俱乐部的发展为标志。在1929年时红四军内有俱乐会,它并非纯粹的社会文化教育组织,而是政治教育的一种,同时在士兵委员会内有娱乐科,具体有演说、新剧、京广团、双簧、跳舞、魔术等娱乐形式,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陈毅:《关于红军的宣传工作(节录)》(1929年9月1日),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这些都为红军内俱乐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的召开对俱乐部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会议决议案指出,在会议召开前红四军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人民军队的宣传工作需要有俱乐部的广泛建立。决议案提出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中建立俱乐部,并提出宣传工作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20页。这为苏区俱乐部建设指明了方向。从古田会议到中央苏区建立,俱乐部主要是在军队当中发展,“在红军中成为教育群众的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1933年6月5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1页。,红军官兵经常在俱乐部中开展唱歌、演戏等文艺活动,以此配合部队的政治宣传。与此同时,军队俱乐部也积极帮助苏区地方群众俱乐部开展活动。1930年冬天,红军建立工农红军学校,其政治部下设俱乐部,下辖文化、体育、戏剧管理委员会,演出革命戏剧,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二)群众俱乐部组织的初步建设
群众俱乐部方面,闽西的俱乐部工作在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古田会议前,闽西在群众文化工作方面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政策上强调俱乐部的组织建设。在1929年5月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即指出,在闽西已经进行的群众工作,尤其是工人运动中,是以办俱乐部作为主要工作方式的。虽然办好的俱乐部仅有建筑俱乐部一个,但也起到了娱乐、宣传政治以及办夜学的作用。*《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军事、党务与地方工作情况》(1929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1929年8月,福建省委致信闽西,指示教育群众是一项主要工作,应通过组织俱乐部来教育群众。12月13日,共青团闽西特委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提出每乡要设一俱乐部。*《共青团闽西特委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决议案(节录)》(1929年12月13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闽西革命史参考资料》编写组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1982年版,第330页。月底,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则提出俱乐部在层级上分为乡、区、县三级,每乡、每区、每县均设一俱乐部,规模逐次增大;结构上由保管股、游艺股、图书股、布置股四部分组成,由俱乐部主任统一领导;俱乐部委员乡一级由群众加入并召集会议推选,区一级则由所在各乡俱乐部代表会推选,县一级则由所在区召集区俱乐部代表推举;设置上俱乐部应当开设在人口集中处,并规定了俱乐部的布置。*《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案》(1929年12月26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345页。然而这一时期闽西苏区俱乐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俱乐部下辖新剧团演员虽然提出要鼓动群众参与,但同时强调“性情比较接近艺术的最好”,倾向知识份子可多一些,*《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案》(1929年12月26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347页。群众工作的指向性不够明确。这一时期俱乐部都是单纯的娱乐场所,很少有革命意义。针对这一点,闽西苏维埃要求俱乐部必须健全地建立起来,不能单纯地娱乐,而要以群众为对象,将俱乐部建成群众的革命教育机关。*《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七号)》(1930年6月20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33页。
在古田会议后,闽西苏区又对俱乐部工作进行了改进,要求各乡村均须建立一所俱乐部,并将俱乐部明确为社会教育机关,强调俱乐部应纠正过去单纯的胡琴锣鼓的错误,以讲有趣味的革命故事、唱革命的歌曲、演革命的剧、通俗演讲等方式起到在娱乐中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政治认识的作用,还提出俱乐部建立通俗图书馆以供给群众适宜读物,建立读报团以宣读并讲解各种革命报纸及宣言等建议。*《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宣传问题草案(节录)》(1930年8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40页。至1931年4月,在《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决议案》中又将俱乐部明确为文化团体,并认为其是“农村中最有力量的文化团体”*《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决议案》(1931年4月21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48页。,应当予以健全。1931年7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委员会通过的《闽西各县、区文委联席会决议案》更是明确提出:俱乐部不是少数会弹琴唱曲人的俱乐机关,而是广大群众的集会场所。*《闽西各县、区文委联席会决议案》(1931年7月8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第2册,1985年版,第68页。
1930年初,红四军回师赣南,中共赣西南特委在新革命形势下制定了“社会教育新计划”,提出组织文化机关俱乐部,但是此时的俱乐部只是打打锣鼓,或集合起来唱革命歌曲、呼口号,偏于娱乐,组织也不健全。*万叶、吴邦初:《中央苏区戏剧史》,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在闽西、赣南等地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况下,1931年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强调在苏区内必须发展俱乐部、游艺会、晚会等工作,并提出应该尽量吸收群众,尤其是青年男女,*《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1931年4月21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1页。这反映出中共中央在闽西、赣南等苏区俱乐部不断建设发展的基础上逐渐认可这一社会文化教育方式,并将其列为文化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点。
二、中央苏区俱乐部的初步发展(1931年11月-1933年5月)
中央苏区建立后,各级党、团、少先队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总结了以往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经验教训,对俱乐部组织制定了新政策。
杨尚昆在强调中央苏区宣传鼓动重要性的同时,提出要有计划地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经常的工作,尤其提出俱乐部应该将内容充实起来,成立唱歌、戏剧、美术等各种小组。*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1933年2月4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59页。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团针对宗教迷信活动,利用在俱乐部内组织“不信神教同盟”进行反宗教行动,使得俱乐部成为反宗教迷信群众工作的重要载体。少先队则发动广大队员及青年工农群众加入俱乐部。
各省苏在前一阶段俱乐部发展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俱乐部的认识,并对俱乐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江西省革命基础深厚,也较为注重俱乐部工作。江西省苏意识到除军队外,俱乐部的工作没有建立,分析其原因为人才和经济的缺乏,也认识到俱乐部是易于团结群众、鼓动群众,容易收广大效力的文化教育组织,俱乐部工作不力会影响到工农群众,使其不能得到识字读书的机会。由此可见,俱乐部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普遍地在各区乡建立俱乐部,注重工农群众的文化工作,提倡用革命竞赛方法促进俱乐部发展,进而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此次会议后,在江西省苏范围内,俱乐部工作大力开展起来。*《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1932年5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2页。
湘赣省处于中央苏区的外沿,更偏重于革命战争中的娱乐工作。其在1932年9月提出,每乡应建立俱乐部,注意各种娱乐事业,*《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节录)》(1932年9月6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第1册,第126页。反映该省这一时期俱乐部工作重点在于组织建设与娱乐工作的开展。
闽浙赣省较有群众文化工作的基础,在1933年3月召开的全苏“二大”文化决议中指出“俱乐部工作,是文化工作最主要的部门,是最易于团结群众、鼓动群众、教育群众的文化机关”,提出普遍建立各乡俱乐部的要求,并提出俱乐部结构应包括识字、读报、壁报、工农补习夜校、新戏运动、晚会、研究工作的各部分,俱乐部工作内容主要是:要以阶级的政治的教育,鼓励群众对革命战争的热情,传达解释苏维埃一切重要决议与中心工作。*《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3年3月23日),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等编:《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而在县、区、乡一级,各地加大了俱乐部的建设。兴国于1932年底在115个乡全部建成了俱乐部,如黄岭乡俱乐部下设教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及政治研究组等机构,成了农村政治工作、宣传教育、文化娱乐的大讲堂,是中央苏区各乡俱乐部工作的一个典型。*兴国革命纪念馆:《苏区兴国革命文化概况》,《江西文艺史料》第6辑,江西文艺印刷厂1989年版,第7-8页。兴国高圩黄岑乡模范支部在1933年4月闽赣两省联席会议上做了工作报告,其中论及俱乐部工作。该乡俱乐部下设教育委员会,含九十多个识字班,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女都参加,七岁以上的男女都识得字,另有墙报委员会和晚会委员会,晚会委员会排演新戏,表演化妆演讲,受到群众欢迎,每次表演观众有数百人。由于该乡俱乐部工作紧密联系群众,群众对俱乐部工作表现热烈,费用由群众自愿捐助,并且群众也能参与俱乐部各种组织及工作。*《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节录)》(1933年4月),《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第6册,第88页。
中央苏区建立伊始,俱乐部组织工作在有基础的地区取得了更加深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过去不重视俱乐部或发展较弱的地区,这一时期俱乐部从无到有,从弱渐强,突出地表现在各地俱乐部广泛建立,如至1932年8月永丰县建立起俱乐部7所,*《中共永丰县委八月份工作总报告》(1932年9月8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2),内部资料,1986年,第7页。胜利县建立起俱乐部38所。*《中共胜利县委八月份工作报告大纲》(1932年9月9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2),第29页。至1932年,胜利等江西省苏十四县俱乐部有712个。*《江西省苏报告(二)》,《红色中华》1932年11月28日,第8版。而中央苏区建立后,相应地各省也建立起苏维埃政府,各省苏纷纷召开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并不断完善文化、教育等组织机构,加强了革命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尤其是社会文化教育工作。这对于俱乐部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促使其由强调娱乐的群众组织逐渐转变成群众性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在此基础上《区乡村俱乐部组织系统与工作任务》出台,规定基层区、乡村俱乐部由县、区文化部领导,县俱乐部设管理委员会,下辖艺术、体育、晚会、墙报、文化五委员会,村俱乐部委员会中的艺术委员会主要负责画报工作,体育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田径赛等体育活动,晚会委员会则主要负责杂耍、歌舞、新剧等工作,墙报委员会主要负责墙报编辑等工作,文化委员会主要负责讲演、读报、研究等工作。*《区乡村俱乐部组织系统与工作任务》(1933年4月2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及补遗部分)》,内部资料,1992年,第113页。这一文件对于之后中央苏区俱乐部组织的规范发展起到了探索作用。
三、中央苏区俱乐部的规范发展(1933年6月-1934年10月)
(一)总结教训
1933年,中央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红五月检查。通过红五月及六月份各级宣传部对俱乐部列宁室工作的检查,反映出上一阶段俱乐部工作的局限:
组织上,俱乐部不健全、不普遍,还有不少的地方没有建立这些组织。同时,各级党的宣传部对俱乐部列宁室工作的领导是异常忽视,没有具体地想出办法去领导这一工作,没有积极地发动党团员去参加这一工作,*《怎样去领导俱乐部、列宁室工作》(1933年7月12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4页。这都反映出党、政、团等各级组织对俱乐部领导和参与还不够。
工作上,大部分的俱乐部工作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俱乐部工作偏重于娱乐方面,即使是已开展的墙报及识字晚会等,有的异常不实际,不重视内容,不能切实联系党的中心任务与群众实际生活,并开展斗争,*《怎样去领导俱乐部、列宁室工作》(1933年7月12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4页。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形式主义严重。晚会的形式主要是老戏、打花鼓、唱京调、跳舞,极少表演有革命意义的新剧和歌曲,不能推动党领导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这就反映出俱乐部的工作没有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偏于单纯的群众娱乐,忽略了党的群众工作服务于革命的重要原则。
另外,虽然各地广泛地建立起了各级俱乐部,但是挂招牌的现象*《提高少先队员的文化水平(加紧少年先锋队的教育工作之二)》(1933年3月19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9页。严重,相当一部分建立起的俱乐部缺乏实际的活动。俱乐部既不能作为中坚组织支撑苏区其它政治运动的开展,也难以有效促进团、少先队等组织的发展。《青年实话》在1933年3月19日即指出加紧少年先锋队的教育,需要俱乐部发动少先队队员积极参加唱歌、音乐、跳舞的训练,这也反映出俱乐部并未很好地起到促进少先队队员发展的作用。
中央教育部认识到前一阶段俱乐部工作的局限,得出了深刻教训:“总括起来说,过去的俱乐部没有普遍的建立,尤其是在乡村没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忽视了政治动员,偏重娱乐,没有很好的利用各种群众集会和开放俱乐部为群众集会场所,来进行教育工作,没有广泛的吸收劳动妇女及儿童参加工作,没有利用墙报做斗争工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1933年6月5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2页。这充分指明了之前阶段俱乐部偏重娱乐、群众工作不力的现象。即使如此,俱乐部因为能利用各种各样适合不同年龄及文化程度的教育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教育广大群众;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吸收群众、动员群众;能利用群众自己参加活动来教育自己,中央教育部仍肯定其在教育上占极高的位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1933年6月5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1页。
(二)新发展
针对上一阶段俱乐部工作的局限,中央苏区在1933年6月之后加强了俱乐部组织的建设。一方面,强调加强党对俱乐部工作的领导,制定各项关于俱乐部的法规制度,要求各级宣传部须对俱乐部工作进行讨论及检查。另一方面,充实俱乐部工作的内容,要求俱乐部工作应与党的任务联系起来,深入教育群众。
1.制定俱乐部法规,完善俱乐部制度
1933年6月,中央教育部颁布《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强调俱乐部是进行社会教育的机关,*中央教育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09页。将其当作除识字运动委员会、夜校外最主要的教育文化工作机关。同时教育部要求加强对俱乐部的领导,要求各级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尤其是社会教育科,应当有计划地领导俱乐部工作,要求乡教育委员会要经常领导和检查乡村俱乐部工作,切实执行中央教育部颁布的俱乐部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1933年6月5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1页。《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将俱乐部的工作主要分为运动、游戏、集会、出版、展览五种;组织上则设立管理委员会及管理委员会领导之下的各委员会;工作形式则设有讲演会、识字运动、墙报、戏剧、活报、双簧、歌舞、科学游戏等;规定俱乐部工作的目的是教育群众,强调利用群众集会如群众大会、讨论会、晚会等;另外俱乐部在经费上利用社会,依靠会员会金,注重节省;于干部方面则在群众中选拔积极分子,尤其注重妇女与儿童的引入。*中央教育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09页。
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重订了《俱乐部纲要》,在俱乐部制度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提升了对俱乐部的认识,“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学识,以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为目的,所以俱乐部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在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强调俱乐部的工作应当是服务于革命战争;二是完善俱乐部设置,强化俱乐部与列宁室的层级关系,每一俱乐部之下,按照伙食单位(或村庄)成立列宁室;三是强制全体公民加入俱乐部,凡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同时为扩大俱乐部的群众基础,规定非公民而能担负俱乐工作并无违犯苏维埃法令的行为者,亦得加入;四是对俱乐部的执行机关进行明确规定,俱乐部必须定期召集部员大会或部员代表会议,定期向群众报告自己的工作;五是规定俱乐部必须以政治动员为中心计划进行工作;六是要求俱乐部的组织形式应当适合当时当地的条件,灵活的适应当地群众的需要;七是内容上要求一定要尽量利用最通俗的、广大群众所了解的旧形式而革新它的内容——表现发扬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八是规定俱乐部的组织结构,最基本的为演讲股、游艺股及文化股;九是强调俱乐部要不断发展自身,可以日益进到比较复杂的组织,如组织各种研究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尤其是戏剧工作,可以成立工农剧社支社,并要加强与消灭文盲协会、工农通讯协会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或体育、文艺等研究会的关系。*教育人民委员部:《俱乐部纲要》(1934年4月),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934年6月,中央教育部发布《俱乐部的组织与工作》,一面规范俱乐部的组织系统,另一面亦强调俱乐部组织的灵活性,制订了俱乐部组织系统表。根据组织系统表,俱乐部设管理委员会,正、副主任各一人,管理委员会下设展览股、讲演股或集会股、游艺股、文化股、组织股。文化股主要含墙报、讲报两项工作。游艺股分为戏剧、音乐、体育、游戏等组。集会股负责组织演讲会及晚会工作。组织股负责统计登记部员和干部,组织宣传队,推动政治动员等工作。展览股负责俱乐部展览室的收集、保管及陈列等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俱乐部的组织与工作》(1934年6月30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22页。
除了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下的群众俱乐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教育部还加强了军队俱乐部制度的建设。1934年9月,中央教育部制定了《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指出了俱乐部在红军文化教育上的重要意义,即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培养活泼的精神与积极工作的兴趣,有利于克服一切政治上、生活上不正确的倾向,养成和巩固红军坚决的革命的精神,有利于培养红色战斗员活泼的生活兴趣,消灭不良习惯,提高文化水平,红军俱乐部正是要通过有计划的、切实地进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用娱乐的方式在军队中深入开展政治教育;规定组织上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俱乐部被确定为各小单位的文化娱乐教育领导机构;俱乐部层级分为两级,以主任为首,管理委员会为执行机关,下辖晚会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墙报委员会、体育委员会、文化委员会。*政治部:《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1934年),《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27页。这一时期军队俱乐部制度的发展为第五次反“围剿”及之后的长征的胜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是军内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一次深刻反映。
2.新俱乐部制度下的实践
在中央教育部出台俱乐部的相关规章制度后,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教育部门即着手改进俱乐部工作。江西省苏维埃于1933年7月29日全省总结会议上通过《江西省教育工作计划大纲》,对俱乐部工作进行了规定:建制上,千人建一个俱乐部;质量上,要求俱乐部从祠堂或没收土豪的房屋中选取大厅来做群众大会的会场,并建设书报社、展览室、乒乓室、奕棋室及运动场等,俱乐部每月要有工作计划、工作检查及布置工作的各种会议,每月要开会员大会一次,管理委员会主任要按月作工作报告,另外俱乐部的工作还要定期检查;内容上,要求俱乐部广泛开展墙报、晚会、政治讨论会、运动会、读报等活动,并编定日历形成机制;组织上,俱乐部应经常征收部员,扩大规模,使俱乐部各个部门都成为群众组织。*《江西省教育工作计划大纲——七月二十九日全省总结会议通过》(1933年7月29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06页。
至1934年3月,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召开了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颁布了《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再次强调整顿并发展俱乐部的工作,强调不应当限于晚会,晚会也不应当限于演戏,要求全面发展俱乐部工作,一方面要求扩充实际工作内容,俱乐部等工作应包含政治演讲会或谈话会、科学演讲会和谈话会、读报和讲报、运动和游艺、墙报、演戏及化装演讲等,另一方面强调群众的参与和地方的需要,提出游艺可以采取乐器、山歌、象棋等旧形式,运动亦可采用农村中原有的体育运动形式。*《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节录)》(1934年3月13日至14日),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第21页。1934年1月湘赣省教育部发布了《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纲要》,对俱乐部的组织机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对湘赣省各级俱乐部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汪木兰、林碧珍:《中央苏区文艺运动大事记》(1987年12月30日),《江西文艺史料》第2辑,第138页。
瑞金等各县也积极开展俱乐部的建设工作,地方各级政府及各级教育部也认识到俱乐部工作的重要性,它们积极进行各地俱乐部的检阅工作。毛泽东1933年年底对才溪乡和长冈乡进行了调查,才溪乡有俱乐部一个,工作人员有五十多人,其中新剧团占三十多人,*毛泽东:《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73页。长冈乡下辖四个村各有一个俱乐部,且结构较为完整,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表演新戏,出墙报,尤其是墙报十篇虽然大部分由小学生编写,但是群众也占两篇,*毛泽东:《长冈乡调查》(1933年12月15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76页。反映了俱乐部工作群众性的特点逐渐凸显。同一时期,瑞京县教育部召集了全县俱乐部大检阅,县辖各区表演了新剧,第一晚表演的人少,看的人也少,但到了第二晚、第三晚,参加表演的人多了,看的人也多了,第三晚虽表演到两点钟之夜,而看的人还有二千多人,没有走灭一个,直到完毕,才热热闹闹的散会,*王昌期:《瑞京全县俱乐部大检阅》,《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6日,第4版。俱乐部工作通过竞赛和检阅得到了较大推动。
至1934年,俱乐部工作有了长足发展,毛泽东在1934年1月《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中提到中央苏区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员49668人,而这仅是中央苏区一部分的统计,从数字上可以反映出俱乐部工作发展很快,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农村中俱乐部活动,是在广泛的发展着。*毛泽东:《苏维埃的文化教育——节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6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80页。
另外,俱乐部还积极参加中央苏区的各项社会运动。俱乐部经常配合生产、支前、扩红等运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江西苏区文学史》,《江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第55页。如苏区进行的查田运动,教育部即要求各地俱乐部组织化装宣传队、标语口号队、唱歌队,并在晚上表演新剧、活报等,来进行查田运动的宣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四号——文化教育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1933年7月7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3页。俱乐部亦通过出版墙报开展反逃兵斗争,《青年实话》第三卷18号记载了长汀濯田等区俱乐部在各村出版反映本村反逃兵斗争运动情况的墙报,以红板光荣和黑板可耻来进行宣传,效果明显。俱乐部的各种活动,推动了苏区查田等运动的开展,推动了苏区社会迅速革命化。
中央和各地还建立各种群众俱乐部。以儿童俱乐部为例,1932年,《湘赣苏区儿童团工作决议案》即明确提出儿童团应参加俱乐部,通过打锣鼓、演新剧、集合唱革命歌曲、呼口号等方式丰富日常文化娱乐生活。*《湘赣苏区儿童团工作决议案》(1932年1月),《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第6册,第49页。儿童俱乐部在1933年“四一”儿童节大检阅后不断涌现,成为苏区儿童的基本活动场所。*吴邦初:《红色区域红孩子成长的催化剂——苏区儿童文化艺术活动史料》,《江西文艺史料》第5辑,江西文艺印刷厂1989年版,第75页。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也发出了建立俱乐部以加紧少先队员文化教育工作的训令。1933年6月,中央教育部在编订《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时亦强调了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提出组织儿童俱乐部委员会,设立游艺、墙报、运动、集会、社会工作五个部门,主要进行游艺、歌舞、活报、故事等的表演及组织会议、演说、讨论、读报等类的集会,并进行墙报工作、参与卫生运动等各种社会工作。*中央教育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17页。1933年9月24日,陈丕显在湘赣闽粤四省县以上儿童局书记联席会议上强调建立与健全儿童俱乐部,提出一方面要组织娱乐团,开晚会,以增强娱乐;另一方面,也强调开展卫生工作等各种社会活动。*《目前苏区共产儿童团的工作》(1933年9月),《陈丕显文选》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1934年9月,中央教育部还制定了《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儿童俱乐部以列小为单位组织,强调其性质为“儿童的一个社会工作与娱乐的练习所”,要求全体列小儿童要参加,校外儿童亦可参加,设管理委员会,下辖墙报组、游艺组、讲演组、读报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1934年9月28日),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第45页。儿童俱乐部队的设立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儿童革命工作的开展。中央苏区还建立了其它各种群众俱乐部,有力地将苏区妇女、青年、儿童等群体纳入革命轨道,宣传了革命,引导群众加入革命,推动了苏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了长征,原中央苏区所在地部分俱乐部坚持发展,为之后的游击战贡献了力量。
四、结语
俱乐部是战时社会文化教育的重要组织形态,在中央苏区建立前,在红军与部分革命根据地中已有初步的实践。中央苏区建立后,工农群众政治经济地位逐渐改善,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群众日益感觉到社会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需求。在此背景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进行了广泛地建立俱乐部的运动,尤其是在1933年6月后,在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俱乐部的法规,使得中央苏区俱乐部运动不断规范化。中央苏区时期的俱乐部工作提高了群众的文化和政治水平,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配合了扩红运动,动员了群众加入红军,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战斗情绪,为革命战争尤其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俱乐部又是重要的群众组织,在中央苏区俱乐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其管理委员会,不断融入甚至主导各群众运动,丰富了群众的生活,由初期强调娱乐逐渐转向革命文化生活,并在革命大众化的同时使得群众不断革命化,成为了党教育人民群众的“大课堂”*祝也安:《闽浙赣苏区的农村俱乐部》,《江西文艺史料》第13辑,第85页。。俱乐部的工作在党的群众路线指导下从团结群众、鼓动群众、教育群众入手,容易受到群众欢迎,收到显著成效。随着中央苏区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群众参加俱乐部组织与工作也不断深入,群众俱乐部数量大大增加,俱乐部工作人员,尤其是群众担任俱乐部工作人员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体现出俱乐部不仅是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教育群众的组织,同时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组织。正如荣孟源所提,“在革命根据地中,俱乐部是普遍的劳动人民的文化娱乐场所、教育机关”*荣孟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第6册,第112页。。因此,俱乐部组织的建立健全与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也从侧面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入实践。
当然,由中央苏区俱乐部组织的发展也反映出其在前期出现了组织发展形式化(“挂招牌”)、组织功能单一(偏重娱乐)、忽视对社会文化教育组织领导、组织发展难以深入基层等局限,这些教训实为苏区社会文化教育组织发展的通病。俱乐部后期的蓬勃发展又反映出党有能力在群众路线指导下推动社会文化教育及其组织的发展,使其成为群众教育的坚强阵地,充分体现了党的社会文化教育政策的灵活性与有效性。由此可见,中央苏区社会文化教育的组织建设的相关经验,能够为当今社会所注意甚至加以借鉴。
责任编辑:魏烈刚
·书 讯·
《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49元
本书系2016年度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对井冈山精神的研究,强化对井冈山精神的宣传,努力使江西在弘扬井冈山精神方面走在前列的一部力作。该书分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四章,每章四节,在进一步深化对井冈山精神内涵研究的基础上,紧抓历史发展与精神孕育的内在联系,紧扣时代发展与精神传承的突出主题,紧把不忘初心与继续前进的逻辑关系,从理论研究到现实推进,从光辉历史到光明前景,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的鲜明特质,阐明了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的不竭源泉。
The Mass Education Position : A Study on the Club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Qiu Quan
The club w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in the Party's mass work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the club work became one of the centers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work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especial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club evolved gradually from the entertainment-oriented mass organizations into the institutionalized and standardized social cultural education institution for the masses. The club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strengthened its contact to other mass organizations. Thus the club eventually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ass education position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club;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soci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邱泉,男,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讲师。(江西赣州 341000)
江西省教育科学重点课题“抗战时期江西社会教育发展研究”(15ZD3L044);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音乐运动与社会改造——以20世纪30年代江西为例”(YG2014028)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