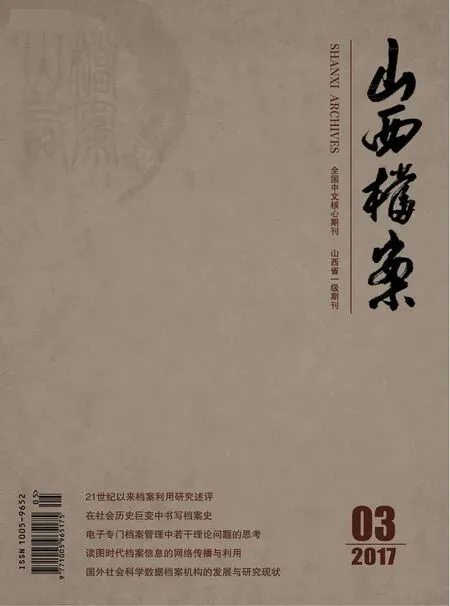元代汉文诗歌中的蒙古语及其成因
2017-01-28赵延花
文 / 赵延花
元代汉文诗歌中的蒙古语及其成因
文 / 赵延花
元朝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汉文创作中大量蒙古语的融入。汉文诗歌作为元朝的雅文学,在诗题、诗序、诗句还有诗人的自注中,都融入了较多的蒙古语。元代诗歌这种时代文化特色的形成,既与元代蒙汉人民的杂居、交融以及抒写的题材内容有关,更与元朝推行的“国语”教育制度联系密切。
元代;汉文诗歌;蒙古语;国语教育
元朝作为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汉文创作中大量蒙古语的融入。这既是民族和谐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对此做了研究。方龄贵的《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是其中较为典型的著作。除了元代戏曲等俗文学,汉文诗歌作为当时的雅文学,在诗题、诗序、诗句还有诗人的自注中,也融入了较多的蒙古语。
一、融入元代汉语诗歌中的蒙古语
元宪宗六年(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北面,桓州以东、滦河(今称闪电河)以北建新城,命名为开平府(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府建元登基,九年迁都大都,开平府改称上都。基于两都制和草原四时“纳钵”的传统习俗,忽必烈确立了两都巡幸制度。每年春、夏季元朝皇帝都率领重要大臣来上都巡幸避暑和处理政务,众多中原甚至江南诗人或扈从结伴来到蒙古族世代蕃息的草原地区,创作多融入蒙古语的反映蒙古族民俗的诗歌。
元诗中写到的衣着,以“质孙服”最具时代特色。质孙,是蒙古语的音译,也作“只孙”、“济逊”等。张昱的《辇下曲》第十四首:“只孙官样青红锦,裹肚圆文宝相珠。羽仗持金班控鹤,千人鱼贯振嵩呼。”[1]345诗中描写参加皇家宴会的官员穿着皇帝所赐的只孙服,官服以青色、红色的锦缎为材料。周伯琦有《诈马行并序》诗,诗序中说:“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只孙’华言一色衣也。”[1]345穿“质孙服”参加的宫廷宴会,称为“诈马宴”。
蒙古族妇女头上戴“固姑冠”。“香车七宝固姑袍,旋摘修翎付女曹。”(杨允孚《滦京杂咏》其五十五)[2]405“固姑”译自蒙古语,有不同的写法,如姑姑、固姑、顾姑、故故、罟罟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3]32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戴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4]63因为冠饰太高,所以坐车时要摘下来。杨允孚在诗后有自注:“凡车中戴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许,拔付女侍手持,对坐车中。虽后妃驭象亦然。”
关于蒙古族饮食,杨允孚写到:“毡房纳石茶添火,有女寨裳拾粪归。”诗后自注:“纳石,鞑靼茶。”[2]408考之蒙古族饮食习惯,诗中的纳石茶就是今天蒙古族人民依然喜爱的奶茶。
蒙古国时期,蒙古大汗和后妃也是住在穹庐中,但他们的穹庐规模比较大,称为“宫帐”或“行宫”。蒙古语称之为“斡耳朵”“斡里朵”“兀鲁朵”等,成吉思汗时建立了四大斡耳朵。对此,葛逻禄诗人迺贤有诗《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柳贯也有诗《观失剌翰耳朵御宴回》,诗中自注:“车架驻跸,即赐近臣洒马奶子,御筵设毡殿失剌翰耳朵,深广可容数千人。”[5]166斡耳朵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固定不动的,一般规模都比较大;另一种是规模小、可以移动的。杨允孚《滦京杂咏》第二十九首:“先帝妃嫔火失房,前期承旨达滦阳。车如流水毛牛捷,韂缕黄金白马良。”自注说:“火失毡房,乃累朝后妃之宫车也。”[2]404李治安在《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一文中说:蒙古大汗有保留生前斡耳朵的制度,后代君主通过祭祀这些斡耳朵来祭祀祖先。忽必烈在大都皇城东华门内设置了此类斡耳朵,称为“火室房子”。[6]162
除了衣食住行外,元代诗人还写到了蒙古族的体育竞技活动。张昱《辇下曲》其五十一云:“放教贵赤一齐行,平地风生有翅身。未解刻期争拜下,御前成个赏金银。”[1]51杨允孚《滦京杂咏》其三十四云:“宫中又放滦河走,相国家奴第一筹。”自注说:“滦河至上京二百里,走者名贵赤。黎明放自滦河,至御前已初中刻者上赏。”[2]404“贵赤”是蒙古语,也称为“贵由赤”,意思是“跑步者”,说明元朝廷举行的是长跑活动。
蒙古族统治者很重视民族教育,成吉思汗时就请塔塔统阿教授其子弟文化知识。元世祖建立了系统的民族教育体制,延请汉族硕儒对蒙古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蒙古族诗人在元代第一次登上了汉语诗坛,并与当时著名汉族诗人唱和。所以元代诗歌中多有蒙古族诗人的名字,如“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虞集就有《别燮元溥后重寄》《闻燮元溥除御史》《燮元溥除御史后寄萧性渊巡检》等诗。燮元溥,本名燮理普化,字元溥,是蒙古斡剌纳儿氏,泰定四年进士及第,《全元诗》存其汉语诗歌两首。蒙古族诗人萨都剌也是泰定四年进士,是目前蒙古族诗人中存留诗歌最多的。他有794首诗被收入《全元诗》,他与当时诗人多有酬唱。虞集诗中就有《寄丁卯进士萨都剌天锡》《与萨都剌进士》等诗歌。泰不华也是著名的蒙古族诗人,字兼善,原名达普化,是元英宗至治元年的状元。元代有十几位诗人留下了与之唱和的诗歌,如李孝光《寄达兼善》、傅若金《奉送达兼善御史赴河南宪佥十二韵》、朱德润《送达兼善元帅赴浙东》、虞集《为达兼善御史题墨竹》等。
元代汉语诗歌中还有一些蒙古族官员的名字,如虞集的《题朵儿只平章紫薇亭》,诗题中的朵儿只是木华黎六世孙,脱脱之子。周伯琦的《赋得莲花漏送宗正朵尔直班公惟中赴淮东监宪任》,其中的朵尔直班是木华黎七世孙,还有周伯琦《送经历伯颜忽都元卿佥宪河南》中的伯颜忽都等等。
柳贯有《八月二日大驾北巡将校猎于散不剌诏免汉官扈从南旋有期喜而成咏》诗,诗题中的“散不剌”也称为“三不剌”“甘不剌”等,是蒙古语“好泉子”的意思,也称北凉亭,在上都西北 700里外。王恽有《甘不剌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侯承旨扈从北回遇于榆林酒间因及今秋大狝之盛书六绝以纪其事》,诗题中说明了散不剌川与上都的距离。柳贯还有诗题为《午日雪后行失八儿秃道中有怀同馆诸公》,“失八儿秃”是蒙古语,意为泥淖之地,汉名为牛群头。周伯琦《怀秃脑儿作》诗题后自注:“汉言后海也。”[7]342杨允孚《滦京杂咏》第二十五首:“鸳鸯坡上是行宫,又喜临歧象驭通。芳草撩人香扑面,白翎随马叫晴空。”诗后自注:“由黑围至此,始合辙焉,即察罕脑儿。”[2]404周伯琦在《纪行诗》第十七首后自注说:“右察罕脑儿。犹汉言白海。”[7]391
二、元代汉语诗歌中融入蒙古语的原因
元代汉语诗歌中之所以会出现蒙古语,是因为元代统一南北后,蒙古族军人及其家属、蒙古族部众大量进入汉族聚居地区,形成了蒙汉人民杂居的局面。为了交流,汉族人民开始学习蒙古语言文字。元代的杂剧是俗文学,是当时庶民百姓最喜欢的艺术形式。据方龄贵教授统计,现存元明戏曲剧目中就含有200多个蒙古语词汇,[9]这说明一般民众对于蒙古语的日常会话语言都耳熟能详。一些蒙古族语言已经渗入到汉语语言之中,比如“胡同”一词就是来自蒙古语。
在表现民俗的诗歌中融入蒙古语,是因为上都地区是蒙古族聚居区,牧民都使用蒙古语进行交流。周伯琦《纪行诗》第十四首说上都地区 “土风多国语,闾井异寻常”[7]391。杨允孚《滦京杂咏》第二十二首也说:“弧矢纵悬扔觅侣,塞前番语笑人迂。”[2]404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元代诗人才会有意识地采撷、提炼、征用蒙古语进行叙事抒情。
元代汉语诗歌中出现蒙古语,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元廷推行的“国语”教育。蒙古族统治者接受了中原儒家思想,在全国建立了儒学教育体制。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建立蒙古国子学,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蒙古字。元廷规定,官方文书使用蒙古语、汉语和波斯语三种文字。最早使用的蒙古语是成吉思汗时创制的畏吾尔蒙古字。之后,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以吐蕃字为基础创制了八思巴蒙古字。张昱《辇下曲》第六十二首:“八思巴师释之雄,字出天人惭妙工。龙沙仿佛鬼夜哭,蒙古尽归文法中。”[1]52诗中所咏的就是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张昱也对蒙古新字创制的意义进行了阐发。忽必烈期望可以用蒙古新字统一全国文字,至元八年(1271)下诏成立蒙古国子学、地方蒙古字学,在皇后斡耳朵、诸王投下及各侍卫军中也都设有蒙古字学,使用的教材是用八思巴字译成蒙古语的《通鉴节要》。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又出版了《蒙古字韵》《百家姓蒙古文》《蒙古韵编》等字学课本。
蒙古族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却不学习汉文儒家典籍,而是将这些典籍翻译为蒙古语,供蒙汉学子、大臣学习。至元十九年(1282),元政府印行了蒙古畏兀儿字的《通鉴》。元武宗即位后,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非常喜爱汉文化,至大四年(1311年)“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节而译之……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10]544。这说明在当时翻译、出版了三部儒家经典,现在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此时刊印的蒙汉语对照的《孝经》残本。《元史》在同一年还记载,爱育黎拔力八达读《贞观政要》,诏谕蒙古族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10]571
在元代,学习蒙古语还成为很多士人改变自身命运和步入仕途的捷径,是“当今所尚,莫贵于此”的时尚,[10]1就连原南宋统治的地区,汉族文人“愿充虏吏,皆习蒙古书,南人率学其字”[11]188。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元代文人大多精通蒙汉双语,甚至有汉族文人做蒙古字学教授。江南宣城人贡奎(1269—1329)有诗《送蒙古字周教授》,提到这位教授的蒙古文水平:“谐音正译妙简绝,穷究根本芟繁柯。牙签玉轴点画整,照耀后世推名科。”诗人对这位朋友充满敬意:“愧予鄙俚事章句,儒冠多误将如何。”[12]128可见,一些有文化素养的汉族文人,蒙古语水平很高,可以作为老师教授别人;在元代的学校教育中,蒙古语、蒙古字是必修课;蒙古字学教授的地位比一般的汉语教授要高,受到人们的羡慕;通过学校教育走上仕途的官员,蒙古语、蒙古字学的水平都不低,在交流、书写上可以使用蒙汉双语。
三、结语
通过对元代汉语诗歌的分析,我们发现,蒙古族的语言成为了诗歌语言的组成部分,增强了元代诗歌的民族文化交融特色。这证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具有多元共融的特征。作为政治文学、庙堂文学的元代诗歌的这种时代文化特色的形成,既与元代蒙汉人民的杂居、交融以及抒写的题材内容有关,又与元王朝推行的“国语”教育制度联系密切。
[1]杨镰.全元诗:第4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杨镰.全元诗:第60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4]叶子奇.草木子[M].北京:华书局,1959.
[5]杨镰.全元诗:第25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李治安.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J].史学集刊,2009,(3).
[7]杨镰.全元诗:第40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
[9]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贾敬颜,朱风.蒙古译语 女真译语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11]郑思肖.郑思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杨镰.全元诗:第2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
I207.22
A
1005-9652(2017)03-0177-0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6ZDA17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虞志坚)
赵延花(1975-),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