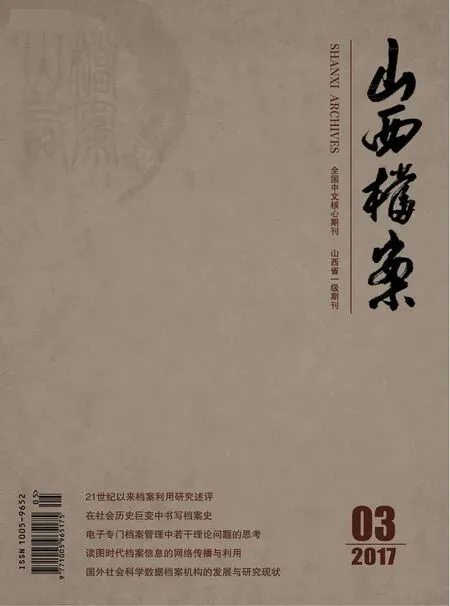梁启超何以对朱舜水关注最晚而评价最高
2017-01-28杜品
文 / 杜品
梁启超何以对朱舜水关注最晚而评价最高
文 / 杜品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通过一系列文章对朱舜水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介绍,与近代其他旅日知识分子相比,梁启超对朱舜水的关注在时间上可谓“最晚”;梁启超从启蒙思想、实学思想两个方面对朱舜水的学术思想与日本水户学、宋明理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基于学理研究基础之上的舜水评价,在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上又可谓“最高”。
梁启超;朱舜水;评价
在明清鼎革之际陆续发生的中国人赴日乞师活动中,朱舜水的乞师行为极富文化上的影响力。近代,在急于效仿日本实现变法维新的舆论背景下,旅日士人将朱舜水的思想及事迹带入到国人视野之中。19世纪末黄遵宪最早对朱舜水的民族气节和乞师行为加以褒扬。孙中山在革命宣传中也时常引用朱舜水的言论,对其反满气节有所钟情。相比之下,梁启超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对朱舜水的事迹及其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与着力的宣扬。梁启超肯定了朱舜水的实理实学思想对日本的近代化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高度赞扬了朱舜水的人格精神,就其研究的全面性以及影响力而言,当居近代中国朱舜水研究中的首位。
一、梁启超对朱舜水的态度变化与原因分析
梁启超与朱舜水同样有着流亡日本的现实行动与欲乞师日本的思想情结。然而这种境遇上的相似性在很长的时间段内并未成为拉近二者的纽带。从思想脉络上看,二者也有相关联之处。李甦平认为,在清代至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存在一个由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梁启超构成的思想系谱,其思想脉络与朱舜水的经学思想同出一辙。因此,“朱舜水的经学思想实为常州学派之滥觞,常州学派的思想渊源应导源于朱舜水”[1]256。这一说法表明,舜水之学与常州学派思想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历史境遇相似,思想脉络关联的朱舜水,为何在梁启超的著述中全无踪影?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早年的梁启超在思想及行动上追随康有为,倡导尊君立宪,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之中。明代遗民朱舜水虽然倡导尊君、大义,但其强烈的排满意志却与当时的维新变法宣传实在难以融合,因而无法进入到梁启超的视野之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思想发生了变化。1899年宋恕在致梁启超的信函中写道:“朱舜水、张忠烈非不能为李光地,姚启圣也,情不能已也。”[2]605宋恕的忠告所指向的正是此时梁启超明显向革命靠近的“变节”思想动向。梁启超与革命派虽然有密切的往来,但在国家的建设目标、实践方法上都大相径庭。革命派将反满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对朱舜水的反满情绪大加利用,而梁启超则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学说,强调大民族主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3]1070,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建国。如此,朱舜水强烈的反满情绪在梁启超处自然可有可无,甚至需要加以适当的回避。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到国内,辗转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思想道德,寄希望于社会、于学术。一战后的欧洲游历使他目睹了西方近代文明造成的无限贪欲的后果,“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3]2974。重新回向传统、回向儒学成为梁启超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方向。基于此,梁启超通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再诠释。也正是在新的诠释过程中,梁启超发现了舜水之学的价值与朱舜水的人格魅力。舜水之学奠基于传统,散播于海外,立言于经世致用、实学实理。朱舜水以个人之人格精神,成就明治维新之千古事功,恰恰为儒家内圣而外王的最好范例。辛亥革命的胜利也使朱舜水的“反满”情结不再构成宣传的障碍,因此,此时的梁启超对朱舜水的接纳与赞诵便在情理之中了。
从1923年至1927年的五年之中,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与朱舜水有关的文章。1923年,梁启超发表《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朱舜水先生年谱》,全面介绍了朱舜水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1924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1925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7年发表的《儒家哲学》,介绍、宣传了朱舜水的生平事迹,对舜水之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梁启超认为,虽然舜水之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影响,却在异域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东亚最为耀眼的文明成果——明治维新的思想源头。通过密集的介绍与宣传,梁启超为国人塑造了一个完整、生动的舜水形象,并使这一形象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对此,有学者评价道,“就梁启超对朱舜水研究和评价的完整性、客观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性而言,说梁启超是‘第一位’未尝不可”[4]88。梁启超不仅将朱舜水作为政治宣传的对象,而且开始尝试深入到朱舜水思想的深处并探讨朱舜水的价值所在。
二、梁启超对朱舜水启蒙思想与实学思想的肯定
(一)对朱舜水启蒙思想的肯定
梁启超认定朱舜水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奠基者,“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动力实在舜水,……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3]4470。文中将朱舜水与明治维新紧密连接在一起,认为水户学是明治维新的思想来源,其注重大义名分与经世致用的学术偏向来自于朱舜水的思想注入。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是梁启超的首创。朱舜水与水户学及明治维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在1908年王三让的《游东日记》里已然有所表现,“水户藩部自古推崇汉学,其文明由贵国先儒朱舜水输入,教育极盛”[5]393。结合《朱舜水先生年谱》来看,梁启超强调的重点在于:将朱舜水与明治维新的关系定位在了朱舜水作为儒学思想传播者、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者之上。明治维新的思想动力来自水户学、来自朱舜水,却并非朱舜水之独创,从根本上讲是来自儒家的政治理念与经世思想。因此,朱舜水对明治维新的价值在于,他充当了启蒙思想家的角色。由此梁启超的观点与近代日本的朱舜水研究在方向上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关注自早年便已生发。对于梁启超本人而言,明治维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成功学习西方走上富强之路的榜样。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的生活使其感受到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即所谓“大和魂”、“武士道”,并进一步认定这种民族精神是日本实现明治维新大业的根源与动力。此时的梁启超开始探索如何树立起“中国魂”、“中国之武士道”,以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通过朱舜水,梁启超获得了依靠传统儒学思想来实现思想启蒙的灵感。儒学思想中不仅有永恒的道德价值,而且具有可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政治价值,明治维新的成功归根到底是儒家思想的产物。梁启超将朱舜水对于明治维新之意义定位在传播儒学、思想启蒙的功绩上,其用意正在于此。
(二)对朱舜水实学思想的肯定
在肯定了朱舜水的启蒙思想之后,梁启超进一步对舜水之学的思想脉络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朱舜水在学术思想脉络上归属于程朱学派,同时又超越了朱子学与王学的门户界限,是二者的综合与提升;舜水之学注重实践、排斥玄谈,是明末王学的反动。
梁启超认为朱舜水为德川日本带去了儒学,具体而言则是朱子学。“尊崇程朱,传其学于海外,当推朱之瑜”,“舜水是程朱学派健将,自他去后,朱学大昌”[3]4985。朱舜水虽为程朱学派,但“他论学问,以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3]4471。梁启超认为,朱舜水的朱子学实际上已经跳出“性命之学”的窠臼,秉承了浙东学派重道德与事功统一、讲究经世致用的思想要旨。从朱舜水本人的思想理路来看,舜水之学确实非朱子学也非王学:“朱舜水所汲取的,是两家学说中,后来几乎均被偏废了的‘格物致知’精神和‘事上磨炼’价值,而不是‘理在事先’、‘心外无物’的禅机玄理。”[6]90对程朱理学,朱舜水曾经给予过尖锐的批评:“宋儒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7]160朱舜水否定了朱子学中因其“习气”所造成的理论与实际的脱离,以及“宏大叙事”的高远务虚之学风。在《朱舜水先生年谱》中,梁启超引用了朱舜水本人的话:“圣贤践履之学,中国已在季世,宜乎贵国之示闻之也。”认为这是“先生讲学发轫”[3]4774。梁启超敏锐地抓住了舜水之学的这一实学倾向,在《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大量记述了朱舜水在日本讲学及生活的各种实行、实事,并强调“舜水不独为日本精神文明界之大恩人,即物质方面,所给他们的益处也不少了”[3]4471。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强调无论朱子学还是王学都有一共同特点,“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3]4429,并认为这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孔子之教的传统,“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人格”[3]4434。梁启超认为,明末的王学反动实际上也是向孔子之教的回归,“他们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3]4434。在确定朱舜水对明治维新具有思想启蒙价值的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认定:朱舜水注重格物致知、事上磨练的实学思想才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动力与根源。
三、梁启超对朱舜水人格精神的评价
梁启超的朱舜水评价建构在冷静的学理分析基础之上,从而使朱舜水摆脱了革命派塑造的狭隘、单一的“排满”形象。朱舜水的人格魅力是梁启超最为关注与钦佩之处,也是他对朱舜水的介绍与宣传中最富情感色彩之处。在近代中国各派知识分子的朱舜水印象中,由于立场不同,对其精神价值宣传的重点也有所不同。黄遵宪对朱舜水誓不降清的气节给予了极高的赞扬,“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8]688。他看中的是朱舜水的尊王、忠君思想,故有伯夷叔齐之喻。革命派则侧重宣传朱舜水的反满精神,看重他的遗民身份及乞师义举。朱舜水在《中原阳九述略》中阐发的虏害思想更是革命派借以发挥的不二文本。梁启超肯定了革命派的朱舜水宣传所发挥的巨大影响,“这类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十年的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3]4471。但从梁启超的文章中来看,最令梁启超所感动的朱舜水精神,不在其反满、乞师等举动上,也不在尊王、忠君思想上,而在于朱舜水的人格精神。梁启超不止一次地对朱舜水的人格精神进行赞扬,认为朱舜水具有“最健全之人格”,“他是个德行纯粹而意志坚强的人,常常报整个人格毫无掩饰的表现出来与人共见”[3]4470。在《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对乞题“明征君朱舜水之墓”问题,梁启超作如下案语:“此事在先生生涯中,如飓风一度来袭,瞥然而逝,然先生方正强毅镇静温厚诸美德,皆一一表现,实全人格之一象征也。”[3]4473
梁启超对朱舜水的集中宣传与竭力赞扬,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的朱舜水研究热情。在《朱舜水先生年谱》中,梁启超还以独特的“谱后”方式将年谱延伸到了朱舜水逝世之后百余年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以表现出历史是如何“尝了他的志愿”,使他的朱舜水研究更全面更完整。梁启超对朱舜水的宣传与评价在近代中国的朱舜水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为舜水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样式与方向。
[1]李甦平.朱之瑜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宋恕.宋恕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钱明.清末民初的朱舜水热[J].浙江学刊,1996,(5).
[5]王宝平.日本政法考察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韩东育.谒余姚[J].读书,2010,(12).
[7]朱舜水.朱舜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钟叔河.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M].长沙:岳麓书社,2008.
B259.1;K248.405
A
1005-9652(2017)03-0174-0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韩开港与城市社会变迁”(项目编号:12BSS01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虞志坚)
杜品(1981-),女,黑龙江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