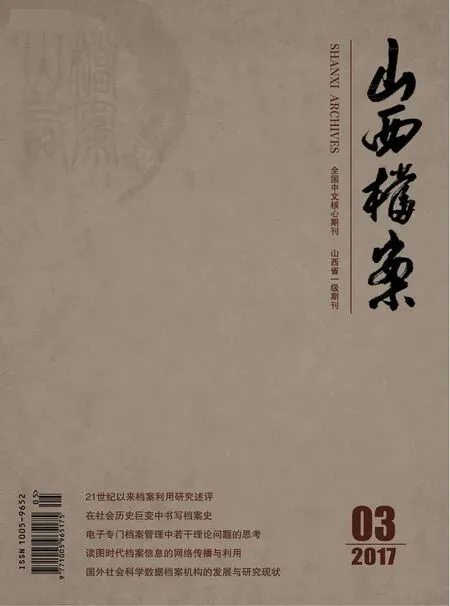理雅各《中国经典》对乾嘉汉学思想的弘扬
2017-01-28朱添
文 / 朱添
理雅各《中国经典》对乾嘉汉学思想的弘扬
文 / 朱添
19世纪英籍赴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在传教布道之余完成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英文翻译,其译作《中国经典》讲训诂、重实证,集中体现了他求真笃实的治学特点,也体现了乾嘉汉学的治学思想对其译经的影响。
理雅各;《中国经典》;乾嘉学术;考据学
清代乾嘉时期,以吴中惠栋、安徽戴震为代表的朴学大师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的通经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发扬汉儒传统,将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之学发展到了顶峰,形成了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乾嘉学派。与此同时,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宣教,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乾嘉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影响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理雅各的译作《中国经典》就是受影响较大的一部。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9世纪英籍赴华新教传教士,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他在传教布道之余完成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英文翻译,成为了第一个完整地将儒家经典翻译成欧洲语言的西方学者。其译作《中国经典》讲训诂、重实证,集中体现了他求真笃实的治学特点,也体现了他在译经的过程中对乾嘉汉学思想的接受与弘扬。
一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系列译著是欧洲汉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地译介儒家经典的皇皇巨著。该丛书共五卷,刊印时间长达11年之久:第一卷1861年首版印刷,主体为《论语》《大学》《中庸》三书的译文及注释;第二卷1862年出版,主体为《孟子》译文及注释;第三卷1863年着手印制、1865年出版完毕,主体为《尚书》译文及注释;第四卷1871年出版,主体为《诗经》译文及注释;第五卷年1872年出版,主体为《春秋》及《春秋左氏传》译文及注释。1893年,已近耄耋之龄的理雅各完成了对《中国经典》第一卷的修订工作,修订本对专有名词的翻译及汉字注音等方面改动很大,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付梓印刷。《中国经典》扎实厚重、学术规范,被西方汉学界奉为“四书”“五经”的标准译本、儒家经典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贡献”[1]。
理雅各赴华前在希格伯利神学院(Highbury Theological College)接受过系统的《圣经》诠释学训练,将地理学、考古学、年代学、语言学等近代科学知识融入宗教经典研究,追寻《圣经》的原旨,为他读经释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当理雅各译介儒家经典时,以训诂和考据为特色的乾嘉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更易为其接受。《中国经典》每卷均在前言中详细介绍理雅各在译注当中所参考的书目,仅译注《尚书》所参阅的25种文献中,除孔国安作传、孔颖达注疏的《尚书正义》和《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两部诠释本外,有9部文字训诂类的工具书。在余下的14部《尚书》研究著作中,清代汉学家的著作就占了9部,其中既有清代汉学发轫之初代表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尚书广听录》《舜典补亡》,也有乾嘉汉学大家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等,理雅各译经受汉学影响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
注是指对古书字句的解释,疏是对注文的进一步解释,宋人将十三经之汉注唐疏合为一编,始有“注疏”合称,成为中国一种传统的注解经书的体例。注疏的内容主要包括阐释题旨、串讲大意、分析句读、字词训诂、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的引证等。清代乾嘉学者继承了汉唐经学家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古代的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地整理和总结,成果丰厚、影响深远。
理雅各在译注《中国经典》时便接受了这一体例。《中国经典》正文由中文原文、译文和脚注三部分组成,其脚注的内容包括题解、字词训诂、音韵说明、语句解读等,有时还会在后面加入案语表达自己的观点。
以《中国经典》第一卷《论语·学而第一》为例,因《学而》是《论语》的首篇,理雅各在该篇注释首先阐述《论语》题旨,题解中指出《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讨论与对话,非孔子本人所做,而是由弟子在孔子逝后集成,整理为20篇;据《论语注疏解经序》,“论语”二字当为“对话摘编”之意,故理雅各译《论语》为‘Confucian Analcts’。继而,对《学而第一》一题进行解读,指出“学而”取自开篇“子曰”后的前两个字,该命题法与犹太教《旧约》大多篇章的命名相似;“第一”则是因整部《论语》包括20篇,该篇是全书第一篇。每篇下有若干章节,通常主题一致或相似的章节会被《论语》的整理者放在一起,构成一篇,也有些篇目没有遵循这一整理原则。《学而第一》篇由16章构成,包括吸引学习者注意及参与实践等基本话题。进而,理雅各表示对一个民族长久以来的、引以为傲的、杰出的教育体系进行研究,“学”无疑占据首位。题解之后,理雅各概括该篇第一章的内容,以疏通文意:“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指学习者的全部工作与成就,首先是完善自己的知识,然后以自己的名声吸引志同道合的人,最终实现自我的完整。总括文意后,理雅各随文而释,对章节中的语词逐一训解。包括语词的本义、文中的引申义、不同注疏家对语词义项的解读、文中的读音或通假情况等。
可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的体例与我国自汉以来传统经学研究著述中的注疏体极为相似,与乾嘉学派的治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
乾嘉学者治学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而是讲求实据,在广泛收集并归纳客观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中国经典》也体现出这样的治学特点。为使译文“忠实于原文”,理雅各坚持直译,因此,许多涉及生词僻字、文化典故、修辞用法的语句,不得不用大量的脚注加以解释,这些注释的篇幅甚至超过了译文本身。详尽而准确的注释展现了理雅各的考据学功底,也使他的译本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
(一)重视通过文字、音韵解释古书的内容
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三卷序言)中提到他在研究中国经典时迫切需要一部“真正好的字典”。所谓“真正好的字典”并非马礼逊等编纂的只关注汉字常用义项和交际功能的实用性字典,而是一种既“能够对汉语中的每个字都作出满意的历史分析,从造字之初最原始的本义一步一步推演出各种不同的义项”,又能够准确地展现汉字的本义及发展源流的字典。可见他在译经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从文字学角度对经典中的字词进行阐释,如“哀公问社于宰我”(《论语·八佾》)之“社”字,理雅各注“社”从“示”从“土”,“示”即“大地的主神”(spirit or spirits of the earth),“土”即“土壤”(the soil),故而“社”就是“土地神主”。又如“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之“坫”字,注为从“土”从“占”,意为“由土或泥炭做成的平台”。
理雅各训解汉字时会兼用形训与声训,如“子张问十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一句的脚注中,理雅各以形说“世”。首先,他指出“世”既可解作“一个时代”“一个世纪”,也可解作“一代”“三十年”。而“三十年”之意源于“世”的部首,即“卅”和“一”。又如,在“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一句的注释中,则以声说“献”。“献”即“贤”,意为“智者”。理雅各的这种从文字、音韵入手训解古书的方法与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是一致的。
(二)重视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的考证
乾嘉时期,考据学家尊经崇汉,主张以专事训诂名物、以典章考圣贤之言。《中国经典》的注释中也包含了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考证。
以《诗经》翻译为例,理雅各1871年译本的《前言》提到,《诗经》翻译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处理书中大量的植物、鸟、兽、鱼、虫的名称。理雅各为了能够准确无误地翻译诗经中出现的名物,充分查阅了中国历代考据学家所撰的《诗经》名物考,甚至还参考了日本学者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除了查阅大量书籍,理雅各还不断地就名物问题向中外学者讨教确认,他曾将《毛诗名物图说》寄给日本专家与英国植物学家求教,考证出其中的159种动物与139种植物,力求将《诗经》中的名物诠释得准确无误。
理雅各在译经中还会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加以说明,如《中庸》第十九章“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句,将该句直译为“In spring and autumn, they repaired and beautified the temple-halls of their fathers, set forth their ancestral vessels, displayed their various robes, and presented the offerings of the several seasons”。为帮助读者理解古代中国的祭礼,理雅各在注释中对“春秋”“祖庙”“宗器”“裳衣”分别加以解释:“春秋”指中国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时节。从春天算起,祭祀的名称有“祠”、“禴”或“礿”、“尝”及“烝”。而另一种说法将春季的祭祀称作“禘”,四季祭祀之名分别为“礿”“禘”“尝”“烝”。理雅各表示虽然文中只提到了春秋两季,但是读者对古代中国四个季节的祭祀活动都要有所了解;“祖庙”是祭祀祖先的厅堂或神殿,帝王设七庙,均属于“宗庙”。接着,理雅各在注“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时,详细地解释了三昭三穆的设置与功能;“宗器”是祖宗传下的或庄严珍贵的器物;“裳衣”,即含下衣“裳”与上衣“衣”的一套服装,为逝者遗留下来的装饰蔽体的衣物。
四
理雅各治学严谨踏实,主要表现在其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直译。理雅各在不同卷本的序言中屡次提及其“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原则,认为根据原文大意而作的解释性翻译是一种敷衍的、违背学术规范的做法。也正因“忠实于原文”,理雅各译文曾被学界诟病文辞质朴、文风拘古,学者化的表达方式削弱了译文的可读性。理雅各也曾考虑在再版《中国经典》时采取“更简洁明快,更富有修辞技巧的方法”对译文进行文学处理,然而,最终他还是决定保持一贯的直译风格,因为他“一直以忠实于中文原文作为其翻译的主要目标,而不是语言方面的优美华丽”。
《中国经典》一、二卷首版后,有西方学者致信理雅各,建议他译注中国经典时,可向精通满语的中国人求助,以便更接近中华帝国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但理雅各更为看重经典产生的时代及宋朝以前注疏家对经典的解读。在他看来,清帝国的官方意识与宋以前的官方意识大为不同,注解中国经典“即使在当今的朝代,很多最杰出的学者以及最高级的官员都果敢地提出并坚持不同于官方意识的解释”(《中国经典》第三卷序言)。
综上所述,《中国经典》是中国古代典籍向欧洲的第一次大规模译介,各卷的陆续出版在西方引起强烈的轰动,由于理雅各在翻译中“贯串考覆”、“讨流溯源”,使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被西方学界誉为中国传统经书的标准译本。《中国经典》不但“成为了近代西方人了解中华文化、认知儒学思想最重要的载体,也成为了西方人汉字启蒙与汉语学习的重要工具”[2],更是之后中国古籍翻译者和中国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理雅各译介《中国经典》的贡献并非仅仅在于中学西传,而是对中国“往圣之绝学”的继承与发扬。晚清思想家王韬将理雅各誉为“西国儒宗”,将其与乾嘉汉学大家阮元、陈奂并提,则是对理雅各汉学成就的充分肯定。
[1]William Edward Soothill.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Yokohama[M].Printed by the Fukuin Printing Co.,1910.
[2]陈树千.《四书》西行与汉语早期对欧传播[J].孔子研究,2016,(1).
H315.9;I046
A
1005-9652(2017)03-0141-03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武亿与乾嘉金石学”(项目编号:YJSCX2017-004HLJU)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虞志坚)
朱添(1985-),男,黑龙江桦南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籍整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