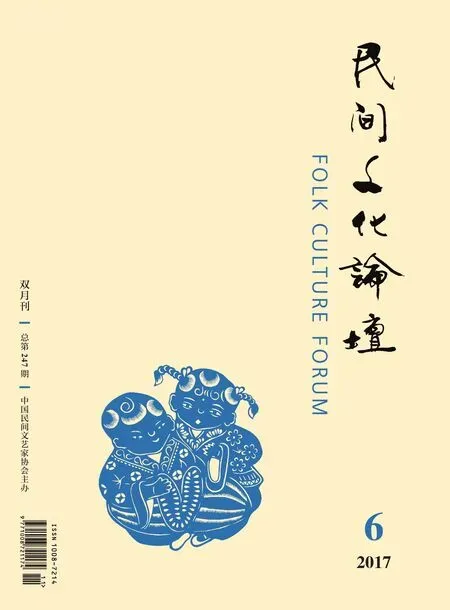“以学术为业”的“知与争”—读《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
2017-01-28叶隽
叶 隽
“以学术为业”的“知与争”—读《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
叶 隽
我很认同韦伯(Weber, Max, 1864-1920)的说法,既然选择“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就应当立定作为学者的坚定立场,他追问得很清楚:“以学术为业,在物质意义的层面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①"Wie gestaltet sich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m materiellen Sinne des Wortes?" Weber, Max: "Wissenschaft als Beruf"(以学术为业). In Weber, Max: Gesamtausgabe(全集). Abteilung I: Schriften und Reden.Band 17. Tübingen: J.C.B.Mohr, 1992. S.1.中译文可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其实就是窘迫困难,就是坎坷歧途,就是持守真知。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②[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7页。,说来容易,但学者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而学术作为一种以追索人类知识乃至真理的智性活动,就必须有真诚的讨论,有良性的互动,有激烈的思想风暴。人文与科学之争是一个经久不息的命题,而且有其历史。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是存在着长久的秘索思和逻格斯之争的,虽然日后以理性、科学为主的逻格斯传统占据了上风,但并非就是绝对定于一尊的;即便是在中国现代学术谱系里,我们也有过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其核心问题仍是围绕着方法论的问题。
195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语境随大时代背景而大变,那种立足于学术本身的真诚讨论和争论似乎越来越少,即便是1980年代以后亦然。这或许也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大家习惯了“温良恭俭让”的彬彬有礼,很不习惯类似西方“针尖对麦芒”的学术争论。21世纪以来,随着资本语境的逐渐生成,更是一味以功利为追逐对象,将更为本质的学术使命大多不知抛到了九霄云外的何处去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欣喜地看到,民俗学场域之中爆发了一场关乎真理问题根本的讨论,这在当下汲汲以“创新为业”的中国学界,可谓难得,是少有的关于“真问题”的讨论,而且因其参与者的多元而显得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象。当事者是这样记录的:
21世纪初,在一贯波澜不惊的民俗学圈内,也掀起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文的激烈论战。“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关于“田野是什么”的论战,无疑可以看作是“科玄论战”在民俗学界的未息余波,这次论战主要围绕着科学方法是否适用于人文研究的问题,论战从早年的科玄是否分家、科学是否万能的问题延伸到了人文学科的学术伦理与科学哲学的问题。这场主要局限于一批青年民俗学者的网络学术论战,其意义却并不限于民俗学科,它对于我们厘清现代民俗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路都具有积极意义。①施爱东整理:《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这个引子是有效的,因为其诙谐幽默的语言引导我们进入的却是一个重要的有真讨论的学术空间。但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看后记“一个技工与一群诗人的群殴”,这场“石榴之争”乃是民俗学界两位学者施爱东、刘宗迪的讨论,两者本科同一理工科专业,刘在南京大学大气物理专业,施在中山大学天气动力学专业;之后都获中文系文艺学硕士学位,做大学教师;再到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刘魁立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后出站之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后转山东大学。施爱东的立场清晰:“实验方法是近现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实验方法的优点在于,通过人为地干预、控制所研究的对象,能够在有意识地变革自然中,更好地屏蔽干扰,突出地把握自然的某一方面的特质。实验观察比自然观察更有利于发挥人的能动性,更有利于揭示隐藏的自然奥秘,它大大扩展了人类经验研究的可能性。”而刘宗迪则彻底否定之:“现代科学是工具和实用导向的,不具有像宗教那样先天的道德合理性,而把他人当成自己的实验对象和检验手段,尤其和民俗学这门学科的精神格格不入。”让我饶感惊奇和兴味的则是:“192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曾经爆发过一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我和宗迪之间的论争,应该算做近百年来‘科玄论战’的余绪,我站在科学派一边,宗迪站在玄学派一边。我原以为战斗一打响,支持科学派的同仁和支持玄学派的同仁大约能占到一半对一半,可是,我没料到围观群众都是纯文科出身的民俗学从业者,而不是随机抽样的知识分子,结果双方观点一亮相,大家呼啦一声,全站到宗迪一边去了。”②施爱东:《代后记:一个技工与一群诗人的群殴》,载施爱东整理:《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61页。科学式微,似乎是这段论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但为什么科学如此地受到民俗学界中人的轻视甚至还带有些“鄙弃”呢?
这样的一种基本论述和观点对峙,就使得这个讨论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而具有更为普遍的学术史价值。歌德的“诗与真”常常被拿来作为文学化的手段,但我认为在学术的世界里,更需要的是理解“知与争”。为什么呢?诚如韦伯在其名著中所言,既然选择了“以学术为业”,就应当承担起“学者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按照费希特的说法,那就是:“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到道德善良呢?”③《论学者的使命》,载[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6页。所以,我们应该理解自己作为知识人的定位,不能放弃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精英的职责与使命,克劳塞维茨曾对民族精神进行反思:“……德意志人的智慧恰好具备这种倾向。对一个已经领悟的思想,它会以更大的坚定性继续追踪下去,不会象法兰西人那样看到自己的想法与实际相吻合,就立即感到心满意足……而是要深入到本质中去,立即进行抽象思维,力求能完全把握住对象。有谁能否认德意志语言和文学中的这种精神?在这方面,德意志人是非常出众的,因为在大自然赋予人的整个精神财富中,这种抽象研究的智力肯定是最高的,并且将永远成为德意志人本性的最高级的装饰品。”①转引自[德]威廉•冯•施拉姆:《克劳塞维茨传》,王庆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0页。这个判断确实非常重要,也切近了德意志民族性的某种本质特征,它是穷追不舍的,是对真理有一种使命感的,正是这种近乎“为天地立心”与“为生民立命”的职责担当,使得这个民族有着一种一往无前、超越艰难的勇气和毅力,并且真的在人类思想试验场的这个空间里展开了艰苦卓绝和卓有成效的旅程,德意志民族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和领头羊。
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能不能出现和保留这样的知识和学术精英,就是检验它是否能负重行远的最关键标志。爱东兄对于学术的执着和热忱让我敬佩,他的那种纯粹科学式的态度其实我并不赞成。我虽然非常认同科学的重要意义及其方法论价值,但却绝不会一边倒地选择纯科学的路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爱东兄的同情之理解和高度欣赏,虽然我们之间的实际交往并不算多。费希特的那段论述确实是让人千载以下都会砰砰然而心向往之的:“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作,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恨,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②[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1页。在现下这个时代里重温这段规训,我们会庆幸,虽然我们生于这样一个颇为无奈的大时代,但在无限度的伦理沉沦之后,我们似乎未必就没有触底反弹的可能性,因为毕竟,我们还拥有和熟记这些文明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哲人和思想,而且我们每当重温它们就能产生那样激烈的共鸣和移情!仿佛黎明之际的雄鸡三唱,天下将白!
我们既然选择了以学术为业,就不能不守持一个学术人的基本位置;我们既然命定为学术人和知识人,就必须听从内心的精神召唤(甚至是使命感的呼唤,berufen),这其中既有“求知”的天然本职感,同时也有那种出于兴趣的“探奇解密”的诱惑行为。所以,概括地说,“知”与“争”是我们的基本使命,论争乃是达致真知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如果我们不能本着追求新知的使命感去积极地参与论争过程,而只是犬儒式的将学问作为谋生获取面包的手段,那么我们就不但是懦弱卑劣的,而且也是有愧于时代家国与人类文明的,我们毕竟还是有共同体归属意识的,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存在是有赖于这样一种“知与争”的过程,我们不但需要重温“科玄论战”的学术史,也应珍惜今日仍能泉泉流淌的“现代民俗学”的思想火花,更应充满勇气和毅力地走入田野,将自己的学术工作建立在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基础之上,助产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原创之思!
K890
A
1008-7214(2017)06-0117-03
叶隽,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 。
王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