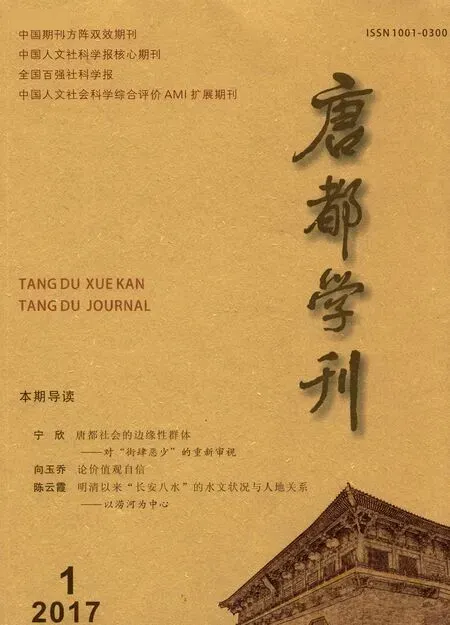“红颜祸水”与伦理责任的合理审视
——基于海伦和夏姬的比较分析
2017-01-28樊智宁陈庆超
樊智宁,陈庆超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伦理学研究】
“红颜祸水”与伦理责任的合理审视
——基于海伦和夏姬的比较分析
樊智宁,陈庆超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红颜祸水”观念内在蕴含着女性容貌对社会发展进程具有直接的影响的意味,这种伦理观念在古希腊悲剧中的海伦和春秋时代的夏姬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尽管西方文化传统和中国文化传统对海伦和夏姬因“红颜祸水”而招致的女性伦理责任归咎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但本质上是男权主义时代道德评价方面性别不平等的反映,女性容貌成了男性意志薄弱和逃避道德责任的替罪羊。
“红颜祸水”;伦理责任;海伦;夏姬
“红颜祸水”论是一种对女性伦理责任归咎观念。红颜是表示女子容貌艳丽,指代美女。“红颜祸水”论认为容貌艳丽的女子能魅惑君王,致使君王怠于朝堂,招惹仇敌,从而贻误政府的决策和国家的正常运行,甚至致使国家的灭亡。事实上,“红颜祸水”论所体现出的伦理责任指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男权主义当道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为男性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寻找一个替罪羊,而美女自然就成了男性逃避伦理责任、放弃道德自省的牺牲品。
一、海伦和夏姬的“红颜祸水”形象
对比中西方文化,我们可以看到“红颜祸水”的论断古已有之。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时期,“红颜祸水”的论断就已经十分流行。古希腊时期以欧里庇得斯悲剧中的海伦为代表;中国的春秋时期则以左丘明解释《春秋》的《春秋左传》中所描写的夏姬为代表。尽管海伦是文学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而夏姬则是历史典籍所记载的真实人物。
海伦出生于古希腊的著名城邦斯巴达,她的父亲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但据传说,海伦是宙斯的私生女。宙斯化身成为一只天鹅,与海伦的母亲勒达交合,生下了海伦。在欧里庇得斯的笔下,海伦是一位绝世美女,海伦的形象在其诸多作品之中都有涉及。在《海伦》和《俄瑞斯忒斯》中,海伦作为主要人物登场;在《圆目巨人》《赫卡柏》《安德洛玛刻》《厄勒克特拉》和《在奥利斯的伊非革涅亚》之中,主人公的对话也都涉及海伦。
在欧里庇得斯的这些悲剧作品中,海伦的艺术形象是不尽相同的。在以海伦为第一主角的悲剧《海伦》之中,海伦是一位美丽动人、忠贞不二、智慧贤良的女性,并非是所谓的“红颜祸水”。然而,在其他的作品中,海伦则是不忠的妻子、战争的罪人、剧中各角色苦难的根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红颜祸水”。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海伦形象,呈现出矛盾的情形。
夏姬出生于中国春秋时期的郑国,她的父亲是郑穆公。夏姬的一生可谓传奇,其事迹主要见诸《春秋左传》中鲁宣公九年、十年,鲁成公二年、七年以及鲁昭公二十八年的记载之中。夏姬被形容为“尤物”,其生活作风淫乱不堪,不仅与多位男性有染,而且不乏出轨和乱伦之事。在一些记载中,夏姬能以床笫之技掌控男性,甚至返老还童。其一生之中三次为王后、七次为夫人,当时的公卿王侯都争抢夏姬。可见,夏姬在中国古人眼中成为一位妖姬,俨然是“红颜祸水”的代言人。
实际上,纵观整个春秋时期,可以看到的是在当时像夏姬一样被视为“红颜祸水”的女性还有很多,如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卫宣公的夫人宣姜、晋献公的夫人骊姬,还有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等,但这些女性的争议性与夏姬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对《春秋左传》记载进行详细的分析,则能发现左丘明并没有明确地将祸国殃民的伦理责任完全归咎于夏姬。夏姬之所以被冠以“红颜祸水”的罪名,很大程度上源于后人对左丘明记载和论述的误解。
此外,欧里庇得斯描写的海伦的艺术形象和左丘明记载的夏姬的历史形象都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完成的,两者大致处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各自正源生成的时期,中西两种文化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红颜祸水”的伦理责任归咎的代表人物。但是,海伦和夏姬在后世的遭遇可谓天壤之别。海伦在后世的西方文化中不再强调其是“红颜祸水”,而是成为了爱和美的化身。夏姬在后世的中国文化中则不仅是“红颜祸水”,甚至被妖魔化。二者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别,值得分析和思考。
二、海伦伦理责任的矛盾与同一
在欧里庇得斯的大部分作品之中,海伦的艺术形象是以“红颜祸水”的身份而出现的。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对海伦的伦理责任归咎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海伦需要为国家的灾难承担伦理责任。在《圆目巨人》中,欧里庇得斯描写在特诺伊之战后的奥德修斯归乡的旅途,其中有一段歌词询问奥德修斯特诺伊之战的目的是否为了海伦,奥德修斯答道:“是呀,我们毁灭了普里阿摩斯的全家”[1]118。普里阿摩斯是特诺伊的国王,毁灭了普里阿摩斯全家的意思即是指代特诺伊灭亡。欧里庇得斯借用奥德修斯之口,表明了特诺伊战争是由于海伦引起的,并且特诺伊的灭亡的伦理责任也应该归咎于海伦。此外,海伦不但需要为特诺伊的灭亡负责,同时也需要为希腊的灾难负责。在《俄瑞斯忒斯》之中,海伦在特诺伊战争之后回到希腊,海伦并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就因此谴责海伦道:“这还是从前那个女人!神们要憎恨你,因为你毁了我和他,和整个希腊!”[1]998由此表明,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海伦首先是需要为国家的灾难承担伦理责任这一“红颜祸水”的形象出现的。
另一方面,海伦需要为许多个人的痛苦遭遇承担伦理责任。在《赫卡柏》之中,阿喀琉斯的灵魂阻止了希腊人归国的船只,需要献祭,文中就提到“他应该要求把海伦做他坟前的牺牲,因为这乃是她引了他来到特诺亚,害了他的。”[1]14人们将害死阿喀琉斯的罪魁祸首指向海伦,需要用海伦作为牺牲在阿喀琉斯的坟前献祭方能平息阿喀琉斯的愤怒。在《安德洛玛刻》之中,特诺伊一方的人们也对海伦不依不饶,赫克托耳的妻子认为正是“为了她的缘故,……那海的女神特提斯的儿子驾了兵车,拖着我的不幸的丈夫赫克托耳绕着墙奔去。”[1]336赫克托耳的妻子将赫克托耳的死和悲惨遭遇也归咎于海伦。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之死归咎于海伦或许情有可原,因为二者皆直接于特诺伊之战中牺牲。然而在《在奥利斯的伊非革涅亚》和《厄勒克特拉》两部悲剧中,海伦却匪夷所思地要为伊菲革涅亚之死承担伦理责任。伊菲革涅亚是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长女,阿伽门农出征前杀死了伊菲革涅亚用以祭旗,海伦的丈夫墨涅拉奥斯就认为伊菲革涅亚“将要去做了牺牲,为了我的婚事的缘故。”[1]252而伊菲革涅亚的母亲也认为阿伽门农是“那找着了背夫逃走的妻子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去惩罚她,所以他就杀害了我的女儿。”[1]916杀死伊菲革涅亚的是阿伽门农,这直接的伦理责任本该由阿伽门农来承担,但欧里庇得斯却将海伦也牵扯进了伦理责任的归咎之中。由此可见,不论是国家的灾难还是个人的苦难,欧里庇得斯都将海伦视为伦理责任的承担者。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海伦确实是“红颜祸水”。
然而,在欧里庇得斯的《海伦》这部作品中,其对海伦的形象的描写则与之前大相径庭,这也使得海伦的伦理责任发生了变化。在《海伦》中,海伦不仅是直接登场的人物,同时是作为悲剧的女主角。在这部剧的开场海伦的一段自述之中,能够体现这部悲剧中的海伦已经不再作为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苦难的伦理承担者。
赫拉和库普里斯和那宙斯的闺女,到伊得山的山谷里帕里斯所在的地方,想要得到那关于美貌的决定。库普里斯得了胜,她拿出我的美来,——若是那种不幸可以叫做美,——给帕里斯去作配偶。……但是赫拉因为没有能胜过那两位女神,很生了气,使帕里斯要娶我的事落了空,她不曾把我去给了他,却用了天空中的云气,造成一个像我的,能呼吸的形象,给予那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1]538
这段描述是解释特诺伊之战的缘起,即天后赫拉、爱神库普里斯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之间的比美,而海伦是库普里斯获胜后许给帕里斯的承诺而已,并且帕里斯从斯巴达拐走的并不是真正的海伦,而是赫拉用云所造出的海伦的幻影。周作人先生甚至认为是赫拉故意破坏库普里斯的计谋,挑起了希腊与特诺伊之间的战争[1]599。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海伦只是被诸神利用了,她在客观上并没有作出背夫出走的行为,更不用说为了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承担伦理责任了。
此外,在《海伦》这部作品之中,海伦甚至主动对本不需要自己负责的战争做出反思。当海伦在埃及听闻特诺伊战争之后的惨状之时,海伦说道:“许多人的生命,为了我都丧失在斯卡曼德洛斯的河流旁边。我承受了一切灾难,被人们诅咒,把我当作背夫的人,给希腊人引起了一个大战。”[1]539相比于《俄瑞斯忒斯》中海伦的冷漠,此时的海伦却为自己无直接责任的战争作出自觉的反思,这是一种理性道德自觉的体现。由此可见,在欧里庇得斯的《海伦》之中,海伦绝非“红颜祸水”,是不需要承担伦理责任的。
通过欧里庇得斯的其他悲剧作品与《海伦》的对比,海伦是否是“红颜祸水”是有争议的,对海伦的伦理责任归咎也呈现出矛盾。但如果做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则可以看出这一矛盾只是表象而已。在欧里庇得斯的诸多作品中,海伦的形象有诸多的不同,但海伦仅仅是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她不过是奥利匹斯诸神作为斗争的工具和筹码。比如特诺伊之战,从根本原因来说,海伦是诸神作为给帕里斯的奖品,海伦和帕里斯坠入爱河也是库普里斯对帕里斯的承诺,其中并不能看到海伦自身的意愿选择。再从战争的直接原因上来说,如果海伦并没有随帕里斯私奔,一切都是诸神的阴谋诡计,那么,不论是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结果上来看,海伦都是清白的。因此,对海伦作“红颜祸水”这样的伦理责任归咎在根源上就是荒谬的。如果海伦确实随帕里斯私奔,那么,在客观结果上海伦需要承担背夫出轨的伦理责任,但海伦是出于自身的意愿还是出于神的意愿,这一点仍然不能做明确的判断,此时贸然将“红颜祸水”之名扣于海伦头上,让海伦完全承担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苦难的伦理责任,未免有失公允。事实上,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对海伦的伦理责任归咎所呈现的矛盾,一方面是因为海伦作为神在人间的符号和象征,谴责海伦实际上也是谴责海伦背后的人和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古希腊人意识到了诸神才是始作俑者,从而索性绕过了海伦这个符号和象征,矛头直指诸神。这就是看似矛盾之下的伦理责任的内在同一性。海伦并不是“红颜祸水”,因为真正的伦理责任承担者并不是海伦,而是奥林匹斯诸神。
三、夏姬伦理责任的误解与重释
相比于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海伦,《春秋左传》中的夏姬作为“红颜祸水”所代表的历史形象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左丘明在《春秋左传》中并没有直接记载夏姬的美貌,甚至连夏姬的具体言行也没有独立的记载。而关于夏姬淫乱的行为的描写,往往是以与她有染的男性为主体而被记录下来。夏姬的事迹首次见之于《宣公九年》与《宣公十年》。夏姬当时嫁给陈国大夫夏御叔,然而夏御叔去世,夏姬守寡。据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示日服以戏于朝。”[2]568陈灵公和他的两位大夫孔宁、仪行父都与夏姬私通。更荒唐的是,三人居然公然将夏姬的内衣穿在身上在朝堂之上嬉戏。大臣泄冶劝谏,然而却被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三人所杀。陈国有这样的荒唐君臣,国家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果然,在次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2]573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三人与夏姬饮酒作乐也就罢了,居然还拿夏姬的儿子夏征舒开如此下作的玩笑。于是,夏征舒因此作乱,弑杀了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则出逃至楚国。次年,楚国则以平定陈国内乱为由起兵,杀死夏征舒,掳走了夏姬,几乎灭亡了陈国。就以上的记载来看,人们都会将陈国的灭亡、两位大夫出奔和夏征舒的死的伦理责任归咎于夏姬,将其视为“红颜祸水”。
当然,关于夏姬之事还远不止如此。夏姬到了楚国之后同时也给楚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首先是楚庄王,当时楚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王乃止。”[2]654-655楚庄王想纳夏姬为夫人,但是巫臣劝谏楚庄王不可贪图夏姬的美色,否则将有大患,楚庄王幡然醒悟,放弃纳夏姬这个念头。其次是楚国大夫子反,“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2]655子反也想取夏姬,巫臣又劝谏说夏姬是个不祥之人,取之则会招祸。于是,子反恨恨作罢,最终楚庄王将夏姬许配给连尹襄老。
经过这一事件,子反与巫臣产生了嫌隙,因为巫臣的劝谏实际上是为了自己霸占夏姬。随后襄老在邲之战中牺牲,寻不见尸首,巫臣趁着带夏姬寻襄老尸首的机会,抛弃家庭逃到了晋国。据《成公七年》记载,巫臣出逃后“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2]689巫臣和襄老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由此可见,《春秋左传》的记载对夏姬十分不利。夏姬对楚国内乱难辞其咎,确实是“红颜祸水”。
《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的一段记载,对夏姬做了盖棺定论。这一段记载也是将夏姬视为“红颜祸水”这一伦理责任归咎的源头。但是,对这段评论存在着一些争议,甚至容易被误读。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2]1562
晋国大夫叔向欲取巫臣和夏姬的女儿,但是叔向的母亲反对,认为夏姬害死了三位夫君、一位国君和一个儿子,而且陈国和两位卿大夫的家族也因她而亡,于是提出了“甚美必有甚恶”的观点。叔向母亲对夏姬的定论就是典型的“红颜祸水”论。夏姬需要为自己的三个夫君、陈灵公和儿子夏征舒的死,以及陈国、巫臣和襄老家的覆亡承担所有的伦理责任。
然而,对叔向母亲的评语作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叔向母亲认为“甚美必有甚恶”,这是抽象的一种表达,具体到夏姬身上则是“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即是说像夏姬这样的“尤物”,能移人心智,如果没有德义,则会招来祸患。恰恰“德义”才是这个盖棺定论的重点,而人们在评价上往往误解了叔向母亲的评论,使得后世将国家覆亡等伦理责任由夏姬一人独自承担,这实在太过于偏激。
左丘明在《春秋左传》中所记载的叔向母亲的话,是否可以作为对夏姬“红颜祸水”形象的重要依据是需要重释的。其一,《春秋左传》强调了取夏姬这样的“尤物”是需要“德义”的,如果没有良好的德性,那么就会招致祸患。言下之意,伦理责任的侧重不在于夏姬的美貌,而在于男子自身的道德修养。再看《春秋左传》中直接因为夏姬而遭难的这些人,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之辈基本上属于荒淫无道的君臣,毫无德义可言;子反因为无法得到夏姬而将巫臣全家诛杀,品行也十分低下;巫臣更是为了得到夏姬而机关算尽,甚至抛下家族出逃,也称不上是有德之人;唯有楚庄王有自知之明,不纳夏姬,得以善终。正因为缺乏德性,陈灵公和巫臣等人才会招来祸患,夏姬不过是一个契机,只是一个外因而已。因此,将“红颜祸水”的伦理责任完全归咎于夏姬是不妥当的,至少夏姬不用承担主要的伦理责任。其二,夏姬在主观上是否是出于自身的意愿而如此淫乱,也有待商榷,但即使是出于自身的意愿也是情有可原的。夏姬不论是在陈国和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还是在楚国和巫臣有染,都是在其守寡的时候发生的事,并未处于婚姻状态之下。而春秋时代有关男女关系的社会风气是相对开放的,夏姬的所作所为不能算是不守贞操。这里,不妨将夏姬与春秋时期其他的女性作对比,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和亲哥哥齐僖公通奸、鲁庄公的夫人哀姜和鲁庄公的弟弟庆父通奸甚至周襄王的王后隗氏和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通奸,以礼乐之邦著称的鲁国公室的夫人和周王室的王后也做出这种苟且之事,而且文姜、哀姜和隗氏皆是在夫君健在的时候出轨,其所引发的混乱比夏姬所引发的混乱甚至更大。然而,她们并未受到太多的指责,夏姬却要独自承担一系列的伦理责任。由于对《春秋左传》中有关夏姬的评价存在着诸多误解,这也使得后世夏姬被妖魔化。
四、海伦与夏姬伦理责任的对比与反思
在对欧里庇得斯悲剧中海伦的艺术形象和《春秋左传》中夏姬的历史形象进行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古希腊时期和春秋时期的“红颜祸水”的女性伦理责任归咎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
首先,海伦与夏姬伦理责任的最终归咎者是不同的。易中天认为这是“神之过”与“人之罪”的区别[3]51。海伦被视为“红颜祸水”在于其行为的客观效果上引发了特诺伊之战,最终导致特诺伊灭亡、希腊城邦遭到重创以及无数英雄和民众死亡等灾难和痛苦。但是,引发战争的所有决定性因素皆与海伦无关,海伦自身是没有选择的,特诺伊之战的背后是奥林匹斯诸神之间的博弈。因此,一切灾难和痛苦的伦理责任的最终归咎者是诸神,而不是海伦。相反,夏姬被视为“红颜祸水”不仅在于其行为的客观效果上引发了陈国和楚国的内乱,还在于引发这一系列事件的源头只有人,而没有神。伦理责任最终也只能归咎到人身上,要么是夏姬,要么是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等人。然而一方面,夏姬的种种行为在主观上是否出于自身的意愿,这一点是难以考证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女性本身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在必须要有一个人承担伦理责任的时候,女性由于缺少话语权且缺少足够的证据证明自身的行为并非出于自身的意愿,夏姬自然就成为伦理责任的被归咎者,沦为“红颜祸水”。
其次,对海伦与夏姬的“红颜祸水”伦理责任归咎的解读上也存在区别。欧里庇得斯悲剧中出现了海伦道德形象相互矛盾的情形,而这个表象上的矛盾是当海伦作为一个诸神的符号和象征时才会呈现出来。对海伦的直接的道德谴责,其实就是将伦理责任归咎于海伦背后的那些人和事,只不过没有明确地指明那就是奥林匹斯诸神的行为。当人们自觉地意识到了在海伦背后的力量是诸神的时候,就绕过海伦这一符号和象征,直接谴责诸神。所谓的“红颜祸水”,在古希腊人的理解中没有普遍的意义,只是一种权宜的代称罢了。实际上,夏姬的历史解读也是有矛盾的,在左丘明的另一部作品《国语》中认为,陈灵公亡国是由于“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4]45,没有将伦理责任归咎在夏姬身上。《春秋左传》与《国语》的记载似乎存在矛盾,但这与后人对《春秋左传》的误解有关。因此,对夏姬的“红颜祸水”伦理责任归咎的解读,本质上是男性为社会主导且女性缺少话语权的社会中的习惯性思维的产物。
最后,海伦与夏姬“红颜祸水”伦理责任归咎对后世的影响也大相径庭。海伦的形象在其后的西方文化中,一直是爱和美的象征,作为纯粹审美的符号而存在。所谓“红颜祸水”的形象也只特指特诺伊战争里的那个海伦,而且古希腊人将伦理责任归咎于诸神,而不是女性。在文明脱去了神话的外衣之后,诸神也不再为一切事物负责。西方人自然就将责任归咎的主体回归到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即人类责任观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人类应该为出于自身自由意愿的行动而负责。因此,在西方文化中“红颜祸水”的观念相对淡薄。然而,夏姬的遭遇则不同,“红颜祸水”的观念日益加深。汉代依然有“夏姬好美,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殆误楚庄,败乱巫臣。子反悔惧,申公族分”[5]287之语。到了宋代,欧阳修还有“女色败人”之言论,即“自古宦、女之祸深矣!”[6]403将女子和宦官并列为国之大害。甚至认为“自古女祸,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犹及子孙,虽迟速不同,未有无免祸者也”[6]127。这种女性伦理责任观实际上是自春秋时代开始的对女性形象的误解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思而形成的历史惯性,真正应该承当伦理责任的不是这些女性,而是缺乏足够德性的统治者。
总而言之,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各自正源生成的古希腊时代和春秋时代,对海伦和夏姬的“红颜祸水”伦理责任归咎有其各自的特点,其解读和反思方式的不同,也导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女性伦理责任观的差异。时至今日,“红颜祸水”的女性伦理责任观依然存在于一些国人的道德观念中,而正确的伦理责任观是没有性别之分的,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培养良好的德性,在享有各项基本权利的同时,切实地履行与权利相应的伦理责任。
[1] 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悲剧集[M].周作人译.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2] 左丘明著,杜预集解.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 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4] 左丘明.国语[M].韦昭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5] 刘向著,张敬译注.列女传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
[6] 欧阳修.新五代史[M].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 王银娥]
Rational Survey of Helen of Troy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elen and Xia Ji
FAN Zhi-ning, CHEN Qing-chao
(CollegeofPhilosophy&SocialDevelopment,HuaqiaoUniversity,Xiamen361021,China)
The concept of Helen of Troy implies that females’ beauty has direct effect o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is distinctly embodied by Helen in an ancient Greek tragedy and Xia Ji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China. Although i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females’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resulted from Helen and Xia Ji due to their beauty, essentially, in the male chauvinism, it has reflected the sexual inequalities in terms of moral evaluation so that women’s beauty has become the scapegoat for men’s weak-mindedness and escape from their ethical responsibility
Helen of Troy; ethical responsibility; Helen; Xia Ji
B82-051
A
1001-0300(2017)01-0041-06
2016-10-10
华侨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伦理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16YJG08)前期成果
樊智宁,男,福建南平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伦理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德性论研究; 陈庆超,男,福建泉州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伦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性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