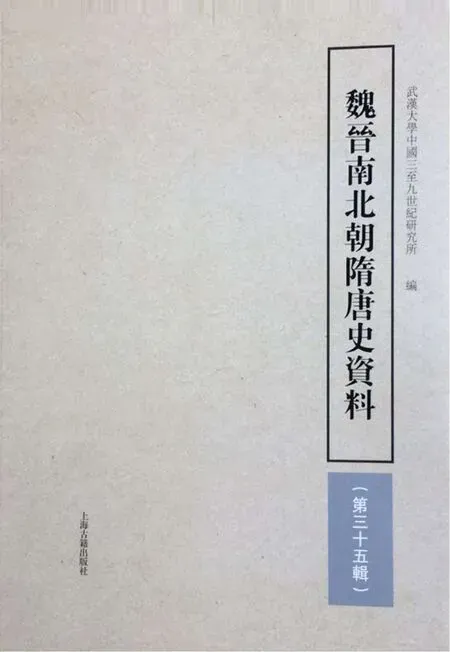唐代中期的道觀
——空間·經濟·戒律*
2017-01-28都築晶子
都築晶子 著 羅 亮 譯
唐代中期的道觀
——空間·經濟·戒律*
都築晶子 著 羅 亮 譯
唐代中期8世紀前後,道教進入一個新發展的時代。從南北朝時代起,依據皇帝的敕命,興建了不少道館、道觀。*卿希泰主編: 《中國道教史》第一卷,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3—566頁。拙作: 《六朝後半期における道館の成立——山中修道——》,收入《小田義久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集》,龍谷大學東洋史研究室,1995年。付晨晨譯、魏斌校漢譯文《六朝後期道館的形成——山中修道》,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5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在隋代和唐初時,因爲皇帝和道士的私人關係,或許還有唐室尊崇老子爲祖先的因素,也修建了若干道觀。但在7世紀後半期,也即從唐高宗時代開始,王朝與道觀的關係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乾封元年(666),在泰山封禪的高宗,於兗州置紫雲、仙鶴、萬歲三觀和封巒、非烟、重輪三寺,並令全國各州置道觀和寺院各一所(《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弘道元年(683),當時各州依據人口多少分爲上中下三等,上州置道觀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觀各度七人(《全唐文》卷一三《改元弘道大赦詔》)。此時,不再是依據皇帝和道士的私人關係,而是作爲國家事業,在全國範圍内興建道觀。可以認爲,道觀和道士的數量在此時急速地增加了。*卿希泰主編: 《中國道教史》第二卷,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2頁。
道觀自然是道士修行的場所。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執行齋醮和上章等宗教儀禮,從皇帝到民衆祈求神明救濟的場所。道觀的興建的確是以宗教爲基礎,但另一方面,也是作爲道士共同生活的場所來經營的。因此,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這種經濟是以戒律來約束的——道士所遵守的規範,和道觀中共同生活的規律有所區别,在此概括地稱爲戒律。*記述從南北朝到唐代道館、道觀規則的道教經典有如《陸先生道門科略》、《千真科》、《洞玄靈寶千真科》、《玄都律文》、《正一威儀經》、《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老君音誦誡經》等。這種規則常被稱爲科、律、科戒、戒等。儀禮和戒律雖然都很重要,但二者並没有嚴密的區分。從南北朝時起,記録宗教儀禮和戒律的科儀戒律書被不斷編成。比如在隋末時完成的《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道藏》七六—七六一册*此處標記“道藏xx册”,爲綫裝本册數,而非下文由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本《道藏》之册數。——譯者注。)即是其中體系較爲完整的一部。*關於《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可參考吉岡義豐: 《三洞奉道科戒儀範の成立について》,《道教と佛教》第三章、第二章第一節,国書刊行會,1976年;大淵忍爾: 《三洞奉道科戒儀範の成立》,《道教とその經典》第七章,創文社,1997年;小林正美: 《六朝道教史研究》,創文社,1990年,第96—97頁。成書年代有梁末、隋末諸説,但通過發現的敦煌文書可以確認,在隋末時已經成書。唐代中期的8世紀前後,在以往的基礎上開始編撰新的科儀戒律書經典。張萬福對儀禮的整理,可以和百年後儀禮的集大成者杜光庭並稱,與此同時,他還撰成總結道觀生活戒律的《三洞衆戒文》(《道藏》七七册)。*南宋編纂的《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道藏》二七八—二九册)卷一《儀範門·序齋第一》稱,陸修静之後,“張杜二師繼出”(9-378中),也即張萬福、杜光庭相繼登場,整備儀禮。張萬福的著作除《三洞衆戒文》外,還有《三洞法服科戒文》(《道藏》五六三册)、《洞玄靈寶三師名諱行狀居觀方所文》(《道藏》一九八册)、《洞玄靈寶道士受三洞經誡法籙擇日曆》(《道藏》九九册)、《洞玄靈寶無量度人經訣音義》(《道藏》四八册)、《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籙立成儀》(《道藏》八七八册)、《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説》(《道藏》九九册)等。幾乎與張萬福同時代的朱法滿,撰成了《要修科儀戒律鈔》(《道藏》二四—二七册),編纂了科儀戒律。可以認爲,唐代中期的8世紀前後,不僅在儀禮上,在道觀的生活戒律上也進行了整頓再編。
那麽,道觀呈現出來的共同生活空間、經濟、戒律究竟如何呢?這個問題,在《中國道教史》的南北朝部分已簡單提及,但未能得到充分討論。*參上頁注①。小林正美: 《中國の道教》對南北朝時代道館的戒律和建築有所介紹,創文社,1998年。中文版爲王皓月譯: 《中國的道教》,濟南: 齊魯書社,2010年。南北朝已降道觀的興起,和佛教寺院一樣,意味着在社會内部出現了以往没有的异質集團。所以此問題不僅僅限於道教,也有助於我們觀察和理解當時的社會結構。總之,本文以記述道觀生活戒律的《要修科儀戒律鈔》(以下簡稱《戒律鈔》)爲中心,並以張萬福編撰的一系列科儀戒律書以及當時常用的經典《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以下簡稱《科戒營始》)爲題材,*吉岡義豐的研究將張萬福的《科戒營始》作爲有力的資料加以利用,並指出該書在當時頗爲流行。見氏著前揭書,第90—97頁。還可參見小林正美本前引書,第300頁。沿着這些書籍的文脉,來描繪8世紀前後道觀的空間、經濟和戒律。
一、 8世紀前後的科儀戒律書編纂的背景
張萬福在玄宗即位的先天元年(711)前後,在首都長安的太清觀有着“大德”的地位。當時太清觀主是史崇玄。史崇玄事太平公主,被稱爲“聲勢光重”,*《新唐書》卷八三《睿宗十一女·金仙公主傳》。睿宗的女兒金仙、玉真兩公主爲道士,以其爲師,接受經典。史崇玄編纂了《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道藏》七六册),張萬福亦參與其中。*關於張萬福,可參《中國道教史》第二卷,第282—290頁;吉岡義豐前揭書,第90—93頁。因此,張萬福登上了首都權威道觀的舞臺。
另一方面,我們對朱法滿所知不多。*關於朱法満,可參《中國道教史》第二卷,第290—295頁。國内(日本)研究中,大淵忍爾氏引《三洞群仙録》指出,朱法滿的傳記中並無其生卒年的記載。大淵忍爾、石井昌子、尾崎正治: 《改訂增補六朝唐宋の古文獻所引道教典籍日録·索引》,國書刊行会,1990年,第9頁。因此《戒律鈔》的成立年代,只能從内容上判斷是唐代後半期。小林正美氏也同意此説,參氏著前揭書,第299頁。關於其生平,中國道教研究常引用《三洞群仙録》卷一三(《道藏》九九二—九九五册)以及《洞霄圖志》卷五《人物門》的傳記記載。*《洞霄圖志》由出仕南宋,元朝建立後隱遁的錢塘鄧牧於元大德九年(1305)撰成。《洞霄圖志》載朱法滿於開元八年(720)五月二十九日去世。因此,朱法滿編纂《戒律鈔》當在720年以前,亦即與張萬福撰寫一系列著作大致同時。
朱法滿,名君緒,字法滿,杭州餘杭縣人,18歲在玉清觀出家修行。《洞霄圖志》稱:“後以玉清地迫喧囂,不可久處”,於是遁入家鄉餘杭縣的天柱山修行,數年後去世。在天柱觀中,他被尊爲“法師”,弟子之中有從玉清觀跟隨而來的暨齊物。
朱法滿修行的玉清觀信息不詳。隋代曾有爲王遠知修建的揚州玉清玄壇,*參吉川忠夫: 《王遠知傳》,《東方學報·京都》六二,1990年。不過在8世紀前後的情況則無從所知。但既稱“地迫喧囂”,則道觀當在都市之中。天柱山是三十六洞天之一。*《洞霄圖志》卷一《公觀門·洞霄宫》云:“兹山爲大滌元(玄)蓋洞天”。杜光庭: 《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道藏》三三一册)《三十六洞天》云:“天柱山大滌玄蓋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11—58中)”。高宗弘道元年(683),如前所述在全國各州興建道觀,敕命“潘先生”營造天柱觀。“潘先生”其人不詳。在此後,葉法師、朱君緒(朱法滿)、吴筠、暨齊物、司馬承禎、夏侯子雲等人都曾暫住或造訪過天柱觀。*《洞霄圖志》卷六《天柱觀記》。《天柱觀記》是錢镠在唐末光化三年(900)所撰。錢镠是之後建立十國之一吴越的節度使。
那麽,朱法滿編撰全十六卷《戒律鈔》的意圖何在呢?朱法滿本人並没有對此加以闡述,但所録内容,始於經典由來,終於道士服制,包含了道觀中儀禮、修行、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内容近七十項。幾乎每項開頭都附有朱法滿簡要的注釋。《戒律鈔》可説是“當時道教戒律科儀的縮略圖”,*《中國道教史》第二卷,第295頁。在徵引了當時流傳的五十餘種經典的基礎上而成,不過卻没有將其整合體系化的意圖。如卷一三所記在道觀中共同生活的戒律的《雜科》,即全部引自《洞玄靈寶千真科》(《道藏》一五二册),同樣,《同學緣》則全部引自已經散佚的《太真科》。*關於《太真科》,參大淵忍爾: 《太真科及其周邊·附太真科輯本稿》,前揭書第五章。也正因爲如此,儘管《戒律鈔》被視爲研究六朝道經的重要參考,但對其本身的研究似乎還没有受到重視。只有末尾卷一五、卷一六的《道士吉凶儀并序》是朱法滿所撰。雖然其開頭即稱“法滿後識晚生,未能窮究至於脉制,深以致疑”(6-993上),——“脉制”當爲“服制”——但文中大半部分都是在總結前人對道士服制的討論。
儘管如此,我們在朱法滿的注釋中還是能看出其編纂的意圖。如卷四到卷六的《衆戒及願念合一千一百條》中稱:“夫經以檢惡,戒以防非,總任枝流,難以取用,撮其機要,易可尋求”(卷四,6-936下),意爲“戒律若全取其支流,是難以使用的,只有選取其要點,纔易於搜檢”。也即是使其簡便易用。又如在《道士吉凶儀并序》開頭的“通啓儀”、“吊喪儀”,便是道士在與對方書信往來時的具體範例,顯示出了類似工具書一樣簡便易用的特點。《道士吉凶儀并序》的序中稱“乃立典儀,訓門中子弟”,由此可見,至少《道士吉凶儀并序》的目的之一是要教導道觀的弟子。
記述道士法服的卷九《衣服鈔》中,朱法滿罕見地對“今”進行了批判,他稱:“今時之輩,或以淨衣穢慢,或以法服借人,或坐地而染塵泥,或藉床而當氈席,使神童而靡衛,令道俗以驚嗟。”(卷九,6-960下)法服是由童子、童女負責管理,必須時刻保持清淨。*如《戒律鈔》卷九引《四極明科》云法服“給玉童玉女各十二人,典衛侍真,不得妄借异人,并犯殗穢,輕慢真服”(6-961上)。由此看來,《戒律鈔》的編撰,表面上是對經典抱有謹慎的態度,但其側面隱藏着對道觀現狀的批判,並且試圖成爲道觀中道士全盤生活的簡便指南。
這種意圖,在張萬福一系列著作中也表現出來。張萬福在總結戒律的《三洞衆戒文》的“序”中稱:“夫戒者,戒諸惡行,防衆行之最”,强調戒律的重要性。又稱:“三洞科儀,備有條格,而師資稟訓,各據一門,吴蜀京都,相承或异……其傳授經法次第,已如三洞法目。今又依經籙出戒文,附諸法次,受法之日,隨法轉授。”(3-396中)科儀戒律,是通過師徒關係,一門傳授而來,因而在江南、四川、首都等地,都是有所差异的。經法的傳授如同三洞法目一般即可,但戒律依據經、籙出戒文,隨經法一同由道士傳授。末尾稱“右(戒文)與所授經法,同時書寫,雖具在經中,臨事披覽難見也”(3-396下),可見他和朱法滿一樣,也希望弟子能够簡便地閲讀戒律。
而且,張萬福在《洞玄靈寶道士受三洞經誡法籙擇日曆》(《道藏》九九册)中,對“今”進行了尖鋭的批判: 種種儀禮的混亂,未能得受全部經法的道士,倚仗“富豪勢力”、“名望高遠”擴大勢力,只顧追求富貴名聲,自恃“年高德重”而賣弄權威,如此種種。又云:
昔嘗遊江淮吴蜀,而師資付度,甚自輕率,至於齋静,殊不盡心,唯專醮祭,夜中施設。近來此風少行京洛,良由供奉道士,多此中人,持玆鄙俗,施於帝里。(32-184中)
在江淮、吴蜀流行的鄙俗的儀禮,因墮落的道士而傳播到首都之中。
由此看來,朱法滿和張萬福,對“當今”道觀科儀戒律頽廢有着共同認識,也都試圖將混亂的戒律予以簡化,作爲教導弟子的指南書。張萬福的《三洞衆戒文》卷上收入的《弟子奉師科戒文》(3-397中~398上),記載了弟子對老師需要遵循的三十六條規矩。朱法滿的《戒律鈔》卷三同樣載有弟子對待師傅的規矩,不過其内容是將張萬福的《弟子奉師科戒文》的每條冠以“律曰”後加以記載(6-933下~935上)。朱法滿和張萬福之間的關係還不明確,但他們都試圖爲“當今”道觀中師徒關係立規。我們可以試做推測,即8世紀前後編撰的這些科儀戒律書與始於高宗時期的全國性道觀、道士的激增是有所關聯的。
張萬福的著作大多散佚,現在僅有部分流傳。這也就意味着《戒律鈔》是我們了解當時道觀生活的重要綫索。
二、 道 觀 的 空 間
1. 道觀的建築
《科戒營始》卷一《置觀品》對道觀做了詳細説明。《置觀品》開頭指出道觀淵源於仙界,接下來記敍了地上道觀的建築。《置觀品》的開頭部分被前面曾提及的《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明居處》所引用(24-727下),而《置觀品》中也能看到和《戒律鈔》所云“精思别院”、“遷化堂”相當的建築。所以認爲8世紀前後道觀建築的規範,在《科戒營始》撰成後就没有發生大的變化是没有什麽問題的。那麽下面來看《科戒營始》中的道觀空間到底是怎樣的。
爲方便起見,將《科戒營始·置觀品》依次列舉的道觀建築,分爲三組,並附上序號:
① 天尊殿、天尊講經堂、説法院、經樓、鐘閣、師房、步廊、軒廊、門樓、門屋、玄壇、齋堂、齋厨、寫經坊、校經堂、演經堂、熏經堂、浴堂、燒香院、升遐院、受道院、精思院、② 淨人坊、騾馬坊、車牛坊、俗客坊、十方客坊、碾磑坊、③ 尋真臺、錬氣臺、祈真臺、吸景臺、散華臺、望仙臺、承露臺、九清臺、遊仙閣、凝靈閣、乘雲閣、飛鸞閣、延靈閣、迎風閣、九仙樓、延真樓、舞鳳樓、逍遥樓、静念樓、迎風樓、九真樓、焚香樓、合藥堂等。(卷一,24-746上)
2. 清淨的空間
首先,①組中的殿、堂、院、樓、閣、房、壇、坊等,既是宗教儀禮和修行的空間,又是道士居住的空間。令人注目的是,這些空間特别强調“清淨”。如抄寫經典的“寫經坊”中設有道具,“每事清淨,不得交凡俗,穢汙混雜……此最大忌”(卷一,24-745下~746上)。在《戒律鈔》中曾提及精思院,《科戒營始》則稱“本欲隔礙囂氛,清淨滓穢,須爲别院,置之幽静”(卷一,24-746上)。③組的臺、閣、樓則是道士、女官馳思於仙界的場所。“既非常事,理須遐絶,宜近精思院”(卷一,24-746上)。①組和③組的建築群,處於相同的空間位置。寫經坊和精思院都需要清淨的環境。因此道觀中還有必備的浴堂以及供道士居住的私院、别院,這些建築“此最爲急”。又因“外犯俗塵,内違真戒,或污垢流漓,灰塵染汙,少不清淨,則犯靈司。既觸仙官,便乖正氣”,在儀禮和修行之前,則需沐浴,“澡鍊身心”(卷一,24-746上)。
道士居住的空間被稱爲“私房”。雖然《置觀品》中没有説明,但大概是高德的道士住在“精思院”,師長住在“師房”,弟子的私房則在“門屋”。《戒律鈔》卷一《治屋》中稱門室、門屋的東間、西間是祭酒居住的地方。*《戒律鈔》卷一引《太真科》曰:“……玄臺之南,去臺十二又(當爲‘丈’),近南門,起五閣三架門室。門室東門(當爲‘間’),南部宣威祭酒舍;門屋西間,典司察氣祭酒舍。”(6-984中)《科戒營始》對這種私房,更爲强調清淨樸素。“凡道士女冠(官)居處唯虚净素樸而已”(卷三,24-755上)。私房中所置物品,也僅有質樸的寢具、法具、食器等。私房中“皆須造浴室,内外密淨。凡犯穢及汗垢,即浴”(卷三,24-755中),這也是講究清淨。
道士居住的空間,與神明降臨的場所有所區别。天寶七年(748),玄宗爲李含光在茅山修建了紫陽觀。《答李含光進紫陽觀圖敕》云:
至於仙真道衆,故亦不可同居。所置紫陽觀大院内,更不須着人居止。但作虚廊四合,清潔殿堂,以修香火,用候雲駕。其道衆等别院安置。(《全唐文》卷三六,《茅山志》卷二,5-556上)
玄宗認爲仙真降臨的空間應與道士居住的空間有所區别,故在圖紙上新添了供道士居住的别院,亦追加了更多的經費。
道觀中道士“死”的場所則是“升遐院”。“凡道士、女冠(官)身亡,皆别置升遐院,須别立一院,造堂室,供器所須,皆備此院”(卷一,24-746中)。升遐院是安置遺骸的場所,《戒律鈔》中的遷化堂則是迎來臨終的場所。朱法滿在《道士吉凶儀并序·疾病儀》中引《千真科》對“遷化堂”有所介紹。道士迫近臨終前,則運入遷化堂。此堂在道觀西北角,别立爲院堂,堂面西北。堂中高座上,造升虚像,左右則置二對真人像。升虚像身坐蓮花,左手指向“天門”。病人則安置於像座之後。用幡的中間繫於左側真人像腰間,一端則放入病人手中,病人則念願隨二真“登天門,詣金闕”。*原文爲《戒律鈔》卷一五:“《千真科》曰: 出家之人,與俗有别……量命無幾,可移入遷化堂。其堂可於觀西北角,别立爲院堂,三間、五架,堂面看西北。其堂中高座上,造升虚像,像身坐蓮花,如人大舉左手以指天門,左右二真俠侍。病人恐命將絶,移入堂中像座後安置,用黄紋全幅爲幡,長二丈四尺,中央繫左真腰,幡頭與病人手捉,令病人直心正念,願隨二真登天門,詣金闕。”(6-996上~中)松村巧氏認爲,“天門”是天上仙界的門户,杜光庭《金籙齋啓壇儀》將設置於齋醮祭場的壇西北角“亥”稱爲“天門”(9-67中),*松村巧: 《天門地户考》,收入吉川忠夫編: 《中國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年。將道觀看作祭場的壇,則西北角即是通向天門的位置。
但另一方面,“死”代表着不淨的觀念仍然存在。《科戒營始》對埋葬道士的儀禮做了以下説明。將亡師的正一符籙及諸券契放入函中,在所埋山谷或墓地内另作坎安置,“餘皆不得輒隨身去。所以者,真經寶重,靈官侍奉,屍朽之穢,寧可近之”(卷五,24-760中)。在這裏,道士腐朽的遺骸被視爲“穢”。在《戒律鈔·殗穢緣》所列種種汙穢項目中,引《玄都律文》記録死亡的汙穢,稱:“遭師主父母大喪,三十日殗,不得齋章。過三十日,外限滿訖,洗浴燒香。”(卷一二,6-980上)作爲道士師長的“師主”,與父母的死亡一樣,都被認爲是汙穢的。由此可以認爲,道教中的死有着兩種意義。
順帶一提,朱法滿《道士吉凶儀并序·入棺大殮儀》中載有道士的隨葬品,例如經典也要盛入函中,與死者一道放入墓中,接受供養,或者預先投於“名山福地淨密處”。隨後朱法滿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今人受法,師猶不盡備經,弟子亦有不能辨。本所寫受經,何必與屍同穴?何必預投名山?經留代代相傳,符籙隨棺入塚。”(卷一五,6-997中~下)《科戒營始》中清淨·不淨的觀念相對更爲濃厚一些,《戒律鈔》這種觀念則較爲淡薄。
3. 賤與俗的空間
接下來看第②組中的坊。净人和家畜居住的空間與道士儀禮、休息、居住的空間有明確的區分。“凡淨人坊皆别院,安置門户井灶,一事已上,並不得連接師房。其有作客,亦在别坊安置。”(卷一,24-746下)净人居住的建築要另外修建,也設有生活必需品,但都不能與師房接鄰。“作客”的客也和净人一樣,是承擔道觀生活的勞動者。
家畜也需隔離,“凡觀門左右,皆别開車馬牛驢出入門,不得於正門中來往”(卷一,24-746中)。道觀的正門是“衆妙之門,往來之逕,群真之户,出入所由”(同上),屬於①組的空間,車馬通行需要設置另外的門户以作區别。值得注意的是,净人和家畜處於同一空間位置,“凡車牛騾馬,並近淨人坊,别作坊安置。不得通同師房及齋厨,院内出入,並近井灶”(卷一,24-746下)。②組中的騾馬坊、車牛坊安置在净人坊附近,而與道士的空間區别開來。
世俗的訪問者也有所區别。“道義”所帶“人畜”,“須别立客院。若未有别院,即安淨人坊,驢騾置驢騾坊”(卷一,24-746下)。“道義”指信衆,*陶弘景《周氏冥通記》卷一記載真人開始降臨至周子良面前的經過時稱:“周家本事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邪氣。”(5-518中)清代黄生《義府》卷下《冥通記》云:“道義,謂同事道法之義友。”由此可見,“道義”有信衆同伴的意味。此條由吉川忠夫氏提示。“人畜”指爲其差使的人和家畜。而從俗界訪問道觀的“俗客”、“門徒”、“官人”被安置在“俗坊”之中(②組中的俗客坊)。世俗的訪問者,只能滯留在與①、③組建築相隔離的空間之中。
與家畜處於同一層次的“净人”,源自於北魏的佛教教團。塚本善隆氏指出,當時爲佛教教團經營寺院田宅、處理俗務、負擔諸般勞役的人被稱爲“净人”。*塚本善隆: 《北魏の僧祇户、佛圖户》,《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第四章,大東出版社,1974年,第126—127頁。唐代義净所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五(《大正藏》卷二三·六五一下)即設有“净人坊”。北魏永平二年(509)的沙門統、慧深上書稱:“依律,車牛淨人,不淨之物,不得爲己私畜。”(《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如後所述,“净人”在當時社會屬於賤人,視同家畜。《科戒營始》將净人與車牛置於同一空間,但是否將其視爲“不淨之物”呢?這一點還不清楚。
道觀中還設有藥圃、果樹園、花園、菜園。在道觀建築的周邊,設有用於治療疾病的藥圃,爲供養三寶而種植的花和果樹,還有爲提供齋食而種植的除戒律規定的五辛之外的時令名菜瓜瓠(卷一,24-746下~747上)。例如天柱觀中,有夏侯子雲營造的“藥圃”,據説栽培了能養神、養性、治病的仙藥(《洞霄圖志》卷五《人物門·夏侯天師傳》)。再如“碾磑坊”,是爲道觀的莊田、碾磑所設置的。有關莊田、碾磑,見於下文。
總之,道觀分爲與神直接交流、道士居住的清淨空間和俗客、净人家畜利用的空間這兩個部分。道觀裏,聖域中的神聖空間和與世俗相關的空間是截然區分開來的。
4. 長生林
道觀的周圍還設置有從高宗時代起被稱爲“長生之林”的區域。朱法滿晚年居住的餘杭縣天柱觀,就有前述高宗弘道元年(683)時建立,但“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采,爲長生之林”(《洞霄圖誌》卷六《天柱觀記》)。弘道元年,部分道觀設立了長生林。如衡岳的衡岳觀,“封岳,辟方四十里,充宫觀長生之地,禁樵采,斷畋獵,罷獻琛,以爲常典”(《南岳小録》,6-862下,《道藏》二一册)。始於高宗時期的這一舉措,之後也得到了延續,如始豐縣天台山的桐柏觀即是一例。桐柏觀曾爲一片廢墟,景雲中(710-711),睿宗下敕重建,“於天台山中辟封内四十里,爲禽獸草木長生之福庭,禁斷采捕者”(《全唐文》卷一九《復建桐柏觀敕》;《天台山志·宫観》,11-92下,《道藏》三三二册)。上文提到玄宗在天寶七載爲道號玄静的李含光在茅山修建紫陽觀,而在天寶四載,李含光入山之時,茅山全境就已禁止狩獵采伐了。*根據《茅山志》卷二《大(太)和禁山敕牒》(5-560下~561上)記載,這片區域包含三茅山及其支脉的廣大地域。
且茅山神秀,華陽洞天,法教之所源,群仙之所宅。固望秩之禮雖有典常,而崇敬之心宜增精潔。自今以後,茅山中令斷采捕及漁獵,四遠百姓有喫葷血者,不須令入。*《茅山志》卷二《玄宗賜李玄静先生敕書》,5-555下。
天寶七載,玄宗對朝廷和民間祭祀所殺犧牲也做了限制,全國的“靈山、仙迹”都禁止采伐狩獵(《册府元龜》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二》)。
一般而言,皇帝陵寢和名山周圍是禁止采伐的,此類記載屢見於史書之中。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前漢高祖、後漢光武帝墳陵崩塌,童兒牧豎踐踏其上,於是下令漢高祖和光武帝的墳陵四方百步以内都禁止耕作、牧畜、采伐(《三國志》卷三《明帝紀》注引《魏書》)。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下詔,高祖李淵七世祖涼武昭王李暠墓旁二十户免除税役,充當陵寢守衛,也禁止畜牧采伐(《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還有一條史料,儘管無法判斷具體年份,但可見此事,即尚書省工部下令:“凡郊祠神壇、五岳名山,樵采、芻牧皆有禁,距壝三十步外得耕種,春夏不伐木。”*《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尚書工部》。《大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虞部郎中》云:“凡五岳及名山,能藴靈産异,興雲致雨,有利於人者,皆禁其樵采,時禱祭焉。”
道觀設置長生林一類的境域,可視作是歷代王朝施策的延續。但禁止道觀所在山林的漁獵則值得引起注意。玄宗有着限制殺生的意圖。《戒律鈔》卷四—六《衆戒及願念合一千一百條》所收戒律也禁止殺生,如《老君百八十戒》中稱:“不得妄伐樹”、“不得教人漁獵、傷害衆生”(卷五,6-945上)。天台山設立“禽獸、草木、長生之福庭”,*孫綽: 《遊天台山賦》(《文選》卷一一)云:“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可以説是動物、植物、神仙的樂園,也含有《戒律鈔》所云“放生度死”(卷四《六度生戒》,6-937中)的意義。按玄宗對李含光的敕命所言,茅山是真仙居住的華陽洞天,“精潔”最應重視。由此可見,除了“放生度死”以外,也有將清淨洞天與俗界隔絶開來的意義。
如此一來,道觀中清淨的空間和賤俗的空間分隔開來。道觀周圍被長生林之類的放生、清淨的境域包圍起來,此外則附有莊田、碾磑之類的生産設施。當然並非所有道觀都是如此。正如《科戒營始·置觀品》中提到天尊殿一樣,“其廣狹脩闊,任時所爲,不定常式也”(卷一,24-745中),道觀也有各種各樣的形態。
不難想像,以此類道觀爲舞臺的道士,日常所爲必然是以修行和儀禮爲主。若是如此,那麽支撑這種日常信仰的經濟基礎又從何而來呢?
三、 道觀的經濟與戒律
1. 關於所有權
道觀的建築、附屬的莊園、碾磑、净人、奴婢、家畜的所有究竟該如何認識呢?《戒律鈔》引《千真科》對此有所説明:
共居觀舍、堂殿、園林、田地,三寶衆(有),殿屬天尊,堂屬道士。若其營造,尊卑有等。其私房是道士自造,廣狹等級,出自己身,生前由身處分。若死後而無付囑,從衆施爲。若白衣童子自所營造,得度之後配别處者,亦聽許自己處分,唯地屬三寶,不得改動。(卷一三,6-986中)*《戒律鈔》中的“三寶衆”,《洞玄靈寶千真科》作“三寶衆有”(34-373上)。
道觀的建築、園林、田地都爲“三寶衆”也即道士所共有。建築中的殿屬於天尊,堂則屬於道士。《科戒營始》談及天尊殿規格時同樣稱:“聖人所居稱殿,凡世所處,通名爲堂。”(卷一,24-745中)*《科戒營始》卷一云:“夫三清上境及十洲五岳,諸名山或洞天,並太空中,皆有聖人治處。”(24-744下)這裏的“聖人”指仙界諸神、真仙。建築中也存在尊卑等級。但是爲道士和作爲道士見習的童子*《戒律鈔》卷一云:“《太真科》曰: 童子,一將軍籙。男女八歲至十九,皆爲童子,動而蒙昧,漸染玄風。”(6-967中)所造的私房,則各自可以加以處分。當然土地依舊歸三寶所有。
道觀的戒律原本是禁止道士占有田地、園林、奴婢、家畜的。《戒律鈔》引《千真科》反復申明此戒律。如“出家之人,清堂虚室,躭著既甚,有十惡累”,所謂十惡累包括廣占荒野,别蓄田宅;種植園林;貯積絲綿穀帛;蓄販奴婢;愛養六畜;貪聚八珍;好樂玩物;雕飾帳帷;衣着奇异;財寶彌勤,“此之十事,於身不得,爲清虚”(卷一三,6-986下)。又云“道法清虚,不希名利,閑居静室,謂曰仙家”。如果弟子多蓄錢財、寶貨、牛馬、奴婢,耽著不已,則是“斷三寶原,奪衆生福”(卷一三,6-984下)。正如所謂“清堂虚室”、“道法清虚”那樣,道法以及道觀生活都以“清虚”爲價值取向,而蓄財則與清虚是相違背的。
即使擁有法師的地位亦不例外。“法師宣化天下萬民,是救蒼生之道,不得貪財傳奴婢”(卷二引《玄都律文》,6-929上)。此外如法師破戒,驅使弟子沽酒買肉,販賣牧牛養馬或從事邪淫等行爲,弟子當諫言稱:“以此所作,非天尊行,某不敢爲師。”(卷三引《千真科》,6-935中)
但是,在處置道觀的共同財産或道士蓄財方面,也設有例外。如信徒布施的“田宅、園林”,爲人侵奪,則“報本捨施主,令其轉貨”(卷一三引《千真科》,6-987中)。關於布施的田宅、園林的所有權,引發了不少問題。往前追溯,南朝宋時范泰曾將“果竹園六十畝”布施給自己興建的祇洹寺,但在其死後,他的第三子范晏爲奪回此地而引發了糾紛。*《高僧傳》卷七《宋京師祇洹寺釋慧義傳》。此條材料,由吉川忠夫氏提示。雖然與布施的情況有所不同,唐律實際上並不禁止買賣皇帝的賜田(《唐律疏議》卷一二《賣口分田·疏》)。有一種慣例,即典當的田宅即使經過漫長歲月,也能被追回。*加藤繁: 《支那經濟史考證》上卷,東洋文庫,1952年,第283—293頁。那麽,布施的田宅、園林在買賣上或許也有某種慣例,需要獲得布施者的同意也未可知。關於道士個人的蓄財問題,則“若諸弟子,恒懼天寒、時亂、飢荒等事,貯積絲綿、帛布、五穀,以備時急惠施者,不禁也”(卷一三引《千真科》,6-987上),也即爲了應對天災、戰亂、飢饉而作準備是可以被容許的。
綜上所述,道觀的建築、田宅、園林都爲道士所共有,道士個人蓄財爲戒律所禁止。正如《正一威儀經》(《道藏》五六四册)所云:“莊田碾磑,家人使役,五行什物,六畜器具,果木華藥,一切所須,皆共愛惜。”(18-258中)共有財産必須小心使用。那麽,這樣的道觀中共同生活的經濟基礎是怎樣的呢?
2. 宗教儀禮
如前所述,道觀主要依靠布施纔得以建立。《戒律鈔》中反復强調,營造道觀有莫大的功德。比如《造殿堂緣》中稱:“建立靖觀,令人代代門户高貴,身登天堂,飲食自然,常居無爲。施一錢以上,皆三十二萬倍報。”(卷一二引《大戒經》,6-979上)不僅道觀如此,還涉及道士的日用品。《善功緣》稱:“若能建立宫觀、壇靖、經室、齋房、厨閣,供養道士,衣服、卧具,悉以供給,如斯之功,受報天宫,衣食自然。”(卷一二引《本相經》,6-982中)
經典傳授時所需的法信、齋醮和上章等儀禮所需的種種信物都是道觀生活中物資基礎。不過,關於法信、信物,戒律中也有所規定。傳授經典時,弟子需向老師交納法信,“爲一切作福田,不得師自私用,其罪深重”(卷一引《自然訣》,6-925上~中)。《戒律鈔》卷一《折傳鈔》對法信的“折傳”亦即分配有詳細規定。法信的分配方案,按傳授三洞經典——洞神、洞玄、上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傳授上清經所得法信,“三分散之,一分投於山栖以卹窮乏之士,一分供己法服,一分以爲弟子七祖立功”(卷一引《四極明科》,6-924中)。上章儀禮中的信物則按上章種類而在量上有所差异,可交納香、席、紙、筆、墨、書刀、米、錢、布等。但“奏章已後,其信物多,可施貧者,宜行陰德,不可師全用之,十分爲計,師可費入者,三分而已”(卷一一,6-975下)。
爲宗教儀禮而布施,當然以皇帝的場合最爲宏大。如天寶八載(749)的《修造紫陽觀敕牒》(《茅山志》卷二,5-558中)稱:*《修造紫陽觀敕》是回復接到修建紫陽觀命令的丹陽太守林洋上奏而由中書門下頒下的玄宗的敕命。參中村裕一: 《唐代制敕研究》,汲古書院,1991年,第520—521頁。
觀内什物五行等。右觀家先貧,什物數少,昨修功德使程元暹奉敕支供黄籙齋外,有回殘銀一百兩,令臣(丹陽太守)分付觀内徒衆,將回市所欠什物等,並令充足。
玄宗在紫陽觀爲供奉祖先所舉辦黄籙齋後,*《大唐六典》卷四《尚書禮部·祠部郎中》列舉七種齋,“其二曰黄籙齋,并爲一切拔度先祖”。還剩下“回殘銀一百兩”,將這本該返還的餘錢又分給道士,用來購買日用品。這一百兩就有布施的意味。
又如,有着首都長安城中權威道觀太清觀背景的張萬福,在《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説》(《道藏》九九册)卷下《明科信品格》中提及了在道觀中傳授經典所需的各種法信。首先,張萬福對弟子給予老師法信的根據作了説明。“凡道由心得,心以道通,誠至感神,神明降接,是以古人求心,末世求財,古人非心不度,末世非財不仙。是故須財以對心,明心而財見。”(32-193中)在末世的當下,只有用“財”纔能作爲表現誠心的法信。那麽,收納法信的法師又如何呢?“其所用法信,事畢,並依經散之也。伏尋經中,信物或云出自神州,非世間所有。今請以某物準當者,將欲引接於貧賤,使同入道也。”(32-196中)法信屬於上天,不當留於世間,所以應施捨給貧賤之人,以引導其信仰。
約定道法的法信,有七寶、金錢、金龍、玉龍、金魚、玉魚、金羊、玉雁、羅錦等物。張萬福又列舉了可能在當時長安流行的種種法信: 名衣上服、牀帳卧具、茵席幾杖、玩弄器物、缾罐履屩、車馬奴僕、莊園屋宅、金銀珠玉、綾羅錦綺、錢絹布帛、釵梳環釧、米麥花果、供養法具、繩牀坐褥等。除將這些物品布施給“道”和“師”外,還可“立觀度人,寫經造像,放贖生命,拯濟飢寒,免賤爲良,弛囚宥罪,廣行慈救,大設悲田”。那麽,拿不出法信的貧賤之人又是怎樣的呢?“若貧賤之人,供師使役,不憚苦辛,遠近陪隨,給侍香火,修營觀宇,植種果林,墾闢田園,栽蒔花藥,捨身落髮,剋己自勞,毫分之間,無所恡惜,晝夜不懈,供事師尊。”(32-196中~下)
順帶一提,道觀還將宗教儀禮所剩餘金作爲本金,用以經營金融業。上引《修造紫陽觀敕牒》中,玄宗修建紫陽觀而剩餘的“回殘錢二百四貫二百八十五文”,根據敕命“便賜觀家,充常住”(5-558中)。然“臣(丹陽太守)又與觀主道士劉行矩等商量,請於便近縣置一庫,收質每月納息,充常住。其本,伏望長存。”在鄰近縣城中(也即市街地)經營質鋪,其所獲利息充作道士的日常生活費用。這便成爲了茅山紫陽觀的經濟基礎。當時佛教寺院經營金融業就號稱“無盡”,*道端良秀: 《中國佛教史全集》第四卷,書苑,1985年,第114—133頁。道觀經營的質鋪也並無太大區别。
上引《科戒營始》在描述道觀時,便已提及附屬的莊園和碾磑。下面討論莊園的經營。
3. 莊園和勞動
a. 莊園
《科戒營始·置觀品》對莊田、碾磑的經營有所説明,“科曰: 莊田碾磑,常住所資,隨處訪求,依法置立。其中區别淨穢,檢校營爲,皆適當時務令得所”(卷一,24-747上)。莊田碾磑中如何判别净、穢並不清楚。恐怕勞動本身即是按照净或穢來區别的吧。
作爲道觀生活資産的莊田碾磑部分由自購而來,但更多的是依靠富裕家庭和皇族的布施。南朝時已見賜予道觀田地的事例。*《中國道教史》第一卷,第559頁。唐太宗貞觀九年(635),爲王遠知在茅山造“觀一所”,並賜田。*《茅山志》卷二二《唐國師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觀碑》(5-640中)。《舊唐書》卷一九二《隱逸·王遠知傳》。天柱觀在中宗時也得到賜予的“觀莊一所”(《洞霄圖志》卷六《天柱觀記》)。之後玄宗在天寶二年(743),對長安太清宫、洛陽太微宫兩道觀“各賜近城莊園各一所,並量賜奴婢等”(《册府元龜》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二》)。
如所周知,碾磑可利用水力來脱穀、磨面。北魏末年,碾磑作爲莊園的附屬設施以華北大地爲中心普及開來。*西嶋定生: 《碾硙の彼方》,《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五章,1966年。首版爲1946年。馮佐哲等譯: 《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 農業出版社,1984年。北朝以降,莊園、碾磑、奴婢被視爲一體。從北朝到唐代的皇帝,以莊園、碾磑、奴婢賞賜立有戰功的武將和佛寺的例子不勝枚舉。不過,《科戒營始》和上引《正一威儀經》提及莊田、碾磑,而《戒律鈔》中只談到莊田而未見碾磑。
b. 道觀的勞動者——净人、奴婢
在道觀的莊田中負擔勞動的究竟是哪些人呢?《戒律鈔》引《千真科》云:“出家之人,務在簡静,非法行事,動則落邪”,並稱有十種行爲是“非法”,其中第四種是“行等淨人、躬執耕稼”(卷一三,6-984中)。農耕是净人的工作,道士參與即是“非法”。又引《千真科》云:“亂衆之人,多不依正法。飲酒醉亂、輕欺上下者”,對這些道士的處罰,首先是罰錢米,或以財物補償罪孽。如不交納罰金,則需杖罰,除剥奪財帛,用以供奉道觀外,還可“苦役治地(‘治’的土地),斬伐草木,鋤禾收刈”(卷一三,6-984下)。農耕是對破壞道觀秩序的道士實施的苦役。如前所述,道觀的空間對宗教儀禮、道士居住、净人和家畜的居所有明確的區隔。同樣,宗教和農耕也有區分。
所謂“净人”的稱呼,在《戒律鈔》中幾乎未曾提及。《戒律鈔》依據的《千真科》本身也只有幾次提及。想必是净人這種源自佛教的提法尚未融入(道教)的緣故。*《戒律鈔》卷一三引《千真科》云:“上德尊人,住持大衆,下小有過……於國王、妃嬪、眷屬、大臣、宰輔、俗人及兒女、小道士、淨人,宿新怨嫌之前,並不得呵責。”(6-984中)《洞玄靈寶千真科》又云:“科曰: ……或媒嫁净人、買賣奴婢及餘畜産。”然此條被《戒律鈔》卷一三(6-985上)引用時,“净人”作“爲人”。但《戒律鈔》引《千真科》下文值得注意,“若有人將使人奴婢以供給者,悉不合受。其使人能齋菜持戒者,受也”(卷一三,6-987上)。這裏的“使人”,應等同於奴婢。使人、奴婢原本是不能作爲布施接受的,但如果使人能堅持菜食並遵守戒律,則可接受。佛教中的“净人”,主要指“已盡受五戒,奉齋修德”之人(《僧祇律》卷二九,《大正藏》卷二二,四六七中)。由此看來,“使人”可視爲净人。
在道教經典中頻繁出現的,與其説是净人,不如説是奴婢。道教中奴婢與家畜等同,是前世、現世罪孽的結果。《戒律鈔》云:“人身中,常有神,隨時上白人善惡。”並記述了從一百二十到三千六百條罪過對應的懲罰,“千八百過爲一患,患者,主爲奴婢、家出内亂”(卷一二引《玄都律文》,6-981下)。《科戒營始》亦云:“經曰: 奴婢下賤身者,從偷盜慳貪中來”、“經曰: 六畜生身者,從殺生抵債中來”(卷一,24-742下)。當時社會上對良人和賤人間的身份區隔十分嚴格,奴婢與家畜被同等對待。*關於奴婢和賤人,可參仁井田陞: 《中國身份法史》第八章《部曲·奴婢法》,初出1942年,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重刻。氏著: 《中國法制史研究 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年。濱口重國: 《唐王朝の賤人制度》,東洋史研究會,1966年。堀敏一: 《中國古代の身份制——良與賤》,汲古書院,1987年。道觀中的净人、奴婢、家畜也處於相同位置,奴婢也好,净人也好,都是賤人的身份。在道教經典中,都視爲對其罪孽的懲罰。
如前所述,道士有禁止買賣奴婢家畜的戒律。接受布施使人、奴婢,在原則上也是禁止的。《戒律鈔》對此反復申明,引《千真科》云:“非法之物,不得布施。問曰: 何爲非法之物?答曰: 牛馬奴婢、軍戎器仗等物是也。”(卷一三,6-985下)但道教對布施奴婢的態度並不一定。如成書於唐代以前的《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開度品》即記載有人布施衣物、田宅、奴婢、牛馬、車乘、卧具(卷一,6-82下、83上)。*《道藏》第一七四、一七五册。參任繼愈主編: 《道藏提要》,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255頁。從前面所述可知,張萬福將奴婢作爲法信之一,玄宗也把莊園和奴婢賜予長安、洛陽的道觀。不僅首都附近,如《修造紫陽觀敕牒》中亦云:“觀内,先有奴婢四人,小牛六頭,車一乘,見在”,雖還不能確定是否是布施而來,但可確定茅山紫陽觀中有四名奴婢和六頭小牛。
其實,唐律是承認奴婢存在於道觀之中的。《唐律疏議》卷六《名例·稱道士女官》云:“觀寺部曲、奴婢於三綱,與主之期親同。”三綱即執掌道觀的上座、觀主、監齋。疏中指出,道觀的部曲奴婢對三綱犯罪,就和世俗中部曲奴婢對主人的期親犯罪一樣,接受相同的懲罰。唐律中,奴婢、部曲都屬於賤人,部曲地位比奴婢稍高一些。目前尚無見到道觀中的部曲,但奴婢和“齋菜持戒”的使人、净人一樣,都屬於賤人,他們之間或者也有區别。
由上可見,無論是道觀還是道教教義,都與“良賤制”這種當時的社會結構相適應。但道觀對奴婢的處理方式與世俗社會有微妙的差异。首先,在戒律上,無論是道士買賣奴婢,還是道觀接受布施奴婢,在原則上都是被禁止的。其次,對待奴婢該如何處置,也有戒律上的規定。《戒律鈔·衆戒及願念合一千一百條》中的《老君百八十戒》云:“不得印奴婢面”(卷五,6-944中),《三百大戒》云:“不得扣奴婢面,傷其四體”(卷六,6-948上)。戒律禁止在奴婢面上紋印,毆打面目,傷害四肢。而世俗社會則對逃亡的奴婢采取入墨紋面的懲罰,主人毆打奴婢,也不會被問罪。*參上頁注①。如此對待奴婢,是當時的習慣。稍微往前追溯,即可看到北魏末年的高謙之的事例,“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魏書》卷七七《高崇傳附謙之傳》,《北史》卷五《高道穆傳附謙之傳》)。高謙之對待奴婢的處理方式,其實是一種特例。這意味着,道觀戒律中對待奴婢的態度,和高謙之所謂的“俱稟人體”存在同樣的認識角度。而張萬福主張利用庞大的法信購買賤人再放免爲良人,也含有从賤人的地位上予以救濟的意義。
值得留意的是,道觀除净人、奴婢等賤人之外,還有負責營繕清掃建築的人。玄宗在天寶七載下令,有洞天的名山(其天下有洞宫山)都置壇和祠宇,並度道士五人,“取近山三十户,蠲免租税差科,永供灑掃”(《册府元龜》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二》)。當時,有華陽洞天的茅山也“紫陽觀取側近百姓二百户,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户,並蠲免租税差科,長充修葺灑掃者”(《茅山志》卷二,5-559中;《册府元龜》同上)。如前所述,名山、皇帝陵寢周圍地域禁止采伐,附近民户也免除税役,而去管理祠廟陵寢。對道觀的做法,也和名山皇帝陵寢與長生林的關係一樣,都可看作對歷代王朝政策的延續。但這些民户與净人、奴婢不同,是承擔税役的良人,只不過是以營繕清掃道觀代替了税役而已。*參濱口重國: 《唐の陵·墓户の良賤に就いて》,前揭書外篇第一篇。
此外,張萬福還列舉了貧賤者的法信,如從事修營觀宇,植種果林,墾闢田園,栽時花藥,供師使役,遠近陪隨等勞動等。
由此可見,道觀之中,不僅有道士專心修行和舉行宗教儀禮,還有人在附屬於道觀的莊田上從事農耕、維持建築。這些人中有净人奴婢之類的賤人,還有王朝免除税役的附近良人,更有提供勞力從而代替法信的信徒。道觀中的宗教和勞動是分隔開來的。道觀中,有宗教的清淨的空間,也有從事勞動的净人家畜和連接世俗的空間,二者截然有别。這意味着,道觀空間上的區分,道士與賤人的區分,和宗教與勞動的區分是重合的。當然,不難想像,這個時代還有親自農耕或從事其他勞動的道士。但在《戒律鈔》中描述的道觀中,戒律規定道士專心從事祈求神明的修行,過着清淨的生活,農耕則由净人奴婢承擔。
四、 結 語
因從南北朝到隋唐的戰亂而荒廢的道觀不在少數。如衡岳的招仙觀。招仙觀相傳可追溯至南朝宋,唐貞觀二年(628)則被稱爲“亂後荒涼”(《南岳小録》,6-863上)。朱法滿在《戒律鈔》中引《千真科》云:“時在飢荒,又屬離亂,各欲隨豐逐静。能有守固,衆可分科財物,以與守固之人也”(卷一三,6-985下),可見面對飢饉和戰亂,道觀的共同生活崩潰,道士也各自離散。南北朝時即存在的道館、道觀,在唐高宗時被急速整備。不僅在首都和地方上興建了許多道觀,還下令保護道觀周圍的地域環境,又爲維持道觀提供了莊園和勞動力。8世紀前後的朱法滿和張萬福在立場、方法上都存在差异,但都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對道觀共同生活的戒律進行了再整理。
受當時社會結構的影響,道觀之中也有良人和賤人的區别。這種道觀和社會的關聯性,還體現在師徒關係上。師徒關係,是道觀共同生活秩序的基軸。雖然道觀的道士出家,即是脱離了家庭,但師徒關係卻常被比喻成親子關係。這種比喻在《戒律鈔》中隨處可見,如“律曰: 弟子見師,敬事如父母,師主見弟子,念之如赤子”(卷三,6-933下)。關於道觀與社會的關聯性,需要另外撰文詳加探討。
還有一點需要説明,道觀的經濟、戒律,説是在佛教寺院壓倒性的影響下形成的也不爲過。而且與佛教寺院的戒律一樣,道教戒律也受到唐代律令的深刻影響——如禁止道士私蓄奴婢、田宅、奴婢,禁止道觀接受布施奴婢等*參諸户立雄: 《中國佛教制度史の研究》,平河出版社,1990年,第202—203、389頁。仁井田陞著,池田温編集代表: 《唐令拾遺補》,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年,第1004、1334頁。——道觀和國家制度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裏僅僅根據道教經典,對唐代中期道觀的空間、經濟、戒律作一描繪。其他問題則是今後研究的課題。
【补遗】 本文論述中,主要記述道觀共同生活如所有、勞動等相關戒律的《戒律鈔》卷一三《雜科》,幾乎全部引自《洞玄靈寶千真科》(《道藏》第一五二册)。本文發表後,又認識到《千真科》全部的109條有中近80條是將7世紀釋道宣所編撰的《四分律删繁補闕行事鈔》(《大正藏》卷四)按照道教教義置换改寫而來。《行事鈔》將印度傳來的《四分律》進行了與中國風土相稱的改編,在中國全境産生了極大的影響。本文所敍述的道觀共同生活的戒律,是在受到佛教壓倒性影響下形成的。下面試舉一例,本文中談及的“遷化堂”,即是《行事鈔》卷下之四《贍病送終篇第二十六》中所見的“無常院”的翻版。
若依中國本傳云,祇桓西北角日光没處爲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中……其堂中置一立像,金薄塗之,面向西方。其像右手擧,左手中繋一五綵幡,腳垂曳地,當安病者在像之後。左手執幡腳,作從佛往淨刹之意。
可參拙稿《道観における戒律の成立——〈洞玄霊寶千真科〉と〈四分律删繁補闕行事鈔〉》,收入麥谷邦夫編: 《中國中世社會と宗教》,道氣社,2002年。
附記:本文原載吉川忠夫主編:《唐代の宗教》,京都:朋友書店,2000年。
* 本文日文版所引《道藏》所標注頁碼爲綫裝本之頁碼,現爲搜檢方便起見,改爲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本《道藏》,1988年。卷次、頁碼標注方式按原版爲文中夾注,並依册數、頁碼、欄的方式排列,如“9-378中”,即表示《道藏》第9册第378頁中欄。——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