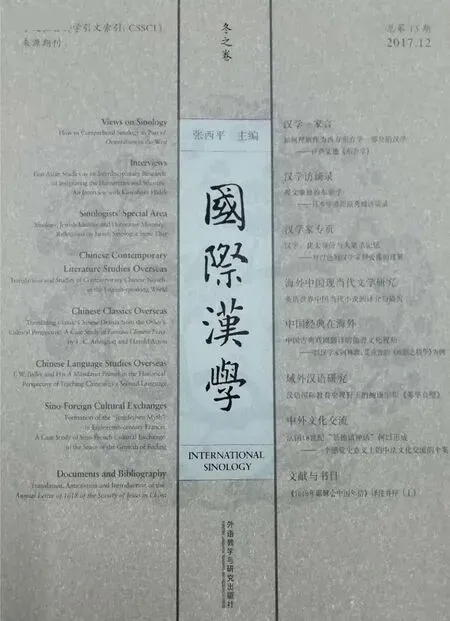评葛桂录著《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英国卷》(2016)—兼论英国作家中国题材创作的阐释模式以及中英文学交流史的写法*
2017-01-28□
□
一部中型的中英文学交流(或称关系)通史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这本是个不易回答好的问题,因为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前,笔者尚未见到中英两国有同一课题通史类的著作出版。最早关注该领域并进行著书立说的,是英美学者,但英美学术界对此的兴趣似乎并不太大也欠持久。①据初步统计,中英文学关系的开创性研究有:Marie E.Meester, Oriental Influence in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Heidelberg, 1915); Louis Wann, “The Oriental in Elizabeth Drama,” Modern Philology, XII (1915), pp.423—447; Louis Wann, “The Oriental in the Restoration Dram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2.(Madison,1918); George C.Martin, “China in English Literature.”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China Society at Caxton Hall, Westerminster, on December 4, 1916 (London, 1916)等,但总体数量不多。然而,西方学术界在英国或西方的中国观,以及中英(欧)文化关系方面的著述颇丰。例如:Raymond Dawson,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Jonathan D.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8.William W.Appleton, A Cycle of Catha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James Bromley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Intercourse and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China from the Year 1600 to the Year 1843 and a Summary of Later Developments.London: Curzon Press, 1909.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 Century (1925).Trans.J.C.Powell.New York : Barnes & Noble, Inc., 1968.,等等。这让中国学者有了后来居上的机会。关于中英文学交流的断代史或者以其中某一两个方面为主题的个案研究著作,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末期后始有刊布。例如,方重著《英国诗文研究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中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部分,陈受颐著《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的中英文学关系部分(如《鲁滨孙的中国文化观》《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里面大部分内容与中英文学交流有关)、《中国文化在英国》②按本著书名页前的说明:“整理自范存忠先生193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系统阐述中国文化对17、18世纪英国的影响及其源流。”(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钱钟书英文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内含长文“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以上著述大都为著作者在民国时期留学英美时的学位论文或以此为基础改写扩充而成,③其英文原文大多被选编入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而且均以17、18世纪的中英文学关系,具体地说是上述时期中国对英国文学文化的影响或者说英国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接受为研究对象。在写作方法上,他们都以扎实的外文(除了英文外,有时为了溯源还需要法、德、拉丁文等西方语言的能力)与原典文献功底为基础,从中英乃至中欧文学关系的重要个案研究入手,从影响、接受、渊源、媒介等方面串联起一个时代的中英文学关系史。总体来说,这是个起步较晚、迄今成果并不算丰硕的研究领域。陈受颐在其《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的《校印后记》(撰于1969年)中指出:“……十多二十年前,中西文化接触史课题的试探,还是史学研究园地里的比较荒芜的小角落,所以几根弱草,也许惹人注意罢了。”①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234页。中英文学关系的著述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沉寂了较长一段时期,②其实也未完全沉寂,范存忠先生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多篇关于中英文学关系的论文,如《〈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中国的思想文物与哥尔斯密斯的〈世界公民〉》(《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始有周珏良先生的《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1987)长文,③参见《周珏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59—199页。该文大部分内容都同文学有关,从中世纪一直谈到1949年之前,在结语中还点到了新中国三十年的成绩,而且该文是笔者所见首次以中英双向交流的模式探讨中英文学文化关系的,既谈中国文学文化对英国的影响,也谈英国文学文化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并展望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前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版了若干部关于中国文学传入外国并得到翻译、评介与接受的著作,其中有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8)、马祖毅等的《汉籍外译史》(1997)、《中国翻译史》(1999)等,里面也都有关于中英之间文学译介的内容。尤其是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1992),时间跨度从17世纪至当代,内容上涵盖中国知识以及中国古典与现当代各种体裁文学在英国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兼及英国文学里的中国题材与中国形象(中国题材与中国形象的内容仅限于17、18世纪),不管在原典实证、学术规范乃至学术视野的广度与研究的深度上都是同类著作中较好的。但本著在体例上也有其缺陷,如19世纪以后英国文学里的中国题材作品与中国形象塑造、英国的华裔文学创作以及民国以来的留英旅英作家的英文、中文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传播工作所做的贡献均付阙如。这个遗憾部分地被赵毅衡的《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2003)弥补。该著以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的代表性人物为纲来写,每篇处理一位。其中与中英交流有关的人物,第一部分“西游记”中有徐志摩、傅斯年、老舍、邵洵美、刘半农、卞之琳、萧乾、蒋彝,第二部分“东游记”中有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瑞恰慈(I.A.Richards, 1893—1979)、狄金森(G.Lowes Dickinson, 1862—1932)、毛姆(W.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奥顿(Hugh W.Auden,1907—1973),第三部分“梦游记”中有约翰·凯利(John Cayley)、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以及在第四部分“游之余”中讨论西方的华裔文学(中国人用西文写作)与华文文学(中国人用中文写作),其中不乏华人旅居英国时的文学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2004年间,葛桂录连续出版了《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史稿》《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三部著作,虽然细读三著后,我们会发现上述著作在史实考辨与论述准确性上并非没有问题,但在同类的课题上,其研究的时代跨度之大、处理的个案之多,均属史无前例。2010年,吴格非的《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出版。该著以中英文学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设立章节,共收录8位英国人(有汉学家、作家、人文学者)与16位中国人(翻译家与作家),以此来探讨百年中英文学关系的三大内容:英国学者与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接受、中国作家在英国开展的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作者在后记里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主张尽可能地把文学关系还原为一种单纯的接触和交往,或者说,只把它当成作家和作家之间的事……接触和交往有两种形式,一是作家之间的事实往来,再就是作家之间以作品为媒介进行心灵的沟通……”按此思路,文学关系的问题确实“好对付得多”,似乎写好相关人物传就行,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也同时剔除了国际文学交流中大量有趣而重要的研究内容,诸如旅行与游记、翻译与改编、报刊与出版社等文学交流的媒介与文学社会学的关注点。
《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钱林森、周宁主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的“总序”提出,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学者要明确“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和“为何研究”诸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占有充分、完整材料的基础上,对双向‘交流’‘关系’‘史’的演变、沿革、发展做总体描述,从而揭示出可资今人借鉴、发展民族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①葛桂录:《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页。一要尽量完整地收集梳理第一手素材,二要勾勒描述完整的“史”,三要在前两项基础上恰当地“论”。“总序”最后进一步指出,“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要点在‘文学交流’,因此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双向阐发’,带着这个问题进入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译介、传播的问题,中外文学相互认知、相互影响与创造才是问题的关键。……文学交流研究应该从一般的‘表象事实’的描述深入到‘文学事实’内具的各种‘本相’的探讨和表达。”②同上,第12页。大致参照以上标准,《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以下简称《中英卷》)著者把中英文学关系研究归纳为三类课题:1.文学文本的跨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2.作家与异域文化及文学关系研究,3.作家作品里的异域题材及异国形象研究。第一类在国际文学关系中属于媒介学领域,大致是对“表象事实”的描述。所谓“由表及里”,弄清表象事实显然是更深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二、三类大致属于在各种文学交流媒介基础上的对文学“本相”的探讨和表达了。
如果从现有同类著作的编撰经验出发,再对照丛书主编与著者对本著的期待,让我们来评价面前的这部500余页的专著,就会发现该著基本上完成了迄今首创的对自中世纪以来600余年的中英文学交流进行系统研究的使命。本著共6章,第一、二章(占全书46页即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非常简略(或可称编年式)地勾勒14—18世纪的中英文学交流,以中国知识通过“人(旅行者)及其见证(游记)”及少量的译介为媒介传播到英国为主要论述对象。启蒙时代是中英文学交流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的文学文化对英国的输出与影响要大大多于中国对英国文学的输入与接受的一个时期,本应大书特书。然而,重要如罗伯特·勃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四大卷不朽巨著《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对当时流传欧洲的中国知识旁征博引,著者仅腾出九行的篇幅予以简单带过。另外,被公认为18世纪英国文学中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中国题材作品—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1762),也同样“吝啬”到仅用了短短一个段落予以概述。不过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一套丛书的各个分册,一般都会有较严格的篇幅限制,难以全面展开做专题论述。另外,关于这一时期的中英文学关系史已有比较全面而成熟的研究,如著者本人尚未有基于新材料、新思维的原创性研究,③本部分著者论述最为详尽的是“英国中世纪想象性游记里的中国印象”,占第一章全部三节中的整整一节,专门研究《曼德维尔游记》中有关中国的内容。然而,有些遗憾的是,本书关于这部英国的中国形象源头的专论,所依据的文本仅是该书一个当代普及性英文读本(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An abridged version with commentary.By Norman Denny and Josephine Filmer-Sankey.London: Collins, 1973),或者说是这部欧洲中世纪名著的节选本。按该书的“导言”中有关选编内容的介绍:“原著有34章[笔者手头有一部出版于1727年的英文本:The Voiage and Travaile of Sir John Maudeville, Kt.Now published entire from an original MS.in the Cotton library.London, 1727。全部章节为31个,其中有关中国部分5章,即第19—23章],大约8万字。……目前的版本,保留了原著的近三分之一。本书的读者对象是那些不愿意花太多功夫即可领略曼德维尔大概的人们。为了给读者一种完整性的印象,编者采用‘连接叙述’来填补空缺。”(“Introduction,” p.13)这个节选本不仅篇幅大大缩短,而且对章节进行了调整,原34个章节被调整为9章,有关中国部分由原来的5个减为3个。这种普及型的读本似乎不应作为《中外文学交流史》这样严肃学术著作的立论基础。另外,本节有部分内容采自上述节选本的《导言》部分,如达·芬奇由佛罗伦萨迁往米兰时随身携带《曼德维尔游记》,莎士比亚和班扬均在其作品中借鉴此书,以及相关的引文,等等(见《中英卷》第5页),著者似应说明史实的具体出处。借用学术前辈的研究成果予以概述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第三章用了一百余页的篇幅探讨了中国典籍在19世纪英国的译介与同一世纪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作品,以及该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英国形象与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关于中国典籍的译介,探讨了本世纪英国汉学三大“星座”—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德庇时(J.F.Davis, 1795—1890)、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以及其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与思想经典的翻译。著者除了介绍这些汉学家的翻译活动以及这些译著的前言、后记、书评等周边文本外,开始有了较大篇幅的内容介绍与译文分析,但略显遗憾的是转引偏多,且多处大段引用他人观点代作评述与总结。①如本部分两处引用“马戛尔尼日记”(“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引用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 1655—1731)的《论中国人的政策和政府》、引用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关于中国人的特性、引用谢林(F.W.J.Schelling, 1775—1854)的《神话哲学》 (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 1842),均属转引。参见葛桂录上引书,第98、100、103、108页。另外,关于理雅各一节,较大量地引用岳峰著《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参见葛桂录上引书,第54页。在论述卡莱尔一节中,先后采用《英雄与英雄崇拜》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1841)的两种中译本,但并未说明其必要性。参见同上第117、118页。关于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题材作品,著者介绍了多部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版的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游记、②但著者统称这些游记“彻底打破了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思想家]们苦心经营的中国神话”(参见葛桂录上引书,第85、86页)未必准确,至少本次使团的官方旅行记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37—1801)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1797)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时代欧洲仰慕中国的延续。浪漫主义诗人与作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兰陀(Walter S.Landor, 1775—1864)、王尔德(Oscar Wilde,1856—1900)、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等等。其中关于王尔德、卡莱尔与道教、儒教之间关系的论述,较好地体现了著者在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上的个案研究功力。
著者在中英文学交流研究上用力最勤、成绩最大的当属对20世纪上半叶的双向研究。这部分是本著的重中之重,占全部六章的三章,篇幅更是占全书的近五分之四。每一节处理一个特定的人物或文类专题,几乎都能成为独立成篇的个案研究论文。在本著处理的三个阶段(18世纪及之前、19世纪、20世纪)中,也只有这个阶段中英的双向交流至少在篇幅上基本平衡(如借用韦勒克 [René Wellek, 1903—1995]“文学外贸”的说法,19世纪之前在国际文学“贸易”上中国都是重要的“出超”国,出口大大多于进口)。第四章讨论中国文学在英国的翻译,前两节专论翟理斯与阿瑟·韦利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后面三节分别就中国古典诗文、小说、戏剧及中国现代文学在英国的翻译进行勾勒描述。第五章重点探讨了七位20世纪英国作家中国题材的创作,分别为专门描写伦敦莱姆豪斯(Limehouse)中国城的托马斯·柏克(Thomas Burke, 1886—1945)、创作傅满洲(Fu Manchu)系列小说的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 1883—1959)、撰《约翰中国佬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1901)的迪金森(Lowes Dickinson, 1862—1932)、撰《在中国的屏风上》(On the Chinese Screen, 1922)的毛姆、撰《爱美者回忆录》(Memoirs of an Aesthete)的阿克顿(Harold Acton, 1904—1994)、英国文学批评家瑞恰慈以及著名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1945)与《1984》(Nineteen Eighty-Four, 1949)的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据笔者所知,其中关于托马斯·柏克描写伦敦莱姆豪斯中国城的系列作品,与乔治·奥威尔创作中的中国元素,国内外除了个别相关的传记及文章有零星介绍外,均未有专题的研究。第六章讨论英国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接受情况。著者研究的模式比较独特,前两节专论王国维、林纾与英国文学,第三节聚焦这一时期中文报刊上的英国作家专号,后面四节以当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四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学衡派)为对象,讨论他们(同时也包括这些社团的期刊)与英国文学的关系。这种体例设置照顾了文学媒介学的更多方面,比吴格非的仅以人物为线索的叙述要合理些。
综上所述,在这部中英文学交流史里,著者对各个时期中英文学(包括人员)之间的接触、翻译、介绍与研究,以及两国作家在这些文学交流媒介基础上的改编与创作进行了论述,尽量还原了种种跨文化、跨语言现象的“事实联系”,并对其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谓既见识了树木,也领略了森林,既把握了现象(事实),也由表及里,看到了其成因、演变过程、后果、效应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文学、文化问题。孟华教授在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中指出: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从原先单向度研究发送国文学的影响,发展到对发送者与接受者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且将对接受者主体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从过去单纯考据式的研究方法,发展到充分利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综合性研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描述现象、勾勒史实,而是在掌握确凿的“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注重以批判的精神质疑[阐释]文学、文化交流中的种种现象,挖掘隐含其中的内在逻辑,探讨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当今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已成功地引入了问题意识,引入了文学批评的精神。①孟华:《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如以此高标准去衡量本著,笔者觉得著者首先是充分地意识到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当代转向”,同时也是努力地按这个方向去做的。不过,对这两个文学大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史做全面研究,要以上述的要求为标准去真正做到并且做得比较圆满确实很难,因为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毕其一生都可能难以达到的苛求—既需皓首穷经,又要有较高的理论与方法论素养。下面,笔者对本著的不足或可商榷之处也分若干方面提出,以供著者及同行参考。
一、本通史考察的下限为民国,把英国的“二战”以后以及中国1949年后六十余年排除在外,同时,本著学术史的考察与研究截至本著出版前十年的2006年。笔者觉得著者在这两项上的做法均值得商榷。
中英之间的文学交流虽然在“二战”后尤其是中国进入“新时期”之前的三十年,由于意识形态与东西方阵营的对立,确实相对沉寂了,但从来没有完全停止。“新时期”以来的三十余年更堪称第二个活跃期,人员的往来、学术的研讨、相互之间的译介以及中英文学中彼此塑造的文化形象,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可能都是空前的。但本阶段的中英文学关系确实研究不多,力作更是难得一见。如著者能不畏艰辛、披荆斩棘来开辟这块处女地,将有开拓者之功,同时也给本学科本领域提供新资料、新文献与新见解。由于著者把“当代”排除在外,中英文学交流的一个独特的领域—英国的华裔或华人文学创作就无法进入本书。虽然英国的华裔/华人文学并不像美国那样历史悠久、成绩斐然,但也出现了蒋彝②蒋彝(1903—1977),笔名哑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1933年开始旅英,英文作品有二十余部,其中最著名的是《哑行者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 etc., 1937—1972 )系列作品(十二本),还有介绍中国绘画、书法、熊猫等的作品,以及《重访中国》(China Revisited, 1977)。、萧乾③萧乾(1910—1999),1939—1946年旅英,任伦敦大学讲师、剑桥大学研究生、《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随军记者。在英期间著有并出版了两部英文著作—《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2)、《龙须与蓝图》(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the Blueprints.London: The Pilot Press, 1944),以及大量的关于英国的通讯,这些通讯均刊登于当时的《大公报》(香港、重庆)上。、叶君健④叶君健(1914—1999),1944—1949年旅英,就读于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在英期间出版了英文著作《无知的和被遗忘的》(The Ignorant and the Forgotten.Sylvan Press, 1946)、《山村》(The Mountain Village, 1947)及从中文翻译的小说集《三季及其他故事》。、凌叔华⑤凌叔华(1900—1990),中国现代女作家,1946—1990年旅英,在英期间著有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 1953)。、张戎⑥张戎(Jung Chang,1952— ),1978年留学英国的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后在英国专事创作,已出版自传体家族小说《鸿》(Wild Swans, 1991),与其历史学家丈夫Jon Halliday合著关于宋庆龄、毛泽东、慈禧太后传记三部。以及人数更多的旅英华文作家的创作,有些作品还曾是当时英伦的绝对畅销书。①关于伦敦的华文文学作家,可参见赵毅衡:《欧洲的晦涩:新海外文学笔记之一》,载《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上海: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92—298页。另外,“新时期”以来,中英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显示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近十年来,不管是长时段的宏观观照还是某个专题的个案研究,不管是专著、期刊论文还是硕博士学位论文,均源源不断,尤其是关于英国汉学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研究更是作品迭出,不乏佳作。当然,著者对以上两个方面的缺失并非没有意识到。其在导论部分第1页有个注释:“本部分研究综述的资料截止时间是2006年左右,近几年学界关于中英文学交流课题研究的新拓展另文再论”,同时,在后记中指出:“本书原计划写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中英文学交流史。但考虑到丛书各卷篇幅字数不宜相差太大,因此,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英文学交流的20多万字的文稿未放在书中……”然而,在笔者看来,在2016年出版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对最近十年来的本领域学术推进采取漠然态度,同时罔顾当代中英文学交流,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均难以自圆其说。
二、本著出现了一些史实、翻译及概念等方面的错误,虽说大多为细枝末节,但同样会损害该著的学术信誉与价值。例如:第2页:“方重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1931)……”;第16页:“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肇始于陈受颐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发表的相关著述。”这两个判断都与事实不符,且细节多有谬误。真实情况应是:方重1923年赴美留学,先入斯坦福后入加州大学,1927年自加州大学毕业回国。其硕士毕业论文研究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该文后译为中文发表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第2卷第1—2期(1931)。陈受颐是1928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其博士论文《18世纪中国对英国文化的影响》后分成若干单篇用中文与英文分别发表在国内的《岭南学报》、《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南开社会经济季刊》(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al Quarterly)、《天下杂志》(T’ien Hsia Monthly)等中、英文杂志上。最早的一篇中文论文刊登于1929年;②参见《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第233页。最早的一篇英文论文发表于1935年。后来,这些文章(原为英文的译为中文)结集以《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在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那已是1970年了。③参见叶向阳:《英国17、18世纪旅华游记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10页,注1。可惜的是,著者未能从整个中西学术史来考察中英文学关系研究的先驱者。因此,他仓促地做出了有关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肇始者为陈受颐的判断。其实,在陈受颐于1929年在《岭南学报》上发表《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之前,西方至少已有一部专著、三篇文章对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进行了研究(篇目与发表时间见本文注①)。范存忠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文化在英国》(“Chinese Culture in England: Studies from Sir William Temple to Oliver Goldsmith.” 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31)的“前言”里即已明确指出其对该研究课题的兴趣来自于一位英国学者的文章:“据我所知,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文化在英国的接受,这个故事尚未有人讲述。也许,与此最接近的是乔治·马丁(George Currie Martin)的篇幅不长的论文《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English Literature”)(目前甚至在大图书馆里都很难找到),作者在威斯敏斯特卡克斯顿大厅的中国学会上宣读。作者很谦虚地说,‘这篇论文仅为了抛砖引玉,激发对于这个迄今尚未得到研究的领域的兴趣’。然而,该文引发了我对本领域研究最初阶段的兴趣。我想在此向马丁先生表示感谢。”④范存忠:《中国文化在英国》,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页。这恰如钱钟书先生坦言其在牛津大学所撰学士(B.Litt.)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937) 的 灵 感 来 自 于法国学者皮埃尔·马丁诺(Pierre Martino)的专著《17、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L’Orient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VIIe et au XVIIIeSiècle)。①钱钟书:《钱钟书英文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其他史实方面的错误还有一些。例如,第24页:“英国地理学家萨缪·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5—1626)搜集、编译的欧洲各国旅行家的东方游记,以《珀切斯游记》(Purchas His Pilgrimage)为书名,于1613年在伦敦出版。……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的书都收在其中……”我们知道《利玛窦中国札记》在1615年才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以拉丁文本整理出版,英文本就更晚了,根本不可能在原著出版前两年的1613年就被《珀切斯游记》收录。原来,收录有《利玛窦中国札记》英文节译的是同一编者在1625年出版的4卷本《续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London, 1625),而非其在1613年编辑出版的《珀切斯的朝圣》(Purchus His Pilgrimage, 1613)。著者显然是把同一编者的这两部书搞混了。②参见叶向阳:《英国17、18世纪旅华游记研究》,第75—76页。
本著还存在一些误译。例如,第18页引莎剧“They are not China dishes, but very good dishes”,引多恩(John Done, 1573—1631)诗句“As men of China, after an ages stay/Do take up Porcelane, where they buried Clay”。该两句中的China,著者均译为“中国[的]”,其实均为“瓷器”之意。该两处估计著者是受到China首字母大写的误导,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文名词一般要大写,如多恩上述诗句中的Porcelain与Clay亦然。在17世纪的英国,关于中国瓷器的制作,曾流传着需埋入泥土百年后才成器的说法(可参见钱钟书上引书第99—101页),这恰好契合上述多恩的诗句:“瓷人,埋入泥土一个世纪/埋入时为黏土,出土时成瓷器。”该句的著者译文—“如中国人,当一个世纪逝去,/在瓷品中采集揉进的瓷泥”不知所云,当属误译。另外,在英国文艺复兴时代,China确实有时可以被译为“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英文中的China就不能被译为“瓷器”。莎剧的这句引文如译为“这些虽非瓷碟,确属上乘碟子”似更合理,因为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来自中国的瓷碟无疑是品质最好的餐具。一个多义词的意义确定,更多的是应该从上下文的语境与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去揣摩。笔者发现本书中至少还有以下几处译文有问题:第181页“老沃尔特·高尔恩(Walter Gorn Old)”,该处的“Old”实际上是姓氏,应译为“沃尔特·高·奥尔德”;第 198 页“《北平年鉴》(The Peiping Chronicle)”,这是一家民国时期在北京出版的著名英文日报,标准译名是《北平时事日报》(1932—1948)。第200页“‘陷入了生活的本质’(plunged in the inward life)”,宜译作“沉浸于内心的生活”,“inward life”即为内在的、精神的生活,只有这个才不可捉摸,能与前面的“像难解的谜团”相契合。
本著在学术概念及表述的逻辑性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第187—189页:“确实,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中国古典戏剧译介中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古典戏剧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形式,仅从译本角度来看,具体表现为:第一,梗概简介。……第二,选译。……第三,转译。……第四,直接全译本。”但著者并未注明以上界定的依据。③谢天振将“节译”“编译”“转译”与“改编”分别称作“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与“特殊型创造性叛逆”。参见谢天振著:《译介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0、82页,但他未说明该界定的依据。关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法国文学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2000),在其《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1958)中,在论述了文学作品在外国读者群中的机运④即外国读者通过翻译在作品中发现了其所追求的东西,而这其实并非是原作者所想要表达的,也许还是他从未想到过的。后,指出:“当然,背叛在此发生了,但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背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里永远都有一个创造性背叛的话,那也许可以解决翻译的棘手问题。说它是背叛,是因为作品被置放到一个与其构思时完全不同的参照系统中(在语言环境上);说它是创造性的,因为它通过提供与更广大读者新的文学交流的机会,给作品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现实,因为它丰富了原初的作品,不仅让它幸存下来,还使它获得了第二次生命。”①Robert Escarpit,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2, p.111.笔者查阅了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1992),其关于“创造性叛逆”(trahison creatrice)的论述集中在第四部分第七章第二节不足两页的篇幅(第111—112页),但只字未提类似于著者所谓的译者在戏剧翻译时对译本做上述处理为“创造性叛逆”。在对“创造性叛逆”做了上述引文中的阐发后,埃斯卡皮随后列举了英国18世纪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和笛福(Daniel Defoe) 的《鲁宾孙漂流记》(The Strang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两部作品在法国的机运。在英国文学中,前一部是激烈的讽刺小说,后一部是为初生的殖民主义所唱的赞歌。但两部作品到了法国,均被纳入到儿童文学类别里,成为了新年的赠品。埃斯卡皮将这种“创造性叛逆”称作“倒掉了开胃酒,吃下了玻璃杯”,即重视了载体,却忽略了内容。作者还认为,这种创造性叛逆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内部,作品不分影响大小都有可能发生。最后,他总结说:“要知道一本书,首先要知道它是如何被阅读的。”(Escarpit, op.cit., pp.111, 112)谢天振在《译介学导论》中也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下了一个定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②《译介学导论》,第72—73页。如果我们从上述埃斯卡皮与谢天振的定义出发,著者列举的几种中国戏剧在英译文里的呈现形式就与所谓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基本不沾边,而仅能算是英国接受中国戏剧的若干种媒介了。同时,判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中国古典戏剧译介中表现尤为突出”似也缺乏根据。
第223页:“罗默表现出了明显的种族歧视以及对亚洲的敌意。他通过傅满楚小说里的人物,直接表示对华人的蔑视。”“傅满楚形象之所以被塑造成‘黄祸’的化身,因为……但是这一形象并不能代表罗默自己关于中国人的真正看法。”上述判断显然自相矛盾!第229页:“16世纪葡萄牙游历家平托曾提出一个利用中国的著名概念,即用中国来批评欧洲的社会风习……”但我们未见著者有丝毫的证据支撑该判断。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第230页“他[迪金森]曾亲口告诉辜鸿铭说”。第249页“德国人施本格勒著《西方的没落》一书,就公开宣告西方文明已经走到尽头,必将为一种新的文明所取代,为了走出困境,欧洲应该把视线转移到东方”。但该书中译本译者齐世荣在卷首的《德意志中心论是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结果—评〈西方的没落〉》一文中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方的没落》……一个核心思想:西方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的最优越文化,二十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西方的没落》……表面上似在讲西方的没落,实则在于论证德意志民族统治全世界的历史宿命。……斯宾格勒的著作虽然也讲西方的没落,但又断言与世界上已经死去的七个文化[包括中国文化]比较,西方文化尚未走到尽头,仍有生命……”③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6页。如果译者的判断正确,那么《中英卷》的著者就恐怕细读不够被书名蒙蔽了。事实的联系(rapport de fait)是国际文学交流研究的生命线,著者的以上欠实证叙述模式显然与此宗旨违逆。
三、著者在“导论”中提出了中英文学关系的四种阐释模式,前两种为“现代性(modernity)视角”与“他者(the Other)形象模式”。在本著中,这两种模式主要被运用到对英国作家中国题材创作的阐释,于是就演变为文本分析的两大思维定势:一个可称之为“东方文明或中华文化救赎论”,另一个是“中国题材写作的策略说”或称“永恒的‘他者’主题论”。
著者认为阿克顿、迪金森的著作是以上两种阐释模式的典型文本。关于阿克顿的小说《牡丹与马驹》(Peonies and Ponies, 1941),著者指出:“《牡丹与马驹》中以西方学者菲利普(Philip Flower)在中国的精神探索历程作为一个鲜活的思想个例,形象地呈现了东方文明拯救西方危机这一时代命题的诸多内涵。”④《中英卷》,第254页。以下引用本书仅在引文后括注页码数。著者还对所谓“东方文明拯救西方危机”的“时代命题”进行了溯源:“关于东方(主要指中国)文明救治西方危机。这一理想经罗素等西方思想家,以梁启超、梁漱溟为首的‘东方文化派’,以及辜鸿铭等人的激扬鼓吹,在20世纪初的知识界荡起了一片波澜。”(248)紧接着,著者对此阐释得更为详尽:“的确,1914—1918年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病,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是一个沉重打击。这让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人,在正视和反省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出路。……罗素……就是带着对西方文明‘破产没落’的哀痛,甚至是对西方文明行将在战火中彻底毁灭的恐惧,朝圣般东来中国,企求能从古老的中国文明里寻求新的希望,呼吁用东方文明救助西方之弊端。”(249)著者甚至认为阿克顿翻译中国古典戏剧也是在“实现其东方救赎”(196)。
笔者以为,就小说主人公菲利普或作者阿克顿个人来说,旅居中国是为寻找精神慰藉是真,而说他为西方文明寻找东方的精神救赎恐怕属于言过其实。菲利普说:“中国已治愈了我所有的疾病。在战争(指“一战”)期间我的生活变为沙漠。北京让它像牡丹般绽放。”①Harold Acton, Peonies and Ponies.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21.显然,在这位小说主人公或我们可称之为作者的代言人看来,中国文化有疗伤的作用,尤其是对像他这样的罹患战争创伤的欧洲人尤为有效。然而,阿克顿在其早小说若干年出版的回忆录里坦言:“我们可能无限地接近佛并沐浴在其巨大平静的阳光里,但我们对于行动以及对于人类思想转瞬即逝的尊严和价值的信仰注定将获得最终的胜利。”②Harold Acton, Memoirs of an Aesthete.London: Faber Finds, 2008, p.283.后者当然主要代表的是西方的文明,作者显然对此有着坚定的信念,换句话说,他并不奢望任何他者的文明能拯救西方。其实在他看来,西方文明仅仅为战争所打断,尚未度过休眠期而已,一旦觉醒,最终的胜利者还是他们!
关于罗素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来华的缘起,其在自传里有较详细的交代,恐怕与著者的判断也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我[自苏联]返回英国时(1920年6月),等待我的信件里有一封来自中国,邀请我以中国讲座协会的名义去做讲演,为期一年。中国讲座协会是一个纯中国团体,致力于每年邀请一位知名外国人来到中国,上一年邀请的是杜威博士(Dr.John Dewey)。我决定,如果多拉[罗素当时的女友,后成为其第二任妻子]能随行,我就去。③Bertrand Russ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London: Unwin Paperbacks, 1978, p.341.
罗素预订了自马赛至上海的船票,但由于船上发生了瘟疫,开航时间推迟了三周,航行时间持续了五六周,最终于1920年8月抵达。在其自传中对此有一段交代:
我们抵达上海时,起先并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我一开始就隐约怀疑这个邀请可能是个恶作剧。因此,为了验证其真实性,在出发前我让中方先付路费。我想很少有人会为一个笑话付125英镑的。然而,在上海未见人迎接时,我们的恐惧再次出现,并开始怀疑我们是否得夹着尾巴滚回家去了。但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的主人仅在轮船到岸时间上出了点差错。他们很快就来到了船上并带我们去了一家中国宾馆。在此,我们度过了从未经历过的最紧张的三天。④Ibid., p.358.
因此,罗素此次中国之行是作为国际知名思想家受到中国讲座协会的“意外”邀请,而著者说他来到中国是为了“朝圣”未免失实。更准确的表述应为:他是受到中国学术机构的邀请来中国讲学的,即他“东来中国”的身份不是朝圣者,恰恰相反,是一位受到我们的热情邀请,来指导我们或者说对我们这个民族进行现代化启蒙的先生。
近些年来,评论者常说“一战”让罗素等欧洲文化的有识之士对欧洲文明产生怀疑,从而转向东方,向中国寻求医治欧洲文明的良方。关于“一战”的影响,罗素在其自传里有过详细的描述:
1914—1918年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我。我中断了学术研究,转向撰写其他性质的书。我颠覆了自己关于人性的观念。人生第一次我确信清教主义无法通向人类幸福。通过死亡场景我获得了对于生命的崭新热爱。我逐渐相信人类的大多数被笼罩在深深的不快乐之中,要用毁灭性的狂怒予以排遣,同时相信只有通过播撒发自本能的快乐才能带来一个美好的世界。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不管是革新者还是极端守旧派都为残暴所扭曲。我对于所有要求遵守严格纪律的意图表示怀疑。我反对所在社会的所有行动,并觉得所有的日常道德都被用作屠杀德国人的手段。为使自己不成为十足的唯信仰论者,我经过了非常困难的历程。然而,由于我对于世界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终于如愿以偿。①Ibid., p.261.
从罗素以上所谈可见,“一战”的残酷只是对于其清教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并坚定了其人道主义价值观。宗教信仰确属文明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甚至非最重要的部分。其实,罗素并未对欧洲文明失去信心,哀叹的只是其被战争打断,有永远失落之虞。他在大战期间(1915年5月10日)致友人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的信中说:
自从我返回此地(指其母校剑桥),我日益感到战争的重压—来到此地人们会强烈地感觉到荒凉。……现在这里一片死寂,所有的日常生活都陷于停顿。除了我们的朋友等人外,世代将会延续下去—然而我一直害怕文明中的某些东西将永远消失,恰如希腊以同样的方式消亡后其文明中的某些东西将不再。人类摆脱野蛮状态缓慢向前,这似乎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我的人生目标并非人类幸福,而是某种思想的艰难浮现。在此,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目标均能获得进展。先驱者所做的一切将会传给后来者,后来者将在我们驻足之处继续前行。而今,所有这一切均停顿下来。无人能知晓该进程将会在暂停之处得以继续……②Ibid., p.276.
显然,罗素绝没有抛弃欧洲文明另寻他途的意思,他对于欧洲文明还有深深的留恋甚至坚定的信心。在“一战”继续可能导致民主派及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革命与同德国妥协以保全欧洲文明之间,罗素宁愿选择后者: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要面临的这种革命,其结果将非常严重、可怕,绝不可能带来什么好处。它将充满暴力、仇恨与血腥,由饥饿、恐怖与猜疑驱使—是一场西方文明中所有美好的东西必将被消灭的革命。这就是我们的统治者要面临的境况。这就是他们为了争夺非洲殖民地及美索不达米亚这些无足轻重的兼并权所要面对的危险。③Ibid., pp.309—310.
《中英卷》还数次提到所谓罗素在其《中国问题》里鼓吹东方文明救赎西方(248、249、250、272),但笔者遍查该书英文原著初版本,④笔者参考的是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2。该版本包括15章正文外加一个附录(Appendix),其中第11章“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ontrasted”集中讨论中西文明的问题。也未见到罗素有关东方(中国)文明与文化拯救西方的明确表述。其实恰相反,本书的主旨在于为中国诊断病症并寻找良方,这当然正是中国人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用意所在。毋庸置疑,罗素在本著中对中国传统文明表示了好感,而且他都是在对比中谈这个问题。不过,他并不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他只是指出这两大文明要取长补短,中国文明中确有许多内容值得西方学习,但显然尚未提高到“救赎西方”的境界。现引用有代表性的两段供参考:
我们【指西方】文明的明显优势在于科学方法,而中国人的明显优势在于对生活目的有个正确概念。我们希望这两个优势可以逐渐融合。……然而,至于另两个恶行—自大(self-assertion)与霸道(domination),我注意到中国人在实践中要明显优越于我们。比起白种人,他们显然对于压迫异民族的欲望要少得多。⑤Ibid., pp.205—206.
……
在我看来,普通中国人,即便是赤贫,也比普通英国人要幸福,因为这个民族与我们相比,建立在更为人道与文明的价值观之上。焦虑与好斗不仅引发明显的恶行,而且让我们的生活不满足,让我们失去了对美的享受能力,并几乎不再能去践行美德。在过去的百年里我们在此方面已迅速地每况愈下。我不否认中国向另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但正因此我觉得东西方的接触对双方都可能有益。他们可以向我们学到最低限度的实践效率,这对他们必不可少,而我们可以向他们学到发自于内的智慧,正是这种智慧让这个民族生生不息,而其他古老的民族均已消亡了。①Ibid., pp.208—209.
从以上笔者认为对中国文化“最理想化想象”的引文中可见,罗素主要看到了西方世界过于混乱与焦虑,而这个混乱与焦虑是由欧洲各国以民族利益至上而互斗引发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平主义”与“知足常乐”的传统价值取向可以为西方提供借鉴,但他也看到中国有其自身的问题,尤其在政府、教育、科学发展尤其在军事能力方面亟需现代化。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救赎”,那也是互相的救赎,而绝非东方对西方的“单向道”救赎。
本著的另一个文本阐释的思维定势是英国“中国题材写作的策略说”,即所谓英国作家描写中国仅仅是为了确立一个“他者”或对立面来反观自身—或自大或自卑的自身,这几乎被著者运用到所有英国作家的中国题材写作的分析之中。现举若干例子:“在中外文学交流思想史上看,西方作家眼中的中国往往是‘异己’的他者,是西方文明陪衬下的‘文化构想物’,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利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自身的深层欲望和需求。”(271)“传统上讲,英国的民族自我向来是以一个海外他者作为对立面才得以形成的。如果说17世纪时的他者是天主教的欧洲,那么随着帝国的发展,这个自我就逐渐变得需要靠殖民地所代表的相对弱小的国家作为陪衬方可得到界定了。……中国同样是英国的他者。”(103)“英国作家借用中国题材一般都是从某种观念出发,或假中国之名来反思、批判自身文化及社会现状,或借丑化、贬斥中国以凸显自我的优越感。”(211)“西方人对‘中国佬’形象的塑造也是西方殖民帝国建构和维护中国认知网络的重要策略”(281)。这个阐释“定势”显然来源于现代性中对“他者”的界定以及解构主义与后殖民理论中关于权力与话语的关系问题,带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色彩。
当然,就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1862—1932)的《约翰中国佬来信》这个“典型”个案来看,著者并未有根本性的误判,有许多“事实联系”的证据足以说明,中国在该作品中确实是主要作为其“对西方文明提出根本性批评”的“背景”或称为“他者”而设的。②E.M.Forster, “Lowes Dickinson.” 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Compiled by Hsiao Ch’ien.London: Pilot Press Ltd., 1944, p.58.不过,如果读者细读文本,应该还能读出作者“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态度极为不满,写出名著《约翰中国佬来信》……强烈抗议庚子事变西方的贪婪掠夺”等等其他并非不重要的信息。③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上海:知识出版社,2003年, 第166—167页。也就是说,迪金森所运用的中国材料及所描写的中国事件(义和团运动)本身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至少“中国”不全是作者为了阐发对自身民族的态度而设置的“他者”傀儡。因此,迪金森的这个“典型”个案其实是对著者以下论断的直接挑战:“在英国作家笔下,……[中国]绝非事实的中国,而是描述的或想象构造的中国。中国对于英国作家的价值,是作为一个他者的价值,而不是自身存在的价值。”(“导论”,15)因此,一种套话般的阐释模式必然会遮蔽许多作家鲜活作品的多层面或多义性。甚至,英国作家借用中国题材也并非都是“从某种观念出发,或假中国之名来反思、批判自身文化及社会现状,或借丑化、贬斥中国以凸显自我的优越感”(211)。相比之下,笔者更认同吴格非一分为二的判断:“狄更生是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的西方学者,他崇拜中国文明,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思考,有些观点态度是合理的,譬如他赞扬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对灌注着儒家思想的中国诗歌和艺术倍加推崇。但有些观点显然出自他对中国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想象。”④吴格非:《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92页。自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善于用与异域对比的方式来更好地认识自我,这确实不假,但这种对比并非就是像著者所说的均属把他者“幻象化”。其实,他也承认英国“中国城(Limehouse)”小说作家托马斯·柏克(Thomas Burke, 1886—1945)对中国题材的兴趣来自其童年时期切实的生活经历,而非出于为验证某种观念的假想。事实上,这种基于“客观与真实”的中国题材创作在英国作家中也并不在少数,毕竟好作家是绝不会用一种模式去写作的,而且我们也丝毫不怀疑,随着英国有关中国知识的增长以及信息流通的更加便捷,经过理性主义洗礼的英国作家是具备客观而准确地刻画中国的能力的。
与《中英卷》形成对比的是,张鸿著《中国文学在英国》的第一章第三、四两节专谈17、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影像”与“中国主题”,分别分析了埃坎纳·塞特尔爵士(Sir Elkanah Settle, 1648—1724)的五幕悲剧《鞑靼征服中国记》 (The Conquest of China, 1674)、笛福 (Daniel Defoe, 1660—1731)的《联合号》(Consolidator,1705)、《鲁滨孙漂流记》(二集)(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与斯蒂尔(Richard Steel, 1672—1729)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1711.3—1712.12, 1714.6—12)上发表的中国故事、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1761)及其若干仿作、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 1701—1760?)与谋飞(Arthur Murphy, 1727—1805)分别改编的《中国孤儿》(The Chinese Orphan: A Historical Tragedy,1741;The Orphan of China, 1759)等。虽然这些论述大多言简意赅,但其撰写方式是以描写史实与文本情节为主,辅以适当的结论,并不套用往往凌驾于史实与文本事实之上的某种固定的阐释模式。即便撇开采用上述“他者”阐释模式所做的判断,是否符合英国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对异域观念的真实状况,这种刻板模式或理论认定在中英跨文化文本阐释中如用得过滥,难免也会让人误认为所有英国作家关于中国的写作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假设在作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新时期”之前几乎对所有文学文本与社会现象的剖析都要将之放置在“阶级斗争”这面放大镜下去审视那样,因阐释的空泛、刻板、武断而令人反感。
已故著名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先生在组织编写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时,定下了以下原则(或称文学史撰写的模式):
以叙述文学事实为主,要把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交代清楚,而不是……以批评、评价为主。要着重作品本身,通过研究作品来讨论问题。因此要描述作品本身的内容和写法,要从中引用若干段落加以翻译阐释,使读者能多少接触到一点原作风貌。写法也要有点文学格调,要注意文字写得清楚、简洁,少些套话术语,不把文学史写成政论文或哲理文,而要有点文学散文格调。①王佐良、周珏良主编:《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序”,第1—2页。
后来,王佐良先生在《文学史写法再思》中对“外国文学史首先应该提供史实,以叙述而不是以议论为主”的原则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其中有“1.全局在胸,对整部书所包括的文学历史有一概观,同时又了解细节……”②王佐良:《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第433—434页。同时,王先生认为叙述中仍须有评论,但特别需要的是“中外诗文评论中常见的一类一针见血之言”③同上,第434页。。其实,研究中英文学关系史的前辈学者方重、陈受颐、范存忠、钱钟书先生遵循的基本上也是这种方法与模式。经过长时间的学术沉淀与淘汰,他们的著作至今仍是本领域的扛鼎之作。
因此,笔者认为,王佐良先生为英国文学史的撰写所制定或者说所总结的原则大致可以为中英文学交流史撰写时借鉴。国际文学交流史属于比较文学影响与接受的实证研究范畴,它特别重视在充分“事实联系”的基础上对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交流、关系做演变、沿革及其发展的总体描述,同时对一些相关的重要人物、创作与流派及其媒介做聚焦式研究。因此,除了突出跨国别、跨文化的特点外,国际文学交流史的写作与国别文学史的写作并无多少区别,其实,法国学者在传统上就是把比较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加以研究的。
如以王佐良先生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制定的写作原则来衡量,《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的不足之处恐怕也是明显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叙述事实(包括中、英文学的相互认知、相互影响与创造等方面的史实)为主的原则,同时,由于著者过于重视理论提升以及阐释模式的运用甚至套用,文学史所应有的“论从史出”往往变成了脱离作家作品等具体史实的批评套话与术语的堆砌,影响了可读性与可信度。最后,同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不仅仅要讲述好不同文学之间因缘际会的佳话,还应该对所涉对象国的文学及文学史有全局性把握与具体性研究,因为文学关系不过是文学发展史的“表象”,而各自文学本身的特性才是各种国际文学关系内具的“本相”。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日本汉学家饭塚容
饭塚容,1954年生,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日中演剧交流协会理事,神奈川文学振兴会评议员。他是日本唯一获得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汉学家。从大学本科阶段开始,饭塚容一直致力于同步跟踪翻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戏剧,持续不断地向日本学界介绍中国新时期文学家、文学作品,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饭塚容以其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世界文学的眼光和方法,不仅关注中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研究,还关注世界各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各国学者的评价或者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获奖情况反观中国文学,通过研究中国文学再观照日本文学,以及东亚文学发展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其父饭塚朗也是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曾经翻译曹雪芹、刘鹗、冯梦龙、张恨水、冰心、老舍、巴金等作家的作品。然而,饭塚容选择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的视角与其父辈不同,他更加关注与自己同处一个时代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并以各种研究成果、形式向日本国内学界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界的最新动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