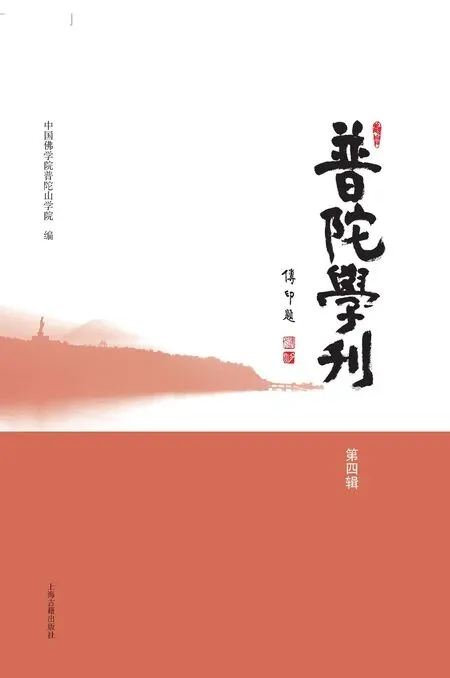不期而遇的“现代性”:清末民国中国佛教学术方法的特色及其启示
2017-01-28王建光
王建光
(南京农业大学)
一、 序: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欧洲的现代性进程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已开始,这是建立在其宗教改革基础之上的持续三百余年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是以资本主义发展、人本主义张扬、全球贸易、学术自由和科学探索等为主要标志的。虽然这股清新的文化思潮早在明末清初之时即已经吹到了中国,但是并没有对中国社会文化造成根本的影响。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交通和通讯的持续改善,欧洲这股现代性的物质和文化力量终于在清末的历史时期,作为一种不速之客,被突然地送到了中国社会之中,显现在传统士人的知识视野之中。因此,自清末以降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社会的政治观念、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宗教文化都因之经过了多重的洗礼与改造。古老的中国也从一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一步步地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多元社会,社会大众那种长期形成的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也慢慢有了某种自卑的甚至妄自菲薄的心态。知识阶层及其学术活动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受到了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方式的转型及新的学术方法的形成。
清末民国的百余年时间,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广为传播和发生影响之世,同时也是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经过艰难的凤凰涅槃,而涌动着陌生的社会思潮、凝聚着现代性力量的历史阶段。正如梁任公所说:
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红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31页。
这一异样的社会思潮对于近百年的知识分子而言有着重要的影响。清末民国的佛教复兴和佛学研究也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上产生和发展的。有学者对晚清之世的佛教文化状况进行了总结,认为此时的佛教有着如下的特点:第一,入世性,即扬弃出世思想,形成“经世佛学”;第二,批判性,即注重审视社会,评价现实;第三,思辨性,专注于佛教的哲学性;第四,随意性——例如康有为的“去苦求乐”,诸如谭嗣同的“虚空”、“以太”,章太炎的“俱分进化”、“五无”、“四感”,梁启超的“心理分析”,都可说是“以己意进退佛说”的产物,为社会革命添置了戒刀和禅杖;第五,科学性,如谭嗣同的《仁学》,将“科学、哲学、宗教治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79—83页。
对于清代的学术方法,梁任公认为,清代学派之运动,乃是“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他也正是将之视为学术收获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收获之原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红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69页。吕思勉也指出,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但于主义者则无有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2月,第3页。虽然梁、吕二人并不仅仅针对本文所言的历史阶段,也并不仅仅针对佛学研究而言,而且他们也是抱着一种不满的态度来评价这种现象的。但事实上,传统的佛学研究可能需要的正是方法的变革。这是因为明清以来的传统佛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一种较为浅显的文本注疏、经典导读和修行指导的层面上进行的,如隋唐一般具有创造性的佛学研究文本已经不再出现。
中国近代的百余年间,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切都影响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促进了新的文化社会思潮的形成。清代以后流行的传统经学到此时被戛然而止地划上了句号,西方的哲学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于此时传入中国,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促使其完成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变。此一阶段的中国佛教的学术研究也因之有着自己的特色和表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广泛的和深入的,本文仅就中国佛教而言。这表现在很多方面,诸如:
中国佛教如何与西方宗教对话?
中国佛教如何应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强力解读?
中国佛教的学术研究出路何在?
如何认识此一历史阶段的现代性与全球化对中国佛教发展的挑战?等等。
这一历史时期的佛学研究者,有的出访过欧美日和南洋等地,有的生活在欧化程度较深的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有的与来华的外国学者、传教士等人保持着长期的接触。在力量强大的现代性面前,清末民国的佛学研究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佛学研究方法以及清代的经学和小学方法,另一方面又大都受到欧美学术方法的影响。
学术的革命首先开始于方法的变革。事实上,没有方法的变革即不可能有学术的进步。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不能取得原创性思想突破的时候,变革方法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显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中,传统的佛教学术研究方法的变革即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二、 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国佛学角色彰显
清末民国现代性思潮的主要影响及其表现之一,即是中国学术方法的革命性转变。正是这种对传统学术方法的变革,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和学术方向的改变,佛教的研究方法变革及其转型也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
(一) 佛学与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的传统谱系之中,哲学一直被视为学科之源。每一学科的发展首先都会解决或必须要解决其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在中国近两千年的佛学研究历史中,佛教本身在其社会文化坐标中一直面临的都是与儒道两家在现实世界和信仰领域的“位置安排”问题,要解决的是传统的“三教”关系问题,而不是其在中国学术谱系中的定位问题,更不是要解决其自身与所谓“哲学”的关系问题。
中国自先秦为始的传统思想中,并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概念,或者说这种“哲学”并不占学术思潮的主流。清代以降,儒学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经学。这与哲学的方法和宗教学的方法都是不一致的。可以说,清代末期对佛学有所关注的学者如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等人,都是从被称为(今文或古文)经学的儒学入手的。这种研究思路当然也影响到他们的佛学研究。
随着“哲学”概念进入汉语之中及西方思潮的深入影响,西方哲学及观念也被引入到中国佛学研究领域。于是,传统的儒释道关系也慢慢转换成了“佛学与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西方哲学,或者是经过西方哲学模式诠释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关系,随之也就有了哲学与佛教(或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关系的研究。而在传统中国佛学研究中,这一点基本上既不是明显的也不是关键的学术问题。
此时的佛学研究者大都重视对佛学与哲学问题进行厘定,他们往往把佛法与哲学对应起来加以研究。早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肇始者杨文会(1837—1911)那里,佛教与哲学的概念即得到了强调和区分。他说:
如来设教,义有多门,譬如医师,应病与药。但旨趣玄奥,非深心研究不能畅达。何则?出世妙道,与世俗知见,大相悬殊。西洋哲学家数千年来精思妙想,不能入其堂奥。盖因所用之思想,是生灭妄心,与不生不灭常住真心,全不相应。是以三身四智,五眼六通,非哲学家所能企及也。近时讲求心理学者,每以佛法与哲学相提并论,故章末特为拈出,以示区别。*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佛法大旨》,《杨仁山居士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3月,第260—261页。
事实上,虽然历史上也有许多哲学命题和概念进入佛学研究的思想和文本之中,但是把佛法与哲学明确地对应,继而加以比较研究,却是清末民国重要学术方法的创新。因为这种哲学方法是一种西方语境的概念,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德性之学,也不同于受到社会重视的治世之学。也正是沿着这个思路,佛学研究者区分了哲学与佛学、佛教与宗教等概念,并由此而生长出中国近代佛学研究领域的新命题——佛法与哲学的问题,才有了关于佛教与哲学间的多种说法。这不仅深化了传统佛学的研究内涵,同时也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咄咄逼人的异样文化面前,“三教关系”的优劣先后已经不再成为问题,而如何安排哲学与佛学的关系、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佛学研究,却是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为了深化对佛学与哲学的深入研究,佛学研究者们对佛教概念作了更为深入和现代意义的比较。章太炎(1869—1936)在流亡日本时也曾经对佛法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参见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页。他甚至更进一步地以“惟心”与“惟物”的哲学概念来解释佛教的“自性”思想,他指出:
凡去自性,惟不可分析、绝无变异之物有之;众相给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组合上别有自性。如惟心论者,指识体为自性;惟物论者,指物质为自性。心不可说,且以物论。*章太炎:《国家论》,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95页。
因为哲学的方法是重要的,所以明辨佛教是哲学还是宗教也就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它也一直是这些学者念念不忘的事,于是即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有欧阳竞无(1871—1943)居士,主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观点,他曾言:
宗教、哲学二字原系西洋名词,译过中国来,勉强比附在佛法上面。但彼二者,意义既各殊,范围又极隘,如何能包含得此最广大的佛法?正名定辞,所以宗教、哲学都用不着。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欧阳竞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黄夏年主编:《欧阳竞无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页。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欧阳居士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想通过拒绝把佛教与哲学相对应加以考虑的方法以消弥这个问题,摆脱这一认知困惑,但是这样做并不能从学术上解决这一问题。
梁启超(1873—1929)对此问题也多有深究,并跳出了“哲学”或“宗教”的“是”与“否”的认识框架,开辟新的认识视角。他作有《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等文,或径从唯物论和佛教心理学的角度来尝试对佛教义理的研究,或用“西洋哲学家用语”解释五蕴,如他说:
色蕴是客观性较强的现象,有实形可指或实象可拟,故属于西洋哲学家所谓物的方面。受等四蕴,都是内界心理活动……即西洋哲学家所谓心的方面。*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黄夏年主编:《梁启超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21—222页。
这显示了佛学是能够与西方学术进行对话的,也是其学术观点和意义之所在。*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有与西方进行对话的平台才是学术能够成立的条件。
汤用彤(1893—1964)则说:
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转引自巨赞:《汤著〈佛教史〉关于“〈太平经〉与佛教”的商竞》,吴志云主编:《巨赞文集》上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253页。
太虚则写下了《论哲学》《佛法与哲学》《佛法是否哲学》《佛教与宗教哲学及科技哲学》《西洋中国印度哲学的概观》《最近西洋哲学与佛学》《关于近人辩证法的讨论》《自治哲学》《唯物唯心唯生哲学与佛学》等一系列文章,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地研究。
事实上,这一阶段不少佛学研究者对有关佛教是哲学还是宗教的争论或论证,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游戏。这种争论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西方的哲学方法在中国佛教学术研究中的应用。这一时期教内外的学者对佛教进行的或哲学或宗教属性的探索,虽然看起来是一种立场的显示,但事实上也反映了这些研究者认识论中深层的困惑。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学者们心中往往都有一个纠结之处,总想用西方的方法来解读中国历史和学术,他们一方面引入或套用西方术语,另一方面又对中华文化有着自豪。在东西方不同模式文化交流中,也有的人甚至有着某种内在的自卑或不安,面临着方法和情感的困惑。也正是在对这种困惑的解决中,中国佛学才在现代诸多学科中明确了自己的位置,“中国佛学”与哲学之间才形成了边界,中国现代佛学才有了自己的主体形象。
(二) 佛学与宗教学
在中国佛教传统中,一直有着“宗教”之说,但是这种“宗”与“教”并不等于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宗教”(religion),中国的佛教研究也不完全等于建立在religion之上的“宗教学”(The Study of Religion)。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宗教学的兴起,中国一些研究者也尝试以西方的学术方法把佛教纳入到宗教学的研究领域。其后在日本佛教学者和欧洲宗教学研究者的影响之下,中国的佛教研究也迈入了新的研究领域,在佛学与宗教学的关系中建立了明确的佛学学科位置。
自杨文会始,其佛学研究与学术活动,即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一定影响。因为他曾随曾纪泽出使过英国,拜访过东方文化学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对西方的社会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所以,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到欧洲、了解欧洲的科技文明,并把佛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放在科学至上的世界中加以考察的中国佛教徒。”*(美)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王雷泉、包胜勇、林倩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9页。而且,他又与日本的佛学界诸家有着深入的交流,经过欧洲学术思想改造过的日本佛学研究方法也对他有着强烈的影响。
事实上,随着对“宗教”内涵的认识,不论是否把佛教看作是宗教,用宗教学的方法来研究佛教都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研究方法,这也给中国近代的佛学研究以明确的学术定位,其后如太虚、印顺以及当代许多学者都是沿着这路走下去的。这不仅有利于佛学研究在后世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中的活动与开展,也丰富了中国佛教的研究方式,拓展了传统的佛学研究领域。
在这种宗教学的研究路径中,传统的佛教研究者已经自觉地从浩瀚的大藏中抬起目光,投向了遥远而陌生的泰西,投向了异样的文化和宗教,以从中吸收营养。如巨赞(1908—1984)曾对西方宗教的文本加以阅读,注意从中研究基督教发展的原因,并有着自己的发现,认识到在新佛教运动的建设中。他说:
尝读《新旧约全书》者,咸知基督教之所以能流行于全世,悉赖其致力社会事业之感化,而教理不足称。*巨赞:《如是斋窾录》,吴志云主编:《巨赞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852页。
巨赞通过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进行考察,通过对西方学者桑戴克(Lynn Thorndike)关于基督教改革的历史观点进行研究,提醒要注重研究和借鉴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并从中提出了新佛教运动建设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参见巨赞:《新佛教运动有回顾与前瞻》,吴志云主编:《巨赞文集》上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646页。其《宗教与民族性》一文,提出了清教徒与近代英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这样的问题都超出了历史上的研究领域。
清末以降,随着出国交流的频繁和西方文化影响的深入,诸如马克斯·韦伯、缪勒、克尔凯郭尔(在鲁迅的文章中译为“契开迦尔”)、尼采、柏格森、罗素等西方学者及其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国一些佛学研究者,尤其是这些人所用的西方学术方法更是受到国人的重视。*日本佛学研究者的方法及其成果对当时中国佛教学者也有着强烈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事例即是最为人所道者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于是传统的佛学研究便引入了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伦理学、考古学、语义学、民俗学、比较宗教学等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虽然在历史上也曾经有僧人或学者使用过,但这都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在学科意义上的方法论自觉。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如陈垣发表于1938年的《汤若望与木陈忞》,因其在东西方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比较了天主教与佛教,而被认为是“一篇比较宗教史研究的典范”,“开宗教史比较研究之先河”。*陈智超:《陈垣先生与佛学》,黄夏年主编:《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页。
环境的改变、方法的多样、视野的拓展,为此时的佛学研究者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他们在诸如佛教因明与形式逻辑、佛教与宗教、佛学与人生、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儒释道三教关系发展与释耶及释伊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丰硕的成果。甚至工业文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议会等概念和思想也都进入到佛教研究的视野之中。
正是发现了基督教在欧美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作用,此时许多研究者认为,宗教实为社会中的必须者,故而他们则是想通过证明佛教属于宗教,所以社会需要佛教。如谭嗣同要建立的佛教、太虚要建立的人间佛教或者杨度等人要建立的新佛教等,盖皆要以之与基督宗教相对应,从而证明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再如,康有为要建立儒教,其思维的形成和目标的确立,也大都受着这一心结的影响。梁启超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保教非所以尊孔》等文,对孔教的提倡或反思也都有此义。因此,关于佛教、哲学和宗教等等争论问题产生的原因,或者说要证明佛教属于或者不属于宗教、属于或不属于哲学的原因,正是在于中国传统学术方式在面对西方哲学、宗教的冲击时的一种本能回应,及其在现代的学术谱系中自证其义的道德性努力。
认为宗教是落后于时代者,则更加关注和强调佛教属于哲学,或者是要以哲学的方法,体会其中的哲学内涵,以与西方哲学相对应,从而挖掘作为中国文化重要部分的佛学之中的合理、合适、合时与合世的因素。
事实上,尽管这一时期的佛学大师们大都对西方文化和哲学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但是,不论其观点如何,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正在于他们仍然把佛教作为佛教去研究,作为“中国的”佛教去研究,而不是将之视为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或宗教,如汤用彤等人即是如此。
(三) 中国佛学与外国佛学
历史上,中国的佛学研究都是在儒释道关系中展开和发展的,但是到了清末,这种社会文化背景已经变成了中西、中日的文化交涉与学术竞争。这就为清末民国的佛教复兴和佛学研究奠定了的复杂的文化基础,教内外修治佛学的方法也因之发生了变化。
清末民国诸家治学,与历史上的所有时期相比都有着自己的特色。这首先即在于他们的心态受到西学、日本关于中国学术研究的冲击,不论对待西学持什么态度,其内心深处对西学都仍然有着复杂的(当然有的人甚至恐惧的)心态。于是向西方学习、引入西方的文化和学术方式即成为当时一些人的伟大志向或者不得已的手段。出洋学习或考察,加强对外部世界的深入认识,即是了解西方学术和宗教的重要手段。
此一阶段的主要佛教交流活动有:
1878年,杨文会随曾纪泽到伦敦。
1905年,笠云、筏喻、道香去日本;笠云访日间的诗作,辑为《东游记》。
1906年,柏桂华去日本。
1915年,吕澂去日本。
1917年,太虚去日本,其讲演、诗文、游记辑成《东瀛采真录》。
1921年、1922年,大勇去日本、显荫等去日本,显荫作《留东随笔》,并将《高野山中学大学之课程表》、《东京宗教大学的学科目录》抄寄太虚,“以备采择施行”(《上太虚法师书》,《海潮音》第5卷第5期),大勇有《留学日本之调查》,载《海潮音》第4卷第6期。
1922年,持松去日本。
1923年(左右)、1925,纯密去日本。
1925年,太虚率团赴日,与南条文雄、村上专精、铃木大拙等交往。
1926年,谈玄去日本。
1928年,太虚旅欧美,法英比德美国,赴法国,建“世界佛学苑”。太虚旅欧,赴法国,与伯希和、马格尔、罗素等学者有所交流,建“世界佛学苑”。定其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造成世界之安乐”。显而易见,此处的“世界”与曾经佛经中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佛学院建设计划——十七年十月改正——)并在英、美、德等国设立佛学苑通讯处。
1935年,(1925年,太虚在庐山大林寺设“庐山学窘”,选优秀学员学佛学和英文,为环游欧美布教作准备,大醒即是其一。)大醒后到日本一个月,回国后作《日本佛教考察记》。
1934年,谈玄去日本。
1934年,王揖唐,去日本参加空海大师示寂1100年纪念会,作《东游纪略》。
1935年,大醒,去日本。
1935年,刘蓬翊,去日本,作《日本佛法考察记》。
1936年,定勋、天慧,闽南佛学院。
1939年,太虚率团访问缅、印、锡,与泰戈尔、尼赫鲁、甘地等会晤,参访、观礼、拜谒佛胜古迹,并提出了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态度。
同时,当时的一些佛教学者对僧众的外语教育也极为重视,如太虚创办闽南佛学院即开有日文课程,聘请日本东本愿寺厦门别院的神田慧去作教官,*肖平:《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55页。以促进对海外佛学研究的了解与学习。
随着新的佛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学者在传统的语录体、僧传体、经疏体和学案体等著作之外,对西方的哲学范畴、史学原则和宗教学方法有着一定的了解,同时也能将之用于其考察和研究之中,以期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史进行剪裁,以新的历史观认识佛教发展的历史,如蒋维乔编著的《中国佛教史》即是如此。此外,如王恩祥编著的《日本大神徐福》、《日本大光照国师隐元》、《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鉴真》等也都体现了这种影响。
同时,国内的《海潮音》等刊物也重视刊载国外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如铃木大拙的《支那佛教印像记》等(载《海潮音》第16卷第6—8期),这一切都使中国佛学研究者对中国佛学研究的内容、目标和方式等有着较为明确的了解。同时,这种方法也被用于对诸如藏传佛教、西域佛教、印度佛教、中印交通的研究及传统佛教文本的注疏与考证等领域,以图打破日本学者在世界佛学研究领域独掌的学术话语权和个别研究者颐指气使的现象。*如一些日本人学者对中国传统经典真伪的考证,即对中国佛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著名者即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真伪之辨。如陈垣曾说:“日本史学家寄一本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陈智超:《陈垣先生与佛学》,黄夏年主编:《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页。
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什么是“哲学”的争论以及对“哲学”概念的使用都是十分复杂的,难以简单地进行评价。本文仅在其一般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
文化交流都是在被别人解读和解读别人的过程中进行和深化的。中国佛教解读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也在解读中国及其佛教和文化。正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的努力,才使中国的佛学研究活跃在世界的学术舞台上,才使中国佛学能够在和日本佛学的竞争中、在面对欧美学术的强力解析中,张扬了中国佛学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佛学的角色得以确立和彰显,形成了“中国佛学”世界学术身份,使中国的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都能有着强大的学术力量。
三、 思想的力量丰富了佛教文本解读方式
欧洲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赋予了哲学以丰富的内涵。这是一种以对本体论的研究为特色,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入手,以关注理性和知识的功能为特色,以强调对物质世界的生灭、运动、生成等概念的考察和数学表达为学术工具的现代理性力量。崭新的哲学思维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的思想为西方文化开辟了新的空间和发展路径,这一切都受到梁启超、胡适等的重视。随着西方哲学的引入,思想的力量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学术动力,也使中国传统士人的思维和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地解放。*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什么是“哲学”的争论以及对“哲学”概念的使用都是十分复杂的,难以简单地进行评价。本文仅在其一般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
(一) 思想的回应
随着时代的发展,清末民国时期的僧人其视野、学识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对西方文化也有着越来越较为深入的理解。如巨赞对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密乐顿的《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等都有着了解。*巨赞:《佛教与中国文学》,吴志云主编:《巨赞文集》上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818页。这一些文献都是西方思想的重要力量之源。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改造理想也对当时的佛学研究者以极大的影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33—134页。太虚大师曾言:
粤友中交有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抵皆新闻记者,但其思想以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为近,以是纷纷以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斯、幸德秋水等译著投阅;张继等数人在巴黎编出的新世纪,亦时送来寓目。我并得读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太虚:《太虚自传——二十八年初稿三十四年秋修正》,《太虚大师全书》第三十一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179页。
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太虚的政治社会思想,乃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其意将以无政府主义与佛教为邻近,而可由民主社会主义以渐阶进。这对其佛学思想的形成及佛教改革理想都有着复杂的影响。显然,这种思想是崭新的,方法是学术的,视野是全球的,内容是时代的。我们很难说太虚其后的佛教改革不是与之有关。所以,有学者指出:“太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他的象征意义:为现代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以及中国佛教徒面对西方的一种极端回应方式。”*(美)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王雷泉、包胜勇、林倩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2页。
同太虚一样,当时其他著名的佛学研究者的文章和著作,也都有着西方思想的影响,也都曲折地传达着其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和政治改革的设想。
值得指出的是,此时的佛学研究者有着以西学比附佛法的特色。如章太炎认为,赫尔图门关于神即精神之说,实为“窃取十二缘生之说。盲即无明,动即是行,在一切名色六入之先,是以为世界所由生也”。*章太炎:《无神论》,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32页。
章太炎还以西学来解读佛法:
近世斯比诺莎所立泛神之说,以为万物皆有本质,本质即神。其发见于外,一为思想,一为面积。凡有思想者,无不具有面积;凡有面积者,无不具有思想。是故世界流转,非神之使为流转,实神之自体流转。离于世界,更无他神;若离于神,亦无世界。此世界中,一事一物,虽有生灭,而本质则不生灭,万物相支,喻如帝网,互相牵掣,动不自由。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一粒飞沙,头数悉皆前定,故世必无真自由者。观其为说,以为万物皆空,似不如吠檀多教之离执着。若其不立一神,而以神为寓于万物,发蒙叫旦,如鸡后鸣,瞻顾东方,渐有精色矣。万物相支之说,不立一元,而以万物互为其元,亦近《华严》无尽缘起之义。虽然,神之称号,遮非神而为言;既曰泛神,则神名亦不必立。*章太炎:《无神论》,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32页。
章太炎还有着以佛法解读西学的思想,如他说:“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章太炎:《国家论》,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95页。他要用佛教的观点解读世界政治与历史,把传统的天下观转换成了国家观。*章太炎:《人无我论》,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65页。
蒋方震在其《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自序中曾说:“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复活,则‘宗教改革’也。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梁任公对此是“深韪其言”,并说:“中国之有佛教,虽深恶之者终不能遏绝之,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无可疑也。其益社会耶?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而已。”*转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0页。
太虚曾因其于净梵院赴弥勒院时触景而有所悟:
然人境交接,会逢其适,不自禁新气象之环感,新意思之勃生也!夫唯识论亦何新之有?然为欧美人及中国人思想学术之新交易、新倾向上种种需求所推荡催动,崭然濯然发露其精光于现代思潮之顶点;若桃花忽焉红遍堤上,湖山全景因是一新,能不谓之新唯识论乎?*太虚:《新的唯识论——九年三月在杭州作》,《太虚大师全书》第九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139页。
当时的西方思潮之与中国佛学研究者的影响何尝不是如此。
这种以西学比附中国佛学概念和思想的原因很多,其一,要以之比附来证明佛教、佛学和佛法加以昌明之必要;其二,要以之证明佛法皆适应自然之发展,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两千年演变,是符合进化之规律的,因而佛学一点也不亚于西方学术;其三,佛教也是符合自然进化论者,以证明佛法是科学的和必要的有力武器。这一切都反映了中国佛学研究者在面对西方学术力量时的一种思想的反应。
(二) 科学的渗入
在清末以后中国的文化生态中,“科学”不仅仅是一种智识的体系,是一种道德的力量,更是一种意识形态。胡适曾对此社会文化现象有所言道: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 无论懂与不懂的人, 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 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 究竟有无价值, 那是另一个问题。*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杨犁编:《胡适文萃》,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9月,第704页。
对科学的崇拜已经成为一种汹涌的社会潮流,这也就造成了此时佛学研究有着“科学”的特色。主要有:
第一,教内外的研究者也都在其研究中竞相谈及科学与理性,并强调佛教的科学性。
随着进化论、细胞学说、原子论、遗传学说等现代西方科学的基本思想和观念先后传入中国,一些学者即喜欢将之与其佛教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以此体现出思想的时代性、科学性和现代性。如章太炎曾说:“昔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曰名分。今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一曰公理,二曰进化,三曰惟物,四曰自然。”*章太炎:《四惑论》,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0页。杨度说:“佛教云者,非迷信的而科学的。”*杨度:《我佛偈赠美国贝博士》,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50页。故而,“今日世界为科学之世界,如欲将东洋固有之佛法(按:此处应指中国佛教),介绍于世界学者,普及于世界众生,则非有论理的科学的法门,不能随缘应机,说法度世。”*杨度:《新佛教论答梅光羲》,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18页。
第二,此时的研究者将科学的概念引入佛学研究之中,并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方式。这尤其在太虚等人那里更为明显。
太虚非常重视“现代思潮”的影响,并把大乘渐教与进化论结合起来考察,*参见太虚:《大乘渐教与进化论——十九年十一月在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讲》,《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十三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338页。重视将佛学概念与科学概念进行对比。他说:
科学之可贵,在乎唯征真理实事,不妄立一标格坚握之。以所知自封而拒所未知耳。若不求真是而妄排蔽,则与迷神教者亦复何异?习唯物科学者,若知佛乘唯识宗学,其贵乎理真事实,较唯物科学过无不及,则必不将佛教视同天魔畏途而相戒不游也。乃作此以忠告诸治唯物科学者!*太虚:《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十三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275页。
将佛学与科学关联起来,这在当时很多都是通过对唯识学的科学性进行强调为代表的,把佛教唯识学与科学结合起来是当时的一大特色。杨度说:“解剖心理,最近科学者,莫如法相一宗。”*杨度:《唯识八偈序》,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60页。黄忏华说:“况且唯识家底治学方法,和科学相近;而他底理论,又往往和科学哲学相发明;义蕴底精深,更有时超过科学、哲学很远,足以满足现代人理智底需要。所以要想在现代建立佛教,必须先弘阐唯识。”*黄忏华:《法相唯识学概论序》,《太虚大师全书》第三十二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503页。也有人说研究唯识学就是要“就科学之法式诠空有等意,引导今世科哲诸学”。*唐大圆:《起信论料简之忠告》,张曼涛主编:《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月,第163页。
第三,佛学研究者还重视从佛学理论中引出科学的方法,挖掘其中的科学功能。
如以救国为例,太虚指出,从佛法角度说,救国必须在“五明”处求,因为这五种科学有着“救世的功能之意义”。*《对于学生救国之商榷——二十年十月在河南大学讲》,《太虚大师全书》第26卷,第333页。具体地说,建设国家、调理社会,都非由力学不可,否则空谈救国,实际上必做不到,充其量不过是“五分钟热心”,根本不可能达到救国的真实功效。*同上书,第336页。太虚认识到,如日本法西斯发动的战争、奴役他人的邪魔力量之所以能够侵略其他国家,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彼日本以小国少数之人民,敢在中国残暴侵犯,虽是他们恶的动机之所发,其所以能养成他的恶势力,也是由于他学成了一种有组织有准备的为恶能力,方能施展出来。”*《对于学生救国之商榷——二十年十月在河南大学讲》,《太虚大师全书》第26卷,第336页。因此,中国的命运也必须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要重视利用科学技术的救国方法和途径。他说:“我们如真正发心救国,亦当从努力为学,去得到充足的学识与能力,方能具备救国的真实能力而负其大任。如致力水利,发达农工,开辟交通,国家内乱消灭,则政治可上轨道,人民之品性道德也自然可以进步。由是而表现强盛的国力,则一切外患亦自然不能侵入,方算真正达到救国之目的。所以,救国非力学不可,非有种种的专门学识与技能,及缜密宏通的思想不可。”*同上。
正因为太虚非常重视用当时的科学概念来诠释佛教思想,所以他写下了《佛法与科学》、《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新物理学与唯识论》、《新物理学的宇宙观》、《爱因斯坦相对论与唯识论》、《宇宙真相》等系列文章。
(三) 文本的转换
随着知识面的拓展,中国佛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汉传佛教的传统范围,目光投向了欧美和南洋,其例证、语汇和名词都有着“科学”和“时代”特色,同时也越来越有了“世界”的特点。欧美历史和人文精神也成了比较研究的对象。西方文化内涵融入到中国佛教研究之中,使中国佛学研究有了更加丰富的文本解读方式。
全新的文本解读和范畴革新,推动着新的佛学理论建构,形成了诸多新佛学思想,这也是与当时社会上盛行“新学”思想的文化环境相应的。所谓新学,即是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谭嗣同等提倡的富国强兵之学。梁任公曾说:“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厉,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传·谭嗣同传》,《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16页。“新学”之著作,著名的当为《仁学》,这是谭嗣同通过“闭户养心读收,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而成,“《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融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智识,尽量应用。又治佛学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12页。
在当时的学者看来,佛教研究不仅有着东西方思想间的交流吸收,有着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问题,有着传统佛教文本的现代性转换问题,也有着从纯文本研究向现实人生建设的转换问题。这一点也正是人间佛教产生的学术动力。虽然各家对“新佛教”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与社会上“新学”流行相应的。如,杨度(1875—1931)于1928年8月曾作有《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谭嗣同则是致力于将传统佛学文本进行现代转换的重要代表。浏阳之学本出于今文经学派,其仁学思想中杂糅中国佛教理论,又吸收了新约及西方算学、格致和社会学的观点,并以之发挥儒家及《礼运》中的大同思想,为其政治主张提供支持。谭嗣同说: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算学即不深,西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
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谭嗣同:《仁学界说》(第25、26、27条),《仁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8—9页。
梁启超对谭嗣同有着高度的评价,称他是当时“未易一二见”的、为数不多的“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12页。并称其学是要“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同上。正是这种带有时代气息的崭新思想对青年时代的太虚有着强烈的影响和启发。太虚曾自称:“对于谭嗣同的仁学,尤极为钦佩。由此转变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太虚:《我的宗教经验——二十九年二月在舍卫国对佛教访问团团员讲》,《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十二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305页。在当时,他甚至有了“凭自所得的佛法,再充实些新知识,便能救世”的思想。*同上。
早年,太虚听了华山法师的指点之后,而对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和天演论等西方科学知识有了兴趣,对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章太炎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诸多他以前不曾注意过的思想和书籍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学术思想和著作曾经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及社会大众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们对年轻的太虚也有着强烈的影响。太虚说:
至世间法则迁流无常;因乎时分而生种种差别,众生之心亦因之而有种种之殊异:若不随顺世间巧施言说,以应其时而投其机,则宜于此者或失于彼,合于过去而不合于现在,故佛法有适化时机之必要!夫契应常理者佛法之正体,适化时机者佛法之妙用,综斯二义以为原则,佛法之体用斯备。若应常理而不适化时机,则失佛法之妙用;适化时机而不契应常理,则失佛法之正体。皆非所以明佛法也。*太虚:《佛乘宗要论》,《太虚大师全书》第一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109页。
当时著名学者的著作,大都是在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也都曲折地传达着其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和政治改革的设想。或者说,都是西方文化的反映。太虚大师革新佛教的精神和人间佛教的建设理念,不仅仍然从本土文化中发掘内涵,也重视将之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太虚说:
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的特点在何处,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力求人类生活如何能够得到很和平很优美。所应用的工具乃科学的;所实行的方法乃社会的、有组织的群众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成功科学的、组织化的生活。现在中国民族所奉行的,是中山先生集合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华和世界上一切文化的特长的三民主义,要求佛学昌明于中国昌明于世界,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昌明佛学,建设佛学!引人到佛学光明之路,由人生发达到佛。小乘佛法,离开世界,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大乘顿教,也有与现代思想不相合的地方。能与现在的中国民族世界人类最相宜的,以大乘渐教为最。大乘渐教以人类为基础,进一步有一步的实证,就是大乘渐进之法,与科学化、组织化渐得完善之法相近。所以在此时显扬佛法,应当提倡大乘渐教。*太虚:《佛陀学纲》,《太虚大师全书》第一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203—204页。
随着对西方文化的深研,此时的佛学研究者已经从传统的比附儒家、老庄,变成比附西方的科学、民主,从言必称《语》《孟》《孝》《礼》,变成言必称柏拉图、康德或卢梭。他们从惯依《诗》《书》《语》《孟》变成了径引康德、斯宾诺沙等人之说,语言中有了物质和意识,有了主体和客体,有了唯物和唯心。在新的文本中,众生换成了人民,天下换成了国家,转轮王换成了总统。这种比附,大都是基于认为欧美文化的先进和欧美社会的繁荣是因其发达的宗教之使然的心态,所以西方的文本模式即不由自主地成为一种学术解析方法。在本质上说,这与汉魏时期的比附在心理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
但是,在借鉴西方和日本学术方法之时,佛学研究者们也发现了西方学术方法的不足。如在中国佛学研究领域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争执之起因,不仅是源于日本人的影响,更是来源于日本和欧洲的历史和哲学方法。所以时人唐大圆(1885—1941)则斥王恩洋关于《起信论》的观点是“明斥远西哲学,而暗效倭人诡辩”。*唐大圆:《起信论料简之忠告》,张曼涛主编:《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月,第163页。
太虚曾深刻指出:
要知西洋人之学术,由向外境测验得来,乍观一层粗浅零碎皮相,后人凭借以条贯整齐之,更进察其隐微,于是日趋完密,或因而又发见另一物焉。不然者,则向学说上推论得来。甲立一说而乙驳之,甲乙相驳之下,两派之短毕彰,两派之长尽露,于是有丙者起,除两派之所短,集两派之所长,而着后来居上之效,故有发达进化之程序可推测。
而东洋人之道术,则皆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又不然、则从遗言索隐阐幽得来。故与西洋人学术进化之历程适相反对,而佛学尤甚焉。用西洋学术进化论以律东洋其余之道术,已方柄圆凿,格格不入,况可以之治佛学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不图吾国人乃亦竞投入此迷网耶!吾为此说,非漫无征据者,在确知东方人道术之来源者,固已不待往下再说;然姑试举印度、支那之学术史数事以证。*太虚:《评大乘起信论考证——十一年十二月作》,《太虚大师全书》第一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27页。
他还说:
近来中国佛教的情形,因为受到日本新的研究方法的影响起了很多变化,尤其是西藏佛教近亦影响内地很大……但西藏依因明比量的辩论方式兴复与现今的中国佛教很有补益,因为中国佛法之衰病在儱侗,以此为劝学因明研究教理之一方便,固亦甚善。所以本人近年在重庆办一汉藏教理院,以汉文藏文而研究此两种文字的佛法,使互为沟通以相补充。*太虚:《几点佛法的要义》,《太虚大师全书》第一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1月,第372页。
随着“天朝”思想的崩溃,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仅是世界万邦中的普通一国,中国的学术也仅是世界学术中的一部分。于是那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上的自豪感和错误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僧众和学者的视野有了很大的开阔,他们对外部世界有着相对深入的认识。欧洲的学术理念、日本的佛学研究方法等曾经对当时的研究者以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佛学研究文本的转变。但是在对他们借鉴学习之时,一些人也对其方法进行了反思,对其学术思潮进行了批判。
四、 在现实社会中建设中国佛学
清末民国的佛教复兴运动,百余年间,大师辈出,成果辉煌,影响深远,标志着中国佛教复兴事业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建设新佛教的运动并没有停止,佛学研究仍然需要有新的学术动力。今天,更高程度的全球化、工业化及其所造就的具有西方话语特色的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学术解析力量,使当代佛学研究面临着更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一) 推动中国佛学的国际进程
文化都是在被传播、转换和创造中发展的。中国佛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佛学研究的国际性。它包括佛学研究者、研究过程、研究方法和内容、依据文本和成果展示等要素的国际性。探索新的国际化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以使在国际佛学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创新中国佛学研究的话语方式等,这对当代中国佛学研究者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挑战。
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学术公器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与百年前相比,中国佛教的学术土壤更为深厚,佛学的内涵更为丰富,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心态更为自信,中外佛学研究交流也更为深远。正因为如此,佛学研究有着更加多样化的内容和方式,有着更为丰富的文本和多元的文化背景,有着越来越国际化的佛学研究主体。今天,中国佛学的研究者不仅包括两岸四地的教内外研究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及其他国家的不同背景和身份的学者。
而且,当代的佛学研究者,由于其文化传承的不同,往往会依据不同语言的藏经,通过各种宗教文化间的比较而开展研究,并以不同的语言为载体发表其成果。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中国佛学的研究也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必须拓展当代佛学的研究领域,掌握并引领佛学发展的学术方向。诸如,在工业化时代继续强化和深化以汉传佛教为立足点的研究,加强与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日本佛教的比较研究,了解并研究百余年来欧美社会中的佛教发展及学术成就,推动国际佛学研究者对中文藏经和近代研究成果的深度使用等。*参见王建光:《促进文本的多样性,强化参与的国际性——当代中国佛教研究文本国际性参与略论》,南京:《江苏佛教》,2011年第1期。
如果说,清末民国时期的佛学研究者们还对西方学术方法的解析有点不适应,还是重在学习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佛学研究应该通过多语种的国际性佛学研究成果的展示,在国际平台上强化中国佛学的角色形象和学术影响,使中国佛学及其研究具有引领性、主导性和国际性,实现从学术方法输入到学术成果输出的转变。
(二) 强化中国佛学的世界特色
如果说,近代的佛学复兴形成了中国佛学的学科特色,有了与欧美学术进行对话平台,那么当代佛学研究应该重在确立“中国佛学”的世界性特色。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欧洲的学术视野中,对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和南亚佛教的认识有着明显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欧洲文化没有在日本和南亚地区遭遇到强大的文化抵抗和学术解读的竞争,所以欧洲人对他们的敌意也相对较弱,对其研究也相对深入。而中国文化由于有着强大的文化抵抗力和国际竞争力,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也更为强烈,这一方面引起欧洲一些人的敌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他们全面客观深入认识中国文化的难度。所以,即使在今天,中国佛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还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困难。
文化都是在竞争中发展的。一方面,中国当代佛学仍然面临着与西方学术研究的竞争,仍然面临着强势的西方文化(比如英语佛教)的解读和挑战;另一方面,今天的学术研究有着比先辈们更好的社会文化背景,学者对西方有着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因此在与西方文化交流和竞争中,能够更好地吸收、消化西方的学术思想,以创新和发展中国的佛学研究。
有鉴于此,在当代中国佛学的研究成果传播、大藏经典翻译、国际学术交流等活动中,要协调、凝聚两岸四地及海外华人佛学研究的学术资源,搭建国际平台,增强话语力量。办好几种当代中国佛学研究的多语种、高品质的国际性学术刊物,以推动新时代“中国佛学”的发展,通过对学术力量和成果的汇聚,推动中国的“中国佛学”走向世界的学术舞台,并最终形成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佛学”。
(三) 增强当代佛学的社会功能
清末民国之际学者进行的新佛教建设,其要实乃志在使传统的佛教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贴近人生。如谭嗣同和杨度的新佛教理想、太虚的人间佛教建设运动等努力,都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相适应、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佛学研究的繁荣必须立足于关注现实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运动。
服务社会和人生正是释迦精神的本质,不仅是当代佛学的力量之源,也是佛法长住的根本所在。不论是新佛教或者是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新佛教,都必须立足于对现实人生关怀的基础上。当代社会的工业发展和生活竞争,使人们面临着更大、更多和更新型的精神与生活压力,人们需要多种的精神关怀。所以,不论是在诸如都市佛教与乡村佛教、丛林佛学与公民佛学、文本佛教与田野佛学(按:姑且如此称之)等的研究中,都必须关注工业化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
现代性是一种学术的动力,也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佛学的现代性和国际性建设不是仅仅通过文本建设能够完成的,不是通过西化的名相和遥远的丛林得以建立的,而是要通过深刻的研究成果,使文本中的力量现实化、社会化,以服务社会、净化人心,并在此过程中,促进中国佛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事实上,中国佛学的现代性建构,不是要把佛教的精神文本化、复杂化,而是要继续拓展研究领域,探索服务现代社会的方法和途径,以更加贴近社会、服务人生。通过服务社会、扎根人心而体现出其中的现代性品质,彰显其中的现代性内涵。*关于现代性佛教的问题,笔者在《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及其当代走向》一文中,曾经提出了三个方面:一者,在现代性的舞台上,中国佛教的现代性首先是应当表现出更多的国际性。二者,在后殖民的语境中,中国佛教应当解决汉语的“中国佛教”如何走向国际的问题。三者,在工业文明的作用下,要重视研究中国佛教主体角色的现代性定位问题。(参见王建光:《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及其当代走向》,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简言之,佛学的现代性的标志正是它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程度。或者说,中国佛学的现代性、中国佛学能否国际化,正是在于它的当代有用性和服务性。
结 语
随着藩属朝贡的东亚体系被世界贸易的大潮冲垮,中国社会新的文化思潮和知识阶层得以形成,并促进了中国学术方法的革命。这主要表现在:格物致知的思想被“科学”思想代替,经世致用的思想被经济和产业的思想代替,重农轻商的观念被富国强兵的思想代替,伦理式的天下观变成了陌生的国家观。
尽管因为时代的制约和文字、翻译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近代的个别佛学研究者对一些西学思想和学术方法的理解并不准确和全面,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中国佛学研究也随之完成了从五印向五大洲的空间转换,完成了从内外之学向世界学术的思想超越,初步形成了世界佛学的研究视野。清末民国的佛学研究,展示了全新的文化力量和鲜明的学术特色,推动着中国佛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初步完成了中国佛学研究的现代性方法转换,这一切都对当代佛学研究与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