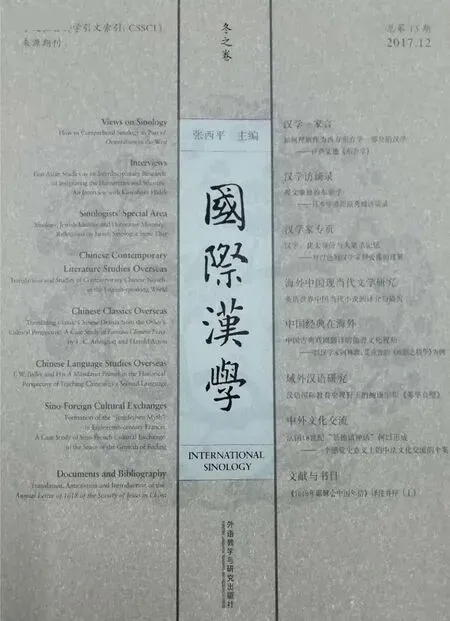“见林而不见树”—评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2017-01-28□
□
任何一部文学史著作皆或隐或显地贯穿、体现着作者本人的文学史观。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Die Chinesischf Literatur IM 20.Jahrhundert)亦不例外。在前言中,顾彬写道,他在“行文中给出的评价都是个人的主观见解,并不图普遍有效,尤其不奢望经久不灭。”①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以下引用该著文字,均于正文中注明页码。此种表述令人惊讶。周作人在90年前即1927年发表的《答芸深先生》一文中,已经涉及文学史撰写及文学史观问题,周作人说,“文学史如果不是个人的爱读书目提要,只选中意的诗文来评论一番”,那么,它就是“以叙述文学潮流之变迁为主”。②周作人:《谈龙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史会仅仅代表著者个人一己之看法。实际上,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更多借助了德国学者的翻译、评论和研究。在第二章中,顾彬甚至以决然的口气说道:“任何一部文学史的写作的关键点在于,它绝对必须以其他学者的认识为依托。”(第60页)文学史家个人的主观见解与其他学者的认识之间,最终要达成某种一致性;而过于强烈的主观见解,则往往造成一种认识上的盲区。
这部文学史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脚注部分已经显示了,它所引用的评论、观点全部出自德国学者,几乎看不到中国批评家、文学史家的论述。一只眼睛只能看到全体的一半。倘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外国文学史家撰写某国文学史,行文中仅仅引用中国学者和翻译家的评述和研究,仅仅依赖二手资料,而不选择、采录该国批评家和学者的批评、论述,那么,如此的著作从成色、质地上看,只能是二三流的,其可信度不可能有多高。中国出色的外国文学史家们,他们奉献出来的著作呈现了原汁原味的特点。举一个例子:叶渭渠、唐月梅著《20世纪日本文学史》③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第4版),青岛:青岛出版社,2014年。,凡所引用之处,均出自日文资料,偶尔采用中译本;著者的史识及史观隐藏在丰富的史料后面,亦体现在对文学思潮的梳理和作家作品的评价等方面。读罢全书,在大体知晓文学史演变的同时,多少了解了优秀作家作品。相比之下,顾彬的“主观见解”以及只引本国学者成果的行文方式,妨碍了他的认识、判断和取舍,不能区分出优秀作家与次要作家,也不能确定经典的和优秀的作品,而这恰是一个文学史家的职志所在,是一部文学史的最终目的。
在文学史的起始和性质、重要文学理论问题、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评价诸多方面,这部文学史都存在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整体框架基本上为一种逻辑的建构,而非史实的描述、辨析和判断,尤非立足于史实基础上对文学史规律的探寻。因而在貌似严密的逻辑链下面,实则是过于随意的链接、撮合,那种表现在论述方面的过度阐释,则贯穿了全书始终,随处可见。
一
顾彬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划分为“民国时期文学”与“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这是一种保险、安全而又不用心思的划分法,没什么可说的。证明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这才显示了顾彬的文学史构想,显示了他的良苦用心。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一个影响颇为广泛的观点—中国现代作家的眼光只盯着自己民族和国家,从未超出中国范畴,未能“把中国的困蹇,喻为现代人的病态”①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61页。,故而与世界文学观念相左,顾彬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可以看出他是并不认可的(第7、9页)。针对一种普遍缺乏的中国现代文学“置根于世界文学”的认识,顾彬提出了他的“关于现代中国文学是自我救赎工程”的论点,来证明情况并非如此。此亦可看作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的定位。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点:
第一,“五四”运动的解放具有双重意义,即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前者从属于后者;无论是个人自由还是社会自由均以“救国”为目的,“这是中国从1919年到1949年走过的道路,文学只是这一道路的反映”。作家甘愿为此放弃自身全部利益,原因在于“这和中国革命的反宗教的、世俗化了的特征有关”。(第30页)
第二,类似于“福音”世俗化形式的“现代和改革”并未带来政治和社会的“救赎”,结果是“旨在将中国从民族和社会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中国现代派的许诺,一旦被当作了宗教替代品,其后果很可能就是让知识分子翘首期待一个‘超人’、一个‘领袖’,也就是一个弥赛亚式的被世俗化的圣者形象,从而无条件地献身到革命事业中去”。(第32页)
第三,对超人的接受以及伴随着“打倒孔家店”之类口号,“导致了对人的力量不断升级的信仰”,过去的传统失灵了,自我在尼采学说的滋养下增强和膨胀;过去是“神的显灵”(传统),现在则是“自我显灵”了,“从‘神的显灵’向‘自我的显灵’过渡不是从宗教向世俗化态度的简单转移,而是新观念利用了旧传统的象征之物,由此使自己成为了一种新宗教。激情再一次为其所用,这种激情现在承担了合法化的功用”。(第43—44页)
第四,以郭沫若诗歌为例,过去依靠传统、依靠宗教来拓展自身能力的东西,现在变成了“自身”,郭沫若诗中“欢呼自我”,将一切“归功于自己”,说明其间发生了一种“崇高的转移”,“崇高的不再是宗教和传统,崇高的首先是个人,然后是集体,尤其是国家”。郭沫若那么起劲地先是歌颂个人,然后再歌颂无产阶级,接着又歌颂起了领袖,即为一个显在的例证。(第46页)
这便是顾彬的中国现代文学“自我救赎工程”的主要内容,再浓缩一下其主旨:传统失灵了,改革“救赎”失败了,个人或“自我”由此膨胀为一种“新宗教”;既然成了“新宗教”,势必会“造神”,会寻找一种替代品—集体、国家,最好是一个超人式的领袖。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推导出的结论与“置根于世界文学”这个大前提之间,南其辕而北其辙。
仿佛为了强化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置根”于世界文学、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顾彬干脆说道:“中国现代文学严格说来也可以理解为对西方范本的‘翻译’。”此处的“翻译”乃实指,非象征意义,顾彬说,“要研究一部现代中国文学的著作,先摸清它当时所据的底本情况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他抱怨本来属于“翻译学”的任务却落在文学研究者头上,负担太重了。(第72页)
顾彬的文学史阐释显然是一种逻辑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基本无关。他不是从现代文学史实中抽绎某种共性,而是先设定了“救赎”观念之后,再以现代文学事例作为证明。其实,这个观念本来不证自明,何须证明。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所谓“救赎工程”内容何以那样的奇奇怪怪、莫名其妙;也唯有明白了这一点,也才能够看出顾彬的“循环论证”让他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救赎”工程导致的自我、集体、国家、超人、领袖云云,不正是夏志清早就指摘过的眼光只盯着民族、国家因而难有超越的观点吗?
在导论结尾部分,顾彬解释了中国现代文学为何至今不能“从阐释的政治轨道上完全挣脱出来”,原因在于“档案还未全部开放”,研究者无法摆脱偏见,“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决于阐释者及其阐释的形象。”(第9页)也因此,顾彬忽视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的共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常识,以阐释代替常识,在两种缺乏内在逻辑关系的对象之间,直接建立起一种逻辑链,就好像历史上确凿无疑地发生过这种事情一样。最典型的案例表现在现当代文学过渡期的描述及阐释上。
从史实的角度言之,苏曼殊对新文学的影响甚微,根本不能与梁启超、林纾等人相提并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二代作家们甚至不提苏曼殊的名字。1948年,朱光潜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一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进行初步总结:
由古文学到新文学,中间经过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时期。在这时期,一些影响很大的作品既然够不上现在所谓“新”,却也不像古人所谓“古”。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林纾的翻译小说,严复的翻译学术文,章士钊的政论文以及白话文未流行以前的一般学术文与政论文都属于这一类。他们还是运用文言,却已打破古文的许多拘束,往往尽情流露,酣畅淋漓,容易引人入胜。
新文学所受的影响主要是西方文学,所以不得不略谈翻译。林纾以古文译二流小说,歪曲删节,原文风味无存。但是,他是第一个人引起中国人对西方小说发生兴趣的,功劳未可泯没。①朱光潜:《朱光潜全集·欣慨室中国文学论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6—157、160页。
史实重证据,后来的研究者哪怕用了再好的阐释,也不能替代事实本身,顾彬却在行文中不经意间把一种解释当成了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一节中,顾彬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实证性地论断道,苏曼殊有几篇小说给文言文小说画上句号,“并且过渡到了一种现代性的叙事策略”;他更为实证性地下断语:
苏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对病态做了不加粉饰的描写。他成功地做到了把新素材示范性地集中于单个人物,通过典范而使之具象化。像众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也为中国现代派的摇摆不定精神打下了根基,这种根基和在西方一样,一方面具有精密、理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却带有迟于行动、内心分裂、躁动、苦闷和自我失落的特点。(第22页)
这段文字中第一句就错了。要论起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还轮不到苏曼殊。胡适于1922年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其中第七节专论章太炎,称赞章是古文学五十年结束时期“结束的人物”,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也即古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②胡适:《胡适文存二集》(二),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147、153页。顾彬所说苏曼殊与“众多同时代人一样”,为一种精神“打下了根基”,本应为确凿的事实和证据,却出自于一种随意的表述。倘要找事实、找影响、找“众多同时代人”、找怎样打下一种精神基础,总之,拿出证据来。还真的没有,因为苏曼殊本来影响就很小,无论怎样夸大亦与事实无涉。
顾彬的逻辑建构还表现在当代文学(1949—1979年)与新时期文学关系的论述上。对这两个时段的文学史,现在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这是两种拥有不同话语系统、不同性质的文学,“阶级性”和“人性”标示了二者间的区别。顾彬声称,他不会像其他人那样避而不谈甚或嘲讽1949—1979年的文学,他认为那几十年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一种自有的美学体系”,要严肃地对待之,目的在于“可以借助这些作品认识毛主义的内在性质,以及去理解1979年以后的新文学,而人们经常把新文学同之前的文学对立起来”。如何理解呢?顾彬做了一个示范性的分析:比如,翟永明1984年发表的《女人》组诗中“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以及“太阳,我在怀疑”,表明“这不仅对郭沫若代表的太阳崇拜,也是对官方话语中的光明隐喻—类似《光明日报》标题—提出质疑”,这种解释似乎把文学当成了社会学材料。顾彬说,他只能如此理解,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可能性。”(第255页)
中国新时期文学对前30年尤其“文革”文学的反拨、改写、戏仿等,不在少数,莫言《红高粱家族》对战争文学的改写,即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顾彬不以莫言为例,而选取了他为之“写了无数文章”的翟永明(第323页注释②),足见他个人的偏好,独不见文学内部的演变规律。在本书中,顾彬多次以翟永明及其诗歌作为阐释的根据,比如“北岛的‘我不相信’和后来翟永明的‘我站起来’共同构成了80年代男性和女性反抗的支柱”(第304页)。“我不相信”(《回答》)在当时即产生了较大反响和影响,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定的和固定的文学形象,传达着一个时代的心声和诉求。相比之下,翟永明的“我站起来”其时鲜有人知,今天亦无人提及。一个影响广泛的意象与一个无人知晓的意象,如何能够同时构成一对精神上的“支柱”?对翟永明的诗歌,顾彬似乎有点欲罢不能,论述杨炼诗《人日》时,他再次写道,杨炼的诗作“再造了由郭沫若创立、由翟永明终结的太阳崇拜”(第334页)。倘若翟永明真的终结了“太阳崇拜”,那将不仅仅是当代文学史,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史上大书特书的一笔,人人皆知了。
附带一句,翟永明诗歌中有一个特点,意象上喜用全称判断,描述和抒情方面则多用极致的说法。试从《女人》组诗中摘出数句,以见一斑:“岁月正在屠杀人类的秩序”“整个宇宙充满我的眼睛”“所有的岁月”“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使大地在你脚下卑微地转动”“我就容纳这个世界”“从此我举起一个沉重的天空”“用人类的唯一手段”“苦难……被重新写进天空”等等。这样一种亢奋、激昂以及大而无当的文风、诗风,与前30年文学尤其与“文革”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真想要细绎两种不同形态文学间的因果变化,翟永明的诗歌当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案例。
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顾彬更是不要事实证据,只着意于一种建构。比如“文革”时期的“三突出”原则,顾彬断然写道:
为了同1949年以来所谓的文艺黑路线作斗争,江青推出五部样板戏作为艺术创作模式,典型体现了“三突出”的新美学观。……我们发现,这实际上移植了基督文明“最后的晚餐”之类的绘画作品,毛主义绘画在突出政治领袖方面无疑借鉴了前者。从文学角度而言,事情当然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但我们无疑可以从中看出某种相似性。(第287页)
“三突出”原则为于会泳首创。据戴嘉枋《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1968年,时值“样板戏”问世一周年,《文汇报》文艺部负责人约请于会泳写一篇文章,专述在江青领导下“样板戏”如何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胜利诞生。于会泳注意到江青在“京剧革命”中颠来倒去只有一句话“塑造好革命英雄形象”,经过反复揣摩、迎合,于会泳第一次发明了新名词“三突出”,后经姚文元修改,遂逐渐成为“文革”时期文艺工作者必须恪守的金科玉律。①戴嘉枋:《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第218—220页。从酝酿到出台,于会泳并没有而且也根本不可能从“基督文明”、从“最后的晚餐”中受到启发,从而发明“三突出”原则。顾彬依据何种稀见史料,那样肯定地说他“发现”了这个名词“实际上移植”了基督文明?
二
在评价、阐释一个文本时,这部文学史著作确乎体现了顾彬本人的文学史观,即个人“主观见解”过于强烈,对某个文本的分析和结论,往往将其从作家的整体创作风格中抽离出来,忽略了文本本身的主旨和意图。所谓主观,不是不要理论,师心自用,顾彬会依仗另外一些他似乎感兴趣的观念、理论,如宇宙、天地、生命、宗教、性等等,切入一个文本。这些观念和理论与一个文本自身得以产生的语境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所以,顾彬的阐释让人一读之下会觉得新奇,再读之后便觉新奇到了奇怪的地步。归纳起来,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放大一个文本中居次要地位的主题,或者给一个文本附加它本身没有的,也不可能拥有的内涵和意义。阅读这种分析,让人觉得好像也有道理,但是觉得无论他怎么说,所说的就是与该文本无关。试举二例。先看鲁迅的例子:
反之,在短篇小说《一件小事》中我们可看到作者后来同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种预示。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的目光离开了粗俗淳朴的民间大众,他通过人力车夫这个形象把无产阶级变成了未来的承担者;同时第一次投身于民国时代的社会事件中。鲁迅是第一位在小说中关注无权无势的下层民众的作家。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阿Q正传》中,他破天荒地给一位农民作“传”,给这位受侮辱者竖起了一方纪念碑。(第39页)
《一件小事》创作于1919年,受到了当时倡导的“劳工神圣”理论影响,也有鲁迅自己的一点平日乘坐人力车经历在内,或许还受到了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橘子》的启发,后者写了一个乡下贫苦女孩的美好心灵。①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一件小事》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大到与其形制、内容不相符合的程度,张中行就颇不以为然地说,是沾了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光,“名声大会孕育独占性”。②张中行:《张中行作品集》(第五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93页。今天回头再看这个小说,它确实只是一篇速写,鲁迅把自己的所见所感,也就是一种即时的情绪放大了,说它乃一时兴到之语,亦未尝不可。1919年的鲁迅,正处于全力批判国民性且锋芒毕露的阶段,他的笔下突然出现了一个背影高大的人力车夫,高大到“须仰视才见”的程度,这与其时鲁迅的整体创作风格严重不符。张中行视此篇为“滥竽充数”,虽用语刻薄,亦属准确评价。顾彬脱离开必要的历史语境,给这个文本戴上了两顶高帽子:“同情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把无产阶级变成了未来的承担者”。对1919年的鲁迅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无产阶级等等还是些很生僻的词语,一直要到1928年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论战时,才渐次出现在他的笔下。其实,顾彬给这个文本戴上大帽子,无非想要表明鲁迅具有预见能力和先见之明。过去鲁迅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将鲁迅拔高的风气,用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印证鲁迅先前发表的文章,其逻辑方法为由果推导出因,最后在因、果之间划上等号。顾彬或许也受此风气浸染,走得则更远了。严格地说,鲁迅“通过人力车夫这个形象把无产阶级变成了未来的承担者;同时第一次投身于民国时代的社会事件中”,整个句子意指它不只是对文本的分析,也是关于鲁迅本人的史实。可是,说鲁迅在1919年就通过一篇速写作品把“无产阶级”变成了“未来的承担者”,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化;同时,鲁迅在1919年“第一次”投入民国的社会事件中,也是一个常识性错误。1912年2月中旬,鲁迅即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参与教育、社会的活动,何必要等到1919年写《一件小事》的时候,才投身“社会事件”中?
再看阿Q。顾彬的第一句话便说错了,阿Q并不是“一位农民”,无需多说;视阿Q为一个“受侮辱者”,也大成问题。喝醉了酒的阿Q,于得意之余,会飘飘然地唱几句“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假洋鬼子”之所以拿黄漆手杖敲打他的癞疤脑袋,盖因他骂人家“秃儿。驴……”在先;头上同样挨了赵秀才的一顿竹杠,也属自找晦气,盖因情欲发动,想和赵家佣人吴妈“困觉”。阿Q性格中颇有好斗的因子,谁敢触及他的“癞疤疮”,便立刻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和王胡打,和小D打,打不过时,“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欺负起更为弱小的小尼姑来,阿Q一点也不手软,摸人家的头,扭人家的脸,于看客们的喝彩声中又狠狠地用力一拧,这才放手。如此一个近似于无赖的人物,怎么可能是“受侮辱者”呢?鲁迅竖起的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诸多低劣不堪的东西,那真的不是一方“纪念碑”。
第二,在一些文本中总想着要发掘出性的意蕴来,在性的主题上又挖出更深的“寓意”。试以对张天翼短篇小说《脊背与奶子》的分析为例。
“族绅”长太爷是一淫棍,觊觎村妇任三嫂,尤对其丰满坚挺的奶子充满难以遏制的欲望,百计勾引、以债相逼而终不成,于是以其有相好为罪名,施行家法,判决“筋条”抽打一百下,后任三嫂设计逃出。这便是《脊背与奶子》的大致情节。故事并不复杂,描画颇为生动,人物情态跃然纸上,多写实,少夸张,与张天翼其他讽刺小说有些区别。顾彬挑出“奶子”意象,阐发了其中意义:
小说把奶子比喻作坟堆,也含有这一种寓意:正是女性生养和哺育了祖先,祖先能继续活在后代的意识中,也是因为后人仿效那哺育了他们祖先的形式。我们知道,以充作榜样的故事中,母乳的滋养也是对病入膏肓的家族长辈一种孝敬的方式。长太爷三次伸手去抓任三嫂的乳房,不只是对一个性目标的攫取,这里的抓也包含了一种延续自己和宗族生命的要求。儿媳妇的密谋让这些希望都化为泡影。她逃脱了,只剩下坟堆和长太爷对她身体的回忆,农村的娜拉取得了胜利,男性家长制势将灭亡。(第144页)
“奶子”和“坟墓”两个意象出自小说第八节也是最后一节:
东边挂出了大半个月亮,像一瓣橘子。长太爷在孝子桥边踱着。突出的颧骨在月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他觉得一切的景物都可爱起来,那些干枯的瘦树仿佛很苗条。前面那灰白色的山似乎在对他笑。坟堆像任三嫂的奶子。
“唔,奶子……”
不过这可有点儿不大对,坟堆是硬的。①张天翼:《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第341页。
比照可知,顾彬误读了,读反了,不是“小说把奶子比喻作坟堆”,长太爷在孝子桥边等任三嫂,淫欲挠心,看着月光下一切都那么可爱,连“坟墓”也像任三嫂的奶子。整个文本的倾向性非常明确:一个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所谓“族绅”,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先使用“家法”把誓不相从的任三嫂打个半死,接着又以任三嫂丈夫欠钱相要挟,让她陪睡来抵账。这是一个否定性的人物,是被作者着力鞭挞的反面形象,可顾彬却从中释读出了正面意义:长太爷多次想抓任三嫂的乳房,表达了延续宗族生命的要求;奶子以及“母乳”也成了对长太爷之流的“孝敬方式”。这样的解释,源于解释者不能体察,尤其不能感受文本的倾向、文气、情调、氛围所致。
再看顾彬对郁达夫短篇小说《过去》的阐释。郁达夫的部分小说中带有色情、变态的意味,这篇也是。叙事者—一个报纸编辑,喜欢上了一个活泼然而时时对其施虐的女子,以肥掌击脸,拿尖头鞋踢腰,一切玩弄、轻视都会让他感到“不可名状的满足”;想到她那肥嫩白皙的脚,要是放在自己的碗里“咀吮一番”,一定很舒服,想及此又“要多吃一碗”饭。对这样一个除了有些许色情意味而别无深意的细节,顾彬从中阐发出了“更深层的维度”:
鞋的象征对象是阴户。去折磨和用来折磨主人公的物件,因此正是他所期盼的对象。此外,饭碗在传统意义上代表着宇宙秩序:上象征着天,下象征着地。男人在传统意义上是天,女人是地。如果这种秩序颠倒过来,碗中的双足象征性地居于上方,女人控制着男人。男人变成了女人的奴仆,咀吮双足对于生命之重要就如同对米饭的需求。(第59页)
这些“寓意”或“维度”,属过度阐释,与文本无关。
类似的阐发所在多有,如茅盾《子夜》“是一部明争暗斗的两性之战”(第113页),如茹志鹃《百合花》中叙事者(护士)和新媳妇都爱上小通讯员,后者牺牲后挂包里的两个馒头也表示了“东西成双,(心上)人迹杳然”(第271—272页)等。顾彬高度评价歌剧《刘三姐》为“民族艺术的典范”,概括它的内容为“一名叫刘三姐的青年女子能够和三名男子对歌。这种常用的舞台技巧叫做‘一女三男’。这种歌剧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国观众”。(第290页)实际上那“三男”只是财主莫海仁请来的三个乡村秀才。莫财主以收田、还钱相逼,欲强娶刘三姐,刘则以对歌为条件:对输了,嫁给莫财主;对赢了,从此不许莫财主禁山封地、霸占西山茶林。莫财主重金请来陶、李、罗三个“之乎者也烂秀才”与刘三姐对歌,这几位哪里是刘的对手,几番比唱,最终“张口结舌”“狼狈下场”。刘三姐与三个“烂秀才”对歌是在第五场“对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即便勉强概括为“一女三男”,也不可以作为全剧的结构或者技巧。①《刘三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第33—51页。不知顾彬何所据,竟归纳出了带有情色意味的“一女三男”的技巧,而且还是舞台上的“常用技巧”。
鲁迅早已指出了,有些“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鲁迅所举的例子,乃日本人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安冈氏说中国人嗜笋,且想象其挺然翘然的姿势,可证这是一个好色的民族。②《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顾彬的阐释比起安冈氏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以西方宗教概念、术语,来比附一些文本或意象,有时甚至走得更远,在没有文献证据的情况下,断定某些文本或意象受到了西方宗教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鲁迅“荒原”意象的阐释。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说独有叫喊于生人中得不到反应,其感觉便“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慨叹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顾彬肯定地说“荒原”一词就是出自于《圣经》:“在鲁迅的早期作品中出现的旷野意象,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派的一个母题,在其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不同的范本来。它与声音的结合最明显的当然是出自《圣经》。但是怎样合乎道理地解释这样的猜想:即它与‘旷野中的呼喊者’是相关的?……作家以先知自命,他在回顾中却充满了批判精神。”(第32页)这里顾彬也作了一点考证,追踪了“参考书目”:辜鸿铭于20世纪20年代曾在德国出版过一本论文集,名为《呐喊》,表示书名的词语可追溯至拉丁文《圣经》中。但是,顾彬并没有进一步论证,辜鸿铭所用的书名与鲁迅小说集名“呐喊”,特别是与“荒原”意象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鲁迅于何时接触到辜鸿铭的论文;谁能证明鲁迅笔下的“荒原”即是通过辜书、再直达《圣经》的,等等。把中文译本《圣经》里的“旷野”等同于鲁迅笔下的“荒原”,也是很随意的一种行文方式。
如果稍稍顾及上下文联系,《〈呐喊〉自序》中的“荒原”一词并非多么难以索解,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怀抱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鲁迅,独自叫喊于“生人”即国民中间,却得不到一丝回应,使他感到寂寞,一如置身于无边际的“荒原”,“荒原”显然指中国社会。尚钺发表于1925年的《鲁迅先生》一文中,以大半篇幅谈论《〈呐喊〉自序》一文,明确地说道,鲁迅文中的“荒原”就是中国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做梦了,“连‘寂寞’也快被摩擦消灭了”,而与此“寂寞”适成反比的“只有沉溺于虚荣、骄傲、势利忙杀、欺骗忙杀的没有灵魂的东西”。③尚钺:《鲁迅先生》,李何林编《鲁迅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页。
《〈呐喊〉自序》中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比喻“铁屋子”,亦指中国社会,与“荒原”同义,此可证“荒原”意象并不是出自《圣经》中的“旷野”。李欧梵认为“铁屋子”可以当作“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象征”,亦可看成鲁迅“黯淡的内心”。④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9—40页。“荒原”与“铁屋子”实则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名称虽异,所指为一,都是为了强化一种启蒙主题和意图。
在当代文学部分,除了前文已引所谓“三突出”理论出自基督文明外,顾彬还以同样的方式论述了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只要浩然作品的主人公在引用毛泽东的话,马上就从普通字体换成粗体字印刷。这种做法也许是借自《圣经》,耶稣和保罗的重要话语也是通过改变字体以示突出。浩然小说标题中“道”和“光”等用语也具有某些《圣经》色彩,符合认知过程的叙述结构以及“寻找”的叙述技巧也是如此。当然“道”也可以从中国传统的“道”的不同含义中得到解释……(第294—295页)
关于“文革”中引用语录时用黑体字,学者赵鹏、王永魁做了考证:“文革”爆发前后,各大报刊突出引文、语录的首选字体是楷体,转折点在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同日刊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引用语录处全部采用黑体。此后,黑体字语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两报一刊”上,黑体字为语录所独享,甚至成了“最高指示”的代名词;有时为了避讳带有贬义的“黑”字,便将这种字体称为“粗体字”。赵、王文章还考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常有黑体字出现,但与“文革”时引用有区别,这只是一种排版手段,意在提醒读者留意而已,但此处并非有什么重要理论,有时也可能是论敌的观点。俄文版中有黑体的地方,中文版也照排为黑体。①赵鹏、王永魁:《“文化大革命”时期领袖语录专用字体的演变》,《百年潮》2014年第6期,第63—64、67页。由此可推断,小说《金光大道》中语录黑体字当效仿“两报一刊”,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两报一刊”是否学自马列经典著作,则不得而知,赵、王二位学者亦未明确出处。那么,所谓“粗体字”或许借自《圣经》,就是一个缺乏根据的虚假判断。
浩然小说中“道”和“光”字具有《圣经》色彩,或与中国传统的“道”相关,亦有可纠正的地方。对于浩然这样一个“左”到骨子里、终其一生以假为真的农民作家而言,自己小说中的关键词“金光大道”,竟然被说成源自于《圣经》,或与中国传统的“道”有关,而非出自“两报一刊”、领袖语录,何劳他人来相帮辩解,浩然本人也会起而抗议的。“文革”期间,宗教同种种传统文化形式一样,皆在彻底扫荡之列;一个对彼时中国历史情状稍有了解的人,不会把一部塑造“高大全”人物的作品与《圣经》、与中国传统勾连到一起。
第四,对有的作品的种类和体裁判断失误,从而导致论断失据。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把老舍《猫城记》视为“科幻小说”—“他唯一的一部科幻小说在西方很受重视,而在中国则不然”(第117页)。
《猫城记》完成于1932年,最初发表于《现代》杂志。1947年出版“改定本”,老舍写了一篇“新序”,开首就说这是一部寓言小说:
在我的十来本长篇小说中,《猫城记》是最“软”的一本。原因是:(1)讽刺的喻言需要最高的机智,与最泼辣的文笔;而我恰好无此才气。(2)喻言中要以物明意,声东击西,所以人物往往不能充分发展—顾及人(或猫)的发展,便很容易丢失了故意中的暗示;顾及暗示,则人物的发展受到限制,而成为傀儡。②舒乙主编:《猫城记 新韩穆烈德》(老舍小说精汇),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年,第2页。
老舍说的“喻言”,即为后来通行的“寓言”。名从主人,老舍对自己小说性质的定位是准确的。小说写了主人公“我”乘好友驾驶的飞机飞往火星旅行,失事后坠落在猫国,友人摔死,自己亦被猫国高官挟持而去,为其看守“迷林”。整部小说叙述了主人公在猫国的种种经历。就批判国民性这一点而言,《猫城记》是老舍所有小说中批判程度至为强烈的一部。在小说中,主人公以“我的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为理想标准,反照了猫国一系列国民性特点,试举几例:“猫人有历史,两万多年的文明”,猫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一切国中最古的国”;猫语“自由”一词意为欺负别人、不合作、捣乱、背约毁誓;“敬畏外国人”是猫人天性中的一个特点;猫人心眼很多,必要时也会冒一些险;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不敢欺负外人,可是对他们自己是勇于争斗的”;猫国的“法律不过是几行刻在石头上的字”;猫人没有帮忙的习惯;“敷衍”是猫人活下去的唯一方式;“见便宜便捡着”是猫人的习惯,等等。《猫城记》是一部伤心之书,是一部寄寓着大沉痛的书。无怪乎梁实秋当年读了小说之后,高度评价这是老舍“最进步的一部作品”,胜过他以前的小说,“艺术思想都到了成熟的地步”。③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七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等著《文学术语词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1957)有一个定义:“科幻小说指的是那样一些故事—与纯粹的幻想小说不同—这些故事通过涉及已知或想象的科学原理,或是设计好的技术进步,或是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试图使其虚构的世界显得合情合理”,而幻想小说则反映了“未来的乌托邦”。④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著,吴松江等编译:《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6—357页。
《猫城记》中既无“科学原理”因素,亦无“乌托邦”因素,所有的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时事曲折隐晦的嘲讽。因此,顾彬说它是科幻小说,他错了;国内也有人说它是一部科幻小说,还有说是政治小说的,他们都错了。
对作品种类的判断失误还表现在关于《四世同堂》的论述上,不知顾彬根据何种版本,认定这是一部“章回小说”和“战争小说”(第183页)。视其为“战争小说”,多少靠一点边儿,小说大背景设置在抗日战争时期;把它当作章回小说,显然不恰当。老舍在序言中交代了小说的组织:一百段,百万字,共三部—《惶惑》《偷生》《饥荒》,系故事紧紧相联的“三部曲”。顾彬那样肯定地说它是“章回小说”,至少能拿出一种表面证据,比如小说形式上有多少回目,可《四世同堂》并非章回形式,是以节为顺序的。
类似的失误不止这一处。在提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时,顾彬写道,这个小说是对清人文康《儿女英雄传》的“再创作”(第271页注释①吴奔星:《文学作品研究》(第一辑),北京:东方书店,1954年,第224—225页。)。既然认定为“再创作”,后一部作品与作为模板的前一部作品之间,当有大体相同的故事、人物、情节以及主题等等,其间变异、演化自不待言。可《新儿女英雄传》与文康的小说,除了借用“儿女英雄”这几个字,加一“新”字以避同名之嫌,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关联的地方。袁、孔小说名亦自有出处,第十六回“爱和仇”第一节,主人公牛大水、杨小梅结婚时,朋友送来喜联,第一副“新人儿推倒旧制度/老战友结成新夫妇”,嵌一“新”字;第二副“打日本才算好儿女/救祖国方是真英雄”,嵌“儿女”“英雄”二词,合起来便是小说名。说借鉴、吸收古典小说方法,亦无不可,吴奔星当年撰文评介此小说,概括了几个特点,其中之一即为继承、发展了《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现实主义传统,采用了章回体的民族形式,吸取、革新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写作方法,强化了故事性,以吸引读者。①吴奔星甚至没有提及文康《儿女英雄传》,这很能说明问题。
从这里也反映出,顾彬分析文本时往往不仅有穿凿过甚的一面,亦有轻率、武断的一面。还可举出不少例子来,如:老残“他生活在‘残’中,却以补残也就是创造秩序为己任”(第14页);《孽海花》写一青楼女子、一朵花,“花”即“中华之喻”(第16页);孔乙己生活不断恶化,“使得他无力偿还酒债而死”(第38页);萧红《呼兰河传》中街道上的“泥坑”代表着“普遍的东西,它生来如此,本质上从没有改变过”(第224页);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倾城”,“自古以来就代表着一种让国家、城市为之而破灭的美”(第228页);老舍《正红旗下》里的“鹞子”象征着“即将摧毁养鸟艺术、中国文化的力量”(第290页),等等。
三
顾著文学史还存在着若干明显的常识性、知识性错误,试略举数例。
第二章论“五四运动”一节中,顾彬写道:“破坏的对象是一切传统的和中国的东西。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1921年胡适提出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第 23 页)
此说法有误。第一,这并非是一个“口号”;第二,准确地说,不是胡适要打倒,而是胡适称赞吴虞“只手”打孔家店;第三,“打倒孔家店”表述不准确,正确表述应为“打孔家店”。这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可以说中国现代史上流传甚广、误传最多的话,出自胡适为《吴虞文录》所作的一篇序文,结尾两段: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②《胡适文存》(四)(影印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259页。
这已经成了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略知其由来的会说吴虞打孔家店,仅凭耳食之言的便纷传为胡适要打孔家店了,至今还在以讹传讹。
吴虞在五四前后颇为活跃,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孔子及儒家学说,锋芒毕露,比如“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比如“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比如孔子“诚可为专制时代官僚之万世师表也”等等。①吴虞:《吴虞文录》,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6、31、35页。所以,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但是,吴虞对胡适的称赞并不十分领情,三年之后即1924年,在回答《晨报》记者提问时,吴虞自称“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胡适他们对自己的称许“皆谬矣”。有研究者认为,吴虞的态度其实不矛盾,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利用了的孔子,而非孔子本人。②邓星盈等著:《吴虞思想研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2—73、74页。胡适后来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说过近似的话,他对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对孔子本人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非常尊崇。③《胡适传记作品合编》(第一卷下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71页。
在第二章第三节“文学的激进化”中,顾彬论述延安文学时写道:“延安代表着由一种批判文学向肯定文学的转折。毛泽东断然宣布,杂文时代已过去了,就是说,在批判对手方面,政论散文在过去已经达到了其目的,现在应该为那些帮助歌颂自己人的文学形式所取代。”(第191页)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第四节中,毛泽东专门谈到了因为“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而产生的“各种糊涂观念”,“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就是其中之一,针对以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为代表所反映出的一种文学倾向,分析并设定了杂文写作的边界:鲁迅生活在黑暗势力统治下,使用冷嘲热讽的杂文是正确的,但在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只要“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非敌人的立场上,可用杂文形式批评“人民的缺点”;立场对了,讽刺也是需要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④《延安文艺作品精编 1 理论诗歌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6—27页。
毛泽东特别强调分清敌我、站对立场,尽管他也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政治观点正确而无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作品,要求艺术与政治、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但主要的还是重在政治方面,看作家的政治表现。也即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而非敌人的立场,讽刺手法的杂文才是需要的。这也意味着杂文会被有条件地允许存在下去。
实际上,即使到了1957年,毛泽东也没有明确反对过杂文、宣布取消杂文;相反,他主张杂文无须只顾及一点,甚至可以写得全面一些。据陈晋《毛泽东文艺生涯》(下卷 1949—1976),毛泽东在1957年数次谈及杂文:于同年3月份的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巴金提到有人说杂文不能全面,鲁迅的杂文就只讲一点,毛泽东接过话头,同样举鲁迅为例,说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杂文就有力量;4月份,对《人民日报》社长邓拓等又说过“杂文要有”,也可以写得全面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云云。⑤陈晋:《毛泽东文艺生涯》(下卷 1949—197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73、483页。可证毛泽东并没有说过“杂文时代过去了”的话。
在论述艾青诗歌时,顾彬附带提到冯至,说了一句颇为严重的话—“曾于1957和1958年间将艾青送到刀俎上的冯至……”(第213页)。倘若事情真是如此,史实亦无可辩驳地证明是冯至把艾青送到刀俎上,那么冯至在文学史上将会以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现。
冯至确曾于1958年发表过《驳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文中充斥着五六十年代特有的词语、术语和文风,是一种蛮横的道德谴责和政治批判,诸如“灵魂这样肮脏”“生活这样腐朽”“站在革命的敌人方面去了”“这些资产阶级的滥调”等等。不止冯至一人,据周红兴《艾青传》,从1957年9月开始至1958年4月,有20多位诗人、作家和学者,在《人民日报》《文汇报》《文艺报》《解放日报》《文学研究》等报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批判艾青,那种谴责和谩骂,与冯至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定要追问究竟是谁把艾青送上刀俎,人人有份,只记到冯至一人名下,这是不公平的。倘再追溯起来,这20多个批判艾青的人未必个个心甘情愿,那样整齐地联手攻击艾青,他们不过是奉命写作、以求自保而已。
艾青之所以被打成右派,除了时代气候外,具体原因是诗人讲了“真话”。周红兴《艾青传》写道:
反右派斗争不断扩大化。艾青对这场斗争很不理解,并说了一些同情被斗争的人的话,像“我们党内总是一些人整人,一些人挨整”、“斗争丁玲是残忍的,斗争江丰是一棍子打死”等等,便被打进“丁陈反党集团”,对他的批判不断升级并迅速公诸报端。①周红兴:《艾青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436页。
1958年1月《文艺报》重新刊登了延安时期的一批杂文,其中就有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由最高领袖亲自撰写的“按语”,把艾青、丁玲、王实味等人打入了“反革命”“敌人”之列,最终宣判了这些人的命运。
就在艾青“陷入深潭之时”,王震伸出了援助之手,请艾青夫妇到北大荒,1958年4月艾青离开北京,乘火车前往黑龙江密山县,这原是他们的终点。次年又被安排前往新疆。对艾青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很及时的保护。比起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致死的人,艾青毕竟还算幸运。附带一句,舒芜将胡风送上刀俎,这才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为恰当的第二个例子了。
还须一提,顾彬对典故“知音”,理解上有偏差:
并且从中国中古时代以来,对于真正友谊的设想就是同他人的声音和倾听有些关系的。一个朋友,一位知音,即知己,就是知道我的声音,也就是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的声音,意味着知道我在讲述时以诗情或音调所要表达的东西。(第215页)
春秋时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能从中听出弹者的心声。此处“音”专指琴声、音乐,并不是人发出的“声音”。《文心雕龙·知音》:“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王运熙先生译文:“知音真是困难啊。音乐确实难以深入理解,能够深入理解的人难以遇到,遇到能深入理解的知音,千年只有一次吧。”②王运熙等:《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8页。后称朋友、知己为“知音”。贾岛《题诗后》:“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杜甫《南征》:“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皆指朋友、知己。顾彬将“知音”理解为“他人的声音”“我的声音”,显然有点望文生义。
也有翻译方面的粗疏大意,最突出的是,随意混用“现代派”和“现代主义”两个术语,试举数例:“旨在将中国从民族和社会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中国现代派的许诺”(第32页);“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旷野的呼喊者’,努力表明自己是出自于(西方)现代派之列的‘拯救者’”(第42—43页);“鲁迅这位现代派老前辈无论在事件风浪中还是在……”(第102页);“如果不对西方现代派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对茅盾有公允的评价的”(第106页);“因此,1949年之后现代派的落潮以及1979年后的现代派回归也伴随着女性身体的遮掩和裸露”(第112页);“废名……似乎又该被称为一个现代派的代表”(第146页);“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心文本是《雨巷》”(第154页);“中国现代主义1925年诞生于上海震旦大学”(第156页);“现代主义这一派实际上是象征派和后期新月派的融合”(第159页),等等。现代主义和现代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袁可嘉先生在《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一书中解释道:“‘现代主义’文学指一种文学思潮,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相对而言;‘现代派’文学是表现这一思潮的六个流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的总称。”③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直接以“现代派”命名的只有戴望舒一派,这一派有时被称为象征派,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派”,主要还是因为施蛰存等主编《现代》杂志,用刊物之名来命名。其他带有现代派色彩的流派,都各有其名,如40年代形成的“《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新时期的“朦胧诗派”等,并无一个明确被称为“现代派”的文学流派。两个术语混用,以至于把鲁迅都划入一个不存在的“现代派”,实为不该出现的失误。
此外,翻译中还有不少硬伤,有必要指出其中几条,如:
“周作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杂文《论人的文学》”(第26页),《论人的文学》应为《人的文学》,这是被胡适称誉为“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①刘运峰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191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这是一篇文艺批评,周作人本人视为文艺“论文”,并不是译者所谓的“杂文”;
“胡适自己1920年作的抒情诗集《尝试》乏善可陈……”(第29页),《尝试》应为《尝试集》,此为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
“李准……的小说《不能走这条路》”(第267页),恰恰译反了,应为《不能走那条路》;
“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简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亦称‘二月纪要’……”(第293页注释③),译名随意增删,“召集”应为“召开的”,“座谈”应为“座谈会”,准确名称应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般简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更多简称为《纪要》,很少有称为“二月纪要”的。
汉学家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其理论是新异的,视角是独特的,但他们缺乏心领神会。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西洋人评论不很中肯,那可以理解。他们不是个中人,只从外面看个大概,见林而不见树,领略大同而忽视小异。”②钱钟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7页。自然,顾彬也不例外。
高奕睿和敦煌汉文写本研究
高奕睿(Imre Galambos),1967年出生于匈牙利,1994年本科毕业于匈牙利罗兰大学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战国时期的汉字正字法研究》(“The orthography of Chinese writing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2002—2012年,在英国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部工作。2012年至今,任教于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精通英、法、德、中、日等多门语言。作为新兴汉学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正字研究和古文书学研究。目前已出版有《汉文传统的翻译与西夏文化的教授》(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2015)、《汉文写本研究:从战国时代至20世纪》(Studies in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20th Century,2013)、《写本与行者:一个10世纪佛教朝圣者的汉藏文书》(Manuscripts and Travellers: The Sino-Tibetan Documents of a Tenth-century Buddhist Pilgrim,2012)、《早期汉字正字法:新出写本的证据》(Orthography of Early Chinese Writing: Evidence from Newly Excavated Manuscripts,2006)等著作和四十余篇论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