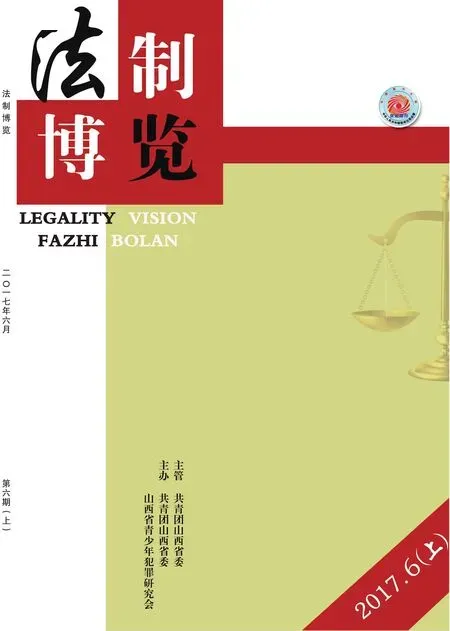胎儿的民事权利
2017-01-28文雪婷
文雪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胎儿的民事权利
文雪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风险因素的增多,司法实践中胎儿损害赔偿案的数量也在日益上升,如何保护胎儿利益己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我国立法中没有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认为在出生之前只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就使得胎儿的权益在法律中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在审判过程中,同一个类型的案件,有的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有的法院不支持,让法官在审判过程当中感到无所适从。因此,笔者将通过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当前我国对胎儿民事权利保护的不足以及提出几点修改建议。
胎儿民事权利;法律保护
一、胎儿的法律定位
要论述胎儿的民事权利,首先要定义何为“胎儿”。在我国法律之中还没有对胎儿进行明确界定,但各个法学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主流观点是我国台湾学者胡长清对胎儿提出的界定,认为“胎儿者,乃母体内之儿也。即自受胎之时起,至出生完成之时止,谓之胎儿”①。也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胎儿”包括了从受精卵期开始一直到出生的生命孕育全过程。
二、我国关于胎儿民事权利的立法
在大陆地区现行的立法中只有《继承法》第28条规定了胎儿的继承权,可见我国现有法律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仅限制在继承权范围,根本没有涉及到胎儿其他利益的保护。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民的人权意识不断提高,在对胎儿保护的领域上不得不做出新的规定。2017年3月15日《民法总则》终于颁布,其中第16条就明确提出:“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将保护胎儿的继承权、接受赠与的权利以及纯获利益权等,但只有在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条件下才有权利能力。虽然《民法总则》相比当前法律来言对胎儿的保护更全面,但依然没有全方位的承认胎儿的民事法律地位。
三、焦点问题与案例分析
胎儿存在于母体当中,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在生存能力和抵御侵害的能力都是十分微弱的。近年来胎儿权益损害的新闻屡见不鲜,下面将针对三个最常发生的情形进行分析与论述。
(一)产前检查失误
产前检查失误之诉指由于医疗机构的过失,未能检查出胎儿的缺陷状况致使父母生育了一个残疾婴儿,父母因其精神和财产遭受损失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在这类侵权中胎儿出生后会残疾是先天的,不是医生导致的,也是医生无法治愈的,医生唯一的过错是没有能诊断出并通知胎儿母亲孩子的健康状况。
我国“不当出生”损害赔偿诉讼始于20世纪90年代,比较著名的案件是台湾地区的朱女士因产下唐氏综合症婴儿提起的索赔诉讼,已由台湾士林法院1995年度重诉字第147号民事判决所确定并被广泛引用。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残疾婴儿的残疾是母体内自然孕育的结果,医疗机构的行为与此并无因果关系,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在1996年,湖南吴某、李某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了医疗机构在发现胎儿异常时没有作进一步的诊断存在过错,应当对父母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案法院的判决确认了医疗机构过失行为对“不当出生”的可责性及原告请求赔偿的合理性。
进入21世纪后,“不当出生”损害赔偿诉讼在我国上海、湖南、重庆、河南等地陆续得到承认,从最近几年法院审理产前检查失误的案件中反映出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不统一,有主张侵犯知情权的,也有主张侵犯其优生优育选择权,还有主张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其次法院对于被告的医务行为与生出残障婴儿是否有因果关系的认定所持的观点不一样,有认为胎儿的缺陷是遗传造成,也有认为是医疗行为的不正确才导致缺陷胎儿的出生;最后即使案件差异不大,但是法院最终判决赔偿的数额却相差非常大,而且赔偿内容也不明确、不统一。
(二)胎儿能否作为主体
案例:2012年原告杨某在被告某医院先后进行了四次产前B超检查。第一次检查结果提示没有查清胎儿的面部并建议复查该部位,第二、三次检查时检查结论中没有胎儿面部、唇线等描述,第四次检查结论又显示胎儿面部清晰没有异样。但原告生下的婴儿宋某确是先天性唇腭畸形,遂杨某以宋某名义将被告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案件发生之时原告宋某还未出生,而依据法律相关规定胎儿是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的,所以宋某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其不是适格的主体。
其实在我国司法实务界对于胎儿权利遭受损害之后能否起诉、如何起诉的态度模糊不明。在学理上,对出生后的胎儿是否是适格的主体的问题存在不同论点,梁慧星教授提出凡是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就应该视胎儿是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同样,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其核心思想是“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妊娠利益和延续人身利益”。②显然,他们都认为胎儿的民事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当涉及到胎儿法益侵犯时,可以将胎儿视为民事主体。
(三)代孕问题中对胎儿的保护
最近合法代孕问题引起了学界和网民们的热议,“借腹生子”这一特殊的现象逐渐浮出水面。从梁彗星教授对代孕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代孕有两种形式,在这我们只讨论“完全代孕”即只借腹不借卵的情形下对胎儿民事权利可能产生的问题。首先,代孕者以及委托者与胎儿的法律关系是模糊的。当胎儿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谁是胎儿的监护人,谁能够代替胎儿行使民事权利,谁能获得损害赔偿金,这都是法律需要填补的地方。其次,在孕妇肚中的婴儿是否享有民事主体资格。如果没有,那么因为服药,输血等导致婴儿在母亲胎腹中便染上疾病,委托人或胎儿本身有资格申请赔偿。如果有,那么代孕者流产,是否属于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甚至是构成了刑法上的杀人。最后,目前我国的法律中只规定了胎儿有继承权,那么胎儿在代孕者体内能否拥有接受遗赠以及纯利益的权利法律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如果真的实现合法代孕,那么在制定代孕法之前先要把胎儿民事权利方面的漏洞填补,这样才能保证的法律秩序。
四、完善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虽然胎儿不是法律意义上完整的人,但其为潜在的人的生命,是诞生一个自然人的前提条件,所以法律仍不得忽视对其利益的保护。对于具体如何立法,笔者认为想要使胎儿的权益受到完整的保护可以通过附条件保护主义立法模式实现。对于具体的规定有以下建议:
(一)在我国民法总则中加入对胎儿利益保护的总括规定,即胎儿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的保护,视为出生。
(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胎儿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抚养权、继承权以及受遗赠权等,同时规定在胎儿成为受遗赠对象的情况下,视胎儿愿意接受遗赠,无须作出明确接受遗赠的表示。
(三)法律规定监护人代替胎儿行使权力,且不得作出不利于胎儿权益的行为,否则政府等有关行政部门可以对监护人提起控诉。同时,如果父母故意对胎儿作出侵害行为应承担责任,但若父母是过失导致的则无需对胎儿承担责任。
(四)规定特殊的诉讼时效制度。虽胎儿还没有降生时就被损害,可这种侵害难以得到证实,如果要进行精准的确定,须待胎儿出生才能进行鉴定,那么应获得的赔偿诉讼就应该在孩子降生之后进行。所以,涉及到胎儿侵权行为提出赔偿诉讼的时间应以孩子降生为起点,在独立请求权人了解由于侵权而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算起。
[ 注 释 ]
①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0.
②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206.
[1]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梁慧星.私法上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4]万媛媛.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研究[D].南昌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2015.
D
A
2095-4379-(2017)16-0210-02
文雪婷(1996-),女,湖南株洲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4级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