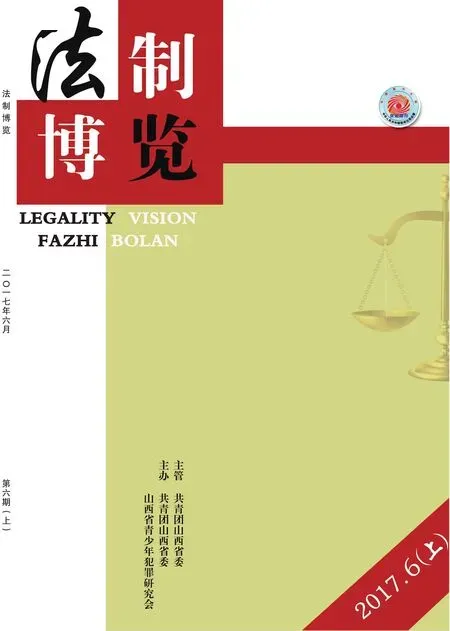关于司法权威的探讨
2017-01-28陈运祥
陈运祥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2
关于司法权威的探讨
陈运祥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2
在现代化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司法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功能,具有着诸如解决纠纷、保障权利、维持秩序和权力制约等等,其重要性自不言而喻,而这一切的基本前提就是司法本身具有权威性。在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而言,司法权威的问题较为突出,因此也就制约了本身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得司法在国家权力架构当中处于一种较为弱势的地位。
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塑造
一、司法权威的来源
(一)与世俗的间离状态
司法机关只有与政治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使得自己不牵扯到各政党的利益之争,以一种超然的状态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才会让人有利于相信司法能够秉持中立。有学者用“间离”二字概括了司法和世俗社会应当保持的适当距离,作为权力斗争这一激烈的博弈过程哦有着中的重要因素,它在现实社会中应当具有自己的自留地,虽不可能保持真空,但也至少有着独立自主的体系。恪尽职守,无需也不必要将自己的触手染指域外。因此在此用的是“间离”一词形容其状态而非“隔离”。这也是司法机关的一种明智之举。①
法律的帝国应当保持岿然不动之势,即使在激流勇进的现代政治生活当中,也要构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政府或者政党自然会向社会大众宣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这是其难免的固有价值取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需要司法在喋喋不休的纷繁争吵时居中裁判。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中,关于是非曲直、情义理法的审判和思辨,是滋养法律成长的源源不绝的动力,也是适用法律的审判者展示其法律素养的用武之地,司法绝对不能成为政治或者政党的传声筒,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理应竭力避免政治生活的干预。西方社会所一直一致认为的法律人应形成自己古语的一种理性思考的能力和话语权,保持自己经过良好法律训练所具有的逻辑思维方式。
(二)民众的信任
“对于美国的实践而言,确实提出了令人困惑的悖论:非民选的法官往往比民选的立法机构和行政首脑更好地保护了民众的权利。”②民众信任司法权力,而且将裁判的权力毫无保留全部授予,加之高薪、终身任职等等职业保障,所期待的就是司法的公正独立。现代来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了这种制度,托克维尔所言的“不是困惑的困惑”成为了世界通行的做法。但是为了保证司法与民众的联系不被司法独立而切断,在设计裁判制度的时候又用了诸多限制,例如案件的公开审理原则,使得民众能够对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监督。法官在对案件作出裁判的生活必须有令人信服的说理过程,而且判决结果予以公开;审判过程中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才能作出判决。最终的裁判结果需要体现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尽管法律的推理和人民的意识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使得某些时候这种判断会一时偏离当时社会主流价值,但是司法仍然可以通过谨慎的表达无可指责的程序方式抵消这种偏差。③
(三)司法是最终手段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杰克逊大法官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错误而成为终极权威,而是因为是终极权威而没有错误。”纠纷一旦被诉至法院,包括被控诉的犯罪嫌疑人,法官通过国家赋予的司法裁判权做出生效判决之后,就作为最后的结局应当得到接受,具有法律强制力。除了法定的情形,任何社会力量或者国家权力,甚至于法院本身都不得奇诡动摇、推翻判决。“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判决的终局性,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且可以不同的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那就阻碍了矛盾的解决”,同时,“无休止的诉讼反映了,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④也就是说,司法判决的终局性是司法权威的重要来源。我们可以假设,司法机关的裁判若长期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诉讼当事人的利益也无法得到确定,显然对于法律所具有的确定性和指引性功能将是极大的伤害。
二、司法权威如何缺失
(一)裁判的终局性难以确立
我国的司法裁判经常处于终审不终、裁判生效却无执行力的局面,法院生效判决书的既判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有错必纠”的理念指导下,再审程序的设计可谓影响裁判终局性的重要因素,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不仅反复申诉,或者利用上访给法院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但是当司法裁判使得当事人考虑的不是如何尽快履行判决,反而是使出浑身解数使尽各种手段启动再审程序以扭转于己不利的判决,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种行为对于司法权威的危害。
(二)执行力不足
民事案件的执行力低下这一问题积弊颇深,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与思考,最高院院长周强在2016年的“全国法院审执分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坚决打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执行不是简单的判决执行结案率或者是司法执行,我们可以在更加广义的视角来理解,就可以大大拓展这一含义,是指司法在国家和社会当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选择性不司法”的现状,针对一些疑难复杂、牵扯人数众多的案件,本来可以纳入法院的受案范围,却不愿受理、不敢受理或者不方便受理,向当事人关闭了权利救济的大门。⑤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就是,法院没有能力和资源去解决。司法救济真空地带的存在或许正是意味着当前司法机关诉讼资源配置的不足、不均匀,难以支撑起法院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表面上看是体现的法院司法功能受到限制,其实更多的折射出法院的无奈。
三、司法权威如何加强
在最后我们应该考虑的就是,现状能够被改变以及怎样做才能改变。有人认为,所有关于制度的精心设计和构建都是多余的,法治无需如此,司法权威本身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秉持着文明滚滚向前的趋势无人能挡的这一信念,法治的秩序便可自由生长。回望来路,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得失兴替,司法权威的加强,更可谓是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法治是一个公共选择和试错过程的产物,而法学研究更多是通过法律话语去形成法律共同体,构建一种法制和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社会共识,并以此来促进法治的形成,法学研究的意义是有限的。”⑥
(一)明确司法定位
司法权威探讨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司法权,也就难以回避国家权力的分配和政治结构,因此这更多的是政治问题。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存在于政治的真空当中,无可避免也无需避免。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稳定压倒一切,“维稳”是政治对司法的要求,可是“被要求”具备的功能,在这一背景之下讨论更多宏伟的法治目标例如权力制衡,就显得背离当下的社会现实。司法改革已经提出有些年头,这种过渡时期也给司法制度的进步带来的契机,我们应当看到,司法制度还是有很大的改造空间。
或许司法恪守被动性,有限性,司法机关所占有的司法资源有限这就决定了有些纠纷由党政机关处理可能更为合适,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有些地区的法院拒不受理某些案件,我们仔细看看其理由就可以得知,⑦这些案件只能依靠具有强大说服力的党政机关。在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考虑法院自身的承载能力,加之被人诟病已久的执行率低下,要想司法为社会纠纷提供更加完善的司法救济,这些问题就应当纳入我们探讨的范围。保守的说,司法权威或许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权威,追求更多的是处理好现有诉诸法院的纠纷,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能追求更大更高的功能。
(二)明确司法与其他权力主体的关系
司法机关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它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有法律明确予以规定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实践当中的操作规范,从而回避掉因为互相之间的权力界限模糊不清而造成的权力越位,更好的使得司法能够独立自主解决分内之事。
政党的领导应该是在遵循司法权运行基本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将自己的意志上升到国家意志之后,由司法机关严格适用法律,这也就可以体现党对司法的领导。这意味着领导方式和原则的法制化制度化,可以很好克服实践当中的无线伸缩和弹性,也可以满足司法机关对于稳定性的要求。法律可以更加权威更加牢固地体现党的意志,也更加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司法机关的遵循。对于领导方式,首先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对司法机关的定位问题加以明确,其次领导司法改革,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通过提名控制法官人选,最后,在面对司法机关无力解决的问题和矛盾的时候,党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利用自己所具备的资源优势进行协调处理,克服当下局面当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和较高的社会期望造成的社会紧张局面。
[ 注 释 ]
①许章润.司法权威——一种最低限度的现实主义进路[J].社会科学论坛,2005.8.
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③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④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桂高法[2003]180号).
⑥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⑦同上引.
[1]许章润.“司法权威”——一种最低限度的现实主义进路[J].社会科学论坛,2005,8:5-25.
[2]徐阳.“舆情再审”——司法决策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法学,2012,2:180-191.
[3]陈光中,肖沛权.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J].政法论坛,2011,1:3-16.
[4]汪建成,孙远.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J].法学评论,2001,4:104-116.
[5]卞建林.我国司法权威的缺失与树立[J].法学论坛,2010,1:5-9.
[6]严励.司法权威探讨[J].法学论坛,2004,4:48-57.
[7]李树民.司法权威价值意蕴及其实现[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3:15-26.
D
A
2095-4379-(2017)16-0122-02
陈运祥(1993-),男,汉族,湖北宜昌人,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