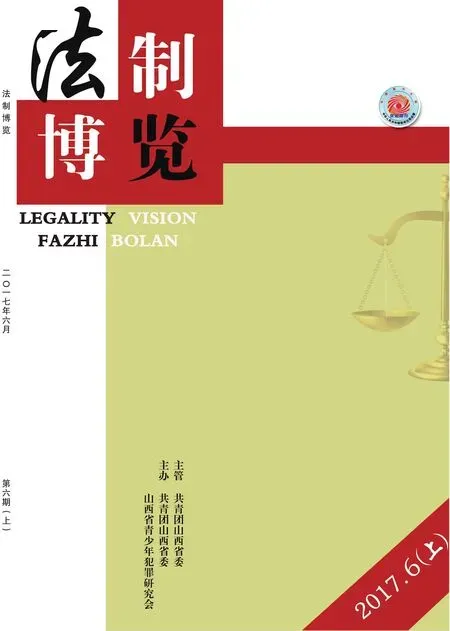《士师记》中“便雅悯事件”的审判因素分析
2017-01-28王思杰
王思杰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3105
《士师记》中“便雅悯事件”的审判因素分析
王思杰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3105
在《旧约圣经》的《士师记》接近末尾的部分,记述了古代以色列人的一场内战,内战的对象是以色列的便雅悯支派。该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极具士师时代的特点。这个事件也为我们探寻《士师记》中古代近东社会的审判因素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素材,我们可以由此管窥士师时代的纠纷解决以及审判相关的具体形态。近代诉讼法中的起诉、应诉、法庭调查以及审判等该事件中都有体现,其同时在审判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讨伐便雅悯;诉讼法;审判;启示
一、讨伐便雅悯事件的基本经过
在《士师记》中,讨伐便雅悯事件的起因是一起惊人的血案。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Mountains of Ephraim)的利未人有一个妾,因为生活纠纷,她回到了自己的娘家伯利恒(Bethlehem)。利未人于是来到伯利恒,与岳父见面后,想要将妾带回去。五天后的傍晚,利未人带着自己的妾起行。他们一行很快来到了耶布斯城(Jebus),也就是未来的耶路撒冷。在当时,耶布斯还是迦南的耶布斯人占领的城市。利未人的仆人提议晚上在耶布斯城住宿,但利未人却认为“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19:12),因此拒绝了这个提议,执意要到以色列人的基比亚城去住宿。①基比亚的居民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人。
利未人一行进入基比亚城后,遇到一位好心的老年人提醒他们注意安全,“不可在街上过夜”(19:20)。老年人将利未人一行领入自己的家里住宿。但到了晚上,基比亚人突然围住了老年人的房子,并要求老年人将利未人一家交给他们,让他们凌辱。情况紧急,老年人劝阻无效,利未人便将自己的妾推出去交给基比亚人,于是“他们便与她交合,终夜凌辱她,直到天色快亮才放她去”(19:25)。第二天早晨,利未人将奄奄一息的妾驮在驴上继续赶路。回到家后,利未人将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19:29)。
二、从诉讼的角度分析便雅悯事件
从以上叙事中,我们可以推测,旅途中的一位妇女在基比亚(Gibeah)被凌辱致死这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无疑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实例。[1]基比亚便雅悯人的“性强暴”很有可能是受了迦南文化的影响。②这反映出当时以色列人道德的堕落和社会的混乱。案件发生后,作为受害者的家属,利未人以特有的方式进行了告诉,他将自己妾的尸身切割成十二块,送至以色列十二支派,申明自己的冤屈。切割尸体的做法,可能有其特定的背景。学者推测,当时以色列各支派之间可能有共同认可的立约条款。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论述中提到的,当时以色列人立约的仪式需要将动物宰杀并切割。利未人将其妾分尸送给各支派,有可能来源于该仪式,表示以色列中有危机,要各支派共同应对。[2]
无论真实的情况怎样,利未人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起诉”,从而开启了审判的程序。这个痛苦的“起诉”引起了以色列人的强烈反响,他们对其做出了回应:
“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士师记》19:30)
当时以色列人并没有国家,也没有成建制的审判机关,各个支派分散在自己的区域内,一盘散沙,没有统一的强力部门,甚至没有各支派间的联络机制。但这种背景下的以色列人仍然对利未人的告诉做出了一致的回应,这相当于利未人的起诉得到了受理。以此为基础,以色列人迅速组成了一个特别法庭:
“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士师记》20:1-2)
可见,这个法庭是由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部落的长老组成的,他们从摩西时代开始,就是以色列人适格的审判官。只是这一次,审理的对象关系到以色列的整体,案件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此时摩西、约书亚都已去世,当时也没有强有力的士师出现,③于是审判官们只得自己起来,组成联合法庭,对利未人的起诉进行审理。
随着审理展开,调查程序开始了。法庭要求利未人报告罪案发生时的真实情况,并呈述自己的请求。于是利未人说:
“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块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士师记》20:4-7)
取得了作为原告的利未人的口供,法庭旋即要求作为被告的基比亚便雅悯人作出回应和答辩。但“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20:13);法庭要求便雅悯人交出凶手,亦遭到了便雅悯人强硬的拒绝。便雅悯人非但不理会法庭的要求,甚至“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20:14)。
事已至此,法庭做出了支持利未人请求的判决。他们相信了利未人的口供,并裁决以色列人全部出动,讨伐便雅悯支派,以为惩罚。于是内战开始了。因为便雅悯人极为凶悍,以色列人开始时损失惨重(20:21-25)。但在上帝的应许和大祭司非尼哈④的鼓励下(20:18),以色列人最终打败了便雅悯人,甚至将其近乎灭族(20:48)。
三、便雅悯事件在审判意义上的启示
人们可能会认为,该事件后来的处理,是军事手段代替了法律的手段,是法律的失败。但我们如果从审判的视角去探讨,仍然能够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首先,我们通过这个事件的记述,可以看明以色列人当时的审判样态居于何种水平上。显然,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常设的法庭,没有有效的证据手段(以口供为主),也没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区分,当然更没有专门处理刑事诉讼的公诉机关。因为公诉机关与国王的关系十分紧密,⑤以及国王对于统一司法权的显著意义,国王在以色列社会的重要性在本案的处理中已经看得出来。因此,学者们认为,从当时以色列的治理结构与审判组织上看,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的确需要国王。[3]这个需求从治理和审判的角度上说是正当的,也是急迫的。
其次,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人的联合法庭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对律法的维护以及对于法庭本身的维护。以色列人之所以迅速做出讨伐便雅悯支派的决定,应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便雅悯人对于该法庭正当要求的极端蔑视,及其对联合法庭本身的蔑视。正是激愤于这种蔑视,抑或说是以色列人为维护自身法庭的权威,方才决定对便雅悯人进行军事打击。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联合法庭裁决进行军事打击的结果,是便雅悯人由此遭受了重创,几近于灭族之祸:
“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二万五千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六百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磐,就在那里住了四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士师记》20:46-48)
便雅悯人这样的结果,固然是一个悲剧,但从审判的角度看,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公正和公义最终得到彰显。联合法庭的判决得到了执行,利未人的诉求也得到了满足。单就这场审判来说,最后的结果是恶者受惩,以色列人法庭的尊严也得到了维护。
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以色列人针对便雅悯人的讨伐与现代诉讼法定义的审判尚有一定区别,但如果还原到公元前13世纪至11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仍然可以将该事件视为一种审判的形制,它的演进在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审判的程序。该事件所展现的内容,能够让我们看到符合那个时代特点的审判样态,这对于我们研究初民社会审判的进化具有参考意义。
[ 注 释 ]
①作者在此可能暗示并讽刺了利未人(以色列人)的自私和自傲,事实上,最后犯下如此骇人听闻暴行的恰恰不是“外邦人”耶布斯人,而是以色列人的手足同胞基比亚的便雅悯人.See J ·P ·Fokkelman,Reading Biblical Narrative:An Introductory Guid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00:110-111.
②基比亚人的“性强暴”让人很容易想到<创世记>中罗得(Lot)神圣的客人在索多玛城(Sodom)的遭遇(19:1-10).学者发现,迦南民俗中,有很强烈的性暴力文化,在迦南人的神话中,他们的神巴力强奸了女神亚拿(Anat)七十七次.由此可见,迦南文化是多么的淫邪暴虐.See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Yahweh and the Gods of Canaan: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wo Contrasting Faiths,Eisenbrauns,1990:128-129.
③<士师记>在记述整个故事时,并未提及当时以色列人的士师.而有意思的是,利未人告诉的行为,却有点像士师——呼吁以色列人出来参与圣战,只是这一次要对付的不是外邦人,而是以色列人本身,这显然又是一个讽刺.曾祥新.士师记注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370.
④非尼哈的出现显示这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人入住迦南,即士师时代的早期.See John Gray,Joshua,Judges,Ruth(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Eerdmans Pub Co,1986:386.
⑤目前学界比较的主流意见认为,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设立总检察长(Procureur Général)为自己的代理人,是为现代检察制度的肇端.从此以后,“特于有关刑事案件等,得不由被害人之起诉,于一定之情形(如命盗案件之情形,被害人不出而起诉,代理人则起诉是也),使为国家之机关,行后世检察官类似之职务,遂成惯例.”[日]冈田朝太郎等口授,郑言笔述,蒋士宜编纂.检察制度[M].陈颐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
[1][英]约翰·德雷恩.旧约概论[M].许一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Alan D.Crown:Tidings and Instructions:How News Travelle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J].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1974(17):253-254.
[3]Robert R.Wilson:Israel's Judicial System in the Preexilic Period[J].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1983(74):239-240.
D
A
2095-4379-(2017)16-0096-02
王思杰(1987-),男,江苏连云港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律文化、外国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