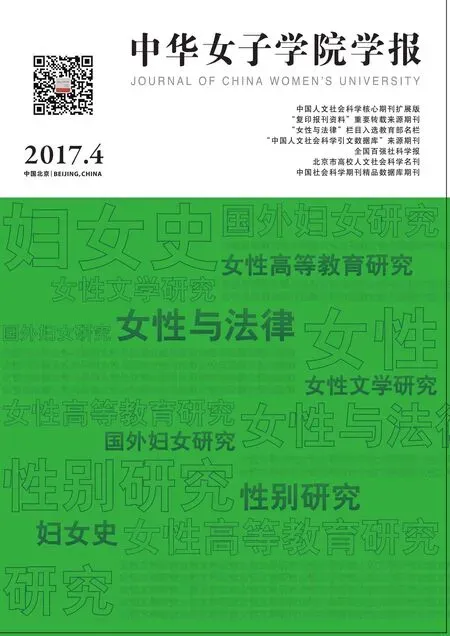审美与政治:20世纪50年代城市女性流行服饰探析
2017-01-27汤锐
汤锐
审美与政治:20世纪50年代城市女性流行服饰探析
汤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始于延安时代的列宁装以朴素、革命的式样逐渐成为女性服饰新的主宰,这与国家崇简的政治理念休戚相关。然而革命时尚的背后却渐及导致浪费衣料与模糊性别的两种趋向,加之中国棉花供应紧缺的现实,致使艺术界发起了一场旨在改进服装式样的花衣运动。中共八大的召开,将花衣运动继续引向新的政治场域。在中苏友好的文化语境之下,苏联的布拉吉连衣裙成为城市女性凸显自我风采的社交符码,其流行的背后隐匿着中苏工业合作以及中国服装产业迅速发展的经济图像。列宁装、布拉吉连衣裙的先后流行,既是国家话语在女性生活实践的一个契入面,又是当时文化、经济发展转换的一个历时性缩影。
城市女性;流行服饰;列宁装;布拉吉
英国学者琼·安娜认为:“服饰是人们思想的表达方式,而且常常和更深层次的道德或者社会价值的根本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服饰可以反映某一特殊时期的本质特征。”[1]120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的审美取向以及审美理念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契合,在人们心中审美的第一标准是个人崇拜与集体意识。“表现在服饰上为统一化的颜色、质地、搭配。”[2]19即男性普遍流行穿着人民装,女性则以穿着列宁装为荣。至1955年前后,穿花衣成为国家、社会各阶层热议的主题。之后,具有女性表征的布拉吉连衣裙开始风靡全国各地。
本文所要关注的是女性着装从1949年以前的旗袍迅疾转换成列宁装,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意涵,花衣运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之关涉为何。另外,布拉吉作为流动的文化载体,如何与中苏友好的工业语境相互映衬并加以契合?因此,本文借助档案馆、杂志、期刊的资料以及当事女性的口述资料,试图复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女性流行服饰的历史本相,并求教于方家。
一、列宁装:革命与崇俭
列宁装①列宁装,十月革命前后因列宁时常穿着而著名,之后由苏联传入中国。“是一种西服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的加一条同色布腰带,双襟中下方均有一个暗斜口袋”。[3]95早在延安时期,女干部们就逐渐流行穿着灰布列宁装②代表女性革命身份的列宁装最早是男性着装,之后出于革命气质的表象模仿,女干部们渐及开始以着列宁装为荣。,并且夏季以单衣为主,冬季则是身着棉衣,统一制作发放。列宁装不同于西式女上衣,亦不同于男式中山装。“这种不加衬里、不加垫肩、简易的苏式服装,在那种革命激情高涨的岁月里,实在是很具有时代精神的。”[4]54
(一)列宁装与女性革命形象
1949年前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巩固人民政权过程的加快,革命文化从延安一隅扩展至全国各地,服装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表现尤为突出。自延安时代开始,八路军机关干部已经开始流行穿着列宁装。及至1949年前后,列宁装逐渐内化为中国式的服装,并且穿着对象从男性群体逐步过渡到女性群体。1950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实行新的军服样式,简称‘50式军服’,其中,陆军女军人冬装即为列宁装”。[5]61女军人身着列宁装是对延安时期女干部身着列宁装的一种回应,社会对于革命军人以及机关干部的推崇,从而使得列宁装具有风靡的基点。
在党政机关与学校,诸多女干部均喜欢穿着蓝色卡其布缝制的列宁装。王芳说:“我在部队退伍之后,分到某机关工作。第一天上班,当我身着旧时列宁女装上下班的时候,女同事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后来有个女同志向我咨询如何定做列宁装,我就把自己以前的一套列宁装借给了她,她说,自己从此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后来无一例外,我们机关的女同志都穿上了颜色不一的列宁装,感觉自己就像在革命的队伍之中。”①参见笔者在天津市和平区对王芳的访谈笔录(2013年7月3日)。王芳,1930年生,20世纪50年代初为天津和平区某机关干部。从女军人到女干部,她的身份虽然发生了转化,然而列宁装与革命进步对等的政治意蕴是一成不变的,列宁装成为革命的界标。
对于学校的女老师而言,身着列宁装本身便是很好的政治革命的体现。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刘思娣说:“上课的时候,发现女老师穿着漂亮的列宁装,英姿飒爽地给我们讲《新民主主义论》,我们都觉得老师就像一个女英雄,列宁装就是革命的服装。后来,同学们也都陆续地穿起了列宁装,大家还在宿舍里比较谁的衣服颜色好看。再上课的时候,我们穿上列宁装听课,立刻就感觉到与老师的革命思想连结起来了,为革命努力学习。”②参见笔者在天津市南开区对刘思娣的访谈笔录(2013年8月29日)。刘思娣,1938年生,20世纪50年代初为天津南开区中学学生。可以看出,女老师讲授的文本与其着装统一,引起了女学生的相应模仿。换言之,衣服相对于课堂课本,更具革命凝集之意涵。
女军人、女干部与女教师的职业属性属于非生产者角色,列宁装在革命宣教与实际应用层面,皆具有推广的社会价值。而作为以劳动生产为主的女工群体,同样对于列宁装青睐有加。“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6]尤其是梁军圆润的脸庞、齐耳的短发,加上灰色的列宁装成为20世纪50年代农场女工的经典形象。进而言之,列宁装符合女性劳动模范的价值标准,职业的属性附属于革命劳动的意涵潮流之下。
女劳模身着列宁装的做法,对于广大女工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卢春花说:“我们的车间组长姓苏,平时上下班都穿着一身蓝色列宁装,我们几个女工都躲在门口看,心里可高兴了。有时候会学一下组长穿列宁装走路的样子,可神气啦。”③参见笔者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对卢春花的访谈笔录(2014年10月20日)。卢春花,1932年生,20世纪50年代初为济南纺织厂女工。不难发现,普通女工对于穿列宁装的崇拜,一方面固然缘于列宁装所蕴含的革命气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女干部的直观影响。
由于当时民众薪水不高,列宁装在部分女工视域之中便成为高贵的革命礼物。女工张小红说:“我姐妹五人,我是家里的老小,当时大姐刚结婚,姐夫来我们家的时候,送我一件黑色的列宁装。偷偷地告诉我,这是女拖拉机手梁军曾经穿过的列宁装款式。我只有周六、周日上公园的时候穿上。”④参见笔者在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对张小红的访谈笔录(2014年10月27日)。张小红,1935年生,20世界50年代初为济南纺织厂女工。可以看出,受女劳模的衣着影响,普通女工将列宁装视为一种实体崇拜,即服装是否具有实际的效力,并不是其考虑的重点。为数甚多的女工群体青睐列宁装,从而使得城市女性服装的样式渐次发生改变。
正是由于女干部、女老师以及广大女工渐次示范蓝色列宁装,从而使得蓝色成为时代的宠儿。1956年的《人民日报》刊出《四季长青》漫画并配有诗句:“桃花开了,姑娘们穿着蓝色;荷花开了,姑娘们穿着蓝色;菊花开了,姑娘们穿着蓝色,水仙开了,姑娘们穿着蓝色。”[7]从中反映出人们对于蓝色列宁装色调的无限憧憬。正如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所言:“一身蓝灰色的服装,衬托出一种温柔而又脆弱的冷淡,几乎不可逾越,它掩护着女人们的身体,就像狂轰滥炸的恐慌年代防护在屋顶上的帆布。”[8]148“在这种遮蔽或突出的功能选择中,表现了人们对身体的认知。”[9]
(二)列宁装与国家崇俭理念
列宁装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推广,从深层次而言,列宁装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要使我国富强起来,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10]317他还说:“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11]491
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穿衣方面一向以身作则。李银桥曾回忆说,毛主席生活是非常简朴的,没有他的亲口允许,是不能为他添置新衣服的。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12]34周恩来的内衣是补了又补,接见外宾时穿的中山装也是十分陈旧,领子部分和肘部都曾补过。[13]319刘少奇穿的也是粗布衣服和布鞋,只有接待外宾的时候,才穿上中山装和皮鞋。[14]对于国家领导人坚持朴素着装的做法,朱德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由于我们中央的同志都是布衣服,大家也都朴素,把解放区的风尚带来了,但没坚持多久。后来我们也穿上了料子衣服,大家也都穿起来了。说明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以后我们还是要改,大家都朴素起来。”[15]282事实证明,党和国家领导人简朴的衣着方式对于巩固新生政权、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起到了积极的功效。这一思想的深入贯彻对民间服饰也有很大影响。一些殷实之家里原有的比较贵重或华丽的服装及衣料,往往压在箱底秘不示人。
与此同时,衣服的靓丽与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的标识之一。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6]317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就遭到了西方敌对国家的经济封锁,进而导致“人们对穿着的要求越来越简单,讲究穿着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17]11学者艾华也指出:“从40年代的延安时期到70年代末,服装在一定程度上男女是一样的。在服装上公然地表现女性气质,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兴趣的表现,与党的思想所要求的节俭、无私的集体主义是不相符的。”[18]124
于是很多城市女性为了表示拥护革命,主动脱下旧时代的旗袍,换上象征革命的列宁装。随后经过“三反”、“五反”以及三大改造运动,穿列宁装成了女性穿衣的首要选择。“这次服饰的演变不是由行政的强制命令来完成的,而是人们在对革命的向往中,在蓝色干部服的不断渗透中,在革命意识逐渐加强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自然形成的。”[19]165至此,大翻领、双排扣、束腰带的蓝色列宁装布衣被视作最革命、最时髦的衣装。更为重要的是,“服饰的变迁滋生出新中国人们的一种集体革命潜意识,于是,新中国的列宁装就具有了新时代的符号意义”。[2]20
二、花衣运动:改变与调适
20世纪50年代女性推崇的列宁装,逐渐造成了社会服饰男女统一化的趋向。当时的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指出:“穿制服的男女一年多似一年,近一二年不但是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穿制服,而且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农村妇女,甚至小学生也有不少穿上了制服。”[20]实际上,列宁装并不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妇女和儿童穿着。“妇女和儿童的服装之所以要有区别,是因为服装必须符合于不同生理和不同生活的需要。”[21]廖沫沙在给好友张文松的信中也说:“女同志穿男制服(列宁装)至今虽已看了四年之久,却始终看得不舒服。男女不分,我觉得这也是不尊重女性的心理之一。”[22]
而之前女性盲目推崇列宁装,造成她们原有的旗袍、裙子被闲置。“还有一些人将原存的西服不穿,一定要重新加工改制成制服才穿。颜色鲜艳的旗袍和裙子不穿,一定要重新染过,染成黑的蓝的再改成制服衬衣才穿,这些做法是很不经济很不合理的。”[20]与此同时,棉花供应紧缺的现实也对女性着装产生了影响。以棉布为例,“1952年虽然增加了27%,可是市场销量竟增加了47%,生产和消费之间产生矛盾”。[23]为了保证纺织工业用棉,保证人民生活所需棉花的供应,“国家决定从1954年秋季新棉上市时候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花统购”。[24]由于各级政府对于统购任务认识不到位、棉农的经济利益未得到及时满足,统购任务完成较差,九十月份仅仅完成了月计划的57%。①参见北京档案馆:《必须努力完成棉花统购任务》,档号040-001-00016,1954年12月9日。因此,基于节约与经济适用的原则,列宁装的改进势在必行,并由此开启了花衣运动之序幕。
(一)改变:花衣设计理念与服装展览会
对于如何改进服装式样或者制定女性新服饰的标准,艺术界的领导、专家首先发表了看法。1955年4月,《新观察》将江丰、张仃等艺术界的领导召集一处,讨论中国服装未来的发展趋势。江丰提出,用长裤和中国式的短袄来代替干部服,认为这样方便工作,也能将男装和女装区别开来。张仃认为,女性晚装可以采用明清风格,而日常穿着则应以布拉吉为主。虽然《新观察》发起的女性服装改进运动未能就日常服饰标准达成共识,却奠定了女性服装设计理念的趋新基础。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列宁装之改进无异于一针强心剂。“这个方针的提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25]以郁风为代表的美术、服装设计师们再次对于服装的改进提出了相关建议,认为应该以我国现存的一些穿衣习惯为基础,逐渐发扬民族服装传统中合乎现代生活需要的部分,而且应同时容许西式服装并存。[26]
女装作为服装改进运动推展之重点,受到诸多服装设计师的关注。1956年4月,《美术》杂志集中刊载了女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式样,如吴淑生、陈碧茵设计的适合中年及青年妇女穿着的浅素色衣裙;顾群用蓝色、灰色、白衣、咖啡色设计的适合工人、工程师以及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罩衣;常沙娜设计的适合一般青年妇女穿着的连衣裙;郁风借鉴江南农村做裙的方法,设计出适合于青年妇女穿的衬衫等。[27]
针对不同的妇女群体,着装引领了之后花衣运动的风向。北京市服装联社设计师李瑞全认为,应该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来选择服装的式样和色彩,比如“身材与服装式样”、“脸型与领口形式”、“肤色与服装色彩”、“性格与服装色彩”、“季节与服装色彩”,并推荐设计“女短衫”、“骑车式秋冬女短大衣”等等。[28]这些针对不同职业、年龄、身材设计女装的做法,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服装设计市场,并带动了服装消费市场之繁荣。
在社会各方呼唤妇女服装多样化的舆论之下,上海、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相继举办了以展示女性、儿童服装为主的服装展览会,引导着社会大众的消费趋向。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其中有不少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鲜艳丰富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上海《青年报》报道并称赞了此次展览会:“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29]
1956年3月11日,南京市美协联合百货公司等8个单位在南京文化会堂联合举办了“服装展览会”。展品是以收集和采购现有的服装为主,并新做了约200多种适合妇女四季穿着的服装。这些服装是选用色彩鲜艳的花布、线绒、印花绒、丝绸和呢料制成的,式样有旗袍、外衣、裙子、毛衣等等。[30]观众对于该展览会很感兴趣,他们在每件服装的意见卡片上表达自己喜爱与否的意见。展览会上也张贴了漫画,讽刺那些对于服装改进持保守思想的人,同时用醒目的标语说明美化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与上海、南京服装展览会注重突出成年女性服装款式所不同的是,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首都服装展览会更为强调从性别本原上对于服装加以调试,因此儿童服装设计成为一时之热点。“这次展览会共陈列了男女童装共计762种,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展出了春、夏、秋三季的式样,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穿着。”[31]从实际效果来讲,女童服装不仅经济适用,而且款式新颖,深受年轻女性的青睐。
由上可知,以郁风为代表的艺术界发起的服装改进运动,其着力点主要是从女性个体发展的需要出发并加以现实考虑,覆盖了各个不同的年龄段。这反映了艺术界、文化界人士对于普通女性阶层生活的关注与重视。
(二)调适:身份与政治之间
吊诡的是,之前首倡“列宁装”的机关女干部却在美丽与政治之间呈现出尴尬之相。例如,河北安平县的女干部一般都有几件花衣服,然而却不愿意带回农村或者下乡时穿上,只因为怕乡亲们说她们到了大都市就不朴素了,怕下乡工作时不好接近群众,这样一来,女干部们所穿的衣服依然保持着列宁装的黑蓝灰色调。县里的几位女同志认为:“要穿就大家穿,否则就显得太个别。”并且提出首先要妇联的同志带头穿,再号召所有的女干部们都穿。[32]
机关女干部惧怕穿着花衣服,折射出传统革命文化的代际影响。曾几何时,列宁装被视为荣耀之衣裳。国家有关花衣之宣传,在她们看来,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效力。“要穿一起穿”,反映了在一种相对固化的集体之中,人们对于彼此类同性的欣赏。换言之,革命的气质不能随意遗弃。
当时的机关女干部沈红芳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列宁装就是最好的衣服,又革命又威武,换什么花衣服?那是资产阶级小姐才穿的哩!等别人都穿上了,我再说吧!”①参见天津档案馆:《服装问题的报告》,档号X0048-Y-000267-013,1956年3月8日。沈红芳的话语反映了当时处于新旧文化的一种碰撞,即国家话语层面的动员与实际层面的滞后性。对于此,瑞士记者莉丽·阿贝格观察到,1956年“五一”游行时,学生、手工业者和其他许多游行者并没有统一着装。“妇女们,尤其是年轻姑娘们穿着漂亮的衬衣和花裙子,几个月前这儿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现在提倡服装多样化。”②参见上海档案馆:《五一大游行》,档号Q192-1-2842,1956年5月3日。因此,社会上对于花衣运动颠覆性的认知,从而使得机关女干部难以定位本身的社会身份。
与此同时,有女性表示,穿花衣会与之前穿列宁装一样,出现某种社会从众现象。“与过去否定花衣服的情况相反,现在出现了一些否定列宁装的偏向。”[33]如果设计家们只热衷于少数几种式样的话,岂不是“人民装”要让位于“布拉吉”。[34]由此可见,长久以来列宁装与女干部对等的社会身份认同,成为女性推展花衣运动的藩篱。
在赞成与隐忧之间,花衣运动是继续推展还是适可而止?适时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从政治层面给予了相关理论支持。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关系”论断,认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主义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漂亮的衣服并不等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的衣着也应该丰富多彩起来,人们有追求美的权利,更有享受美的权利。”[35]166
在“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之际,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兼顾。”[16]92他还指出:“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的生活。”[16]36周恩来亦指出:“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6]143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人民生活的相关指示,实际上是对花衣运动持默许态度。随后,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女联合会明确提出,爱美是人的天性,美和装饰是一种艺术,服装的整洁美观是一种有文化修养和热爱生活的表现,从而形成50年代以来人民在穿着上最活跃的时期。[37]诸多女青年穿起花布罩衫、绣花衬衣、花布裙子等,在展示女性美的同时,彰显出当时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趋向。
由此观之,花衣运动缘起为经济与性别的双重诉求。伴随着在现实层面的日益推展,女性阶层的穿着遂成为社会注目之焦点。国家对于女性穿着多样化的默许与认可,从而为布拉吉连衣裙的流行奠立了政治舆论基础。
三、布拉吉:中苏友好背景下的性别图像
1956年春夏之际,为了响应中共中央以及全国妇联穿着多样化的号召,北京各大街道兴起了名叫“姑娘们穿起来”的宣传画,动员广大妇女们踊跃穿起“布拉吉”。①“布拉吉”(Blazy)为俄语的音译,是连衣裙的意思。北京大学的食堂、墙壁几乎一夜之间贴满了鼓励女学生穿布拉吉的大字报、漫画。“一时间,北京街头到处是穿花色‘布拉吉’的妇女,‘布拉吉’继‘列宁装’之后再度成为女性服饰之时尚。”[38]42需要提及的是,当时的布拉吉风尚承接的依旧是花衣运动之理路,即美观是女性着衣的第一要素。
从材质而言,布拉吉连衣裙上半身吸取了男式衬衣的式样,尖领、长方形前襟,下部与裙子相连,整体造型美观、大方、明快,色彩上鲜艳多变。[39]13相较之前严谨的列宁装,布拉吉常见的身形有收腰型、直身型、旗袍型、马中型、喇叭型及细褶型等。[40]101另外,“布拉吉的衣领到腰节,和从腰节到下摆往往呈黄金比的关系,而不像别的衣服那样故意要高腰节、低腰节或没有限节,因此布拉吉很耐看。”[41]91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女子爱美、交际的心理,因此倍受女青年的欢迎。
(一)移植性别:布拉吉与苏联女专家
1958年7月31日,苏联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第二次来中国访问,感受到中国服装过于单调,提出中国当时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他说:“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裙,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并建议女性可以穿俄式连衣裙——布拉吉。”[42]175赫鲁晓夫对于中国女性服装的建议,耦合出“此时中苏关系进入到亲密合作时期”。[43]143在此之前即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40周年观礼,同时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共运会议,并重申了中苏之间的革命友谊。故此时中国女性仿穿苏联布拉吉便有了新的时代意涵,即超越性别本身的指代性,上升为大国之间的文化推手。
此时的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迅疾通过电影、画报、期刊等媒介引入了一大批苏联各行各业身着布拉吉的女性图像,因应苏联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国家导向,故画报中尤以身着布拉吉的工业建设女性为多。这恰恰契合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代之理路,中国妇女就业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家庭妇女参加工业建设的热情无以复加,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44]197
对于城市女性学习苏联女专家踊跃穿着布拉吉,亲历者依然如数家珍。魏晓红说:“那个时候(1958年)我13岁,满大街都是为了学习苏联女专家,要踊跃穿着布拉吉连衣裙的海报。暑假考试我考了个全班第三名,妈妈非常高兴。作为奖励,送给我一条漂亮的花色布拉吉裙子。我记得妈妈说,以后你要向苏联女专家学习,去苏联学习工业建设专业,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②参见笔者在天津市和平区对魏晓红的访谈笔录(2013年7月3日)。魏晓红,1945年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天津二十五中学生。
身为一线工人的贺素芝也有类似的历史记忆。她说:“我当时是一名毛纺厂工人,1958年女工有一次开大会,工会主席讲了很多向苏联学习的话。最后,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印有苏联女专家穿着布拉吉的海报说,苏联女专家多好看啊,穿上布拉吉连衣裙那就更好看。我们要努力生产,争取每一个人都穿上布拉吉去莫斯科!”③参见笔者在天津市河西区对贺素芝的访谈笔录(2013年7月4日)。贺素芝,1939年生,20世纪50年代为天津纺织厂女工。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发现,身着布拉吉成为当时大多数女性学习、工作进步的标志,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女专家的表征之一。
努力学习苏联女专家,亦体现出中苏友好背景下中国着力发展工业建设的经济意涵。按照《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以及“一五”计划的规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集中主要力量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进行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45]80事实上,“截至1957年,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建设的项目,全部和部分投产的分别为68个和27个”。④参见北京档案馆:《中苏工业合作报告》,档号040-001-00016,1954年12月9日。为了加速中国现代化工业进程的建设,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关注工业建设方面的技术专家,尤其是具有性别解放意涵的苏联女专家备受社会推崇,其衣着打扮自然也在注目之内。
(二)助推性别:布拉吉与中国制造
模仿身着布拉吉的苏联女专家,亦在一定程度上耦合出中国纺织业学习苏联的阶段性成果,即具备充裕的花布材料。自1956年之后,在苏联等相关技术部门的援助之下,我国纺织工业得以迅速恢复,印染技术的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制作布拉吉的花布逐渐变为国产品牌。例如,上海在印染布产量中的花布产量大大增加,“花布总产量1956年较1949年增加了4.6倍,较1952年增加了2.7倍。1956年更是大量就制新花色品种,并获得很大成就。全市共试制新花色、新规格的纺织品4000种,其中,64%获得成功,一部分并得到广大人民喜爱”。①参见上海档案馆:《上海纺织工业概况文件》,档号Q193-1-1232,1956年11月21日。
就在几年前,中国的花布还主要依赖苏联的进口。“1953至1954年,中国进口苏联花布的比重占到总进口额的1.5%与3%。”[46]30“一时间家家户户,从床单、被面到窗帘,凡有用得到布料处,几乎都是俄式花布,就是用这种苏联大花布,做成了青年女子的布拉吉。”[47]93因此,当我国妇女使用国产花布裁剪布拉吉时,有人曾不无担忧地指出:“我们不用苏联花布了,那苏联还会像以往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业建设吗?”②参见北京档案馆:《群众眼中的苏联花布》,档号179-001-00016,1954年12月9日。“苏联老大哥会不会从此疏远我们啊?”③参见北京档案馆:《苏联花布状况调查》,档号179-002-00015,1954年12月11日。甚至有人将是否穿着苏联花布做成的布拉吉看成是政治态度。时任北京某学校教员的柳倩君说:“只有购买苏联花布才能证明我们与苏联之间是友好的,不购买苏联花布将破坏中苏联盟,损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这正是帝国主义所盼望的。”[48]27
实际上,中国纺织业的迅速崛起,与中苏友好下的工业建设合作并不矛盾。进一步说,中苏友好并不意味着苏联文化的单向度输入;相反,中国通过自力更生之研发,完成纺织品自主制造,同样是中苏友好的态度使然。对于此,毛泽东在会见赫鲁晓夫时曾经郑重地指出:“中国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需要外援,但不依赖外援。中国将努力发展生产,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43]121
正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奉行独立自主的工业建设思想,所以以布拉吉为代表的衣服制作方式逐渐从手工裁剪过渡到机械化制造阶段。“从1958年开始,服装行业的机械化程度逐年提高,电动缝纫机、电动剪刀、电熨斗等一批电动工具逐渐普及。以后又出现了裁布机、锁眼机、钉扣机、包缝机、整烫机等。”④参见上海档案馆:《中外服装调查概况》,档号Q195-1-124,1959年1月10日。由于机械化、电动化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水平,布拉吉质量也大大地提高,不但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员,而且满足了广大女性的审美需求。
中国服装产业的迅疾发展,逐渐引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瞩目。1958年,第九届国际时装会在罗马尼亚举行。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时装发展的方向,提高服装的艺术和技术水平,从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中国作为受邀国家,郑重出席了本次时装大会,并推出26套服装,其中以女性、儿童服饰居多。“各国代表对中国所展示的服装给予了肯定,尤其是对以中国花布制作的布拉吉连衣裙给予很高的评价。”[49]主办国罗马尼亚引导中国代表参观服装工厂,对于女性、儿童服装的制作、加工等给予相关指导,并对布拉吉、旗袍等服装给予了具体改进意见。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视阈来看,中国通过布拉吉的制作,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女性的国际形象,并由此融入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网络。
要而言之,布拉吉确实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走进了城市女性的日常生活,凸显了其强烈的社会性别表征。这种性别首先是通过移植苏联女专家形象来完成的,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成为回归中国本土性别的胜利之匙。一如英国学者珍妮弗·克雷克在《时装的面貌》中指出的:“服饰是构建人自身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身体技术,人们通过穿衣配饰这一装饰身体的行为达到自我认同。”[50]8
四、结语
列宁装与布拉吉两款女性服装的相继流行,彰显出时代所赋予性别的特殊意涵。列宁装的适时出现,旨在表明当时的女性对于革命话语的深度诠释,即服饰的类同性给予其内心世界强烈的安全感与幸福感。“服装和外观提供了一种肉眼可见的基础,可以表达对团体的认同,建立起能够提供荣誉、名声与认同的社会身份。”[51]438但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包裹在黑、蓝、灰色的劳动制服下面的身体方便女性进行劳动生产的同时,拒绝表现女性身体的性别特征”。[9]
“一五”计划的完成为女性回归本体身份奠立了经济基础,“双百方针”的提出则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上一次新的解放。因此,布拉吉的流行具备了良好的国内空间。与其相适应的是,布拉吉的迅疾流行始于中苏两国在政治层面的亲密合作交流。这种合作呈现出双向互动之情态,一方面,苏联援华女专家成为中国女性关涉工业崇拜之偶像;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独立自主之发展理路,故以布拉吉为切口,具有中国风尚的纺织业、服装业皆迭次而起。正如法国文化史学者丹尼尔·罗什所说:“服饰文化首先是一种秩序,透过服装语言的嬗变,可以看到各国社会价值的转化。”[52]
[1](英)琼·安娜.服饰时尚800年[M].贺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雷蓓蓓.从建国后的服饰流变看国人审美观念的演化[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华梅.中国服饰[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4]陈明远.革命女性的标准时尚[J].文史博览,2013,(1).
[5]刘爱芳.现代女性打扮的风格[J].现代服装,1996,(6).
[6] 田君.列宁装、人民装[J].装饰,2008,(2).
[7]人民日报社.四季常青[N].人民日报,1956-04-11.
[8](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M].赵靓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9]韩敏.新中国妇女的视觉形象建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28.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2]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13]诸葛铠.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14]舒薇.保姆爆刘少奇的“私生活”让人心酸[J].政府法制,2011,(2).
[15]朱德.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7]樊志辉,王秋.中国当代伦理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8](英)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M].施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9]王东霞.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0]张琴秋.谈谈服装问题[J].新观察,1955,(11).
[21]丁正.谈服装的变化和服装改进问题[J].美术,1956,(4).
[22]陈海云.廖沫沙的风雨岁月[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23]人民日报社.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N].人民日报,1954-09-14.
[24]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N].人民日报,1954-09-09.
[25]金风.双百方针的社会反响[N].大众日报,1956-04-29.
[26]郁风.发扬服装的民族风格[J].美术,1956,(4).
[27]郁风.妇女服装设计[J].美术,1956,(4).
[28]李瑞全.谈服装[J].装饰,1958,(1).
[29]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N].青年报,1956-01-10.
[30]纪维周.南京举办服装展览会[J].美术,1956,(4).
[31]甸义.记首都的服装展览会[N].人民日报,1956-04-01.
[32]记者.活泼的小乌鸦[J].新中国妇女,1955,(3).
[33]记者.群众对于改进服装的意见[J].美术,1956,(4).
[34] 关仲.对改进服装的几点建议[J].美术,1956,(4).
[35]王东霞.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6]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7]北京服装纺织杂志社.新中国服饰的演化[J].北京服装纺织,2008,(4).
[38]宋卫忠,蒋方.当代北京服装服饰史话[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39]蔡磊.服饰与文化变迁:以20世纪以来中国服饰为例[D].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0]徐清泉.中国服饰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41]张竞琼.服装艺术:衣品如人品[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
[42]刘建美.从传统消遣到现代娱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43](俄)顾达寿.直译中苏高层会晤[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44]华梅.服装美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
[45]孙璐.从追随到竞争:苏联与中国经济速度的设定(1951—1960)[M].北京:世界图书上海出版公司,2013.
[46]郭国有.四进央行[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47]王德智.华夏风情[Z].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2.
[48]马长凯.打你不许哭[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49]陈光宇.第九届国际时装会议与新中国的服装事业[J].装饰,1959,(5)
[50](英)珍妮弗·克雷克.时装的面貌[M].舒允中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51](美)Susan B.Kaiser.服装社会心理学[M].李宏伟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
[52]汤晓燕.服饰与19世纪初法国女性性别角色观念[N].光明日报,2015-10-24.
责任编辑:张艳玲
Aesthetics and Politics:Analysis of Urban Women Fashion during the 1950s
TANGRui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China,the appearance of Lenin in Yan’an era gradually became the newtrend of women’s clothing,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State.Revolution behind fashion,however,gradually led to waste of material and the confusion of gender.In addition,the reality of China’s cotton supply shortage eventually resulted in a campaign to improve clothing style in the art world.The opening of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ed to lead the movement to a newpolitical field.Under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Sino-Soviet friendship,the Soviet Union’s“Blazy”dress became urban women’s fashion trend which improved women’s status in social communication.Its popularityimplied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othing industry.The popularity of Lenin’s clothing and Blazyhad been a cuttingprofile ofn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practice ofwomen’s life,and a microcosmofthe transition of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newChina.
citywomen;fashionable clothing;Lenin coat;“Blazy”dress
10.13277/j.cnki.jcwu.2017.04.011
2017-06-05
D442.9
A
1007-3698(2017)04-0081-09
汤 锐,男,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276826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阈下的城市女工研究(1949—1966)”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DDJJ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