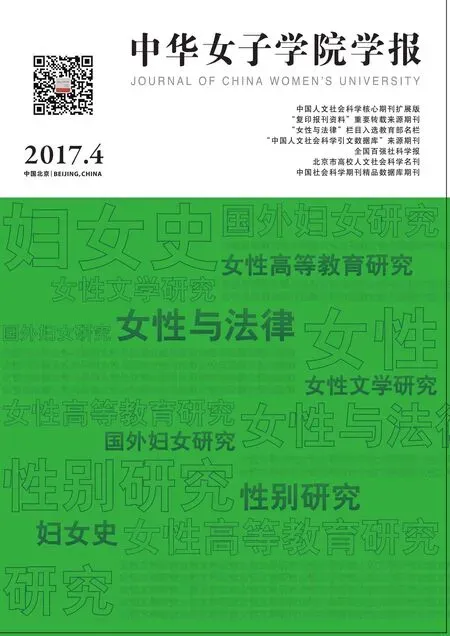女性主义法学视角下的代孕规则检讨
2017-01-27张融
张 融
女性主义法学视角下的代孕规则检讨
张 融
代孕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我国现有的语境下,代孕并不为立法允许。表面上看,禁止代孕是出于维护女性利益考虑,但由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存在着性别差异,因而禁止代孕从本质而言是性别偏见的产物,其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还使不孕女性和代孕女性的权益裸露在立法的保护范围之外,间接上也造成了地下代孕市场的畸形繁荣。在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和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禁止代孕无疑与主流发展趋势相违背,其使女性遭受不可预料的伤害。因此,立法者必须立足于实际情况,以女性主义法学为视角,对禁止代孕的规定进行重新审视,并从女性利益立场出发,在性别平等理论的指导下重构代孕的规则体系,具体而言,应在允许妊娠型代孕的同时禁止基因型代孕与捐胚型代孕。
代孕;生育;女性利益;女性主义;性别平等
女性主义法学最初由美国安·斯盖勒于1978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女权运动。虽然其后分化出诸多流派,但是在追求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即以女性视角对父权文化下的社会制度进行抨击,追求男女权利的实质平等,扫除法律对女性的偏见,维护女性的权益,最终实现妇女的解放。[1]目标的一致性使女性主义法学得以自成一派,其对于女性权益的维护具有重大意义。女性主义法学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我国,至今已逾三十多年,其研究成果在推动立法保护妇女的权益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①如在200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总则”中明确规定,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又如2015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维护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人身权益。这些法律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保障了女性的合法权益。但从整体而言,我国的法律现状与女性主义法学的目标仍存在差距,法律的性别化现象仍局部存在,女性权益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合法掠夺。与女性利益紧密相关的代孕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现有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规则从实质上来说存在着性别偏见,给女性的权益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若不予以改变,将无助于实现女性主义法学的目标。
一、作为本文研究视角的代孕
由于立法并无明文对代孕做出界定,因而代孕在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定义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条件,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借助语言描述事实问题的时候,明确的定义是科学研究成功的前提。只有语言表达方式统一才能使科学交流成为可能,定义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是不能放弃。没有确定的定义就不能清晰地思考、科学地认识。”[2]9因此,如果不对代孕进行清晰的界定,那么将难以发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规则存在的性别偏见。总的来说,在诸多争议观点中,对代孕的界定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代孕,又可称为借腹生子,主要是指女子以为他人生育小孩为目的而怀孕生子的行为,这里的“他人”多数是不能或不宜生育者,而不包括自己的丈夫或性伙伴。[3]本文暂且称这种观点为借腹生育说,其系对传统代孕行为的诠释与承继,着重强调代孕行为中的借腹,而无视代孕女性怀孕时采取的手段,因而通过性行为导致的代孕女性怀孕情形也被视为代孕。
第二种观点认为,代孕主要是根据委托协议,采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将适合委托方夫妻的精子和卵子,或夫之精子与第三人之卵子,或妻之卵子与第三人之精子在体外结合,然后将形成的受精卵或胚胎植入代孕者子宫内,在怀孕生产后,由委托方夫妻以法定父母的身份抚养子女的行为。[4]本文暂且称这种观点为隔离血缘说,其立足点在于孕母与孕子的非血缘关系,认为卵子来源于孕母的情形只能称为自孕,而自孕不仅会引起孕母和委托父母的纠纷,而且会带来伦理上的危机,因而代孕应仅包括妊娠型代孕。
第三种观点认为,代孕是指女性接受他人委托,采用人工生育方式为委托人生育子女的行为。[5]本文暂且称这种观点为借腹借卵说,其与借腹生育说相似,但又存在着根本差异,即借腹借卵说排除了自然生殖的可能性,强调代孕必须通过人工技术的手段进行,而对于卵子来源并不在意。因此,代孕不仅包括妊娠型代孕,而且还包括基因型代孕以及捐胚型代孕。①妊娠型代孕是完全代孕的一种,它是将不包含代孕女性自身卵子在内的受精卵植入代孕女性子宫,代孕女性仅为委托方夫妻提供健全的子宫怀孕生子,代孕女性与孕子不存在血缘关系,但夫妻一方必须与孕子存在血缘关系。捐胚型代孕亦是完全代孕的一种,是主要由第三人供精和供卵而实施的代孕,孕子与代孕女性、委托夫妻双方均无血缘关系。基因型代孕又可称为局部代孕,它是将代孕女性的卵子与委托方夫或第三人的精子以人工技术手段授精,在这种方式下,代孕女性不仅提供子宫,而且提供卵子,因而代孕女性与婴儿存在着血缘关系。
以上三种观点均从不同角度对代孕进行了诠释,具有其合理性。但本文更倾向于借腹借卵说,即认为代孕应是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将委托方丈夫或第三人之精子注入代孕女性的体内受精,或将委托方夫妻之精子和卵子、第三人之精子与妻之卵子、夫之精子与第三人之卵子、第三人之精子与第三人之卵子在体外人工培育成受精卵或胚胎后,植入代孕女性体内的行为。这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在我国的现有语境下,代孕必须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手段进行,因而通过自然生殖怀孕的行为并不能纳入规范调整的范围,这种方式充其量只能是传统“借腹生子”方式的延伸,其容易损害孕母的性自主权,借腹生育说具有先天的滞后性。其次,隔离血缘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代孕女性因孕子而与委托夫妻间产生的纠纷,但是却人为地缩小了代孕的范围,无视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孕母提供卵子进行代孕的情形②如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 (2012)浦民初字第1674号民事判决书中,由代孕女性提供卵子进行生育也被视为代孕的一种情形,代孕女性为所生子女的生物学母亲。又如在美国著名的M-baby案中,对于代孕女性怀特海德自行提供卵子的情形,法官亦将其视为代孕。,这不仅会致使基因型代孕裸露在法律规制的范围外,而且也容易造成法律与实践的脱节。最后,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代孕一词的词义,主要是指受他人委托,用人工辅助生育的方式为他人怀孕生子。[6]250由于语言饱含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反映着具体的鲜活生活[7],因而可以这么说,社会的一般观念也认为,代孕无须区分卵子的来源,而只要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手段实施即可。可见,借腹借卵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均较为契合实际,能全面反映社会中出现的代孕现象,具有其科学合理性。
二、禁止代孕的性别分析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目的在于解决人类的不孕不育问题,而人工授精和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代孕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立法层面上,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代孕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部门规章中有所涉及,如由国家卫生部2001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在其第三条中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规范代孕的价值取向,即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在这种价值的引导下,此后出台的多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均明确禁止实施代孕。总的来说,代孕技术在我国并不具备合法性的土壤。
(一)禁止代孕是性别偏见的产物
在实际操作中,代孕的实施既可运用人工授精,又可运用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其本质上是两种技术交叉衍生的产物。为了区分方便,一般认为,实施代孕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方部分或完全丧失生育能力,且其子宫完全丧失孕育胎儿的条件。而人工授精则一般适用于男方因无精、少精等部分或完全丧失生育能力的情形。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①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即日常生活中大众所熟知的试管婴儿技术。则一般适用于男方因无精、少精等部分或完全丧失生育能力,或女方因输卵管梗阻等部分丧失生育能力的情形。[8]19-20可见,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存在着性别差异。
与代孕的严令禁止不同,人工授精和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却被允许实施。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运用存在性别差异的语境下,这无疑在保障男性生育权利的同时限制了女性生育权利的行使。对于禁止代孕的法理基础,立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学术界和司法界产生了多种见解。但从禁止代孕的最新规范来看②2015年4月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中宣部办公厅、中央综治办秘书室等12部门发布《关于印发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严肃查处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和中介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这是禁止代孕的价值指引下的又一项新的规范。,禁止代孕的缘由在于:其一,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需要;其二,维护正常计划生育秩序的需要。这两项依据源于维护社会公益的需要,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价值进路,在内涵上虽具有其正当合理性,但却在无形中造成女性权益的损害。从女性主义法学的角度而言,禁止代孕的两项事由显然忽略了不孕女性的正当诉求,这无疑是父权文化的再现,使得女性权利在充满正当性的外衣下难以得到彰显,客观上导致规范的性别偏见。表面上看,两项事由冠冕堂皇,但从实质而言,却饱含着对不孕女性的偏见。
首先,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事由显然经不起推敲。显而易见的是,与代孕同为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在我国被允许实施,而两者所产生的医学效果是一样的,既然代孕有损人民群众健康,那么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何以具备实施的正当性?其次,维护正常计划生育秩序事由显然难以成立。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自诞生起,其在客观上造成的唯一后果是,促进人口的增长,这无疑与计划生育的目标相违背,令人疑惑的是,代孕、人工授精与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在人口增长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并无不同,既然后两者被允许实施,那何以独禁代孕?唯一能解释的理由只能是,因为代孕主要是为了解决女性的不孕不育问题,这直接导致不孕女性的生育权利被合法地剥夺。可见,规范中禁止代孕的事由,不过是父权话语下的托词,其最终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男女在生育权利上的失衡。
(二)“工具说”之提出与辩驳
由于规范中禁止代孕的事由不具说服力,为此,在学术界涌现了一批学者,分别从文化、市场、伦理等角度对禁止代孕的合理性进行剖析与论证。在其中,有一部分学者以代孕女性为视角论证了禁止代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工具说”理论,认为这不仅是维护女性权益的必要之举,而且还是女性主义法学的精神要义。具体而言,禁止代孕的主要原因在于,代孕使子宫工具化和商品化,使妇女沦为生育的机器,委托方将代孕母作为满足私欲的工具,这是不道德的。[9]
“工具说”源于康德哲学中的“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的道德律令,表面上看,其维护了女性的人格尊严,避免女性沦为男性的生育工具,体现了女性主义法学的精神内核。但从实质而言,这种观点不过是借用女性主义法学的口号来表达男性利益的诉求,在正当性的外衣下,它使女性争取权利的冲动被麻痹,其能否真正维护女性权益不无疑问。
首先,“工具说”表达的利益诉求较为片面。“工具说”仅以代孕女性为视角,其严重忽视了不孕女性的正当诉求,事实上,不孕女性的痛苦绝不亚于女性生产时的痛苦。据一份调查表明,几乎所有的妇产科医生都有同感,不孕不育症患者给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不育给患者带来痛苦与无奈,并且造成其长期处在精神和经济压力之中。[10]
其次,“工具说”难以解释我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现状。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中,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和部分代孕均需要通过体外授精成胚胎后再行植入女性的子宫,两者不同的是,前者胚胎的植入子宫系夫之妻的子宫,而后者胚胎的植入子宫系代孕女性的子宫。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代孕会使女性子宫沦为生育工具,那何以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能允许实施?更何况实施代孕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子宫完全丧失孕育能力。可见,在我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现状之下,“工具说”本身存在难以解决的内在逻辑矛盾。
第三,“工具说”否认了代孕女性的现实需求。器官、组织和细胞对于生物体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每个器官、组织及细胞的存在都有其唯一的功能,例如,精子和卵子的唯一功能是生殖,子宫的唯一功能是孕育胎儿。从另一方面来说,不同器官、组织和细胞的不同功能,在人类目的的实现上具有差异性,如胃存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类消化食物,而精卵子、子宫存在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人类生殖,这些器官、组织和细胞从本质而言都天然地具备工具属性。然而,“工具说”却将人格尊严与器官的工具属性相捆绑,导致器官的工具属性在社会观念中异化。事实上,代孕不过是女性利用自身器官的工具属性而实施的行为,这正如为治疗尿毒症而进行的肾器官移植。既然与身体相分离的器官移植能够被允许实施①为了规范医疗中的器官移植行为,国务院于2007年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在其第六条规定:“国家通过建立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动工作,确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组织协调人体器官的使用。”可见,国家对于器官移植行为是允许实施的。,那作为女性利用自身器官的代孕为何要禁止呢?更何况代孕女性并非仅仅将子宫视为生殖工具,而是包含着其特有的个人目的②对于女性进行代孕的目的,欧洲的V.Jadva教授曾随机对不同地区的女性做过详细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代孕女性并非盲目地仅仅将子宫作为生育工具,而是存在其特有的目的。在调查的样本中,79℅的女性进行代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不孕夫妇,12℅的女性进行代孕的目的是为了体验怀孕的感觉,5℅的女性进行代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金钱回报。参见:Janice.C.Ciccarelli and Linda J.Beckman,Navigating Rough Water:An Overview of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Surrogacy,Jouenal of Social Issues,2005,(1).,诚如有学者所言,“她们在代孕时,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也实现了自己的某种目的。”[11]以“工具说”否认代孕女性根据自然属性来利用自身器官的可能性,无疑是否认了代孕女性意欲通过自身器官的利用来实现个人目的现实需求。
可见,“工具说”不过是借用维护女性利益的口号来确保男性生育秩序的稳定,是男性代替女性行使话语权的结果。代孕的性别偏见并非如规范抑或是“工具说”理论中的冠冕堂皇理由所言,其存在有着深厚的父权文化根源。
(三)禁止代孕的性别根源分析
传统父权文化下,贞操被视为女性立人的根本,因此有古语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其中的“节”即是贞操,对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与性和生殖相关的事情上。[12]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未出现前,性与生殖紧密相关。在父权文化下,女性只有一辈子不和任何男子性交,或是一辈子只和丈夫这一个男人性交,这才叫保持了贞操。[13]133-134这决定了女性若想实现生育权利,那么其只能与丈夫一人通过性交的方式进行,这样才能避免“失贞”。通过贞操义务的设置,使女性的性权利和生育权利牢牢地掌握在丈夫手中,从根本上维护了男性的绝对权威地位。
虽然在历经多次的女性主义运动后,女性的地位已有所提高,但是文化天然的延续性,使得男女不平等的格局在客观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而且表现得更为隐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得性与生殖可以分离,女性的怀孕可不以性交为前提。但在社会世俗观念看来,性和生殖仍被捆绑在一起,与两者有关的行为被视为伦理禁忌。禁止代孕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女性利益,不如说是贞操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从现有的规范来看,男女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必须以存在婚姻关系为前提,因而仅在夫妻间进行的人工授精和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得以合法实施。而代孕则涉及婚外第三人,禁止代孕无疑确保了女性的生殖只为丈夫一人进行,这与传统的贞操义务何其相似,从本质上说是父权文化的再现。通过对女性生殖的控制,避免女性因为他人生殖而对其丈夫的地位形成挑战,从而防止父权家庭的危机,有效维护了男性的生育秩序。①司法实践中,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张×与高×离婚后财产纠纷案”,表明在现实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生殖控制意愿仍非常强烈。该案中,上诉人张×称,其妻高×在婚姻存续期间为人代孕,存在着重大过错,因而要求二审法院判令高×在离婚后赔偿其精神损失人民币10万元。女性代孕可能会损害丈夫的贞操情结,引起父权家庭的危机,在男性利益与女性权利的博弈下,立法往往会牺牲女性的利益而保障男性利益的最大实现,借以寻求男性秩序的稳定,这种结果源于男女的生理差异,使女性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终字第03323号民事判决书。可见,禁止代孕并非出于维护女性的利益考虑,其施行深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倘若不能及时革除,实现性别平等,那么女性的权益将继续遭受不可预期的正当性伤害。
三、禁止代孕对女性角色的伤害
据统计,我国育龄夫妇不孕不育发病比例达到1/8,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5000万人,不孕妇女占育龄妇女10%左右,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上升。[14]禁止代孕的实施,不仅导致代孕机构转入地下,而且关闭了不孕女性寻求合法生育的渠道。“当制定的法律与社会现实生活相背离时,人们就会规避法律,法律就犹如形同虚设,就会引起法律与社会间的疏离。”[15]当不孕女性难以寻求合法渠道实现生育权利时,强烈的抚育意愿必然促使其铤而走险寻求地下代孕机构,禁止代孕的规定如同虚设,地下代孕机构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日益繁荣。②南方日报记者的一份调查(发文于2011年11月28日)表明,目前全国有四五百家或大或小的地下中介代孕公司,其中广州就有四五十家,客户一般从网上或者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代孕公司。 而绕过中介自己找代孕妈妈的客户群体同样数量庞大。以“代孕”为关键字上网搜索,可以搜到180多个大大小小的QQ交流群,而且基本满群,同时约有3万名QQ用户在网上交流或寻找代孕合作者。由此可见,自2001年开始禁止代孕以来,地下代孕市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繁荣。参见凤凰网:《揭秘代孕江湖利益链:医院是真正获暴利者》,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babaotai/content-4/detail_2011_11/28/10945609_1.Shtml.由于代孕被严厉禁止,因而地下机构在实施代孕时无规范可循,这直接导致地下代孕乱象丛生,特别是对于代孕女性而言,其权益遭受侵害时往往求助无门。可以说,禁止代孕无论对于不孕女性的利益,抑或是代孕女性的利益,均产生了极大的伤害。
(一)对代孕女性的伤害分析
1.身体权权能的减损。身体权是自然人维护其身体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权利。[16]398身体权是公民人格权的基础,身体权的支配性意味着权利人对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享有自主支配的自由。禁止代孕,阻断了代孕女性自主利用自身器官去实现个人目的的可能性,这直接造成其身体权权能的减损。值得一提的是,依据我国的相关立法规定,基于自主意愿的捐献器官行为属于合法行为。③2007年国务院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的第七条规定:“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器官捐献与代孕同属于身体权的行使方式,既然与身体相分离的器官捐献行为合法,那仅仅利用自身器官功能进行代孕何以被禁止?
2.健康权的不当损害。禁止代孕,意味着国家不会就代孕行为出台相应的技术规范,这直接导致代孕委托主体的资格条件、精、卵来源、代孕女性的准入资格、代孕技术实施细则等事关代孕女性健康的事项规定仍处于空白状态,在地下代孕机构以盈利为目的的语境下,这无疑使代孕女性的健康权益陷入高风险的境地。④由于地下代孕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在无规范进行管理的情况下,委托人只要出足够的钱即可进行代孕,而对于精、卵来源等事关代孕女性健康的事项不闻不问,代孕女性可能因为精子、卵子供体核查不严而导致肝炎、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传播。目前,代孕都是地下进行,既无正规的医疗场所,又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更不会事前告知相关风险,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这诚如有关专家所言:“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过程中会涉及不同患者的用药敏感度、手术风险等问题,如果没有严格的规范,会对妇女身体健康造成伤害。”[17]
3.其他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首先,代孕的非法化,使得地下代孕市场游离于法律的边缘,代孕协议因此而被认定为无效。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在(2011)城中民一初字第83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代孕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内容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这直接导致代孕女性的利益裸露在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外。一旦出现代孕纠纷,代孕女性将无法可依,其往往只能忍气吞声。②中国妇女报2013年4月11日的一则新闻,现实地反映了代孕女性维权无门的状况,新闻中写道,代孕女子因怀的是女婴而被委托人“赖账”,导致其流落街头。由于代孕不受法律保护,代孕女子往往维权无门。类似的新闻报道频繁出现在媒体中。参见:《代孕,身心不能承受之重》,《中国妇女报》,2013年4月11日。其次,国家对代孕的严厉禁止使得代孕双方必须通过地下中介联系,而由于中介只以盈利为目的,因此这不仅会导致代孕的价格虚高,客观上阻碍了经济不富裕的不孕女性的生育权实现,而且对于代孕女性而言,其经济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盘剥。据报道,在一条代孕产业链中,一单市场价为三十万元的代孕,代孕女性至多仅能拿到十万元,而代孕中介竟可轻松拿到五万元中介费。[18]
在禁止代孕的语境下,代孕市场并没有被完全取缔,反而在地下获得畸形繁荣。在非规范化的代孕市场环境中,代孕女性的权益时刻处于被侵犯的境地。面对此种情形,立法不仅消极作为,怠于规范代孕市场,而且还对代孕女性的正当权利予以限制,这直接致使代孕女性的现实处境被人为地漠视,无疑把代孕女性推向绝望的深渊,给代孕女性的权益带来了不可预期的伤害。
(二)对不孕女性的伤害分析
1.生育权的不当限制。在我国传统语境下,“生”和“育”不可分离,生育一般被认为系有关求偶、结婚、生殖、抚育等一系列行为。[19]100因而男性即使不能分娩或不能产精,但一般均认为其仍享有生育权。③在立法层面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出台的目的在于规范生育秩序,确保不孕夫妇的生育能安全、有效和健康发展,而在其附则中,人工授精被分为丈夫精液人工授精和供精人工授精。可见,即使丈夫不能产精和分娩,其仍享有生育权,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方式生育子女。在司法实践中,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在其(2016)浙0902民初3598号民事判决书中称:“……原告杨勇会与周军因不孕而在被告舟山市妇幼保健院实施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有利于保障原告和周军的生育权……”可见,从本质上说,生育权是获得子女的权利,其与是否能生育无必然的联系。同理,女性即使不孕不育,但其生育权仍客观存在。生育权的内涵包括对是否生育、生育伙伴、生育时间、生育方式、生育质量和生育数量的自主选择。[20]105-115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规则的性别偏见,导致不孕女性的生育权遭到限制。一方面,禁止代孕的规定,致使代孕机构转入地下,这使遵守立法以及信息来源匮乏的不孕女性在行使生育权利时只能选择不育,与生育权的自主选择内涵相违背;另一方面,在市场规律下,地下代孕的价格虚高,这直接限制了经济不富裕的不孕女性对生育的选择,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孕女性群体行使生育权的两极分化。可见,在现行规则下,生育权遭到最大损害的无疑是信息来源匮乏和经济不富裕的不孕女性,这部分不孕女性是社会中的不利群体,立法对此不仅不予以保护,反而限制其权利的行使,这无疑使法律与公平正义理念相背离。
2.精神上遭受损害。与西方个人本位观念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之下,中国人的人生基调主要以家庭为本位,这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生育观。因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女性而言,生育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冲动是在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深深影响之下,内化到心灵深处的。[21]118通过生育可以使女性感受到家的完整。在我国,女性的生育诉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源于男性的强制压迫,而更多的是基于其内心的渴望。④在国家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有学者专门就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据广东省的一份调查结果表明,愿意生育二孩的女性为34.39%,比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女性多出将近10%,但是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女性本身已经拥有子女。另据一份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的调查结果表明,愿意生育二孩的女性为56.1%,而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女性仅为19.6%。参见张晓玲、戈祥:《“全面两孩”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然而禁止代孕却关闭了不孕女性生育选择的大门,这种想要而不能的局面会给不孕女性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
“女性控制自己生育的能力是她们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22]85,生育规则上的性别偏见不仅会导致女性其他权利行使的受制,而且还给女性带来不可预期的伤害,这不利于女性主义法学目标的实现。女性主义运动要求男女地位实现平等,而在法学领域则表现为男女权利平等的实现。现有的规则造成了女性生育选择上的不平等,这不仅与我国宪法倡导男女地位平等的价值相违背,而且也偏离了世界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潮流。因此,立法者必须立足于女性利益,充分考虑不孕女性和代孕女性的现实需求,以女性主义立场对现有的代孕规则进行重新建构,从而实现男女权利的实质平等。
四、女性主义法学视野下的代孕规则初探
“立法目的不是由立法制定者主观臆造,而是源于人的法律需要。每当人们对时下某种现实不满足,例如,某种社会关系缺少法律调整时,人们便根据已有的经验,提出充实和完善某一立法的设想,使之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能性。”[23]基于生育选择上男女不平等的现有格局,代孕规则的制定必须能回应女性的现实需求,体现女性的根本利益。女性主义法学的精神要义在于突出女性的特定性,提倡理论和制度必须建立在特定的女性现实之上,为此,女性主义法学者提出了特定化理论,即制度的建构须以“作为女性进行思考”的方法进行。[24]52在建构代孕规则的方法上,女性主义法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法律以妇女保护为由进行替代性判断不一定符合妇女自身的利益。”[20]268如前所述,无论对于不孕女性抑或是代孕女性而言,实施代孕技术并非源于强迫,而是有着其特殊的个人目的。既然女性基于自主选择了代孕,我们又何以越过女性的思维去代替她们思考呢?代替思考最终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结果与女性的意愿相违背,立法价值体现的仍是男性利益。因此,在代孕规则的制定中,必须立足于女性思维进行思考。对此,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设想。
(一)捐胚型代孕及基因型代孕之禁止
“作为女性进行思考”,意味着规则的建构须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女性主义法学认为,代孕尽管看起来是一种摧残,但却提供了一种救济形式,否则就会导致多数女性在不被允许控制的情况下被排除了选择权。[25]361适当放开代孕的限制,可以有效地保障女性对生育的控制选择权,而这本身又是她们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但是,允许代孕并不意味着允许任何形式的代孕,代孕的合法化必须以女性的利益为边界,对于损害女性利益的代孕则仍应禁止。具体而言,应以二分规制法为标准,允许妊娠型代孕的实施,并同时禁止实施捐胚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
二分规制法实施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允许妊娠型代孕可以有效地减少地下代孕行为,促进代孕机构的规范化发展;第二,允许妊娠型代孕不仅可以使代孕女性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而且不孕女性的生育权也得以彰显,其有效地满足了不同群体女性的现实需求;第三,捐胚型代孕作为精卵均来源于第三方的代孕,由其所生子女与委托主体、代孕女性均无血缘关系,在效果上与收养无异。既然收养可以达到捐胚型代孕的效果,那么禁止捐胚型代孕无疑是对不孕女性和代孕女性的权益均无害的最好路径;第四,女性主义法学的特征理论强调对女性的关怀,即从女性的独特情感、情境和经验去构建相应的规则。[24]78-85基因型代孕的卵子来源于代孕女性,子女的出生与代孕女性存在着事实上的血缘关系,相比于卵子非来源于代孕女性而言,基因型代孕更容易使代孕女性产生难以割舍的母性情结,在交付子女时这种情结往往会对代孕女性造成情感伤害①司法实践的实证数据表明,卵子来源于代孕女性的基因型代孕更容易对代孕女性产生情感伤害。以“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为例,在其中输入 “代孕”、“子女”字样,出现案例40篇,其中有4篇涉及代孕子女的亲权。在4篇案例中,有1篇为妊娠型代孕,案件焦点与代孕女性无关;有3篇为基因型代孕,其中1篇孕子已给代孕女性抚养,其余2篇则因代孕女性难以割舍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孕子女而要求委托主体返还。在美国著名的M—baby案中,代孕女性怀特海德因难以割舍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孕子M而毁约,并带着M迁往他州。很多学者也认为,基因型代孕因代孕女性与孕子女之间具有血缘关系,能够很自然地产生母子(女)亲情,因而应予禁止。但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妊娠型代孕会出现类似情形。参见吴国平:《“局部代孕”之法律禁止初探》,载于《天津法学》2013年第3期;刘长秋:《代孕规制的法律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6—98页。,因此禁止基因型代孕是对代孕女性的情感关怀。
(二)代孕女性的资格限定及权利规定
代孕是一项艰辛的劳动,在长达9个月的孕期里,代孕者要投入全部身心,要承担许多痛苦,其对代孕者的身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6]因而在代孕规则的重构中,必须首先站在代孕女性的立场去思考,以维护代孕女性的权利为第一要义,特别是当不孕女性和代孕女性的权利产生冲突时,应该以代孕女性的利益为重,这样才符合实质公平正义的理念要求。
首先,应限定代孕女性的准入资格。准入资格的设定,其目的在于避免女性因代孕带来的风险大于收益,造成其利益的不当受损。依据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情况,可对代孕女性的准入设定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处于育龄中,身体符合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条件;第三,有生育经历。①有生育经历的女性,可以有效地处理妊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女性因代孕而使身体受损。
其次,赋予代孕女性特定情形下的堕胎权。由于代孕承载着不孕女性与代孕女性的复合利益,所涉及的关系比较复杂,因而代孕女性在行使堕胎权时应特别谨慎。一般而言,代孕女性只有处于风险大于或等于收益的特定情形时,堕胎权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特定情形应包括:第一,危及代孕女性的生命;第二,危及代孕女性的健康;第三,所孕胎儿畸变。
最后,明确代孕女性的报酬标准。如前所述,代孕是一项艰辛的劳动,因而赋予代孕女性在经济上的选择权是合理正当的。对于代孕的报酬标准,应以社会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着重突出报酬的补偿性。报酬标准的确定,不仅可以有效地抑制代孕价格的虚高,保障经济不富裕的不孕女性生育权利的行使,而且能避免代孕女性的经济利益遭受损害。但报酬标准的确定,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代孕均为有偿,基于代孕女性动机的不同,代孕亦可为利他代孕。
(三)委托主体的资格限定
性别平等理论的精神要义下,决定了女性主义法学并不准备重建一个只对女性有利的法律制度,而是要重建一个平等对待女性的法律制度,扫除法律对女性的偏见。[27]在代孕委托主体的资格确定上,不应超越男性现有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否则出现的结果不过是以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去代替另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因此,代孕的委托主体理应与人工授精、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等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委托主体相一致。具体而言:第一,委托主体必须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禁止单身女性、女同性恋等实施代孕;第二,委托女方仅为不能孕育胎儿的女性,禁止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寻求代孕;第三,委托主体不应违反我国的计划生育原则;第四,禁止委托主体进行性别选择。
五、结语
201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生不出二孩真烦恼》一文,再次将代孕合法化的争议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我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的大背景下,代孕成为不孕女性解决生育问题的现实需求。禁止代孕的规定,不仅降低了我国生育政策实施的实效,而且造成不孕女性和代孕女性的权利难以得到维护。在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今天,禁止代孕无疑与提高女性地位的大潮相违背,其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立法的倒退。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修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删除了原草案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的规定,这不仅是世界代孕立法发展在我国的体现,而且是女性争取权益的证明,指明了我国代孕规则的未来发展方向。相信在未来的立法中,立法者能充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女性主义法学为视角,对禁止代孕的规定进行重新审视,并建构出一套性别平等、科学合理的代孕规则体系。
[1]杜瑞芳.关注弱势群体——女性主义法学的启示[J].妇女研究论丛,2002,(1).
[2](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丁晓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王贵松.中国代孕规制的模式选择[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4).
[4]李惠.论代孕的分类与法律涵义[J].医学与法学,2014,(4).
[5]许莉.代孕生育中亲子关系确认规则探析——兼评上海“龙凤胎”代孕案[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1).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高其才.法社会学的中国化思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1).
[8]刘长秋.代孕规制的法律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9]王彬.法律论证的伦理学立场——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J].法商研究,2016,(1).
[10]纪红建.不孕不育者调查[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11]梁立智.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的伦理辨析[J].哲学动态,2016,(7).
[12]杨遂全,钟凯.从特殊群体生育权看代孕部分合法化[J].社会科学研究,2012,(3).
[13]刘达临,胡宏霞.中国性文化史[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
[14]林培.“10万妇女不孕”告诉我们什么[N].新华日报,2013-01-08.
[15]盛张龙.论法律与社会间的紧张、疏离与相互影响[D].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6]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17]唐绪萍.揭开广西“专业代孕”背后的隐秘[N].新华社每日电讯,2013-01-25.
[18]林洪浩.代孕:谁在分钱,水有多深[N].广州日报,2011-07-06.
[1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周平.生育与法律:生育权制度解读及冲突配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22]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23]黎建飞.论立法目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1).
[24](美)朱迪斯·贝尔.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M].熊湘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5](美)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M].曲广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6]任汝平,唐华琳.“代孕”的法律困境及其破解[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7).
[27](美)帕特夏·史密斯.女性主义法学的合法性[J].王洪偏译.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5,(4).
责任编辑:蔡 锋
Analysis of Ban of Surrogacy and Legal Suggestions
ZHANGRong
Surrogacy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procreation technology.Surrogacy is not allowed in China’s legislation.Prohibition of surrogacy considers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but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artificial procreation technology makes prohibition of surrogacy a result of gender bias,which makes women vulnerable and be out of protection of laws.It indirectly leads to underground and illegal surrogacy.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feminism move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status,the ban of surrogac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main trend and leads to the infringement upon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Therefore,legislators should reconsider the regulations on surrogacy from legal feminist perspective and reconstruct the rules of surrogacy with the guidance ofgender equality.
surrogacy;child birth;women’s rights;feminism;gender equality
10.13277/j.cnki.jcwu.2017.04.003
2017-05-08
D923.9
A
1007-3698(2017)04-0023-09
张 融,男,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法。410006
本文系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民法典体系下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价值取向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CX2016B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