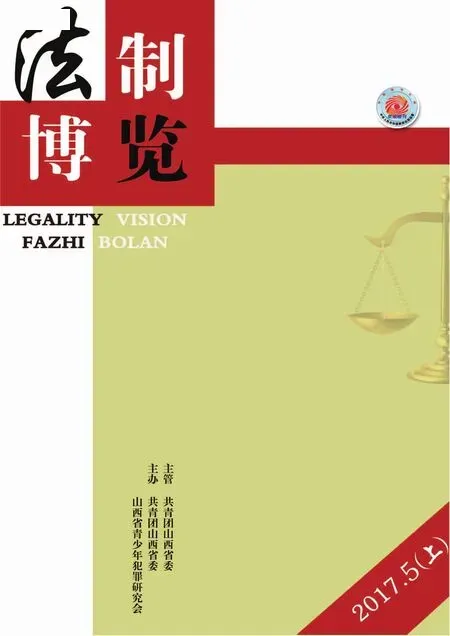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下举证模式的弊病
2017-01-27邹利伟
邹利伟
丽水市人民检察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下举证模式的弊病
邹利伟
丽水市人民检察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下的举证模式不区分证据资料与证据方法,通通以宣读笔录的方式调查证据。这种举证模式存在诸多弊病,表现在剥夺了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不能保证辩方的有效质证;使审判者承袭了侦查程序的心证,难以甄别材料真伪;使公诉人的举证显得单调呆板;也导致了控辩不平衡。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证据资料;证据方法
一、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下的举证模式
学者陈瑞华认为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是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模式,即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刑事法官普遍地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普遍通过宣读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作的笔录。[1](一)证据资料与证据方法的区分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举证模式是根本不区分证据资料与证据方法的,这是当前公诉人举证模式的现状。证据资料是指所有可能与待证事实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信息内容,其来源可能是任何一种相关的人、地、物。证据资料必须透过特定的方法才能显现,此特定方法即称证据方法,指探求证据资料内容的调查手段。
法定的证据方法包括被告、证人、鉴定人、勘验与文书五种。证人、被告的证据方法是听取自然人对过去事实的亲身体验,而鉴定则是听取具有专门知识的非当事人对事实进行的确认或者评价(意见),而勘验则是以感官感受(看、听、闻、尝、感知)人、物或状态,书证的证据方法则是以朗读的方式为之。被告、证人、鉴定人被称为人的证据方法,勘验与文书被称为物的证据方法。
(二)现状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一系列证据都通通能够转化为案卷笔录而存在。物证,可以拍照附卷;书证,直接附卷;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可以制作成笔录,勘验、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本身就是笔录;而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能够制作成光盘,或以书面形式打印附卷。另外,还有大量的情况说明、证明等法定证据种类以外的证据制作成案卷材料。
按照我国诉讼程序阶段划分,分为立案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与执行阶段。其中,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是主要的阶段。某一阶段的工作成果就是案卷笔录材料,而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的流转,也是通过案卷笔录材料的转呈的方式实现。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在公安卷,检察机关补充收集的证据在检察卷,而审判机关进一步补充收集的证据在法院卷。
检察机关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其举证责任之落实,便是由公诉人对案卷笔录材料的宣读与展示。依照高检院《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指导意见(试行)》中关于举证的定义,举证是指在出庭支持公诉过程中,公诉人向法庭出示、宣读、播放有关证据材料并予以说明,以证明公诉主张成立的诉讼活动。出示、宣读、播放只能是文书与勘验的物的证据方法,而并不包括被告、证人、鉴定人的人的证据方法。由此可见,在我国长期司法实践中及相关司法机关的认知中,公诉人的举证方式,是不区分不同的证据种类的不同证据方法,通篇以宣读案卷与展示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举证。在该模式下,公诉人的举证方式,并不区分证据资料与证据方法。
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下的举证模式的弊病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于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的规范是这场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下的举证模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病,正日益成为这场改革的重要桎梏。
(一)辩方的视角——不能有效保证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证权
就被告人角度而言,其具有天然的本能诉求,要求与指控其犯罪者面对面对质;而且,一般而言,证人当面向着被告人说谎较之背后说谎更为困难。辩方能够通过询问证人,戳穿证人在感知、记忆、表达、态度等方面的瑕疵与缺陷,从而有效检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在英美法系中,交叉询问被视为发现真实最伟大的利器。[2]圣经中苏姗娜与长老的故事就充分展现了交叉询问对于发现真实的价值,两位长老偷窥苏姗娜沐浴,心生邪念,求欢却被苏姗娜拒绝,遂怀恨在心,便诬告苏姗娜在树下与人通奸,人们信以为真,欲判苏姗娜死刑。丹尼尔受上帝指派为苏姗娜申冤,遂分别询问两长老,苏姗娜在何树下与人通奸,一则答乳香树,一则答橡树,戳穿了两长老的谎言,还苏姗娜以清白。如若仅以两长老的书面证言质证,不予交叉询问的机会,根本无从有效检查证人证言客观与真实与否,将使被告人蒙冤。
(二)审判者的视角——承袭了侦查程序的心证,难以甄别证言真伪就审判者角度而言,根据直接审判原则的要求,其应当接触证人,听其言,观其行,通过观察被询问者感官及身体反应而确定其陈述之真假。法院应当尽量采用原始的第一手的证据方法,而不应采用从第一手材料中派生出来的证据方法。对于记载证人证言的笔录,相对于原始的陈述,就是第二手的证据材料。二手材料相对于一手材料,多多少少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从发现真实的目的出发,应当尽量采用第一手的直接的证据方法,而应当禁止一手证据材料的代替品。作为第一手证据的证人证言,采用原始的证据方法甄别证言的真伪已然十分困难,更何况采用证据替代品的书面证言,在其本身的风险之上又添加了笔录制作人员即侦查人员感知、记忆、表达、态度的风险——侦查人员有无理解听清证人的意思,其在笔录制作过程中,有无清楚记得这是证人的原话,其笔录本身的表达是否存在问题,侦查人员态度是否真诚,是否存在恶意,对于甄别真伪的困难度更是雪上加霜。[3]正如林钰雄所说,法官难以形成对抗侦讯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础,如果承认此种证据之替代品,将使本来功能不同的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容易变成不当的接力赛关系,而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相悖离。
(三)公诉人的视角——对于诉讼主张的证明不够具体与实质
就举证的公诉人角度而言,检察官到庭宣读笔录,虽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框架下笔录仍然是法定的证据,但相较于检察官在庭审中对证人、鉴定人等进行直接及反对询问时,其证明方式仍然没有那么具体与实质。证人出庭说出的证言相较于呆板的笔录,更容易使法官获得直接生动的印象及心证确信。
(四)诉讼结构的视角——控辩不平衡
实际上,对于辩方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作为控方的公诉人同样存在着难以有效质证的问题。但是作为控方,公诉人就可以凭借公权力,能够在庭外直接询问证人,从而缓和了上述问题,而且由于律师伪证罪的存在,实践中律师主动取证的情形,也少之又少。因而,作为控方的公诉人而言,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动因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与实践中,辩方动不动就申请证人出庭的情形大相径庭,其缘由在于辩方不大可能在庭外接触到控方证人。依照刑诉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于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的许可,以及被取证人员的同意;对于其他证人,要征得被取证人员的同意。而在被取证人员不同意的场合,辩护人便不能向他们取证。因而,便不象司法机关一样可以向被取证人员告知其具有作证的义务,强制取得证言。由上分析可知,由于控方强制取证权的存在,使得能够有效对辩方提供的书面证言有效反驳质证,而辩方却无从实现。因此,控方没有要求辩方证人出庭的情形,并不能说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需要,而仅能说明控方单方的强制取证权存在的不平等。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09.
[2]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0.
[3]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47.
D
A
2095-4379-(2017)13-0166-02 作者简介:邹利伟,丽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助理检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