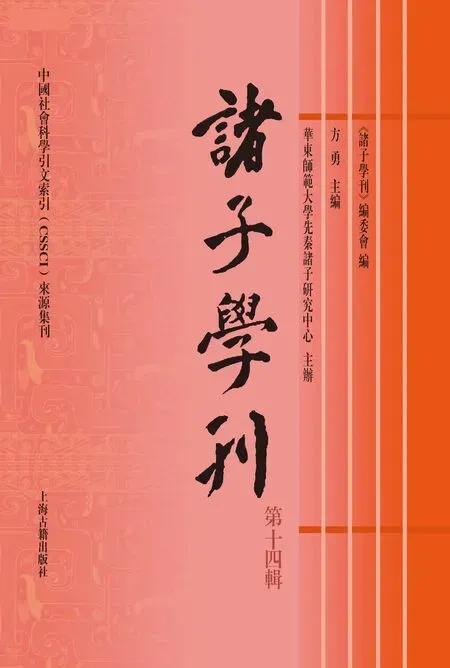歷代莊子闡釋的儒學化傾向
——2015年11月22日在華僑大學的講演
2017-01-27方勇
方 勇
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大家好!今天很榮幸能站在八閩大地的講臺上來做一場關於“莊子學史”的講演。
我之所以説榮幸,這是有原因的。八閩大地英傑輩出,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莊學大家。之前我作莊子學史,發現古代解莊的著述中,福建籍的學者特别多。僅就趙宋一朝來説,如吕惠卿、陳祥道、林自、趙以夫、林希逸等福建學者都留下了重要的解莊著作,其中如林希逸的《莊子口義》甚至可推爲宋代解莊著作之冠。從那時候開始,我對福建就有了一種特殊的印象,相信這裏一定會遇到很多嗜《莊》的同道中人。所以,今天站在這片孕育了衆多莊學大家的土地上,來講述千年來莊學發展的歷史,我的心情是很激動的!
先來簡單説説林希逸《莊子口義》這本書吧。林希逸是南宋末年福建福清縣人,他是理學大家,被歸爲“艾軒學派”,但他思想亦傾向於佛家,曾自云:“癡因好佛蒙嗤誚。”可見其好佛程度遠甚於當時一般的儒士。憑藉着這種豐富的思想,林希逸對《莊子》的闡釋便有了獨特的風貌,概括地説,他是莊學史上首位系統地熔儒道佛於一爐來解莊者,這奠定了他莊學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具體來説,他繼承並發展了前人以儒解莊和以佛解莊兩條路,將兩者融於一書之中,對後世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那麽諸位會問“以儒解莊”和“以佛解莊”到底是什麽含義?爲什麽林希逸將兩者融合便會有這麽大的影響?本次講演,限於時間,將主要就“以儒解莊”這個現象進行闡發。各位會在這個過程中理解到林希逸的重要性。
一
中國是一個重視典籍傳承的國度,每一部經典的傳承,都會經歷各代學者的注解與闡釋,學者們闡釋經典,都以發明其本義爲宗旨,但實際上這些闡釋或多或少地滲透着自己的思想,經典的内涵由此得到“豐富”、“擴展”。尤其是像《莊子》這種哲理性極強的經典,主旨幽邃,文辭縹緲,歷代解釋者對其見解紛繁,又莫衷一是。其實,《莊子》就是一條静而深的河,你看不到底,只能看到自己,説得極端一點,並非我注《莊子》,而是《莊子》注我。而且,《莊子》博大的内涵,讓人們在闡釋時總能找到各種切入點,參考各種成體系的思想來解讀它的文義。這時,人們不僅從這條河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也看到了自己頭頂上的一片天。於是這條寬廣的河面便成了“斑斕多姿”的畫卷,儒學、佛學、老學、易學、陰陽學等等思想紛紛亮相,導致了莊學史中以儒解莊、以佛解莊、以老解莊、以易解莊、以陰陽解莊等等現象。有學者曾經説過:“可以説,一部《莊子學史》,幾乎就是半部中國文化史。”*郝雨《千年莊學一部大史——評方勇〈莊子學史〉》,《文匯讀書周報》2008年12月5日。回顧莊子闡釋的歷史,可知此言不虚,《莊子》這條亘古久遠的大河,幾乎映照了中國思想天空千餘年的風雲變幻,而幸運的是這些河面上“浮光掠影”的東西至今還保存了許多,它們就在《莊子》原文的旁邊静静躺着,等待我們的發現。
中國的思想天空中,儒學一直如日月般高懸(佛道則如雲霞,讓天空不再單調),所以莊學史上“以儒解莊”的方法一直處於主流。當然,儒學本身經歷了巨大的變遷,於是莊學史中亦呈現了“長河映白日”與“明月照大江”相更演的圖景。今天我們回顧這段“以儒解莊”的歷史,所梳理的不僅是莊子學自身發展的過程,更是要思考中國文化演變的脈絡*同上。。
下面我們就來具體談一下“以儒解莊”的問題。
這首先要明確一個前提,莊子的思想到底和儒學有什麽關係?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爲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裏面説得很清楚了,他説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莊子寫了十餘萬言,大都是寄寓之言,他的思想傾向則是批判儒家和墨家,而他的本意則歸到老子的學派裏,這説得再清楚不過了。我想,這應該就是《莊子》斑斕河面下真實的水中世界。
但爲什麽後世就出現了以儒解莊的現象了呢?這與漢武帝後儒學獨尊有很大關係,儒學成爲後世的官方哲學,其思想成爲士人心中的圭臬。在具體傳承的方式上,儒學和經學相結合,樹立了絶對的話語權威,於是它的觀念成爲不刊之教,被人們當做天經地義,同時它自身又不斷發展,演變出理學的形態,將世界本原、萬物規律等高級範疇亦納入其思想體系中。那麽,儒學在士人心中便的確如日月一般,燭照一切,成爲他們認識、評判事物的標準,换句話説,他們的思想被儒學框住了!這種對思想“權威”的推崇和依附,可以命之爲“經學思維”,這是中國人潛意識中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其實用老莊的觀點看,這個世界的一切正如《莊子·齊物論》中所説“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即一切都在變化之中,哪有一成不變的呢?相比之下,儒學的看法就太僵硬了,中國人受它的影響,總覺得上面要有一個絶對權威的意識形態作爲“皇帝”,然後才能進行物質與精神領域的生産活動。這種“經學思維”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大頑疾,所以我之前提出過“新子學”這個概念,就是希望將這種思維破除掉。但思想的改變不是一日之功,“新子學”的作用還是等待時間來證明吧。
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通過上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理解爲什麽莊子的闡釋中會有儒學化傾向,正是因爲中國人潛意識裏有一種“經學思維”,總覺得只有這種解釋才能“心安理得”。當然,在我們今天看來,這種“水中之月”雖然美好,但終歸是虚幻。不過,這些“幻景”對今天的我們來説,仍是頗有啓發意義,所以下面我們有必要依照時間的順序對它們做些梳理。
二
先從戰國時代説起。其實“以儒解莊”的方式在《莊子》本書中便已有了苗頭。衆所周知,《莊子》分爲内篇、外篇、雜篇三個部分,一般認爲内篇是莊子本人所作,外篇、雜篇當多爲莊子後學所作。如果我們再深入分析一下,便可以發現内篇中的一些篇章和外篇、雜篇中的一些篇章在内容上有着對應關係,即後者在前者義理的基礎上進行闡述和發展,明清學者將其稱爲“經傳”關係,比如《齊物論》篇爲經而《秋水》篇爲傳,《人間世》篇爲經而《山木》篇爲傳等等。這裏我們要講到的是内篇中的《應帝王》篇,它是專門談政治的,而外篇中的《在宥》《天地》《天道》《天運》這幾篇内容上和它相對應,清人林雲銘的《莊子因》便認爲《在宥》《天地》是《應帝王》的傳。如果將這裏的“經”、“傳”作對比,我們便可以發現一些問題。
在《應帝王》篇中,莊子認爲帝王應當“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這樣天下方能大治。如果像儵與忽那樣,想有所作爲,去替渾沌開鑿孔竅,就會把渾沌鑿死,就會貽害天下。如其中“肩吾見狂接輿”的寓言故事説明,治國在於純任百姓自爲自化,而不能憑藉法度規矩來統治天下。“無爲名尸”一段文字説明,帝王治世,若能虚己任物,遊於無有,百姓就能自治自化,自己也不會有所勞損。“渾沌死”寓言説明,帝王治世應當虚己無爲,一任自然,否則便會鑿死渾沌——人類的自然本性。總之,莊子的政治主張就是徹底無爲,任憑天下萬物自由發展。而到了《在宥》等四篇中,這裏的政治論便有了微妙的變化。這四篇整體内容還是對《應帝王》中“無爲”的政治思想的闡發,但在具體的細節上則有些發揮。如云: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在宥》)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天道》)
這裏所強調的是君主“無爲”而臣下“有爲”,與《應帝王》篇主張一切無爲的思想已大有區别,顯然是爲了適應現實政治發展需要,較多地吸收了黄老學的治世思想。而黄老思想産生於戰國中後期,它並非純粹的道家思想,而是糅合了各派,尤其是儒家、法家思想更是其主要的構成要素。上述四篇中所藴含的黄老思想體現的儒家傾向更加明顯,如《天道》篇云: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党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這裏明顯體現了儒家的倫理觀念。同樣,上面所引的兩則材料其儒家傾向也是很強烈的,如“臣者,人道也”、“下必有爲而天下用”這很鮮明地體現了儒家入世、致用的心態。
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講,《莊子》本書中的這類現象不能稱爲“以儒解莊”: 在思想上,它不是純粹的儒學而是駁雜的黄老;在方法上,它不是文旨的解析而是義理的發展。但上文已經説過,這四篇的思想是向儒學傾斜的,而至於其方法,明清歸納出内、外篇之間所具有的經傳關係亦近乎後世解莊的先聲。更關鍵的是,後學“改造”莊子思想以適應現實需要的做法,與後世“以儒解莊”實在有本質上的相通之處。綜上,將此定爲“以儒解莊”現象的萌芽,於理可通。
這種對莊子的接受方式在兩漢時期得到了繼承。兩漢初期黄老之學盛行,《淮南子》便是這種思潮下的産物,正如上文所説,黄老有儒家因素,《淮南子》所反映的黄老思想亦有此特點,而且很多地方是在對《莊子》接受中體現出來的。首先來看它對“無爲”的定義,《修務訓》云:
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
本段中,“循理而舉事”這個説法有很重要的意義,這規定了《淮南子》的“無爲”其目的是“舉事”,其手段是“循理”,這對“無爲”概念是一種發展與創新,我們可以看到其中儒家思想的要素。以這種思想爲根基,《淮南子》對《莊子》的接受自然有了儒學化傾向,《修務訓》中有一段話以馬喻“不以人易天”的思想,可以作爲鮮明的例證。其云:
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蹄足以破顱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
我們知道,《莊子·秋水》通過“牛馬”設喻而引出了“無以人滅天”的命題,而《馬蹄》又對這一命題展開了全面而深入的闡述,認爲凡“加之以衡軛,齊之以月題”等等,都是對“馬之真性”的戕害,都是“伯樂之罪”。《淮南子》接過《莊子》這一命題後,卻對它進行了一定的改造,從而提出了一個“不以人易天”的新命題。這個新命題認爲,馬與魚、人都不一樣,它的本性是“跳躍揚蹄,翹尾而走”,而人們順着它的這一本性“掩以衡軛,連以轡銜”,使之能够“歷險超塹”而“可駕御”,這就是“不以人易天”的“教之所爲”。由此可見,《淮南子》闡釋的目的就是要把因任自然與發揮人的能動作用統一起來,以便爲漢初最高統治者提供一套適應當時社會實際情況的治國理論。從這個層面來講,它與莊子後學對莊子思想的改造現象是一脈相承的,雖然這種對《莊子》的接受與“以儒解莊”尚不能完全等同起來。
上述儒學化傾向主要表現在打通莊子與儒學在政治理念上的隔閡,而在漢代對《莊子》接受還有另一種方式,便是將其與儒家道德理念相融合,這可以以韓嬰的《韓詩外傳》爲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
這裏“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都是化用《莊子》而來,含有莊子的思想在裏面,但韓嬰卻巧妙地將其與儒家學説整合,引出了孔子積極救世的人生理想。在《韓詩外傳》中有大量故事都是化用自《莊子》的寓言故事,但其中承載的卻是儒家的思想,如用“輪扁論書”説明“天道難知”的道理,用“原憲居魯”説明“君子固窮”的道理,用“廟中犧牛”與“樊中澤雉”説明“就有道而正”的道理,這些道理都是儒家的修身、出處之道,體現了儒家對個人道德的規定,於是這些《莊子》寓言的原旨便被暗中替换了,它們成了儒家思想的寓體。這種接受方式與後世“以儒解莊”聯繫更爲緊密,它將《莊子》與儒家巧妙地融合起來,其意義亦值得重視。
不過從總體上來看,漢代對《莊子》和儒家的界綫還是分得很清的,這可以漢代前後兩大史家司馬遷和班固對《莊子》的接受爲例。司馬遷強調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這在上文已經講過了,不必贅談。至於班固,從古人的引述中我們可以知道班固曾注解過《莊子》,説明他對《莊子》同樣有深入的研究。但對莊子思想班固每予排斥,《漢書》中的《古今人表》將莊子排在第六等,在《幽通賦》中也説“周賈蕩而貢憤”,而且他還專門寫過一篇《難莊論》來批駁莊子思想。而衆所周知,班固是一個受儒家思想影響極深的學者,他對莊子的批判顯然是基於其内心的儒家思想,由此可知班固並没有融合莊子與儒家的嘗試。當然像班固這樣將莊子與儒家尖鋭對立起來的做法在漢代亦屬特别,大多數士人對於《莊子》與儒家還是分開對待的,儒家思想指導士人立身處世,《莊子》思想作爲潛在的思潮調節着士人的心理,兩者並行不悖,只是偶有交集。所以,戰國秦漢這段時期,應該屬於“以儒解莊”的萌芽期,出現了種種迹象,但一切尚在孕育中。
三
到了魏晉時期,《莊子》思想在士人心靈中逐漸由潛流轉變爲主流,作爲“三玄”之一的《莊子》成爲魏晉玄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玄學發展的前半階段,《莊子》往往是作爲儒學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尤其是嵇康、阮籍等人的“竹林玄學”將《莊子》作爲對抗名教的武器,將莊子的批判精神發揮到了極致。
但又要注意到,此時也有一些玄學家希望將儒道融合起來,向秀的《莊子注》就是典型。《晉書·應貞傳》提到“昔者向子期以儒道爲壹”,這種“儒道爲壹”的觀點在其代表作《難養生論》中有很鮮明的體現。在這場與當時激進派代表嵇康的論戰中,向秀既講情欲自然,又表達出對名教的認同,已然以名教來補充自然,調和自然與名教關係。向秀認爲當個人與社會産生激烈矛盾的時候,個人應當做出妥協退讓。他的《莊子注》主張自然與名教合一,就是爲了調合儒道、解決二者在理論和實踐中相互對立的問題。據《晉書·向秀傳》載,向秀在進京面對司馬昭“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之問時,他的回答是:“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莊子·逍遥遊》有“堯讓天下於許由”的寓言,莊子顯然是抑堯而揚許的。讀《莊子》的人都能意識到這一點。但此處向秀則揚堯而抑許,已然表達出自己的“入世”精神,這種觀念與莊子的無爲精神是大不相同的。向秀注釋《莊子》時直接提出了重申儒家名教價值,欲以調和道家重生命與儒家重治世的思想,這正是站在調和儒道立場上對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關係作出的妥善處理。後來郭象則對向秀的玄儒兼治思想進行發揮,在《逍遥遊》篇注中提出“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遥一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等言論,將“以儒解莊”的方法真正地發展成形。
在竹林七賢後,是玄學發展的後期階段,這時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元康玄學家大都出於西晉王朝統一之際,對司馬氏政權不再有嵇阮等人的抗拒心理,並且爲了適應大一統國家的需要,名教必須被樹立爲統治思想的主體,故而這個時期的玄學家對當政者與名教都表現出了主動迎合的態度。但作爲之前名教的對立面——《莊子》,此時已成爲名士的精神食糧,難以割捨。所以如何將新歡和舊愛融合起來,這成了時代的課題。最終,郭象的《莊子注》成功調節了兩者,這本書也成爲了莊學史上的經典,它同樣也可以看做“以儒解莊”的重要著作。
郭象注莊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名教即自然”,這規定了他闡釋莊子的具體方式。名教與自然之辨是魏晉玄學的一個核心命題,它經歷了正始時期何晏、王弼“名教出於自然”,和“竹林時期”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元康時期郭象、裴頠“名教即自然”三個發展階段。何、王試圖以“自然”改造“名教”,嵇、阮則以“自然”對抗虚僞的“名教”,而到了郭、裴這裏則希望取消“名教”與“自然”的對立或隸屬關係,追求將“自然”的精神融入“名教”的體系中去。這三個階段表面上看經歷了一個從統一到對立再到統一的循環過程,其實這應該被理解爲一種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它反映的是儒、道兩家精神漸進地交融。
實現“名教”與“自然”的融合,意味着郭象必然要對《莊子》篇旨作更大的發揮甚至改造。郭象的這種“改造”以“自然”這個道家核心概念爲突破口。《莊子》所講的“自然”強調的是順從天道、無爲無作,他的著眼點在天(即造物者),完全摒棄人爲因素,萬物有其天性,不要人爲去改變它,儒家仁義禮樂就是逆人天性的,故應抛棄。而郭象在注《莊子》中則重新闡發了“自然”之義,這首先以其“獨化論”爲基礎,他認爲在“有無”問題上,是萬物自己産生自己,而不依賴造物者,即《齊物論》注中所説:“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物各自造”是郭象所認識的“自然”,他承認萬物具有自然而然的本性,卻不認爲是受之於所謂造物者的。這樣郭象巧妙地將《莊子》“自然”受之於天的觀念改造成了“自然”受之於己,從而輕鬆取消了名教與自然的對立。如下面兩例: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在宥》注)
夫仁義自是人之情,但當任之耳。(《駢拇》注)
這裏等級、仁義被郭象詮釋爲由人自性而派生的,屬於“自然”,故有存在的合理性,這樣名教的各種理念就在《莊子》中被“挖掘”了出來,《莊子》與儒學實現了融合。很明顯,莊子提出“自然”的主張是針對儒家宣揚的仁義禮樂制度而發,但到了郭象這裏卻變成了這套制度的理論基石,其改造幅度實在驚人。
基於上述思路,郭象對莊子具體字句的闡述顯示出了很強的儒學化傾向。比如“無爲”一詞在《莊子》中是核心概念之一,莊子的“無爲”強調要順應天道自然,即“無爲爲之謂之天”(《天地》),但郭象在《逍遥遊》注中則對其内涵做了相應調整,認爲“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可以説,從莊子的“順應”到郭象的“自爲”是質的轉變,郭象稱“無爲”實際上是有爲,是萬物各司其職的自爲。有了對“無爲”基本認識的轉變,郭象從《莊子》中道家色彩鮮明的寓言裏闡釋出了儒家的意藴。如《逍遥遊》篇中,《莊子》原文是通過堯讓許由而不受的故事,説明了儒家的理想人物唐堯“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只不過是凡夫俗子,而許由無心追求名位,才是真正的聖人。郭象此段注對兩者評價則倒了過來,他説: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泛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
所謂“對物”,是説與外物相對立;“與物無對”,就是不與外物相對立。郭象指出,許由自以爲是,把自己與現實社會對立起來,而唐堯卻順從他物,“與物無對”,同時又“無心玄應,唯感之從”,境界高得連自己都覺察不到,所以唐堯是可以爲君的聖人,許由只不過是俗中之一物罷了。郭象説:“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逍遥遊》注)在郭象看來,莊子把“拱默山林”看成“無爲”,把什麽事也不幹的隱者許由稱作聖人,這是要不得的。於是,他在詮釋《逍遥遊》篇“藐姑射山神人”一則寓言時進一步指出:
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黄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逍遥遊》注)
這就是説,聖人雖然處於廟堂,忙於政務,但他在精神上卻淡然自若,逍遥自得,猶如處於山林之中,可是世人不懂得這一道理,一見到聖人戴黄屋,佩玉印,跋涉山川,與民同事,便以爲足以擾亂他的心情,使他遭到極大的精神困頓,他們哪裏知道這原來都是聖人天賦才能的自然表現,不能使他的自然本性有絲毫虧損的呢!郭象以“本性”爲支點,將《莊子》原書中貶低的帝王(如堯舜)在境界上大大提升,將原書的“無爲”發展爲一種特殊的“有爲”,契合了儒家的思想和名教的要求,這是思想史上對儒、道關係調和的重要一環。他給士人提供了一種典範,即“遊外宏内之道”,強調精神上遊塵垢之外(即“遊外”),而實際上則參與事務(即“宏内”),兩者在聖人那裏得到了統一,故士人也應追求這種狀態。可以看到,郭象“名教即自然”的思路最終在現實政治的層面結出了理論的果實,應該説這種成果爲《莊子》的流傳注入了新的生機,甚至當時士人的心靈也莫不受此潤澤。
除了調節《莊子》與名教的矛盾外,郭象還注重“改造”《莊子》中不適應現實社會發展的觀點,使之契合於儒家實用性的理念,如其《馬蹄》注與《秋水》注,郭象認爲“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所以“寄之人事”的“落馬首”、“穿牛鼻”是牛馬本性的要求,這相比《馬蹄》篇中“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的説法,兩者相隔河漢,但仍是因爲中間有“自然”和“本性”這類概念作過渡,讓我們看起來没有感覺注文太牽強。上文提到了《淮南子》對《莊子》這個觀點也有過改造,亦是由“本性”的角度切入,《莊子注》與其思路如出一轍,只是所述没有郭象那麽系統深入,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感覺到“以儒解莊”在歷史上的演進軌迹。
郭象“以儒解莊”爲後世莊學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莊、儒相通逐漸成爲士人心中的一個普遍意識,可以説《莊子注》之所以成爲經典,很大程度上緣於郭象“以儒解莊”的方法。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郭象以儒解莊所做的仍只是將《莊子》局部語段或核心概念闡釋出儒學的意味,這一方面是指他的注文並未能與原文做到融通,很多情況下都是莊子説莊子的,郭象説郭象的,另一方面是指郭象《莊子注序》中對莊子的認識仍是“百家之冠”,並未完全將其列於儒門。這兩方面爲後世學者“以儒解莊”留下了巨大的開拓空間。所以,魏晉時期,在向秀、郭象等玄學家的推動下,以儒解莊的方式漸具雛形,這一階段是其初創期。
在魏晉時期,儒、道兩派在中國人思想的天空中如同日月與雲霞,相争而又相映,《莊子》這條河的水面亦呈現出了斑斕的畫卷。同時,一團龐大的祥雲正從外面徐徐而來,到了南北朝時席捲了這片天空,它就是佛教。佛教在六朝士人思想中佔據着重要位置,有力地衝擊了儒道的地位,這種思潮的變化給莊學研究帶來了不小的革新,以佛解莊開始興起,僧人支遁對“逍遥”義的全新闡釋顯示了這種方法的潛力。之後以佛解莊成爲了僅次於以儒解莊的莊學“流派”。
四
隋唐時期思想界的特點是三教並行,相互交融。而此時,因爲李氏家族推尊老子,《莊子》的地位也得到進一步提高,有段時期甚至和科舉相關聯。這種背景必然促使更多的學者以更多的方式參與到莊學研究中去。在這個過程中,儒學化傾向逐漸升温,並最終在一些方面實現了對郭象以儒解莊的突破。
總體來看,唐代莊學著作以儒解莊的情況很普遍,只是儒學化的程度有高有低而已。
成玄英的《莊子注疏》是隋唐莊學著作中最經典的作品之一,本書“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可見其思想以郭象爲基礎,另如序言中云:“(莊子)暢無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此處繼承郭象“獨化”概念,亦可見其對子玄的信服。上文已論,郭象《莊子注》開導“以儒解莊”之先路,成玄英在這方面亦是繼其踵武,他對郭象“足性逍遥”、“寄之人事,當乎天命”、“遊外宏内”等説法進行引申與發揮。具體可以用“堯讓天下”這個寓言的闡釋爲例,上文已列原文與郭注的對立,而成玄英此處則力求在堅持郭注的基礎上來調和兩者:
睹莊文,則貶堯而推許,尋郭注,乃劣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勳(唐堯)大聖,仲武(許由)大賢,賢聖二途,相去遠矣。故堯負扆汾陽而喪天下,許由不夷其俗而獨立高山,圓照偏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故有爝火之談,郭生察無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説,可謂探微索隱,了文合義,宜尋其旨況,無所稍嫌也。
這裏成玄英的疏承認了郭象注與莊文相牴牾之處,但他做了相應的解釋,啓發讀者不要拘泥於莊文的表面文義,而是要像郭象一樣“探微索隱”。依據這種“尋其旨況”的思路,讀者對本段原文與注釋之間的差異自然是“無所稍嫌”了。在“以儒解莊”這條路上,成玄英主要還是按郭象的思想進行闡發,但他在闡發的過程中又注意彌補郭注與莊子原意間的裂縫,這是他的一大貢獻。除了這個例子外,前面提及郭注儒學化傾向的幾個重要觀點如“獨化論”、“遊外宏内”在成疏中都得到了闡發,雖對原論有取有捨,要之不離郭注本旨,仍是傾向於儒學,同時追求與原文相融通,與上面所述情況近似,這裏不一一列舉。不過我們也要意識到,成玄英作爲一個道士,其思想與郭象是不會完全相同的,所以在一些具體的闡釋上,成玄英的儒學化傾向没有郭象那麽強。成疏在莊學史上發揮了一種平衡作用,它帶來的佛道思想與重視原文的精神糾正了郭注對儒學的過度偏向。歸其原因,這應該是唐朝三教並行的思想背景與成玄英自己獨特的身份所致。
唐代對《莊子》注解的書籍很多,但可能因爲普遍水準不高,故很少有留存下來的。根據現存材料,除了成疏外,我們瞭解較多的還有文如海的《莊子正義》和張九垓的《莊子指要》。兩本書的作者和成玄英一樣都是道士,但他們皆不滿郭注,而追求創立新説。但即使是這樣,他們在儒學化傾向方面與郭注仍有相通之處。如吴澄在《莊子正義》的序中寫道:“(文如海)能獨矯正郭氏玄虚之失而欲明莊子經世之用。”將《莊子》用於經世在上文已經有所論述,這是莊學史上一個非常悠久的“傳統”,體現了向儒學精神的一種傾斜。此外,再如權德輿爲《莊子指要》寫的序中云:
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爲家爲邦、爲仁爲智,泳之游之,日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躁者静,循之而愈照,冥之而愈妙。攖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張九垓)之意,明此而已矣。
這裏雖然是權德輿的文字,但也反映了張九垓的莊學思想,文中提到道能够“爲家爲邦,爲仁爲智”,家邦、仁智皆是儒學關懷的問題,序中將道和它們聯繫起來,亦體現了一種儒學化傾向。
以上介紹的是隋唐時期闡發《莊子》義理的著作,它們的儒學化現象較爲普遍。然而這個階段其他不以義理闡釋爲主的相關著作,在《莊子》的接受上亦有向儒學靠近的迹象。
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中有《莊子音義》三卷,其主要意義在於輯録漢魏古注、六朝音義及自己對《莊子》字音字義的注解,其中不易看出陸德明本人完整的莊學思想。但是陸德明將《老》《莊》兩書與《周易》《詩經》等儒家經典並列在一起放置於《經典釋文》中,一方面是因爲他本來就推重《莊子》,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爲在他意識中《莊子》在思想上與儒家經書本是相通的。這樣後一種對莊子的認識便有了儒學化傾向。
此外還有魏徵等《群書治要》中的《莊子治要》、馬總《意林》中的《莊子鈔》,它們不是對莊子的注解,只是對《莊子》相關語句的選録,但這種取捨的過程亦能反應編者對莊子思想的理解。如《莊子治要》中有針對莊子“無爲”的政治思想進行的選録,其所選都集中於外篇與雜篇,内篇則完全被拋棄了。結合上文所述可知,《莊子》内篇中亦有不少語句闡釋“無爲”的政治思想(如《應帝王》篇),只是相比起來,外篇中的“無爲”政治思想更有關懷現實的特點,成爲“君人南面之術”,之前已列舉了有這種特點的語段。而再回顧《莊子治要》,則可以發現上述語段基本都收到了該書中,尤其是融會了儒家精神的《天道》篇,更是被選録了近一半的文字,於是《莊子治要》中呈現出的《莊子》思想便有了與儒學能相通、能互補的一種特點,這種有選擇的接受方式對促進《莊子》融入儒學政教體系有着一定的作用。唐代《莊子》地位得到提高,被統治者接受,與這種接受方式亦有一定關係。
總體來看,上述隋唐時期《莊子》接受過程中的儒學化傾向,其大略不出漢魏六朝“以儒解莊”的基本框架,只是有了一些發揮或調整。在以儒解莊的模式中,《莊子》是恒量,儒學是變數,一種模式的演化必須要依賴變數的發展,儒學在中唐時的新變令“以儒解莊”現象有了新突破。
中唐時期,國家經歷了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内外交困,士人中有了改革的呼聲,復興儒學成了客觀現實的需要。韓愈是當時崇儒教、排佛道的主力,在儒學史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成爲儒學轉型的一個關鍵人物。他追求建立儒學道統,這在儒學發展史上很有創新意義;同時他對儒學也有超乎俗儒的自信,而其膽才識力亦超過一般的士人,這幾個方面是他成爲一代大儒的基礎,同樣也讓他對莊子做出了全新的儒學化闡釋。韓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説: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韓愈從《莊子》中看到了“儒學因素”,並且相比前人更進一步,發揮了他的“道統”説,將莊子看作孔門支脈的傳人。韓愈用他畢生力量來伸張儒學,希望儒學能佔據世人思想的絶對主體,同時他把儒家思想看作“道”的代表,相信儒學思想在層級上高於其他思想,這種自信也促使他將莊子吸納到聖門之下。韓愈此處的看法,於理自然牽強,但這極大地啓發了後世莊學研究以儒解莊的新方向。韓愈所革新的儒學,其“文化自信心”更強,不僅要壓蓋佛老,還力圖拓展到天道人心各層領域,使其影響力無所不在,這是後世理學發展方向,由此一來,主談道德性命較多的《莊子》便被更全面地包融到了儒學之中。從這個層面來看,韓愈關於莊子身份的新説在以儒解莊的歷程中意義是比較重要的,他不僅爲後人提供了一種“納莊於儒”的思路,更是留下了一種“儒學自信”的精神。
其實,這種影響在韓愈的後學中便有了體現,如其弟子李翱,繼承韓愈復興儒學的事業,在完善儒家心性思想方面作出了較大貢獻。而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復性書》,其實它吸收了很多《莊子》的心性理論。文中他用水性比喻人性:
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勿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之性也。
這種思想應本之於《莊子·天道》:“水静猶明,而況精神乎?聖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宋前言心性的思想派别,成就較高者爲佛、道兩家(道家中猶以《莊子》爲重),兩者都可能對李翱的心性論産生影響。但李翱在《去佛齋論》中表示過:“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所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可知李翱有揚道抑佛的傾向,他發展儒家心性論必然更重視道家的《莊子》的啓迪。這種援《莊》入儒的手段,反映了儒學内在的創新與生命力的焕發,經過完善的儒學内涵更豐富,與莊子有着更多的相通之處,保證了之後宋儒將“以儒解莊”上升到更高的一個境界。
綜上可知,莊學史上以儒解莊的現象在南北朝經歷了短暫低谷之後,在隋唐迅速回升,在中唐儒學新變之後,它又開始有了新的態勢,這預示着其更加成熟的形態將在之後的宋代來臨。
五
宋初的幾十年間,朝廷實行無爲的黄老之政,儒學没有太大發展,主流依舊是漢唐的注疏之學,這就決定了該階段對《莊子》的闡釋没有太明顯的儒學化傾向。但到了北宋中期,伴隨着政治改革而出現的儒學復興潮流,讓以儒解莊的傳統重新回歸。因爲,爲了創造有别於傳統儒學的新儒學(理學),宋儒必須要增加儒學的思辨性,進而在天道心性層面對抗佛老。當然這種表面的對抗意味着深層的融合,儒、釋、道在理論層次和思維方法上由宋儒實現了貫通。這在學術史上的表現之一就是《莊子》闡釋的高度儒學化傾向。
宋代學術派别繁多,這裏僅針對和莊子學聯繫密切的幾個學派進行論述,分别是王安石的新學、蘇軾的蜀學以及宋代理學的主流程朱之學,另外還有由林希逸等人所構成的艾軒學派。
宋代的新學與當時的政治改革聯繫密切,以熙寧改革的首領王安石爲代表,包括王雱、吕惠卿、林自、陳詳道等學者。王安石的學説特重道德性命,對孟子十分推重。但他的思想體系的根本處又深受道家影響,以“空無”爲本,由此而産生了仁義禮樂這些“有”的範疇。後世理學家如朱熹批評説“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就是針對這個方面而發。可見道家在王安石思想中有重要地位,這成了他建構其道德性命之學的根基之一。所以在具體的學術活動上,王安石及其門人都特别看重老莊,王安石有《老子》和《莊子》的注解,但他《莊子解》已亡佚。不過從現存的材料中我們仍然能够發現他在莊學方面獨到的造詣,以儒解莊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上文已提到王安石用道家思想幫助建構其道德性命的學説,他將莊子思想納入儒學體系就是其中的一種手段。所以,王安石的“以儒解莊”主要圍繞道德性命學説的建構展開,這從下面的材料可以得到體現。王安石《答陳柅書》中提到:
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説,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説,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説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説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説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説,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
本文首先提到“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他將性命之説作爲《莊子》的思想核心,以此將其與儒學貫通。這裏他繼承了韓愈“莊子爲孔門傳人”的説法,並且對此進一步申發,認爲莊子是“學聖人而失其源者”、“有志於道者”,這顯然是對韓説的完善,歸納起來就是其本與聖人同、其末與聖人異,這便使莊子思想在儒學體系中得到了合理的安放。至於莊子與儒學具體的同異以及對待莊子的應有態度,王安石在《莊周(上)》一文中給出了詳細的説明:
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趍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説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説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説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遍、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説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説,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這裏王安石歸納《莊子》的價值是矯當時人心敗落之弊,這在一定程度上來講也是“存聖人之道”,但短處在於他亦是“一曲之士”,甚至矯枉過正而爲“邪説比”。從這個方面看,莊子與儒學有同有異,本同而末異,所以王安石在給出了他對待莊周的態度是“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説”。莊子的爲書之心,以他的説法就是矯世弊存聖道,所謂“世弊”,從文章開頭來看,就是人心不古、溺物逐利,而所謂“聖道”,從《答陳柅書》開頭來看就是“性命之分”,這兩方面與王安石志於道德性命之説以規範世道人心的思路是相契合的,從這個角度我們能對王安石儒學化闡釋《莊子》有深刻的理解。相比韓愈率爾之説,王安石以“性命”爲切入點的闡釋更加準確、合理,並與自己的學説相契合,使以儒解莊有了理論的落腳點。
王安石在以儒解莊的方式上同樣給了後人很大啓示,他在《莊周(下)》中説: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説,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説而謹行之,説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淳而後喻,譊譊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這裏王安石抬出了《孟子·萬章》“以意逆志”的闡釋方法,強調讀莊應不爲表面文辭所拘束,而是要探究其本初之意。比如文中已提到“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這些話都反映出了王安石讀莊時的獨特意識,即認爲文辭所述未必是周之本義,周之本義是被有意地隱藏在文辭之下的。王安石的這種意識在之後被廣泛繼承,爲後世學者在《莊子》寓言中挖掘代表儒學的“新義”提供了方法論的啓示。其實,這種意識在郭象《莊子注》中已有肇端,學者稱其爲“寄言出意”,而王安石對此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給出了更“合理”的解釋,與同時代蘇軾“陽擠而陰助之”的説法交相輝映,成了莊學史上解莊的一種重要意識。
當然,王安石作爲一個政治家,也不可避免地將《莊子》與政治改革相結合,這種結合的切入點也大多是“道德性命”的問題。比如他的《九變而賞罰可言》即發揮《莊子·天道》中“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的觀點,並用《尚書》的原文來依次證之,從而建構了一個從明天到明道德最終到明是非而明賞罰的政治思想框架,這是典型的儒、道相融的政治理念,它將莊子後學已有儒學化傾向的思想加以改造,變成了切合當時政治改革的儒學思想。但我們也要注意到,王安石作爲一個改革家對《莊子》中“無爲”的思想是堅決排斥的,在很多詩文中都體現了他這一態度,對於這些内容王安石應該没有刻意去進行儒學化闡釋。王安石解莊,對待其中各類思想標準明確、涇渭不混,雖傾向儒學,但取捨有分寸,這是其一大特色,根本來説此類情況源於他對莊子的基本認識及他本人的學術個性。
新學中的其他學者對莊子同樣十分重視,他們在整體思路上遵循了王安石“以儒解莊”的路子,在具體操作上有王安石的影子,也有自己的特色。下面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王雱是王安石的兒子、門人,他有《南華真經新傳》傳世,其中體現了鮮明的儒學化傾向。王雱的莊學與荊公莊學有許多一脈相承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從儒家視角發揮莊子思想中的“性命”之學。北宋無名氏在爲《南華真經新傳》所作的序文中已指出了這一點,認爲“莊子之書實載斯道(性命道德)”而“王氏(雱)又嘗發明奥義”。在王雱具體的注解中,如《繕性》新傳認爲“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這同樣體現了儒道精神在性命問題上的融通。相比而言,王雱繼承其父在《莊子》性命之論上的興趣,但放棄了其父對莊子之説的基本否定態度,追求將《莊子》中性命之學的要素進行全面的闡發,這是《莊子》進一步融入儒學思想體系的關鍵環節。
林自,雖不是王安石的門人,但在思想和政治上是王安石的擁護者。他的《莊子注》也有很多王安石莊子學的影子。該書同樣在性命之學中下工夫,但與王氏父子之説相比,又有了創新之處。上文提到,王安石在本體層面上的思考依舊是以無爲本,仁義等儒家概念置於次,王雱也繼承這一理念,所以《南華真經新傳》中性命之説並未與“仁義”全面結合。但林自思想更近於理學家,特别強調儒家倫理道德,所以他在《莊子注》中對“性命”的闡釋就更富有道德色彩。《莊子注》中“躬服仁義所以盡性”、“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仁義,真人之性也”,這些將仁義與性相結合的論斷在該書中比比皆是,遠多於王雱的論述。王安石與林自相比,前者以儒解莊是站在天道的角度,所持儒學是儒、道相合後的儒學,而林自以儒解莊則站在人倫的角度,所持儒學是較爲純正的儒學。故林自解莊儒學化傾向更強,可以視爲對王氏父子的進一步發展。
吕惠卿是王派新學的中堅人物。他的《莊子義》與王安石的莊學思想聯繫密切,這主要表現在吕著是在解莊方法上繼承了王安石“以意逆志”的主張,將王安石以儒解莊的理念進一步發展。比如《莊子》中常有非議孔子的言論,吕惠卿在這些地方往往會進行辯解和轉化,在不甚偏離原義的前提下使之符合儒家思想,從而重新塑造出了一個“亦儒亦道”、又“非儒非道”的孔子形象。另外,在闡釋《莊子》時,吕惠卿還經常援引儒家經典如《論語》來申説己意,這與王安石《九變而賞罰可言》中以《尚書》作《莊子》注釋的做法是相通的,它們都使《莊子》與儒家思想更緊密地結合。這幾種手段在王門學者注莊活動中都是經常用到的,在後世也是一種普遍使用的方法,由此可見王安石在莊學中的重要影響。
陳詳道亦是王安石的門人,其《莊子注》與前列作品有着很多共同的特點。但在將《莊子》與其他儒家經典相貫通的方面,陳著則更進一步。這主要體現在他不僅用各種儒家經典(包括《周易》《尚書》《論語》《孟子》等)來證莊子,而且還“獨具匠心”地用《莊子》中的話來解釋《論語》,這就進一步實現了儒、道的相互通融,使得莊子在儒學化的進程中又出現了一個突破。
與新學並起的蜀學,在莊子儒學化的進程中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這主要反映在蜀學領袖蘇軾的莊學成就上。
蘇軾没有專門注解《莊子》的書,但他作有《莊子祠堂記》一文,該文在莊學史上同樣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在該文中,蘇軾著手解決的同樣主要是《莊子》詆儒的問題,文中提到: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同樣是爲莊子辯白,王安石認爲莊子是在“矯弊”,而蘇軾則認爲莊子是在“助孔”,兩人在“以儒解莊”的層面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無可争議。但此處我們有必要對兩人的細微差異作些分析。《莊子》中有詆毁儒者的語句,王安石的“矯弊説”指出這些都是假象,而蘇軾的“助孔説”則進一步説明了這些假象的用意。爲此蘇軾舉出了楚公子出亡的例子,結合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揣測蘇軾對莊子詆儒現象的理解。在他的想法中,大致莊子是故事中的僕人,儒學是楚公子,而故事中的門人則喻指當時反對儒學的人,莊子表面上詆儒是爲了便於讓這些人接受其説,而其説中則有儒家精神,足以潛移默化地“感化”這些人,實現儒學的傳播,這種“助孔”方式和僕人助主出亡的方法是異曲同工的。蘇軾將這種方式稱爲“陽擠而陰助之”,並且之後又專門強調莊子尊孔的意識,一則“(莊子)詆訾孔子”時又“微見其意”,二則《天下》篇中孔子與諸子不相混。第二條亦見於王安石的《莊周》,是當時學者證明莊子尊孔的常用證據。至於第一條“詆孔”問題,則是蘇軾爲莊子“辯護”的一大焦點,《莊子》在這方面不太激烈的言辭,蘇軾都嘗試化解,強調莊子在其中都“微見其意”以自清,至於表現特别明顯的地方,蘇軾則將其歸於僞作。
相比王安石“(莊子)矯世弊而過正”的説法,蘇軾“陽擠而陰助之”的説法爲以儒解莊開拓了更大的闡釋空間。如果在王説中,莊子與儒學的聯繫在於其所習是聖之道,那麽在蘇説中,莊子所爲則幾於聖之徒矣,無疑蘇説將莊子與儒學聯繫得更緊密。
蘇王差異究其原因,首先在於新學和蜀學學術特色的不同,如錢穆先生在《宋明理學概述》中所説蜀學“長於和會融通”,它富有文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尤其是其領袖蘇軾,憑藉其過人才識,常能看到萬事萬物間的深層聯繫,提出許多獨到的説法,此處“陽擠而陰助”之説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也要看到王蘇兩人對莊子的態度有些差異,王安石是以莊用事,蘇軾是以莊寄心。王安石對莊子的接受在上文已説過,主要側重在心性問題與政治問題上與《莊子》的結合。而蘇軾與《莊子》的關係,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提到:
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這裏説明了早年蘇軾對莊子的傾心,而之後人生的坎坷歷程則使《莊子》更成了他精神的支柱。蘇軾是士人在生命中融通儒、釋、道三教的典範,其處世哲學受莊子影響極深,這些都促使他對《莊子》作更深層次上的儒學化“改造”。
蘇軾調和莊、儒矛盾的努力還體現在對《莊子》一書文獻的辨僞方面。在《莊子祠堂記》的後半部分中,他認爲詆毁孔子最嚴重的《盜跖》《漁父》兩篇皆是後人羼入的,並非莊子之筆。他還列出了文獻上的證據: 《盜跖》《漁父》《讓王》《説劍》這四篇在書中次第相連,而這四篇前的《寓言》篇其尾與四篇之後的《列禦寇》篇之首,在内容上正好銜接。於是他懷疑《寓言》《列禦寇》本來相連,是後來才羼入了這四篇“僞作”。這種獨特見解在莊學史上影響很大,唤起了之後學者對《莊子》作者問題的思考,同時使《莊子》的儒學化闡釋顯得更爲合理可信,從而使以儒解莊的方式更易被人接受。
可見,蘇軾在莊學史中的地位與王安石一樣十分重要,《莊周》與《莊子祠堂記》兩篇文章在莊學史上交相輝映。由於兩人都屬於當時文化的領軍人物,他們對莊子的重視態度以及闡釋方法自然被之後士林廣泛接受,這對以儒解莊的潮流起到了極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上文提到的新學中學者的解莊思路頗能反映出王、蘇“以儒解莊”帶來的影響。除此之外,這種影響同樣也波及整個宋代的莊學研究,僅列舉以下幾部莊學著作便可見一斑。
兩宋之交的程俱著有《莊子論》,其中認爲“雜篇而終之以《天下》,則知孔子之書終言堯、舜之事,……孟子之書終言禹湯文武者,皆是莊子之微旨也”,這裏將《莊子》篇末與《論語》《孟子》篇末相提並論,自然是想證明莊子尊孔的心態,這可以看作是對王、蘇《天下》篇闡釋的發展。其他如將孔孟思想與《莊子》中的概念相比附,亦是與王雱、吕惠卿等人的做法如出一轍。並且,程俱將莊子與儒學結合得更爲全面,在《莊子論五》中,他論證莊子未嘗滅禮樂亦未嘗絶聖棄智,這對以儒解莊的進程又是一次推動。
南宋時期的趙以夫著有《莊子内篇注》,他在莊孔互參、莊孟相照方面同樣有很多嘗試,是對之前學者以《莊子》反推儒書作法的進一步發展,所以劉克莊謂“如虚齋,乃可謂之善學,因漆園之書以推它書,其高妙精詣,切於世用,抑又可知也”(《趙虚齋注莊子内篇序》),可見趙以夫在這方面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並且能“切於世用”,將《莊子》轉化爲儒學的過程中又注意到了其現實的政治意義。這些都是當時“以儒解莊”風行的表現。
以儒解莊的傾向不唯出現在當時儒士的著作中,一些以道家精神闡釋莊子的著作同樣有融合儒學的迹象。如北宋道士陳景元在《莊子注》中便有“藏仁義於己,則道德何由失;約禮樂於身,則邪僞莫能干”這種表述;南宋道士褚伯秀亦有“觀是篇(《天道》)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這種評價。這些都没有將《莊子》與儒家禮樂仁義作完全的對立,而是體現了調和兩方的努力,其中亦包含了“以儒解莊”的思路。
當然,以儒解莊雖然是當時的莊學主流,但仍然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存在。一方面,這體現在當時的一些重要的莊學著作中,比如羅勉道有《南華真經循本》,此書以“循莊子本指”爲特色,力圖去除後人在《莊子》中添加的儒學或佛學色彩。在注解《天地》篇“王德之人”時他認爲“老莊所謂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將《莊子》的“王德之人”與“平坦”的“儒家正理”作了辨析,這裏便解釋出了儒道二家學説本質方面的巨大差異。可以説,他反對闡釋《莊子》時“強附儒家正理”,是對當時“以儒解莊”盛行的一種反思。另一方面,這體現在當時一些理學家對莊子的接受態度中。此處將涉及當時與新學、蜀學並立的另外一個重要學派——洛學。洛學以程顥、程頤兄弟爲首,他們以天理爲本體構建了自己的學説,其形而上學體系借鑒了佛、道關於宇宙本體的理論,但目的是發揮儒家的倫理哲學與政治學説。所以他們特别強調儒學的“純潔性”,常辨析老、莊與儒學之異,並對此展開批判。他們這些批判,也可以看做是對當時莊子闡釋儒學化的一種反撥。
二程之學是宋明理學的基礎,但他們對莊子的批判並不意味着理學與莊子的絶緣。實際上,自二程之後,理學家逐漸向《莊子》靠近,當兩者實現結合時,“以儒解莊”無疑就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這從閩學的領軍朱熹開始就有了兆頭。朱熹與二程在學術上一脈相承,他們的學説構成了理學的主體,世稱“程朱理學”。朱熹繼承二程“衛道”的精神,也將莊子視爲異端,常將其與楊、墨並提。並且,朱熹對將《莊子》與儒家經典互參的做法也頗爲反感,如《朱熹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中有批評謝良佐所注《論語》中“公西華侍坐”一節,朱熹云:“至引列子御風之事爲比,則其雜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氣象尤顯矣。”但這些卻不能否定朱熹對莊子接受時又有儒學化傾向,他對莊子十分重視,作了很多評價,除了一些從理學角度對其批判的言辭外,還有很多評語體現了他對莊子有深入獨到的認識。《朱子語類》卷十六記載其語:“莊子,不知他何所傳授,卻自見得道體。……度亦須承接得孔門之徒,源流有自。”這裏朱熹與韓愈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與之前的王、蘇之説亦相通,這反映了他亦有調節莊、儒兩家矛盾的願望。對莊子的這種認識還體現在他對宋人莊學研究的評述上,如提到“得吕吉甫解看,卻有説得文義的當者”。吕惠卿《莊子義》有鮮明的儒學化傾向,朱熹對它認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説明他本人亦不反對“以儒解莊”的整體思路。再如他亦認可蘇軾對《莊子》辨僞的成果,認爲蘇軾“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絶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可知在朱熹的意識中,莊子亦並非真正詆毁孔子,莊、孔之間並無水火不容的對立。朱熹作爲一個標準的理學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二程嚴辨莊、儒的態度,體現了希望調和兩者的心理。朱熹作爲一代理學宗師,他的這種觀念,爲之後理學與莊子的結合打開了一道缺口,這亦是以儒解莊發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理學與《莊子》相結合在理學家林希逸《莊子口義》中得到實現。這標誌着以儒解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林希逸屬於艾軒學派,這個理學流派始於林光朝(艾軒)。之後有林亦之(網山)、陳藻(樂軒),然後傳至林希逸,他們和林希逸一樣都是福建人,而且有講解莊子的傳統,《莊子口義》中還保存了他們解莊的言語,由此可見福建和莊子的密切關係。總之,在林希逸之前已經有這些解莊的理學家,可知林希逸作爲一個理學家取得如此卓越的莊學成就,這並不是偶然,而是經歷了前期的積累與發展。此外,這些前輩爲林希逸留下的傳統必然是以儒解莊,這從本書所收的艾軒之説中可以體會出來,林希逸也在本書末作了相關評價。故以儒解莊注定成爲本書基本的特色與突出的“亮點”。
作爲宋末的治莊者,林希逸可以説將莊子儒學化推到了最“圓滿”的地步。他充分吸收了前人對莊子儒學化闡釋的精華,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發揮。比如在莊子學派歸類這一根本問題上,林希逸在闡釋《天下》篇時綜合了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説法,之後又在解析中用大量篇幅結合原文對這些説法作進一步闡發,使得這種“莊子歸儒助孔”的説法顯得更爲“完整可信”。林希逸的這些努力使莊、儒間的矛盾得到了更大的調和。
除了調和矛盾外,《莊子口義》“以儒解莊”的思路更明顯地體現在對莊子學説與儒學的整合上。這種整合在之前所介紹的宋代莊學著作中也有嘗試,但林希逸所作的整合相比前人則更加全面、更加精當。《莊子口義》中更爲普遍地引用儒家經典與莊文互參,在規模上超越了王雱、吕惠卿等人。《莊子》中很多的思想内容,林希逸幾乎都可以從儒學中找到有關思想資料來加以詮釋,從而使莊子學説和儒學中一對又一對相異的思想概念分别納入了幾個整體之中,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整合體。
從深層次來看,林希逸主要側重《莊子》與孔顔思想行爲、思孟思想學説的整合。
“孔顔之樂”是北宋儒者喜愛討論的一個話題,它關係到儒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宋代對“孔顔之樂”作的解釋很多,見解各異,歸納他們的基本精神,我認爲就是強調從哲學的高度認可儒家的倫理道德從而實現怡然心境。這在二程思想中體現得尤爲典型,而艾軒學派與洛學有傳承關係,故“孔顔之樂”在林希逸的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而《莊子》又恰有紓解士人心靈的文化意義,林希逸在注莊時自然追求將儒家的這種樂融入《莊子》中去,從而使《莊子》以儒家的方式來履行紓解心靈的“文化使命”。在具體的操作中,林希逸對寓言故事中的孔、顔並未“附會”這種思想,而是將《莊子》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與“孔顔之樂”相結合。典型的如《逍遥遊》題解:
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遥,言優遊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遥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爲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
在《莊子口義》這裏,莊子的“逍遥”和宋儒觀念中的孔子之樂成爲等同的了,這個思路的確很巧妙。當然,兩者的差别我們在之前也已經提到了,今人曾對此作過深入的辨析,認爲這兩者都是一種“自樂”,即精神的内在滿足,故林希逸將它們相混同,這在《讓王》注文中有所體現,即“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顔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這應該就是林希逸所理解的逍遥遊的樂*詳見張毅《以儒解莊——讀林希逸〈莊子口義〉》,《南開學報》1990年第5期。。雖然這是一種混淆,但這種混淆客觀上幫助《莊子》更加適應當時儒學的體系。
對於莊子學説與子思、孟軻思想學説的整合,更是《莊子口義》中的一項重要内容。發掘《莊子》中的性命之學,並與《孟子》的心性學説相參,這在新學派的解莊著作中便有嘗試。到了林希逸這裏則更進一步,他認爲莊子與思孟學派的這些説法在本質上可以整合爲一。所以當《莊子》中出現有關“性命”的言論時,林注都努力地將它們靠近到思孟的心性學説中。如解釋《繕性》篇“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時,他便斷定這段話便是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的意思。再如《庚桑楚》中有“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林希逸則用《中庸》中“誠而明”的思想來解釋它。這些例子都無不説明,在林希逸所構建的框架裏,莊子的道德性命之學與思孟學派的心性道德之説幾乎都得到了巧妙整合,成了一個整合型的思想體系。
林希逸還用理學學説改造了《莊子》中關於本體的思考。對於《莊子》的道論,林希逸或者用周敦頤的“無極而太極”説來闡釋,或者用朱熹的“天理”説來闡釋。尤其是後者,闡釋中所含的理學色彩更加鮮明。如《外物》篇有“僓然而道盡”之語,林希逸解釋説:“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汩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莊子這裏所説的“道”,是指自然之道所賦予的生理,而林希逸卻以程朱理學所謂的“天理”加以解釋,使之具有了合自然與倫理的本體意義。
理學還強調對内心的體察,將它與天理相統一,從而有了“道心”、“人心”的命題。林希逸同樣將這些理論融入對《莊子》性命學説的闡釋中。比如在《秋水》注中云:
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説聽之自然!……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
這段話討論的是《秋水》篇中通過“牛馬”設喻而引出的“無以人滅天”的命題,上文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反映了《莊子》的“自然”思想。可是林希逸此處則排除了“自然”,直接用“道心”和“人心”這組概念來解析原文,這樣經他闡釋過的《莊子》中便有了“道”、“道心”、“天”、“天理”與“人心”、“人欲”的對立,體現了理學典型的思路。甚至在《外物》篇的注解中,他乾脆把莊子説的悟道過程解釋爲“除去物欲而全其天理”的過程,從而使莊子的悟道思想與程朱理學所謂“存天理,滅人欲”的説法幾乎成了一個整體,這種以理解莊的路子無疑使《莊子》闡釋的儒學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綜上,我們可以説,宋代是“以儒解莊”的成熟期。在這一時期,由於儒學内在的新變,宋儒將《莊子》與儒學做了更多融合,相比前輩,他們的“以儒解莊”在許多方面都實現了突破,這包括對莊子的認識、對原文的理解、對文獻的分析、對思想的整合等等方面。明清學者或是在這個框架内繼續探索,或者在這個基礎上做些發揮,總體上未離其宗。
六
元代和明前期的莊子學很不景氣,到了明代正德後,莊子學又呈復興態勢。中晚明的莊子學在“以儒解莊”方面大體仍繼承宋代的路子,但其中出現了很多新變。這些新變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方面: 由學術發展而導致的新變,由求奇的學風而導致的新變,由鼎革的時代背景而導致的新變。下面將擇要對這三方面作介紹,至於基本因襲宋代以儒解莊路子的著作,它們數量衆多,本講因限於時間就不予贅談。
理學發展到明代便出現了心學,王守仁的學説反對朱熹將“天理”和“人欲”對立,強調“致良知”,之後由王艮開創的“泰州學派”在這方面進一步發展,逐漸成了一股解放思想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泰州學派又特别重視對《莊子》的專門研究,《莊子》經過該派學者闡釋,與這種新生的儒學思想又融合起來。泰州學派對莊子的儒學化闡釋相比之前又有一些創新之處。如楊起元的《南華經品節》反對理學家解莊引入“孔顔之樂”的做法,在《寓言》篇“顔回家貧居卑”之處其眉批有云:“程子教人,每令尋顔子樂處,不知所樂何事!”可見心學家、理學家解莊的差異。楊書有意識地將心學的概念融入《莊子》,《庚桑子》中有“能兒子乎”這句話,楊氏闡釋其爲“此皆返樸還淳之道,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也”,這種説法顯然受到了其業師羅汝芳“赤子良心”説的直接影響。再如焦竑的《莊子翼》,在分析莊子學派歸屬時有自己獨到見解,認爲孔孟與老莊殊途同歸,老莊能補孔孟所闕,經過這樣整體上對儒、道的調和,《莊子》便更加順利地融入焦竑的儒學體系。焦竑這種由大處著手的“以儒解莊”方式,是與泰州學派儒、道、禪互滲的複雜思想密切相關的。其實這種意識在之前朱得之《莊子通義》中也有反映,他很注重發掘《莊子》中孔、老二聖的“相知”之情,從而調和莊孔的關係。朱得之是南中王門心學的代表,焦、朱兩人在這方面的相通很能反映出心學在以儒解莊方面的新特色。
明代晚期思想十分活躍,學界有標新立異的風氣,這對以儒解莊的發展也有一定影響。比如陳深的《莊子品節》在賞析文辭外常有獨特見解,《莊子·天下》中有“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紳先生多能明之”之語,陳深解釋“鄒魯之士”云:“此上所指,則周衰以後,鄒魯之士,紳先生,詩書禮樂之徒,孔孟是也。”之前人們都認爲《莊子》中没有一字提到孟子,陳深在這裏則“找出”了孟子,對於後學理解莊、孟關係不無啓發意義,這在客觀上也促進了“以儒解莊”的發展。
明清易代之際,士人的心態發生重大轉變,其中一些遺民的莊學研究爲“以儒解莊”增添了新的元素。如遺民僧覺浪道盛提出了莊子爲“堯孔真孤”、《莊子》爲“儒家别傳”的説法,以寄托其希望傳承華夏文明的心志。其徒方以智著成《藥地炮莊》發展了這個説法,以表明對故國的忠貞不貳之心。之後僧人浄挺將其中“儒家别傳”的説法改成了“釋家别傳”,這便遭到了另一位遺民錢澄之的反對,這説明了《莊子》在此時已是與遺民忠貞不貳的儒者情懷相融合了。陳子龍則將莊子與屈原並提,認爲兩人都是“才高而善怨者”,此處他借莊周抒發了自己作爲一個亂世之民的怨憤之情,而經過他這種闡釋,莊子與屈原在人格上便有了相通之處。無論是覺浪道盛的“堯孔真孤”,還是陳子龍的“莊屈並提”,他們在闡釋莊子時都結合了儒學的元素,這亦是“以儒解莊”的表現,並且有着深刻的時代烙印,體現了與之前不同的特色。
總之,宋代形成了“以儒解莊”的成熟模式,之後的晚明在這方面雖然没有更高的發展,但也因爲各種特殊原因出現了一些新鮮的元素,相比宋前平穩的發展過程,這個時期的以儒解莊在短時間内發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故應當以新變期稱之。
七
在經歷了宋代的成熟和明代的新變之後,清代的“以儒解莊”迎來了一個高峰期,大多數莊學著作都以此爲指導原則,而在路數上則基本因循宋代,没能取得實質性突破。可以説,清代學者在“以儒解莊”的發展歷程中,其意義不在於“開風氣”,而在於“作總結”,即將前人在這方面的思路和經驗進行綜合運用,將“以儒解莊”的“潛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然而,這同樣意味着“以儒解莊”作爲莊學中的一種學術思路,其生命周期也開始步入尾聲,學者沿着這一思路難以再“玩出新花樣”。當然,以上是從學術發展的内在理路所作的分析,如果將視野轉向外部環境,我們同樣可以分析出“以儒解莊”在此時“盛極”的原因與之後“必衰”的命運。因爲清代士人充分反思明代心學的空疏放誕之弊,而朝廷同時又將程朱理學定爲官方哲學並采取高壓的文化政策,這便導致士人對《莊子》這部思想“獨特”的經典作闡釋時,必然努力向儒學靠近。但也要看到這時儒學的鼎盛只是回光返照,近代之後它再也難以維持獨尊的地位,故“以儒解莊”也必然走向低潮。
清代的莊學著作汗牛充棟,其中有儒學化傾向的亦是不勝枚舉,比如: 孫嘉淦的《南華通》,四庫館臣謂“頗以儒理文其説”;陸樹芝的《莊子雪》,尹廷鐸在序中謂“非邃於理學者,亦烏能爲此解哉”;方正瑗的《方齋補莊》,上官德輿在序中謂其“因莊補莊,所以正莊,所以述孔”;吴世尚的《莊子解》,四庫館臣謂其“大旨引《莊子》而附之儒家”。還有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經解》、胡文英《莊子獨見》、林仲懿《南華本義》、劉大櫆《莊子評點》、姚鼐《莊子章義》、梅冲《莊子本義》、劉鴻典《莊子約解》、方潛《南華經解》、馬其昶《莊子故》、王闓運《莊子王氏注》、劉鳳苞《華南雪心編》,都同樣具有這種特點。本講限於時間,不能對它們一一進行介紹,故這裏僅將此時“以儒解莊”的情況歸納爲以下幾個方面,每一方面舉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爲例子來反映其大致的情況。
1. 以儒家作爲莊子的學派歸屬
清儒在闡述自己對莊子的基本認識時,大都否定莊子與孔子的對立,強調二者相通相合的一面。以此爲原則,他們討論了莊子與孔、老、佛的關係,在這個過程中又涉及了子夏、顔回、孟子、屈原等人物。下面分别作些介紹。
一些學者認爲莊子在儒、釋、道中處於中間地帶,如林仲懿《南華本義凡例》云:“莊子不願學孔子,而特以聖人尊孔子,重言十七,孔子居多,不應便坐以詆訾孔子之罪。固是宗老子,亦不盡與老子合。老子之學,尚要應世,莊子卻不然,故朱子説他走了老子的意思。彼先得釋氏之意,而自成一家言者也。”這種看法首先強調的還是莊子尊孔,其次是説明莊子非老,再次是提出莊子與佛義亦相通。這種説法比較能代表清代治莊者的典型認識,不過一般來説,其他人要更強調莊子傳承孔子之處,如孫嘉淦在《南華通》中説“誰謂莊生可以概以異端目之哉”,認爲莊子之道“斯卜氏之傳與”,但同時又説“特其(莊子)知性不真,止見其氣之合,而不能細察理一分殊之大全,是以爲二氏之鼻祖,而非聖門之嫡傳也”(詳見《逍遥遊》通)。這裏強調莊子得孔子之傳,但非嫡傳,這是清儒的主流看法。對於莊子對孔學的傳承問題,姚鼐《莊子章義》則探討了莊子和子夏在“禮樂之原”問題上的相承之處,這便“坐實”了莊子與儒門的關係,是對前人的一個發展,但他同時認爲莊子雖出於儒門,通於儒教,卻“是真禪學,其詆孔子之徒,如以呵佛罵祖爲報佛恩,其意正儼然以教外别傳自居”(詳見《莊子翼語五則》)。在姚氏看來莊子本於孔子,後來則别爲一支,但其心仍是向孔,甚至以詆毁的方式助孔。吴世尚《莊子解》認爲莊子所言亦是孔子之道,只是“特不肯做莊語而質言之”。
王闓運在《莊子王氏注序》中則讚歎“莊子真孔子之徒”,還説:“以莊合佛,晉唐之過也。”並認爲:“雜篇《天下》篇叙論諸家,别於關尹、老聃,而自爲道術,非欲繼乎老也。”這裏他更強調了莊、孔的相通之處,疏離莊老、莊佛間的關係。林雲銘在《莊子因》中提到“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也是這個思路。孫嘉淦《莊子通》也強調莊子與釋道境界上的不同,提出“莊生高於仙佛也”(見《德充符》通),這與王、林態度相近。此外王闓運又根據書中的文字推測“要其學過子夏並顔子矣”,“孟、荀傳儒,莊子同時,未數數然也”。這裏他將莊子納入先秦儒家的體系下進行討論,類似的還有劉鴻典在《莊子約解》中並提莊、孟,認爲“孟子之學出於子思,而莊子之學出於子夏,派雖别而源則同,亦可見尼山之大與天侔”。而且在劉氏看來,莊子所詆者是蠹附於孔子的僞儒,而孔氏不得而聞的性與天道,又在《莊子》“心齋”、“坐忘”的論述中得到流傳,可見劉氏努力將莊子納入正統的儒門。因而,他和王闓運一樣反對混淆莊佛、莊道,認爲“莊子非僧也、非羽也”、“今觀二氏(佛道)重莊子如是,則儒門好處又被二氏竊去矣”。還有的學者則將莊子與諸子區别開,從而凸顯他與儒家的關係,如陸樹芝《莊子雪》則將強調《莊子》思想異於諸子,而與六經相通,認爲它有“維持六經之功”,而“莊子正先聖之外臣猶子,心在君父者,雖真儒讀之,可以無惡矣”。上述這些人的説法都側重於闡發作爲儒家的莊子所藴含的文化意義,去除莊子中道、佛、子的性質,將儒家和莊子聯繫得更密切了。
清代甚至還有極言莊、孔之同的説法,如宣穎《南華經解》説:“唯蒙莊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有以見儒者一宗,蕭邈希微,常行於人倫物則之際,而孔孟之嫡傳,宛然其未亡,然則莊子之傳非别子,固大宗也。”還有胡文英《莊子獨見》提到“莊叟折衷至聖”,“知夫子者,唯漆園一人”。這些説法固然可以理解爲一種文學修辭,但同樣能反映出清代以儒解莊的風氣之盛,及其在學者中的影響之深。
2. 用儒學闡釋《莊子》核心命題與概念
在具體的闡釋過程中,清代學者常針對《莊子》中的重要命題與概念作儒學化的説明。將這些關鍵點注入了儒學的元素,整部《莊子》自然有了儒學色彩,這是以儒解莊的一個重要手段,從郭象開始就已熟練掌握,在清儒中運用得更是廣泛。此處分幾點進行介紹。
《莊子》中有很多對“道”的思考,這是它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在書中有大量文字涉及這一點。關於這些内容,林仲懿、陸樹芝、吴世尚等學者愛用周敦頤的“無極而太極”的思想來闡釋。而宣穎《南華經解》則常用《中庸》上的思想來闡釋“道”,如《知北遊》解中説“寫‘道’只是一‘無’,若莊語之,便是《中庸》末後一節文字”。《天地》篇“泰初有名”這段話也反映了《莊子》的“道論”,郭嵩燾《莊子扎記》闡釋它則引用了《易經·繫辭》“一陰一陽謂之道”的説法,將莊子的自然天道觀變成了儒家的性命之學。
《莊子》中有一些重要的概念承載了莊子獨特的道家思想,如“逍遥”便是其中典型。清儒闡釋這些概念也加入了大量儒家思想。宣穎《逍遥遊》解中將“逍遥”歸於儒家思想之中,提到“故竊謂孔子之絶四也,顔子之樂也,孟子之浩然也,莊子之逍遥也,皆心學也”。而方正瑗《方齋補莊》中解釋“逍遥遊”則加入了“五倫”(即文中所説“有父子之仁”、“有君臣之義”、“有夫婦之别”、“有兄弟之序”、“有朋友之情”)這些有儒家色彩的元素。再如劉鴻典《莊子約解》則將《莊子》中“心齋”、“坐忘”的概念賦予了儒家心性之學的含義,在《序》中他提到“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心齋、坐忘,直揭孔顔相契之旨”,之後他又在《人間世》篇“顔回心齋”、《大宗師》篇“顔回坐忘”兩則寓言故事後對此進行了具體闡發。
3. 援儒典比附《莊子》文義大旨
援用儒家經典解釋莊文,這是從宋代就有的傳統,清儒則將其踵事增華,把它運用得更廣泛、更“深入”。如吴世尚《莊子解》在内七篇之末總結性地説:“《莊子》内七篇窮奇極變,千古文人有一無二,而其實我孔子只數語了之。《逍遥遊》不過‘鳶飛戾天’一節也,《齊物論》則‘巧言亂德’四字而已,《養生主》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人間世》豈有出於‘無道則愚’之一語哉?《德充符》則‘知德者之鮮’,《大宗師》正‘知生知死’、‘朝聞夕可’之理也,至於《應帝王》之‘爲政以德’,我於前評評之矣。”這裏用《論語》等儒家經典中的語句來總結莊子各篇大旨,大多是牽強的“比附”。這是整體層面的比附,在具體段落的解析中,這種比附更是屢見不鮮。如孫嘉淦在闡釋《人間世》篇“孔顔問答”時,數引《論語》原文作爲依據來理解《莊子》中孔子的言語,其比附之迹亦甚爲明顯。將《論語》比附於《莊子》,這體現了清儒調和莊、孔,將《莊子》作儒學化的努力。
《孟子》也是常用來比附《莊子》的儒家經典。如方潛《南華經解》在詮釋《逍遥遊》篇時曾提到:“《逍遥遊》即是《孟子》立‘大體’意,培風、御氣即是《孟子》‘養氣’意,但《莊子》作用自别。《齊物論》即是‘知言’意,第彼直欲一概掃去耳。”“大體”、“養氣”、“知言”皆是《孟子》中的經典概念,在當時影響極大,用它們來比附《莊子》一些篇目的大旨,無疑使《莊子》所蒙受的“儒學色彩”顯得更加明顯。
除了《論》《孟》等傳統儒家經典外,宋明理學家的一些文章言辭同樣被用來比附《莊子》。比如馬其昶《莊子故》在《至樂》篇總論下説:“朱子謂‘學者當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蓋自古大儒名臣未有不勘破生死者。《莊子》書尤數數言此,特恢詭出之,遂覺詞旨别耳。”這種比附將《莊子》納入了理學“天理”、“人欲”的體系,從而使《莊子》與當時主流的修養工夫理論結合到一塊。
4. 據儒家標準對《莊子》文辭進行“改造”或“弘揚”
《莊子》中有不少詆孔毁儒或逆於聖教的言辭,王安石、蘇軾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不以辭害意”、“陽擠而陰助之”的指導思想,後世以儒解莊者大都貫徹了這些思想,清儒亦是如此。對於這些言辭,一些清儒不認爲它們體現了莊子與儒家的矛盾,轉而在其中尋求莊子的深意。下面僅擇其中較有特色的幾部書進行介紹。
陸樹芝《讀莊子雜説》解釋《莊子》中存在的“異説”,認爲莊子是“因異説之至精者而更精之”,以使“詹詹者皆廢”,又説“人之處荒要爲外臣者,當群盜充斥之日,能入賊而爲之魁,舉萑苻竊據之徒一掃而清之,使群盜息而王靈自振”,更説“必識罵佛確是愛佛之理,則莊子正先聖之外臣猶子,心在父君者,雖真儒讀之,可以無惡矣”。這裏將莊子以異説“詆儒”的目的解釋爲“息異説”、“護儒學”,莊子儼然是大忠若奸的形象。
劉鴻典《莊子約解序》則將莊子所詆的對象由孔子轉向了僞儒,認爲“僞儒之附於孔子者,實爲孔子蠹。攻木之蠹,勢不能累及夫木,則莊子之用心爲甚苦,而後人反謂其詆訾也,不亦謬乎”。
這些對莊子詆儒言辭的“辯護”,在王安石、蘇軾等人的基礎上又進行了發揮,算是在這方面比較有新意的説法。清儒對這些言辭具體的“改造”可以參考劉鴻典對《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的詮釋: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而儒者假之,以濟其貪污。……夫儒以孔子爲宗,而其弊至於發冢,是尚得爲孔子之徒乎?孔子之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固知後世必有竊儒之似,而亂儒之真者。莊子斥其僞而存其真,非特西河之高弟,實爲孔子之功臣也。
經過劉鴻典這種轉移批判對象的“改造”,莊、儒不僅矛盾全無而且相通爲一了。
莊文中除了有一些明顯詆儒的激言外,還有一些在深層上與儒家思想相違逆的字句,其中大多是藴含着道家無爲、虚無的思想。對這些言辭,清儒在闡釋時也進行了改造,如梅冲《莊子本義》在《齊物論》篇“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語後給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爲:“庸者,常也,子臣弟友之事也。性道之至精至高,本合萬殊爲一貫,而聖言不可得聞,唯即天下相通、日用不可離者以爲教,而道在其中,所謂寓也。”莊子所謂的“寓諸庸”,本來是説既然衆生各執是非,與之相對應的聖人就對衆生之心一味隨順,了無分别,也就是説,“無分别”才是莊子“寓諸庸”的落腳處,可是這樣一來,立即會跟事事講分别的儒家世界觀産生衝突。於是,梅冲利用了這“寓諸庸”與“中庸”字面上的互文關係,巧妙地轉换了莊子的論述重心,他在《中庸》中找出“子臣弟友”這一世間倫常的代稱,以此釋莊文之“庸”,便將這個“庸”字做實了,更符合儒家的思想。
有趣的是,清儒雖然強調不要拘牽於文辭,但又經常揪住《莊》文中的一些字句不放,將其作爲莊子尊儒的鐵證。如《齊物論》篇中有“《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之語,孫嘉淦便將其與“孔子成《春秋》”、“《春秋》微言大義”等説法聯繫起來,認爲以此可見莊子“尊經仰聖,其言粹然”。對於這段話,方潛《南華經解》也説:“莊子何嘗不尊聖人?此段層層歸結聖人,可知其意矣。未可因其放論而議之,以意逆志可也。”莊子此段所述何義、聖人何指,一直都有争論,而孫、方兩人直從字面入手,言之鑿鑿,殊不可以爲解。可見清儒解讀《莊子》的標準並非“不以辭害意”,而是完全以它們是否符合儒家思想爲轉移。此處對這些言語的“弘揚”與上文提到的“改造”一樣,都是以儒家標準爲依據的。
5. 重塑《莊子》中孔子形象
莊子中有很多直接描寫孔子的文辭,這些孔子形象的好壞直接決定了莊子與儒家的關係,故歷代以儒解莊者都在這方面下工夫,力圖以自己的理解來重塑莊文中的孔子,從而調和莊、儒矛盾。清儒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這在他們注文的字裏行間都有體現。
《德充符》篇中有“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的寓言故事,顯然是抑孔揚王的格調,孔子形象在這裏只是王駘的陪襯,但吴世尚卻解釋説:“讀此篇,莊之尊孔可謂至矣。蓋此老胸中,原以爲千古之德充符者,唯我孔子耳,而嫌於以己説孔子第屬造道之言,不若以孔子説孔子乃爲有德之言,故特地撰出個王駘、哀駘它來,從孔子口中寫出許大深微弘至之語,此豈説王駘、哀駘它哉,實莊子説我孔子也。”經吴世尚如此説,孔子又恢復了至上聖人的形象。吴世尚對莊文出現孔子處特别著意,甚至看出了其中的“史料價值”,在《莊子解序》中他便提出:“又其(《莊子》)時時稱述孔子諸言論,儒者以其不復概見他書,遂疑其皆周所托者。不知孔、顔終日言,無所不説,則當日師弟間,必不僅於今問仁爲邦、用行舍藏諸云云,可知矣。則安知周所述之非我孔子之實言實事乎?”這種觀點更突出了莊文中孔子形象的重要性,故重塑孔子形象成了吴世尚在以儒解莊時所要着力完成的任務。
6. 結合篇章真僞否定“詆儒”之説
蘇軾《莊子祠堂記》開啓了辨别《莊子》篇目真僞的風氣,但這並非純粹針對文獻的研究,它同樣涉及了莊、儒矛盾的問題。清儒常常以考察篇目真僞的方式來否定“詆儒”之説,他們發展了蘇軾“《盜跖》四篇爲僞作”的説法,同時又強調内七篇爲莊子手筆,來論證莊子“尊孔”的態度。如胡文英《莊子獨見》云:“《讓王》《盜跖》《説劍》《漁父》四篇筆力庸弱,詞句淺率,其爲贋手所托無疑。”(詳見《讓王》篇末總評)吴世尚《莊子解序》則云:“而内七篇,則又蒙叟所手定,更醇正而無疵者也。”再如孫嘉淦《南華通》云:“詆訾孔子者,皆外、雜篇所載,乃後人之贋作,内篇初無是也。”這些針對文獻的研究,也成了清代治莊者“以儒解莊”的重要手段。
以上幾條是在以儒解莊的歷史中逐漸凸顯出來的幾個現象,到了清代更是成了以儒解莊内部構成的幾個中心。單從這幾點來看,清代以儒解莊的路數發展得更加全面,成果也很多。但是,正如我們上面所説,它難再有實質性創新,而且時代馬上又發生了巨變,故這種解莊方式在清之後再也難成主流了。
八
隨着清朝的滅亡,以儒解莊的高峰期也過去了,民國時,雖時有著作遵循此思路,但也大都是“歷史的回音”,難以再構成學術主流,故該階段應該稱爲以儒解莊的延伸期。
對以儒解莊的反思從晚清起就出現了,陳壽昌在《南華真經正義序》中明確提出本書要“一洗援儒入莊之弊”,可見“以儒解莊”的衰弱遵循了學術發展的内在理路,體現了物極必反的規律。而且隨着外在學術風氣的變化,清末民初的幾部開風氣之先的莊學著作,如嚴復《莊子評點》、梁啓超《莊子學派概觀》、章太炎《齊物論釋》等,它們所體現的儒學色彩也大大減少。
但歷史的慣性是強大的,民國時期仍有一些莊學著作帶有以儒解莊的特點,它們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着這方面的探索。其中也不乏對前説有發展的,如蔣錫昌《莊子哲學》認爲《莊子》外篇中“臣道”理論來源於孔子,又認爲“(莊子)故未嘗絀儒,且與之相當之地位”,這些都是對蘇軾“陽擠而陰助之”觀點的補充和修正。再如胡遠濬《莊子詮詁》謂,“莊子破儒家之執,故立詞不得不異,而其旨實同”,“孟子痛斥言利,莊子深譏近名,名即利也,亦即刑也”,這些闡釋較前人更深入一些。此外,黄元炳《莊子新疏》則説“(外篇)兼師孔、老,而出入於《(大)學》《(中)庸》《道德》者也”,“其書老氏骨而孔氏髓”,又主張將莊子與子夏之儒相區分,把他的思想歸爲曾、顔的後傳,這些説法雖然於古有之,但作者將它們總結得更精煉,表達得更鮮明獨特,尤其是區分莊、夏之説,更是新穎。鍾泰《中國哲學史·莊子》中持説相近,認爲“莊子之學實出於孔門顔子一脈”,而傳的正是“内聖外王”之學。這時還有郭沫若的《十批判書·莊子的批判》也主張莊子爲顔氏後學,他在前人基礎上又羅列了大量證據,使這種説法産生了更大的影響。但相比前面幾家,郭氏的莊子研究立足於學術史的大視野,“以儒解莊”在本書中已與其他新的學術思路相融合,有了新的氣象,畢竟民國學術研究範式相比往昔發生了巨大變化,兩種範式下,同一種路數産生的效果與所藴含的意義也有了差異。從這一層面上來説,郭氏的這種研究意味着之後“以儒解莊”還會以新的形式存在於莊學研究中。
這便是“以儒解莊”延伸期的大概情況,在這個階段,以儒解莊作爲曾經的主流,它依舊有市場,作爲悠久的傳統,它仍會有新變。直到現在,我們也能在衆多莊學著作中看到它的影子,可見它在莊學史上的影響之深遠。
總之,“以儒解莊”是莊子學史上最爲普遍的一種現象,其中的問題也很多,我們無法在此講中全面説清楚,但仍希望大家予以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