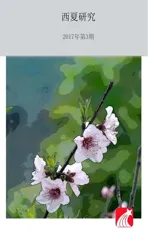嘉靖《河州志》所载墓碑考释
——兼论康熙《河州志》与《河州志校刊》之错讹
2017-01-27他维宏
□他维宏
嘉靖《河州志》所载墓碑考释
——兼论康熙《河州志》与《河州志校刊》之错讹
□他维宏
明吴祯所撰《河州志》载有墓志一则,在传抄流传的过程中出现讹误,后世修志、校刊者直接移录,不加辨证,以至出现错误。考释其志文,嘉靖《河州志》志文中的“唐后周石兰靖之墓”的题名应为“后周石靖墓”;“授开封府”应为“授开府”;“随道武帝西征”应为“随太武帝西征”。石靖的事迹,为我们观察北周时期的河州提供了一个窗口。
北周;石靖;《河州志》
河州,故称枹罕,处于古代西北交通要道上,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现存民国前所修的河州地方志有:明吴祯所撰嘉靖《河州志》四卷,清张瓒修康熙二十六年《河州志》二卷,清王全臣所修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六卷,清张封武修、杨清等纂宣统《河州续志》(或题《河州采访事迹》)[1]94-99。嘉靖本《河州志》,由马志勇先生校刊,于2004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校刊本),其余方志尚待出版。嘉靖本《河州志》载有一则墓志志文,此志文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有待考辨,康熙四十六年本和校刊本在著录志文和点校上存有错误。笔者不揣浅陋,撰此短文,首先对墓志作一考释,其次考辨嘉靖本中墓志的部分错误,再次考察康熙本、校刊本在转录和点校时的错误,以就教于学界。
一、志文内容及考释
此墓志原物已佚,志文载于嘉靖本《河州》卷一《地理志·丘墓》,题名为“唐后周石兰靖之墓”,清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所撰《河州志》、民国张维所撰《陇右金石录》亦录其文,文字略有不同。所有版本的《河州志》都作“唐后周石兰靖之墓”,根据志文,墓主名为石靖,是北魏、北周时人。而非志所载之唐后周石兰靖。《甘肃通志》已辨其误,“南北朝后周刺史石靖墓,在河州北原(即广大塬)上”[2]巻二五《陵墓》。此志文的来历,《河州志》载:“嘉靖乙酉,耕农获半石,遇郡医戴氏,与家收半石合之,果一志石也。文无遗损,因录其志文。”[3] 25康熙本《河州志》同。笔者查阅了嘉靖四十二年刘氏仕优堂重刻本影印,间以抄本配补的嘉靖本《河州志》[4]今重新著录并点校如下。
君讳靖,字士安,冀州乐陵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子石文候之孙。汉魏以来,兖绂相传。十一世祖苞,晋录尚书、荆州刺史。累业重光,英辉相继。祖延,便弓马,从魏道[太]武○○西征,任统军,留镇枹罕,因而家焉。父雀,夙经行阵,任第一军主。公,幼怀朗悟,明惠若神。永熙三年,任洪和郡守。至大统二年中,授都督任河州。寻除大都督仪同三司。武成元年,授开封府。二年,除甘州刺史、仓泉县开国公、邑三千五百户。降年有永,春秋六十有七,薨于位。有诏督河、渭二州刺史。以大周天和三年岁次戊子十月二十二日,葬于枹罕县广大塬。立碑封树,乃为铭曰:猗欤胄胤,世出能官,惟公继诸,神武桓桓。方超逸翮,邃掩幽攒。庶因真础,永播芳兰。
1.墓主及祖先
根据墓志内容可知,墓主石靖逝于大周天和三年(569)十月二十二日,享年67岁,由此可以推算出墓主生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2)。墓主是冀州乐陵人。冀州,“……慕容垂治信都。皇始二年平信都,仍置”[5]2464。起初后燕并未占据信都,故384年陈留王慕容绍行冀州刺史曾屯广阿①[6]3375。385年,慕容垂遣从弟慕容精率军攻打占据信都的苻定②[6]3408。太元十一年(386)六月,苻定降,后燕冀州当于此时始镇信都。396年改镇邺城③[6]3480。北魏时冀州治信都。冀州于皇始二年(397)平定时辖有乐陵等十六郡。熙平二年(517)置沧州,乐陵郡划出,乐陵郡治乐陵,初领乐陵、阳信、厌次、湿沃四县。墓志所说冀州乐陵,乃墓主郡望之地。
墓志随后追述墓主的先祖,其先祖是周成王之子石文候之孙。十一世祖石苞在西晋时官至录尚书、荆州刺史。魏晋之际,也有一位名臣石苞,其籍贯亦为冀州乐陵,恐非与此石苞同一人,墓志所云当另有其人。祖父石延跟随道武帝西征,任统军。统军:统兵武官,北魏置,位在军主之上,别将之下,北齐时列为备身五职之一,北周定为五命。[7]813至枹罕,留下来镇守枹罕,因此,在此地安家。其父石雀,夙经行阵,任第一军主。军主:统兵武官,位在统军之下,其下设有军副,所统兵力无定员,自数百人至万人以上不等。北齐时为备身五职之一。北齐定为从七品。北周四命。[7]506
从祖先世系可以看出,一是墓主十一世祖至其祖父之间的先祖及事迹是模糊的;二是墓主祖父、父从军,以军功做到中级武官的行列。
2.墓主的仕宦经历
墓主石靖的祖父、父都仕于北魏。他本人于永熙三年(534),任洪河郡守。墓主如何入仕,墓志不详,但是从任用的郡守官职来看,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深明民政之事。洪河郡,《魏书·地形志》河州条云:“有伏乾。阙二字。真君六年置镇,后改。治枹罕。领郡四:金城、武始、洪和、临洮。”[5]2620墓志作洪河,当为音同而误。
大统二年中,授都督任河州。寻除大都督仪同三司。大统二年(537),石靖从其祖父迁至河州,到他这一代,已历三世。虽然在追述籍贯时仍然称“冀州乐陵”的郡望,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河州的地方“豪右”、乡帅。宇文泰将已获得其信任的出身名门望族者作为乡帅配置在各自的本州,使其统辖州内的“豪右”军团。[8]338加强对此地的控制。因此,任命石靖为河州都督,统辖河州一地的乡兵,不久提拔为大都督仪同三司。《周书》卷二四《卢辩传》载卢辩与苏椿制定的官职官品表,通过该表可以看到都督、大都督仪同三司的位置。
正九命 柱国大将军、大将军
九命 开府、仪同三司
八命 大都督
正七命 帅都督
七命 都督
正六命 别将
正五命 统军
四命 军主[8]349
都督为七命,大都督仪同三司为八命。有意思的是石靖越过正七命的帅都督,直接由都督升任大都督仪同三司。一般情况下,统帅乡兵的将领加帅都督,再者,石靖的升迁不可能不经过帅都督一阶。因此,石靖所任的都督很有可能是具有统帅乡兵的帅都督,而墓志的撰写者笼统地称为“都督”。
武成元年(559)八月,“授开封府”一句有误。一是北周时无开封府,开封府时称汴州,汴州下辖开封郡,也已在北齐时所废。二是宇文泰将已获得其信任的出身名门望族者作为乡帅配置在各自的本州,使其统辖州内的“豪右”军团,借以控制河州,不会让石靖任官于汴州。因此,此句应为“授开府”。从上文的官品表来看,大都督仪同三司为八命,升迁至九命的开府、仪同三司是合理的。
武成二年(560),除甘州刺史,仓泉县开国公,邑三千五百户。甘州,今甘肃张掖。仓泉县,《北周地理志》卷二《陇右》成州仇池郡下“仓泉县,今甘肃西和县南洛峪镇。后魏置。《魏书·地形志》:‘仓泉,太和四年置。’”[9]157即石靖的封邑。
从石靖的仕宦官品来看,从(帅)都督—大都督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从七命至九命,石靖通过父辈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做到北周的高官,这也是墓志说他“幼怀朗悟,明惠若神”的原因。从仕宦的地域来看,河州、甘州都是陇右地区的重镇,历来为兵家争夺之地,体现了西魏、北周任用当地豪右任本州,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的政策。
二、志文中“从魏道武西征”的真实性
众所周知,在道武帝时代,拓跋部的势力还未及“河南地”。但是,墓志云石靖祖父随道武帝西征至枹罕,留其镇守,因而安家于此。没有其他的史料来明确判断这一说法的真实性。首先,我们假定此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引出的问题是道武帝何时西征?《魏书》、《资治通鉴》中记载道武帝时期西征者,总共有三次。
(1)隆安五年(401)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跋率众五万袭没弈干于高平[6] 3533。“魏军追至瓦亭,不及而还,尽获其府库蓄积,马四万余匹,杂畜九万余口,徙其民于代都,余种分迸。”[6] 3535
(2)元兴元年(402)正月癸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没弈干弃其部众,率数千骑与刘勃勃奔秦州。平阳太守贰尘复侵秦河东,长安大震,关中诸城昼闭,秦人简兵训卒以谋伐魏。[6] 3535-3536
(3)元兴元年(402)五月,后秦姚兴派遣义阳公平、尚书右仆射狄伯支等率步骑四万进攻北魏乾壁,姚兴自率大军为后援。六十多日后,姚平攻克乾壁。[6] 3543七月,拓跋珪以镇西大将军、毗陵王顺、长孙肥等三人将六万骑为前锋,自己率大军为后继,抵御后秦[5] 40。
但是这三次西征最远达高平、瓦亭一带,并没有进入河州之地,且按墓主生于502年,与此三次西征最晚的时间相差100年,与其祖父的年龄相差太大,这不符合常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假设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志文关于石靖祖父随道武帝西征至枹罕的记载是不真实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石靖的祖父是随军西征至枹罕安家的,因为墓碑的书写者在书写的时候一定得到过石靖家人的叙述的材料的,不可能无的放矢。既然石靖祖父石延随道武帝西征是不真实的,而其西征是真实的。那么作为统军的石延是随谁西征的呢?
墓碑云:石延随军西征,“留镇枹罕”,说明此时的枹罕已成为北魏的统治区域。《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下》载:“河州,有伏乾。阙二字。真君六年置镇,后改。治枹罕。”[5] 2620校勘记中有所补充,钱氏《廿二史考异》卷三○云:“按乞伏国仁尝自称河州牧,当云‘乞伏乾归置’。‘有’盖‘乞’之讹。”[5]2649此说甚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上》亦云:“后魏平定秦陇西,改置枹罕镇。”《魏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只是说明枹罕纳入北魏的管辖,其具体过程不详。
在北魏统治之前,枹罕之地分布着羌、氐等少数民族,征伐不断,为兵家必争之地,各个政权之间互为争夺。先是,枹罕为陇西鲜卑乞伏国仁所建的西秦政权所有。西秦乞伏乾归太初十三年(400),后秦姚兴伐西秦,乞伏乾归兵败,奔南凉,不久又降于后秦。西秦亡,西秦所辖枹罕归后秦,后秦任用当地羌首彭奚念为河州刺史,镇守枹罕。姚兴署乾归为“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10]2981。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为借乞伏势力统治陇右,并继续向河西深入,使乾归还镇苑川,至苑川后,乾归开始韬晦,“以边芮为长史,王松寿为司马,公卿、将帅皆降为僚佐、偏裨”[6]3521,暗中积聚力量,为复国做准备。弘始四年(402)夏四月,乞伏炽磐从南凉西平逃归苑川,投奔其父,南凉王傉檀归其妻子。乞伏乾归使炽磐入朝于秦,姚兴以炽磐为兴晋太守。[6]3542弘始八年(406)十一月,乾归朝于长安。弘始九年(407)正月,姚兴看到乾归父子势力逐渐膨胀,难以控制,因其入朝,遂为软禁,“以其世子炽磐行西夷校尉,监其部众”[6] 3594。十月,后秦河州刺史彭奚念降于南凉,姚兴即以炽磐行河州刺史[6] 3602。
乾伏炽磐看到后秦与夏赫连勃勃、北魏连年战争,势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于弘始十年(408)十月,“招结诸部二万余人筑城于嵻山良山而据之”[6]3609,以抵御后秦。十二月,率军攻打盘踞在枹罕的彭奚念,但是被彭奚念击败。第一次进攻枹罕失败。弘始十一年(409)二月,“乞伏炽磐入见秦太原公懿于上邽,彭奚念乘虚伐之。炽磐闻之,怒,不告懿而归,击奚念,破之,遂围枹罕。乞伏乾归从秦王兴如平凉;炽磐克枹罕,遣人告乾归,乾归逃还苑川”[6] 3613。四月,乞伏乾归与其子炽磐会合,重建西秦政权,枹罕之地重归西秦政权。
西秦建弘七年(426),乾伏炽磐派人至平城,请太武帝拓跋焘出兵灭夏。这一举动激怒了夏政权,开始了西秦与夏的战争,最终在乞伏暮末永弘四年(431)为夏所灭,西秦亡,枹罕之地归夏。但是同年迫于北魏的压力,渡河欲西击北凉,结果在中途为吐谷浑所灭,吐谷浑因此获得金城、枹罕、陇西之地。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夏四月庚戌,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于阴平、白兰。诏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枹罕……什归闻军将至,弃城夜遁。秋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迁徙千家还上邦”[5]98。以上是在北方十六国时期枹罕之地的臣属政权的变化轨迹。
太平真君六年(445),枹罕归属北魏。是年,与墓主石靖的生辰北魏景明二年(502)相差57年,符合常理。因此,墓碑中的道武帝当为太武帝之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能是嘉靖本《河州志》在传刻、抄写导致的。
三、康熙四十六年本讹误与校刊本的标点错误
嘉靖本《河州志》所载的北周石靖墓墓碑志文,康熙四十六年本《河州志》(简称康熙本)亦有录文。民国时期陇上著名学者张维所撰《陇右金石录》从康熙四十六年本《河州志》移录,并云:“按《魏书·地形志》,河州领枹罕、金城、武始、洪和、临洮五郡,志作洪河,当以音同而误。开府久作开封府,则俗抄增入。《魏志》南秦州仇池郡有仓泉县,即靖所封,旧讹食泉。今原石久佚,皆以意更正之。”[11]15973张氏直接移录康熙本《河州志》中的志文,并对康熙本中的讹误作了解释,但他并没有查阅嘉靖本《河州志》,致使自己所录志文亦有错误遗漏。
以嘉靖本《河州志》为底本,校刊康熙本,则康熙本出现许多讹误遗漏。
(1)“十一世祖苞,晋录尚书、荆州刺史。”康熙本漏“苞”,“晋”误为“普”。
(2)“累业重光,英辉相继”,康熙本作“累业光辉,英风相继”。
(3)“从魏道武○○西征”,康熙本无“○○”。
(4)“父雀”,康熙本作“父崔”。
(5)“明惠若神”,康熙本作“明哲若神”。
(6)“永熙三年”,康熙本作“永熙二年”。
以上是康熙本遗漏错讹的情况。
校刊本所载的志文是原嘉靖本,因此文字错误甚少,主要是标点的错误。见于下。
(1)此志文的题名应为“后周石靖墓”,而校刊本未做校正。
(2)“从魏道武○○西征”,校刊本却作“从魏道武□□西征”。
(3)“君讳靖,字士安。冀州乐陵人也。”应标点为“君讳靖,字士安,冀州乐陵人也。”
(4)“其先周成王之子石文候之孙。”应标点为“其先,周成王之子石文候之孙。”
(5)“十一世祖苞晋录尚书荆州刺史。”应标点为“十一世祖苞,晋录尚书、荆州刺史。”
(6)“祖延便弓马”应标点为“祖延,便弓马”。
(7)“父雀夙经行阵,任第一军主。”应标点为“父雀,夙经行阵,任第一军主。”
(8)“公幼怀朗悟,明惠若神。”应标点为“公,幼怀朗悟,明惠若神。”
(9)“永熙三年任洪和郡守。”应标点为“永熙三年,任洪和郡守。”
(10)“二年除甘州刺史,仓泉县开国公,邑三千五百户。”应标点为“二年,除甘州刺史、仓泉县开国公,邑三千五百户。”
(11)“有诏督河渭二州刺史。”应标点为“有诏督河、渭二州刺史。”
(12)“立碑封树。乃为铭曰”应标点为“立碑封树,乃为铭曰”。
综上所述,通过墓碑的考释,通过对石靖墓志的考释,厘清了墓主石靖先祖的事迹及他的仕宦经历。经过考辨,志文中“从魏道武西征”是“魏太武帝西征”之误。以嘉靖本《河州志》为底本,对校康熙本《河州志》,指出了其中的错讹,以及校刊本的标点错误。
附记:此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冯培红教授的指点,附此声谢。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一○五,孝武帝太元九年(384)正月壬子条云:“燕王垂攻邺,拔其外郭,长乐公巫退守中城。关东六州郡县多送任请降于燕。癸丑,垂以陈留王绍行冀州刺史,屯广阿。”
②《资治通鉴》卷一○六,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十二月云:“秦苻定据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从弟北地王精为冀州刺史,将兵攻之。”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太元二十一年五月辛亥条云:后燕“以范阳王德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邺”。
[1]张思温.临夏自治州地方志提要[M]//周丕显,等.甘肃方志述略.长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
[2]许容.甘肃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吴祯,著.河州志校刊[M]. 马志勇,校.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
[4]中国地方志辑成:甘肃府县志辑·嘉靖河州志[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9.
[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张政烺.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8]谷川道雄,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M]. 李济仓,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9]王仲荦.北周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张维.陇右金石录[M]. 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民国三十二年(1945).
(责任编辑 魏淑霞)
他维宏(1992—),男,甘肃临夏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