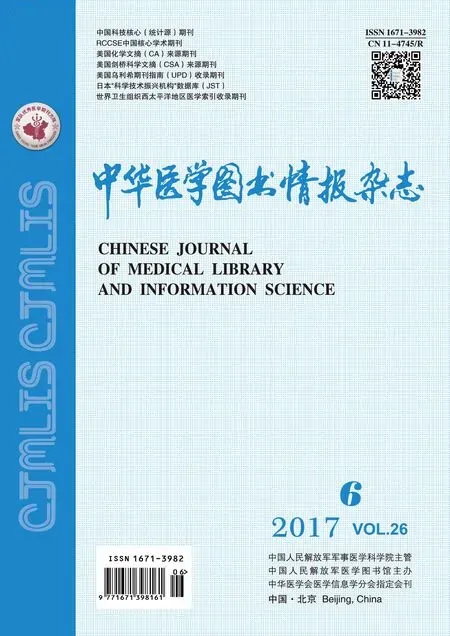我国药品强制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17-01-27,,,,
,,,,
获得药物是有效治疗疾病的必要环节,而如何提高药物的可及性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1977年,WHO基本药物政策(Essential Drugs and Medicines Policy,EDMP)首次倡导药品可及性问题并概括其具有的药品选择恰当性、市场供应能力、患者支付能力和患者信息获取能力四层含义;2004年,WHO针对药品可及性列出四项影响因素,即药品的合理使用与选择、可以承受的药品价格、持续的资金支持、可靠的药品供应体系[1-3]。国际贸易组织在《多哈宣言》协议中明确指出每个成员国当处于诸如艾滋病、疟疾、结核病和其他流行病等造成的公众健康危机时,即构成可以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紧急状态”,具有使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权利,从政治和法律等方面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获得药物的能力。
我国虽已基本建立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是尚未真正开展实施,药品强制许可处于“零”颁布状态。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我国爆发,特效药达菲供不应求时,广州白云山药业曾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提前受理我厂仿制磷酸奥司他韦原料及胶囊的注册申请”报告,希望通过启动强制许可程序获得生产许可,然而最终没有获得实施[4]。这对于一个技术相对落后、产业发展受制于人、药物可及性不高、国民人口总数占世界第一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正常状态,反映出我国在药品强制许可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5]。本文通过讨论和剖析药品专利权强制许可制度国内相关法律规定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在此领域可改进及完善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制度。
1 资料来源和方法
主要通过文献检索、临床调查、企业论坛、部门需求四类方法进行调查研究。
1.1 了解临床需求
通过临床用药研讨会拜访临床诊疗专家,了解我国用药的实际状况及需要解决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以艾滋病为例,我国为了有效控制艾滋病蔓延,2003年底出台“四免一关怀”政策,开始为符合标准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6]。根据抗病毒治疗方案中所需药品情况,国内免费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分成一线药物及二线药物两类[7]。一线药物易耐药且副反应强,而我国二线药物的可及性远不如部分非洲地区,临床医生面临因药物短缺而被动改变处方的窘境。
1.2 了解药企现状
了解具备生产能力的药品企业生产先进专利药物存在的法律障碍。
由于药物研发时间长、投入大,虽然国内药企和科研院所已经在进行艾滋病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但是跨国药企依然控制着中国乃至全球抗艾滋专利药物的供给。目前我国仅有南京前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艾博卫泰”进入临床三期的后期阶段,却因种种问题仍未获得新药证书。
我国已经有上海迪赛诺等制药企业获得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MPP)授权生产二线抗艾滋病药物原料药。除此以外,华海制药公司、深圳东阳光制药公司也具备生产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经验,既满足 WHO 的预合格标准,也具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要求的最低质量标准,并已经取得MPP药品专利分许可。然而,中国却未从MPP取得药品专利许可来解决国内的药品可及问题。据吉列德公司声称,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属于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而吉列德通过MPP救助目标主要是低收入或是治疗艾滋病面临较大经济负担的国家,这一规定致使我国用药水平远不及不具备药物生产能力的非洲,而人均收入高于我国的巴西却可以从MPP中获得艾滋病二线药物。
1.3 咨询相关政策解释
向知识产权局、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技部、商务部、工信部等政府部门咨询其对我国实行药品强制许可的政策建议。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有关药品专利的立法情况
以我国为代表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签署了《TRIPs》协定,这是加入WTO从而获得成员国市场准入权的先决条件,我国作为《巴黎公约》和《TRIPs》协定成员国,对于药品专利权的国内立法保护体系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2.1.1 专利法
1979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谈判推动了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出台,1984年我国颁布了《专利法》,以法律制度承诺对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予以保护。
1992年1月达成《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并据此对我国《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扩大了专利保护的技术领域,延长了三种专利保护期限,增加了可以使用强制许可的情况。 2000年按照国际公约《TRIPs》协定进一步修订了《专利法》,旨在加大专利保护力度,简化专利审批程序。2008年为激励自主创新,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又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即为我国现行《专利法》。
现行《专利法》第六章“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用11条立法条目对强制许可做出规定[8],明确我国在“未充分实施”“ 垄断行为”“ 紧急状态”“ 非常情况”“ 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 公共健康目的”“ 专利依赖”几种情况下可对专利申请强制许可。
可见2000年以后对于《专利法》的修订和相关立法及制度建立,是来自于我国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
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保护专利权,完善其实施,200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并于2010年进行修订。本次修订明确了取得专利药品的概念,增加了出于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目的颁发强制许可的规定。
2.1.3 《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办法》(2003年31号令)
2003年我国爆发“非典型性肺炎(SARS)”,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健康危机使国内专家学者及立法者达成共识,即药品专利权强制许可制度应该在我国发生公共危机时发挥重要作用。200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办法》(2003年31号令),此行政规章对专利许可实施的有关程序做出了规定。
2.1.4 《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2005年我国大规模爆发禽流感疫情,进一步暴露了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应对紧急公共卫生危机时不够完善的问题。2001年《多哈宣言》、2003年《总理事会决议》和2005年《修改 TRIPs 协议议定书》等国际条约的通过,为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2006年1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05年37号令)实施,进一步明确了药品强制许可的有关问题,如《专利法》第49条以及《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等,规定了强制许可的实施条件。这一办法的提出,将《多哈宣言》以及《总理事会决定》中有关因“公共健康目的”“ 紧急状态”“非常情况”“公共利益的目的”而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具体落实到国内法律层面。例如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导致公共健康问题可申请专利强制许可的几种传染病,其中艾滋病居首位。第四条,在面临公共危机或紧急、非常情况时,需要大量治疗某传染病药品的储备。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据规定,批准强制许可给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在本条规定中明确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授予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9-11]。
2.1.5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12年64号令)
为了落实第三次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国家知识产权局对2003年颁布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和2005年颁布的《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进行整合,公布了新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12年64号令)(以下简称《办法》)。在第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分别对因公共利益和公共健康原因申请专利强制许可的一般性操作做出规定[12]。
2.2 我国在药品强制许可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2.1 相关规定的实施效力低下
首先是相关规定不统一。目前我国涉及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相关条款分散于几部法律和规章制度当中,存在矛盾和不统一的问题。
如《办法》第6条和《专利法》第49条关于因公共利益实施的强制许可规定就存在彼此不符、矛盾和效率低下三方面的问题。立法内容虽然含盖了“国内实施强制药品发明专利强制性许可”,但2012年修改的《办法》第6条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与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第81条“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的规定不符。在制定艾滋病专利实施强制许可时,此办法第6条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就要涉及到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2012年国务院部门机构改革,原食品药品监管权从卫生部分离,成立同级部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但是,按照2012年《办法》第6条的规定,不能确定具体国务院有关部门是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商务部门等其他部门。
此外,此办法仅为专利局部门令,对同属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其他具有相关职能的部门效力过低。
其次是“公共”的范围界定不清晰。《专利法》第49条和第50条都规定了因“公共”原因可进行强制许可,但“公共”所涉及的地域并不相同,专利法第49涉及中国大陆境内、专利法50条涉及中国大陆境外的部分国家或者地区。
第三是操作程序不详。《办法》第6、7条对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的认定条件和程序不详,建议对强制许可请求的提出与受理、审查与决定、审查和裁决,以及终止强制许可请求的审查和决定相关规定进行补充完善。
2.2.2 企业对法律和制度了解不足的问题
2016年9月,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的关于新药研发科技重大专项艾滋病药物研发企业座谈会上,与会企业表示,已获得MPP授权并具有生产艾滋病原料药物的能力和初步具备生产仿制药物的能力,在中科院等国内一流仿制药实验室技术力量支持下,如果原料准备充分,很快可实现复制并批量生产。但是,在讨论到有关药品专利权的授予、与MPP的谈判、强制许可的操作性等立法及制度问题时,企业均表示不了解。经在场专利律师初步解释后,对要付给专利持有人的专利补偿金和药品利润率表示担忧。这充分表明国内的制药企业对专利强制许可的认识不足。
2.2.3 政府部门依职权行使问题
《办法》第12条中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授予强制许可的单位需要进行推荐”;在《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第4条规定中要求“治疗某种传染病的药品在我国被授予专利权,我国具有该药品的生产能力,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专利法》第49条的规定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强制许可”。这两项规定涉及到两个甚至更多部门对被授予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单位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详细论证。而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推荐主管部门,这在没有国务院建立的多部门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很难开展。
《专利法实施细则》中第72条第2款提出了强制许可的主要程序,规定要求证明文件里要有申请单位或个人具有实施该专利能力,如在技术、人员、设备等方面均有实施该专利条件的证明,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制定相应的论证章程及操作细则,而且必然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导致强制许可程序时间上的延误。
在《专利法》第55条中规定了“应根据强制许可的理由规定适时的范围和时间”,而这一时间的长短需要专利人根据理由消除再次向专利局进行申请,审核后予以终止,并非提前约定,这一规定易造成专利相关药品的市场恐慌,相关部门无依据提前判定。
在《专利法》57条中规定了被强制许可的专利人应当得到合理和必要的经济补偿,但没有规定具体费用和计算方式,强制许可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生产量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3 对策与建议
3.1 强化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效力
目前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相关法律及制度规定见于《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办法》、《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学科办法》几部法律和制度中,约束效力不一,且过于分散,建议整合,提高实施效力。
3.2 进一步明确和调整药品强制许可相关操作规定
3.2.1 明确界定“公共”的地域范围
《专利法》第49、50条中对于“公共”所涉及的地域并不相同,49条的公共为中国大陆境内,而50条的公共则为中国大陆境外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冲突,需要明确和调整。
3.2.2 明确认定实施的条件和程序
《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办法》中第6、7条没有具体可实施专利的单位认定条件和程序,对于“国务院有关部门”操作性可依据力不足,需进一步明确规定提出、受理、请求审查和决定、许可裁决、终止请求和决定的程序,便于有关部门和企业操作。
3.3 提高国务院有关部门依职权行使强制许可的可操作性
3.3.1 明确推荐的主管部门
明确《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中可推荐强制许可单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避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职责不清而造成的拖延。对于因国务院机构改革而造成的依职权行使部门不清的问题,建议尽快修改相应法条或规章制度。
3.3.2 制定规章提升实施效率
对于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有关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以达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效力。
3.4 加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普法宣传工作
根据实际调研情况不难得出我国制药企业通过近三个“五年计划”的技术培育,在国家自然基金、行业基金、973、863、科技重大专项和国际合作等多种基金支持下,已经具备了生产强仿药和原研药的能力。MPP是跨国制药集团应付强制许可、维护自身利益的对冲工具,通过设置许可条件,拥有专利权的国际药业集团利用中国企业的产能,为其生产专供外销出口的抗艾滋病专利药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销售以避免第三世界国家对这些专利药的强制许可。而我国药企生产这些MPP高污染艾滋病原料药物,则承受了高污染附加费、低原料药利润率、降低原始创新积极性等多方面问题。利弊权衡需要广为宣传。
4 结语
虽然我国至今没有因公共健康危机问题实施过一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但是使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现阶段提高我国药物可及性的备用手段。我国在药品强制许可制度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立法、制度建设、普法宣传等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以便当我国面临严重公共危机问题时,能够利用完善的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及时提高药物可及性,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