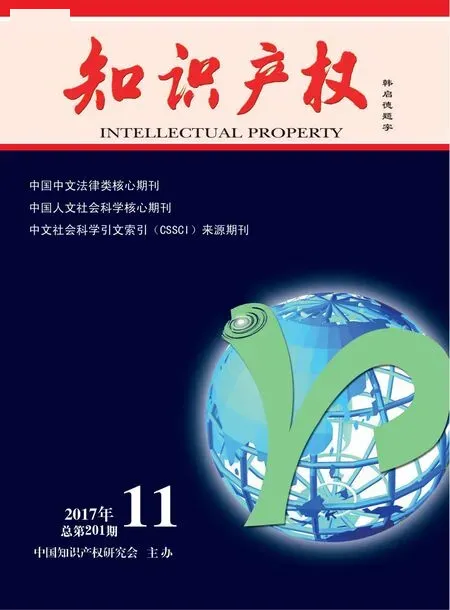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理由和具体方案
2017-01-26王太平
王太平
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理由和具体方案
王太平
“知识化”问题是中国民法典编纂需要回答的“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问题的最重要方面之一。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民法典编纂的趋势、经济新常态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均要求中国民法典“知识化”。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的关键是总则的“知识化”,可以通过将知识产权客体和有体物并列作为权利客体章的一节而提升知识产权客体的地位而实现总则的“知识化”。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的独立成编,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产权不能独立成编的理由不能成立,知识产权编独立成编的具体内容包括合理安排知识产权编在民法典中的位置、知识产权编的具体内容和编排方式。物权、合同、侵权责任、亲属、继承等编的“知识化”是中国民法典“知识化”的重要内容。
知识经济 中国民法典 知识化 知识产权 权利客体
引 言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民法典编纂被列为“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立法”,提出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2015年12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把《民法总则》列为“初次审议的法律案”。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可以说,民法典编纂已经成为我国建立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与步骤,成为立法和研究的重点。
民法典编纂的“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我们编撰的应是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①王利明:《民法典应反映21世纪时代特征》,载《检察日报》2014年12月2日,第3版。因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决定民法典编纂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民法典的基本构造与根本面貌。自新中国编纂民法典以来,除了是否编纂民法典的问题之外,关于编纂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的问题曾发生过一些大的争论,比如究竟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究竟是编纂一部体系化的民法典还是编纂一部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究竟是制定一部传统的民法典还是制定一部绿色的民法典?究竟是制定一部人文主义的民法典还是制定一部物文主义的民法典?这些问题的争论和回答对民法典的基本构造和根本面貌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助于形成一部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的民法典。②就这些问题,尽管某些问题仍然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可以说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
然而,在究竟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上,我国仍然有一个被忽视的重大问题,即民法典充分反映21世纪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问题。由于“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7页。而“民法典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民法典必须反映21世纪的时代特征,彰显21世纪的时代精神,适应21世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正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反映了19世纪风车水磨的农业社会、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反映了20世纪的工业社会一样。④参见王利明:《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7页。21世纪的社会既不是19世纪的农业社会,也不是20世纪的工业社会,而是新型的知识经济社会,不要说早在20世纪末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已经宣布其成员国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即便是尚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都已经初步迈过知识经济的门槛。⑤具体论述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21世纪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要求我们将要编纂的民法典必须能够充分反映知识经济的经济生活条件,即必须是“知识化”的。⑥所谓“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并非要使中国民法典变得更有知识或者包含更多的知识,而是指中国民法典要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具体是指中国民法典各个部分要充分吸纳、包含、融合调整知识关系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而作为民法典的一编固然属于“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的最典型内容,而将知识产权客体纳入民法典总则的权利客体制度,将知识产权作为质权标的、侵权行为的对象、遗产或者夫妻共同财产均为“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的题中之义。然而,当前的民法典编纂却有些忽视知识经济的经济生活条件。2015年4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民法典总则专家建议稿》)的民事权利客体章完全无视21世纪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无视知识财富早已超过物质财富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的客观社会现实,不要说突出作为第一财产权利的知识产权⑦参见刘春田:《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0期,第8页。客体的地位,知识产权客体甚至与性质非常接近的作为物质财产权的物权的客体并列都做不到,而仅仅属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这种做法,不仅将使中国民法典错失成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民法典范式之历史良机,更可能因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而使民法典阻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使编纂中的民法典全面“知识化”,使其充分反映21世纪知识经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国民法典才可能是合格的民法典,才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2017年3月15日最终通过的《民法总则》比《民法典总则专家建议稿》有所进步,其“民事权利”章,将知识产权和人格权、亲属权、物权、债权、继承权并列,拉开了民法典“知识化”的序幕,但民法典的全面“知识化”不应仅限于此,而是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独立成编和民法典其他各编的“知识化”,中国民法典“知识化”的道路仍然遥远,仍需探索。
一、中国民法典“知识化”的必要性
中国民法典之所以有必要“知识化”,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国民法典应该充分反映21世纪知识经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其二,中国民法典应该顺应甚至引领世界民法典编纂的趋势;其三,中国民法典应该为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法律制度支撑和保障。
(一)知识经济的发展与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
由于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⑧王利明:《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6页。因此,民法典是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最集中、最完整的反映和体现。那么,当前我们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又是什么呢?本文认为,种种证据显示,我们当前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可以概括为知识经济。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现在已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⑨Se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1996, http://www.oecd.org/sti/sci-tech/theknowledge-basedeconomy.htm, Retrieved on 5th, May 2016.鉴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当前世界的发达国家早已经在20世纪末进入了知识经济社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1年7月18日科技部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就设定了“科技进步贡献率力争达到55%”的发展目标,而“十二五”末,即2015年底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55.1%,⑩参见董碧娟:《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5.1%》,载《经济日报》2016年2月25日,第5版。我国GDP的55.1%已经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可以说我国经济已经初步迈过知识经济的门槛。[11]许多著名民法学者支持21世纪属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判断。王利明先生认为:“民法典必须反映高科技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同注释④,第8页。)王家福先生认为:“21世纪是高新技术革命实现新的突破,更加迅猛发展的世纪,是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成熟和发展的世纪,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世纪,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达到现代化彼岸的世纪。”(王家福:《21世纪与中国民法的发展》,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第7页。)苏永钦先生认为:“到了世纪末,知识产权代表的价值已有凌驾自然资源之势,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做出“知识产权是私权”的宣告时,各种体系化的努力,包括调和其与民法典的关系,才算拉开序幕。”(苏永钦:《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为中国大陆的民法典工程进一言》,载《交大法学》2010年第1期,第66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苏永钦显然所说的确认“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而不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民法学者对知识产权的知识和理论的把握程度。不只是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在积极谋划着发展知识经济。[12]比如,海湾国家本质上正试图越级直接从采珠捕鱼和贸易经济跃进到知识经济(Martin Hvidt, The State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 the Gulf: Structural and Motivational Challenges, The Muslim World, Vol.105, 2015, p24),而事实上目前这些地区也存在着知识经济,尽管和其他地区相比存在着知识差距。See Samia Satti Osman Mohamed Nour, “Overview of Knowledge Economy in the Arab Region”, 6 J. Knowl Econ. 2015, p903.
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后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区别于以物质和资本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最突出的特点是知识的经济功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知识创造的价值在产品价值构成中占据最大的比重,区别于物质在产品价值中占最大比重的工业和农业经济。[13]参见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1996, http://www.oecd.org/sti/sci-tech/theknowledge-basedeconomy.htm, Retrieved on 5th, May 2016.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经济日益建立于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之上,知识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信息、技术和学习的作用成为经济绩效的新焦点,知识的不断编码化及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传送已经将人类社会带入信息社会,获得各种技能并持续适应这些技能的需要促成了学习经济,知识和技术扩散的重要性要求更好地理解知识网络和国家创新体系。[14]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1996,http://www.oecd.org/sti/sci-tech/theknowledge-basedeconomy.htm, Retrieved on 5th, May 2016.知识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知识、智力和人的创造力等因素,而不是自然资源,知识、智力和人的创造力不仅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在使用中其价值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因此,知识经济有利于改善工业文明带来的能源短缺、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进而实现人类的永续生存与发展。[15]参见高洪深、杨宏志著:《知识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李玉峰、梁正、李建标、高进田著:《知识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知识经济的社会经济条件要求民法典必须反映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突出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集中反映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民法典必须是“知识化”的。
(二)世界民法典编纂的趋势与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
自古罗马以降,近现代的世界民法典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先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成为农业社会的民法典范式,后是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成为工业社会的民法典范式。20世纪的经济发展渐渐使得经济活动不再限于商人而是扩展到全部民事主体,割裂民商事活动的民商分立体制给社会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惑,日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20世纪中叶,意大利、荷兰先后通过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实现了私法统一,解决了民商分立带来的诸多困惑和不便。
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民商分立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均未规定知识产权不同,采用民商合一体制的《意大利民法典》将知识产权包括其中,从而似乎开启了一个知识产权进入民法典的潮流。目前,尽管知识产权进入民法典的模式和规模均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荷兰民法典》《越南民法典》《蒙古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等诸多民法典在起草时均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知识产权似乎已经成为当代民法典编纂的重要内容。
《意大利民法典》是最早涉及知识产权内容的民法典,也是知识产权民法典化模式的一种典型代表。《意大利民法典》第五编“劳动编”分别在第八章“企业体”中规定了商号权(第二节)和商标权(第三节),第九章“对于智能的作品及工业的发明权利”中规定了著作权(第一节)、专利权(第二节)、实用新型权和外观设计权(第三节),第十章“竞业及业务协作的规制”中规定了不正当竞争(第二节)。总体上,《意大利民法典》规定的知识产权种类是比较全面的,[16]鉴于其产生时间,《意大利民法典》也没有规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但《意大利民法典》仅仅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方面的内容,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取得、行使、存续期间等内容均授权特别法另行规定,且其知识产权是夹杂在劳动之中规定的,严格地说并非独立的知识产权编。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同样是较早涉及知识产权内容的民法典,尽管其最终完成立法的时间晚于《意大利民法典》,但从起草思想的萌发来看,其却是最早欲规定知识产权的民法典,也是第一个完全依靠民法典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是知识产权民法典化的另一典型代表。1907年公布的《俄罗斯帝国民法典草案》第三卷第七编和第八编即包含了著作权、发明权、商标权和商号权等有关内容,尽管1922年匆忙制定的《苏俄民法典》没有包括知识产权的内容,但前苏联从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先后完成的4个民法典草案(1940年、1947年、1948年和1951年)均规定了著作权,其中1940年和1951年草案还规定了发明权等工业产权的内容,尽管这些草案均未完成立法程序,最后仅形成1961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以下简称《民事立法纲要》),《民事立法纲要》仍然规定了著作权、发明权、合理化建议和外观设计以及发现权等知识产权的内容。1964年通过的《苏俄民法典》则正式在第四编、第五编和第六编分别规定了著作权、发现权和发明权,知识产权正式进入民法典。1992年俄罗斯开始进行新的民法典编纂,知识产权属于民法典的一部分,2006年最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在第七编“智力活动成果和个性化手段的权利”中全面规定了知识产权。[17]参见张建文:《俄罗斯知识产权与民法典关系的立法史考察》,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2期,第38-40页。与意大利知识产权立法不同的是,《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知识产权不仅是独立一编,而且俄罗斯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全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实现,民法典之外不再制定知识产权特别法,从而实现了知识产权的完全民法典化。
在意大利和俄罗斯开启知识产权民法典化的大门之后,埃塞俄比亚(1960)、荷兰(1992)、蒙古(1994)、越南(1995)等国的民法典纷纷涉及知识产权。[18]当然,1992年最终的《荷兰民法典》并未包括知识产权的内容,其根本原因是和最初设想相比“情况变化很大。一部统一的欧洲专利法正在起草并已部分完成,统一商标法已通过并生效,有关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新法律,情况也是一样。”[荷兰]亚瑟·S·哈特坎普著:《荷兰民法典的修订:1947-1992》,汤欣译、谢立新校,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1期,第65页。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欧洲法的统一,《荷兰民法典》最终会包含独立的知识产权编。不同的是,有些民法典,如《越南民法典》,其全面规定了知识产权,而有些民法典,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蒙古国民法典》,则仅仅部分或者象征性地规定了知识产权。
在这些知识产权民法典化的民法典中,《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和《荷兰民法典》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结构”。因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已经成为除波罗地海三小国以外几乎所有前苏联成员国的民法典的范本;荷兰民法典正在争取成为将来的欧洲民法典的范本,并已实际对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制定产生了广泛影响”。[19]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以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45页。可以说,“知识产权和国际私法被纳入民法典并独立成编,以及把债权总则与债权分则分开的处理,代表了世界性的潮流”。[20]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以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44页。当然,知识产权民法典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1995年《越南民法典》全面规定知识产权内容之后,相关知识产权单行法全部被废除,但却在2005年重新制定了《知识产权法》,2006年《越南民法典》虽仍然包含知识产权的内容,但内容却大大简化,其知识产权保护体制转变为《民法典》和知识产权特别法并存的局面。至少,知识产权民法典化的探索已经成为目前世界各国民法典编纂的重要特征之一,甚至连光荣的《法国民法典》的故乡都已经在探索知识产权成为民法典一编的可能,[2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成立了民法典改革委员会重订法国的民法典,在提出的四种方案中,有一种方案将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称为智力权),有两种方案将知识产权与物权并列而作为一编(参见徐国栋:《〈法国民法典〉模式的传播与变形小史》,载《法学家》2004年第2期,第45页。),尽管最终未能完成立法使命,但法国人本身的探索却给我们以启示,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甚至独立成编已是法国学界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知识化”代表着21世纪民法典编纂的潮流和趋势。尽管这些国家的民法典仅仅涉及知识产权或者将知识产权独立成编,总体上并不涉及民法典其他各编,与本文所述的民法典的“知识化”的内涵存在差异,但知识产权的民法典化仍然是民法典“知识化”的重要内容,而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则是在适应甚至引领这种民法典编纂潮流。
(三)经济新常态、创新型国家建设与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使用新常态概念。2014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用新常态来概括经济形势。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并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强调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2014年12月9日至11日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从九个方面,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成因及发展方向,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央首度详细阐释经济新常态,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生产要素优势、市场竞争、资源环境、风险积累与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与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概括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会议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的研判是: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2日第1版。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九个方面的概括是比较全面的,然而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还必须深刻认识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抓住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矛盾。那么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经济新常态表现为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但是从本质上看,经济新常态则体现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23]参见周跃辉:《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载《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8期,第61页。另有学者指出:“经济新常态的深层次特征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新变化与新特征:动力转换——从依靠资源投入向依靠效率提高转变。旧动力弱化、新动力有待形成。”宋立、郭春丽等著:《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意味着我们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摆脱,意味着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24]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载《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第13页。本文认为,根据经典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最终只能归结为生产力的新发展。而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只有以知识、智力和人的创造力等智力因素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才能够实现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因此,新常态经济的本质就是知识经济,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就是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
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下简称《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见》),指出“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201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央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7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则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是创新,而科技创新又是创新的核心和重中之重。《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九大报告》则继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见》则提出要“坚持全面创新”,即“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科技、管理、品牌、组织、商业模式创新,统筹推进军民融合创新,统筹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合作创新,实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开放创新的有机统一和协同发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更为明确地指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抓创新首先要抓科技创新,补短板首先要补科技创新的短板”。
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因素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知识、教育、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则强调科技创新在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因素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一致的。因此,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也只有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知识产权制度是调整知识关系的法律制度,对于知识活动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见》,还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均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说,知识产权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因素与环节,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法律保障。由于民法典是对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集中反映,是民事立法的最高级形式,民法典的“知识化”将会提升知识产权的地位,全面扩大知识产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为经济新常态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中国民法典“知识化”的关键:民法典总则的“知识化”
尽管在中国民法典编纂中,设立总则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学界也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由于“总则的设立避免了各个分则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提供了更为清晰、简明的民事法律规则,增加了法典的逻辑性和体系性,进一步促进了民法法典化的科学性”,[25]王利明著:《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页。目前不仅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总则肯定论”取得了压倒性优势,[26]参见温世扬:《略论民法典总则的内容构造》,载《时代法学》2012年第1期,第3页。《民法总则》的通过已经将“总则肯定论”变成立法现实。由于其“提纲挈领”的地位和作用,民法典总则对民法典分则具有统领性的作用,它不仅“为法典分则各部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联系纽带”,使民法典的“各部分形成一个逻辑体系”,[27]王利明著:《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页。对民法典分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民法典分则的基本框架。[28]尹田教授认为:“民法典总则更像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和一个纲领。总则的规范不仅是各种具体制度的渊源,而且是链接具体规则的粘合剂和协调其相互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平衡器。”尹田:《民法典制定的机遇与挑战》,载《法制日报》2011年5月11日,第011版。房绍坤教授认为:“总则是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式从民事法律制度中抽象出来的共同规则,具有直接适用性,对分则具有统率作用。”房绍坤:《关于民法典总则立法的几点思考》,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第8页。因此,总则是民法典“知识化”的关键,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必须自民法典总则开始。
(一)民法典总则对民法典构造的决定性作用及其逻辑
在设立总则的情况下,民法典总则对于民法典的构造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主要取决于民法典构造的“法律关系”方法。就民法典的构造方法来看,尽管我国在民法典编纂讨论中就民法典的构造方法上存在着“意思表示说”“民事权利说”和“法律关系说”等多种学说,但由于“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是构建民法规范的逻辑性和体系性的基础”,“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揭示了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方法”,“法律关系正是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它将民事主体、客体、行为、各种民事权利等诸要素整合为一体,形成清晰的脉络”,民法典应该依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造其体系。[29]参见王利明著:《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248页。民法典构造的“法律关系”说不仅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在我国也已经具有相当的学理传统基础,无论是民法教科书还是大学的民法教学,法律关系说均已成为构造民法体系的基本的逻辑概念工具。而具体到民法典的制定,“法律关系说”也已经成为我国民法典构造方法的主导学说,[30]除前引的王利明先生的观点之外,梁慧星先生的观点参见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7-8页。另参见李永军:《民法典总则的立法技术及由此决定的内容思考》,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第1页;屈茂辉、李龙:《论民法典总则的功能及体系》,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2期,第60页。法律关系成为构造我国民法典的主要方法与工具。
民事法律关系构造民法典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民事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以及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主要工具——行为,民法典的内容就是由民事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构成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同要素的具体安排最终形成了民法典的结构,包括民法典总则与分则的“总+分”结构、民法典总则的结构和民法典分则的结构。民法典总则是从各种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提取公因式而来的,所提取的内容是民事法律关系要素中除内容即权利之外的其他要素,主要包括主体、客体、法律行为和民事责任等内容。民法典分则是各种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无法被提取公因式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组成的,主要是各种具体的民事权利。总则和分则的分立构成了民法典整体的“总+分”结构,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法律行为、法律责任等构成了民法典的总则,而法律关系的内容即各种民事权利则构成了民法典的分则。民法典总则和分则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总+分”结构的民法典,当分则中所规定的人格权、物权、债权、亲属权、继承权等权利与主体、客体结合时,就分别形成了相应的人格权、物权、债权、亲属权、继承权等具体民事法律关系。可以说,民事法律关系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民法典,科学而富有逻辑地将民法典各个部分有机地连接在一起。[31]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的立法思路》,载《求是学刊》2015年第5期,第80页。我国学者多认为民法典总则应该包括权利客体制度。王利明、梁慧星领衔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均设置了总则,而且权利客体均为总则的内容,徐国栋领衔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尽管没有设置总则编,但仍然在序编规定了权利客体。另参见杨立新:《民法·总则编的框架设计及应当规定的主要问题》,载《法制日报》2015年5月13日,第009版;李永军:《民法典总则的立法技术及由此决定的内容思考》,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第6页;温世扬:《略论民法典总则的内容构造》,载《时代法学》2012年第1期,第5页,等等。
民法典构造的上述法律关系方法不仅决定了上述民法典的整体框架和基本面貌,而且也意味着民法典总则对民法典分则构造的决定性影响。[32]有学者认为,“虽然说,民法典之‘总则’的内容是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从各编中抽象出来的,但这种立法技术同时也影响着民法典的编排(分编)。”李永军:《民法典总则的立法技术及由此决定的内容思考》,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第4页。如前所述,民法典总则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法律行为和民事责任,而民法典分则的内容则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那么,是民法典总则的什么内容决定性地影响着民法典分则的结构呢?本文认为,决定民法典分则构造的民法典总则的具体内容是权利客体制度,因为民事权利客体的类型和体系是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和体系的根本因素,而法律关系的类型和体系则是决定民事法律制度的类型和体系的根本因素。一方面,客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支点,没有客体,主体的权利义务就丧失了客观依据,成了空中楼阁;而且客体不同,也往往会使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发生变化。[33]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权利客体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权利类型(即法律关系类型),权利客体是权利类型的基础。[34]参见李永军:《民法典总则的立法技术及由此决定的内容思考》,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第6页。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最终又形成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进而形成整个法体系。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区分是法体系区分的基础,法体系围绕着法律关系而展开,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构造决定了民事法律制度的体系构造。[35]参见朱虎:《萨维尼法律关系理论研究——以私法体系方法作为观察重点》,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第121页。
总的来说,正是民法典总则中的民事权利客体成为了民法典总则和分则联系的连接点,民法典总则规定的权利客体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事权利的类型,决定了民法典分则的构造,而民法典总则中的权利客体的具体类型和内容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法典总则应该和民法典分则的哪个具体部分相结合而形成相应的具体法律关系。当然,本文并不认为民法典总则中的权利客体的类型和体系与民法典分则的结构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因为民法典分则的结构除了受到权利客体的类型和体系决定性影响之外,还会受到立法传统、法典编纂的具体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二)民法典总则“知识化”的关键与具体内容
从民法典总则对民法典构造的决定性作用及其逻辑来看,决定民法典分则的主要是民法典总则的权利客体制度。因此,民法典总则“知识化”的关键是权利客体制度的“知识化”。
从涉及知识产权的世界各国民法典来看,《意大利民法典》《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均没有设置总则,《越南民法典》虽设置了总则,但总则中并不包含权利客体内容,包含权利客体内容的是《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和《蒙古国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一编第三分编规定了“民事权利的客体”,其中第128条规定了“民事权利客体的种类”,是民事权利客体的总括性的规定,“信息”和“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均属于民事权利客体的种类之一,第138条和第139条分别进一步详细规定了“知识产权”和“职务秘密和商业秘密”。可以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中权利客体制度中规定的知识产权客体为第七编“智力活动成果和个别化手段的权利”提供了支点以及与民法典总则的连接点,使得其第七编“智力活动成果和个别化手段的权利”变得顺理成章。《蒙古国民法典》总则[36]本文以下关于《蒙古国民法典》的条文均引自LAW OF MONGOLIA:CIVIL CODE(January 10, 2002),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 le_id=183496, Retrieved on May 23th, 2016.尽管没有规定单独的权利客体制度,但在总则第8条“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根据”中规定了“智力价值的创作”,同时在所有权编第83条规定了“财产/资产”,其中包括“智力价值”。基本上可以说,《蒙古国民法典》在知识产权客体和知识产权的规定模式上类似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不同的是,《蒙古国民法典》采用的是一种我国学者所称的“糅合式体例”,[37]曹新明:《知识产权与民法典连接模式之选择——以〈知识产权法典〉的编纂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第30页。即将知识产权客体包含进传统所有权客体之中,而将知识产权内容融入传统所有权之中,其第98条规定“本法第89-94条的相关条款适用于获得智力价值和权利的占有”,明确将所有权的规则适用于知识产权客体。总的来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和《蒙古国民法典》在权利客体中规定的知识产权客体制度为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提供了一个连接点,不管是采用整体单独纳入民法典的方式,还是采用糅合式的方式。[38]2015年4月20日,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组织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在第五章规定了“民事权利客体”,该章分三节规定了民事权利客体,第一节为“物”,第二节为“有价证券”,第三节为“其他民事权利客体。”其中“其他民事权利客体”节分别规定了“人身利益”“智力成果、商业标记和信息”“财产权利”“企业财产”等其他民事权利客体。从《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来看,其民事权利客体制度完全是“非知识化”的,固执地坚守工业社会物质财产的中心地位。这种“非知识化”的民事权利客体制度完全不能反映社会经济中知识的地位早已超过物质财产的知识经济的“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不符合世界民法典编篡的趋势,不能满足当前我国经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的需要,完全是一个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民事权利客体制度。2016年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民法总则》(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的第五章“民事权利客体”一章为“民事权利”一章替代,经过三次审议后,《民法总则》于2017年3月15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最终的《民法总则》延续了“民事权利”章的安排,条文数由最初草案的14个猛增至26个。尽管《民法总则》的做法延续了《民法通则》的做法,基本符合“提取公因式”和“规范性”的立法技术要求,但却也缺乏民事权利客体等内容,所规定的债的简单规定也无法替代债法总则。(参见李永军:《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评述》,载《法学家》2016年第5期,第59页。)本文认为,这种机械延续《民法通则》的做法,不仅本身体系混乱,详略失当,而且与分则叠床架屋,导致民法典体系混乱,远不如《征求意见稿》的体系安排,是不足以采用的。
要实现民法典总则的民事权利客体制度的“知识化”就必须提高知识产权客体在民事权利客体中的地位。本文认为,可以考虑的方案是将知识产权客体作为民法典总则民事权利客体章中的独立一节,节名为“知识产权客体”,具体可以考虑设置三个条文,分别规定创造性智力成果、识别性工商业标志、识别性信息等。鉴于知识产权客体发挥作用时对物权客体的依赖作用,“知识产权客体”节可以考虑置于“物”节之后。[39]当然,《征求意见稿》的民事权利客体制度至少还有三大问题:缺乏民事权利客体通则的规定;对人身利益的地位不够重视;没有规定债权客体。当然,这些问题非本文主题,此处不赘。
三、中国民法典“知识化”的核心:知识产权独立成编
中国民法典“知识化”的最重要方面无疑是知识产权成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尽管我国几乎所有学者均认为民法典应该反映知识经济的社会特征从而应该包括知识产权的内容,然而除了少数学者之外,包括知识产权学者在内的多数学者均反对知识产权整体纳入民法典。但事实上,学者已经提出的反对知识产权整体纳入民法典的理由均是不成立的。[40]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将“反对编篡民法典”的理由和“反对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的理由混为一谈,以“反对编篡民法典”的理由“反对知识产权独立成编”。显然,其逻辑是不严密的,因为既然“反对编篡民法典”,讨论知识产权是否独立成编岂不多此一举?相反,民法典内容上的全面性、创立世界民法典的新范式的需要以及提升知识产权地位和教育全民族的需要成为知识产权整体纳入民法典的有力理由。
(一)知识产权不能独立成编的理由及批驳
大多数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不能独立成编,其理由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但本文认为,这三个方面均不能成立:
第一,知识产权的特殊性。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有适用与不适用传统民法一般原则的两个方面”或“特有的两面性”,多数情况适用民法一般原则,但也有不少重要场合不适用一般民法原则。[41]参见郑成思:《民法典(专家意见稿)知识产权篇第一章逐条论述》,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308页。另参见崔建远:《知识产权之于民法典》,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1期,第88页。就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尽管不乏支持者,但反对者也不少。多数学者均承认,知识产权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42]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第53页。因为“除了权利客体非为有体物之外,无形产权在许多基本的方面与所有权并无不同”,“作为规范无形财产之支配、利用关系的法律,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无形产权法与规范有形财产归属关系的物权法并无本质区别”,“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无形产权应当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43]尹田:《论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关系》,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5期,第14、16页。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性质取决于它所反映和调整的社会关系,知识产权所反映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因而知识产权具备了民事权利的最本质的特征,仅仅是民事财产权利的一种类型,与传统的民事财产权利没有本质区别,是与物权属于同一逻辑层次、同等重要的民事财产权。[44]参见刘春田:《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0期,第4页。
第二,知识产权法具有变动性或不稳定性。这种理由认为知识产权法涉及政策、科技发展和国际协调,修改频繁,稳定性不如传统民法。然而,当我们认真分析而不是想当然想象的时候就会发现,与传统民法相比,知识产权的修改次数并不比传统民法频繁,甚至修改幅度更小。以传统民法学者最为推崇的《德国民法典》为例,自1900年1月1日颁行至1998年6月29日,98.5年中《德国民法典》共修改141次,平均每年修订1.43次。[45]参见《德国民法典》,郑冲、贾红梅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的话”,第1页。而21世纪以来,《德国民法典》的修改甚至更为频繁,自2005年3月1日至2010年1月1日不到58个月的时间里,德国立法者已经通过31部新的法律(外加联邦宪法法院的一个裁定),修正、增加和废止了《德国民法典》的诸多条文,涉及的条、款、项、句达700余处。[46]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版前言”,第1页。由于《德国民法典》共达2385个条文,仅仅修改次数或者具体修改条文数尚不足以客观反映其修改的频繁程度,因此,本文以每年的修改比例来客观反映其修改的频繁程度,具体算法是修改条文数除以原条文数再除以修改时间,以此计算,《德国民法典》平均每年修改条文占比5.87%。以我国修改次数最多的知识产权法——《商标法》的修改作为对比,1982年《商标法》(8月23日通过)共42条,1993年共修改9条,1993年修改后的《商标法》共43条,2001年共修改47条,2001年修改后的《商标法》共64条,2013年共修改53条。自1982年8月23日制定至2013年8月30日最新修改历时31年,各次修改前《商标法》原条文共计149条,3次修改共计修改109条,平均每年修改比例仅为2.36%。[47]本文采用的《商标法》3次修改条文数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相应修改决定。精确计算表明,我国《商标法》修改的频繁程度比不上《德国民法典》,其甚至不到《德国民法典》的一半。
第三,知识产权法具有综合性,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相对单一性。[48]第二、第三点均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设想》,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第6页;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第53页;崔建远:《知识产权之于民法典》,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1期,第88页。事实上,传统民法早已不纯粹、不单一,“20世纪的民法典在体系化上碰到的最大困难,应该是反映国家管制和私人自治间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公与私的规范明显纠缠不清”。[49]苏永钦:《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为中国大陆的民法典工程进一言》,载《交大法学》2010年第1期,第62页。事实上,随着《TRIPS协议》明确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知识产权的授权观念和垄断观念均日益弱化,知识产权已经成为较为纯粹的民事权利。即便是专利法、商标法中的权利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其性质上和物权法中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并无本质区别。知识产权法本质上并非什么综合性的法律,而是地地道道的私法。
(二)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的理由
本文认为,除了前述的中国民法典“知识化”的理由之外,知识产权独立成为民法典一编的主要理由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民法典内容上的全面性要求知识产权独立成编。民法典是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最集中的反映,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民法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内容上的全面性”,即“将同一领域同一性质的法律规范,按照某种内在的结构和秩序整合在一起,能够覆盖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对市民社会中需要法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能够提供基本的法律规则”。[50]王利明著:《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页。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知识关系显然已经成为市民社会中需要法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不仅需要设立知识产权法来进行调整,而且需要将知识产权整体纳入民法典而成为民法典的一编进行调整。不然的话,民法典就不能充分反映知识经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丧失其“内容上的全面性”,成为名不副实的民法典。
第二,创立世界民法典的新范式的需要。尽管目前前述的“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尚“并非范式”,[51]吴汉东:《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50-53页。但这些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民法典化的探索却是客观存在的。更何况,“‘范式’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论我们在哪个领域使用‘范式’这个概念都必须与‘范式’的转换联系在一起,都必须将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作为这一领域发展的关节点、‘革命’的标志。”[52]朱爱军:《论库恩的范式概念及其借用》,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第52页。也就是说,范式本身即蕴涵着自我否定的基因,最终被打破是其必然命运,不包含知识产权内容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虽然分别成为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民法典范式,但知识经济的到来已经产生范式突破的例外因素——知识产权的民法典化,《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均不足以担当21世纪民法典范式的重任,“知识化”的民法典最终必将成为知识经济的范式民法典,而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的民法典是知识产权民法典化最彻底的“知识化”的民法典,当是21世纪范式民法典的不二之选。
第三,知识产权独立成编是提升知识产权地位和教育全民族的需要。尽管目前中国早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目前知识产权仍属“小众”事业,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仍然有待提高。民法典制定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作为全民族的教科书”,[53]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4页。教育全民族,没有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的中国民法典是一部遗漏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最重要方面的民法典,不配作为全民族的教科书,无法教育全民族,尤其无法满足国家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相反,一部包含了知识产权编的民法典不仅有助于提升知识产权的地位,而且有助于教育全民族,提升全民族的知识产权意识,有利于促进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三)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的具体方案
知识产权独立成编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民法典知识产权编的位置安排。就知识产权编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安排来说,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将知识产权编作为最后一编,置于国际私法编之后,而《越南民法典》则将知识产权编置于合同性质的“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之后、国际私法性质的“涉外民事关系”之前。我国赞成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的学者多认为,知识产权应该置于物权编之后和债权编之前。[54]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将知识产权编置于第五分编“物权法”之后第七分编“债法总则”之前(参见徐国栋著:《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版),易继明教授主张民法典为九编制,知识产权编置于“物权法”之后,“合同法”之前(参见易继明:《历史视域中的私法统一与民法典的未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38页)。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采纳。这里补充如下两点理由:其一,知识产权和物权的性质非常接近。以最早在民法典中设立物权编的德国为例,德国存在着不同于物权的对物权的概念,对物权是特定的人对包括有体物、无体物和其他具有财产意义的物等的广义的物的直接支配的权利。物权、知识产权均是对物权的一种,性质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德国许多人把物权法的原理应用于工业产权的解释和实践。[55]参见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其二,物权相对于知识产权的基础性。物权相对于知识产权的基础性体现在:首先,尽管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重要性的确已经超过了物权客体的有体物而具有支配性的地位,知识产权已经超越物权而成为“第一财产权利”,[56]刘春田:《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0期。然而相对于知识产权来说,物权仍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其次,知识产权发挥作用多依赖于物权。知识产权的客体为知识,知识对人类当然是有用的,但精神性的知识并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的生理需要,知识要满足人类的生理需要必须要通过有体物的中介。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发挥作用多需要依赖于物权。第三,物权的规则比知识产权的规则更为成熟。物权自遥远的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而知识产权只不过近代的产物,只具有非常短暂的历史。因此,物权的规则比知识产权的规则要成熟得多,可以供知识产权制度借鉴。因此,尽管知识产权已经是第一财产权利,知识产权编和物权编并列而置于物权编之后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第二,民法典知识产权编的实质内容。民法典知识产权编到底包含哪些实质内容?是将原先各知识产权法律的相关规定全部移入民法典吗?本文认为,为了确保民法典作为私法的纯粹性,只应该将现行知识产权法律中的相关民事实体法的内容规定进民法典,而将知识产权法律中的程序性的行政规定[57]尽管知识产权法律中有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事实上没有实质意义,仍需借助《刑法》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相关知识产权法律中完全可以不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置于民法典之外,或者制定相应的单行法,或者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同时,即便是知识产权民事实体法的内容也并非全部规定于民法典知识产权编,正如本文第五部分所述,知识产权合同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内容将分别规定于民法典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其余的内容才规定于民法典知识产权编。和民法典物权编一样,这样规定可以确保民法典知识产权编仅仅包含绝对权性质的内容,相对权性质的内容则规定于民法典相应各编,维持了德国民法典传统的绝对权与相对权的二元结构[58]当然,传统民法典的绝对权与相对权主要是物权与债权的二元结构。参见胡波:《中国民法典编纂体例之我见——以绝对权与相对权的二元结构为中心》,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7期,第132页。的构造逻辑。
第三,民法典知识产权编的结构。民法典知识产权编究竟是按照权利客体、权利内容、权利归属、权利限制、权利保护的模式来安排结构还是仍然按照传统的权利类型来安排结构?本文认为,尽管前一种模式在形式上更为体系化,更符合传统民法典的风格,但因各种知识产权的个性及其法律制度的特殊性,不宜为了追求形式上的体系化而彻底打乱传统知识产权法律的构造,而是可以借鉴物权立法的模式,按照总则、著作权、专利权及相关技术成果权、商标及其他商业标志权、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模式来安排知识产权编的结构,既可以通过总则规定诸如法律原则、权利冲突等知识产权法的一般问题,促使知识产权法律适度体系化,又可以保持传统知识产权原有的法律构造与逻辑,保持知识产权法律的稳定性、延续性。
四、中国民法典“知识化”的重要内容:民法典其他各编的“知识化”改造
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不只是总则的“知识化”和知识产权的独立成编,由于民法典的物权、合同、侵权责任、亲属、继承等其他各编均或多或少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因此,民法典的这些编同样也要进行“知识化”改造。
(一)中国民法典物权编的“知识化”改造
民法典物权编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质权,我国现行《物权法》将来基本上会转变为民法典物权编,然而从现行《物权法》来看,尽管其规定了知识产权质权,但其知识产权质权事实上却完全是传统动产质权模式下的规定,是“非知识化”的,不符合知识产权的特点,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
《物权法》第227条第2款前半段规定:“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对比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的相应规定可以看出物权法规定的“非知识化”。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39条规定:“以著作财产权为质权之标的物者,除设定时另有约定外,著作财产权人得行使其著作财产权。”[59]其他国家也有许多类似规定,参见《日本著作权法》第66条、《日本商标法》第34条、《日本专利法》第95条和第96条、《韩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2款等。在我国,尽管按照一般理解,知识产权出质之后,“出质人仍可继续使用知识产权,”[60]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66页。但除非另有约定,出质人是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的,这与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财产权人行使其著作财产权是很不相同的,因为其出质人除了自己使用其知识产权之外,尚可以径行转让或者许可其知识产权,而无需特别约定。要知道,知识产权与物权最大的区别就是其时间性,即知识产权均是有期限限制的,且很多情况下知识产权的实现并不是靠自己使用知识产权而进行的,而是通过转让或者许可的方式来进行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作为权利人的出质人并无能力自行使用知识产权。比如在我国,不通过出版社,个人的著作权基本上是无法通过自行使用而实现的。因此,法律将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完全是传统动产质权的强调留置效果的观念的产物,不符合知识产权本身的特点,不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是“非知识化”的。事实上,知识产权质权在性质上更接近于抵押权,因为权利质权人与抵押权人一样只是取得了对标的物的法律上的控制力。[61]参见王利明、程啸、尹飞著:《中国物权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22页。同时,由于质权的物上代位性和我国物权法对知识产权采用的严格的登记生效要件主义的权利变动原则,质权人的权益是能够得到保障的,物权法完全没有必要限制出质人转让和许可知识产权的权利。
只有民法典物权编的知识产权质权制度“知识化”,未来民法典物权编才能是“知识化”的。具体来说,未来的民法典物权编应将《物权法》第227条第2款前半段修改为:“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后,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由出质人行使,除非设定质权时有特别规定。”
(二)中国民法典合同编的“知识化”改造
现行《合同法》在第十八章规定了“技术合同”,共规定了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等四种合同,其中技术转让合同又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法上的主要合同类型基本上已经为合同法所包含,相反专利法则没有详细规定专利合同的内容。由于现行合同法的大多数内容将来会成为民法典合同编的内容,因此可以说,中国民法典的合同编已经是部分“知识化”的,只是尚没有规定著作权、商标权等合同的内容而已。要实现中国民法典合同编的全部“知识化”,所需要做的工作无非是将现行几大知识产权法律中的著作权、商标权等合同的内容规定进未来民法典的合同编之中。
那么,民法典合同编到底应该如何具体规定知识产权合同呢?本文认为,应该单设知识产权合同章规定知识产权有关的合同,合同法中原先规定的与技术有关的知识产权合同和新进入民法典合同法编的著作权、商标权等合同均应在知识产权章进行规定,而除去与专利和商业秘密有关的知识产权合同之后的其他技术合同仍然规定为技术合同章。理由包括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合同性质的考虑。合同法规定的各种技术合同尽管因均与技术相关而被称为技术合同,但是各种技术合同的性质差异还是相当大的。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开发合同属于提供工作或者服务的合同,合作开发合同属于双方共同提供工作或者服务的合同,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和商业秘密转让合同类似于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类似于转移标的物使用权的合同,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则属于提供服务的合同。因此,合同法将这些与技术有关的合同统称为技术合同而进行规定固然有其道理,但逻辑上却也并非无懈可击,尤其是技术转让合同与其他类型的技术合同在性质上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将与专利和商业秘密有关的技术转让合同从技术合同章分离出来而规定在知识产权章逻辑上更为合理。其二,合同条文规模的要求。现行合同法的技术合同章的条文数较多,仅仅少于作为合同法分则的总则[62]《合同法》第174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关于该条的深入研究参见易军:《买卖合同之规定准用于其他有偿合同》,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88页。的买卖合同章,将性质有较大差异的著作权、商标权等合同规定在技术合同章势必会使得技术合同章条文数进一步增多,破坏民法典合同编的美感。
鉴于知识产权合同主要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合同,民法典合同编的知识产权合同章可以考虑规定于融资租赁合同章之后承揽合同章之前,而技术合同则可以考虑置于原处,因为在性质上技术合同和前后的运输合同和保管合同均是提供工作或者服务的合同。
(三)中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知识化”改造
现行侵权责任法已经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规定为受到保护的民事权益,可以说,侵权责任法已经是“知识化”的。侵权责任法规定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这种方式和规定侵犯物权的责任的方式类似,但不同的是,由于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因此,将来编纂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应该强化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规定,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应该成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独立一章,进一步提高其“知识化”程度。
从其规定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方式来看,现行侵权责任法显然是将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定性为一般侵权责任的。然而,作为一种新型的侵权责任类型,侵权责任法对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一般侵权责任的定位与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状况并不一致。从世界各国传统民法来看,不管是涉及知识产权的民法典还是不涉及知识产权的民法典,民法典的债编通常不规定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并不能简单地归属于一般侵权责任。而在英美法系,商标、专利、著作权侵权通常使用“infringement”一词,不同于传统侵权行为法的“torts”一词,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同样不能简单地归属于任何种类的传统侵权责任。从世界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来看,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基本上区分停止侵权与损害赔偿两类责任(救济),其中大陆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不仅较明确地区分两种类型的责任,而且对不同类型的责任规定不同的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责任需要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要件,而停止侵害责任则不需要主观要件。[63]参见《德国著作权法》(2009)第97条第1款、第2款;《德国商标和其他标志保护法》(1996)第14条第5款、第6款;《德国专利法》(1994)第139条第1款、第2款;《日本著作权法》第112条第1款、第114条;《日本商标法》第36条、第38条;《日本专利法》第100条、第102条。英美法系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定同样区分两种类型的救济(责任),对于禁令救济完全不需要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要件,[64]如《美国专利法》第283条、《美国著作权法》第502条第《A》款、《美国兰哈姆法》第34条。而对于损害赔偿救济是否需要故意或者过失条件,其法律规定并不明确,但通常似乎会考虑到主观方面。[65]如《美国专利法》第284条、《美国著作权法》第504条、《美国兰哈姆法》第32条第1款。美国法这些规定没有明确损害赔偿救济是否需要故意或者过失要件,但事实上考虑了主观方面,如《美国专利法》第287条规定了专利权人在其专利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专利”字样的义务,如果专利权人未正确履行义务则不能得到损害赔偿金。《美国著作权法》第504条第3款第2项规定,如果侵犯著作权是故意的则可增加法定损害赔偿金,反之则可减少。第405条第2款规定,侵犯遗漏了版权标记的无恶意侵权人不承担损失赔偿的责任。《美国兰哈姆法》则不但规定了对故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而且规定,商标权人在使用商标时,如果正确加注了诸如®、TM和SM等标志,则将有助于确定侵权行为的故意动机。参见伦纳德·S·杜博夫著:《艺术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还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多采用推定的方式确定被告的主观状态,[66]比如,在德国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原告不必证明被告的行为是过失还是故意,因为被告有举证责任,以表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参见迪茨:《著作权问答》,高琳、何育红、高思译,许超校,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四辑),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因此,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事实上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67]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均规定有停止侵权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然而,无论是停止侵害还是损害赔偿,法律均没有规定类似于德国和日本知识产权法律的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要件,而只是在帮助侵权(《商标法》第57条第6项)、善意销售(《著作权法》第53条、《专利法》第70条、《商标法》第64条第2款)等侵权的例外情况才涉及被告的主观方面,除此之外,几乎只要判决侵权成立,被告就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行为的成立和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几乎等同。因此,可以说,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更接近于无过错责任。
正由于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必要设专章规定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而不是仅仅作为一般侵权责任而不作特别规定。由于按照本文设想知识产权将成为民法典的单独一编,类似于物权请求权的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可以规定于知识产权编,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仅仅规定债权请求权性质的损害赔偿等责任即可。当然,鉴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构成的特殊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也应当一并在侵权责任编规定。
(四)中国民法典亲属编的“知识化”改造
民法典亲属编调整的主要是亲属关系,尽管亲属法立法内容的重心日益向重视财产法转变以及日益借助财产法的调整方法的发展趋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亲属法的基本属性,[68]参见余能斌、夏利芬:《试论亲属法的基本属性——兼谈亲属法应否从民法典中独立》,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138页。但亲属法立法内容和调整方法的这种发展趋势却日益提高了财产关系在亲属法中的地位,财产关系成为亲属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今天,知识和知识产权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不仅在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中知识资产已经成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一些家庭的财产中也已经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比如,第十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于2016年3月22日发布,作家江南以3200万元荣登榜首,雷欧幻像和郑渊洁分别以2000万元、1900万元位列第二、第三名。[69]参见段思平:《“作家富豪榜”浮华背后的冷思考》,载《中国商报》2016年03月25日,第2版。与企业家排行榜中的企业家的收入相比,这些收入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作为家庭收入,这些收入是不容忽视的。作家收入的来源主要是作品和著作权。根据我国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只有这些作家已经得到的版税收入甚至已经签订使用许可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版税收入可以成为这些作家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家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国婚姻家庭法的这种规定显然是“非知识化”的,不仅完全无视知识经济发展的现实,也与世界各国婚姻家庭法的发展趋势不符。[70]研究表明:“目前,在夫妻一方婚后所得财产性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上,法定共同财产制(包括迟延共同制)各国立法趋势是由夫妻共同享有。”张学军:《论夫妻一方婚后所得财产性知识产权的归属》,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43页。
我国未来民法典亲属编的“知识化”需要从夫妻财产制度着手,具体而言就是将财产性的知识产权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另外,为了使民法典亲属编的夫妻财产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创新的目标相协调,可以规定,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知识产权的分割应当适当向知识产权创造人倾斜,以激励知识产权创造人创造的积极性。
(五)中国民法典继承编的“知识化”改造
继承法“实为财产法与亲属关系之融合”,“为亲属关系上之财产法,”[71]史尚宽著:《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因此,作为财产的知识产权在继承法上的地位几乎毫无疑问,世界各国法律或者在继承法中或者在知识产权法律中规定了知识产权的继承问题。我国继承法同样承认知识产权的遗产地位,“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属于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的范围。尽管继承法只列举了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作为遗产,但从立法精神上看,实际上应当包括各种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商标专用权、公民的发现权、发明权、科技进步权、合理化建议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均可以作为遗产。[72]参见彭诚信著:《继承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因此,可以说我国继承法,即将来民法典继承编实质上已经是“知识化”的。当然,鉴于继承法规定的知识产权种类的不完全性,如果未来民法典继承编仍然采用列举式方式[73]诸多学者认为继承法或者民法典继承编不应该采用列举方式,而是应采用概括方式规定遗产。参见张玉敏著:《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郭明瑞:《民法典编纂中继承法的修订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第89页。来规定遗产的话,有必要将商标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知识产权明确规定为遗产。
结 语
诚如学者所言,“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的问题的确是民法典编纂的首当其冲的问题。自新中国民法典编纂伊始至今,关于“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已经经过了几场较大的争论,有些争论仍在持续,有些争论则已经有了基本明确的结论。不过,与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相比,那些所谓的重大的争论却难言重大、其实难副: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问题早已经是世界立法趋势解决了的问题,少数商法学者的呼吁似乎难以影响大局;民法典的绿色化观念的提出不过是环境危机之下的应时之举,虽会影响民法典的风貌,但却很难对民法典的根本构造形成什么影响;松散式、汇编式民法典与体系化民法典之争实质上是要不要编纂民法典的问题,松散式、汇编式民法典根本不是什么民法典,其实质是否定编纂民法典的必要性,这种观点在我国未曾成为主流,将来也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即便这些问题对民法典的未来风貌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却也难言根本。
民法典的“知识化”问题则不同,该问题本质上是民法典反映知识经济的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问题,关系到知识经济时代的范式民法典的形成。与《法国民法典》成为风车水磨的农业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以及《德国民法典》成为机器大工业的工业社会的范式民法典类似,民法典的“知识化”意味着民法典的基本风貌和基本构造的根本性改变,民法典不仅将新增《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所缺的独立的知识产权编,总则、物权、合同、侵权责任、亲属、继承等其他各编也将打上知识经济的烙印而充分“知识化”,民法典将是“知识化”的,而不是像《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那样的“物化”的,“知识化”的民法典或将成为知识、信息、数据、网络的知识经济社会的范式民法典。民法典不是儿戏,不是法学家的一己之私,因此,我们不应为范式而范式。当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呼唤的时候,当时代将历史的重任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迎难而上,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为我们的民族铸造新时代的民法典,为21世纪建立民法典新范式。
How to deal with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s an unavoidable question regard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To make IPR an independent part of Chinese Civil Code is a unanimous requirem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general trend in global civil law code compilation, new normal economics, and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The papers suggests that the general rules of Chinese Civil Code should obviously refl ect the importance of IPR, which can be achieved by juxtaposing the objects of IPR and the tangible things under the section of “object of right”. The core of a Civil Code featured by IPR lies in the existence of Independent IPR part. The opinion that IPR can’t be an independent part is not reasonably justifi ed. The detailed proposal for making IPR an independent part of the Civil Code includes: reasonably locate IPR in the Civil Law Code, the specifi c content of IPR, and the scientifi c arrangement of the IPR content.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Chinese Civil Code to also refl ect IPR in the content of property, contract, torts, succession etc.
knowledge economy;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featured by IP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objects of rights
王太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华南国际知识产权研究院研究员、“国际知识产权法制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