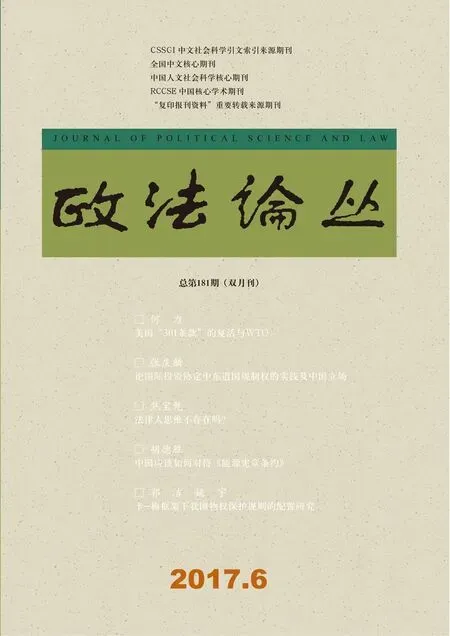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
2017-01-26张庆麟
张庆麟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430072)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
张庆麟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430072)
保护外国投资一直是国际投资协定的价值追求与主要内容。随着晚近以来国际投资协定日益丰富,尤其是投资仲裁案件的不断增多,外国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协定挑战东道国规制权的现象也日渐凸显。因此,在国际投资协定的条约实践中有关东道国规制权的内容也逐渐增加,其突出体现于国际投资协定的序言、征收条款、例外条款和程序条款之中。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对于晚近在协定中增设规制权的做法应当仍予以支持,同时,不必主张所谓的“身份”混同而有所不同。
国际投资协定 规制权 投资仲裁(ISDS)
保护外国投资一直是国际投资协定的价值取向与主要内容。然而,晚近国际投资协定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增设专门条款或在原有条款中加入维护东道国规制权的内容。
“规制权”这一概念,应该来自于英美法,并且也不是较为严格的法律术语。其含义大致为“国家寻求指导或者鼓励那些如果没有国家干预就不会发生的经济活动,其目标是纠正市场失灵以满足集体或公众的利益。”[1]P2对于政府的这类行为,德国通常在其经济行政法、法国依其经济公法来予以规范与调整。在英美没有相对应的法律,学者们为了便于研究,笼统的以“规制”或者“规制法律”等“公认但并不精确的词汇来填补空缺”。[1]P2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规制权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所围绕的权利有着客观的国内法基础,无须依赖贸易或投资协定的授权。[2]规制权常受习惯国际法保护,尤其是作为条约中的例外条款,常见于一般国际法。因此,不管国际投资条约中是否对其有明确的措辞,规制权都是东道国所固有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美国对外关系法第三次重述》的注释将“正当的政府管制”划定为“诸如诚实的一般征税行为、刑事惩罚或者其他被公认为属于国家治安权力范围内的非歧视性的行为”,[3]国家对其引发的不利经济后果免责。此外,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人员在其报告的附件三第3条中对“管制权利”进行了解释,即“缔约方可采取、维持或实施其认为能以关切健康、安全或者环境的方式来确保投资活动与本协定一致的任何适当措施”。[4]
国际投资协定设计之初其宗旨就在于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财产利益不为东道国政府所肆意侵害。受这种目的的局限,在协定中忽略对东道国规制权的规定亦属正常。如前所述,规制权是国内法所授予本国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利,任何国家均会在本国宪法、行政法或者类似立法中明确给以规定,赋予本国政府管理国家相应权力,并且该权力还得到了习惯国际法的认可。作为在东道国从事投资活动的外国投资者当然应该尊重东道国规制权并受其管制。然而,由于国际投资协定条款所赋予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挑战东道国的规制权,使得东道国正常行使其规制权的权能受到阻碍,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所谓“规制寒颤”①的现象,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考虑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增设东道国规制权的相关内容,以减少甚至消除外国投资者利用国际投资协定挑战东道国规制权的情形。本文将结合国际投资协定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实践,分析东道国规制权在新近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发展状况,以期把握其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为我国的相关实践提供帮助。
一、东道国规制权权利宣示条款
此类条款主要是对东道国的规制权起到宣示的作用,表明国际投资协定对东道国规制权的认可,要求外国投资者对其予以尊重。从目前的实践看,这类条款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序言中的目标条款。作为国际投资协定目标和方向的集合,序言内容无法产生实体权利义务,也不受投资仲裁机制的管辖约束,但其能覆盖整个投资协定内容,而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条约解释功能。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序言中的目标是条约内容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仲裁员可任意使用的重要解释工具。为拓展公共政策空间的范围,东道国常常在国际投资协定的序言中阐明对规制权的立场。如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以下简称“美国范本”)的序言中规定:“希望缔约方在实现投资目标时,能采取适应保护健康、安全、环境和国际劳工权利的方式”。与“希望”的含蓄态度不同,《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以下简称“欧加协定”)直截了当地确认了东道国规制权,该序言规定:“本协定保护缔约方在其领土范围内的规制权,决心维护其实现合法公共目标的自由权,如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公共道德及文化多样性。”由于仲裁庭对投资保护的传统立场偏向,在序言中增加东道国规制权以拓宽公共利益范围确实有助于仲裁庭作出对东道国公共利益的有利解释。然而,公共利益列举的非穷尽性,以及序言的法律效力不足,都制约着序言目标功能的实现。
另一类是专门的规制权条款。在重视和保护东道国规制权方面,欧盟的投资条约实践比较超前。为弥补上述序言条款中的缺陷,TTIP投资章节草案设置了“东道国规制权”的专门法律条款。[5]该草案第二部分“投资保护”章节的第2.1条规定:“本节投资保护不影响缔约方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规制权,即东道国为实现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公共道德、社会保障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等公共目标,可在必要时采取措施。”在随后的欧加协定中则是在“投资保护”部分设置了“投资与规制措施”条款,其第8.9条第1款规定,“为了本章之目的,成员国重申其在其领土内的规制权,以取得政策目标的合法性,如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环境或公共道德、社会或消费者保护或促进与保护文化多样性。”这是欧盟首次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引入独立的规制权条款,为东道国规制权设计了更全面明晰的功能。若能被应用和推广,将显著提高东道国规制权在国际投资法中的地位,并有效发挥其在解决投资争议的作用。特别是规制权条款作为实体规则被纳入“投资保护”的专章,东道国可据此直接享有并行使该项实体权利。作为规制权的直接、明确的表达方式,东道国规制权条款具有其他表现形式在法律效力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理论上讲,该条款可直接适用投资仲裁机制,并作为缔约方维护本国公共利益的有效抗辩,但实践中东道国该如何具体应用,仲裁庭会如何判断及裁决等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二、征收条款中明确将东道国的“管制性”征收作为例外
国际投资协定的最初目标就是为了使外国投资者免遭东道国政府的征收,并逐渐形成了若干习惯国际法原则。实践中对征收和合法管制措施的界定原本就存在争议,而间接征收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间接征收成为了国际投资主体共同面临的重大风险,极易引发投资争端。[6]P85为维护东道国对重大公共利益的管制权利,晚近国际投资协定对间接征收规则不断予以完善。
(一)间接征收的认定
美国范本附件B对间接征收进行了定义:“东道国的行为虽然不构成所有权的正式转移和全部没收,却产生了与直接征收相同的效果”。欧加协定还增添了东道国的行为属性,要求“实质上剥夺了投资者对投资财产所拥有的使用、占有、处置等根本性权利”。在判定间接征收时,美国范本附件B排除了单一的经济影响标准,要求仲裁庭在对具体的个案事实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应综合考虑“政府行为对投资的经济价值所产生的影响”;“政府行为对投资者明显合理期待的妨碍程度”及“政府行为性质”等因素。TPP投资章节附件9-B第3条b款给出了判断投资者投资期待“合理性”的具体标准,包括“取决于相关限度内政府是否向投资者提供了约束性书面保证,政府管制的性质和程度,或政府对相关部门的管制能力”等因素。对保护公共健康的管制行为的解释也被列入该条注释。
然而,这种列举方式无法穷尽所有情况,单个仲裁庭仍然享有判断征收的最终的决定权。欧加协定的征收附件进行了如下改进:不仅把“东道国实施措施的持续时间”增列为间接征收的认定因素之一,还强调对东道国的行为目标、内容和意图的关注。此外,东道国措施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必须达到明显僭越其目的的程度,从而进一步确定了间接征收的可操作界限。如果说美国范本对间接征收的界定和解释都比较概括,为仲裁机构预留了相当大的裁量空间,不利于东道国规制权功能的稳定发挥。那么欧加协定则设置了较高标准的间接征收适用规则,通过对习惯国际法规则适用的进一步澄清,明显减轻了对东道国规制权行使能力的消极影响,并进一步限制了外国投资者利用征收条款挑战东道国规制权的空间。
(二)间接征收的例外
间接征收的认定本身就包含了东道国规制权和外国投资者合法权利的冲突。由于公共利益理念的不断深化,间接征收的藩篱逐渐被拆除。东道国为维护重大公共利益实施的合法管制措施也因规制权的庇护而免予赔偿,形成了间接征收的例外。例如美国范本附件B第4条规定:除非少数情况,任一缔约方为实现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环境等合法公共利益目标的非歧视性管制措施都不能归为间接征收。该项例外通过对赔偿责任的免除,实质上排除了这些合法管制措施的征收性,发挥了东道国规制权的应有功能。但这种“除非少数情况”的措辞并没有明确肯定的认可规制权,可能使东道国在未来投资仲裁中丧失一定优势。TTIP投资章节草案的征收附件删去了“东道国措施对投资者合法期待的妨碍程度”的认定因素,并把间接征收的公共利益例外情形扩展至“公共健康、环境、公共道德、社会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该扩展与东道国对本国重大公共利益的重视和维护不可分割,是其国内管制政策的直接体现。这种对公共利益的例外规定有利于协调投资的经济利益和环境社会利益,值得借鉴和推广。[7]P47
综上,晚近国际投资协定征收条款对东道国规制权的关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细化对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尤其是综合考察东道国管制措施的性质及经济影响因素,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澄清,为仲裁庭的个案判断提供了一定指示;另一方面是把东道国规制权直接确认为间接征收的例外,极大地提高了东道国规制权的可适用性,有助于东道国对重大公共利益目标的维护。这种规制权例外模式为间接征收与治安权设置了更明显的边界,也能为仲裁庭作出公正裁决提供更有效的指导。
在有关间接征收的东道国规制措施方面,往往还会涉及治安权这个概念。治安权最早是美国法上的一个概念:(1)指一个主权国家所享有的,为维持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德和社会正义而制定所有必需和正当法律的内在和绝对的权力。它是政府所必需的一项基本权力,不能为立法机关所放弃或从政府中转移。(2)指根据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授予州的权力,依此权力,州有权制定和实施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的法律,或将此权委托给地方政府。不过州行使此项权力应受正当程序和其他规定的限制。(3)泛指政府对私有财产使用的干预,如将该财产予以征用。[8]P1276现在,治安权已广泛接受为国家固有的一项管理国家公共利益的权力,特别是在评断一项管制措施是否是间接征收时往往会考量国家的治安权力,这已成为国际法上的治安权原则:习惯国际法承认东道国在特定情况下有权规制或者采取其他显著的影响外国人财产利益的措施而不构成需要给予补偿的征收。但是,该等措施必须致力于合法目的,其目标是为了普遍福利,且是非歧视性的,完全在该国一般规制或行政权的限度内实施。[9]P223-255对于在一国享有的治安权范围内、由于善意的非歧视管制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不予赔偿,这是习惯国际法上公认的原则。[10]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的一长串事例表明,立法机关可以在不违反财产保护的情况下,制定一般性的法律,以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和秩序。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是财产权的享有本来就要受制于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它不能损害到公共的健康、安全和秩序。[11]P162因此,尽管表述不一定一致,具体的含义也会有一定的偏差,但是,治安权却是现代法治所赋予一国政府维护公共福利的正当权力。
虽然治安权是国家固有的管理公共利益的权力,其也为国际社会公认为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但是,它的实施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须由国家善意为之。由此,我们不能把治安权解释成代表公共利益而行为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否则,作为例外情况的治安权就将压倒征收条款本身。[12]P118尽管承认治安权或管制权是一国固有的权利,但是,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条约(BIT)或自由贸易协定(FTA)时也会承诺对其适当的限制。因此,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保证其实施治安权应依照特定条约的条款并满足一定的条件。[13]P161
三、例外条款对东道国规制权的进一步确认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近期以来“有关直接投资是否可能发生负面作用的争论正在进行之中,在此种背景之下,愈来愈多的国家在其缔结的BIT中强调,实行既定的投资保护不能以牺牲东道国合法的公共关切作为代价。为此,多数国家采取在条约中设定各种例外的做法,以维护东道国制订各种条例的权利,即便所制定的条例与BIT不相一致。除了‘传统’(作为BIT的共同特征而实施了较长时间)的税收和经济一体化例外领域外,如今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协定将保证东道国的重大安全与公共秩序、保护国民健康与安全、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文化多样性以及东道国在金融服务方面采取慎重措施等等,全部或部分列入东道国义务的豁免范围。这些例外豁免规定表明了缔约各方在决策考虑方面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并且把对投资的保护从属于缔约各方所追求的其他关键性的政策目标。”[14]P142
(一)环境、劳工的专门例外
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国家经济决策的重要考量,并伴随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而日益强化。但国际投资实践中却出现了牺牲环境利益来吸引外商投资的乱象,不仅破坏了全球生态平衡,还引发了国家间投资待遇的不正当竞争。 为构建正常的投资竞争秩序,国际投资协定出现了对一国环保法制的规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率先通过“环境合作、劳工保护”的两个附属协议,建立了投资与环境的法制,特别是第11章第1114条具有突出的环保意义。
美国范本确定了更严苛的东道国环保和劳工责任。该范本第12条明确规定:禁止东道国通过弱化或降低环境法保护标准的方式来鼓励投资,并应确保不放弃或承诺放弃、减损其法律法规,还具体解释了“环境法”。这种义务性措辞的环境规制手段,实质上强化了东道国的环境责任。虽然该范本第12.3条也承认东道国享有合理管制的自由裁量权和对资源分配的善意决策权。但是,保留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不等同于授予和认可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权,而且缺乏对“合理”和“善意”的统一解释,作用比较有限。另外,美国范本第12.6条建立了国家与国家间的磋商机制,作为环境保护争端解决的专门程序。比照“投资与环境”的模式,美国范本第13条确立了“投资与劳工”规则,对“劳动法”的定义和磋商机制均与前述环境规则模式一致。但第13.1条重申了缔约方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义务,以及对《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补充规则的所作承诺。
TPP投资章节由于所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较多,利益交错复杂,条款设置较粗略,远不及美国范本对环境和劳工的保护力度。该章节第9.15条简单指出了“不阻止东道国为实现环境、卫生和其他管制目标所采取的适当措施”;第9.16条也仅仅对企业纳入社会责任规则作出原则性说明和鼓励。欧加协定与TTIP投资章节草案并不存在专门的环境、劳工例外条款,仅在序言或正文中对东道国的环境、劳工利益进行概括性规制。如欧加协定第22.3条第2款鼓励企业通过自愿履行诸如《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指导下的最佳实践,以增强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一致性,进而间接规定了外国投资者的义务。尽管该条款的约束力不是太强,但是却是在目前的国际投资协定实践中较为少见的。
(二)安全例外条款
实践中,若干国家受GATT一般例外条款的启发,在国际投资协定中逐渐发展出一般例外条款和重大安全例外条款,试图确认东道国的规制权。如1998年毛里求斯-瑞士BIT第11条第3款:“本协议中的任何规定都不得解释为妨碍任一缔约方为公共健康或者动植物疾病预防而采取必要的措施”。有些协定则与GATT第20条要求类似,规定了非歧视、不得作为伪装的投资限制等要求,但针对公共目的的较为单一。例如,1999年阿根廷-新西兰BIT第5条:“本协定不得限制缔约一方采取任何为保护自然资源和实体资源或者人类健康所必要的措施的权力,此种措施包括对动植物的破坏、财产没收或者对股票转移的强制限制等,但此种措施的采取不得构成随意的或者不公平的歧视。”②
国际投资协定的例外规定通常可分为“一般例外”和“重大安全例外”,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太相同。作为整个条约的例外,一般例外条款常常表述为“本条约不要求缔约方”或“本条约的任何条款都不应被解释为阻止一方”。由于内容过于空泛并且局限于所列举的公共利益目标,该条款的有效性被大大降低。例如在美国范本第12.5条、TPP投资章节第9.16条中,东道国的例外措施必须符合适当性,这就要求对必要联系的存在与否展开客观评估。而重大安全例外条款一般是绝对适用,很少有政策偏离,重大安全利益的认可也直接决定了东道国规制权的功能发挥。根据美国范本第18条的规定,东道国可采取其认为能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本国根本安全利益的必要措施,对违背自身根本安全利益的信息可不予公开。这里的“其认为”和“其确定”是一种自裁决条款,赋予了东道国主观判断及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决定权,仲裁庭只能进行善意评判。如今,自裁决条款已成为国际投资的立法趋势之一,并作为重要的“安全阀”为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提供有效保护。
国际投资协定中参照GATT第20条制作的一般例外条款较为典型的当属2009年新修订的东盟综合投资协定第17条的规定:“如果下列措施的实施不会在情形相同的国家及其投资者之间构成任意的或者不合理的歧视,或者不会形成伪装起来的对国际投资流动的限制,本协定中的任何条款不得解释为妨碍缔约一方采取或者实行这些措施:(1)为保护公共道德或者维持公共秩序所必需的;(2)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3)为保证与本协定相符的法律法规的实施而必需的;(4)旨在保证对任何一方的投资或投资者公平或有效的课征或收取直接税;(5)为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者考古价值的国家财产所必需的;(6)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相关的,并且该措施必须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同步实施。”③2007年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简称COMESA)投资合作协定第21条的规定则略有不同:“如果不会在同类投资者间构成随意的、不合理的歧视或导致变相的限制投资流动,本协定不能被解释为妨碍缔约国制定或实施以下措施:(1)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道德所必需的;(2)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须的;(3)保护环境所必需的;(4)经共同投资区委员会同意,缔约国随时可以决定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
除上述所谓一般例外条款外,一些国际投资协定中还从国家安全、国际和平的角度设置了所谓重大安全例外条款,如,1998年德国-墨西哥BIT议定书第3条规定:“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公共健康或公共道德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不应给予外国投资者更为不利的待遇。”2008年美国-乌干达BIT第18条规定“本条约的任何部分不得被解释为阻止一国采取其认为必需的措施,履行职责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或者保护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等等。④此外,一些BITs中以“一般例外”作为标题的条款除了规定保护公共利益的例外情形,还规定了保护国家根本安全利益的例外情形。如日本-越南投资自由化与促进和保护协定第15条的一般例外,就同时包含了重大安全例外的内容和一般例外的内容。
从前述可见,一般例外条款的表现形式和范围纷繁多样。就范围而言,不同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条款涵盖的范围各有差异,有的只规定单一公共目的的例外,如文化利益例外、环境保护例外、自然资源保护例外等等,有的则规定了从公共道德、动植物生命及健康到自然资源保护的综合例外。而该条款中公共目的的表述如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等也缺乏明确的内涵范围界定,这就使得一般例外条款的范围宽泛而多样,从而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较为广泛地确认东道国的规制权。
(三)其他例外条款
除了常见的安全例外,东道国规制权的正常行使也关乎一国金融体系安全。为克服金融危机风险以及避免后期被投资仲裁缠身的困境,许多国家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增加了金融审慎例外安排。美国范本第20.1条设置了该项例外,并在注释中澄清了“审慎原因”,包括维持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定和完整;维护支付清算系统财务和运营的完整和安全。第20.3条c款ii项还明确了由缔约双方共同决定对审慎原因的判断。然而,这种模式仅仅局限于金融服务领域,至于非金融领域的政府措施,东道国则不能援引此条进行抗辩。这点可以说明美国对东道国享有较宽泛的金融规制权仍存在顾虑。
税收问题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是东道国规制权的传统覆盖领域。美国范本第21条设计了专门的税收条款,确定了缔约方优先履行其在税收协定项下的义务,并且由同一税收协定下的主管当局来单独决定责任承担。虽然规则设计不够精细,但该条款明确肯定了税收的可仲裁性,并规定了适用条件。作为投资协定的例外,该条款可以防止投资者对税收争议仲裁的滥用,从而维护东道国的税收主权利益。
虽然上述例外规定比较零散,但却能促进和规范东道国对关乎重大公共利益的外资管理。
四、程序环节加强对东道国规制权的维护
国际投资协定中涉及的争端主要两种:一是缔约国之间因条约的解释与履行等产生的争议,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通常而言不涉及挑战东道国规制权的问题;另一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这类争议往往是外国投资者以东道国违反国际投资协定为由而提起,它直接针对的就是东道国的规制权。在国际投资协定创设之初,为了避免这类争议解决的政治化,借用了解决商人间纠纷的国际商事仲裁模式来解决国家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纠纷(这种机制现在通称ISDS机制)。随着ISDS实践的发展,逐渐暴露出外国投资者利用该机制挑战东道国规制权的缺陷。为了减少这种情况,在没有对ISDS机制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形下,国际投资协定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加强对东道国规制权的维护,减少外国投资者挑战东道国规制权的可能性。
(一)磋商机制
磋商程序作为投资仲裁机制的前置程序,是国际投资协定的普遍立场。根据美国范本第23条、第24条,缔约方必须首先通过磋商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TPP投资章节第9.18条还强调磋商程序的进行并不代表对仲裁庭管辖权的承认,并要求申请方在提交书面磋商请求时,对东道国的相关措施事实作出简要描述。欧盟则进一步细化了磋商机制的适用规则,极大地提高了该机制的适用性。通过强化磋商在投资争议解决中的作用,不仅可以减轻ISDS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反映欧盟尊重和维护东道国规制权的立法倾向。其内容概括而言:首先扩充了磋商请求的必备内容,包括投资者信息;被指控违反的条款(违约法律基础);被指控违反条款的待遇(争议措施);寻求的救济和损害赔偿额等。其次确定了磋商请求的“诉讼时效”,自知晓违反行为和损失后3年内,或用尽当地法院救济程序后2年内,但任何情况下不得晚于10年。⑤第三,若申请人自提出磋商申请之日起18个月内未申请仲裁请求,应视为对磋商请求的撤回;第四,磋商的内容也是今后外国投资者提起仲裁的内容,既如果磋商不成,外国投资者提起仲裁只能以磋商的内容为依据,不得增加新的内容。欧盟的这种制度设计具体反映在欧加协定第8.19条以及TTIP投资章节草案第3节第4条、欧盟-新加坡自贸协定第9.13条、欧盟-越南自贸协定第2章第3节第4条等,它们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磋商规则。
磋商机制的灵活适用,不仅能提高东道国对投资争议解决的参与度,减少对ISDS的依赖,也有助于加深对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考量,促进规制权的正当行使。
(二)缔约方对条约的联合解释
为避免仲裁庭进行扩大解释,有必要改变传统解释规则,尤其是提高东道国的解释参与度,联合解释规则便应运而生。一般而言,国际投资协定的缔约方无法对ISDS实行联合干预或决定摆脱仲裁庭的约束。虽然国际投资协定是由各方共同签署,但当仲裁庭对协定的解释违反其立法意图或现行目标时,缔约方也无计可施。为保证东道国能对国际投资协定的解释施加影响,需要就特定的法律争议设置有约束力的解释条款。至于作为非争端方的投资者母国,也可参与对国际投资协定的解释。
根据美国范本第30条规定,缔约双方对协定条款作出的联合决定对仲裁庭有法律拘束力,仲裁庭的裁决必须要与之相符;第31条也赋予了缔约方对附件解释条款的联合决定权,并将书面提交期限修改为90天。TPP投资章节与美国范本的规则一致,只是把联合决定权授予了未来成立的“某委员会”。[15]欧盟也认为东道国的扩大参与可以限制仲裁庭的随意解释,提高对仲裁结果的预见性。为此,欧加协定第8.31条、TTIP投资章节草案第3节第13条对适用法和解释规则作出规定,二者均要求仲裁庭在解释本投资协定时,应遵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及可适用于缔约双方的其他国际法原则及规则。而且,针对可能引起投资重大关切的条约解释,欧加协定和TTIP投资章节草案均规定(服务与投资)委员会可以把缔约双方达成的协定解释推荐给(贸易)委员会,一经贸易委员会采纳,该解释将适用于本协定下的所有仲裁庭。尽管由专门的委员会代表行使,缔约双方仍享有对协定的解释权。此外,TTIP投资章节草案对国内法的适用作出补充说明:仲裁庭在确定东道国的国内法某项条款的具体含义时,应遵循东道国法院或当局对该条款的现行解释,且该解释不能约束东道国法院及当局;仲裁庭无权决定所谓的东道国违约措施在国内法的合法性。
(三)防止外国投资者滥诉以维护东道国规制权
晚近国际投资协定在仲裁程序中设置了无理诉讼的应对机制,使得相当的仲裁案件被驳回,滥用诉权的申请人也被要求分摊一定的法律费用。东道国则通过对不当诉求的进一步限制加强了规制权的行使,并摆脱了ISDS对国内政策措施的干涉。因此,对无理诉讼的迅速驳回成为国际投资协定的总体趋势,并通过各种程序条款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标准。[16]P154如TPP投资章节第9.22条第4款至第6款,“不符合裁决规定”或“明显没有法律依据”的诉请被视为争议解决的先决问题,被申请人可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异议。一旦程序启动,仲裁庭应中止与实体问题相关的所有程序,并迅速作出异议的裁决或决定及理由陈述。若符合程序滥用,仲裁庭在适当的情况下,由败诉方承担整个异议过程中的合理费用及律师费。
为防止诉诸仲裁的恶意行为,欧盟对其近期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了更多改进。欧盟希望通过构建程序保障措施,减少投资者随意申请仲裁尤其是强迫发展中国家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为提高保障措施的有效性,欧盟还对轻率仲裁的投资者同时采取了拒绝补救措施和分担费用的惩罚措施。欧加协定第8.32条、第8.33条确立了适用投资者轻佻仲裁、无理仲裁的专门程序,赋予仲裁庭在程序初期对该类诉求直接否定的权利,并要求仲裁庭对构成先决问题的法律问题、诉求或其他事项进行审查。为防止投资者滥用程序,欧加协定第8.18条第3款还明确排除了投资者利用欺诈性陈述、采用隐瞒、贿赂或滥用程序的投资行为的可仲裁性。作为防止投资者滥诉的创新规则,欧加协定采用了“败诉方支付”的一般付费原则。[17]TTIP投资章节草案基本采用了与欧加协定中上述两种特殊程序和付费原则,仅对程序期限做了零星修改。[18]这些程序若能践行甚至推广,则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东道国的司法主权,提高ISDS的利用效率。
通过避免投资者的无理诉求和轻率诉求,尤其是转移被告东道国的费用承担,能防止投资者得到双重救济以及后续对东道国管制措施的影响。而拒绝明显无理和丝毫没有法律根据的索赔请求,也是欧盟受到了2006年修订的ICSID仲裁规则的启发,将其发展为清晰的仲裁规则。[19]P661不过,这种设计也存在一定问题。对投资者不当诉求的有效隔离,固然能为仲裁庭节约大量时间和支出,然而投资者可能会借机利用程序漏洞来拖延和扰乱程序进行,尤其是仲裁庭并无权强制推进仲裁程序。[20]P708虽然付费原则使东道国不必再为投资者的无理行为买单,并可从投资者那里获得成本,有效克服了传统投资仲裁中“各方承担费用”的弊端。但投资者胜诉的话,东道国也必须承担上述费用。因此,该制度对一国监管能力的具体影响还不清楚,能不能实现设计初衷也有待实践证明。
五、中国的立场
东道国规制权由主权派生而来,是现代法治赋予一国政府维护公共福利的正当权力,也是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之一,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各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作出的让渡或减损规制权的承诺,是在主权原则基础上,自愿接受对其主权的某些限制。但由于不同的国际投资协定对东道国规制权的认可程度不同,东道国的实际免责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国际投资协定中的认可和澄清对东道国行使其规制权至关重要,这是现阶段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主要方向。当然,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制度安排不是否定投资自由,而是一种带有内嵌自由特征的高水平的平衡措施,是为了实现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应准确把握规制权的发展趋势,在全球投资治理中积极作为,通过借鉴美国和欧盟的发展模式及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的指引下,重新审视和确立BIT谈判中有关规制权的立场及规则,为未来国际投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新兴国家的重要力量,必须坚持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立场。这不仅关涉对外投资大国的投资利益,也是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肩负构建新一轮国际投资秩序的使命使然。当前,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出现社会化浪潮,传统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的“南北矛盾”演变成更复杂的矛盾,并输出了构建综合发展观、重视东道国规制权等新型价值观。 为顺应时代形势,美欧等发达国家通过增设BIT或含有投资章节的FTA中的规制权规则,试图对构建未来规制权的多边及全球规则作出事先安排。中国也应抓住机遇,勇敢作为,促进规制权制度的健康发展。
据统计,自1983年中瑞BIT签署以来,中国已签订了128个BITs,并积极推进含投资章节的FTA及其他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签订。 回顾中国现有BITs的签订历程,基本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1989年以前的第一代BIT只接受ISDS对征收补偿数额的管辖权;1990年至1997年的第二代BIT也保留了较大权利;1998年到2009年的第三代BIT,基本接受了ICSID对绝大部分投资争议的管辖权;2010年以后的第四代BIT开始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权利,如对间接征收的例外规定。 由此看出,中国对国际投资协定的态度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全面开放”再到“注重平衡”的发展过程。以新近签署的中澳自贸协定为例,其投资规则框架引入了透明度规则、投资仲裁机制及上诉机制,中方还承诺未来谈判将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并确立评估投资章节等工作机制,提供了更加自由便利、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在平衡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方面,不仅明确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在ISDS中的适用,还对管辖预审制度、法庭之友和仲裁费用作出安排。其第11条直接规定:基于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公共道德或秩序等合法公共利益的目的,东道国所采取的非歧视性措施不受ISDS的管辖。该条不仅明确认可东道国规制权的管辖例外,同时设置了磋商程序中的“公共利益通知”等具体规则。这些条款的规定,反映出我国促进和发展外资的迫切需求及完善国内市场体制的殷切愿望。但我国的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存在形式多样、结构混乱、内容存在矛盾等问题,不利于东道国规制权的维护。因此,在今后的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中,我国完全可以接受当前国际投资协定中增强维护东道国规制权的改革实践,在国际投资协定的框架内促进东道国规制权的健康行使。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就谈判立场选择而言,我们应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国家,不应根据国家法治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进行区分,更不要以所谓的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身份”的不同或者所谓身份“转换”、“混同”,而采取不同的谈判立场,这不仅不会带来预设的效果,反而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国际投资协定普遍存在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自然会“拉平”这种“差别”,而实际上很难实现这种“差别”对待;而且以所谓“身份”的理由不断变化谈判的立场,导致的是无原则之国家形象并极易授人以“投机”之柄。
虽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所谓不同的“身份”而产生不同的利益,⑥进而在相关的国际关系中采取不同立场从事的情形,但无论如何,在法律制度的构建上,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一样的,立法者应当具有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必须坚守一定的法律原则,需要明晰构建某一具体制度的目的与价值追求。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保护私人财产权是处理政府与私人关系的永恒法治主题。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21]P2并且这种自由交易既需要国家权力的保护,又要排除国家权力的侵害。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个人能够合法地取得与拥有财产,并能够不受外力干涉地自由处置其财产从中受益。也就是说,个人的财产权利及其法律保护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离开了个人的财产权利及其法律保护制度是谈不上市场经济的。因为,离开了个人的财产权利,或者得不到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利,市场经济无从开始,更无法进行。经济主体能够拥有完全的财产权利是其从事交易的前提,也是其从事市场活动的原动力。因为:
首先,没有财产的主体无法从事交易,自然也就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合格主体;其次,主体对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的满足也有赖于有效的产权制度的保障,并特别有赖于产权的排他性属性及其主体本己利益最大化的内部化功能。[22]P370-371亚当·斯密就曾强调,市场的适当运作取决于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的适当转让,后者不仅被看作是私人生产性活动的一种激励,而且也被看作是防止武断地对个人自由的重商主义政府限制的一种保障。[23]P101可以说,私有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个人拥有财产权并受到法律的完备保护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与归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政府施加给个人生产者、贸易者和消费者的那些规则必须尊重并符合个人经济主体的内在权利和行动本能,只有这样,经济与社会过程才会平稳地进行。假如政府的各项贸易法规专断地干预了国内公民的平等自由和财产权利,则他们便有可能产生出无序状态并减少经济福利。[23]P189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所言,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并且可以说是首要职能,就是向社会上一切合法利益集团与个人,提供财产权的保障。这种对财产权的保障,是政府所能提供的一种能为全体公民共同享有的重要的“公共物品”。[24]P14凯利教授从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同样得出“共同体的政府一旦组成就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保护其成员的财产”[25]P207的结论。并且这种基本职能构成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正是宪法中人权规范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人是物质的存在,同时又是精神的存在,这种双重性的存在都与财产权不可分离。作为物质的存在,人不能在没有占有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情况下维持个体生命的存在;而作为精神的存在,人同样不能在没有占有相当的物质资料的情况下保持独立自尊的人格。因此,财产权与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密切联系。“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以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它“是市民社会和民间的政治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26]P104-105具体到国际投资协定的实践,尽管目前出现了相当多的改革呼声,出现了增强维护东道国规制权的内容,但是,国际投资协定对外国投资者财产权的保护依然是核心内容。目前的改革只是对外国投资者可能滥用国际投资协定追求其最大个体利益的一种修正或修补。因此,我们所应坚守的法律原则与价值追求仍然是如何保护投资者的私人财产权益,使其不受东道国政府的肆意侵犯,只是在此基础上,应考虑如何做到既要充分保护投资者的个体利益,又要维护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而已。诚如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所认识的:尽管国际投资协定有利于构建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缔约国在国内政策制定上的权利。因此,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必须确保缔约国保留其为追求公共政策利益而进行规制的权利,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如保护环境、促进公共健康及其它社会目标。当然,保障规制权也是缔约国实施经济或金融政策所必须的。但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必须警惕在为政府提供追寻善意公共产品的时候应当避免无意之中为投资保护主义和不公平的歧视提供了法律外衣。[27]P128所以,在对待外国投资者的总体待遇方面,一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应当是“均衡的”,即,投资政策应包含投资自由化及保护、促进和便利化措施,同时东道国的总体规制框架需要最小化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加强规制以备应对危机之不时之需。[28]P108
注释:
① 规制寒颤,在中文中有多种译法。这里的意思主要是指由于投资者通过投资仲裁利用国际投资协定的规定挑战东道国的规制措施,使得东道国付出巨额的赔付而导致东道国在实施新的规制措施时会心有余悸。
② 类似的还有:1999年澳大利亚-印度BIT第15条规定:“本协议不得排除缔约一方依据其可正当适用的法律,在不歧视的基础上采取的为疾病或者虫害的预防而采取任何措施。”
③ 与此类例外条款类似的还有:加拿大2004年FIPT范本第10条规定:“如果下列措施的实施不会构成任意的或者不公平的歧视,或者不会形成伪装的对国际贸易或者投资的限制,本协定中的任何条款不得解释为妨碍缔约一方采取或者实行这些措施:(1)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2)确保与本协定条款不冲突的法律法规的实施;(3)保护可用尽的或者不可用尽的自然资源。”2005年美国-乌拉圭BIT第12条规定:“本协定中的任何条款不得解释为妨碍任一缔约方采取、保持或者实施其认为适当的、为确保其境内的投资活动与其环境关切保持一致的措施,该措施不得违反本协定规定。”
④ 另如,1998年美国-玻利维亚BIT第14条规定“本条约不得阻止缔约国采取必要的措施,履行职责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或者保护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2000年墨西哥-瑞典BIT第18条规定:“争端解决条款不适用于缔约一国因为国家安全原因,根据本国法律做出禁止或者限制缔约另一国投资者并购本国国民拥有或控制的在本国境内的投资的决定。”。2003年越南-日本BIT,1998年美国-莫桑比克BIT第也有类似规定。
⑤ 其中欧盟-新加坡自贸协定中把用尽当地法院救济程序的期限设置为一年,而最长诉讼时效10年的期限仅适用于CETA和TTIP投资章节草案中。
⑥ 身份学说主要是建构主义的主张,提出行为体的身份界定行为体利益的论断,并以此作为建构主义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点。其代表性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系统地引入并界定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身份的概念,提出了社会身份形成与转化的逻辑假设。但是,不大。至今,学者们对于身份的概念、身份的形成、身份的研究路径、集体身份形成及其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难以达成较为广泛的一致意见。参阅季玲: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
[1] [英]安东尼·奥格斯. 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M]. 骆梅英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8.
[2] IISD,The Right of States to Regulat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5,adopted on 6-8 Nov.2002[EB/OL]. available at http://www.iisd.org/pdf/2003/investment_right_to_regulate.pdf, visited on 21 Aug. 2016.
[3]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Law Institute,Volume 1, 1987, Section 712, Comment g.
[4]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Repor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Negotiating Group).DAFFE/MAI(98)17[EB/OL]. 4 May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1.oecd.org/daf/mai/pdf/ng/ng9817e.pdf.
[5] TTIP Commission Draft Text, Sep.16, 2015,Trade In Service, Investment and E-commerce, Chapter II-Investment, Section 2 Art. 2.
[6] 王小林. 国际投资间接征收的中国关切[J],北方法学. 2015,2.
[7] 石俭平. 论国际投资条约征收条款的适用危机[J]. 学术交流. 2012,8.
[8] Brayan A. Garner (ed.), 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2009.
[9] Caroline Henckels,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the Right to Regulate: Revisiting 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and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5(1).
[10] OECD“Indirect Expropriation”and the“Right to Regulate”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Law[R].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Number 2004/4.
[11] [美]亨金等.宪政与权利[M].郑戈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6.
[12] [美]理查德·A·艾珀斯坦.征收——私人财产和征用权[M].李昊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3] Surya P. Subedi,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conciling policy and Principle,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2008.
[14] UNCTAD,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95-2006:Trends in Rulemaking,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2007.
[15]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Chapter 9 Investment, Article 9.24(3), Article 9.25.
[16] Mysore S, Vora A. Tussle for policy spac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orm setting: The search for a middle path? 7(2) Jindal Global Law Review. (2016).
[17] CETA, Article 8.39.
[18] TTIP Commission Draft Text, Section 3 Article 16, Article 17,Article 28.4.
[19] Titi C.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26(3)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5) .
[20] Nyer, Damien, The Investment Chapter of the 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3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5).
[21] 张曙光.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A]. 刘军宁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2] 李晓明.私法的制度价值[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23] [德]E.-U.彼德斯曼.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功能与宪法问题[M]. 何志鹏等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4] 樊纲.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职能[A]. 刘军宁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5] [爱尔兰]J.M.凯利. 西方法律思想简史[M]. 王笑红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26] [奥]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7]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28]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
StudyontheRighttoRegulatein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andtheStandpointofChina
ZhangQing-lin
(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The protection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alway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main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IIAs). However,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IIAs,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s, the phenomena that foreign investors challenging the right to regulate of host States has been apparent recently. Therefore, contents related to the right to regulate of host State was increased concequently in IIAs, which embodied in the preamble, expropriation, exception and procedural aticles.China has participated negotiations of IIAs for a long time, it should adopt the practices of adding articles on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IIAs.Meanwhil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treat the partners differently in light of the “mix identit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IIAs),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vestor-state disputes settlement
1002—6274(2017)06—068—10
DF964
A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外资法律制度重构研究”(14ZDC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庆麟(1963-),男,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
(责任编辑:唐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