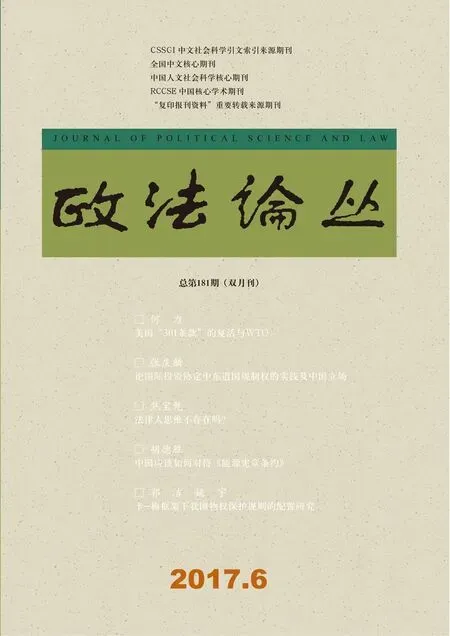论东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统一化*
2017-01-26苏号朋郭静静
苏号朋 郭静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29)
论东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统一化*
苏号朋 郭静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29)
近年来,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跨境消费迅猛发展,涉外消费者合同纠纷日益增长,但中日韩三国消费者保护水平的差异影响了消费安全,有必要在东亚地区实现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统一。中日韩国内法均就涉外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作出特别规定,其共性特征是法律统一化的基石和支撑。虽然三国国内法规定有所不同,但并非实质性差异,不足以阻碍法律统一化进程。为了向东亚跨境消费者提供一体化保护,设想基于中日韩三国消费者合同冲突法现行规范,通过签订多边条约,统一消费者概念、意思自治限制的范围、强制性规定的适用等基本规则。
消费者合同 法律适用 东亚 经常居所地 法律统一化
位于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国内法均有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则,但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不利于跨境消费者的保护。从国际范围观察,为了减少法律制度对跨境消费制造的障碍,不少地区都在进行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统一化,如欧洲、南美。本文以法律统一化为目标,以强化消费者保护为价值追求,以中日韩三国国内法规则的相通性为基础,以化解中日韩三国国内法规则的差异为突破口,以寻找可为中日韩三国普遍接受的规则为路径,为东亚地区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法律统一化方案,从而降低跨境消费的法律风险,进一步促进东亚地区跨境消费的发展及消费者法律保护的标准化。
一、东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统一化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学认为,投资、消费、出口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出口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对较少。不过,从2013年开始,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贡献不断增强。从2014年到2016年,消费连续三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2017年前三季度,消费增长态势良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加突出,已经达到64.5%。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表述正式宣告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进入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新的增长模式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经济韧性的增强均具有战略意义。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发展的传统思路,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包括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完善,以解决消费者愿意消费、便利消费、放心消费、安全消费等问题。
中、日、韩三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韩国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三国均位于东亚地区,地缘接近、文化相似,经济均持续增长,尤其是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今后仍会维持6-7%左右的年增长率。三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国民生活迅速得到改善,而且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财富,居民消费数量大增,且三国经济互补性强的特点促使跨境消费日益增加,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消费者在日本、韩国的消费频次、数量、金额均大幅度增长。
随着跨境消费的增加,涉外消费者合同纠纷亦不断发生,但跨境消费维权面临语言不通、渠道不畅、法律不同等困境。近年来,三国政府主管机构或官方设立的消费者保护组织为了解决跨境消费纠纷,各自建立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机制,如中国国家工商总局与其他国家签署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备忘录,日本国民生活中心与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保护机构设立合作机制,韩国消费者院与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建立跨境消费争议解决促进机制等。不过,这些机制都不具有强制性,仅为消费纠纷解决的协调方式,对于纠纷的最终解决,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借助政府或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跨境消费者的保护问题。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终途径,跨境消费者的权利保障同样需要依赖司法作为终极手段。但是,中日韩三国在涉外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规则上的差异影响了消费者寻求司法保护的便利,影响了东亚地区整体的消费者保护水平,因此有必要在此领域推进法律的统一化。目前,无论是中日韩三国政府的主管机构,还是三个国家的法学界,均有意愿推进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统一化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东亚地区的跨境消费中,中国公民居于主流,无论是消费者数量,还是消费范围和消费金额,都是日韩两国无法比拟的。因此,东亚地区如能实现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统一化,最大的受益者必将是中国消费者。另外,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意图建立起“共商、共享、共建”的开放型国际经济带,而日本和韩国是这一经济战略的重要节点国家。如能以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统一化为先导,进而推进三国在投资、贸易等领域的法律统一,必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并充分发挥中国的牵引作用。因此,统一东亚地区的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规则,不仅有必要,亦恰逢其时,可顺势而为。
二、东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统一化的基石
共处于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在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领域之所以有可能实现统一化,其基石在于它们均在此领域信奉相同的法律理念: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作为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并在进行国际私法立法或修法时,通过一定的法律技术,将这一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贯穿其中。
传统冲突法追求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正义,也称形式正义,确保涉外法律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是“最适当”国家联系的法律。冲突法应当致力于冲突法公平,即确保适用最适当国家联系的法律,而不期望获得实体法公平,因为那是国内实体法所追求的公平。[1]此种理念支配下的冲突法强调规则适用的一致性,即同一个案件,不论在哪国法院提起诉讼,都应只受同一个实体法支配。基于冲突正义的传统冲突法力求实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但对于法律适用结果即所涉双方当事人是否得到了公平对待,判决结果是否公正均不予考虑。[1]可见,传统国际私法所体现的正义是一种总体的正义,并未突出对某类案件的特别调节,亦未对某类主体给予特别的关注。[2]P16随着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入,国际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员、技术、资金的跨国流转越来越频繁和多样化,当事人因经济条件、社会背景等方面的悬殊差异而存在实质性的不平等,如再适用同样的冲突法规范,将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因应时代的变迁,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冲突法革命”,[3]主张采取更为灵活的法律选择方法,而其中一些方法明确提出实质正义的价值观。美国冲突法革命后,各种现代国际私法学说为公平解决个案纠纷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应当指出的是,国际私法的上述变化是与实体法的理念变迁紧密相连,并由后者决定的。在实体法领域,自18世纪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法倡导人人平等的原则,即当事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此种平等只是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抽象平等,完全忽视现实生活中的民事主体在身份地位、经济条件、专业认知、信息获取等方面存在的具体差异。此种仅赋予民事主体以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不顾及其现实差别的法律原则,会在个案中导致实质的不平等,无法实现实质正义。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校正近代民法存在的这一缺陷,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体现实质正义、倡导人文关怀的社会价值开始在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到重视与体现,近代民法逐渐过渡到现代民法。现代民法在注重形式平等的同时,开始关注具体人格和实质平等,对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如消费者、雇佣者)给予特殊保护。
国际私法在调整上述领域(如消费、雇佣)的民事关系时,也不得不就此作出特别回应,在弱者利益保护方面充分表现出人文关怀和实质公平价值取向。[2]除了因应实体法保护弱者利益的思想外,消费者在交易中愈发恶化的弱势地位也引起了国际私法自身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进入了恢复和发展期,社会生活与消费的大规模化使得消费者保护问题日渐突出。垄断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交易地位逐渐失衡,消费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不能与经营者相对抗。[4]P19要求保障实质正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呼声此起彼伏。在上述情形下,欧洲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有必要通过国际私法保护作为弱势一方的消费者,以追求冲突法的实质正义。[5]P214此种观点认为,如果对消费者的保护性规定仅仅停留在国内实体法的层面,即使是一国国内法以牺牲合同自由为代价来保护消费者,也可能会出现被保护方的对方当事人选择保护程度较低的其他国家的法律作为准据法来规避。因此,消费者保护必须延伸至冲突法的领域,对当事人的选择权予以限制。[6]P1121980年,冯·梅伦教授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14次大会上提出对消费者适用特别的保护性冲突规范,以此区别于普通合同的适用规则。[7]此种学术观点逐渐被接受,并在各国国内法及国际条约中得到兑现。
冯·梅伦教授的这一理念首先体现在同年的欧共体《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公约》(也称为《罗马公约》)之中。[8]P1516该公约第5条专门对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特别规定,并以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为基本的准据法,从而就消费者合同与普通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鲜明的区别对待,以充分体现消费者保护的新理念。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20条则对消费者合同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予以绝对限制,不允许当事人自行选择法律,而是强制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此后,保护社会和经济上的弱势当事人利益(尤其是消费者权益)的理念被广为接受,成为各国国际私法立法的最新发展趋势之一。[9]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韩三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均接受了这一理念,就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了特别规定。韩国率先修订了1962年《韩国涉外私法》,于2001年4月7日通过了《修正国际私法》(以下简称《韩国国际私法》)。该法受到《罗马公约》的巨大影响,其第27条②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即遵循《罗马公约》确立的原则,以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为消费者合同的基本准据法。[10]P707日本于2006年通过修改《日本法例》而形成新的《关于法律适用的通则法》(以下简称《日本通则法》)。日本此次修法增加了对消费者合同的特殊规则,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第11条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制定专门的国际私法立法,其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散见于《民法通则》及其他立法、司法解释之中。2011年4月,中国制定了首部国际私法立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④(以下简称《中国法律适用法》)。该法第42条⑤首次使用了“消费者合同”这一概念,就其法律适用作出了特别规定。和日韩立法相同,《中国法律适用法》亦将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作为消费者合同的基本准据法。
三、东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统一化的立法体例与规则支撑
东亚地区在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领域之所以有可能实现统一化,除了中日韩三国均信奉相同的法律理念,还在于它们采取了相同的立法体例,在核心内容上设计了相似的法律规则。
在立法体例上,中日韩三国的国际私法均采取了集中立法的模式,在一部法律中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全面规定,如《中国法律适用法》、《日本通则法》、《韩国国际私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际私法在立法形式上的“法典化”,[11]实现了国际私法领域立法的现代化。就消费者合同而言,三国法律均将其从一般的债权合同中分离出来,作出特别规定,具体表现为《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日本通则法》第11条、《韩国国际私法》第27条。从一般的债权合同与消费者合同准据法规则的法条安排来看,《中国法律适用法》的第41条、《日本通则法的》第7、8、9、10条、《韩国国际私法》第26条均是关于合同准据法的一般规定,而中国法的第42条、日本法的第11条、韩国法的第27条则是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特殊规定。在“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的适用关系上,三国法律均体现了“特殊规定”排除“一般规定”的原则,即消费者合同只适用特别规定,而不适用一般规定。比如,日本法的第8条第1款、韩国法的第26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时,合同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而在消费者合同的适用上,则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
中日韩三国不仅立法体例相同,而且在设计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具体内容时,在核心层面也采纳了相同或者相似的规则。
首先,三国立法均排除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20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法律选择方法,最密切联系原则要求法院在确定某一案件应适用的法律时,应考察并权衡各种与该案法律关系或有关当事人具有联系的因素,从而找出适用解决该案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近年来,最密切联系原则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国内法所接受,成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尤其是合同之债法律关系的基本准据法规则,⑥中日韩三国立法均采此例(参见《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1条、《日本通则法》第8条、《韩国国际私法》第26条)。但是,为了对消费者权益进行特别保护,三国国际私法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则均排除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迳行将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作为消费者合同的基本准据法。此种立法模式将“消费者”认定为弱者,认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能力的差距、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处于实质上不平等的地位,无法与经营者抗衡,有必要对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予以补救,从而保障消费者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害。由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是消费者最为熟悉的法律,将其作为消费者合同的基本准据法通常最有利于消费者。就立法内容而言,日本、韩国立法明确规定消费者合同排除适用普通合同的准据法规则,如根据《韩国国际私法》第27条规定,消费者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时,排除第26条(即关于普通合同准据法的规定)的适用,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虽然中国法没有做出如此清晰的规定,但在理解上,应与日、韩立法的意旨相同。
其次,三国立法均限制当事人自由选择准据法。在消费者合同订立过程中,消费者的意思自治受到极大限制,尤其在以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中,消费者几乎丧失了表达意思的机会,完全服从于经营者意志,双方的意思自治严重不对等,传统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已经演变为当事人一方(经营者)的单方意志。因此,在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上,不宜再采取普通合同的模式,完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现代国际私法中,为了平衡意思自治这一最基本的私法原则与消费者保护这一特别目标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国家在消费者合同准据法选择方面,一方面继续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12]以落实消费者保护的精神。中日韩三国立法亦体现了这一精神,但具体做法有所不同。其中,中国的选择最有特色,即仅允许消费者单方选择适用法律,而不允许当事人双方协议选择(《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第2句);日本、韩国虽允许当事人双方协议选择适用法律,但受到若干限制,尤其是受到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中强制性规定的限制(《日本通则法》第11条第1、3、4款,《韩国国际私法》第27条第1款)。例如,根据《韩国国际私法》第27条规定,消费者在被动消费的情况下签订的消费者合同,即使当事人选择了准据法,也不能剥夺由消费者的经常居所地国家强制性规定赋予消费者的保护。《日本通则法》第11条亦规定,对于消费者合同的成立与效力,即使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为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以外的法律,如果消费者表示需要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的,该消费者合同的成立及效力,适用该强制性规定。
最后,三国立法均适当顾及经营者利益。消费者保护的目的是矫正消费者的劣势地位,不让其从中受害,而非让消费者成为优势方并获取额外利益。因此,消费者作为弱势一方,应当获得法律的特别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忽视经营者利益。如果经营者没有得到法律的合理尊重,其必然会提供劣质商品或服务,或者增加消费者负担,最终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因此,消费者保护立法往往在优先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适当顾及经营者利益,中日韩三国立法均遵循了这一原则。例如,依《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消费者的选择权仅限于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此外,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则不应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而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显然,上述规定考虑到了经营者的合理期待利益,从而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法律适用方面实现一定平衡,毕竟经营者不可能洞悉世界各地消费者经常居所地的法律。《日本通则法》第11条第6款、《韩国国际私法》第27条第1款中的第(1)-(3)项亦体现了这一立法精神。
四、东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统一化的制度障碍
尽管中日韩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国际私法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并呈现共性特征,但三国立法在消费者范围、准据法选择方式、准据法选择范围、强制性规定适用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首先,三国立法对消费者的范围界定不同。在消费者保护法领域,“消费者”的界定是最为基本的问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消费者保护水平的差异以及对消费者保护法适用范围的认识分歧,各国立法和学术界对“消费者”的范围认定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状况在中日韩三国亦有明显表现。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中国消法》)第2条是对该法调整范围的规定,但并未就“消费者”作出定义。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法律语境下的消费者,是指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⑦中国法院则认为,《中国消法》第2条明确了消费者应有生活消费而非生产消费的需要,因此应当将消费者限定为自然人。[13]依日本《消费者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限于自然人。[14]P14不过,日本学界对此有所争论,认为法人虽然不属于法定的消费者范围,但像连锁店加盟等合同类型,基于其在现实中的弱势地位,也应当允许法人获得和自然人消费者一样的保护。⑧韩国立法未统一界定消费者概念,而是在各单行消费者保护法中分别予以规定。《消费者基本法》、《电子交易消费者保护法》、《访问销售法》、《标识·广告法》等法律均对消费者作了定义。《消费者基本法》第2条第1款将消费者界定为“用于作为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而使用企业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的人,或者由总统令指定的用于生产活动的人。”韩国学界认为,立法并没有把消费者限制为自然人,如果法人为了非商业目的而购买消费品,也可作为消费者看待。⑨
其次,三国立法对当事人准据法选择权的赋予存在差异。在传统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决定合同关系准据法最重要的连结因素,这一连结因素对于当事人都是商事主体的普通合同来说是合适的。[15]在消费者合同中,消费者缺乏主动、充分的选择性,如果不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加以限制,消费者的权益就难以得到保障。中日韩三国立法均对消费者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出明确限制,但程度有所不同。在选择准据法范围上,《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立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即仅承认消费者单方的选择,但限定了选择结果,即仅限于选择“商品或服务提供地法”。[16]与中国不同,《日本通则法》、《韩国国际私法》都未限定选择准据法的范围,当事人双方可通过协商自由选择适用其他法律,条件是不能剥夺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给予消费者的强制性保护。在准据法选择方式上,《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并未规定消费者的选择方式,但该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这表明,《中国法律适用法》要求当事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应当明示,不承认当事人以默示方式选择法律。《<中国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8 条第 2 款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这种方式可以视为默示的选择,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有限度地承认默示选择。[17]不过,《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仅赋予消费者单方选择权,因此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消费者合同。从国际范围观察,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各国普遍接受明示选择,对默示选择的态度则有所区别,有的国家甚至不承认默示选择法律的效力,如土耳其、尼日利亚、秘鲁。[18]P57这是因为,既然意思是不明确的,那么根据这种意思推定的准据法就很有可能不是当事人想要选择的法律。[19]P76-78不过,韩国有条件地承认当事人对准据法的默示选择。《韩国国际私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合同适用当事人明示或默示的选择。但默示选择以能够通过合同内容或其他所有相关情况被合理认定为限。”《日本通则法》第7条规定:“(由当事人选择准据法)法律行为的成立及效力,适用行为时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该法第11条第4款规定,“消费者合同的成立,依本法第7条的规定,选择了消费者经常居住地法的情形下,该消费者合同的形式要件,消费者对经营者明示需适用消费者经常居住地法的,不受本法第10条第1款、第2款和第4款的约束,适用消费者经常居住地法。”因此,可以将日本法的规定理解为:如果法律特别规定当事人应以明示方式选择消费者合同的准据法,则应以明示方式选择;如果法律无特别规定,则当事人既可以明示方式,亦可以默示方式选择消费者合同的准据法。
最后,三国立法对消费者是否受其经常居所地法律的强制保护不同。由于消费者最为熟悉的法律是其经常居所地法律,且经常居所地法律往往会对消费者给予特别保护,因此《罗马规则Ⅰ》确立了如下规则:“不得减损消费者经常居所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给予他的保护。”中日韩三国立法对这一规则的贯彻程度有所差异。《日本通则法》第11条规定,“如果消费者表示需要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的,该消费者合同的成立及效力,适用该强制性规定。”《韩国国际私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即使当事人选择了准据法,也不能剥夺由消费者的经常居所地国家的强制性规定赋予消费者的保护。”尽管《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但根据《中国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10条,消费者合同并未明确纳入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范围。如果将该司法解释第10条的规定理解为消费者保护不适用《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则会造成《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对消费者保护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当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时,消费者就不能行使单方选择权,只能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消费者此时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商品、服务提供地的法律对消费者保护程度和水平低于消费者经常居住地的保护程度和水平,是否仍要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如果仍要适用,就与第42条的宗旨(保护消费者)相悖,显然是不合适、不合理的,[20]更与国际私法保护弱势群体这一主流趋势相违背。也就是说,如将《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规定的消费者合同排除在强制性规则保护范围之外,就会导致赋予消费者单方选择权的规定不够严谨,不仅未达到保护消费者的预期效果,反倒会被商家利用该规定的漏洞而逃避某种法律的适用,最终导致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实质性的保护。[7]另外,如果认为消费者保护不适用《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还会出现如下奇怪的现象:“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在强制性规则的保护范围之内,但同样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却不在强制性规则的保护之列。[21]不过,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就《<中国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答记者问时谈到如何把握该司法解释第10条的“强制性规定”时,明确提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并指出该条是“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解决可操作性问题”。[22]这似乎意味着,虽然该司法解释第10条未明确将消费者保护列入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范围,但中国法院仍可适用该条第(六)项“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条款,将消费者合同解释为应在适用中国法强制性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过,为避免司法适用中的分歧,中国法律应当就消费者是否在强制性规则保护范围之内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
五、东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统一化的基本路径与制度建构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可见,中日韩三国在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领域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如此情势下,东亚地区在此领域的法律统一化是否还有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日韩三国均在此领域信奉相同的法律理念、采取了相同的法律设计模式、法律规则的核心内容亦非常接近。且三国法律制度的差异都是细节性的、技术层面的,可以通过协商、谈判予以解决。
近年来,消费者合同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已经在世界各地展开,[23]P693-712欧盟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全面考虑到了整个欧洲范围内的统一。[24]《罗马条例I》是欧盟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最新统一立法,也是国际私法统一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25]P95-98《罗马条例I》第6条是针对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在详述部分第23-31条对其进行了详细解释,条例第27条也将消费者合同纳入了复审条款。[18]P32受欧洲的影响,美洲国家近年来也针对跨境消费者保护国际私法的统一,提出一系列的国际私法公约草案,如巴西政府提交的《美洲国家跨境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公约草案》。[7]为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和法律一体化,保护跨境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增加消费者跨境消费的信心,中日韩不妨借鉴欧盟、美洲国际私法统一化实践,借力自贸区谈判经验,通过签订多边条约方式,尽快推动东亚地区消费者合同国际私法的统一进程。鉴于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与跨境消费相关的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私法立法、司法解释和学术探讨对此所做出的积极回应,中国应在此统一进程的谈判中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可由中方先主持完成条约草案,再由中日韩三国通过协商谈判确定其内容。国内法与条约不一致的,由缔约国立法机关进行条约转化,以避免法律适用冲突。
在制度建构上,东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统一规则首先应基于中日韩消费者合同冲突法的现行规范,顺应整个国际私法对消费者等弱势群体提供实质保护和人文关怀的发展趋势,重述相同规则、统一差异性规则、适当补充尚待明确的规则。
首先,建议该统一规则将消费者限定为自然人。消费者范围的核心争议在于是只包括自然人还是扩张到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此,韩国学术界的态度是在法人进行非商业目的的消费行为时,可以视为消费者。[26]韩国之所以有如此观点,主要是基于立法者不仅保护用于生活消费的自然人,而且还要保护经济活动中弱者的立法理念。[14]P13日本近年来也有意将处于弱势地位的法人纳入到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之中[27]P243-245。笔者认为,虽然日本、韩国已经有将消费者由自然人扩张至一定情形下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趋势,但多存在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中国虽有个别判决认可法人的非商业消费受《中国消法》的保护,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仍认为消费者仅限于自然人。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求同,减少统一化障碍,建议在统一化的初期阶段将消费者限定为自然人。
其次,建议该统一规则在排除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前提下,赋予消费者对准据法的单方选择权,并适度扩大选择范围;如消费者未作选择,则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在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上,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的规定均对当事人意思自治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日本通则法》、《韩国国际私法》较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于消费者合同的成立与效力,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以外的法律作为准据法;如果未作选择,则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中国法律适用法》采取了与日本、韩国不同的规定,赋予消费者单方选择权,不过所选择的法律种类受到限制,只能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和商品、服务提供地法之间进行选择,未作选择时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如果经营者未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则只能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相比之下,对消费者保护程度较高的规则是赋予消费者对适用法律的单方选择权。笔者建议,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方面,法律统一方案应在借鉴中国做法的基础上,扩大消费者单方选择的准据法范围,只要连接点与合同密切相关即可。如果消费者未行使选择权,则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
最后,建议该统一规则区别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分别设计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规则。根据《日本通则法》第11条规定,对于消费者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无论当事人合意选择何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只要消费者表示需要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的强制性规定,则该消费者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均应适用该强制性规定。[28]韩国规定在三种情形下,即使当事人选择了准据法,也不能剥夺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国家强制性规定赋予消费者的保护。[29]中国在此方面则没有明确规定。从国际范围观察,多数国家和地区关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强制性规定的适用与韩国类似,[30]P848-850并不要求消费者主动提出需适用其经常居所地强制性规定,而是法官对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和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进行比较,适用对消费者更有利的法律。日本则要求消费者提出主张方能适用,这是日本法与其他立法例的不同之处。对此,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有关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规则对消费者保护力度不够。[31]但是,日本实务界则认可现行法的规定,并认为由法官对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和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进行查明、比较,会加大法官的负担,不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32]
笔者认为,在统一规则中,涉及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强制性规定的适用时,应区分主动消费者和被动消费者。所谓主动消费者,是指自己主动离开其居所地到外国经营者所在国家缔结消费者合同的消费者。所谓被动消费者,是指本身没有意愿和外国经营者缔结合同,而是受到外国经营者广告诱使或要约邀请在其居所地缔结合同的消费者。之所以区分主动消费者和被动消费者,一是为了对被动消费者进行更好的保护,二是为了顾及经营者利益,鼓励经营者将其产品更多地投放到国际市场。[33]就主动消费者而言,日本将是否适用经常居所地法的强制性规定的决定权交予消费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对消费者意思自治的尊重,另一方面降低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不过,就被动消费者而言,为了避免形式上的意思自治给消费者造成的实质不利,宜借鉴韩国做法,由法官直接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的强制性规定。事实上,《日本通则法》第11条第6款规定的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四种例外中,有两种情形旨在保护被动消费者。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统一规则中,对于主动消费者,应赋予其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强制性规定的决定权;对于被动消费者,则规定直接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的强制性规定。
注释:
① 在2016年8月于韩国首尔召开的“中日韩跨境消费救济”国际研讨会上,韩国消费者院法制研究部Kim Sung Cheon部长、日本国民生活中心咨询部Daisuke Hayashi部长、中国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保护局张道阳处长等官方代表都表达了此意向。
② 该条规定:“1.消费者以职业或营业活动外的目的签订的合同,如有下列各项情形之一时,即使当事人选择了准据法,也不能剥夺由消费者的经常居所地国家强制性规定赋予消费者的保护:(1)在签订合同之前,消费者的相对人在该国从事通过广告的交易的劝诱等职业或营业活动,或在该国之外的地区对该国进行了通过广告的交易的劝诱等职业或营业活动,且消费者在该国进行了签订合同的必要行为的;(2)消费者的相对人在该国接受消费者的订单的;(3)消费者的相对人诱导消费者到外国发出订单的。2.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时,根据第1款规定的合同,排除第26条规定的适用,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3.根据第1款规定的合同形式,排除第17条第1款至第3款规定的适用,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4.根据第1款规定的合同,消费者可以在其经常居所地国家对相对人提起诉讼。5.根据第2款规定的合同,消费者的相对人对消费者提起的诉讼,只能在消费者的经常居所地国家提起。6.根据第1款规定的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书面进行国际裁判管辖约定。但是,该约定只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有效:(1)争议已经发生的;(2)根据本条的管辖法院之外,允许消费者可以在其他法院提起诉讼的。”
③ 该条规定:“1.个人消费者(不包括经营者出于营业目的作为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下同)与经营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为营业为目的的个人,下同)之间订立的合同(不含劳动合同,本条中均称“消费者合同”)的成立与效力,即使依本法第7条的规定选择或依本法第9条的规定变更合意适用的法律为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以外的法的情形时,如果消费者表示需要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的,该消费者合同的成立及效力,适用该强制性规定。2.消费者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未依本法第7条的规定作出选择的,不受本法第8条的规定的限制,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3.消费者合同的成立,尽管依本法第7条的规定,选择了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以外的法的情形下,该消费者合同的形式要件,消费者表示需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的,不受本法第10条第1款、第2款和第4款的限制,适用该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中的强制性规定。4.消费者合同的成立,依本法第7条的规定,选择了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的情形下,该消费者合同的形式要件,消费者对经营者明示需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的,不受本法第10条第1款、第4款的限制,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5.消费者合同的成立,未依本法第7条的规定作出选择时,不受本法第10条第1款、第2款和第4款的约束,该消费者合同的形式要件,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6.本条的各项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适用:“(一)消费者前往经营者的营业所订立消费者合同,且该经营者的营业所所在地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在不同法域的。但经营者在营业所所在地区邀请消费者前往其营业所订立合同的除外。(二)消费者基于消费者合同须在经营者营业所所在地受领履行或被认为是受领履行,且该经营者的营业所所在地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在不同法域的。但是,消费者受经营者邀请在经营者营业所所在地受领了全部债务的履行的除外。(三)订立合同时,经营者不知道且有充分的理由不知道消费者经常居所地的。(四)订立合同时,经营者误认且有充分的理由误认交易相对人非消费者本人的。”
④ 该法是中国第一部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为内容的单行法律,体现了中国国际私法领域立法的现代化。
⑤ 该条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
⑥ 合同关系准据法的确定首先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其次是特征性履行或最密切联系原则。
⑦ 参见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 政治与法律》, 2002, 2;屈茂辉, 胡蔷薇:《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的修正》,《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 2;孟勤国, 戴盛仪:《论“消费者”之界定要件》,《理论月刊》, 2015, 2。
⑧ 观点来自中日韩跨境消费救济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关西大学Karaiskos Antonios教授对本文的点评。
⑨ 该观点得到韩国消费者法研究会会长徐锡熙教授确认,他的原话是:“In Korean Consumer Law consumer includes legal entities, which differs from Japanese law. If a legal person buys a thing for just consumption purpose, then it is treated like a consumer.”
⑩ 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三)涉及环境安全的;(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五)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1] 肖永平, 周晓明. 冲突法理论的价值追求 [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3.
[2] 徐冬根. 人文关怀与国际私法中弱者利益保护 [J]. 当代法学, 2004, 9.
[3] 贾明顺, 夏春利, 张欣. 国际私法中弱者保护与意思自治问题探究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
[4] 苏号朋. 格式合同条款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 Ole Lando. Consumers Contracts and Party Autonomy in the Conflicts of laws [J].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42, Issue 1, 1972.
[6] T. C. Hartley. Consumer Protection Provisions in the EEC Convention [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1982.
[7] 于颖.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评析 [J]. 法学评论, 2011, 2.
[8] Recommenda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nference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inal Act of the Fourteenth Session,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19, 1980, 6.
[9] 肖永平.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J]. 法学论坛,2011, 2.
[10] 沈涓. 国际私法学的新发展 [M].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 2011.
[11] 郭玉军.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反思及其完善[J]. 清华法学, 2011, 5.
[12] 杨志仁. 国际消费合同的法律适用研究 [J]. 学术探索, 2014, 2.
[13]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3419号民事判决.
[14] 崔吉子. 东亚消费者合同法比较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5] Mario Giuliano, Paul Lagarde.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R].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0,C282.
[16] 许军珂. 论消费者保护的法律选择模式 [J]. 法学家, 2011, 5.
[17] 吕岩峰. 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法律实践 [J]. 法治研究, 2013, 11.
[18] 凡启兵. 《罗马条例Ⅰ》研究,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19] 沈涓. 合同准据法理论的解释,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20] 张兴旺. 论国际消费合同的法律适用 [J]. 前沿, 2013,3.
[21] 张丽珍. 关于中国涉外消费合同法律适用规定的思考 [J]. 消费经济, 2013.6.
[22] 张先明. 正确审理涉外民事案件 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EB/O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1/id/810388.shtml,2017-10-22.
[23] Arroyo, Diego P. Fernandez. Current Approach towards Harmonization of Consume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mericas [J].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7, Issue 3 and 4, 2009.
[24] 范征, 王凤华. 欧盟统一大市场中的消费者保护一体化研究 [J]. 法学, 2000, 10.
[25] Gillies, Lorna E. Choice-of-Law Rules for Electronic Consumer Contracts: Replacement of the Rome Convention by the Rome I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Issue 1, 2007.
[26] 【韩】徐锡熙. 比较法视野下对韩·中·日消费者法的考察 [J]. Ilkam法学, 2016, 33.
[27] Mankowskiu Peter, The New Japa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ct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C].Japa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2015,6.
[28] 【日】阿部耕一. 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效力(第7条)、不法行为(第11条)相关规定的重新审视、消费者保护规定 [J]. 金融法务, 2008, 4.
[29] 【韩】李秉钧. 国际私法视野下对国际消费者合同的考察 [J]. 国际私法研究2017,1.
[30] Conklin, William E. The Peremptory N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 3.
[31] 【日】西谷祐子. 消费者合同及劳动合同的准据法和绝对性强行法规的适用问题 [J].国际私法, 2007, 9.
[32] 李旺. 关于日本新国际私法的立法——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介评 [J]. 环球法律评论, 2007, 5.
[33] 向在胜. 日本国际私法现代化的最新进展——从《法例》到《法律适用通则法》[J].时代法学, 2009, 1.
StudyonUnificationofLawApplicationofConsumerContractinEastAsia
SuHao-peng,GuoJing-jing
(Law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During recent years, the cross-boarder transactions have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among China, Japan and Korea, as well as the consumer contract disputes. However,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protection for consumer granted by China, Japan and Korea impacts th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nify the application of law related to consumer contracts in East Aisa. The common character of the provisions related to consumer contracts containing foreign affairs in the laws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is the basis and support to unify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is regard. Although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among the laws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such discrepancies are not material, which would impede the unification of laws.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grated protection for cross-boarder consumers in East Asia, we hereby assume to unify the definition of consumer, scope of autonomy of will, and application of mandatory requirements, through multilateral treaties basing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regarding consumer contracts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consumer contracts; application of law; East Asia; residence; unification of law
1002—6274(2017)06—038—09
DF525
A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格式条款立法缺陷的清理及修法方案研究”(13BFX09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消费者合同解释的比较研究”(2014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撰写得益于中日韩跨境消费救济国际研讨会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与评论,在此对他们表达谢意,尤其感谢韩国消费者法学会会长Seo Hee Seok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Lee Byung Jun教授以及日本关西大学Karais kos Antonios教授对本文部分观点的指正。
苏号朋(1970-),男,山东济宁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法基础理论、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郭静静(1988-),女,河南信阳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合同法、消费者保护法。
(责任编辑:唐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