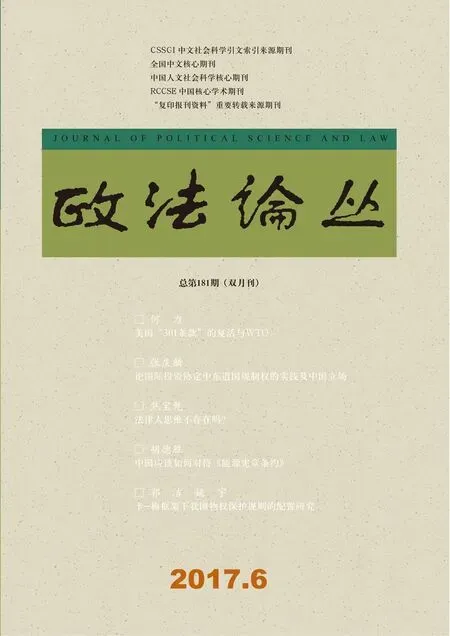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价值的冲击与立法应对*
2017-01-26孟凡壮
孟凡壮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241)
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价值的冲击与立法应对*
孟凡壮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241)
克隆人技术发展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可被用于“生育”孩子、治疗疾病和怀念故人。但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宪法上的生命价值、人的尊严、社会和家庭秩序构成强烈冲击,需要积极予以立法应对。在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过程中,应当以宪法上的生命与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遵循宪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参与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必要的平衡。展望未来,我国应当以生命和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进行合宪性调整。
克隆人技术立法 生命与人的尊严 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明确性原则 比例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末生命科学的三大突破——基因工程、人体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兴起,预示着21世纪会成为生命科学的世纪。[1]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经开始迫切地想用科技去改造、甚至创造新的生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生命技术便是克隆人技术。通过克隆方式产生一个孩子,在很多情况下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克隆人技术可以作为生育孩子的方式,对于不孕不育的夫妇或想过单身生活的人,克隆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生育选择。对于一方具有基因遗传病的夫妇,若其不愿让孩子冒携带遗传病的风险,通过克隆人技术,可以克隆没有携带遗传病的一方,产生克隆孩子。克隆人也能被用于扩大非传统的家庭选择。克隆人是同性生育的重要突破,有助于实现同性恋者的生育权。比如,纽约的一个同性恋活动组织克隆权利联合战线(Clone Rights United Front)反对纽约禁止克隆人的立法提议,认为克隆人是同性生育的重要突破。在有些情况下,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可能被用于产生一个孩子,以寄托父母对已故的孩子的思念之情。有些父母可能为了寄托对故人的怀念之情而希望克隆他们已故的孩子。[2]克隆人技术在医疗方面也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在治疗性克隆技术方面,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对人类克服诸多疾病带来希望,比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等历来难以克服的疾病有望得到缓解。并且,在当前诸多病人需要的人体器官极度短缺的情况,治疗性克隆技术通过对胚胎干细胞的引导,能够使其发育成人体所需要的器官。但正如有学者适切地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给宪法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宪法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冲击。[3]克隆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宪法保护的人的价值也构成强烈地冲击和威胁。而如何对迅速发展中的克隆人技术予以适切地法律规制便是本文的核心命题。
二、人类克隆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克隆是由一个个体通过无性繁殖方式产生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4]P283克隆是从英文的“clone”一词音译而来的,而英文的“clone”是源于希腊语的“Klon”。“Klon”在希腊语中意思是“细枝”,希腊人了解到折下有些树的枝条予以栽培,将会复制该树。[5]P17“克隆”这一最初与园艺学相关的概念后来被用于描述动物的“无性生殖”。克隆被用于描述人的无性生殖时,出现了“克隆人”、“生殖性克隆”等概念。人或动物的克隆有多种方法,主要包括卵裂球分离、胚胎分裂和细胞核置换。卵裂球分离是通过分裂细胞期胚胎(如2-8细胞期胚胎),使其形成多组相同的卵裂球,进而发育成多个相同个体的一种克隆方法。胚胎分裂是通过将有性生殖产生的受精胚胎分裂为两个或多个胚胎以产下具有相同基因组的人工双胞或多胞胎。细胞核置换是指将成年供体细胞(体细胞含有完整的染色体)的细胞核转移到去核的卵子细胞(卵母细胞)。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进行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体细胞内取出细胞核置换到去核卵子中,通过电击使得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发育成胚胎、随后将胚胎移植到子宫发育成新的个体。克隆羊多莉便是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的。本文探讨的克隆人技术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克隆胚胎用于提取干细胞从事治疗研究或用于产生新的人类个体的技术。
克隆一词运用于人类的时候,存在 “克隆人”、“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等概念。“克隆人”是比较常用的概念,通常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作动词时指运用克隆技术产生人类个体的尝试,作名词时指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人。治疗性克隆是以治疗为目的,借助克隆技术产生胚胎干细胞。[6]生殖性克隆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一个新的人类个体,相当于动词意义上的“克隆人”。生殖性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人体细胞中取得细胞核,将妇女的卵母细胞去核,通过电击等方法使得体细胞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使其发育成人体胚胎,然后将该胚胎移植到妇女子宫内进一步发育成胎儿,进而产生克隆孩子。生殖性克隆与人类传统的有性生殖截然不同。有性生殖是通过精子与卵子结合为受精卵,发育成胚胎进而形成胎儿、产生孩子的过程。此种方式产生的孩子的基因来自提供精卵的男女双方。生殖性克隆是一种无性生殖,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克隆孩子的基因结构几乎完全复制了供体的基因结构。克隆人技术与动物克隆技术在技术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克隆人技术的最初发展体现为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1938年,德国生物学家汉斯·斯佩曼(Hans Spemann)提出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进行动物克隆的设想。1952年,美国胚胎学家布利格斯和肯恩成功克隆青蛙早期胚胎细胞。1958年,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格登的研究团队成功克隆蝌蚪。1996年7月5日,英国的威尔慕特用成年羊体细胞克隆出克隆羊“多莉”,打破了科学界关于细胞分化不可逆的想法,很多其他的哺乳动物相继被成功克隆出来。2001年11月,美国一家先进细胞技术公司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7]P1-22015年12月,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已经掌握了最先进的克隆人技术,从事人的克隆已经在技术上完全可能。①
三、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价值的冲击
作为20世纪末生命科学革命重要的突破之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能够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宪法保护的价值带来了巨大冲击。
(一)克隆人技术对生命价值的冲击
克隆人技术的研究首先给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带来巨大冲击。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会在医学研究领域带来突破,尤其面对当前用于器官移植的人体器官极度匮乏的状况,治疗性克隆技术的发展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治疗性克隆研究的过程需要从克隆胚胎中提取胚胎干细胞,必然要损害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的生命。在医学研究领域,科研工作者以治疗疾病和保障国民健康的名义故意损毁胚胎,对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构成侵害。在生殖性克隆领域,克隆人技术目前还不成熟,克隆孩子可能面临严重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方面风险。动物克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动物克隆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成功率很低。动物克隆技术尽管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但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便是其成功率很低、克隆出来的动物可能存在生理和免疫方面的缺陷。有学者指出,动物体细胞克隆的成功率很低,目前公认的成功率在1%-3%,克隆胚胎移植后的出生率平均不到10%。[8]在277只克隆羊实验中,只有一只羊(克隆羊多莉)得以存活。[9]P811第二,基因异常、疾病与畸形。动物克隆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疾病或遗传性畸形问题。20世纪50年代对于青蛙的克隆实验有时会出现遗传性畸形。在德克萨斯州的格林纳达公司曾经运用分化的胚胎细胞对牛进行克隆时,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异常大,有些出生时便重达180磅,比正常75磅的出生重量的两倍还多。并且,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伴随着疾病,比如糖尿病、心脏肥大,有18%-20%的克隆牛,出生后死亡了。克隆羊多莉诞生后,克隆多莉的科研团队利用胚胎细胞进行转基因动物克隆。这次试验中,团队将羊的胚胎细胞的DNA转移到425个去核卵子中,有14个成功受孕,最后只有6只羊成功被克隆出来,有些羊的重量是正常羊体重的两倍。实验中的高死亡率预示着克隆可能实际上会破坏细胞的DNA。此外,克隆人也可能面临分化细胞基因片段的重新排列,此类重新排列会使得克隆人产生问题。[10]P651-652第三,过早老化问题。当前科学界没有研究清楚细胞老化的过程,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克隆孩子很可能会遗传供体的年龄或基因钟,这可能导致克隆人是短命的。②克隆动物成功率低、畸形问题和早期死亡问题意味着通过克隆人技术生产人类个体也会面临同样的遭遇。而有意制造可能有缺陷的人,这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
(二)克隆人技术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冲击
克隆人技术也对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带来了冲击。克隆人技术会改变“人”的生物学基础,对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概念带来冲击。对人类传统生育方式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由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传统生殖领域中性交生殖的基本模式,其最初的发展面临社会的重重阻力,随着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诞生,人们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的人工辅助生殖方式。而当前的克隆人技术将会更加深刻地改变生育观念中关于“人”的基本概念,[11]因为通过克隆人技术生育的孩子与传统生育方式和当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具有本质的差别,其不是基于精卵结合的产物,而是对已经存在的基因的复制。克隆人技术能否作为一种新型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已经不是一个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问题,因为哺乳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克隆人技术已经具有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尽管其安全性目前仍然被人们所担忧。克隆人技术能否被不孕不育的夫妇用于产生孩子已经成为一个在价值观念和法律规范领域应不应当允许的问题。这便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基本概念。宪法学必须要回答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的克隆人是不是宪法上的“人”,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一个孩子是否在传统宪法上生育权的保护范围。在宪法上是要坚持关于“人”和“生育”的传统观念,对克隆人技术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还是要随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对宪法概念的内涵作出适当地调整,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克隆人技术,这也是宪法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当前的宪法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宪法学并没有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对于什么是宪法上的“人”并没有形成稳固的宪法基础理论,对于宪法上生育概念的生物学基础也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另一方面,克隆人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一日新月异的技术做宪法学上的判断,需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并且判断的过程必然具有极大的推测性和不确定性,比如克隆人技术对克隆孩子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其实难以形成确定性的科学证据,对其进行判断必然是具有推测性的。
生殖性克隆还涉嫌侵蚀人的自主与自由意志,侵犯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生殖性克隆方式产生的孩子会丧失掌控自己生活和个人信息的能力,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NBAC观察指出:细胞核置换的克隆,在某种程度上,为完全控制一个孩子的发展的重要方面(基因)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完全的控制,这种控制引发了根据一定的规格生产孩子的想象。如果克隆人是被创造出来满足被克隆者的虚荣心或满足已经存在的个体的需求,比如一个孩子需要骨髓,它可能会降低克隆人的人格。从死去的孩子上克隆的孩子,在获得自身内在价值方面,有相对少的机会。[12]P52-74我们在一个基因决定的时代,DNA的发现者之一James Watson和人类染色体工程主任指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命运在星球之中,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命运在我们的基因之中。”[13]P217大量的心理成长的研究说明,孩子需要一个自治的意识。这对于从其父母或死去的孩子那里克隆出来的克隆人来说非常困难。尽管克隆人可能不相信基因决定,被克隆的生活将会一直萦绕于克隆人,对于克隆人的生活造成不适当的影响,并以一种其他人不会遭遇的形式形塑克隆人。[14]P1686生殖性克隆通过复制他人的基因而克隆孩子,使得克隆孩子像工厂的产品一样,被有计划地设计与生产出来,故意创造一个基因与其他人相同的孩子涉嫌对宪法上关于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价值构成挑战。
生殖性克隆还有影响克隆孩子的自我印象,涉嫌侵犯其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克隆人与天生的双胞胎非常不同。对于双胞胎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开始于未知,因此,与其他非双胞胎一样,保持着对于未来的选择。据此,一个人的基因组对其未来影响的未知,对于自发、自由而真实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和自身,是必不可少的。克隆人影响了孩子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15]P561-567
宪法学必须要回答克隆人技术是否侵犯了宪法上人的尊严的问题。基因独特性是否是宪法上人的尊严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人的尊严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判定是否侵犯了人的尊严的方法有哪些,在宪法学上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即使在人的尊严价值得到广泛运用的德国,人的尊严也被批评囊括的内容过于宽泛。并且,在克隆人技术领域,伦理层面的人的尊严与宪法上的人的尊严交织在一起,而如何在宪法规范层面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关于人的尊严的判断标准也面临挑战。
(三)克隆人技术对社会与家庭秩序的冲击
克隆人技术还对宪法上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带来冲击。在社会秩序方面,克隆人技术可能会被滥用。生殖性克隆可能会带来人类个体的商品化。波士顿学院的神学家Lisa Sowhill Cahill指出生殖性克隆可能会导致人的基因的商品化,也会导致对人类基因的操纵以生产社会期待的孩子。[16]P60生殖性克隆可能会让社会逐渐认为孩子是一种可批量制作的“产品”,克隆人可能成为“可被用于拆卸为备用零部件”被制造的目的仅仅在于医疗用途,比如要求其捐献其器官。[17]P65有些想追逐“长生不老”的人可能会通过克隆孩子寻求需要移植的人体器官,使得克隆孩子成为人类器官的储存器。此外,克隆人会被提前知道其基因构成,因此克隆人可能受到非难或歧视。比如,如果某人被克隆,年轻时便死于遗传性疾病,该年轻人的克隆人可能会被要求保险或遭受就业歧视。
生殖性克隆对个体概念的侵蚀会影响整个社会关于“人”的观念的变革,进而会冲击传统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结构。有学者指出,对于自己或他人,具有被提前决定的基因身份,其隐私与自主可能会被严重削减。不顾及个人或公众知晓被克隆人。克隆技术可能会通过侵蚀个性的概念而扩大对社会的影响,而个性概念是隐私与自主观念的核心。克隆除了会削弱个体的自由意志外,还会削弱那些致力于培育个人自主及禁止对个体进行强制操纵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18/]P498
生殖性克隆复制人类基因,可能会对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构成威胁。克隆人的前景引发了对社会整体影响的诸多严重关切。克隆可能会影响到进化,因为它会提升基因的单一性,由此会提升危险性,因为克隆人对于将来的某些疾病会没有抵抗力。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George Johnson教授反对克隆人,因为“基因多样性是我们应对不确定未来的首要防御。剥夺基因多样性,哪怕是部分的,也会威胁到我们的物种。”[19]遗传的适应性使得人类能够生存,生产基因相同的人会威胁到人类。尽管克隆羊已经怀孕了,克隆人能否怀孕也值得关切。尽管存在上述危险,也有评论者认为如何克隆人被限制在极少数情形下,那么人类的进化不会受到影响,其对人类的基因库的影响也不会高于自然生育的双胞胎对人类的基因库的影响。[20]
在家庭秩序方面,在传统观念中,男女结合生育孩子、繁衍后代是他们缔结婚姻、构建家庭的核心目的之一,而克隆人对于婚姻与家庭在营造生育环境的重要地位上构成重要冲击。生殖性克隆会改变传统上父母子女关系的认定,因为克隆人是被克隆者的基因的复制,克隆人与被克隆者与自然性交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与其父母的关系不同,不具有在遗传学上的继承性,这样以来,可能会导致代际关系的混乱,对宪法保障的伦理秩序构成冲击。在家庭关系中,生殖性克隆产生的克隆孩子会更像物而不是人,因为克隆孩子是被设计和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礼物。此外,在有些特殊情况下,生殖性克隆产生的孩子可能会面临不合理的期待。比如,当克隆孩子的基因是源自于夫妇死去的孩子的基因,这时可能被这一夫妇视为第一个孩子的替代品,而对于第一个孩子的个性等特征的期待往往会被强加于第二个孩子之上。但实际上,由于后天环境的不同,克隆孩子与第一个孩子在基因上虽相同,但在性格特征等方面会有差异。由于经历了失去孩子的痛苦,夫妇可能对于克隆孩子会过度保护,并会将第一个孩子的喜好强加于克隆孩子身上。此外,对于克隆孩子基因是源于优秀运动员的情况,夫妇对克隆孩子往往具有一定的期待,但克隆孩子的发展可能会与夫妇的期待相背离,比如克隆孩子可能会摔伤了腿而不能做运动员。[21]P653宪法应当如何应对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保护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的冲击也是宪法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总之,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宪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也为宪法(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而如何通过宪法规制克隆人技术的立法,为克隆人技术的研究确立界限,保护生命和人的尊严价值,并在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合理的平衡是无法回避的宪法命题。
四、克隆人技术发展的立法应对
面对克隆人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国家应当积极予以立法应对,并要在立法中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贯彻尊重和保障生命与人的尊严的宪法价值。
(一)生命与人的尊严作为立法的价值基础
在人类的文明演进中,人们选择通过宪法治理国家的根本的目的在于保障生命与人的尊严。生命和人的尊严是自由和其他宪法价值所依存的根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的生命和尊严价值的威胁不再仅局限于自然灾难,而更来源于科技的发展。科技能够为自由和权利提供物质基础,也能够摧毁人们的生命和尊严。宪法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要维护有益于人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科技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毁灭性破坏。如何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捍卫人的生命和尊严价值是现代宪法的核心主题。科技发展中对功利主义价值和自由主义价值的过分强调,会威胁到人们更为根本的生命和尊严价值,这背后也交织着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研究人员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普通民众对于科技发展的盲目崇拜。在这一背景下,宪法应在科技发展中担当护卫生命和人的尊严价值的角色。在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中,应当通过生命与人的尊严价值来抑制克隆科技发展的非理性,科学研究自由与生育权的价值的实现应当以人的生命与尊严价值的保障为基础和前提。
在克隆人技术立法方向的选择与立法的过程中继续坚持生命与人的尊严价值在立法中的价值引导作用。对此,首先需要培育国家公职人员尊重生命和人的尊严的宪法意识。克隆人技术立法的提出、起草和讨论过程都是由国家公职人员主导的,公职人员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应有法治思维,还应当具有宪法思维。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公务员都要严格按照宪法办事,养成维护宪法的意识,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以宪法作为其行为的最高准则。[22]国家公职人员应当在立法的过程中维护宪法至上的思维,重视生命与人的尊严在宪法价值中的基础地位,在立法的过程中主动贯彻尊重和保障生命和尊严价值的理念。此外,还应当重视培养科研人员、伦理学家和普通民众等群体尊重生命和人的尊严的宪法观念。在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过程中,科研人员和伦理学家是重要的立法起草参与人,其对于生命和人的尊严所持有的立场和观念直接影响到立法对于克隆人技术的整体的规制方向和具体的规制方式。科研人员和伦理学家有时会基于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念影响立法过程,对此应当培育其尊重生命和尊严的宪法意识。另外,还要培养民众的尊重生命和尊严价值的宪法意识。公民宪法意识是推动宪法实施和民主政治、法治发展的精神动力,公民对于生命和人的尊严所秉持的态度,对于克隆人技术立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家对于克隆人的立法往往缘起于民众对于克隆人技术带来的危害的忧虑。
(二)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
由于克隆人技术立法涉及生命权、人的尊严、生育权和科研自由等重要的基本权利,立法内容涉及对违法行为的刑罚和行政法处罚,根据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应当由议会通过法律予以规制。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立法机关的法律作出。[23]在德国,基本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律保留原则,但可以从基本法第20条第3款的法治国原则和基本权利的保护条款中推导出来。[24]在我国,根据宪法第2条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和宪法第62条授予全国人大对刑事、民事等基本法律的制定权和修改权等规定,都可推出法律保留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③宪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中得以具体化。从世界各国克隆人技术立法的相关情况来看,由议会(国会)讨论通过克隆人技术相关法律是比较普遍的。很多国家甚至将立法规制的层级上升到宪法高度,对于立法主体的正当性要求更高。而当前我国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规制主要体现于卫生部与科技部的部门规章,立法层级太低,违背法律保留原则。
此外,克隆人技术立法不仅涉及民众的生命健康,还涉及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群体的意见,这是宪法上民主参与原则的基本要求。根据宪法学基本原理,立法过程应当公开并保障立法的民主参与。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是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宪法原则。在我国,民主参与原则体现于宪法和《立法法》之中。根据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有参与国家立法事务的民主权利,这一权利在《立法法》第5条中得以具体化。根据立法第5条的规定,应当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克隆人技术立法过程中应当重视如下几个群体的参与:第一,法学家。克隆人技术立法涉及重要的法学问题,应当有法学家的参与。第二,伦理学家。克隆人技术立法也涉及重要的伦理问题,克隆人技术立法起草工作也应当吸纳伦理学家的参与。第三,科研工作者。克隆人技术立法过程中,克隆科技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必要的。克隆人技术立法也会涉及专业的概念和克隆技术的控制问题,这都需要克隆人技术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的参与。第四,民众的意见。克隆人技术立法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听证程序等方式吸纳民众的参与。克隆人技术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有助于确保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也有助于提升民众和科研人员尊重生命和人的尊严的宪法意识。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过程中民主参与原则也没有得到贯彻。我国2003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就存在概念模糊,立法程序民主参与不够等问题。[25]
(三)遵循法律明确性原则
克隆人技术立法涉及对公民财产和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其在立法内容上应当具体、明确,符合宪法上的法律明确性原则。最初,法律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部分在刑罚领域发挥作用。二战以后,德国《基本法》第80条第1款有关“联邦政府、联邦部长或州政府根据法律的授权颁布行政法规。此项授权的内容、目的与范围应以法律规定之”的规定创设了授权要件明确性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自此成为一项独立的宪法原则。[26]法律明确性原则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的补充和细化,是为了防止因为限制性规范内容模糊而造成基本权利被过度限制。[27]P191-192在美国,法律明确性原则在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中演绎出“不明确即无效原则”(void for vagueness doctrine)。所谓“不明确即无效原则”是指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必须是意旨明白、清晰无误的规制,否则,该法律就违宪无效。④法律明确性原则作为法律保留原则的补充和细化,也应当被视为我国宪法上的基本原则。2015年我国《立法法》第6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第2款,对于法律规范的明确性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克隆人技术立法也应当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当前我国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规制也存在立法不明确的问题。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克隆人技术立法应按照立法明确性原则的要求,在立法规制的对象、措施、范围等方面要明确、具体。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违背法律明确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立法规范的对象方面不够明确。在生殖性克隆方面,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关于禁止生殖性克隆的规定,在规制对象方面,禁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人员”、“医务人员”以及从事涉及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活动的人员从事生殖性克隆,但立法对于上述人员之前的其他人员是否可从事生殖性克隆并不明确。在治疗性克隆方面,国家对于从事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人员的限制性规定涉及的对象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涉及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活动”的人员,这一规定也是比较模糊的,是否包括所有的人也不明确。第二,立法规范的行为不够明确。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在表述方面使用了“克隆人”、“生殖性克隆技术”和“生殖性克隆人”等概念,但对于这些概念并没有给予明确界定。《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对于“胚胎”、“人胚胎干细胞”、“囊胚”、“单性分裂囊胚”和“遗传修饰囊胚”等概念也没有给予明确界定,这会导致立法规制行为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三,立法规定的监管主体的职责不够明确。比如,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4条和第12条规定,卫生行政主管机关享有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监督管理的职权,对于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涉及的医疗机构具有行政审批权,但对于医疗机构通过审批后,监管主体如何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进行日常监管没有明确规定。在治疗性克隆方面,监管主体主要包括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单位和伦理委员会。但在相关主体的职责方面,《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只规定了伦理委员会的职责是“对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及科学性进行综合审查、咨询与监督”,其他主体的监管责任并不明确。第四,立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方面不够明确。在生殖性克隆方面,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人员违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从事“克隆人”、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单位人员违反《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等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也没有规定科研单位从事生殖性克隆的责任承担问题,只是在第11条中规定“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在治疗性克隆方面,《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对于违反本原则从事治疗性克隆的人员和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没有具体规定。
(四)遵循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
克隆人技术立法内容涉及对公民科学研究自由、生育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限制,这一限制也应当遵循宪法上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发端于德国警察行政法,后来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比例原则是指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必须在限制的目的与限制的手段之间进行衡量,目的要正当,而手段也必须适当而必要,不能不择手段地追求某一目的。比例原则的审查包括四个步骤:目的正当性的审查、适当性原则的审查、必要性原则的审查和狭义比例原则的审查。[28]P66比例原则是各国宪法普遍要求的一项基本原则。比如,在加拿大,宪法第1条规定:“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保障的权利与自由,只有在自由与民主社会中能说明正当理由并基于法律的合理规定才可被限制。”加拿大最高法院在R.v.Oakes案中进一步确立了分析宪法第1条的指导性框架,对于本条中法律是否“合理”的判断进行比例原则的审查。[29]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药房案”判决中详细阐释了比例原则作为立法机关限制基本权利的审查标准,完了传统“三阶”比例原则的建构。[30]在我国,比例原则也可以从宪法文本中解释出来。有学者认为《宪法》第33条第3款以及《立法法》第6条可有限度地为比例原则提供宪法规范依据。[31]
克隆人技术立法应当遵循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在立法目的上应当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生命与人的尊严的基本要求,对克隆人技术研究规制手段的选择上应当与立法目的相符合,在所有能够达成目的的规制手段中选择损害最小的手段,所选择的规制手段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的损害与所追求的立法目的成比例。而我国克隆技术立法在规制手段上违反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所采用的规制手段难以达成规制目的。比如,在生殖性克隆的立法规制方面,我国克隆人的立法监管主体的责任和相关违法的责任不明确性,刑罚规定缺失致使禁止生殖性克隆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在治疗性克隆的立法规制方面,《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大多是原则性规定,在监管责任和法律责任方面规定不够明确,这会导致对于治疗性克隆的规制流于形式,难以达成监管目标。
展望未来,我国应当以生命和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进行合宪性调整。可考虑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克隆技术管理法》,在立法中界定克隆人技术的相关概念,明确规定监管主体的监管职责以及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可考虑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将生殖性克隆入罪。
注释:
① 参见《中国科学家已经掌握最先进的克隆人技术》,环球网,http://tech.huanqiu.com/news/2015-12/8099583.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6-09-01.
② 贝勒医学院的遗传学家和妇产科医师Dr. Sherman Elias呼吁对动物核移植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以确保人类克隆免于过早老化或老龄细胞相关的潜在危害。参见Terence Monmaney. Prospect of Human Cloning Gives Birth to Volatile Issues, L.A. TIMES, Mar. 2, 1997.
③ 由人民主权原则逻辑性推导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行使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构成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基本形式,因此作为民主的起点和归宿的公民基本权利,自然只能由人民代表按照人民的意志予以保障或限制。参见秦前红.“论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规定”, 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④ 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V. Kentucky案中首创了“不明确即无效的理论”。参见欧爱民.“法律明确性原则宪法适用的技术方案”,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
[1] 杨怀中. 人类需要治疗性克隆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10.
[2] 甘绍平. 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4.
[3] 韩大元、王贵松. 谈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宪法(学)的关系 [J]. 法学论坛, 2004, 1.
[4] 徐惟诚.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M].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5] Barbara MacKinnon. Human Cloning: Science,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6] 刘长秋. 刑法学视域下的克隆人及其立法 [J]. 现代法学, 2010, 4.
[8] 张荣昌等. 哺乳动物的克隆技术——哺乳动物克隆的原理、方法、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J]. 中国畜牧兽医.2006, 10.
[9] I. Wilmut, A. E. Schnieke, J. McWhir, A. J. Kind & K. H. S. Campbell. 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 [J]. 385 NATURE 810 (1997).
[10] Lori B. Andrews. Is there a right to clone?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bans on human cloning [J]. 11 HARV. J.L. & TECH. 643(1998).
[11] 韩大元. 论克隆人技术的宪法界限 [J]. 学习与探索, 2008,2.
[12]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Cloning Human Beings [R](1997).
[13] Leon Jaroff. The Gene Hunt [N]. TIME, Mar. 20, 1989.
[14] Charles C. Mann. Behavioral Genetics in Transition [J]. 264 SCIENCE 1686(1994).
[15] Dena S. Davis. Genetic Dilemmas and the Child's Right to an Open Future [J]. 28 RUTGERS L.J. 549 (1997).
[16] Kenneth L. Woodward. Today the Sheep[N]. NEWSWEEK. Mar. 10, 1997.
[17] Philip Elmer-Dewitt. Cloning: Where Do We Draw the Line? [N]. TIME, Nov. 8, 1993.
[18] Francis C. Pizzulli. Asexual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A Constitutional Assessment of the Technology of Cloning [J]. 47 S. CAL. L.REV. 476 (1974).
[19] George B. Johnson. What Rights Should a Cloned Human Have? [N]ST. Louis POST-DISPATCH, Mar. 20, 1997.
[20] Max Bader. Threats from Cloning Shouldn't Be Overstated [N]. PORTLAND OREGONIAN, Mar. 9, 1997.
[21] Lori B. Andrews. Is there a right to clone?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bans on human cloning [J]. 11 HARV. J.L. & TECH. 643 (1998).
[22] 韩大元. 培育领导干部的宪法思维 [N]. 检察日报, 2015.12.5
[23] 张翔. 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 [J]. 法学家, 2008, 1.
[24] 吴万得. 论德国法律保留原则的要义 [J]. 政法论坛, 2000, 4.
[25] 邱仁宗. 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 [J]. 医学与哲学, 2004, 4.
[26] 欧爱民. 法律明确性原则宪法适用的技术方案 [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8, 1.
[27] 芦部信喜. 宪法 [M]. 李鸿禧译. 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1.
[28] 张翔.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 基本权利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12.
[29] R. v. Oakes, [1986] 1 S.C.R. 103.
[30] 刘权. 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 [J]. 中国法学, 2014, 4.
[31] 门中敬. 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与规范依据——以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为分析视角 [J].法学论坛, 2014, 5.
TheImpactofHumanCloneTechnologyDevelopmentonConstitutionalValueandLegislativeResponse
(Law School,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lone Technology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which can be used for "childbearing" children, treatment of disease and miss the dead relatives. Human Clon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an bring convenience to huma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constitutional value of life, human dignity, social and family order that need legislative respons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lone technology legislation, we should regard constitutional life and human dignity as the value base, follow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clear statement and proportionality, and proper balance the conflicting values. Looking ahead, our country should take the value of life and human dignity as the foundation and carry on the constitutional adjustment to the human clone technology legislation.
Human Clone Technology Legislation; Life and Human Dignity, 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Principle of Clear Statement;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1002—6274(2017)06—030—08
DF2
A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中国的立法体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5JZD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孟凡壮(1985-),男,山东日照人,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宪法学,教育法学。
(责任编辑:黄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