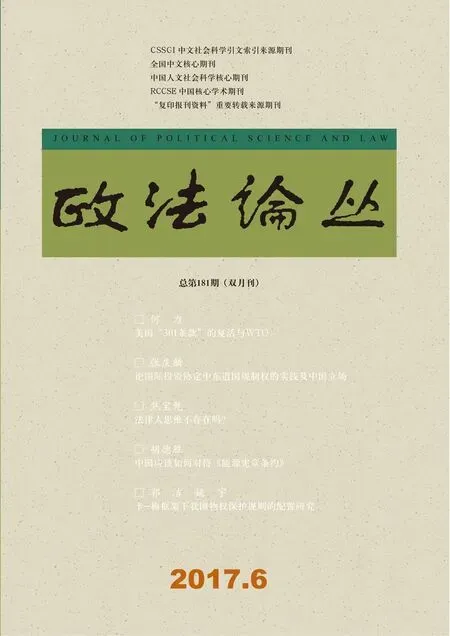美国“301条款”的复活与WTO*
2017-01-26何力
何 力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8)
美国“301条款”的复活与WTO*
何 力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8)
美国决定对中国发起“301条款”调查,意味着“301条款”的复活。“301条款”是美国在WTO之前建立的对美国实行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国家实行贸易报复的措施,具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和单边主义的性质。它显然与WTO的多边主义格格不入,在WTO时代遭受了WTO合规性挑战。但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及其专家组在欧盟诉美国“301条款”案中进行妥协,以不对抗WTO及争端解决机构的规则为前提容忍了其继续存在,为”301条款”的复活留下了后患。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这一后患变为现实,中国成为第一个对象原因很复杂,必须认真对应。
美国 “301条款” WTO 中国
2016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针对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重点调查中国企业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做技术转让,以及美国企业是否被迫与中国中方合作伙伴分享现今技术”等议题。8月18日,莱特希泽宣布,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条款”调查。“301条款”是美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著名的单边贸易措施,在美日等贸易摩擦中用来对付别国,是逼迫他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向美国做出让步的强大武器,被称为“经济核威慑”。在1995年WTO成立之后,多边主义压倒了单边主义,美国也很少发动“301条款”措施,使得该条款的贸易措施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重燃。美国立即退出TPP,WTO、NAFTA等多边体制和区域体制也受到冲击。同时,美国在处理贸易摩擦问题时,重拾“301条款”为代表的单边主义措施就成为美国有力的贸易政策工具了。
一、“301条款”的由来和性质
“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修订的《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到第310条的条文所规定的内容及其制度和程序。①由于后来还演变成“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所以“301条款”的原始形态也称为“一般301条款”。狭义的“301条款”就是指的“一般301条款”,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就属于这一种。而广义的“301条款”则包含了“特别301条款”(Special 301)和“超级301条款”(Super 301),它们共同构成了“301条款”体系,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法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301条款”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已经淡出多年,但在WTO成立之前的单边主义盛行时代,“301条款”却是最为著名的国际贸易规制的法律制度之一,极大地影响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贸易及其法律制度,是当时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各国政府和商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也是当时各国国际经济法和国际贸易法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1]
“一般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贸易协定、损害美国贸易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最早源于《1962年贸易扩展法》。《1974年贸易法》将其该制度完善化,得以定型,后来又经过《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进行修改完善。“超级301条款”是《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2条(a)的规定,作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的强化版。该条款只有两年有效期,本来只限于1989年和1990年,但到1994年3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行政命令使得该条款得以复活。但是这些复活都是有期限限制的,所以后来也断断续续复活。“超级301条款”则是根据《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3条(b)的规定,作为《1974年贸易法》第182条而增加的条款,是“一般301条款”关于知识产权措施的特别版。
”301条款”针对的是美国认为存在的外国政府实行的不公正贸易行为。美国对这类不公正贸易行为启动调查程序,即“301条款”调查。如果调查认定确实存在不公正贸易行为,贸易代表将与该外国政府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对方的不公正贸易行为未得到改善,美国将对该国实行贸易报复。[2]
所谓不公正贸易行为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违反贸易协定的行为以及不正的行为,其中后者是指违反国际义务(包括条约、协定以及习惯国际法)的行为。其二,歧视行为,包含拒绝给予美国产品、服务以及投资享受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的行为。其三,不合理行为,是指“不公正且不公平”的行为,包含拒绝给予开业的机会、拒绝对知识产权提供适当并有效的保护、拒绝给予市场准入。而拒绝市场准入包括政府默认限制美国产品市场准入的外国民营企业进行的有组织反竞争活动、出口限制、习惯性拒绝赋予劳动者权利等行为。无论哪种情况,都必须要以对美国的商业交易构成减损或制约为要件。
贸易代表是对“301条款”实行调查和实施贸易措施的决定者,也是贸易代表必须履行的职责。在确定符合实施“301条款”措施条件下,贸易代表必须实施该措施,对对象国的贸易实行包括增加关税、限制进口等制裁措施。贸易代表在认定存在不正行为、歧视行为或不合理行为的场合,就要确定是否采取报复措施和采取哪种报复措施。在实行附期限的报复关税的时候,要考虑因该不公正行为造成的美国商业交易的损害和对价。美国总统可以否决贸易代表的决定,因为贸易代表的权限归根到底是美国总统的行政权。这和“337条款”程序中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导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是独立于美国总统和国会权限的机构。如果对象国政府同意停止被指控的违反协定行为或不正当贸易行为,或者同意提供补偿,“301条款”的制裁措施也成为不必要的了,因为目的已经达到。
“301条款”的程序开始于调查。调查请求可以由声称遭受外国政府不公正贸易行为损害的商家提起,也可以由贸易代表依职权提起。商家提起的场合要有贸易代表依其裁量权决定是否要发起调查。调查结论如果符合发动“301条款”报复措施条件,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发动报复措施。[3]“301条款”调查以及决定采取措施的期限一般为12个月内,而违反协定的场合是18个月内。采取的报复措施为4年,实行落日条款,4年期满,报复措施即告终止。
“301条款”实际上建立了一个美国发动单方面贸易报复措施的制度及程序的平台。在此平台上衍生了“特别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特别301条款”主要针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的国家启动“一般301条款”调查义务化,并且将调查期限从原来的12个月之内缩短为6个月内,而复杂案件可以延长到9个月,其他规定都和“一般301条款”一致。《1974年贸易法》规定,贸易代表每年3月末要向总统和国会提出《外国贸易壁垒报告》,而“特别301条款”要求,在NTE报告提出30天内要发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报告》(也称“特别301条款”报告),根据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将问题国家划分为优先国、优先观察国和观察国三类。另外还有最严厉的“306条款观察国”。只要被制定为优先国,就开始进行“特别301条款”调查和当事国进行谈判。谈判不成功即采取制裁措施。将某对象国从优先国除名也是可能的,但要向国会做出说明。
“超级301条款”作为“301条款”的强化版也是依赖总统的行政命令实施,而每次行政命令有效期为2年,内容也近似于“超级301条款”,在当年的NTE报告基础上,将有贸易障碍的特定国家列为优先国或优先措施(即将特定的贸易障碍措施单列),当年4月底有义务向国会报告。该条款期满失效后,又有数度复活,复活的条款内容也多少有所变动。
“301条款”措施在WTO成立之前的GATT时代是理所当然的贸易措施。这是因为当时虽然也存在GATT等多边、区域或双边的贸易机制和协定,但GATT本质上是一个协商性的多边贸易机制,并无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双边谈判是主要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而谈判不成就自然诉诸单方面的贸易措施。这类贸易措施有效与否是取决于双方贸易状态。一般而言,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并存在较大贸易逆差一方更有底气推行单方面贸易措施来解决贸易争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贸易大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其制造业受到日本和欧盟的严重挑战,自然就拿起“301条款”为武器,保护自己的产业,对那些采取各种贸易壁垒限制美国贸易,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国家进行贸易威胁或报复。当然,威胁并获得对方让步是通常的实践,走到贸易报复的情况非常少见。
二、对“301条款”的WTO合规性挑战
1995年1月1日WTO成立。美国是WTO成立的主要推动着之一,WTO规则和制度设计中也充分反应了美国的意愿。而WTO本质上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根据WTO规则的要求,包括贸易措施和贸易报复在内的制度也是多边规则,而不符合这一多边规则的各国国内法律或措施不具有WTO合规性。合规性一般是指公司治理一种方式,及企业活动必须要遵从法律和企业内部规范,但更加广义的合规也包括一个WTO成员的国内法以及措施是否符合WTO规则,即WTO合规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某项贸易法规或贸易措施符合一个国家的宪法或法律,但如果不符合WTO规则及其要求,就有可能因为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的认定不合规而遭遇WTO合规性危机,最终不得不废止或修正该贸易法规或贸易措施。[4]美国的“301条款”虽然制定于WTO成立之前,但由于其核心是关于美国的单边调查和采取单边报复措施的规则,至少从条文规定上看是不符合WTO的多边规则的,所以自然就面临WTO合规性的挑战。
这一挑战从WTO成立不久就开始了。1995年5月17日,日本在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向美国提出磋商,即“日本诉美国进口汽车报复关税案”。②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制造业如日中天,日本制汽车以其强大的竞争力大量出口美国市场,对美国的核心产业汽车制造业形成巨大冲击。而美国厂商制造的汽车对日本的出口却毫无进展,于是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国内汽车市场存在贸易障碍,阻碍了美国汽车进入日本市场。美国启动了“超级301条款”,发动了该条款的调查程序,并进行了激烈的谈判交锋,爆发了日美汽车贸易大战。1993年,日本将此问题诉诸GATT,指控美国“301条款”违反了GATT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市场准入规定。1995年WTO成立后,日本又将此案提交到WTO争端解决机构,使其成为WTO争端解决机构最早受理的案件之一。澳大利亚作为第三方参加。日本认为,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304条对日本进口实行报复关税等单方面对抗措施违反了GATT第1条的最惠国原则,以及第2条市场准入的规定。但很快到了6月28日,日本和美国在WTO之外达成了妥协,《日美汽车协议》得以签署,日本部分接受了美国要求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的数量限制。这虽然与GATT规定不符,在WTO框架内难以解决,但WTO并不禁止成员之间达成双方都接受的贸易协议,所以双方决定不再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中就法律问题争高低。7月19日,双方正式宣布本案程序不再进行下去。这样,美国“301条款”所遇到的首次WTO合规性挑战被日本美国的妥协化解了。[5]
真正正面向美国“301条款”发起WTO合规性挑战的是1998年欧共体(欧盟)诉美国的“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310条案”,即“301条款”案。③欧盟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却深受美国“301条款”之害,终于带头向“301条款”发难,引起广泛的关注。1998年11月25日欧盟向美国提出磋商请求,1999年1月26日欧盟要求成立专家组。3月2日专家组成立。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中国香港、印度、以色列、牙买加、日本、韩国、圣卢西亚、泰国以第三方身份加入其中,已经包含了美国之外世界上的各主要经济体,也说明了世界对“301条款”是如何的反感。中国还没有入世,但也作为观察员以第三方身份参与进来。11个WTO成员在案件审理中发表了意见。专家组3名成员是D·Hawes、T·Johannessen以及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JosephWeiler。由于这时正是WTO草创初期,争端解决机构及其专家组处理案件基本上按照法定时限进行,所以当年12月22日专家组就公布了该案报告,并于2000年1月27日被争端解决机构所采纳。
与上述1995年日美汽车案中日本注重301条款中的最惠国待遇和市场准入等实体问题不同,欧盟力图从程序上对“301条款”的WTO合规性进行挑战。本案实体问题的欧盟实行的香蕉进口措施,美国认为这构成美国商家的贸易障碍而对欧盟进行了劝告,欧盟无视美国的劝告,于是美国单方面决定对欧盟启动了“301条款”。欧盟认为,美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文件生效之后还继续坚持、维持和适用“301条款”,是完全违背了美国对《建立WTO马拉喀什协定》及其他WTO成员的历史性承诺。既然美国已经承诺要认可争端解决机构(DSB)及其专家组乃至上诉机构的报告,就应该完全而确实地放弃多年以来一直实施的单方面贸易报复措施。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第三部分第一章第301-310条,特别是第305-306条所规定的单方面发动报复措施的制度并没有WTO的DSB认可,违反了DSU第23条(禁止单方面措施)等规定,导致欧盟利益减损,侵害了欧盟的利益。
面对欧美围绕“301条款”的尖锐对立和激烈交锋,WTO的DSB专家组也面临着苦涩的重大决断。显然,“301条款”条文是过去的立法,成立于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出现之前,其所规定的单边调查和单边报复措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用WTO成立后的眼光审视,这样的规定从程序上看与《关于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的谅解》(DSU)的规定是相矛盾的,因为无论DSB是否采纳专家组乃至上诉机构报告,美国贸易代表都可以确定其他WTO成员方是否侵害了美国的贸易权益。无论DSU第21条第5款的程序是否完结,美国贸易代表却要决定是否实施DSB的劝告。因此,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到310条创造出了对WTO统一性有一定偏向的行政行为模式,因此违反了《建立WTO马拉喀什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的必须确保本国法令及行政程序符合WTO诸协定义务的规定。这也是欧盟在DSB向专家组提出的问题,要求专家组认定美国的“301条款”整个不具有WTO的合规性。④对此,美国认为欧盟的主张是在法律外衣下将政治性事项带到了贸易争端里来了。美国的“301条款”都不影响美国履行DSU乃至WTO的义务。⑤
欧盟的攻势是猛烈的,而美国的辩驳似乎不太有力。但专家组能够简单地下结论,一劳永逸地解决“301条款”问题吗?显然是不能的。“301条款”虽然有问题,但如果彻底否认其WTO合规性,势必导致美国国内保护主义的巨大反弹,也会引起与美国有类似制度的很多国家的连锁反应。事实上,包括本案中作为第三方参加的很多国家自身的对外贸易法以及贸易措施同样难以接受WTO合规性审查。所以,专家组最后采取了妥协的方式处理,弱化了“301条款”的问题和冲突。
专家组认为,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4条等条款从条文上的确有违WTO规定,但应该注意美国履行WTO义务的实际效果,而非拘泥于条文本身。应该将该法律与美国总统颁布的关于该法律的解释指南以及美国联邦政府相关的解释综合起来理解,该法被指示将按照不违反WTO规则的方式适用,因而该法相关的法律程序并不能说违反了WTO协定。专家组具体解释到,美国在SAA(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中,“WTO协定违反或者美国在协定上的权利受到侵害的《贸易法》301条款决定,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要有DSB采纳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决定为基础”的规定,以及承诺遵守专家组审理结果,因此有关的问题措施并不违反DSU。
专家组进一步论证,专家组考虑到本案件在政治上非常敏感,专家组的任务还是集中在司法性上,因此并不打算对《1974年贸易法》第301~310条做出整体评价,只对于欧盟的主张进行个别判断。关于国内法的WTO合规性判断,要考虑到各国国内法的多样性,因此应该注重结果,至于如何达到该结果则是不重要的。不尊重和不理解各国法律制度的特殊性,是无法做出正确的WTO合规性判断的。“301条款”中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实际上是现代复杂的经济性规则性立法中共有现象。立法机关不可能全面掌控该法律的所有执法环节,而是将其委托给了既有的或者专门设置的行政机关,该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设定的一定标准与裁量范围内完成任务。该裁量范围或者大于立法机关的意向,或者小于立法机关的意向,而“301条款”的相关制度就是这样的法律制度中的一部分。⑦因而“301条款”不能光看立法的条文,而是要结合执行该条款制度的行政要素,具有多种因素。这是理解WTO合规性所必须的。比如某个行政机关被授予特定的权限的法律规定,一看虽然符合WTO规则,但在该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中却实行了与WTO义务不相符合的内部标准或行政程序,从结果看该法全体便不具有WTO合规性。这一点相反的也成立。⑧
即使是法律条文上违反了DSU规定,也有不修改法律的解决方法,但必须是合法的方法。比如行政机关如果做出了无视国内法的承诺,也不能达到WTO合规性的目的。美国的行政机关将贸易法的一般适用与受WTO规则约束的部分分离开来。总统对议会发表的关于无论根据“301条款”做出了什么决定,都必须基于DSB采纳的专家组乃至上诉机构报告的承诺就属于这类做法。这就明确排除了DSU程序完成之前美国国内作出不符WTO规则决定的可能性。虽然行政上的宣言以后也有可能变更,但即使是立法也有可能被事后的立法所变更。因此重要的是这样限制是否合法,并且是否具有实际效力。
专家组所做出这样的判断解决了“301条款”相关条文的WTO合规性问题。而本案中专家组对美国就此问题进行了咨询,得到了美国方面明确的、正式的、反复的、无条件的确认。一个国家单方面声明不应该轻易赋予国际法上的意义。但声明是美国官方政策的反映,并非新的政策,将国内实际上的一贯做法运用到国际的场合。因此,专家组认为美国的这类声明是属于可以由所有成员方信赖的官方立场,虽然不是给美国课以新的国际法义务(美国作为WTO成员方是要受到DSU第23条约束的),但国际的层面是可以理解为美国的确可以明确履行DSU第23条第2款(a)规定的义务。所以,美国政府的宣言以及专家组审理中得到的美国政府的声明是可以直接对其他成员方、间接对市场给予遵守DSU第23条的保障的。
专家组的报告被DSB所采纳。当然DSB也无法阻止专家组报告的采纳,因为只要有一个成员方同意专家组报告,专家组报告即算通过,成为DSB的正式的立场。欧盟也接受了专家组报告,并没有上诉。这样,“301条款”度过了WTO合规性挑战。
最后一个涉美国301条款的WTO案例是欧盟诉美国的“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6条修改案”。⑨2000年6月5日,欧盟提出向美国提出磋商请求。欧盟认为,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6条被美国的《非洲CBI法》第407条修改,违反了DSU第3条第2款、第21条第5款,第22条和第23条。同时也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了GATT第1条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和第11条禁止一般数量限制的规定。厄瓜多尔、牙买加、日本、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加拿大、巴拿马、澳大利亚、圣卢西亚等过也提出参加的意愿。但该案并没有进行下去而不了了之。这样,WTO就失去了直接判断美国“301条款”是否实质违反WTO规则的机会。此后WTO再无涉美国301条款的案例。而美国也再无积极运用“301条款”的意愿,只是偶尔启动之,并没有到达单方面实质性报复措施阶段。
三、WTO体制下美国“301条款”的复活的法律基础
熬过了“301条款”的WTO合规性风波,“301条款”实际上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但却在WTO体制下被温存下来。这就为“301条款”有朝一日在WTO体制下复活留下了伏笔。为什么WTO体制下美国“301条款”那样的国内法制度能够温存下来呢?这与美国国内法制度和国内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国家权力由联邦和州分享。“301条款”是关于美国国际贸易的权限,属于美国宪法赋予联邦权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处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的法律框架中。它是经过正规的美国联邦法律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因此是联邦立法。《建立WTO马拉喀什协定》除了该协定正文本身之外,还包括其附件《关于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的谅解》(DSU)在内的WTO项下的各个协定、议定书、谅解等。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巨大的WTO规则体系。WTO的相关部长会议决定、具有拘束力的宣言、DSB的决定等也在这一规则体系之中,即所谓的“WTO规则”。这些WTO规则有很多名称,但从条约法上看都属于国家间的协议,具有广义的国际条约的性质,可以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来处理WTO规则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乌拉圭回合”协定法》,批准了《建立WTO马拉喀什协定》,使其成为对美国有拘束力的国际条约。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6条的规定,“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 以及合众国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这条规定表明,在美国,经国会批准的国际条约可以纳入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并且和美国联邦法律处于同一位阶。因此,“301条款”与WTO协定实际上是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体系之中。也就是说,WTO规则在美国并不能理所当然地高于“301条款”,即使是后者与前者的规定不符。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像很多明确在宪法或法律中规定了国际条约优先于国内法那样,确保WTO规则高于“301条款”。因此,美国并没有干净地处理WTO规则与美国国内法的关系,确保WTO规则的优先性。
如果是同一位阶的法律,则应该遵从“后法废前法”的法理,《“乌拉圭回合”协定法》的规定在后,优于之前的“301条款”。但在美国,不同的法律之间如果出现了规定的不一致,只要在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权认定之前,是不会对此明确化的,因此并不能理所当然地认定美国国内所有的与WTO规则不符的法律条文无效。
美国的体制和国情也决定了美国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处理。美国实行的总统制,虽然实行的是民主选举,但总统与国会议员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各自都有独立的权力本源。总统及其行使的行政权对外代表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和缔结国际贸易或投资协定。而国会行使立法权,审查和批准国际贸易或投资协定,并使其生效。如果国会(主要是美国参议院)与总统有不同意见,就可能否决总统代表美国政府推动并签署的国际贸易或投资协定。因此,美国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构成了美国在国际条约上的否决机制,导致美国在进行国际承诺、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采取的是议会制,国家元首只具有象征意义,而行政权掌握在能够控制议会的多数党手中,因此除非出现陷入到失去议会多数的不信任危机,政府首脑行使行政权力进行国际贸易谈判、签署国际贸易或投资协定是应该获得议会批准的,所以不存在国际条约上的否决机制,不会导致国际承诺、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不确定性。当然,国际社会中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并非只有美国一个,而且还有不少国家实行的是像法国那样的介于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总统内阁制,如果都是向美国那样,将国际承诺、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置于不确定状态下,那么当今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贸易体制的成立和运行也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态呢?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使其才能如此任性,将其国内法与WTO规则的关系置于不确定状态。
无论是GATT也好,1995年成立的WTO也好,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美国本身通过这样的多边贸易体制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并且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样的体制如果美国带头违反,无视WTO规则和相关法律,导致GATT/WTO不能正常发挥其机能,最后受损的也是美国。因此,美国首先还是要维护WTO体制的。美国批准WTO的国会立法就体现了这一点。该法确保WTO规则能够在美国得以生效,让美国可以履行对WTO的承诺和义务,其美国国内法的根据是“快车道程序”相关的授权法。
本来,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国会拥有包括决定关税税率等对外贸易事项的立法权限。即使美国总统进行了贸易谈判,只要国会没有授权,总统的谈判只要涉及到美国的贸易立法的规定,其谈判的结果是不能产生效力的。这样的权力构造使得美国参与谈判的贸易协定及其今后的效力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对于国会通过的贸易立法,总统则以拒绝签署使其生效,来对国会进行牵制,其结果是总统和国会之间还是要达成某种妥协,也包括国会向总统授权一定期间可以进行关税等贸易谈判。这样谈判的结果国会当然不会阻拦,因为它本来就是国会的授权。但如果授权的期限经过了一定时期,国会议员的构成也可能发生变化,也可能出现国会与总统在贸易谈判和缔结贸易协定问题上产生分歧。“快车道程序”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总统将谈判结果贸易协定提交国会审议的时候,国会只能就赞成或反对进行表决,不能够就谈判内容进行修改等进行讨论。快速审议,只求结果,省略过程,正是所谓“快车道”的本质所要求的。这说明,美国宪法规定的由国会行使贸易权,独占贸易立法权,已经不适合当时国际经济贸易局势瞬息万变,需要行政府迅速做出对应现状,有可能出现美国国家利益受损的事态。这实际上扩大了总统的贸易方面的权限。也说明了美国还是具有一定变通的。
这样的机制是在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中最早建立起来的。该授权期限是3年,后来又断断续续进行了多次延长,多次中断。1947年美国国会虽然阻止了《哈瓦那宪章》(并没有到参议会投票阶段),但却没有阻止GATT的生效,就是因为GATT的谈判还是处于该授权期限之内,美国国会还不能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废掉GATT。美国《1974年贸易法》在规定了“301条款”的同时,但也规定和建立起了“快车道程序”的授权规定,从1975年1月3日起授权美国总统进行为其5年的贸易谈判权,并且以此为依据在1979年通过了《1979年贸易协定法》解决了“东京回合”谈判结果的美国国内批准问题。而1979年的该立法又进一步将授权总统贸易协定谈判的权限延长8年。1988年《综合贸易法》第1102条到第1103条又授权美国总统在1993年6月30日之前进行“乌拉圭回合”的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谈判,但是授权期满谈判还没有结束,于是进一步延长到1994年4月15日。由于之后再获得延长又要经历严峻的国会论战,所以“乌拉圭回合”谈判各方都是以这一天为最后期限展开了最后的交涉,并终于达成协议,完成了《建立WTO马拉喀什协定》的签署,避免了重蹈1947年《哈瓦那宪章》那样的悲剧发生。这样的美国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内斗牵动着WTO的动向,也是WTO的DSB为什么要在前述欧盟诉美国“301条款”案中在“301条款”合规性中如此处理的根本原因所在。既然WTO和美国之间在“310条款”问题上通过该案的处理达成了某种默契,那么要指望彻底解决“301条款”的问题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所以,美国始终存在着“301条款”复活的法律基础。美国批准和加入WTO的国会立法并不能确保WTO规则和法律对美国国内法的优先地位。WTO的成功运行也不能从法律上阻止“301条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复活的可能性。
四、“301条款”复活的保护主义背景
通过上面的分析表明,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国际贸易问题上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在这样的对立之中,美国国会容易走向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而美国总统则还得顾及美国在国际上的基本的信义和国际承诺。这在美国总统和国会多数派不是一个政党的场合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美国的两院制也会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即使是美国国会,特别是参议院的多数党与美国总统同属一个政党,由于美国并不存在议会制国家那种严格必须保持一致的政党纪律,所以具体的议员反对同一政党的美国总统也是司空见惯。美国国会议员由自己的选区选出,只向本选区选民负责,不向总统及所属政党负责,因此在国际贸易问题上,更多的国会议员与其说关注世界局势和国际贸易,倒不如说更关注本选区的就业和经济状况。
以WTO多边贸易体制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下发生和推进的,当然符合美国的国家整体利益。这也是美国在WTO成立之后一直还是比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基本上冻结了“301条款”运用的原因所在。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美国根本没有将WTO规则与美国国内法进行彻底的WTO合规性处理,美国国内的贸易法始终是违反WTO规则的温床。它们会体现在各个方面,表现为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代表、国会或议员的动向。美国从来就没有彻底解决国内的保护主义问题。[6]当保护主义露头,美国国内法始终可以为那些违反WTO规则的措施提供炮弹的。这些,我们都可以从美国的贸易救济等问题上看出美国的一贯做法。但是,“301条款”问题则太重大,美国不会轻易动用这个武器的。
WTO规则和法律在美国的效力的基础并非法律基础,而是基于美国政府在总统权力下承诺不会做出违背WTO规则和法律的举动,承诺美国的国内法措施不对抗DSB及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得出的结论。这样的承诺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美国掌权执政的两党政府都是理性的。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精英治理之下,所以美国虽时有违反WTO规则或法律的事态发生,但大体可以冷静接受DSB及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做出的决定,修正自己被认定不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7]这样的状态也为WTO及其各成员方所接受并习惯。美国的任性如果换作是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可以说不仅WTO不会容忍,各成员方也不会如此娇惯。其实,从美国对WTO以及各国对外贸易法制度的贡献度,以及美国每年数以千亿美元规模的贸易逆差将利益普惠于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各个WTO成员来看,美国对世界、对各国的利是远远大于弊的。美国再不济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并引领了新的技术革命、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不但自己富裕起来,还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从与美国的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
自从WTO成立后,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一直基本上维持了对WTO规则的遵从。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大大改变了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在美国国家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却未能实现美国国内利益的合理分配。这样的结果导致特朗普的上台,为“301条款”的复活具备了条件。以本次美国对中国开始“301条款”调查为契机,美国保护主义的潘多拉魔盒是否已经打开了呢?
特朗普的执政理念非常清晰,并明确体现在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上。反全球化就是其鲜明的特征。“美国第一”与WTO互利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很多方面是对立的。更何况,特朗普作为一个生意人深谙谈判交涉的技巧,重新拾起美国当年常用的将贸易与政治等其他非贸易因素挂钩的做法。他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就对中国、日本、墨西哥等与美国有着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多方指责和攻击,总统竞选成功后组织起对外贸易的团队也是充满保护主义色彩,而对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团队也充满地缘政治思想。美国这次对中国开始“301条款”的调查也不单纯是一个贸易摩擦问题,而是混有朝鲜半岛危机的因素等其他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混合复杂的问题。
中美贸易只要每年高达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问题继续存在,单单就此经济贸易原因就足以构成使特朗普政权启动“301条款”的调查程序的充分理由。因为在特朗普政权下,美国不会作出违反WTO规则以及DSB(包括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决定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能够理性掌控和处理包括“301条款”在内的美国国内法与WTO体制之间关系的精英群体已暂时不处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之中。在特朗普政权下,谁也难以保证美国不会在对WTO承诺的信守上不会走偏。更何况,美国国会还会在这条路上推波助澜。美国国会才是美国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选出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的本选区的选民没有必要具备全球视野。他们是通过最直感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投票的。美国总统领导下的行政机关对外代表美国,是维护美国利益,信守国际承诺的承载体。所以在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对立的构图中,美国的总统一般是扮演着国际协调的角色,与代表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势力的很多国会议员对立和斗争。但是特朗普的执政则完全改变了美国的这一传统的政治默契。当总统和国会在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沆瀣一气时,美国的政治生态必将发生重大改变,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趋于保守几乎是一个大概率的趋势。美国总统不但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制动者,反而成了推动者,而国会在此问题上只会推波助澜。这样的环境下,“301条款”成了体现特朗普及美国国会中保护主义势力的绝好工具,其复活也许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为什么“301条款”的复活是从对中国开始的呢?这也许并非简单的贸易问题能够解释的。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美国国内政治、中美关系等都可能会有影响。由于“301条款”的发动是要动用总统权力的,所以特朗普的个性、他周边对他的决策产生影响的人都有可能是部分原因。比如朝鲜的核问题以及洲际导弹问题也许触动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神经(包括保护美国的盟国韩国和日本)。以特朗普的固执,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不足,实施经济制裁不够而引起的。回想起特朗普早在竞选总统时就放言,如果中国能够让朝鲜弃核,美国将会在贸易上给中国好处。反之也可以理解为,如果中国没有按照美国所期待的那样在朝鲜弃核问题上发挥很大作用,美国就会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为难中国。这样,中国成为美国启动“301条款”调查的第一个对象国就并不奇怪了。特朗普政府如果是秉承这样的思路行事,那就开始了一个贸易政治化的不好先例。作为一个一直没有完全根除冷战思维的国家,美国曾经长期以来一直在处理中美贸易关系上采取了贸易政治化的做法。这个做法直到中美关于中国入世谈判达成协议,美国无条件赋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才告结束,中美贸易非政治化后来得到WTO体制的维护。而美国开始重启“301条款”来处理中美贸易关系,势必使得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变得非常不正常了,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
当然,事态也并非到了不可挽回的境地。因为美国国内的问题,特朗普在执行政策,实现自己的理念方面并非得心应手,反而处处受到牵制,很快成为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被捆绑手脚的总统。国会反对他的势力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共和党的主流建制派,总统府的助手和内阁成员们在政策决定和执行中也不得不理性行事。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理念形成影响最大,并成为总统顾问和助手团队最初的核心人物,包括班农、福林等也相继被解除职务。美国制度下存在的纠错机制和精英势力的影响力也并非完全失去效能。即便是发动了对中国的“301条款”的调查,也不能断言在长达一年的调查期间情况不会发生变化。更何况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上早已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中国的贸易赤字的实态也表明,美国国家及美国企业也在巨额的贸易不平衡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即使事情已发展到最后一步,也就是美贸易谈判已经完全失败而决裂,还有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最后手段可以奋争到底。因此在美国复活“301条款”,采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手段处理中美贸易关系的这个时期,坚定地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在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下挫败美国“301条款”,才是我们的重要使命,也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支持。
注释:
① 美国法律条文“Article”不能等同于中国法律条文的“条”。其内容很多,条款规定繁多,因此也可以翻译成“节”。
② WT/DS6,Japanv.U.S.,United States-Imposition of Import Duties on Automobiles from Japan under Sections 301 and 304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③ WT/DS152,ECv.U.S.United States - Sections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④ WT/DS152/7.2-7.8.
⑤ WT/DS152/7.9.
⑥ WT/DS152/7.24.
⑦ WT/DS152/7.25.
⑧ WT/DS152/7.27.
⑨ WT/DS200,EC v. U.S.,United States - Section 306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and Amendments Thereto.
⑩ 见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关于关税的规定。
[1] 杨国华.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研究[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 2.
[2] 徐泉.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与其经济霸权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2.
[3] 高永富.评美国贸易代表对301条款调查申请的拒绝[J].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报,2007, 2.
[4] 梁咏.WTO体制内中国“稀土保卫战”的合规性研究[J].海关与经贸研究,2012, 2.
[5] [日]石黒馨.国際通商交渉と制裁の威嚇[J].[日]国民経済雑誌,190(3),2004年9月.
[6] 郭雳.美国310条款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互动及其前景[J].中国法学,2001, 5.
[7] 吴伟.WTO机制下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评述[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Resurrectionof“Section301”inU.S.andWTO
HeLi
(Law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
The United States decided to initiat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to China. This means the resurrection of “Section 301”. “Section 301” was enacted before the WTO was established, and used to retaliate against those countries that practiced unfair trade behavior measures for trade of US, with strong protectionism color and the nature of unilateralism. It is clearly out of tune with WTO multilateralism, suffered WTO compliance challenges in the WTO era. But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of WTO and the panel in the EU v. U.S “Section 301” case compromised,and tolerated it to continue to exist As long as not against WTO and DSU rules as a prerequisite. This left the future trouble of the resurrection of “Section 301” became a reality after Trump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U.S..The reasons that Chinabecame the first object of Section 301 are very complex. We must be seriously correspond.
U.S.;“Section 301”; WTO;China
1002—6274(2017)06—003—09
DF96
A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欧美投资条约可持续发展条款对上海企业海外投资影响法律问题”(项目编号:SPH3457003)的阶段性成果。
何 力(1955-),男,重庆市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
(责任编辑:黄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