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童年
2017-01-24陈赛
陈赛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调查研究了几万名在科学、文学、艺术、政界、企业等行业卓然有成的“自我实现者”,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具有孩子气。他说:“我所研究的那些自我实现者,他们因为成熟才被挑选出来,但他们同时也很幼稚。”他把这种幼稚称为“健康的幼稚”,一种“返老还童”的天真、“再度的天真”。
百亩森林:错置的童年
有时候,我会给儿子小虫读《小熊维尼》,虽然他还听不大懂,但他喜欢看谢泼德的插画,尤其是百亩森林的下午茶。没有人能像谢泼德那样捕捉那种小世界里纯粹的、不掺任何杂质的喜悦。淡淡的几笔铅笔素描,铺展开一片寂静的山林,轻柔的草地,野餐布上摆着篮子、蜂蜜、面包……小虫会用小小的手指戳戳那些瓶瓶罐罐,像一个小主人一样,兴高采烈地张罗着,招呼粉红猪、跳跳虎们喝茶,吃蛋糕。
A.A.米尔恩是在儿子克里斯托弗·罗宾3岁的时候开始创作《小熊维尼》与《维尼角落的家》的。这些故事虽然以罗宾为主角,但米尔恩从未给儿子讲过他写的这些故事。
多年后,克里斯托弗在他的自传《着魔的地方》中提到,他的父亲一生最深切的情感,其实是对他自己的童年的乡愁——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所以,当他有了孩子以后,他最初的心愿大概是在儿子的陪伴下重新再过一次自己的童年,但出于种种原因,他转向了在纸上创造一个童年,而不是陪伴那个真正的男孩度过他的童年。
对此,克里斯托弗的解释是:“有些人善于与孩子相处,有些人不行。这是一种天赋,要么有,要么没有。我父亲没有。正因为他没办法与自己的儿子一起玩,所以他从另一个方向寻找满足——他以儿子的名义写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A.A.米尔恩与儿子克里斯托弗·罗宾
“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差不多是一起长大的。我3岁的时候,他也3岁。我6岁的时候,他也6岁。”
1925年,A.A.米尔恩甚至在自己童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萨塞克斯(伦敦南部)买下了一个农场(科彻福德农场),邻近阿什顿森林,青山寂寂,溪流密布,也就是后来“百亩园”的原型。
多年后,米尔恩对自己创造出来的小熊维尼充满了怨怼,因为没有人再记得他的严肃文学事业,作为《笨拙》的编辑,作为伦敦西区剧院的剧作家,而是那个“为小孩写了几本关于一只没什么脑子的熊”的作家。当年米尔恩在书中对儿童的自我中心暗含的反讽,再也没有人在意。人们更愿意从这些文字的表面来理解这个故事,一个关于童年的理想,那种与自然、与生命之间形成的强大而亲密的连接。
关于米尔恩的故事,另一层错置在于,90年前,这本书给一对父子的真实生活造成了那么多的烦扰与痛苦(克里斯托弗长大以后痛恨那些令他不朽的故事),但90年后,作为一个母亲,我却试图以这本书建立起与我的孩子之间更亲密的连接。我习惯性地让他躺在我的左边——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人的心脏在左边,这样他能感觉到我的心跳,记住我的声音。
关于亲子阅读,《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论断:所谓“沟通领域”很多时候是“冲突地带”——多愁善感的成年人遇到渴望长大的孩子。
“在儿童文学中,成年人想要一个关于童年的抚慰图像,或者一个熟悉的名字或者故事;孩子则想要一艘船,一个出口,一种彼岸生活的案例。孩子想出去,他们的父母则想回归。成年人渴望通过奇境、纳尼亚、乌有乡回到童年的愉快光景,而孩子们想把这些地方当作超越孩子气的跳板。成年人被乡愁驱动,孩子们则想把它们作为漫游真实世界的地图。”
就像小熊维尼的茶会,给予小虫的是一种对于自主性的幻想,而我怀念的则是百亩森林里幽静、安全、慢悠悠的节奏,仿佛从急景凋年里偷回一点点时光。
我从来没有米尔恩那种强烈的想要重新过一次童年的愿望——对于童年,我并没有留下多少清晰的记忆。更何况,作为成年人,我们想要回去的,往往并非我们实际生活过的童年,因为那个童年里有那么多记不起来的困难、羞辱与问题。我们真正想要回去的,不过是一个幻想出来的更简单的金色时光而已。
但是,躺在小虫身边,读着百亩森林里的居民们说着幼稚天真的语言,干着无聊可笑的傻事,以一己之心揣度世间万物,我觉得自己内心深处特别柔软的某一处正在渐渐敞开。在离开童年多年以后,距离故乡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一个“内在的小孩”似乎执意地想要现形。
虽然,经过记忆不可避免的丧失和后来经验的滤网,我深知这个“内在的儿童”并不是我曾经是的那个孩子,但这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如果我更诚实地面对内心深处这个蠢蠢欲动的孩子,是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召唤那个失落已久的童年?如果童书中有一条“回到童年”的秘密通道,那么,我多年前遗失的那个童年和小虫当下正在进行中的童年是否可以在百亩森林里有一场更美好的相遇?而我与他之间亦达成某种更深层次的爱与理解?
向童年寻求什么?
我首先向那些距离童年最近的人请教:作为成年人,他们如何召唤童年的记忆?当他们回望童年时,是在向童年寻求什么?
除了极少的例外,童书作家作为一种职业,需要一种独特的天赋:与自己的童年保持联系,他们仍然记得做小孩是什么感觉,因而对他们抱有特殊的同情和理解,以至于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可以用一种“儿童式的感知方式”书写、绘画。比如美国图画书作家莫里斯·桑达克曾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才华,那绝不是我比别人画得好,而是我能记得别人早已忘却的事情:童年时代某个特定瞬间的声音、感觉与图像,以及其中的情感质地。”

美国图画书作家莫里斯·桑达克。他一生都在画那个4岁的小男孩,孤独、忧郁、充满了时日无多的无助感
桑达克4岁那年,著名飞行员林白之子被绑架一案闹得沸沸扬扬,这个事件成了他整个童年时期最严重的创伤体验——如果一个孩子,父亲是飞跃大西洋的国家英雄,母亲是世界公主,家中有德国牧羊犬守护,居然还被人绑架和杀害,那么作为普通人家的孩子,还有什么指望?当那个孩子的尸体最终被发现时,桑达克“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某种很重要的东西也跟着死了”。
所以,他一生都在画那个4岁的小男孩,孤独、忧郁,充满了时日无多的无助感。比如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主角是一只小猪,叫阿尔蒂,9岁了还没过过一次生日,于是给自己办了一次盛大的生日化装舞会。
疯狂的派对结束后,阿姨说:“好了,聪明鬼,你开过派对了,但下不为例。”
阿尔蒂含着眼泪说:“我保证,我发誓,我永远不会长到10岁的。”
在一次采访中,他说,这两句台词总结了他的人生,以及他一生的创作,无论疯狂的、荒唐的、搞笑的,或者诡异的。它如此真实,尽管连他自己也未真正明白它的含义。
与桑达克相反,中国的绘本画家郁蓉一直在画一个“在山野中奔跑的,快乐的、粗野的、满脸泥垢的、头发永远凌乱的小女孩”。
郁蓉自幼受父亲熏陶,对绘画情有独钟,曾就读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后定居英国,如今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是那种在最好的阳光雨露中长出来的植物,全身散发出来的那种快乐、活泼与明朗,浑然天成,不带一点矫饰。
她说,童年于她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她的家住在一片大竹林旁边,竹林被小河环绕。竹林的一头养了很多鸡,另一头种了很多菜。“我的童年是在大自然中度过的。每天花很多时间跟花鸟虫鱼玩耍,让我积累了很多对生活的直接感官认识,也培养了对生活中很多细节的观察力,也学会了对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各种动物的尊重和爱惜。”
她说,她的童年就像一个大柜子,里面有很多抽屉,每一个抽屉里都装满了故事,每一个抽屉打开现在就能用。比如《云朵样子的八哥》是关于她和妹妹小时候收养的一只八哥的故事。在为曹文轩的作品《烟》所画的插画,则是她童年家庭生活的完整回忆。“从房屋的设置、成员的组合以及家庭关系,都是我童年生活的采集。我用铅笔线描画了很多家庭活动的细节,比如爬树、钓龙虾、弯腰跳绳、烧柴火做饭,全部来源于我童年的回忆。”
“很奇怪,我几乎从未写过自己的童年,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幻想小说。”彭懿用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口气告诉我。
唯一可以与真实的童年扯上关系的,是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书中描写过校园暴力。他关于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是,一天下午,在一个公园的小山边,一个大孩子走过来,突然扇了他一个耳光,而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的经历发生过不止一次。所以,在他的幻想小说中,他的主人公一开始总是软弱的、受人欺凌的少年,但经过一番冒险,最后成为英雄。
“是不是童年那一束阳光没有照进来,于是在日后的创作中,这个主题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弥补?”他在电话那头说,“我不知道。”
他说,他心中很羡慕《山中旧事》里描绘的那种童年,小姑娘与爷爷奶奶一起住在一座大山里,可以如此的亲近自然:夏天在深水潭里嬉水,也许那里还有蛇,可她一点都不害怕;周末,她会和小伙伴们一起穿过牧场,参加教会的活动。她和小伙伴们在锡制的大木桶里泡澡,用死蛇围在脖子上照相……
“我觉得我的童年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文革动乱之中,父母不在身边,又被包围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他说,“我现在写东西越来越追求温情,并不是年纪大了,只剩下温情了,而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童年中曾经匮乏的,希望靠写作索取回来。我觉得童年就应该在自然、在山野中度过,大片大片的树林,很多很多的虫子……”
对于我的问题,殷健灵提起自己还是小女孩时唱过的一首英文歌《What ever will be,will be》。歌中写道: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当我还是个小女孩)/I asked my mother,(我问妈妈)/What will I be?(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Will I be pretty?(我会漂亮吗)/Will I be rich?(我会富有吗)/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她是这么说的)/Que sera,sera,(长大就好)/Whatever will be,will be,(顺其自然吧)/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我们不能预见未来)/Que sera,sera(长大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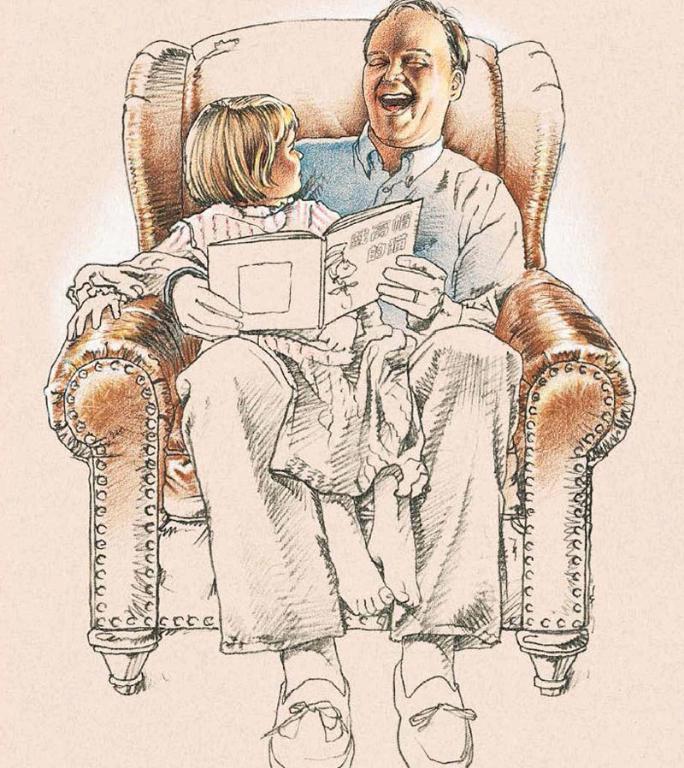
美国图画书 《和爸爸一起读书》,以阅读为主轴,讲述了一对父女一生的阅读之旅
她说,最初的写作,不仅源自表达的冲动,或许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抚慰,是为自己年少时未曾看透的问题找寻答案。尤其走入青春期后,曾经有很长一段迷惘和困惑的日子。没有来由的欢喜,没有来由的悲伤,外界一点点细小的变故,都能在心里无限放大,任何茶杯里的风波都成为惊涛骇浪。面对所有的第一次,不知道之后的结果会如何。没有人可以真正帮到你,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走完那段青春的暗道。所以,她的《纸人》《野芒坡》等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写过来人的故事。“希望今天的孩子不像我当年那么无助与孤独。”
“重温童年大概可以让人避免成为一个庸人。”她说,“这个世界,本来哭声就多,灰暗的颜色也不会少,人生本质上是沉重的。当我们的孩子在人生旅途上刚刚启程的时候,需要的是温暖的底色,让温暖明亮的底色打底,我们才能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才会有力量去应付日后即将经历的暴雨寒风。”
内在的儿童
在《为什么长大》中,哲学家苏珊·奈曼从启蒙传统的脉络中,探寻成长的意义,追问哲学能否帮助我们在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隐含着全新开始的热望,但经验很快会告诉我们,我们出生在关系网络之中,这张网在支撑我们的同时束缚着我们。只要我们稍微长大一点,有了一定的经验,就会明白我们来到的这个世界是给定的,很少顺遂我们的意志。”
她认为,成长是一个获得判断力以及运用判断力的勇气。成长意味着承认贯穿于我们生命始终的不确定性;甚至成长意味着,明明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却认识到我们必然会继续追寻确定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好的儿童小说都是成长小说。一个少年/少女,离开熟悉的家,踏上冒险的征程,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与险阻之后,归来时对家和自我都有了一个新的、更好的理解,也拥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这样的故事能帮孩子处理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内心冲突,是他们的自我发现之旅。
但是,作为成年人,“回去”童年又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站在童年的彼岸,回望幼时的自己,检视自身命运展开的图景,我们又在寻求什么?仅仅是一种乡愁的驱动吗?是一种巨婴的怯懦吗?是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而向童年寻求安全与庇护?是深陷技术理性所致的功利与冷漠之中对于儿童纯真坦荡的向往?还是说,“回去”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成长?是回到生命的根基所在,回到生命最初本就不确定的独一无二性,回到生命每时每刻潜在的开放性,重新以惊奇的目光打量世界,再次追问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世界可以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遇到一个叫晴川的女孩,听她谈起《冰龙》时泪盈于睫的样子。
《冰龙》的主角是一个叫阿黛菈的小女孩,她在冬天苦寒之日出生,母亲因生她难产而死,她对父亲也不像寻常小女孩般会撒娇、受宠溺。可能是外人的言语和父亲表面对她的态度,让她觉得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幸和灾难,因此逐渐将自己封闭。但有一天晚上,父亲晚上与叔叔聊天时却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爱她?噢,三个孩子里我最疼这个娇小的冬之子。”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我们都那么羞于表达对对方的爱,甚至会经常产生误解。”她告诉我,“母亲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出省打拼,反倒是父亲留在我身边,非常笨拙地教我女孩子青春期身体和生理的一步步发育,让我不要慌张。虽然他尽力在做,但性别上的差异,依然让我感觉到孤独和手足无措。小时候我非常恨我的母亲,为什么我最需要她的时候不在我身边?她没有尽到她作为母亲应有的责任。他们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他们爱我,以及不能陪伴在我身边的理由。”
“我也没有表达过我对他们的爱,一次也没有,尽管长大后,我慢慢能够理解他们。去年父亲生日,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达了我对他的爱。但是那封信现在依旧躺在我的书桌上,始终没有给他。”

还有之苏,另外一位热爱童书的女编辑,她跟我提到几年前读《地海传奇》,读到欧吉安在寒冷的清晨醒来时,看到格得留下的信,字迹几乎消退:“师傅,我去追了。”(格得是《地海传奇》的主人公,天生拥有强大的法力天赋,因为年少气盛、滥用法术而酿成大祸,遭到未知的黑影袭击,几乎丧命,于是一直在恐惧中躲避黑影。)
读到这里,她觉得那一瞬间如遭雷击。“我突然想到自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那个孤孤单单的女孩,这么多年来被母亲不断地否定着,被恐惧和焦虑追逐着……突然间生出了一股子力量,明白了我也应该转身去追,而不是逃。”
这样醍醐灌顶的时刻,在成年人阅读童书的过程中并不罕见。最好的童书,并不是人生的简化版本,而是以一种极致的优雅与简单处理生命中极为复杂的问题,如爱、孤独、失去、生命的循环。无论4岁,还是40岁,我们都在处理同样的问题。即使有一天,当我们垂垂老去,仍然会像孩子一样受伤、愤怒、受挫折。说到底,是谁在童年和成年之间划上一条界线呢?
在写给24岁的儿子的信中,英国诗人泰德·休斯曾对所谓“内在的儿童”有过一番非常动人的描述,大致总结如下: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小孩,那是我们心中唯一真实的东西,是我们的人性,是我们的灵魂,是一切可能的魔法与启示的中心。
对大部分人而言,在成长的过程中,正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我们构建起一个“第二自我”来应对外部世界的冲击。那是我们展示给世界看的面孔。至于那个“内在的小孩”,它在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的同时,也从此与我们的人生隔绝了。我们从不曾让他参与到自己的生活,承担生活的责任,因此也从未让他真正地活过。这就是大部分人的“内在儿童”。
只有当人生真正的风雨到来,某种普遍性的危机、无助或者孤独袭来时,第二自我溃不成军,“内心的小孩”才被推到前线——毫无准备,带着童年时代所有的恐惧与不安。但这样的时刻正是它想要的时刻,也是它复活的地方——哪怕被淹没、被迷惑、被伤害。同时也是它召唤自身资源的时刻——真正内在的“资源”,一种真正生物性的能力,去应对,去利用,去享受。
泰德·休斯并没有解释“真正内在的资源”是什么,但我想,那大概就是荣格所说的“原型”吧。所谓“原型”,是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先天倾向,是心理经验的一种先在决定因素,是历代祖先的典型生活场景和心理活动的不断重复,最初的感性具体的记忆表象在典型情境中不断地重复,从而形成的精神发生的普遍模式和心理结构,通过遗传传递给个体。
荣格认为原型有很多,出生、死亡、英雄、上帝、武器、自然界的月亮、风、水都是原型。通过原型,个人与往昔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原型中蕴藏着人类生命进化的秘密。童年也是一种原型,它不只是个体生命的一个阶段,也是一种超越了历史、环境和个体经验的存在,儿童的精神先天地携带着原发性的远古心灵的痕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童年对于每一个个体都是一种共享的“资源”。它以“永恒的孩子”停驻在我们身心之中,就像一棵植物的根苗,是生命最深层最根本的能量。成年之后,忽略和遗忘会让它枯萎,但如果不断重回童年,就能使这根苗发芽成长,呈现蓬勃生机。
童年持续于人的一生。童年的回归使成年生活的广阔区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童年从未离开它在夜里的归宿。有时,在我们的心中,会出现一个孩子,在我们的睡眠中守夜。但是,在苏醒的生活中,当梦想为我们的历史润色时,我们心中的童年就为我们带来了它的恩惠。必须和我们曾经是的那个孩子共同生活,而有时这共同的生活是美好的。从这种生活中人们得到一种对根的意识,人的本体存在的这整棵树都因此而枝繁叶茂。诗人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在心中发现这生机蓬勃的童年,这青春常在的持续而静止不动的童年。
这是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中的一段话。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梦想,通过诗,而不是通过现实,追寻童年。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再次体验到那个潜在的童年的可能性。
童书,最好的童书,是否也可以召唤那个内心的孩童?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门德·德扬曾说:“倒回到(童年的)本质你只能下去,你只能进入——深深地进入。一直穿过潜意识所有深深的、神秘的本能层,回去进入你自己的童年。如果你下得足够深,变得足够基本,再一次成为你曾经是的那个孩子,那么你借助潜意识进入普遍儿童的状态似乎就合情合理了。那时,只有那时,你才是为儿童写作。”

《我是花木兰》,秦文君与郁蓉合作的一部绘本,讲述一个现代小姑娘与花木兰之间的神交
秦文君,国内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也是这么说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仅仅是写自己的童年,也是关注人类的童年,一个广泛含义上的童年。”
在她看来,“童年”里蕴含了很多优美的东西,比如爱、勇气、想象,这些都是一个孩子与生俱来的能力。因为生命际遇不同,有些人能将这些能力保持到很久,有些人则渐渐消失了、褪色了。一个人在童年期,心大都是比较柔软的,也更宽容、和解、原谅、怜悯。他们对爱的渴望比较强烈,对家庭的珍视也比较真诚。很小的孩子,无论如何总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最好的。长大以后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心也渐渐变得硬了。
至少对我而言,阅读童书的过程,就是重新构建那个“内心的儿童”的过程。——一点点学着像孩子一样思考、感受、理解,一点点学着将孩童的心智重新运用到成年人复杂的生活中,培育它,给它力量,而不再隐藏它。
比如,读“十四只老鼠”系列,我学会了如何欣赏儿童的目光的诗意之处,发现“每一片叶子都有不同的表情”。读《上学路上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学会了欣赏儿童胡编乱造的借口背后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我上课迟到了,是因为巨型蚂蚁吃了我的早餐;是因为邪恶的忍者突袭了公交站;是因为一只大猩猩把公交车当香蕉吃了;是因为叔叔的时光机出了问题,把我发射到了恐龙时代……正是由于儿童天生的对于成人世界里抽象的、机械化的理性逻辑的叛逆,他们的世界才有着如此荒诞不经的奇思妙想,颠三倒四的随意发挥,无拘无束的冲动与鲁莽。
读《风去哪里了》,我试着认真思考孩子无休止的提问背后蕴含的天真无邪的哲学发问——是啊,风停了以后,它到哪里去了呢?当暴雨过了以后,雨到哪里去了呢?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云飘过天空,到哪里去了呢?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就是由无数的问号组成,而提问就像呼吸一样发自本能,自由而充满想象力。
在桑达克的《野兽国》中,我试着重新感受了童年是一个让人恐惧的人生阶段,伴随成长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恐惧、焦虑与挫败感。我也学会了幻想的疗愈作用——当桑达克的小主人公回到现实的时候,大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平静与和解。这是孩子通过想象,将创伤性的经验转化成生存和成长的正面能量。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童书里,我学会了再次以惊奇的目光打量世界。人到中年,我们大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世界并不在乎我们的意志。在很小的时候感受到的新奇可能还会在某些时刻再度出现:美妙的乐曲、迷人的风景、新的爱情故事、生孩子,这些事情都会再次激发新奇之感。但这样的时刻只是回响,而且很少出现。这样的时刻让我们心怀感激,同时又满心惆怅,因为不管多微弱,它们让你想起,在过去某一个阶段,这样的时刻多得不得了,好像充满了整个世界——也许是冬天夜空的繁星;也许是第一次在海滩边,眺望大海,手中抓起数不胜数的沙子;也许是台风来的那个夜晚,听着外面大风大雨,鬼哭狼嚎,房子仿佛随时要被吹到天上去,让你惊叹这样狂暴的自然之力到底来自何方?而童书中,充满了这样的时刻。
在此过程中,我的孩子就像那位来自B612星球的小王子——正是他的执着追问唤醒了飞行员心中沉睡的童年,让他最终抛掉了成人世俗化的认知,回归到童年本真,并最终找到了自己隐匿已久的童年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