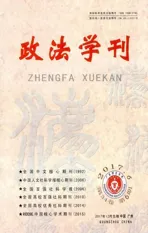我国民法的法源及其解释
2017-01-24周友军
周友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191)
一、《民法总则》中法源制度的发展
民法的法源,也称为民法的渊源,是指民法的具体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民法”并不限于制定法,而是指所有具有法效力的规范。[1]1-2
我国《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是《民法总则》就法源所作的规定,其在法律适用中具有重要意义。
与《民法通则》第六条相比,《民法总则》第十条没有再将国家政策作为民法的法源,这一做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国家政策”,是指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委颁发的关于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任务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①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第六条却认为,国家政策仅仅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笔者认为,《民法总则》废止国家政策作为民法的法源,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需要。理由主要在于:其一,国家政策的本质就是依据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或工具。[2]“靠政策治理的实质是一种人治”[3],在我国《宪法》明确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不宜将政策作为民法的渊源。其二,从我国司法实务来看,《民法通则》第六条中关于国家政策规定的适用颇为混乱,误用、滥用的判决屡见不鲜。[4]其三,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来看,其也已经否认了国家政策可以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第六条规定 : “对于本规定第三条 (刑 事裁判文书)、第四 条(民事裁判文书)、第五条(行政裁判文书) 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民法总则》第十条还增加了习惯(实际上是习惯法)作为民法的法源。这一规定是我国长期司法实践经验和立法经验的总结。在建国初期,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就曾以解释承认法官可以用习惯法补充法律漏洞,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①1951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关于赘婿要求继承岳父母财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当地有习惯,而不违反政策精神者,则可酌情处理。”我国一些法律中也认可习惯法可以作为法的渊源。②例如,我国《物权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
《民法总则》增设习惯(实际上是习惯法)作为法源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这契合比较法上普遍的做法。在现今各国法制,在民事方面,不论其法典本身有无明文规定,不承认习惯法为法源的观念已经没有了存在的空间。[5]306第二,这有助于实现判决的可接受性。这是法律为人们接受的前提,也是减少交易成本、形成稳定预期的前提。习惯法以法律共同体中的长期实践为前提,而且此种习惯必须以法律共同体的普遍的法律确信为基础。[6]106既然是人们的共同习惯,以其作为裁判依据,就有助于实现判决的可接受性。第三,这有助于避免法律的僵化和填补法律的空白。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这些都要求我们应当较多地尊重习惯,只要不与法律和公序良俗相违背即可。习惯法的认可,可以使社会规范进入法律,使法律能够与社会同步发展,进而避免法律的僵化和填补法律的空白。例如,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存在其民族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可以作为民法的法源。再如,公众人物人格权受限制规则,经过范志毅赌球案、杨丽娟诉南方周末案等,已经可以被认可为习惯法,就应当作为法源,从而填补我国法律的空白。
遗憾的是,如果法律没有规定,也没有习惯法时,将以何者作为民法的法源,《民法总则》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从法制史的角度观察,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反思实证主义和法典主义的局限,在其第一条承认法典的不完美性,明确了制定法、习惯法作为民法的法源,同时赋予法官在发现法律的漏洞时,立于立法者的地位造法的权力。③参见苏永钦:“民法第一条的规范意义”,载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这一做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继受。例如,旧中国民法就借鉴了《瑞士民法典》的经验④参见苏永钦:“民法第一条的规范意义”,载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于第一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韩国民法典》第一条也有类似规定。⑤《韩国民法典》第一条规定:“关于民事,如无法律规定,依习惯法;如无习惯法依法理。”
有学者认为,如果制定法和习惯法不足以因应的,则应当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以“法理”作为民法的渊源可能更为妥当,毕竟民法的基本原则只是法理的表现形式之一,以“法理”作为民法的渊源更具有包容性。而且,以法理作为补充性的法源,有助于克服实证主义的不足,明确司法者作为立法者助手的地位,从而因应社会的变迁。
二、我国民法上的法源
(一)制定法
《民法总则》第十条所说的“法律”,应当理解为制定法。自清末变法以来,我国就被纳入了大陆法系,所以,制定法是我国最重要的法的渊源。
在特殊情况下,民事法律就特定事项,明确其仅可以适用特定范围的制定法,这些规定应当理解为就民法的法源作出了特别规定。例如,《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这就意味着,在对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判断时,民法的法源限于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和行政法规(国务院制定的)。
从长远来看,只要是依据《立法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应当作为民法的法源。至于部门规章等较低层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损害民事主体权益等问题,可以通过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等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在我国未来还应当确立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以避免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因此,作为法源的制定法应当包括各个层次的制定法或者说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狭义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条例、办法、地方性法规等。
但是,在当前我国没有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定的背景下,作为民法法源的制定法,应当作出限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应当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狭义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在认定作为民法渊源的制定法时,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其一,制定法是否包括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法律法规所作的解释。它的形式包括“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都赋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的权力。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于第一百零四条再次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严格贯彻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离的宪政理论,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应享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从司法解释的实际效果来看,它具有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特点,在我国发挥了制定法的作用。所以,我赞成此种观点,即司法解释是准立法。[7]314
其二,制定法是否包括国际条约?举例而言,我国《著作权法》中尚没有强制许可的相关规定。但是我国已经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这些公约中规定了著作权的强制许可。如果在国内案件中涉及到著作权的强制许可,是否可以适用该国际条约?对于国际条约的国内效力问题,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条约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约定,其只能拘束国家,不能直接约束其国民。[8]26因此,国际条约在国内发生效力的前提是由国家通过个别立法来实施国际条约,这种立法活动可能是立法行为,也可能是国际条约颁布或其它宪法程序。此种模式被称为“间接适用模式”或“个别转换模式”。[9]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条约虽然是国家之间的约定,但同时也是国家的意思决定,它的签署就是对国民发生拘束力的表示,所以,也具有拘束国民的效力。[8]26换言之,国家一旦缔结或加入某一国际国际条约,该国际条约便自动地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从而无需转化即可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此种模式被称为“直接适用模式”或“或自动纳入模式”。[9]
就此问题,我国现行法上并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做法:[10]33-34
一是一些国内法明确规定,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如有条约的,直接适用条约。例如,1985 年《继承法》第 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于涉外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
二是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要求或与其他部门联合通知要求直接适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 1987、1989 年的通知中,要求各级法院直接执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三是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了条约。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1 年 11 月 15 日就荷兰英特艾基系统有限公司(宜家)、美国杜邦公司、美国宝洁公司状告北京国网信息有限公司域名纠纷等六个涉外知识产权案作了终审判决。由于我国《商标法》对域名纠纷、驰名商标的认定尚无立法,故判决书中直接适用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总体上,笔者更赞成“直接适用模式”,毕竟国家有贯彻国际条约的义务,而且,我国一些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已经采取了这一模式。另外,在我国,因为立法机关的任务繁重,国际条约及时转化为国内法往往不太可能,如果不能直接适用,就使得我国违背了贯彻条约的义务。
(1)无效力说。此种观点认为,从近代立宪主义的精神及近代宪法成立的历史背景来看,基本权利本身是一种消极的权利,是一种对抗国家侵犯的防卫权。所以,其效力仅限于公法领域。在私法领域,考虑到“个人与国家的二元对峙结构”,基本权利的效力不应当在民事主体之间产生。(2)直接效力说。此种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的巨大发展,社会结构也相应随之改变,使得私法主体之间呈现出地位、力量悬殊,基本权利也经常受到平等主体的侵扰。因此,基本权利的条文在私法关系中也应有“绝对效力”,并且可直接援用。(3)间接效力说。此种观点在维护了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权力的传统观点的前提下,认为基本权利只能通过民事立法或者法官对于民法概括条款的解释而对民事案件发生效力。迄今为止,德国与日本的宪法判例均采纳了该学说,这也使该学说居于通说的地位。我个人赞成间接效力说,这不仅是基本权利性质的要求,也是实现私法相对独立性的需要。因此,宪法并不能作为民法的渊源,但是,它可以通过民法上的制度安排(如一般条款等)发挥间接效力。另外,我国《宪法》上的规定基本上都是不完全法条,实际上也无法作为裁判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并不赞成齐玉玲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因为其将宪法作为民事案件的直接裁判依据。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不过,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7次会议于2008年12月8日通过了《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其理由是“已停止适用”。当然,在民事案件的裁判中,法官也可以将宪法的规则和原则作为说理论证的依据。[12]例如,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诉被告沙某某信用卡纠纷一案中,法官认为,如果认可信用借款超高额利率,则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限制民间借贷利率的做法不同,从而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②参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5)高新民初字第6730号民事判决书。其三,制定法是否包括宪法?这涉及到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理论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11]292法院在此处引用《宪法》并非作为裁判依据而仅用于判决说理论证。
(二)习惯法
习惯法,是指基于国民的直接的法认识,以继续不息、反复奉行的习惯,被确信为法律,从而被援用的法。[13]9《民法总则》第十条使用了“习惯”的概念,笔者认为,作为法源的应当是习惯法,而不是单纯的习惯。
习惯法的效力如何,在学说及立法例上有3种不同的做法:(1)绝对无效说。此种观点认为,法律限于成文法,习惯没有法律的效力。例如,《萨克森民法典》第二十八条就曾规定,习惯仅能解释当事人的意思,没有法律的效力。(2)绝对有效说。此种观点为德国历史法学派所主张,其认为,习惯与法律有同等的效力,习惯甚至可以改废法律。(3)相对有效说。此种观点认为,习惯仅具有补充制定法不足的作用。相对有效说为很多国家所认可。[14]31
我国《民法总则》第十条实际上是采纳了相对有效说。这就明确了,习惯法应当作为法的渊源,但是,仅辅助制定法发挥作用。
当然,在具体法律规范中,也可以确认习惯具有排除或变更法律的效力。[15]例如,《日本商法典》第一条规定:“关于商事,本法无规定者,适用商事习惯法,无商事习惯法,适用民法典。”这一规定表明,通过法律确认,习惯法可以优先于特定的法律规则而适用。虽然在我国法律中尚未有类似规定,但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问题是,习惯法的存在是否应当由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对此,在理论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当事人举证说。从罗马法的注释法学派直至19世纪初学说上的权威意见认为,习惯法仅是一种事实,应由当事人主张并负举证责任,否则法院可以置之不问。其目的在于,排斥地方习惯而重视罗马法。[5]309二是法官依职权查明说。此种观点认为,习惯法虽是一种事实,但同时就是法律,所以法官应当知道,也应当和成文法律一样依职权查明。德国学者普赫塔(Puchta)等人持此种观点。[5]309三是折中说。此种观点认为,法官要知道习惯法的存在及其内容,不像成文法那样容易,要求法官对习惯法和成文法同样适用,乃是强其所难。所以,如果法官不知道习惯法的存在,可以命当事人举证。当事人也可以自动主张而举证,此时,法官可以自由地凭其意识取得心证,以定舍取。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等人持这一观点。[5]309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习惯、地方制定之法规及外国法为法院所不知者,当事人有举证之责任。但法院得依职权调查之。”这实际上是采折中说。笔者赞同折中说,毕竟习惯法属于法律问题,而并非事实问题,应当由法官依据职权予以查明。但是,如果法官确实不知道,也可以要求当事人举证。虽然在比较法上也有将这一规则纳入民事诉讼法之中的做法,但是,将其纳入民法之中规定也并无不妥。笔者认为,可以在我国司法解释中明确这一规则。
(三)法理
法理,是指法律的原理。[16]6我国《大清民律草案》曾使用“条理”的概念①我国《大清民律草案》第一条的立法理由中曾提出,“条理者,乃推定社交上必应之处置,例如事君以忠,事亲以孝,及一切当然应遵奉者皆是。”,后来,旧中国民法改采“法理”。就民事案件来说,法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而拒绝裁判(参见《法国民法典》第四条),否则就是拒绝正义。但是,正所谓“法条有尽、世事无穷”,法官不可能从制定法之中寻找到所有可供适用的裁判依据。此时,其就应当借助于习惯法或法理。从比较法上来看,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都明确了,法理可以作为法的渊源。法官以法理作为法的渊源,实际上就是以法理为基础,依据自己如作为立法者应提出的规则进行裁判。同时,法官所依据的法理应当是公认的法理。虽然《民法总则》没有明确法理是民法的法源,但可以通过漏洞填补的方法,确认法理是补充性的法源。法理的表现形式很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其一,制定法。在制定法中,其条文背后就体现了一定的法理,法官可以通过探求条文背后的法理,作为裁判待决案件的依据。此时,法官要借助类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的方法。
其二,比较法。它是指国外的立法和判例。法国著名比较法学者勒内·达维德说过:“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其他国家或地球上其他部分的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命运;了解和借鉴他国的法律,在今天的世界是需要的,在明天的世界则是必需的。”[17]5可以说,比较法体现了人类处理法律问题的智慧和经验,相当于一个工具箱(toolbox),因此,可以作为法的渊源。我国作为法律继受国更应当重视其地位。
其三,民法的原则。法律的原则,是指作为现行法的若干规定基础的一般价值和目标。[18]485在我国,不少法律都规定了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法律的原则并非裁判规范,其不包含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只能在漏洞填补时作为法官创造性补充的依据。从我国实践来看,法官往往以民法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依据进行裁判。有学者提出,可以以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源,但是,考虑到对何为“基本”的问题难以达成共识,笔者认为,还是采“民法的原则”的表述,以避免学界的争议,而且使其可包含的更丰富的内容。例如,信赖保护、权利外观保护等也可能不被认为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也可以作为民法的原则,从而作为裁判的基础。
其四,判决。它是指法官在适用法律或解释法律时表示的意见。[5]315在我国,判决不能作为判例,但可以作为法官创造性补充的依据。不过,这里所说的判决,是指没有形成习惯法的判决。
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确立案例指导制度,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类似案件判决差别过大的难题。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2010〕51号)发布,开始推行案例指导制度。依据该规定,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不过,指导性案例的地位如何值得探讨。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扩大司法解释的种类范围,将指导性案例规定为一种新的司法解释。[19]也有学者认为,因最高法院拥有法律解释的制度性功能、法律规范的复合型确证授权以及试行立法的制度性实践,指导性案例已成为司法裁判中基于附属的制度性权威并具有弱规范拘束力的裁判依据,具备“准法源”的地位。[20]从目前的数个民法典总则草案建议稿来看,仅有龙卫球教授主持的《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第三条将其作为民法的渊源。 笔者认为,考虑到指导性案例具有的适时废止的特点,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中的判决理由其作为法理的表现形式,不宜将其作为一种司法解释或直接的法律渊源。②该草案建议稿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和惯例的问题,可以结合审判实际需要和有关实践发展情况进行合理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有关立法精神。另外,考虑到指导性案例中的判决理由有可能因滞后于社会发展而违背了法的正义性的要求时,法官应当可以不予参照。毕竟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如果参照会影响司法公正,当然应当予以突破。只不过,法官不予参照,应当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应当负有较重的论证义务。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4号“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旨在明确交通事故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如果法官认为,这一指导性案例中的判决理由并不妥当(如与过失相抵规则存在内在的冲突),则应当负有充分的论证义务。据笔者与法官交流的情况,很少有法官在受害人特殊体质案件中参照适用第24号指导性案例所确立的规则。
其五,学说。它是指私人就法律从事科学研究时所表示的意见。[5]315学说作为法理的表现形式,参与司法裁判,有助于实现民法研究领域与民事司法领域的良性互动。不过,据学者调查,现实并非总是令人满意。[21]41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出路在于,强调通说见解的法的渊源地位,并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拘束法院的效力,以实现司法界和理论界的配合。[22]这至少体现在法官的论证义务方面,如果法官在漏洞填补时违背通说见解,应当负有更重的论证义务。
其六,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并非立法或司法解释,其如果要发挥拘束力,只能解释为其属于法理的表现形式。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无法行使监护权的,依照婚姻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代替自己已经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子女对孙子女、外孙子女尽抚养义务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主张探望权的,予以支持。”这就可以用于填补我国探望权规定的漏洞。
三、我国民法法源的解释
(一)民法法源解释的永恒主题:法的安定性与法的妥当性的关系
民法法源的解释,也就是法律解释。法律解释的永恒主题是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的关系,民法的解释也是如此。法的安定性,大概可以理解为法的确定性、法的一致性以及法的可预期性。而法的妥当性,大概可以理解为法的合正义性,尤其是个案正义。
正如美国学者庞德所言,“一般安全中的社会利益促使人们去探寻某种据以彻底规制人之行动的确定基础,进而使一种坚实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得到保障。但是,社会生活情势的不断变化却要求法律根据其他社会利益的压力和种种危及安全的新形式不断做出新的调整。因此,法律秩序就必须既稳定又灵活。”[23]4法律秩序必须“稳定又灵活”的要求,落实到法律解释领域,就成为其永恒主题,即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的关系问题。
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史,就是处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关系的历史。在19世纪,概念法学盛行。此种理论强调法律体系具有逻辑自足性,法官应当消极地司法,法官只是“法律之嘴”而已。概念法学的目的主要是要保障法的安定性,或者说,以法的安定性为最高价值,这符合19世纪中期德国社会的需要,当时是德国资本主义的稳定时期,韦伯的预测可能性、计划可行性是反映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色的哲学思潮的典型代表,而概念法学无疑是该社会性对法学的要求和该哲学思潮在法学中的反应。[24]20
但是,概念法学过分强调法的安定性,难免忽视法的妥当性。在此背景下,德国学者耶林(Jhering)提出了“目的法学”的主张,认为法律应当来源于目的并为目的服务。其思考的着重点就是法的妥当性,也从此揭开了反对概念法学的序幕。此后,在20世纪初叶,德国又出现了“自由法运动”。德国学者福煦、康托洛维兹等自由法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法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由地发现法律,并用这些自由发现的法律指导案件的判决。[25]他们强调审判过程中直觉和感情的成分,要求法官根据正义和公道运用法律。[26]显然,自由法运动又过分倾向于法的妥当性,而忽视了法的安定性。
在批评概念法学、吸收耶林“目的法学”思想以及避免“自由法运动”弊端的基础上,德国学者黑克(Heck)发展出了利益法学。它以法官应当注重各种“利益”为核心,认为,法律起源于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判决应该在各种冲突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25]利益法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两点认识:首先,法官应受法律约束。法官也要像立法者一样界定利益,并对利益冲突进行判决。但是,立法者所作的利益衡量应当优先于法官的个人评价,对法官具有拘束力。其次,制定法是有缺陷的,它们不够完全,也并非全无矛盾之处。现代的立法者意识到法律的这种缺陷,因此期待法官不是依循字句,而是合乎利益要求地服从法律;他们不仅要在既有的法律命令下进行逻辑归入,还要对欠缺的命令进行补充,对有瑕疵的命令予以纠正。[27]利益法学的思想丰富,难以做简单的评价。但在总体上,利益法学其就是要谋求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的平衡。例如,按照黑克教授的看法,法官是“立法者的助手”。“法官造法的权力”这个说法,他认为是允许并值得推荐的。[6]241-242这就有助于实现法的妥当性目标。同时,利益法学也强调法的安定性。利益法学的支持者强调,法官要查清立法者通过特定的法律规范要保护的利益。同时,法官应当受到立法者评价的约束。[6]241-242正如黑克自己所指出的,“法官的职责不是要自由创造新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在现有的法律制度范围内参与实现那些已被承认的观念。”[27]
后来,以德国学者拉伦茨(Larenz)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又倡导价值法学(或称评价法学)。价值法学继承了利益法学,并予以发展。就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关系的处理,其与利益法学差别不大。所以,德国学者科因(Coing)认为,“价值法学是利益法学高贵的女儿。”
在20世纪40年代,还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法学思想,即动态系统论。该理论是奥地利学者威尔伯格(Wilburg)在1941年出版的著作《损害赔偿法的要素》中首次提出的。[28]后来,奥地利的比德林斯基(Bydlinski)教授又在合同法领域发展了这一理论。[29]这一理论的基本构想是,“特定在一定的法律领域发挥作用的诸‘要素’,通过‘与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相对应的协动作用’来说明、正当化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在动态系统中,按这些要素的组合,进而按它们的满足度的总量,不仅可以相应地决定法律效果的发生与不发生,还可以决定其在多大程度上发生的范围。所以,这些要素具有跨越要件和效果两个侧面的“动态性格特征”。[30]177要理解动态系统论就必须考察该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首倡者的问题意识。威尔伯格提出这一理论之时,正是概念法学出现危机,而自由法运动开始流行的时期。他希望在克服概念法学的僵化性的同时,探索克服自由法运动中过分自由的问题。[30]180因此,该理论在观察法律体系时,不是聚焦于由法律概念、法律制度组成的外在体系,而是聚焦于其背后的内在体系。而且,在对待评价问题时,其不是预先确定评价的内容,而是试图给评价的方法提供一个框架。[30]233-234应当说,动态系统论也是力求在法的安定性和法的妥当性之间谋求平衡。不过,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对法的安定性较为忽视。例如,德国学者艾塞(Esser)、克茨(K·tz)、马藤(Marton)、艾恩哈特(Reinhadrt)等都提出威尔伯格的理论会导致重大的法的不安定性。这种批评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威尔伯格的构想放弃了包含固定的构成要件的规则。他虽然列出了要考虑的要素,但没有阐明这些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具有多大的分量。①Esser,Theorie und System einer allgemeinen Deutschen Schadensordnung,DRW 1942,71,78f.;Kötz,Haftung für besondere Gefahr,AcP170(1970),20;Marton,Versuch eines einheitlichen Systems der Zivilrechtlichen Haftung,AcP162(1963),36f.;Reinhadrt,Beitr?ge zum Neubau des Schadensersatzrechts,AcP148(1943),186.转引自[日]山本敬三:《民法中的动态系统论》,解亘译,《民商法论丛》第23卷,第194页。
(二)民法法源解释的目标
民法法源解释(即民法解释)的目标是什么?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主观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解释的目标是探究立法者的意旨。法律的解释就是立法者意思的再现,即将立法者的认识,重加认识,因而对于立法理由书、审议记录等特别重视。[8]74
二是客观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解释的目标是探究法律的意旨。法律一旦成立,即与立法者分离,而独立存在,成为国家的意思,不受以前立法者意思的拘束。法律解释应当探究法律的独立的意思,也就是说,应探求其公平合理性。[8]74例如,德国学者拉伦茨(Larenz)就认为,解释的目标是“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标准意义”。[31]199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所说的“法律比立法者更聪明”,就是客观说的通俗表达。
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区别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主观说是以制定法律之时作为时间参照来确定法律的含义,而客观说是以适用法律之时作为时间参照来确定法律的含义。[18]428其二,主观说注重历史解释的方法,而客观说并不过分强调历史解释。主观说的支持者认为,在法律解释过程中,所有的立法资料应当被综合运用,以确定立法者的意思。因为它们是最重要的确定立法者意思的素材。[18]430而在客观说之下,历史解释只是确定法律的规范意旨的重要途径而已。[31]199
笔者认为,就民法解释的目标,原则上应当采主观说,但是,如果有充足的理由,则应采客观说。这就是说,民法解释原则上应当探求立法者的意旨,因为司法权的行使应当是贯彻通过立法程序所体现的公众意志,这是司法权的定位的要求,也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依法裁判”的要求。但是,司法又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法官对立法应当是“有思考的服从”,应当充当立法者的“助手”。所以,如果有充足的理由,即为了实现“此时此地的正义”,则应当探求法律的意旨,不应拘泥于立法者的原意。当然,在探求法律的意旨时,也应当充分考虑立法者的意旨。
(三)民法解释方法与民法的法源
正如德国学者齐佩利乌斯所言,“对象决定方法”。[32]1法律解释方法也应当对应于法的渊源。就制定法来说,其解释应当对应于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和价值补充方法。习惯法的解释对应于以习惯法来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而法理的解释,则对应于类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和创造性补充的方法。当然,法律解释方法应当是人们达成共识的方法,下文中所述的各种法律解释方法,都是在总结法官裁判经验和理论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
就习惯法和法理的解释而言,都是以制定法存在法律漏洞为前提的,或者说,两者只有在存在法律漏洞时才作为法的渊源。所谓法律漏洞,是指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状态。[31]251法律漏洞的概念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圆满性。所谓不圆满性,就是法律应当对其进行规范,但是没有规范。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规范”。就明显的法律漏洞来说,其不圆满性是通过法律条文的可能文义范围来认定,也就是说,法律条文的最大可能文义范围都不可能涵盖待决案件。正如德国学拉伦茨(Larenz)教授所言,“法的解释及(补充或改造法律的)法的续造,两者的界限只能是语言上可能的字义,实在不能发现其他的界分标准。”[31]203二是违反立法计划。法律漏洞是法律“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是否存在违反立法计划,应当从法律的总体来考虑,此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法律的价值、法律的目的、法律的原则等。[18]473在民法法典化的背景下,法律的制度和规则将得到完善,法律漏洞将大为减少,但也不可避免出现漏洞。因为成文法是以事先确立的统一的规则来规范生活,其难以避免地出现“有限理性”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法律漏洞的认定本身也属于价值判断,法官要考量各种因素进行论证,而最重要的考量则是“此时此地的正义”的要求。例如,非婚同居者是否可以请求死亡赔偿金,这就涉及到是否存在法律漏洞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对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四)以制定法作为民法法源时的解释方法
在以制定法作为法的渊源时,其解释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和价值补充方法。在民法法典化的背景下,民法典就是制定法的最主要体现,因此,此种解释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国学者萨维尼曾经提出了法律解释的4种方法,即语法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①语法解释以将立法者的思考转变为我们的思维的媒介的用语为作为对象,说明立法者使用的语言规则;逻辑解释存在于思想的组合,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逻辑联系之中;历史解释以由现行法律中关于法律关系的各种法规规定的状态为对象,通过这种方式,使新法和旧法互相关联,使旧法适应新的形势;体系解释,强调所有的法律制度以及法规都是一个大的统一体,他们是互相连接、彼此结合、具有内在的联系。体系解释就是要提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某项法律如何有效地介入这一体系。参见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247页。, 但也有一些后世法学家予以突破。究竟有哪些法律解释方法,可谓见仁见智。笔者结合我国学者的研究,赞成将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分为3类:(1)文义解释。它是指运用语法、与语言相关的经验,尤其是语言习惯,进行的法律解释。[18]437(2)论理解释。它是指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字句,而以法秩序的全体精神为基础,依一般推理作用,以阐明法律的含义。[8]74论理解释可以具体包括如下几种:一是体系解释。它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即依其编、章、节、条、款、项的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的含义为依据而进行解释的方法。[7]316二是历史解释。它是指以作为立法背景的立法者的想法、判断和目的作为依据而进行解释的方法。[18]449三是目的解释。它是指以法律条文(或法律制度)的规范目的为依据解释法律的方法。四是当然解释。它是指法律条文虽然没有规定,但是依据规范目的衡量,待决案件的事实较之于法律所规定者,更有适用的理由,而应当适用该法律规定的解释方法。[33]120当然解释包括两个次类型,即举轻以明重和举重以明轻。五是反对解释。它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文字,推论其反面的结果,从而解释法律的方法。[33]114六是比较法解释。它是指引用国外立法例和判例为依据,以解释本国法律的方法。[7]288七是合宪性解释。它是指要尽可能地避免与宪法规则和原则相冲突的解释结论的解释方法。[18]455(3)社会学解释。它是指通过社会效果的预测来进行的法律解释。[34]236-237例如,非登记动产的物权人请求返还财产,如果对《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项进行反对解释,似乎要适用诉讼时效。这一解释可能危及人们的正常交往,影响社会秩序。
在这里,当然解释和反对解释被作为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仍然是在法律条文的文义射程范围内的解释。在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其属于漏洞填补,因为解释结论已经超出了法律条文的文义射程范围。笔者认为,解释结论是否超出了法律条文的文义射程范围,并无十分明确的标准,需要借助于社会一般观念来认定。但是,如果将当然解释和反对解释作为漏洞填补方法,其就属于法官造法的范畴,如此,会增加法官适用这两种方法时的心理压力和论证负担。所以,将两者作为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更容易为法官所接受。此外,在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属于法律解释方法。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只是从法律解释结论与法律文义对比的角度进行的观察,并没有明确解释的依据是什么,因此,不宜作为法律解释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解释方法在诸多解释方法中,应当具有特殊的地位,理由主要在于:其一,这是法律适用合宪性的要求。“民主、权力分立和法官受到法律约束,这些宪法原则要求法院尊重现有的法律评价。这首先意味着一种义务,即借助于可使用的方法去考察这些价值标准是否现实存在。因此,只要可能,宪法就要求对产生历史进行研究。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违背了上述宪法原则。也就是说,历史解释是任何合宪性法律适用的不能放弃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6]351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也可以理解为,我国司法适用合宪性的宪法依据。其二,这是提升司法权威的需要。历史解释的目的在于,重建立法者赋予法律规范的意义和目的。[6]342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尊重立法原意,根据立法者的规范目的进行审理,尽最大程度地排除个人价值偏好,将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司法极不统一的社会现状,提高法官威望,树立司法权威。[35]14
当然,如果法官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其也可以违背历史解释的结论。“为了做出公正的判决,法院不得不表现得更加大胆;它们必须摆脱立法者提出的,同新的社会条件不相适应的指示。为此目的使用过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在于把法律条文与历史背景分开。对法律所用词句的解释,不考虑其历史渊源,不问立法者的意图,而是赋予今天显得满足正义要求的意义。”[17]111
价值补充的方法,是对于一般条款和不确定概念的解释方法。价值补充,是指立法者已授权法官于个案中进行补充,且其补充方式是由法官依价值判断将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具体化。[34]297价值补充,究竟属于狭义的法律解释,还是漏洞填补,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补充属于漏洞填补。在存在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情况下,也构成法律漏洞,并将其称为“法内漏洞”。因为法律虽然对特定事项有所规定,但是,规定得过于模糊,存在法律的不圆满状态。另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补充属于狭义的法律解释。制定法是通过文字的形式存在的,价值判断只是隐藏在文字的背后。[36]狭义的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区分的关键是,作为法律的基础而存在的价值判断,是否可以适用于待决案件。[37]在存在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情况下,法律中的价值判断是可以适用于待决案件的。笔者认为,价值补充应当属于狭义的法律解释的范畴。理由在于:第一,在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之下,法律文义的可能范围涵盖了待决案件。狭义的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的区别是法律文义的可能范围。只要判决是依据法律的可能文义而作出的,它就可以认为是直接遵从了立法者的命令。如果超出了文义的可能范围,就必须借助其他的理由来加以论证和说明。[38]第二,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存在表明,无法认定“违反立法计划”这一要件。因为立法者已经认识到相关的问题,并已经对其作出了规范。
不过,价值补充的方法是与狭义法律解释的方法相对独立的,因为其适用对象限于一般条款和不确定概念。例如,《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确立的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就需要进行价值补充。理论上,一般认为,价值补充需要借助于类型化的方法。笔者赞同这一看法,但必须强调的是,类型化的运用应当尽可能结合社会生活和法院判决来进行,需要实证研究的基础。例如,《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这就是一个概括条款,其中应当包括“夫妻关系的存在”这一类型。
(五)以习惯法作为民法法源时的解释方法
以习惯法作为法的渊源时的解释方法,实际上就是以习惯法填补法律漏洞。此时,首先应当认定法律漏洞的存在,然后再认定习惯法的存在。
习惯法的认定,必须满足如下几个因素:(1)存在经久的惯行。习惯的产生,源自人类模仿的本能。而习惯法的认定必须要有经常的惯行,至于时间的长短,无法以确切数字计算,但是应当是经常发生的。[5]如果是全国人民所遵守的习惯,则形成普遍适用的习惯法;如果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习惯,则只可使该区域内的人民受到拘束。[13]9(2)存在法效的确信。习惯法与习惯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包含了“法效的确信”的要素,后者则没有。如果缺乏这一要素,则只是普通的习惯(如小费的给予、礼物的馈赠等),不能发生法的效力。[5]310从“法效的确信”这个认定要件来看,《民法总则》第十条使用了“习惯”而非“习惯法”的表述,并非十分严谨。比较法效的确信和经久的惯行两个因素,前者最关宏旨,因为一旦在社会上形成法效的确信,即所有人都应该受其拘束的信念,纵使历时不长,一样可以形成习惯法(时间只是形成确信的一种方法)。[39]10(3)不违反强行法和公序良俗。这是对习惯的合法性控制,可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民法总则》第十条仅强调习惯法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确有缺陷。法官填补法律漏洞,应当在整个法秩序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他不能选择违背了整个法秩序的习惯法。例如,在我国山东等地有所谓“买房先问四邻”的做法,但是,这一习惯违反了“财产权自由流转”的公共秩序,不得作为习惯法来对待。再如,在云南的独龙族,女子接受彩礼后与他人私奔,有所谓“以其姐妹顶替”的习惯,这一习惯就违反了公序良俗。
(六)以法理作为民法法源时的解释方法
以法理作为法的渊源,也应当以法律漏洞的存在为前提。以法理作为法的渊源时,其解释方法包括如下几种:
1.类推。它是指就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比附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的规定,以为适用。“相类似之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是类推的法理基础。[33]146类推可分为个别类推和总体类推。个别类推,也称为法律类推,是指将特定的、单一的法律规范类推适用于待决案件。总体类推,也称为法的类推,是指从多个既存的法律规范之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的原则,再将该原则运用于待决案件。[18]477类推适用可以使得法官的评价与现行法的评价保持一致。例如,在我国,曾经发生过骗子冒充自己是房主,从而冒名处分他人不动产的案件。就冒名处分不动产的行为,就可以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定,认定该交易行为无效。在该类案件中,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也不应适用,因为善意取得适用的前提是除了无处分权以后,合同并无其他效力瑕疵。善意取得的功能仅仅是要解决合同当事人无处分权的问题。既然冒名处分不动产的合同因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而被认定为无效,就不必再探讨其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再如,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本条仅规定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对于其他的民事责任竞合并无规定。这就构成了自始的法律漏洞。考虑到其他的民事责任竞合与《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责任竞合具有类似性,笔者认为,法官可以运用类推适用的方法,来进行漏洞填补。例如,小偷盗窃他人的名画,此时构成侵权责任(即故意侵害他人所有权的责任)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即占有不当得利返还)的竞合,受损害方也应当有权选择请求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或不当得利返还责任。
2.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是指依据法律的规范目的,将既有的法律规定,扩张适用于待决案件的漏洞填补方法。目的性限缩,是指依据法律的规范目的,将法律条文核心含义所包含的案型,排除于该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之外的漏洞填补方法。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都是依据法律的规范目的而进行的法律解释。[40]只不过,前者适用于明显的法律漏洞,而后者适用于隐藏的法律漏洞。例如,《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条将紧急救助作为免责事由加以规定,回应了我国当下出现的“老人倒了扶不扶”的社会问题。这里的紧急救助就是管理他人的紧急事务。“紧急”应当理解为,避免受助人的急迫危险。[41]507救助人所管理的他人事务包括对于财产的救助(如抢救他人商店中的商品)和人身的救助(如从火中救人)。考虑到本条的法律后果是救助人完全免责,可以进行目的性限缩,即这里的紧急救助限于对他人的人身的救助。再如,在一个赠与的案件中,62岁的王某(女)和贺某(男)是黄昏恋的再婚夫妻。2005年,王某住进贺某家里。贺某于2010年9月过世,王某却当了被告,贺爷爷的子女要求她搬家。贺家子女称,其父早在2007年就立下遗嘱,由他们3个子女共同继承房屋。贺某生前还请了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律师见证书》。2008年,贺某又立下赠与合同,约定将此前遗嘱涉及的房屋赠与3个子女,自己不再拥有所有权。该赠与合同经公证处公证后,房屋也过户到3个子女名下。依据《继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问题是,在本案中,贺某是通过生前赠与的方式,规避了必留份的规定。因为必留份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要保障必留份权利人的生活,具有死后扶养的意味。法官如果要使王某获得必要的遗产份额,就应当借助于目的性扩张的方法。可见,目的性扩张不仅有助于实现法律的规范目的,而且有助于解决法律规避的问题。
3.创造性补充。它是指脱离了制定法和习惯法,法官依据法理的创造性运用而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都还没有完全脱离制定法,创造性补充则完全脱离了制定法。具体来说,创造性补充的依据包括:民法的原则、比较法、判决、学说。例如,自助行为是否可以作为阻却违法的事由,我国《民法总则》和相关法律都没有规定。在比较法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关于自助行为的规则①《德国民法典》第229条和第230条、《瑞士债务法》第52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51条。,在实践中,民众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常常需要实施自助行为(如饭店经营者扣留未付款顾客的手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借助学者的通说见解和比较法来进行创造性补充。
四、结语——通过司法解释完善我国民法法源及其解释规则的建议
虽然《民法总则》第十条就民法的法源及其解释的规定不太完整,但是,这一规定毕竟可以为司法解释的拟定提供了基础。
在德国,其民法秩序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依赖于三个因素:制定法、法官法和学说。“立法都局限于一般原则性规定,而将法律体系符合时宜和客观情况(zeit- und sachadäquat)的具体化和续造留给了法官法和教义学。”“法律进步很少由立法者而更多地由‘法官判决和静谧的学术研究’促成。”[42]7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民法秩序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仰赖于四个要素,即制定法、司法解释、学说和指导性案例。较之于德国,我国制定法的部分作用被司法解释所取代,立法者在立法之时似乎就预设了“反正以后还会制定司法解释”,所以,不少条文趋于抽象,不少条文表达模糊,也有不少规则缺失。另外,在我国,德国学说发挥的作用也部分地被司法解释所取代。司法解释通过结合司法实务中的问题和学界的研究成果,将部分学说“成文化”。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完成之后,司法解释是否还继续存在?这个问题目前尚不明确。②深入的研究,参见薛军《民法典编纂如何对待司法解释》,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48页以下。据笔者判断,只要我国《立法法》(参见第一百零四条)没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就享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权力。民法典编纂完毕之后,其也就会出台若干司法解释,其条文数量甚至会超过民法典本身。在此背景下,民法法源及其解释规则,可以考虑在司法解释中进一步完善。
从目前我国已经出现的数个重要的民法典总则建议稿来看,都对民法的渊源和法律解释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③龙卫球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以经实践确定的惯例作为补充。”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和惯例的问题,可以结合审判实际需要和有关实践发展情况进行合理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有关立法精神。”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法需要解释时,应结合法律文义、法律体系、立法意图和规范目的等因素予以解释,但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二款规定:“裁判者基于既有民法规定或体系的逻辑理解和价值推论,有充足理由认为民法应该规定而未及规定的,可采取类推适用、举重明轻、明示其一即反对其他、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等方法,以填补漏洞。”杨立新教授主持的第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依照本法以及依据本法制定的其他法律中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法律没有规定的,依照习惯;没有习惯的,依照法理。”第十七条规定:“法律解释应当兼顾法律文义、法律体系以及法律目的,在宪法确定的价值体系内进行。”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适用前条规定的解释方法进行解释。”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法律存在的漏洞,比照最相类似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类推解释。”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以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释。”同条第二款规定:“法律以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依照习惯。习惯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而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草案建议稿》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民事关系,本法和其他法律都有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习惯的,可以适用公认的法理。”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习惯,以不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为限。”这些建议稿的规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借鉴这些建议稿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未来通过司法解释实现法律解释规则的成文化时,其条文可以拟定为:
§1 《民法总则》第十条中所规定的“法律”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视为《民法总则》第十条所规定的“法律”。
§2 法官在解释《民法总则》第十条中的“法律”时,应当从文义出发,考虑立法者原意、法律的规范目的、法律体系、宪法的规则与原则、社会效果等因素。
如果法官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可以突破立法者原意。
§3 《民法总则》第十条中的“习惯”应当限于民事主体对其具有法的确信的习惯,即习惯法。
作为裁判依据的习惯法,不仅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且,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法官应当依据职权查明习惯法的存在,但可以要求当事人举证证明习惯法的存在。
§4 没有法律和习惯法时,法官应当以法理作为裁判依据。
法官以法理为裁判依据时,应当考虑法律的原则、比较法、判决、学说、指导性案例中的判决理由等,依据自己如作为立法者应提出的规则裁判。
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中的判决理由,但法官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不予参照的除外。
§5 法官裁判案件,应当参酌通说见解和实务惯例。违背通说见解和实务惯例时,法官应当进行充分的论证。
[1]六本佳平.日本法与日本社会[M].刘银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刘颖.民法中的国家政策——以《民法通则》第6条为中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6).
[3]任剑涛.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J].开放时代,2010,(7).
[4]李敏.民法上国家政策之反思——兼论《民法通则》第6条之存废[J].法律科学,2015,(3):96.
[5]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6]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8]郑玉波.法学绪论[M].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
[9]罗国强.论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J].兰州学刊,2010,(6).
[10]王新新.论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及我国对策[D].上海:华东政法学院,2006.
[11]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克劳斯-威尔海姆·卡纳里斯.基本权利与私法[J].曾韬,曹昱晨,译.比较法研究,2015,(1).
[12]张红.民事裁判中的宪法适用——从裁判法理、法释义学和法政策角度考证[J].比较法研究,2009,(4).
[13]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4]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5]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生活世界、价值体系与立法表达[J].清华法学,2014,(6).
[16]杨与龄.民法概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7]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8]Franz Bydlinski,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M].Wien/New York 1982, S.
[19]陆幸福.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法律效力之证成[J].法学,2014,(9).
[20]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J].中国法学,2015,(1).
[21]徐涤宇,等.现代中国民法的知识转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22]黄卉.论法学通说[J].北大法律评论,2011,(2).
[23]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4]王茵.不动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5]吕世伦,孙文凯.赫克的利益法学[J].求是学刊,2000年,(6):66.
[26]波顿海默.利益法学和自由法律运动[J].邹甸,译.中外法学,1984,(4):45.
[27]黑克.利益法学[J].付广宇,译.比较法研究,2006,(6):145-146.
[28]Wilburg,Die Elemente des Schadensrechts[M].Marburg 1941.
[29]Bydlinski,Privatautonomie und objektive Grundlagen des verpflichtenden Rechtsgesch?fts, Wien/New York 1967.
[30]山本敬三.民法中的动态系统论[A].解亘,译.民商法论丛(第23卷)[C].
[31]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2]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M].金振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3]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4]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35]向容.法律解释方法之适用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2.
[36]Canaris,Die Feststellung von Lücken im Gesetz,1964, S.19f.
[37]Heck,Gesetzesausleg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AcP112(1914),170f.
[38]Canaris,Die Feststellung von Lücken im Gesetz,1964,S.20.
[39]杨与龄.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0]Pawlowski,Methodenlehre für Juristen,3 Aufl.,Heidelberg 1999,S.221.
[41]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2]维滕贝格尔.德国视角下的基础研究与教义学[J].查云飞,张小丹,译.北航法律评论,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