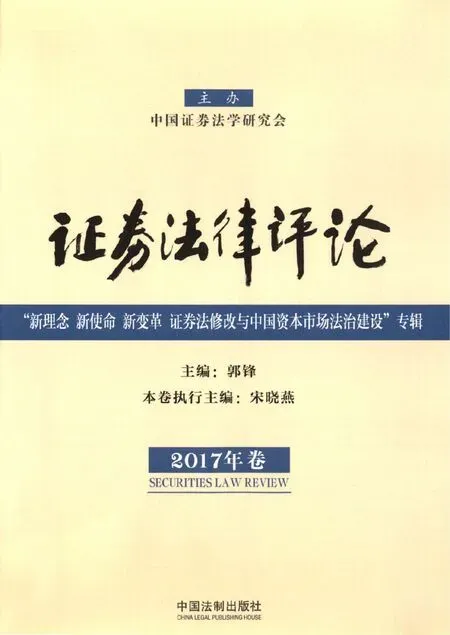我国证券市场“诱空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
2017-01-24樊健
樊 健
【证券欺诈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证券市场“诱空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
樊 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没有规定“诱空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损害赔偿,导致法院判断因果关系与认定和计算损失时发生错误适用。实践中,“诱空型”虚假陈述常见类型为持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大额持股信息和上市公司隐瞒或者推迟披露利好消息。在前者,持股人为适格被告;在后者,适格被告与《规定》相同。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持有并在实施日至揭示日之间净卖出股票的投资者由于该虚假陈述遭受损失,具有交易上因果关系,为适格原告。对于因系统性风险所造成的部分或者全部损失,被告无需赔偿。投资者的损失为除去系统性风险的基准价减去平均卖出价乘以净卖出的股份数。
“诱空型”虚假陈述 因果关系推定成立“净卖出法”
引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只规定了“诱多型”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而对“诱空型”虚假陈述没有做出规定。所谓“诱多型”虚假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者故意违背事实真相发布虚假的利多信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空信息不予公布或及时公布,使得投资者在股价处于相对高位时,进行‘投资’追涨的行为”。〔1〕李国光、贾纬:《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141页。相反,“诱空型”虚假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者发布虚假的利空信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好信息不予公布或者及时公布,使得投资者在股价向下运行或相对低位时卖出股票,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者被更正后股价又上涨而投资者遭受损失的行为。”〔2〕李国光、贾纬:《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实务中,法院认为“诱空型”虚假陈述“表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虚假的消极利空内容信息,或者隐瞒遗漏重大利多内容信息,诱使投资者在股价相对低位时卖出而遭受损失。”王艳与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57号。《规定》仅规定“诱多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是证券市场当时发生的虚假陈述均表现为诱多型虚假陈述;二是这两类虚假陈述对投资人心态和投资行为影响截然相反,因而与投资损失的因果关系确定不同,当时尚未找到同时在《规定》里设计两类因果关系条文的方法;三是当时《证券法》对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很原则,境外证券法也没有细致如此。”〔3〕贾纬:“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之完善”,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7期。
然而,事实上《规定》本身并不限制投资者基于“诱空型”虚假陈述而提出民事诉讼,并且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法院受理因“诱空型”虚假陈述而引起的民事诉讼。但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往往还是会以《规定》没有规定“诱空型”虚假陈述而认为投资者的索赔没有法律依据。例如,在黄其安与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上诉案中,〔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34号。被告主张:“鸿基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约束及调整的范畴。本案鸿基公司的行为隐瞒了实质性的利好消息未予公布,属诱空虚假陈述。《若干规定》仅对诱多的虚假陈述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作出了规定,而未对诱空的虚假陈述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如何承担责任作出规定,黄其安要求鸿基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法律依据不足。”〔5〕又例如,张淑煜诉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商初字第97号。本案中,被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损失赔偿仅适用于诱多型证券虚假陈述,并不适用于诱空型证券虚假陈述。本案所涉虚假陈述被披露或更正后当天及以后数日,案涉股票的价格并未出现急剧下挫或异常下跌,相反,却表现出超过大盘涨幅的上涨,甚至逆势上涨。因此,即便张淑煜真实地购买了案涉股票,其损失与南京医药公司的虚假陈述也不具有因果关系。”有学者也认为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诱空型”虚假陈述的情形下,投资者不能索赔,〔6〕参见叶承芳:“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19卷第4期。该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作为投资者因虚假陈述而提出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69条并没有区分“诱多型”或“诱空型”虚假陈述。因此,只要虚假陈述行为致使投资者产生损失,行为人即应承当损害赔偿责任。〔1〕本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剥夺“诱空型”虚假陈述受害人诉讼的权利,并无合法性。〔2〕朱锦清:《证券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由于《规定》对“诱空型”虚假陈述缺乏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诱空型”虚假陈述的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裁判标准,因此产生了一些问题:第一,没有准确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虚假陈述行为,错误地将“诱多型”虚假陈述的构成要件等适用到“诱空型”虚假陈述中。〔3〕例如,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与柳彩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46号。第二,对于“诱空型”虚假陈述与投资者交易之间因果关系判定含糊,〔4〕例如,北京高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诉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商重初字第3号。本案中,法院没有分析在何种情况下“诱空型”虚假陈述与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甚至出现误判的情况。〔5〕例如,王艳与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57号。本案中,法院认为“在实施日后揭示日前买入、又在该时段内卖出股票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虽然从买入时间上看,晚于应当披露的时间,但其损失亦由利好消息未能在其持股期间公布,系因虚假陈述行为人补救措施不及时所致,投资者亦没有享受到本应享有的信息红利而受到利益损害,故该部分投资者可以要求行为人赔偿”。但是,事实上,该类投资者并没有遭受损失。理由后文会做深入分析。第三,没有具体规定认定和计算损失的方法,致使可能获得赔偿的投资者没有获得赔偿或者使得不该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人承担了“无妄之责”。〔6〕例如,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与柳彩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46号。本案中,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没有按照规定披露其大额持股信息,实质上是“诱空型”虚假陈述。但是,法院仍旧以“诱多型”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来分析被告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总之,目前关于“诱空型”虚假陈述的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存在诸多问题,不仅不利于保护真正受到损失的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可能使某些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不应其承担的“无妄之责”。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实务中常见的两类“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目的在于提醒法院和诉讼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当出现此类情形时,应当注意,不能错误地套用《规定》关于“诱空型”虚假陈述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分析适格被告。第二部分,分析“诱空型”虚假陈述中的因果关系,包括交易上因果关系与损失上因果关系。第三部分,分析“诱空型”虚假陈述诉讼中损失认定和计算方法。最后,总结全文。
一、“诱空型”虚假陈述的常见类型与适格被告
(一)“诱空型”虚假陈述的常见类型
“诱空型”虚假陈述是行为人披露虚假的利空消息,或者隐瞒或者推迟披露真实的利多消息,使得股价处于低位状态。此时,投资者若卖出股票则可能遭受损失。在我国证券实务中,虚假陈述行为人隐瞒或者推迟披露真实的利多信息的情形最为常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持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大额持股信息;二是上市公司隐瞒或者推迟披露利好消息。〔1〕由于股价处于低位状态对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管而言并不有利(例如可能出现“门口的野蛮人”或者无法实现行使股票期权的条件等),因此即使出现该情形也仅仅是暂时的。相对而言,行为人披露虚假的利空消息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主要介绍前两种情况。
1.持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大额持股信息
我国《证券法》第56条〔2〕本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5%,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第13至15条规定了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3〕参见张子学:“完善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若干问题”,载《证券法苑》2011年第五卷。即当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统称为持股人)拥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披露相关信息。〔4〕《证券法》第57条规定了应当披露的信息,包括“(一)持股人的名称、住所;(二)持有的股票的名称、数额;(三)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收购办法》则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申言之,《收购办法》第16条条第1款规定,股份持有人不是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但未达到20%的,应当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办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股份持有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0%但未超过30%的,应当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收购办法》的规定,兹不赘述。此后,该持股人的持股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5%,也需要披露相关信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持股人减少持股数额在多数情况下会打压公司的股价,属于利空消息,所以持股人隐瞒或延迟披露减少持股数额的信息,属于“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可直接适用《规定》。因此,本文研究的是持股人的持股数达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5%或者之后每增加5%,持股人隐瞒或延迟披露该信息。这种情况在证券实务中较为常见,属于典型的“诱空型”虚假陈述。持股人之所以会隐瞒或延迟披露大额持股信息,是因为该信息将极大地增加其持有(购买)成本,甚至当持股数额达到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30%时,在没有获得豁免的条件下,必须向所有投资者发出要约收购,收购成本又将大幅度增加。〔1〕《证券法》第55条第1款,“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有法院也认为,“在证券市场,对投资者而言股份收购系利好消息,利好消息的披露一般会引发被收购证券价格的增长,从而亦增加收购成本,当收购人为降低其收购成本而隐瞒股份收购的利好消息时,收购人的隐瞒行为即为消极沉默的诱空型虚假陈述。”北京高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诉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4)济商重初字第3号。此外,其他竞买者可能也会购买该上市公司的股份,或是上市公司为了反收购进行股份回购,都会使得上市公司的股价上涨。总之,对于大额持股信息,“市场一旦得到收购的信息,目标股票价格必然猛涨,收购成本也就高了”。〔2〕朱锦清:《证券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因此,隐瞒或延迟披露大额持股信息,可以使得持股人在上市公司股价处于低位的时候买进股票,节省成本。但是,该信息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利好消息,由于持股人隐瞒或者推迟披露大额持股信息,对于受此欺诈而卖出股票的投资者而言,则遭受了损失。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京博控股”案中,“从国通管业(上市公司)与所在的沪市主板市场及所在行业板块交易指数涨跌比较来看。在虚假陈述揭露日2012年3月16日至基准日2012年12月15日,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下跌10%,国通管业所属的工业指数收盘价下跌14%。同期内,国通管业的收盘价由9.63元上涨到10.13元,涨幅5%。在大盘指数和行业板块指数均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国通管业未跌却升,大幅上涨。”〔3〕北京高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诉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4)济商重初字第3号。因此在揭示日之前卖出国通管道的投资者即遭受近每股5%的损失。
2.上市公司隐瞒或者推迟披露利好消息
在证券实务中,还有一种常见的“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是上市公司有意隐瞒或者迟延披露利好消息,此类“诱空型”虚假陈述类型比较多样。首先,最常见的是在公司进行合并或者重大资产重组的时候。按照《证券法》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关于合并或者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1〕《管理办法》第30条第3项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上市公司及时披露该信息的义务,该条规定“第三十一条上市公司应当在最先发生的以下任一时点,及时履行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义务:(一)董事会或者监事会就该重大事件形成决议时;(二)有关各方就该重大事件签署意向书或者协议时;(三)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知悉该重大事件发生并报告时。在前款规定的时点之前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现状、可能影响事件进展的风险因素:(一)该重大事件难以保密;(二)该重大事件已经泄露或者市场出现传闻;(三)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常交易情况。”但是,考虑到过早披露信息可能会使公司股价产生异常波动或者引发其他主体参与到合并或者重大资产重组中来,使结果产生不确定性。当然,也有可能是上市公司的相关人员通过隐瞒或者迟延信息披露,进行内幕交易,获得非法收益。〔2〕实务中,公司并购和资产重组事件,是内幕交易的重灾区。有学者对31起内幕交易案件进行了分析,发现“在被查处的内幕交易案件中,有接近一半(14)件是利用并购重组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这充分映证了并购重组领域是内幕交易的‘重灾区’,如果考虑到与并购重组有关的持股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如重大债务豁免),则这一比重可能更高。”蔡奕: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法学实证分析——来自31起内幕交易成案的统计分析,载《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7月号。总之,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面对媒体等询问,上市公司会否认合并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存在,从而误导投资者,致使其在公司处于低位的时候卖出股票,因而导遭受损失。例如,在美国著名的Basic案中,被告公司虽然与其他公司在进行合并谈判,但是面对媒体的询问,该公司连续出了三个公告来否认与其他公司的合并谈判。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Basic公司构成“诱空型”虚假陈述。〔3〕Basic Inc.v.Levinson,455 U.S.224(1955).关于本案的简要介绍,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重印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页。其次,在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时候,为了降低回购成本,上市公司也有可能隐瞒或者迟延披露利好消息。〔4〕该行为可能构成操纵市场,参见朱庆:“论股份回购与操纵市场的关联及其规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再次,还有其他一些上市公司隐瞒或者迟延披露利好信息的非典型“诱空型”虚假陈述,例如有意隐瞒重要合同〔5〕例如,王艳与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57号。或者股权代持〔6〕例如,黄其安与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34号。等。本文认为这两种情况是非典型的理由在于上市公司(包括其董事、经理等)隐瞒或者迟延披露这些信息并不能给其带来多少好处,但是一旦该虚假陈述事实被发现,则上市公司和相关责任人可能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则民事诉讼,得不偿失。最后,是不太常见的“诱空型”虚假陈述,即上市公司未遵循相关会计法等规定,造成财务数据错误。〔1〕例如,章文磊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535号。法院认为,“2009年3月3日,华闻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等媒体上发布的《关于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公司2007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暨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中载明,调整后的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少数股东权益、利润总额、所得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少数股东损益等均比原来公布的增加,而负债总额是减少的,这些纠错后的客观调整,增加了华闻公司资产利润总额,这对华闻公司而言,是正面消息,对投资者而言,是利好消息。”又例如,方向诉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105号。法院认为“上市公司的业绩是投资者选择股票时重要考量因素,上市公司的业绩越好,越能吸引投资者投资。在被告被处罚的错误中,少计营业外收入236万元,多计2005年度财务费用374万元,对于被告来说是少计了企业利润,只会导致年报中披露的业绩比实际业绩差,不会成为吸引投资者购买被告公司股票的元素,因而对投资者不会产生误导作用。”当然,证券市场纷繁复杂,不排除其他上市公司隐瞒或者迟延披露利好消息的情形。
综上所述,对于由前两种情况所引发的诉讼,法院与诉讼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同样应当十分警惕,不能错误地套用《规定》关于“诱多型”虚假陈述的规定。
(二)“诱空型”虚假陈述中的适格被告
在上市公司自身披露虚假的利空消息、隐瞒或者推迟披露利好消息的虚假陈述行为中,适格被告与“诱多型”虚假陈述并无本质不同,可以根据《规定》第7条第1至6项来认定适格的被告。〔2〕本条第一至六项规定为,“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一)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三)证券承销商;(四)证券上市推荐人;(五)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六)上述(二)、(三)、(四)项所涉单位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但是,如果是持股人隐瞒或者迟延披露其大额持股信息,认定适格被告在实务中可能会存在争议。当然,违反规定的持股人自身构成虚假陈述,自无疑问。〔3〕在前述北京高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诉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京博公司在2007年7月24日始至2009年4月9日期间,大宗持有国通管业股票应当披露而未予真实披露、虚假披露的事实,业经证监会(201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六条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证券市场中的信息公开制度,隐瞒真实情况,构成不正当披露,故京博公司系具有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属于虚假陈述行为人,依据《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七)项的规定,京博公司因其虚假陈述而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如果持股人是法人,则其董事、高管等信息披露责任人也应当承担责任,这与《证券法》第65条与《规定》第21条相同,〔4〕《规定》第21条,“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前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无须赘述。争议问题在于,发行该股票的上市公司是否应当民事责任。《收购办法》第13条规定,当持股人持股数达到法定要求时,持股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实务中,通常是由上市公司披露持股人的大额持股信息。此时,由于持股人的原因致使上市公司隐瞒或者推迟了大额持股披露信息,该上市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本文认为,由于上市公司本身不是大额持股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对于此类信息上市公司不具有确保其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披露的义务。〔1〕《证券法》第63条,“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上市公司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持股人的通知而披露有关信息,本身无法确定该大额持股信息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以及及时地披露,因此上市公司本身不需要承担责任。实务中,法院亦持有同样观点。例如,在吴雪明诉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224号。法院认为,“就实际控制人的虚假陈述行为,〔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2013)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被告存在以下违法行为:2005年6月2日,被告与案外人合计持有金陵公司(即上市公司)股权比例7.59%(其中被告直接持股0.43%),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被告应当予以披露。2005年6月3日,上海市国资委将所持金陵公司股权转至被告名下后,被告与案外人合计持有金陵公司股权比例为24.95%(其中被告直接持股17.71%),被告仍未对合计持股情况进行披露。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已有所规定,依照该规定,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操纵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应由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实际控制人违反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进行虚假陈述的,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条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故依照上述规定,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且上述规定之所以将实际控制人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规定为由上市公司先行赔偿,系基于在此种情形下,上市公司为形式上直接侵害投资者权益的侵权人,故应由上市公司先行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而本案中被告作为实际控制人直接就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相关信息进行虚假陈述,在形式上已成为直接侵害投资者权益的侵权人,其情节较前述情形更为严重,据此亦应认定被告应就原告的损失直接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当然,如果上市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持股人隐瞒或者迟延披露信息的,但是上市公司却不予披露或者及时披露,则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综上,就适格被告而言,在持股人违反规定隐瞒或者迟延披露其大额持股信息的情况下,一般而言,该持股人而非发行该股份的上市公司是适格被告。在其他类型的“诱空型”虚假陈述中,与《规定》所规定的适格被告相同。
二、“诱空型”虚假陈述中的因果关系
“诱空型”虚假陈述的损失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该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卖出股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卖出股票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前者被称为交易上因果关系,而后者被称为损失上因果关系。〔1〕刘新民:《中国证券法精要: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56页;彭冰:《中国证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255页;盛焕炜、朱川: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因果关系论,载《法学》2003年第6期;马其家:“美国证券法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3期;石一峰:“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中的交易因果关系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对于“诱多型”虚假陈述中的因果关系,《规定》并没有明确区分交易上因果关系与损失上因果关系,但是从条文本身和体系解释而论,《规定》事实上区分了这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2〕《规定》第15条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对于“诱多型”虚假陈述,《规定》直接推定交易上因果关系和损失上因果关系成立,投资者无需举证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被告想要推翻该推定,则需要自行举证证明。〔3〕《规定》第19条。“《规定》参照了欺诈市场理论的思路,以‘推定信赖’的原则,确定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与否。只要《规定》设定的有关基础事实得到证明,就可以推定该因果关系存在。”〔4〕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重印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页。理由在于“由于证券市场主要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所主机撮合成交的方式进行,所有不可能将虚假陈述行为人(侵权人)、行为受益人以及受害人之间的联系特定化,使得遭受损失的投资人难以就其损失与侵权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举证证明。”〔5〕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重印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本文认为出于同样的司法政策考虑与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对于“诱空型”虚假陈述中的因果关系,也同样应当推定成立,但是被告可以举证推翻该推定。
(一)“诱空型”虚假陈述中的交易上因果关系
1.交易上因果关系成立的推定
在一个有效率的证券市场里面,不论是行为人披露一个虚假的利空消息还是隐瞒或者迟延披露一个利好消息,产生的结果都是股价低于其真实价格,从而使得投资者作出错误的投资决定,即卖出股票。“追涨杀跌”本来就是投资者的一般交易模式,因此应当推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交易决策之间存在交易上因果关系。〔1〕此乃前述Basic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采用的“欺诈市场理论”(fraud-on-the-market theory)的要义所在。该理论认为,“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欺诈的是整个证券市场;投资人因相信证券市场真实、证券价格公正合理而进行投资,因此其无须证明自己信赖了虚假陈述行为才作出的投资;只要证明其所投资证券的价格受到虚假陈述行为影响而不公正,即可认定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此,在北京高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诉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商重初字第3号。中,法院认为“在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中,利好消息即便未披露,也不会诱使投资者作出积极的投资决定。京博公司虽然存在未及时披露信息的违法行为,但其行为并非采取浮夸、误导的方式公布信息,从而引诱投资人作出积极投资的行为,而是延迟披露重大信息,故京博公司被证监会处罚的行为即为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由此,高石公司的投资交易并不是由京博公司未及时披露信息的行为所决定的,其投资决定并未受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与京博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其中,积极的投资决定应当是指买进股票。然而,按照法院的反面解释,如果原告高石公司采取了消极的投资决定即卖出股票,似乎可以理解为该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交易上因果关系。
在王艳与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上诉案中,〔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57号。一审法院对于投资者损失与“诱空型”虚假陈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地讨论,逻辑严密。本部分结合法院的分析,展开评述。一旦确认因果关系,则此时的投资者是适格原告,可以提起诉讼。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并没有区分交易上因果关系与损失上因果关系,统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1)法院认为,“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前即持有、〔4〕对于“诱空型”虚假陈述而言,虚假陈述实施日是行为人披露虚假利空消息之日,或者行为人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披露信息。就后者而言,虚假陈述实施日应当是相关规定要求披露信息截止日的次日。但是,有法院认为法定截止日当天为虚假陈述实施日。例如,刘清江诉鲜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236号。法院认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当在2012年5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履行公告、报告等信息披露义务,并通知上市公司。鉴于被告的不正当披露行为性质上属于消极虚假陈述,故该虚假陈述实施日的确定取决于信息披露的法定期限,即法定期限的最后一个日期应当为消极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故2012年5月23日应当为被告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并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前卖出股票的投资者。其投资行为显然没有受到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即使有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本文赞同,投资者卖出股票的行为发生于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之前,显然没有受到该虚假陈述的影响。
(2)法院认为,“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前即持有、并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后、揭示日(揭露日或更正日,下同)〔1〕对于揭露日和更正日,“诱多型”虚假陈述与“诱空型”虚假陈述并无区别。根据《规定》第20条,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披露证券市场信息的媒体上,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并按规定履行停牌手续之日。”前卖出股票而发生亏损的投资者。其没有享受到本应享有的信息红利而受到利益损害,故该部分投资者的前述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有因果关系,可以要求行为人赔偿”,本文赞同。“诱空型”虚假陈述的后果是使股价处于低位,此时投资者卖出股票而遭受损失。因为,如果虚假陈述行为人披露真实的信息,则投资者可能不会卖出股票或者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股票。由此,投资者卖出股票的交易行为与“诱空型”虚假陈述之间存在交易上因果关系。有司法界人士也认为“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诱空型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已经买入并持有该证券;2.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卖出该证券产生亏损。”〔2〕贾纬:“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之完善”,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7期。
(3)法院认为,“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前即持有、并在虚假陈述行为揭示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股票的投资者。因利好消息披露的时间点(虽然是迟延披露)处于其持股期间,其已经可以享受到消息红利,即使发生亏损,也失去了可以索赔的前提。”本文赞同,由于真实信息已经被揭示出来,因此不论是投资者卖出或者继续持有,其卖出或者持有股票的行为是基于真实信息基础之上的投资判断,与虚假陈述没有关系。若投资者在市场没有充分吸收该信息的情况下卖出股票,理论上虽然也可能遭受损失,但是此时投资者还有持有不卖出的权利,因此该损失与虚假陈述无关。
(4)法院认为,“在实施日后揭示日前买入、又在该时段内卖出股票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虽然从买入时间上看,晚于应当披露的时间,但其损失亦由利好消息未能在其持股期间公布,系因虚假陈述行为人补救措施不及时所致,投资者亦没有享受到本应享有的信息红利而受到利益损害,故该部分投资者可以要求行为人赔偿。”对此,本文不赞同。本文人认为此类投资者并没有遭受损失。理由在于在此情形下,投资者的买入价也没有受到“诱空型”虚假陈述的影响,其是在股价处于低位的时候买入。因此,虽然投资者卖出的时候没有“诱空型”虚假陈述的影响在低位卖出,但是由于其是“低价买进,低价卖出”,因此投资者并没有损失,即使发生损失也并非由“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所引发。事实上,由于利好的真实信息会在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前多多少少地泄露到市场上,因此投资者的卖出价中也多多少少地包含了真实的利好信息,因此相比于买入价,投资者甚至还有赚头。〔1〕贾纬:“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之完善”,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7期。贾纬法官认为当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投资者已如数买入了证券,人民法院应认定诱空型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总之,由于投资者在此阶段购以低价购入了股票,其在卖出阶段的损失,通过低价购入股票得到补偿,因此投资者没有损失。如果只算卖出损失,不算买进收益,对于虚假陈述行为人而言,承担过多的损害赔偿责任。〔2〕法院并没有分析,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持有股票,在实施日至揭示日之间同时有买进和卖出股票行为,如何认定因果关系。本文在第三部分会分析,在此情况下,只有投资者净卖出股份时,才可认定该卖出的股份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投资者可以要求赔偿。
(5)法院认为,“股票是在实施日后揭示日前买入、在揭示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或至基准日后或继续持有,因其已经享受到信息红利,即使发生亏损,也与该虚假陈述行为本身没有因果关系。”本文同赞,“诱空型”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后,投资者卖出或者持有的投资决定是基于真实信息之上,与虚假陈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事实上,对于此类投资者而言,其以低价买入并以高价卖出或者持有,不仅没有亏损,反而有赚头。若投资者在市场没有充分吸收该信息的情况下卖出股票,理论上虽然也可能遭受损失,但是此时投资者还有持有不卖出的权利,因此该损失与虚假陈述无关。
(6)法院认为,“在揭示日后买入股票,因该虚假陈述行为已经为公众所知晓,投资者应该了解该揭示行为的警示和提醒作用,意识到自己下一步投资行为可能存在的机遇和风险,在此情况下其仍然作出投资决定,即使发生亏损,亦属于自身判断和决策的失误,与虚假陈述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无权就所发生的损失主张赔偿。”本文赞同,此时投资者的购买行为显然与虚假陈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分析,只有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前即持有、并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后、揭示日前净卖出股票的投资者,其卖出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成立交易上因果关系。
2.交易上因果关系成立的推翻
被告可以通过以下的抗辩,来推翻交易上因果关系成立的推定:第一,投资者明知有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还是卖出股票。显然,该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第二,投资者意图内幕交易或者操纵市场而卖出股票,“从事这类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恶意行为者,推定其明知虚假陈述的存在,或其无论是否明知虚假陈述存在都会投资,因此即使因虚假陈述遭受损失,也不能主张赔偿。”〔3〕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重印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第三,被告可以证明投资者并非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已经持有,并在实施日至揭示日之间净卖出股票。
(二)“诱空型”虚假陈述中的损失上因果关系
1.损失上因果关系成立的推定
对于损失上因果关系而言,法律应当推定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已经持有,并在实施日至揭示日之间净卖出股票的投资者,其所遭受的损失与卖出股票行为之间存在损失上因果关系。如果投资者在实施日至揭示日之间卖出股票,但是在此期间其又买进了股票,即“补仓”,并且买入的股票数大于卖出的股票数,则即使投资者发生损失,也与其卖出行为无关。因为,前面已经提到此时投资者是“低价买进,低价卖出”,两者相抵,只有在卖出大于买进即净卖出的情形下,投资者才有损失。
2.损失上因果关系成立推定的推翻
被告可以举证其他因素导致了投资者的全部或者部分损失,从而推翻或者部分推翻损失上因果关系的成立,减免自己的责任。司法实践中被告普遍采用的方法是系统性风险的抗辩。《规定》没有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定义。有法院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对证券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风险因素,其特征在于系统风险因共同因素所引发,对证券市场所有的股票价格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为个别企业或行业所不能控制,投资人亦无法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1〕“陈丽华等23名投资人诉大庆联谊公司、申银证券公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1期。也有法院采用大盘综合指数与行业指数等来综合认定系统性风险的。例如,在苏万福诉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中,〔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苏民二终字第0112号。法院认为“系统风险既是以证券市场的综合指数、流通股总市值等因素综合体现出来的,则在确定系统风险所致的损失时,亦不能采用单一标准,而应在综合分析能够具体体现系统风险的‘上证综合指数’、‘沪市全部A股流通股总市值’、‘纵横国际所在的机械类行业板块指数’、‘机械类行业A股流通股总市值’这四类数据变动情况的基础上加以把握。”就“诱空型”虚假陈述中的系统性风险而言,被告应当举证在揭示日至基准日之间存在使得股价上涨的系统性风险。测定系统性风险最佳的方法应该是行业指数,在缺乏行业指数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大盘指数。原告也可以举证在此期间存在使得股价下跌的系统性风险。〔3〕《规定》没有赋予原告可以举证系统性风险存在的权利,但是从平等对待的角度和证券市场实际情况而言,原告应当享有举证系统性风险的权利。
三、“诱空型”虚假陈述中的损失认定与计算方法
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投资者的真实损失是该股票实际价值与其在低价位卖出股票价格之间的差额再乘以投资者净卖出的股票数量。理论上,有两种方法可以认定并计算出投资者的损失,一种是事前方法(ex ante),一种是事后方法(ex post),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案,司法实践中采用后者。
(一)损失认定与计算的事前方法
损失计算与认定的事前方法是指投资者的损失在其卖出股票是即已发生,该股票的真实价值与实际卖出价之间的差额即为投资者每股的损失。〔1〕Merritt B.Fox,After Dura:Causation in Fraud-on-the-Market Actions,31 J.Corp.L.529(2006).我国司法实务也有持相同观点的判决出现,但是为数极少。例如,周斌诉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51号。本案中,就“诱多型”虚假陈述中的投资者损失,法院认为应当是投资者在购买该股票时多支付的价款。“原告系于被告的虚假陈述被揭露数年之前买入系争股票,此时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已经发生,由于在证券市场中系争股票的价格与被告的重大信息存在密切关系,故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在原告购买股票时已经影响了该股票的价格,并导致此时该股票的价格处于不公正的状态,而原告在被告的误导之下购入系争股票,必然会导致其投资因不公正的价格因数而遭受损失,故应认定原告自买入系争股票是即已产生了投资损失。”对于“诱空型”虚假陈述中投资者的真正损失,也应当是投资者在股价处于低位卖出时其所少获得的卖出价款。具体而言,在“诱空型”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前(当然,诉讼发生在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后),通过“事件分析法”〔2〕“事件分析法是一种证研究方法,最早运用于金融领域,借助金融市场数据分析某一特定事件对该公司价值的影响。由于事件分析法具有研究理论严谨、逻辑清晰、计算过程简单等优点,已被学者运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来研究特定事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王玲、朱占红:“事件分析法的研究创新及其应用进展”,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1期。计算出除去其他因数的情况下(例如大盘或者行业风险),该股票的真实价值,然后再用真实价值减去实际卖出价格,即为虚假陈述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也就是投资者的每股损失。此外,还需要按照“净卖出法”计算出此间卖出的股票总数。“净卖出法”是指如果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示日之间,从事了多次买进和卖出股票的交易,那么两者相抵消,如卖出的股票多于买入的股票,则该卖出股票即为投资者可获赔的数量。因为,投资者在实施日至揭示日之间是“低价买进,低价卖出”,所以两者应当相抵消。当然还要考虑除权的影响。〔3〕《规则》第35条规定,“已经除权的证券,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时,证券价格和证券数量应当复权计算。”最终,净卖出的股票数量乘以虚假陈述对股价的影响,即为投资者损失。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损失认定与计算方法,因为该方法最为直接和准确。但是,如何算出该损失难度比较高。如果行为人积极地披露一个虚假的利空消息,致使公司估计下跌,通过“事件分析法”大体可以测算出该虚假信息对公司股价的影响。但是,如果行为消极地隐瞒或者迟延披露一个利好消息,因为该虚假陈述行为实施之后并没有对公司股价产生影响,所以很难计算出除去其他因数情况下该虚假陈述对公司股价的影响。〔1〕Frank Torchio,Proper Event Study Analysis in Securities Litigation,35 J.Corp.L.159,at 163 ~164(2009).
(二)损失认定与计算的事后方法
在理论上,事前方法认定和计算损失最为直接和准确,但是真正实施起来难度颇大,因此比较实务的做法是通过事后方法来认定和计算损失。事后方法是指“诱空型”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后除去系统性风险的每股基准价减去卖出价乘以投资者净卖出的股票数量得出投资者损失。〔2〕John C.Coffee,Jr.,Causation by Presumption?Why the Supreme Court Should Reject Phantom Lossesand Reverse Broudo,60 Bus.Law 533(2005).简单来说,计算除去系统性风险的基准价的方法应当是,基准价/(1+系统性风险)。如果系统性风险是上涨,则系统性风险为正值;反之为负值。这样的计算除去系统性风险的基准价对原被告双方都较为客观。其中,基准价是指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后至基准日之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被揭示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实务中最常用的基准日是指从揭示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除去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3〕《规定》第33条。其他计算基准日的方法可以参阅本条。对于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示日之间,投资者的卖出数量及价格,首先按照“净卖出法”算出可获赔股票数量,然后再通过“先进先出”加权平均算术法计算出平均卖出价。假设,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拥有10000股ABC公司股票,每股价格为13元。行为人隐瞒一个利好的消息没有及时公布,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起至该消息被揭示之前进行了如下操作:以13.5元/股的价格卖出5000股;以14元/股的价格买进3000股;以14.7元/股的价格买进1000股;以15.1元/股的价格卖出2000股。该虚假消息被揭示之后,公司股价逐渐上升,至基准日股价上升至17元/股,此时该股东持有该公司7000股股票。按照“净卖出法”算出可获赔的股份数为3000(10000-7000)股。之后,根据“先进先出法”认定该卖出的3000股是投资者在第一次卖出时的股份,则每股价格为13.5元。〔1〕将本案例稍微调整。假设,第一次以13.5元/股卖出2000股,之后以14元/股的价格买进3000股;以14.7元/股的价格买进1000股;以15.1元/股的价格卖出5000股。此时,按照“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计算每股平均卖出价的方法是(2000×13.5+1000×15.1)/3000=14.03元/股。经计算,投资者损失为(17-13.5)×3000=10500元。当然,这只是本文所建议的一种计算损失的方法,还有其他计算方法可供参考。〔2〕参见王丹:“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计算方法论”,载《法学》2003年第6期。
事后方法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行为人在虚假信息被揭示之前先披露一个真实的利空消息,使得公司股价下跌,之后再行更正虚假信息,这时股价即使是上涨,也许会低于卖出价,从而投资则无法获得赔偿。〔3〕赖英照:《股市游戏规则:最新证券交易法解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页。因此,事前方法虽然准确但是复杂,而事后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准确性不够。但是,从便于审理的角度出发,事后方法更优一些。“在计算虚假陈述所致损失时,因价格偏离的事实业已不可逆转的发生,现有任何一种事后计算方法都无法完全还原当时的市场环境和交易状况,进而精确计算损失。确定采用何种方法计算损失,只能是建立在相对准确和公正的基础上,同时还需考虑计算的简便易行,以利于解决纠纷。”〔4〕胡某与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五(商)终字第16号。
结论
《规定》仅对“诱多型”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作了具体规定。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法院在审理“诱空型”虚假陈述虚假陈述时,往往会错误地套用“诱多型”虚假陈述的规定,在因果关系判断和损失计算等方面发生错误,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使得本能够获得赔偿的投资者失去了索赔机会,同时也使得本来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行为人承担了“无妄之责”。
本文介绍了我国常见的两种“诱空型”虚假陈述,包括持股人隐瞒或者迟延披露其大额持股信息和上市公司隐瞒或者迟延披露利好信息。在持股人隐瞒或者迟延披露其大额持股信息的情形下,适格被告为持股人自身,上市公司无需承担责任,除非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持股人存在该情况,但是不予纠正。在其他情形下,“诱空型”虚假陈述中的适格被告与“诱多型”虚假陈述中的适格被告并无不同。就因果关系中的交易上因果关系而言,应当推定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持有,并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示日之间净卖出的投资者,其卖出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其也为合格的原告。被告可以举证投资者明知虚假陈述而投资或者进行内幕交易或操作市场等违法行为而推翻该推定。就因果关系中的损失上因果关系而言,应当推定投资者的损失与净卖出股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可以举证全部或部分损失由系统性风险造成,来减免责任。本文建议采用事后方法来认定和计算损失。首先,计算出除去系统性风险的基准价作为该股票的真实价值;其次,依据“净卖出法”计算出可索赔的股份数量;再次,依据“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计算出平均卖出价;最后,再用基准价减去平均卖出价乘以可索赔数量,算出投资者最终的损失。相对而言,这种比较简便明确,便于法院采用。
**樊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