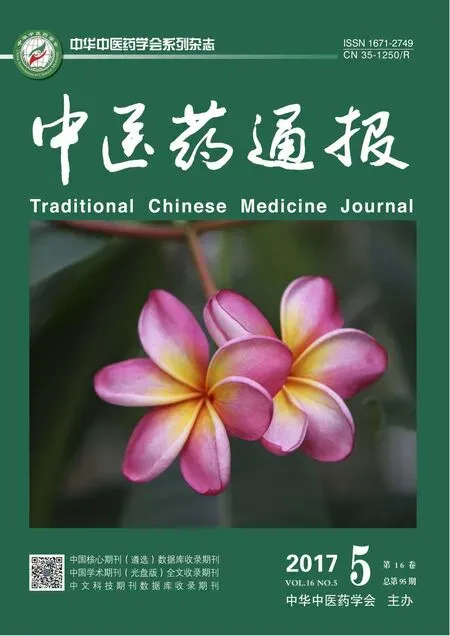从误诊误治案例再谈“平脉辨证”
2017-01-14蒋宁峙指导陈利群
● 李 航 蒋宁峙 指导:陈利群
从误诊误治案例再谈“平脉辨证”
● 李 航 蒋宁峙 指导:陈利群
误诊误治 医案 平脉辨证
笔者弱冠起侍诊于国家级名老中医杨少山教授,学习其采用辨证论治方法治疗各种常见病和疑难杂病[1-4]。杨师临证时常教导:跟师学习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死记其常用药方或药对,而是学习如何辨证,方可举一反三,从而灵活运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中医常用法则,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而平脉辨证法作为临床上最基本的辨证方法,首先确定主症(可以是一个症状,也可以是两个密切相关的症状,或者是一组症状);其次确定脉象;后将两者结合起来,经过辨析,再参考兼症和舌象后方可确定证型。在平脉辨证中,脉诊是否正确是个关键。脉诊有误,辨证必然错误。由于脉诊的学习较为困难和复杂,现平脉辨证法已非临床中医师最常用的辨证方法。现笔者举隅临床十余年来误诊误治案例4则,以期再谈“平脉辨证法”在临床辨证中的重要性。
1 咳嗽“肾阳虚兼太阳中风、营卫不和、寒热错杂”证误辨为“肺阴不足”和单纯“太阳表虚”证案
王某,女,19岁,因“反复咳嗽少痰伴口干咽燥3个月”于2001年立夏就诊于笔者。现病史:近3个月来反复咳嗽少痰,夜间为甚,伴口干咽燥,无咽痒、鼻流清涕,无发热,多方求医均辨证为“肺阴不足”型咳嗽,予“沙参麦冬汤”合“止嗽散”加减服用月余仍不效。就诊时症见:形体肥胖,咳嗽,口干咽燥而不欲饮,伴盗汗、恶风、恶寒,但时有潮热,舌质淡红,苔薄,脉浮缓而无力。笔者根据《伤寒论》原文而辨证为“太阳表虚证”,故拟“桂枝汤”原方2剂,后因前症反加重,患者家属拟另寻名医,笔者经其家属同意后一同就诊。该医家先反复诊脉5分钟左右;同时望其形体肥胖,审其舌苔见舌质淡红,苔薄黄;并闻及患者语声轻微;另询得患者有腰背冷、口苦。医家采用“平脉辨证法”为主,将脉象和上述异常主症和兼症记录于册,并将处方一同交由助手录于方中,内容如下:诊得右寸脉浮紧,右尺脉虚浮,舌质淡,苔薄黄,主诉咳嗽3个月,伴口干不欲饮、腰冷、口苦以及盗汗、恶风、潮热。辨证为素体肾阳虚,复感风邪而引起太阳表虚证,且寒热错杂(寒重于热)。予“桂枝加附子汤”合“阳旦汤(黄芩仅用6g)”服用7剂。复诊时诉服用1剂后咳嗽、口干咽燥即大减,当晚即无明显盗汗,目前上述症状均除,该医家再次诊脉发现:右寸脉已不浮紧,然右尺脉沉而无力,右关脉细缓,左关脉虚弦,舌苔已转薄不黄。予肾气丸加生黄芪30g、党参15g、当归10g、炒白芍10g,后随证加减。笔者每周电话询问患者家属,1个月后医家建议可改为仲景牌“金匮肾气丸”合“归脾丸”巩固疗效。后随访至今,未再复发。
按本例因存在“反复咳嗽少痰,夜间为甚,伴口干咽燥”等症状,故多位名医均辨证为“肺阴不足”型,然为何连续服用3个月滋养肺阴药而无效?而笔者接诊时根据患者存在“咳嗽伴恶风、盗汗、潮热、脉浮”等主症脉象,故辨证为“太阳表虚证”,然为何服用“桂枝汤”原方2剂后反加重?后医再次细审脉症时发现,患者右寸脉浮紧,结合主症(恶风、盗汗、潮热),辨证为“太阳表虚证”当属无疑;同时发现右尺脉虚浮、舌质淡,结合主诉腰冷,则提示素体肾阳不足;舌质淡、苔薄黄和腰冷、口苦则提示:寒热错杂证。综上,该例肾阳虚证为本,太阳表虚证和寒热错杂证为标,故予“桂枝加附子汤合阳旦汤”标本同治,以治标为先。获效后标证渐除,而见肾阳虚证明显,同时根据右关脉细缓、左关脉虚弦,辨其同时存在“气血不足”证,故予滋肾助阳为主,佐益气健脾养血法以治本。
笔者重温《伤寒论》第21条:“太阳病发汗,遂漏汗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对照原文,本证是因过汗误治伤阳而致阳虚之病因,但结合多位现代经方大家经验,凡因“阳虚兼太阳表虚、营卫不和”所致的各种疾病均可选用本方(笔者在2010年12月曾采用该方治疗1例因“阳虚兼太阳表虚证”所致的顽固性带下病,5剂后获愈)。笔者认为,本例误诊误治的原因主要是医者诊治疾病时欠缺较好“脉诊”技术,致本应根据“平脉辨证”法而不难做出正确辨证的病例迁延不愈。因此,笔者之后拜名师、读经典,且在临床上更重视“脉诊”,并细心体会其奥妙。近5年来笔者采用“平脉辨证”法为主,且以“切、望、闻、问”诊的顺序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2 耳鸣“脾气阴两虚兼肝血不足,夹湿夹瘀”证误辨为“肾阴不足”案
方某,女性,52岁,因“反复耳鸣1年”于2017年5月2日就诊。现病史:近1年来反复耳鸣,伴腰膝酸软、大便隔日一行,质干,夜间口干咽燥,前医辨证为:“肾阴不足型”耳鸣,予“六味地黄丸”之意加减治疗2个月,诸症均未减。就诊笔者时,主诉症状同前,诊得右关脉缓而无力,左关脉虚弦,舌质干红,苔薄腻,以根部为甚,边有瘀点。辨证为:“脾气阴两虚兼肝血不足,夹湿夹瘀型”耳鸣。予“参苓白术散”加减。药用:太子参40g,生黄芪25g,炒白术10g,茯苓12g,生甘草3g,陈皮6g,生薏苡仁30g,淮山药20g,白扁豆15g,芡实12g,当归10g,葛根10g,丹参20g,阳春砂6g(后下),川朴花9g,苏梗10g。7剂。
二诊:1周后复诊,诉耳鸣较前稍减,腰膝酸软仍显,然夜间口干咽燥大减,且大便日行一次,已较前明显通畅,舌质已不干,余同前,再守前方续进1周。
三诊:主诉耳鸣、腰膝酸软大减,夜间口干咽燥已除,大便已正常,且详诊脉象所见:右关脉缓而较前有力,左关脉已不虚弦,舌质已不红,苔薄根仍微腻,边有瘀点。后嘱其续守前方加减至今,暂未见明显症状反复。
按中医传统理论认为:肾主耳,耳为肾之窍,为肾之官。《灵枢·脉度》也提及“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能闻五音矣”。提示古代中医对耳鸣耳聋多从肾虚论治。加之本例患者除耳鸣外,伴腰膝酸软、夜间口干咽燥、便干、舌红等典型肾阴虚症状,故前医嘱其服用“六味地黄丸”。然为何疗效甚微?笔者根据该例患者右关脉缓而无力,舌质干红,结合主症之一的“夜间口干咽燥”,辨证为“脾气阴两虚”;同时因该例未见左、右尺脉异常脉象,故不应辨证为“肾虚证”;左关脉虚弦,则提示:肝血不足;舌苔薄腻,根部为甚,提示脾虚湿滞;舌苔边有瘀点,提示兼夹瘀血。根据上述表现和症状,应辨证为:脾气阴两虚兼肝血不足,夹湿夹瘀型”耳鸣。且根据脉象提示当以虚证为主,故当予“健脾益气养阴”“兼补肝血”为主,佐以“化湿活血”。治疗后不仅便干、夜间口干咽燥渐减,且耳鸣、腰膝酸软症状亦大减,舌、脉亦均有改善。此乃脾运得健,水谷精微化生有力,即可滋肾,正如孙思邈所云:“补肾不如补脾。”笔者在未习“平脉辨证”法前,临床辨证主要凭症状、舌苔,每每见患者“耳鸣、腰酸、舌红”时也多辨证为肾阴不足;结合本例误诊,再次凸显“平脉辨证”作为中医最常用辨证方法的临床重要性。
3 咳嗽“脾肾气阴两虚兼肝血不足”证误辨为“肺脾气阴两虚,兼肺热不清”证案
杨某,女,59岁,因“反复咳嗽、咯痰10年,加重1个月”于2017年3月就诊我院。西医诊断为:支气管炎。现病史:咳嗽有痰,咯痰不畅,色白,以后半夜为甚,伴口干欲饮,大便时有稀溏,舌质干红,中有裂纹,脉细。前医辨证为“肺脾气阴两虚兼肺热不清”之本虚标实证,故予“黄芪、党参”补益肺脾之气;“天冬、麦冬、知母、玉竹、玄参”养阴清热润肺;“石膏、黄芩”清泻肺热,且随症加减服用3个月。然因近1个月上述症状反有加重,且伴口干、盗汗而赴笔者处就诊。诊得右脉缓而稍显无力,左关脉小弦,左尺脉虚浮,舌质干红,苔中有裂纹。结合舌、脉、症,辨为咳嗽“脾肾气阴两虚兼肝血不足”证,予“六味地黄丸”合黄芪、太子参、当归、生白芍为主,佐以“沙参麦冬汤”加减养阴润肺。上方服用7剂后,患者诉后半夜咳嗽症状消失,口干、盗汗已减,舌、脉同前。后予前方加减续服2个月,诊得右脉缓而较前有力,左关脉已不弦,左尺脉已不虚浮,然仍稍细,舌质已不干红,苔中裂纹仍存,嘱其改“六味地黄丸”合“黄芪生脉饮”以巩固疗效。
按本例存在“反复咳嗽、咯痰,以后半夜为甚,伴口干、脉细、舌质红、苔中有裂纹”,故前医辨证为“肺阴虚兼肺热证”;然时有大便稀溏,故前医辨证为“脾气虚证”。综上,前医辨为“肺脾气阴两虚兼肺热证”,予“补益肺脾气阴”为主,佐以“清热化痰”。辨证看似无误,然为何无效?笔者详审脉症,诊得右关脉缓而稍显无力,伴便溏,则提示脾气虚;左尺脉虚浮则提示肾阴亏虚;左关脉小弦,提示肝血不足。综上,笔者辨为“脾肾气阴两虚兼阴血不足型咳嗽”,故拟六味地黄丸滋养肾阴,太子参、生黄芪补益脾气,当归、生白芍养肝血为主,佐以沙参麦冬汤以涵“金水相生”之意。笔者认为,本案误诊的关键在于前医诊脉时未查及左尺脉虚浮,再次提示“平脉辨证”的重要性。
4 泄泻“少阴阴虚兼水热互结”证误辨为“脾虚、湿热下注”证案
王某,女,因“反复腹泻1年”于2006年赴笔者处就诊。前医辨证为:脾虚型腹泻,经用“补中益气汤”数剂无效。刻诊所见:形瘦,每日腹泻5~6次,伴腹痛,泻后痛渐止,夜间口干咽燥,且喜冷饮,时有咳嗽,下肢轻度浮肿,六部脉均沉,舌质干红,苔薄中黄。根据“平脉辨证法”为主,因存在“腹泻、口干喜冷饮和脉沉、舌红苔薄黄”等主症和舌脉,故辨证为“湿热下注(热重于湿型)”型泄泻,予“葛根芩连汤”合“香连丸”原方治疗1周,因无效而改赴“浙江省名中医馆”某名医处就诊。1个月后电话询问患者近况,患者诉服用某名医“药方”2天后,腹泻即止,口干咽燥、腹痛即大减,后连续巩固12剂而停服。药方:猪苓10g,茯苓10g,泽泻10g,滑石10g(包煎),阿胶(烊化)10g。该方服用14剂后,笔者再次诊脉已未及沉脉,且舌苔薄黄已除,舌质不干,仅微红。“以方测证”,该病例当辨为“少阴阴虚兼水热互结”型泄泻。
按笔者诊治患者时出现六部脉沉,提示里证,并据其舌质干红、苔薄中黄结合腹泻、口干喜冷饮等表现,故辨证为“湿热下注(热重于湿型)”证。然予清热为主佐以利湿法而无效。而后医采用“猪苓汤”治愈。《伤寒论》第319条云:“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结合本例存在“下利、咳、渴”症状,笔者思之良久,认为本例误诊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抓住主症,而后医则从“下利、咳、渴”等主症的辨认中抓住了相应的方剂猪苓汤,故疗效非凡。正如刘渡舟教授晚年在多次学术会议中提及的“抓主症是辨证的最高水平”。本例再次提示“抓主症和诊脉”同样重要。
[1]李 航.杨少山治疗老年病经验[J].中医杂志,2007,48(4):301-302.
[2]李 航,杨少山.浅谈阴虚血瘀的机理及其治法[J].中医杂志,2011,52(23):2062-2064.
[3]李 航,杨少山.杨少山运用膏方调治老年病经验浅谈[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22(11):780-782.
[4]李 航.杨少山运用养阴法治疗举隅[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5,29(3):47-48.
浙江省杭州市东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3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