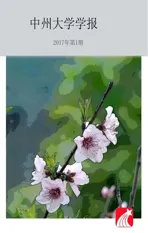普希金的《现代人》杂志研究
2017-01-12耿海英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普希金的《现代人》杂志研究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普希金于1836年创办《现代人》并主编4期。杂志内容不仅具有多样性,同时,其混合内容的协调性和目的性使《现代人》具有了特别的意味——在严苛的书刊检查下,普希金以巧妙的内容编排,曲折地关注当时的社会问题: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民族和农民问题,殖民与平等问题等。这些连续的相辅相成的主题证明了办刊者缜密的思考,体现了在当时出版物普遍商业化和大众化的文化生态中,其坚持严肃文学的办刊立场。普希金的《现代人》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反应时事的敏捷性,题材的多样性,都被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所继承。
普希金;《现代人》杂志;研究
《现代人》是普希金于1836年在圣彼得堡创办的一份文学杂志,从1836年至1866年前后历时30年;其间三易其手,经历了普希金(1836)、普列特尼约夫(1838—1846)、涅克拉索夫(1847—1866)三任主编,发表过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丘特切夫、果戈理、伊·屠格涅夫、赫尔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格利戈罗维奇、鲍特金、安年科夫、谢德林等众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且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论坛,在19世纪中期成为俄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鉴于篇幅,该文仅研究普希金的《现代人》。
普希金不仅是俄国大诗人,还是热忱的新闻人、出版人和编辑。在他独立出版《现代人》杂志之前,就曾参与俄国《北方之花》《文学报》的工作,为其后来主编《现代人》杂志奠定了基础。
一、普希金与《北方之花》和《文学报》
1824年12月下旬,安·安·杰利维格和奥·米·索莫夫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不定期集刊《北方之花》(1825—1832,普希金主编和出版1832年号丛刊),刊物分为《诗歌》和《散文》两个栏目,其作者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圈子,有安·杰利维格,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维亚泽姆斯基,德·达什克夫,伊·科兹洛夫,巴拉津斯基,费·格林卡,彼·普列特尼约夫,阿·伊斯梅洛夫,尼·奥斯托洛波夫,玛·达尔戈梅日斯卡娅,瓦·图曼斯基,费·图曼斯基,瓦·格里戈利耶夫,米·扎戈尔斯基,普·奥博多夫斯基,阿·沃耶伊科夫等。从这个圈子中,我们可窥视到那个“黄金时代”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圈子里产生了创办一份新报纸的想法,期望文学能审视时代的社会问题,涉足政论和社会批评。这个倡议人就是普希金。这个想法立即获得了圈子其他成员的支持。因此,《文学报》的诞生完全是普希金促成的。
《文学报》1830年1月1日开始发行,五天一期,主编和出版人依然是《北方之花》的杰利维格,外加他的助手——文学家、新闻人索莫夫和编辑部秘书弗·夏斯内,三人承担编辑工作。秘书除了技术性工作,还从事翻译和转载科技文章。新闻检查机关只批准了新报纸的文学性质,政治板块则没有通过。普希金为报纸奔走争取完全独立的权利,请求放宽限制,允许开辟其他板块,但他所有的努力都落空。尽管政治栏目不被允许,但报纸出版伊始就表露了自己的立场和情绪,从第一期起就带上了自己的政治倾向,例如对刚刚过去的土耳其战争(1828—1829)的回忆不是在《万岁—爱国主义》的文中,而是在人类的残酷和不义的观点中流露出来,这与官方的立场及给沙皇和俄罗斯军队唱赞歌的官方出版物相悖。这样,它以其发表的作品区别于趋于保守和主张“纯艺术(无涉政治)”的刊物,如布尔加林的报纸《北方蜜蜂》(1825—1865),米·彼·波戈金的杂志《莫斯科新闻》(1827—1830)和尼·阿·波列伏伊的杂志《莫斯科电讯》(1825—1834)。
关于报纸的目的,编辑部声明:“该报的目的在于,给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读者介绍最新的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1]5报纸在强调自己的文学性质的同时,也强调自己的主要对象是针对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读者;同时声明:“报纸将不给谩骂式批评以版面;对于批评家们,将不以个人关系,而是本着有利于某种科学或艺术,满怀感激地接纳进《文学报》……而一切合乎报纸目的的文章都将不胜感激地予以采用。”[1]5关于供稿作者,编辑部在自己的公告中说道:“六年来那些在《北方之花》上发表自己作品的作者都会经常为《文学报》撰稿(当然,两位杂志出版人,忙于自己的刊物,将不成为该报的撰稿人)。”[1]5这两位先生指的是布尔加林和格列奇,在《北方之花》所有撰稿人中唯有他们两位拥有自己的刊物。这样,《文学报》立即就将自己置于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和格列奇的《祖国之子》(1812—1852)的对立面了。
《文学报》主编杰利维格编了两期之后,就因事暂时离开彼得堡而把报纸交给了普希金两个月,因而普希金成为接下来的十期的实际主编,他和索莫夫一起出版了第3-12期。《文学报》辟有散文、诗歌、国内外图书、学术资讯、杂俎五个栏目。诗歌板块允许普希金畅通无阻地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报纸第一期就刊登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八章片段。诗歌栏目还发表过主编杰利维格本人的诗歌以及维亚泽姆斯基、巴拉津斯基、费·尼·格林卡、阿·瓦·科利佐夫、杰尼斯·达维多夫及其他诗人的作品。此外,报纸还匿名发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阿·阿·别斯图热夫和维·卡·曲谢尔贝克尔的作品。散文部分给读者提供了各类作家的文章。这里发表了俄国著名的散文作品和戏剧作品,例如阿·阿·沙霍夫斯科伊的《斯摩尔陵斯克人在1611年》,果戈理最早的作品也发表在这里,以及司各特、霍夫曼、蒂克、雨果等的译本。散文作家中还有安·波戈列利斯基,安·波多林斯基,尼·斯坦凯维奇,阿·霍米亚科夫等。批评部分聚集了俄国当时最卓越的作者和思想家,他们毫不留情地解剖和评析当时那些最主要的作品,发表了巴·阿·卡捷宁、维亚泽姆斯基、普希金的评论、随笔、观察。作者中还有索莫夫、瓦·柳比奇-罗曼诺夫斯基(历史学家、文学家、果戈理的中学同学),甚至有流放中的维·卡·曲谢尔贝克尔(其《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思考》)等。普希金也积极投入图书栏目的工作。1830年他在《文学报》上发表20多篇文章、评论、论争性杂文,还有十多篇完成但未及发表。在学术资讯栏目经常发表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短文。杂俎栏目提供各种文学的和接近文学的文章,包括发表过亚当·密支凯维奇的书信选,回忆艺术家、回忆拿破仑和若泽芬娜的文章。
作为反对派的活动,在当时沙皇专制制度下当然不可能持续太久。报纸在第一期就刊登了冯维辛的翻译作品,他的创作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打压;也发表了十二月党人匿名的作品。1830年8月,杰利维格因《文学报》上出现过法国革命歌曲的词句而受到申斥,10月在第61期上引用了卡·杰拉韦温献给1830年七月革命牺牲者纪念碑揭幕的四行诗。而与此同时,《北方蜜蜂》的出版人布尔加林的创作不止一次地遭到《文学报》有根据的攻击和嘲笑,因而他恼怒《文学报》,指责其政治不正确,因而《文学报》引起第三厅将军阿·赫·本肯多夫将军的注意,结果《文学报》的整个工作都被置于第三厅的监控之下。作为回应,普希金在《文学报》上发表了讽刺诗和小品文,揭露布尔加林就如同为本肯多夫的机关服务的代办和特务。《北方蜜蜂》对普希金展开公开整治,两个刊物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于是1830年10月所引用的卡·杰拉韦温的四行诗就招致了《文学报》不可避免的厄运,杰利维格被免去报纸编审职务,报纸的出版被迫停止。本肯多夫愤怒地以流放西伯利亚威胁报纸的主要作者和编辑杰利维格、普希金和维亚泽姆斯基。杰利维格据理力争,最终《文学报》重获出版,但是主编被更换为索莫夫。而被此事震动的杰利维格很快就病倒了,并于1831年1月14日病逝,享年33岁。报纸又持续了不久,到1831年6月30日停刊。
《文学报》总共出版了一年半,对于一份报纸来讲实在是太短暂了,而且在同时代人中并没有广泛的受众和太高的知名度,仅限于社会很小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但是,它对于俄罗斯文学和艺术性政论的发展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和重要阶段。
1831年1月杰利维格病逝后,他坚持多年的《北方之花》也在一月刚出版不久①。为了纪念诗人,他的朋友们决定再出一集“1832年号”。普希金主持并编辑了该期,发表了杰利维格生前未被发表的作品及朋友们悼念诗人的作品。
二、普希金的《现代人》
普希金早就希望获得许可,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它应该是一份具有独特的组织结构和主题的新型杂志,以区别于当时刊物中已经非常明显的“商业倾向”。这就是后来的《现代人》。然而这个愿望的实现并不容易。早在1824年时,他就给维亚泽姆斯基写信说:“你所说的关于杂志的事情,早就在我脑子里萦绕不去。”[2]96但那时从首都被驱逐出来的普希金②和处于秘密监视中的维亚泽姆斯基,没有可能出版一份杂志,所以当杰利维格着手办《北方之花》时,他竭尽全力支持,慷慨地提供自己的许多诗歌作品③,这些作品很快就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经典作品。但是集刊,在普希金看来无法代替杂志或报纸。1826年,普希金结束流放返回莫斯科后不久,他就和莫斯科欲意出版《莫斯科新闻》的文学界朋友商谈,希望全权管理这份刊物。1826年11月,他给维亚泽姆斯基写道:“也许,不是波戈金,而是我,将成为新杂志的主人。”[2]304-305但是,莫斯科圈子是极其坚硬难啃的“桃核”,这使得普希金慢慢失去了对《莫斯科新闻》的兴趣。正如我们前文指出的那样,他后来积极参与了《文学报》的事业。《文学报》停刊后,他就又开始忙于出版自己的报纸。1832年他获得了许可,但是阴差阳错,现实条件并没有让他顺利实施:1832年初,伊·瓦·基里耶夫斯基的杂志《欧洲人》第二期被禁④,原本在上面应该刊登普希金的作者名单。1832—1833年,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一再向政府递交出版刊物的申请方案,都无果而终。同时,报刊业越来越成为并不太干净的盈利途径,布尔加林和格列奇步步高升,他们的报纸《北方蜜蜂》灵敏地感应和捕捉政府在文学领域哪怕最小的政策变动。“百科全书式”的杂志《读者文库》1834年开始出版,其主编奥·伊·先科夫斯基事业的惊人成就证明,这位机智的、有时肆无忌惮的主编能准确无误地猜中社会需求。后来的“大型”杂志如《祖国纪事》等都借鉴了他的经验。但是《读者文库》的作用不仅仅是正面影响,它是最早预示了“大众”文化的杂志之一。普希金圈子的作家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正是《读者文库》的这一副作用。普希金希望打破布尔加林、格列奇、先科夫斯基的“报刊三寡头”的垄断及商业倾向,坚持不懈地争取办自己的刊物。1835年12月31日,他给本肯多夫写信请求允许来年出版“四卷纯文学(诸如中篇小说,诗歌之类)、历史、学术,以及批评分析国内外文学作品的文集,就像英语季刊《观察》一样”。[3]69尼古拉一世准许了“上述定期刊物”,1836年1月普希金获得了官方许可。终于,最大的外部障碍排除了,然而,另一些外部阻力接踵而至。
普希金要出版杂志的消息在出版界引起了不小骚动。对《现代人》的围攻甚至在杂志还没有到达读者手里时就开始了,手段五花八门。《读者文库》的出版人斯米尔金和主编先科夫斯基先是劝说普希金以一万五千卢布的价格将《现代人》出售,普希金当然断然拒绝。随后,先科夫斯基就展开了另一种攻势,他在1836年第一期《读者文库》上刊登文章,对德国诗人克·马· 维兰德⑤的一本诗歌集的俄译本进行讥笑式评论。这部作品是一部题材相当古老的诗体小说,早在1807年就由在皇村供职的叶·彼·柳岑科译出,当时普希金曾建议斯米尔金出版未果,而后自己出版,标明“普希金出版”,没有显示译者,因而此时遭到先科夫斯基的诽谤,说普希金自掏腰包一千卢布,买下了署名权,将译本据为己有。所以他在评论中引用柳岑科最平庸的诗,不无恶意和讽刺地说这是普希金的诗:“这是他的诗,令人吃惊的诗!”[4]5《读者文库》的攻击还不止于此。在《现代人》第一期面世前,先科夫斯基从侧面了解到将要在此发表《论1834和1835年新闻报刊的动向》一文,其中论及他的杂志活动。没有等到《现代人》出版,先科夫斯基就在四月号《读者文库》(3月27日通过审查)上发表杂文谈论普希金的杂志,说它出于对《读者文库》读者量的嫉妒,这将是一本谩骂式丛刊,必将灭亡于肮脏的争论。先科夫斯基甚至不惜对普希金直接威胁:“请自重!不谨慎的天才!”[4]5事情的实质是,先科夫斯基向政府和新闻检查机关提示,怀疑普希金的政治善意问题——说他是尖刻的讽刺诗及小品文作品的作者,暗示这些作品鞭挞了尼古拉一世的近臣国民教育部部长谢·谢·乌瓦罗夫。
因担心《现代人》的命运,普希金转而请求《北方蜜蜂》的支持。他利用《读者文库》与《北方蜜蜂》出版人个人性格的磨擦,采取措施,润滑对他的攻击。1836年4月17日《北方蜜蜂》上出现了未署名文章《关于“现代人”说几句》;《莫斯科观察家》也在1836年第四期上发表文章《应该怎样进行批评》出面为普希金辩护。就是在如此激烈的气氛中,《现代人》第一期面世了。
在应付外部阻力的同时,普希金同样面临内部困难——如何选择撰稿人。普希金考虑,自己圈子里的作家应该成为《现代人》的撰稿人。正如他后来在第三期《现代人》中写的,在主要方面“都将是《文学报》的继续”。[5]331但是,距离《文学报》停办已经五年过去了,这些年发生了许多变化,杰利维格和索莫夫都去世了,卡捷宁不再从事文学活动,普希金圈子里被认为最具批评天才的基里耶夫斯基被禁止发表作品。尽管如此,在1837年出版的四期《现代人》中,被普希金采用稿件的作者20多人,但投稿者相当多。没有被采用的有叶·罗森男爵和彼·沙利科夫公爵的诗,米·博格金的历史文章;罗森的关于写木偶戏演员的文章的建议没有下文;有一些被普希金约稿的文学家没有实现他的要求;流放地诗人曲谢尔贝克尔寄往《现代人》的文章手稿《诗与散文》被截获而没能到编辑手里;普希金也曾请米·谢普金和巴·纳晓金为杂志写回忆文章。在撰稿人中有些知名人士,如彼·科兹洛夫斯基——外交官、自然科普工作者;杰·达维多夫——1812卫国战争的英雄、诗人;文坛新人——果戈理,娜·杜罗娃,科利佐夫,丘特切夫,这些作家和诗人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注意,他认为他们具有无可怀疑的天才。
编辑稿件时,普希金关心的是它们是否符合杂志的精神和风格。他从娜·杜罗娃的札记中删去了针对亚历山大一世冗长的颂词,在给作者的信中普希金建议风格尽量平实些,并且建议作者放弃最初的题目《娘子军札记》,改为更简单朴实的《娜·安·杜罗娃札记》。普希金对果戈理的影响更是文坛佳话。众所周知,在1837年3月28日果戈理从罗马给普列特尼约夫的信中这样写道:“没有他的建议我就无从开始,没有他出现在我面前,我简直难以想象,我会一行字也写不出来。他所说的、所批评的、所嘲笑的、所永恒赞美的,就是占据我全部身心的东西,给我力量的东西。”[6]186而《娜·安·杜罗娃札记》、果戈理的《鼻子》等都附带着普希金善意的评论出现在杂志中。可以看出,在使稿件严格符合杂志精神的同时,普希金对文学新人给予悉心的呵护和指导。
普希金对《现代人》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在出版《现代人》期间,他写有超过百封信件,几乎一半与杂志有关。他生平最后一封信是给儿童作家阿·伊希莫娃的,在决斗那天普希金请她为杂志翻译巴里·康沃尔⑥的诗歌并给出了建议。在决斗前夕,他催促彼·科兹洛夫斯基完成答应过的关于蒸汽机理论的文章;据书商伊·季·利先科夫所见,普希金曾去书店挑选为杂志的“新书”专题所需的书籍;他还认真读完杂志文章的校样,并与书刊检查机关进行了交谈。
关于对《现代人》的书刊检查,亚·瓦·尼基坚科在自己的日记(1836年1月20日)中作了这样的记录:“审查官委派阿·阿·克勒洛夫为新杂志的检查员,他是我同行中最胆小的,因而是最严格的。”[7]过了三个月,尼基坚科在4月14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检查员经常挤压普希金,普希金对他多有抱怨,要求给自己另派一个来协助第一个,结果给他派来了加耶夫斯基。普希金懊悔不迭,但已经晚了。加耶夫斯基早被关禁闭吓怕了,他曾被拘留8天。所以现在甚至类似国王去世这样的消息是否允许刊发都值得怀疑了。”[7]作为主编的普希金的处境艰难,还因为教育部长谢·谢·乌瓦罗夫和彼得堡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米·亚·科尔萨科夫对他也都有敌意,因为诗人曾针对他们分别写过讽刺短诗和小品文。有一批准备用于《现代人》的作品完全被禁止发表:普希金的文章《亚历山大·拉吉舍夫》,果戈理的《彼得堡和莫斯科》,卡拉姆辛的《古今俄罗斯札记》,丘特切夫的《两个恶魔》。达维多夫的文章《德累斯顿战役》《论游击战》遭到了删减;在《德累斯顿战役》一文中达维多夫讲述了卫国战争的最后一战,几个将军希望无论如何获得战功,不惜以血战赌注,并预先准备好了胜利简报。阿·屠格涅夫⑦的文章《俄国年鉴·巴黎》出现在第一期《现代人》中,是经过了主编坚持不懈的斡旋的结果;果戈理的《鼻子》中的一些揭露性片段并不为读者所知。米·彼·波戈金的文章《莫斯科漫步》、丘特切夫的诗歌《自然,不是你所想的……》被删节发表。普希金的作品也备受折磨。他的《阿尔兹鲁姆旅行》由沙皇亲阅并删除了一系列关于政府对高加索政策的批评意见;《我的主人公谱系》《彼得一世的盛宴》《统帅》等作品最终能够面世,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检查机关的审理、反复进行交涉和通信等环节后才得以实现的;《上尉的女儿》则不得不给出解释:姑娘米罗诺娃究竟存在不存在,她实际上究竟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见面没有。而卡济-吉列伊·苏尔丹的文章《阿日图加伊的长度》已经刊发出来后,又收到了本肯多夫的来信,指责编辑破坏了最高守则里禁止军人没有得到上级裁定不得刊发自己作品的规定。作为编辑的普希金的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的,许多隐情并不为外人知晓。
根据杂志的备案和出版许可,《现代人》表面看来与其他刊物没有什么区别。封面上表明“现代人,文学杂志”,目录分为两个栏目《诗歌》和《散文》,但是内容被普希金巧妙地编排,具有了文学—社会杂志的特点,其中文学艺术类散文、诗歌与政论、文学批评夹杂在一起,许多文章以事件日期开头,《散文》栏目中的“新书”专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杂志所刊发的内容不仅具有多样性,同时,其混合内容的协调性和目的性使《现代人》具有了特别的意味。
第一期刊发的文章《论1834和1835年新闻报刊的动向》由果戈理执笔,但发表时没有署名。果戈理指出了大部分当代期刊没有什么鲜明色彩,他称《北方蜜蜂》“在文学意义上没有任何确定的调子”,“它是一只编筐,想装什么就装什么”[8]203;而《读者文库》的主编先科夫斯基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确定的信念和感情,他“今天喜欢的,明天就成了他嘲笑的对象”[8]198。果戈理嘲笑他的“轻率”,“因为他从来不关心自己说了什么,在下一篇文章中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之前所写的东西了”[8]199。果戈理还不无揶揄地指出在俄罗斯闻所未闻的现象,就是《读者文库》主编相当勇敢地公开宣布,他把几乎所有刊发的文章都作了修改和重编,“任何一条新闻都不是照原样发表的”,经过他们的“照顾”,“文章便大有起色”[8]202。果戈理的文章公允地评价了当时的各主要报刊,还指出了刊物中的“商业倾向”。不过果戈理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商业倾向”,“文学应该成为商业现象,因为读者的数量有了增加,阅读的需求也有了提高”,应该“从作品内在价值的角度”判断作者和出版物的作用,“而不是去计算他们的利润”[8]213。关于文学的“商业倾向”这一问题,普希金也不止一次涉及。他在去世前不久给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巴兰特的信(1836年12月16日)中谈到《1828年4月22日法规》,这一法规为俄国作者的权利打下了基础,他讲道:“文学在我们这里成为工业的一个重要分支,仅仅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在此之前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优雅的贵族的事情。”[3]401在欢迎文学界的新秩序——建立法规、保障作者的权利——的同时,普希金也指责那些把文学变成了“跳蚤市场”的杂志人和出版商。
果戈理的这篇批评矛头明确且犀利的文章被其他出版人看作是《现代人》杂志的纲领,并把它算在普希金头上。《现代人》面世前已经引发相关人的围攻,发表后更是招致各相关方的论战。为了《现代人》能生存下去,普希金不得不在第三期杂志上发表《致出版者的一封信》,假托署名А.Б.并注明信来自特维尔市,且在第二期“编者的话”里就已经预先说明,该信因时间仓促无法及时刊登。特维尔市的这位居民惊奇于《现代人》宣布自己的目的是与《读者文库》进行斗争。显然,普希金无法在《现代人》这份三个月一期的杂志中进行有效的争论,他希望息事宁人。但是他也没有完全拒绝论争,他坚持自己刊物的另一个目的,正像后来别林斯基所阐明的:“普希金创办自己的刊物并不是为追逐《读者文库》那样的荣誉(很可怀疑的荣誉!),而是为了俄罗斯哪怕有一份刊物,在上面那些天才、知识、价值、独立于商业要求的文学见解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9]在来自特维尔的信中,普希金认为《读者文库》出版得及时有序,也承认《北方蜜蜂》付费广告的实际效用,他说:“拥有15000订户的英文报纸,仅用刊登广告的收入就足以抵偿发行的费用。”[5]326-327这位特维尔居民认为《论新闻报刊的动向》一文的不足在于,作者“在谈《望远镜》时没有提及别林斯基,他正显露头角,大有希望”。[5]327在给来自特维尔的信所作注释中普希金声明:“《论新闻报刊的动向》一文发表在我的刊物中,但不能以此就认为文章中所表达的充满年轻人活力和直率的见解与我本人的意见完全吻合。无论如何该文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纲领。”[5]329而同在第三期上的普希金的“编者的话”实际上成为了对署名А.Б.来信的实质性评论和注解,其中讲道:“《现代人》的出版人没有发表任何自己杂志的纲领,因为他认为‘文学杂志’——已经说明了一切。一些杂志人认为有必要为新杂志撰写纲领,有人宣称《现代人》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斯米尔金先生出版的《读者文库》搞糟;而在《北方蜜蜂》中则说《现代人》将是已去世的杰利维克公爵出版的《文学报》的继续。在此《现代人》出版人不得不声明,他没有这份荣耀,与这些杂志人先生素无任何往来,他们往自己身上揽活儿,要为《现代人》撰写纲领;他从没有委托他们此事。但是,在拒绝与文学家不相称的和《读者文库》不公正地强加于他的目的同时,他完全承认《北方蜜蜂》上的说法是正确的:《现代人》就其批评精神,就其撰稿人的名单和分工,及对事物的见解的表达方式和应有的评判,都将是《文学报》的继续。”[5]330-331普希金办杂志的目的,一如过去的《文学报》,在于捍卫真正的艺术价值,在于传播科学和文化成就,在于确立社会生活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从他在《现代人》上刊发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他选用的作品所关注的问题,就可窥视一斑。
《现代人》问世时正值俄罗斯悄无声息地纪念十二月党人事件十周年。普希金绝无可能公开谈论十二月党人,但是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同胞想起那些被流放的人,他们中有许多是他的朋友。第一期就出现了《彼得一世的盛宴》,其中写的是沙皇与自己的臣民和解。该作品写于1835年末,其实是希望尼古拉一世在其继位十年之际宽恕十二月党人,但是期望落空,十二月党人处境依旧。在普希金的诗歌中,彼得一世是作为呼吁宽恕、和解的榜样而发声。同期发表的《阿尔兹鲁姆旅行》,普希金重又提起一些阴谋家,当然只是用开首字母或**代替真名,但作者在军人中指出他们,其真实意图相当明显。在第三期的“新书”专题中,刊登了一则没有署名的对意大利作家西里沃·佩利科的著作《论人的责任》的俄译本书评,也出自普希金之手,它引起了读者对这位意大利诗人命运的关注——他因被控与烧炭党有联系在狱中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生活,最后被奥地利皇帝赦免。西里沃·佩利科的生活道路引起人们联想起十二月党人的命运。在第四期出现了《上尉的女儿》,作品最后一个场景发生在皇家花园:玛莎·米罗诺娃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谈话,请求宽恕格利涅夫。小说注明写作日期为1836年10月19日。这些与皇村回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表达了作者对青年时期朋友的怀念,其中就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曲谢尔贝克尔。这让我们想起普希金在创作诗歌《纪念碑》时,认为自己对人民的功绩之一是“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
1836年,卫国战争25周年前夕,1812年主题成为重要话题。《北方蜜蜂》《读者文库》刊登显要人物的回忆和文章,他们将所有战功归于沙皇。《现代人》从另一立场走近这一主题。分别刊于第一期和第三期的1812年的真正英雄娜杰日达·杜罗娃、杰尼斯·达维多夫的作品,讲述了游击队员的机智,士兵们的勇敢,人民对祖国的爱。普希金注意到天才的统帅库图佐夫、巴克莱·德·托利⑨的功绩。《现代人》把卫国战争视为俄罗斯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
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族问题,它在普希金的杂志中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在俄国期刊中尚属首次。在第一期中,“半开化的高加索的儿子”切尔克斯人卡济·吉列伊在特写《阿日图加伊的长度》中,讲述了本民族对教育的向往以及这条道路上的障碍。普希金的写实作品《阿尔兹鲁姆旅行》中,隐含着政府殖民政策的谎言性。他写道:“切尔克斯人恨我们,我们把他们从辽阔的牧场赶走,他们的山村被毁坏,整个部落被消灭。他们越来越潜进深山,从那里实施自己的攻击。”[8]25在第二期中这个问题以新的材料展开。在一篇民族学文章《沃佳克人和切列米斯人的神话》中,阿·叶米切夫写道:“使人不得安宁的客人强烈地逼迫那些长久居住在这里的人,要么毁坏他们的住所,要么让他们搬到新地居住……”“仿佛弗拉基米尔的新时代成千上百的人被赶到河里接受洗礼。1834年炸毁了最后一块孤独地躺在荒野里的巨石——他们多神教崇拜的对象。”[10]181,187在这里普希金看到了俄罗斯人对边区族群文化与生存的毁灭性破坏。
在第三期普希金以英文署名“一位观察者”发表了政论文章《约翰·滕那》。该文写的是1830年出版的美国人约翰·滕那的回忆录——他9岁时被印第安人绑架,在他们中间生活了30年。在此期间他忘记了母语和自己的英文名字,完全养成了印第安人的传统和习性、世界观和信仰。他返回后,在美国博物学家和研究者爱德文·詹姆斯博士的帮助下,写就了《关于被绑架和受苦难的故事——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间三十年》。普希金的文章大部分是转述和片段翻译约翰·滕那的回忆录,这里他关注的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1836年普希金阅读了托克维尔的论著《论美国的民主》,在它的影响下,普希金撰写了文章《约翰·滕那》。19世纪30年代,欧洲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之一就是民主制度,与此相关,欧洲尤其对美国发生了兴趣。欧洲不无嫉妒地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每一步,对其时而报以赞赏,时而报以怀疑。结果,不仅新历史活动家可以成为“神话”(如拿破仑),年轻的国家也可以成为神话。因此,1835年在巴黎出版的托克维尔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化生活的重要事件,它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并迅速成为描写异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典范。普希金最早是从阿·屠格涅夫寄给《现代人》第一期(通过审查日期是1836年3月31日)的文章《俄国年鉴·巴黎》⑩中得知此书的,文中写道:“昨晚是在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度过的。塔列兰称此书是我们时代最智慧、最值得一读的书,而他本人了解美国,他本人就是贵族,就像托克维尔一样。”[8]273阿·屠格涅夫希望引起俄国读者对此书的兴趣,同时借法国外交官塔列兰的话安慰书刊检查员。可以推断,普希金应该是在1836年春天读了此书,又立即在《约翰·滕那》一文中提到托克维尔(《现代人》第三期标明的出版日期是1836年9月)。看来,诗人了解托克维尔的书与写《约翰·滕那》一文,几乎是在同时,在他的意识中,法国思想家的名字与这位半开化的“白人”印第安人有了有机的联系。
诗人本人很少翻译散文,而他在文章中却详细转述甚至大量翻译滕那的回忆录,以让读者了解美国的总体情况,了解印第安人的处境,了解美国文明的特点,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了解仅限于小说中,因而应当了解一些他们现实的情况。普希金在文中指出:“夏多布里昂和库柏两人呈现给我们的印第安人带着诗性的一面,是用他们自己的想象之色彩涂抹了真相。而华盛顿·欧文说:‘小说中呈现出来的野蛮,如此像现实中的野蛮’。”[5]206-207看得出来,在半开化的作者朴实的讲述中,普希金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重要的佐证:“叙述朴实而平静,它们最终将在世人面前证明美国在19世纪扩张自己的统治和基督教文明时所使用的手段。”[5]207在文中进行转述以及对滕那的话进行诠释时,普希金对美国“文明”表达了负面的评价:“印第安人所遭遇的苦难和贫穷远远超乎人们所能达到的想象。”[5]223诗人同时阅读的滕那和托克维尔的书中有什么东西同时回响着,相互补充着,从不同角度照亮现实。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印第安部落的现状和可能的未来》一章中,所呈现的画面和表达的思想,在滕那朴实的讲述中找到了独特的支持。托克维尔指出:“自从欧洲人在印第安人居住地区附近定居以后,飞禽走兽都吓得逃进森林而不再回来……”[12]407-408“原来在那里过的还算丰衣足食的印第安人,现在处于难以维持生计的境地……赶走他们的猎物,其后果等于我们农民的耕地变得贫瘠不毛一样”,“他们在那里只有饿死和受苦”,于是,“终于决心离开,跟踪野兽逃退的路线,让野兽指引他们选定新的家园”。“随着这种被迫迁徙而来的可怕苦难,是不堪设想。当印第安人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时,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衰败不堪;而在他们新选定的落脚地区,又早已住有只会对新来者怀有敌意的其他部落。他们背后是饥荒,前面是战争,真是到处受苦受难”[12]409。托克维尔的论述借助的是推断,而滕那的叙述借助的是现实。
普希金毫不怀疑滕那叙述的真实性,他几乎用类似的话语描述印第安人的处境:“他们处于不断的迁徙中,整天整天地没有食物,他们陷入覆盖冰雪的深谷,借助随手得到的薄树皮涉过湍急的河流,每时每刻都处于失去生命的危险之中。”[5]223在涉及到滕那回忆录真实性问题时,诗人提到的正是托克维尔的名字,两个印第安人生活的观察者在这段行文中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份回忆录的真实性不应遭到任何怀疑。约翰·滕那还活着,许多人(包括托克维尔本人)见过他,并从他本人那里购买他的书。他们认为,伪造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消读上几页,就会确信:没有任何艺术痕迹和朴拙得简直寒酸的叙述保障了真相。”[5]207普希金的整篇文章除大量转述之外,只在文首、文末加了简短引言和结语,却对约翰·滕那书中的美国现实给出了深刻的判断:“人们无不吃惊地在民主中看到了可憎的犬儒主义,残酷的偏见,难以忍受的残暴。一切崇高的、公正的,一切滋养人类心灵的东西——都被冷酷的自私和渴望舒适的情欲压倒;无耻地压制社会的大多数,在教育和自由中奴役黑人;在人民中间实行种族排斥,没有贵族精神;而选民贪婪嫉妒,管理者胆小、奴颜婢膝;天才,出于对平等的尊重,勉强自愿地自我放逐;富人,穿着破烂的长袍,为了在街上不伤害傲慢的穷人,可他们在暗中却是被藐视的。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图景。”[5]205-206滕那的书成为普希金这篇政论文章思考的出发点。他所指出的文明的美国人无人道地对待印第安人的情况,对于俄国读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内省作用——他们看到的“可怜的黑人”,正如俄国农奴制下的农民。
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民族和农民问题,殖民与民主、平等问题,这些主题的连续的、相辅相成的呈现证明了杂志结构缜密的思考。《现代人》上发表的普希金的每一篇政论文和文学作品都成为每一期杂志主导的、确定的意图。还有那些对日常事件的反应,如维亚泽姆斯基对《钦差大臣》上演的评论,弗·佐洛特尼茨基对《纳西切万省的统计学描述》一书的意见,阿·屠格涅夫的信件《俄国年鉴·巴黎》,普希金的文章《论米·叶洛巴诺夫对国内外文学精神的见解》,以及他对俄国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会议的总结等,都赋予了《现代人》新闻的敏捷性。而彼·科兹洛夫斯基公爵按照普希金的请求所写的《巴黎数学年鉴整理》,以及他的科学论文《论希望》,都担当了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
普希金的《现代人》所提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反应时事的敏捷性,题材的多样性,都被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所继承。民众教育问题,科学知识普及问题,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十年之后占据了杂志的中心地位,这时杂志的精神领袖已经是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
普希金共出版了1836年的四期《现代人》,并部分地准备了1837年第1期的稿件。诗人1837年1月27日决斗,1月29日去世。去世后,以茹科夫斯基为首的友人们按照接下来的序号出版了1837年的四期《现代人》,以纪念普希金、抚恤他的家庭。主持出版的友人分别是:普列特尼约夫第5期,克拉耶夫斯基第6期,奥多耶夫斯基第7期,维亚泽姆斯基第8期。1838年,普列特尼约夫接手《现代人》。
文章至此。再过两旬许恰值诗人普希金辞世180周年,谨以此文向伟大的诗人致敬!
注释:
①《北方之花》是当时坚持时间最长的不定期期刊,持续了8年,从1824年到1832年,共出了8期。
②1820年5月—1824年7月,1824年8月—1826年9月,普希金分别被流放在高加索和米哈伊洛夫斯科村。
③《叶甫盖尼·奥涅金》片段,《奥列格之歌》《普罗塞庇娜》《恶魔》《莫扎特和萨利里》《回声》《大胆的人》《群魔》等。
④基里耶夫斯基在1832年开始出版《欧洲人》杂志,但很快就被尼古拉一世禁止发行,因为上面刊登了基里耶夫斯基的文章《十九世纪》,文中被看出要求为俄国制定宪法。
⑤德国诗人克·马·维兰德(КристофМартинВиланд)。
⑥巴里·康沃尔(БарриКорнуолл,英文BarryCornwall,笔名。真名Проктер Брайан Уоллер, 1787—1874),英国诗人和戏剧家。
⑦不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家伊·屠格涅夫,而是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阿·屠格涅夫(1784—1845)。
⑧即米哈伊尔·博格丹,1761-1818,公爵,俄国元帅,苏格兰人。
⑨普希金把自己的朋友阿·屠格涅夫长期在国外期间寄到俄国的一系列书信发表在《现代人》上,并称其为“俄国年鉴”。它们是对欧洲生活敏锐的观察,普希金意识到了这些书信的价值。
[1]Касаткинa В Н,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А С,Пушкина и А А.Дельвига[J].1830 год(№ 1-13).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1988.
[2]Пушкин А С.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 томах[M].(Том 13).Изд-во AH СССР,1937-1959.
[3]Пушкин А С.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 томах[M].(Том 16).М.: Изд-во AH СССР,1937-1959.
[4]Синюков B И.Современник——литератуо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C]//Приложение к факсимильному изданию.М.:Изд-во Книга,1987.
[5]Синюков B И.Современник——литератуо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M].Т.III М.:Изд-во Книга,1987.
[6]果戈理.果戈理书信集[M].李毓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根据原文文中改译)
[7]НикитенкоА В.Запискии дневник(В 3-х книгах)[M].М.: Захаров.2005.(http://az.lib.ru/n/nikitenko_a_w/text_0030.shtml).[8]Синюков B И.Современник——литератуо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M].Т.I М.:Изд-во Книга,1987.
[9]Белинский В Г.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9-ти томах[M].Т.3.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2180.shtml).
[10]Синюков B И.Современник——литератуо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M].Т.II.М.:Изд-во Книга,1987.
[11]Пушкин А.С.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 томах[M].(Том 12).М.: Изд-во AH СССР,1937-1959.
[1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Study of Pushkin’s Magazine Modern Man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Pushkin founded theModernManmagazine in 1836 and edited four issues. With its diversified contents, its coordination and teleonomy endowed themodernmanmagazine with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strict censorship, Pushkin makes a delicate arrangement of the contents and pays tortuous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problems at that time: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the decembrists, the national and peasant issues, the colonial and equal problems, etc.The continuous and complementary themes prove the meticulous thinking of the Journal, embody the editors’ insistence on serious literature in the ecological culture of widespread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ssification.The depth and importance of questions raised by Pushkin’sModernMan, the agility to reflect current events and the diversity of subjects are all inherited by Nekrasov’sModernManmagazine.
Pushkin;ModernMan; research
2016-12-10
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俄罗斯宗教哲学教学、研究和翻译近30年。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1
I106
A
1008-3715(2017)01-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