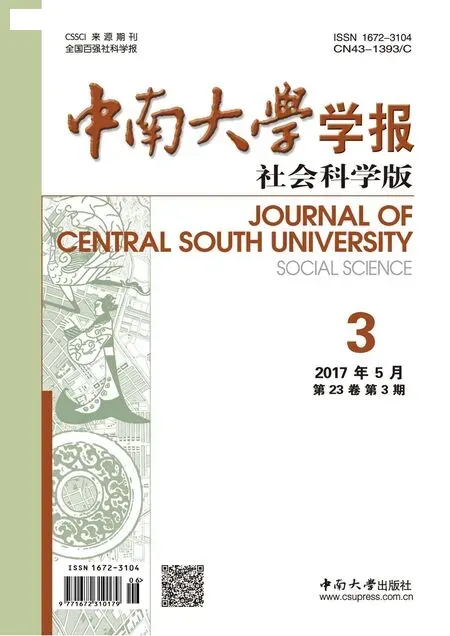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文学的现代性关联
2017-01-12卢衍鹏
卢衍鹏
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文学的现代性关联
卢衍鹏
(1.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63;2. 枣庄学院文学院,山东枣庄,277160)
在“年代学”或“断代史”文学研究中,存在二元对立的思想倾向,从现代性、整体性的角度考察80年代文学与90年代文学的关系,更能发现两者在叙事上的“历史连续性”,其内在连续性大于表面的“断裂”和差异性。通过“缝合”历史的断裂带、对接80、90年代文学通道,梳理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文学表达方式,发掘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来把握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并在连续性的时空中摸索其审美逻辑和内在规律。“现代派”小说表征了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想象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表达了“个人”对“现代”的敏感体验,90年代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纷争其实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
历史连续性;现代性;文学现代性;年代文学;现代性叙事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走向纵深,有了新的拓展,海外学子提出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口号,深化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学术界对90年代文学的研究也取得新的进展。但是,目前学界偏重从“年代学”或“断代史”的角度展开当代文学研究,强调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差异性、断裂性,并且某一年代上的断裂常常以否定以前的文学为代价来突出自身的合法性。这种以“断裂”为特征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是需要反思的。具体到“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以二元对立思维来切割文学的做法就更加明显。如:一种流行的说法是,80年代是精神高扬的年代,是“文化人时代”;90年代是物质至上的年代,是“经济人时代”。这样对两个年代“断裂性”的思维判断自然影响了当代文学研究者对80、90年代文学之间的判断,研究者往往强调、突出、论证二者之间的差异、断裂的一面,如:80年代文学是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90年代文学是私人写作、欲望叙事等。而对二者之间“延续”的一面却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
与以上不同,我们希望以整体性的眼光重新审视80、90年代的文学,认为它们之间内在的连续性大于表面的“断裂”和差异性,并通过重新“缝合”历史的断裂带,重新对接80、90年代文学通道,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寻找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文学表达方式,从文学角度发掘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来把握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寻求一种将这种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在连续性的时空中展开的自我逻辑和内在规律。
一、文学的“现代”:一个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超级词汇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现代”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无法回避、涵盖性极广的超级词汇,这不仅由于“现代”本身的复杂性,更是源于中国社会对文学的期望和要求。“现代”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时间指向的范畴,成为承载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审美转向的指向标,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现代”的理解,每个人都有对于“现代”文学的认识,因为每个人都有对于现在的认识和未来的想象。
“现代”的英文词modern源自法文moderne、后期拉丁文modenus,早期意为此时此刻,文艺复兴之前已经确立现代与古代的区别,19世纪之前大部分有负面的意涵,直到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趋于正面——改善的、有效率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18世纪最开始被用于描述建筑物和拼词法,常与机制、工业相关,用来表示令人满意或喜欢的事物。由现代延伸出来的词语,比如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主义者(modernist)在意义上由广义变为狭义,专指特定的潮流、趋势。从人类文明历史来说,“现代”特指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形成的价值系统,这一系统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政治上,“现代”主要是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五四”时期就风行一时的“德先生”;经济上,“现代”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工业化,晚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就引进了西方的军事工业,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历程;社会上,“现代”主要是指城市生活方式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普及;文化上,“现代”主要是指人的价值和人性的张扬。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学科或知识的母题,一切非现代的事物都受到质疑或否定,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怀着对“现代”的憧憬和期望,“现代”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价值、理想和未来,“现代化为中国当有的出路”[1]。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寻求中国未来之路的时候,很自然地将“现代”的民主与科学作为西方富强的主要原因,而将没有“现代”特征的传统文化视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作为一场全球化的社会变革,“现代化”是贯穿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虽然这一时代主题的外来作用力大于其内在动力,而且这种外在动力首先引起思想、文化和政治变革,然后再推动经济、社会变革,文学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现代”在中国产生和使用的语境来看,让当时的人们单从学术立场进行讨论几无可能,“复古”或“西化”的论争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或西方现代的范畴,“现代”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更是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不仅如此,“现代化”在中国的演进已经超出了社会理论的范畴,以及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客观实证原则。从西方语境来看,“现代”仅是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之一,而且经过韦伯、帕森斯等思想家的反思和批判,已经认识到“现代”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什么样”的“现代”。对于中国来说,经过保守、激进、中立等不同立场的角逐,“现代”已经演化为更为综合的概念——“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新名词”[2],而且将“现代”具体到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文学的现代化。
李泽厚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来概括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基本趋向,其核心指向是中国现代化之路——“革命”,一个在复杂性上足以与“现代化”相媲美的词汇。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一直到1954年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才将社会重心转移到“建设”。即使如此,由于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反特斗争、抗美援朝等现实威胁的存在让“革命”从未真正远离,反而在特定时期(比如“文革”期间)被一再放大。
因此,文学的“现代”是考察中国现代变革的窗口,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人心的变迁,更能看出中国文学通向现代之路的艰难历程。
二、文学的幻象:“改革”的意识形态与现代化的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和个人有着一致的现代化追求,改革文学就是充满现代化想象的叙事,这种叙事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性纷争有着紧密的联系,现代性纷争围绕“现代”展开——什么样的“现代”?如何才是真正的“现代”?如果脱离80年代的社会实践、文化意识和文学想象,这些问题将难以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得以重新启动,而且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文学的现代化提上日程——文学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对国家而言,尽快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及其造成的混乱局面、快速恢复正常的国家秩序成为当务之急,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的人。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如自然科学那样受人瞩目,但显然也深受鼓舞,自觉地加入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大潮中。对个人而言,融入重启的现代化浪潮,不仅是为了现实境遇的需要,而且也是压抑许久的精神释放和文化理想的重新张扬。
从现代化的视角,国家和个人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在文学上表现为现代化想象,改革文学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代表。改革小说的重要作品《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引发的争论焦点是如何看待四个现代化与“揭批查”运动的关系问题[3],批判者注重以“继续革命”的立场讨伐“四人帮”、林彪等的罪行,肯定者着重以“现代化”的眼光赞扬“乔厂长”的改革,最终改革的现代化诉求获得了胜利。“改革”的意识形态作为改革小说的内在机制,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文学的标准,因为“改革”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必然要求。其中,对于“时间和数字”的推崇显示了改革小说对现代化思维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和文学表现不久前在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中还被视为“唯生产力论”而遭到批判,尽管这种表现在后者还只是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改变其实还是文学对于政治时局的积极回应,“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4]。当然,改革文学对于政治的回应,并非被动地、违心地跟从,而是主动地、热情地去回应新时代的到来,因为改革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包括作家内在的广大人民的心声。如果说蒋子龙在《机电局长的一天》中对于生产力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表现,那么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对生产力则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描绘,但效果却截然不同——“机电局长”因冲淡了革命叙事而备受责难,而“乔厂长”因担当了改革者、推动现代化的角色而被神化。
从现代化的视角看,现代人对物质和经济的追求是正当、合理的,改革文学试图改变人们原来传统落后的经济观念,将经济冲动作为文学叙事的核心内容。经济头脑、经营管理能力、科学技术水平等成为改革人物的标签,政治不再是衡量和评价一个人的第一标准,搞活经济成为共同的特征。典型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改革中的领导者必须有经济领导才能,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经济行为展开的,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认定也是从经济层面来实现,个人的经济诉求得到尊重和鼓励。作家们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普遍持积极和欢迎的态度,其实具有理想主义和想象的成分,“面向现代化,首先是我们的文学作品要努力反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程”[5]。理想化、想象化的改革文学对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反映其实仍然带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尽管改革文学一直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有人质疑改革文学对于政治的直接响应,认为文学又一次充当了政治的工具和宣传的渠道,但是如果政治(改革)本身就具有合法性,那么这种工具或宣传也是极有价值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家的担当意识和参与意识在整个社会上都属于先觉者和先行者,对于作家的创作激情和介入现实的勇气,无论如何都要加以肯定。
改革文学对于现代化的想象来自对于“现代”的焦虑,这种文学焦虑本身就具有一种现代性特质。长期以来,文学焦虑来自因物质的匮乏而引发的身体焦虑。很难想象,在物质匮乏的世界,如何要求作家能够超越“现实”而无视关乎生存与发展的经济问题。赤贫不再是光荣的象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幻象,作家的焦虑其实代表了广大民众对于生活和未来的普遍担忧。文学焦虑和现实的需要让改革文学在细节上不那么真实,例如《新星》写李向南在贫困县推广水陆养殖和生态旅游,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不过时,显然对改革的环境、成本等现实因素没有细加考究,图解政治政策的意图大于文学审美的真实表现。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早已开启,重启“现代化”也并非恢复到中断之前的“现代化”,而是重新提出对“现代化”的理解和阐释。从改革小说来看,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类似框架性的原则或共识,“现代化”已经由西化转变为“中国化”——空间的转换带来时间的分野。就“现代化”的逻辑而言,在完成现代化之前,“改革”应该没有休止符,而“改革文学”却没有因改革的继续而继续风行。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改革”对于改革文学的决定性作用,或者很难说改革文学对于现实中的“改革”具有多大的推动作用。但起码可以推断,“改革”或“改革文学”中的一方,出现了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如《乔厂长上任记》中对于“数字和时间”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经济理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一切,没有更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层面,这是改革小说无以为继的深层原因。
三、现代化叙事的流变:从改革文学到“现代派”小说
如前所述,改革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对于改革的外在表现(数字和时间等)大于社会表层之下的暗流涌动,文学形象对于改革者的神化超过对于人物内心的挖掘。
其实,在改革大潮中,变动最大、影响最深的并非数字和时间等客观的经济指标,而是改革在人心中掀起的巨大波澜,是深入骨髓的人性纠结和精神裂变。现代化叙事围绕经济层面的结果,就是改革文学在审美上仍然延续“十七年文学”甚至“文革文学”的叙事模式,在人物塑造上要么因袭传统清官形象,要么带有“高大全”的无产阶级英雄的痕迹,造成人们对于改革文学“空心化”“刻板化”的负面印象。对此,人们希望能够看到改革之后的人们内心深处的变动,尤其是人性和精神的深刻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蒙的一组“意识流”小说其实就是“改革文学”(现代化)的变体,王蒙等作家正是看到了改革文学的弱点,才试图采取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来填充和弥补这一现代化叙事的空白和缺陷。
在现代化叙事的探索上,王蒙的《春之声》等小说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呼应毫不逊色,同时又有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文学创作手法,在文学“现代化”的形式创新上更进了一步。王蒙作为主流作家的代表,对于党的文艺政策和时代主题的把握超出常人,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要使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言行切实有利于人民、有益于安定团结、有益于四个现代化”[6]。王蒙在意识形态上向主流靠拢的同时,又大胆地实践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改革文学的桎梏,内容的保守与形式的激进相结合,显示出与改革文学不同的叙事策略。“意识流”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王蒙并不是第一个使用的中国作家,但重启了这一现代艺术,其价值并非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以形式解放撞开了精神解放的大门”[7]。也就是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以现代派艺术的形式创新,带来了思想解放、审美解放的效果,重新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现代链接,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所在。《布礼》以碎片化的时间流来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主人公钟亦成因诗被打成右派,时间从1957年到1966年再到1949年,再从1966年到1970年再到1949年,从被批判、殴打到参加革命活动,从被怀疑到入党宣誓,二十多年的精神历程被交替错落回放,支撑主人公的信仰、爱情、亲情等在磨难中书写了知识分子的血泪史和精神史。意识流写法的优点是直白地书写内心和精神深处,但王蒙笔下的人物还是有明显的理性线索(比如20多处时间明确的标题),庄严与荒谬的并存与对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相比改革文学,我们从意识流小说中看到了更多的精神和内心,尽管这种精神是以分裂和片段的方式展开,内心的揭示也被涂抹了层层伪装,但是毕竟能够感受到一种旧的价值体系的坍塌,以及重建新的价值体系的努力。除了对精神世界的浓墨重彩和深入挖掘,意识流小说对于人、人性和人物的把握也与改革文学截然相反,人的渺小与卑微替代了改革文学中英雄人物的伟大与坚强,激情燃烧的岁月化为虚无缥缈的梦境。
宗璞的小说《我是谁》关注人的“异化”问题,在写作风格上更是接近卡夫卡的《变形记》,以现代派艺术的方式重启了文学的知识分子问题探讨。宗璞在“文革”结束之后,能够较早地认识到并创作出《我是谁》《蜗居》等小说,可见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我是谁》很显然是对自己身份的追问,主人公韦弥一直困惑并挣扎着寻找自己的身份,外界环境给的身份让她陷入痛苦和绝望的境地。一方面,在他人看来(甚至自己也认为),自己和很多教授、讲师等一样,都是痛苦不堪、伤痕累累的虫在地上“一本正经地爬着”[8]。这里的“虫”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意味着阶级出身不好、思想反动,甚至直接被称为“大毒草”“大毒虫”。另一方面,自己的内心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并非“虫”,而更像是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立志报效国家的“雁”——在国外学有所成而心系祖国的知识分子,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投入战火中新生的中国。韦弥和丈夫孟文起失去了作为学者的职业、权利,以及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而被称为“牛鬼蛇神”、作为敌人而对待。孟文起的上吊和韦弥的投湖,不仅仅是失去了教授的职业和做人的身份,而且致命的是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而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因为他们回国的目的就是投入祖国人民的怀抱。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追寻自我的过程,其实是身份认同的过程,韦弥们的反思并不能确认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因为他们已经不自觉地将自己归入“人民”的宏大叙事,即便自杀也只是逃避身份的无奈选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身份问题。可见,宗璞对人的“异化”书写还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造成异化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语言暴力带来的精神折磨甚至要超过身体暴力带来的肉体伤痛。二是自身的焦虑和缺乏反思意识,既要对外界、他人(包括“人民”)进行反思,又要对自我进行反思。当然,我们这里强调的不仅是宗璞的“反思”,而且是对宗璞“反思”的反思。
相比王蒙、宗璞等对现代派写作手法的探索,徐星、刘索拉等对现代艺术的实践已经深入到哲学和理念的层面,他们以反叛传统的姿态书写城市文化,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效的历史联系。城市本身就是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中国的城市由“城”和“市”构成,分别具有防御功能和经济功能[9],中国文学中的城市应该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质,比如中国传统的诗性文化就是底蕴深厚的文化资源。但是,徐星、刘索拉等作家对于城市文化的书写显然更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以青年亚文化代言人的姿态,侧重于形而上地去表现当代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那种无以名状的压抑感、空虚感、孤独感和幻灭感,以及对生存方式和个体命运的抗争、思索、追问。徐星、刘索拉等对于现代城市的书写是一种“想像性写作”,“想像这一概念绝不等同于‘虚假意识’,或毫无根据的幻想,它紧紧表明了共同体的形成与人们的认同、意愿、意志和想像关系以及支撑这些认同和想像的物质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10]。这里的“物质条件”就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城市改革和迅速发展,关于城市的现代性想像并没有完全屏蔽文学所处社会的客观性和作家的切身体验。正好相反,关于城市的形而上想像是作家在城市生活经验与现代思想建构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关于城市的文本一定是关于城市的经验(包括形象性经验),而城市经验转化为文学文本其实也是现代性想像的过程。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用戏谑的叙述语言和闹剧式的情节来非线性地展示城市生存状态,给人以陌生化的感性认识和真实性的精神体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迷茫反讽的基调来展示城市生存的玩世不恭和真实痛苦,在消解精神丰富性、复杂性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哲思的直觉化、情感化,尽管这种城市人生显得那么厌烦、冷酷、沉闷和疏离,但是又那么真实、深刻。这些“现代派”小说从一个特殊角度表征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想象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表达了“个人”对“现代”的敏感体验。
因此,从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的现代叙事流变,既是中国社会现实对文学期望和要求的提高,也是文学从更高的层面反映现实的叙事策略。
四、文学现代性的纷争:从现代到后现代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到90年代文学的转变,其连续性远远大于断裂性。20世纪90年代关于现代性的纷争其实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或者说是继承和延续了80年代关于现代性讨论的思想成果,但在实质上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严格的意义上,所谓“现代性断裂”“重写现代性”等纷争,与80年代就开始的“重写文学史”“重估现代性”等相呼应,在方法论上都是西方现代理论的又一次上演。
有人用“幽灵”比喻现代性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仿佛是在指称一种熟悉而陌生的存在。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现代性存在更多的共识(共同的现代化目的),那么90年代的文学现代性趋向更多的分歧(不同的思维方式)。汪晖对现代性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的分析[11],在梳理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思路,希望通过提炼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来探究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与汪晖们不同,倡导后现代的学者提出了“现代性终结”的命题,认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学要走出现代性,其依据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要转型——市场化、消费化,再加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传播,现代性逐步将被后现代取代。我们不得不追问:“当我们在谈论现代性或后现代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或者说,我们的文学中有没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我们如何面对文学的现代性或后现代?
首先,中国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的审美因素,现实主义文学复苏与现代主义创作实验频出,不断翻新的文学潮流和新的文化立场让文学的现代性变得复杂和多元。尤其是1987年以后很多作家开始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于既有意识形态的反讽和对于传统价值信仰的否定,以各种方式来表现躲避崇高、对抗现实、消解意义,从文字游戏到游戏人生,喧嚣中弥漫着一种刻意为之的审美倾向。但是,反叛现代性不等于后现代,文学的表面新气象不一定带来文学内在的新质。
其次,对于文学是否现代性或后现代的判断,出发点和观察角度很重要,从概念出发,还是从文学出发,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如果从文学创作出发, 90年代的先锋文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形式的模仿,还是精神的因袭,都流露出或多或少的痕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断定先锋文学就是后现代文学,更不能以西方后现代主义来衡量中国先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从概念出发,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来套中国的先锋文学,可能会失望地发现其中掺杂了现代性的因素,或者会惊喜地发现先锋文学丰富了后现代的视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之所以引进和吸收西方后现代文学,肯定有其内在的审美需求和文学自觉,其中既有现代性诉求,也有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好奇,不能简单而论。甚至可以说,先锋文学在最初时可以看成是现代派,而后才被视为后现代文学,文学语境的不同可能带来相左的文学观念。
再次,要分清楚文学和审美层面的“现代”与“后现代”,这与中国社会现实层面的“现代”与“后现代”有所区别,两者既存在联系,又不能等同。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经验,中国远没有达到后工业社会的阶段,甚至有些地区还处于前现代社会。再者,就算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不意味着在文学、文化和思想上就能产生与西方同步的后现代主义。同样道理,即使中国在经济社会层面远未达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水平,也不等于中国不能产生后现代主义文学因素。就如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拉丁美洲,而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被认为在作品中体现了类似风格,但判断文学的标准绝不仅限于某种风格。
最后,与其辨析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复杂关系,不如将其看成具体文学问题的语境和方法,立足中国文学实际比跟风西方潮流更为重要。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文学终结论”虽然与世纪末的悲观情绪有关,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文学边缘化的现实。在后现代的视域下,对于文学边缘化的认识更为明晰——从艺术中心走向边缘、从文化中心走向边缘,艺术领域中影视占据了中心地位,文化领域中以科技、创意、传媒、资金等为纽带的文化产业成为中心。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依赖技术进步的综合媒介艺术迅速崛起,文学往昔的优势和光环不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已经不再遵从审美现代性所指定的规则,尼采美学所宣示的精神虚无也影响到中国,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性初建时就伴随着尼采批判的声音,“尼采反对的是西方的现代,鲁迅怀疑的则是正在建构的中国的现代”[12]。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纷争扩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观念和审美认识,其中就包括对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判断。从中西比较(中国文学现代性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内外对比(文学内外、文化内外)的多维视野,为中国文学打开了更为立体的审美空间。
总之,以“现代性”这一叙事视角,通过考察改革文学到现代派小说等转变过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重新“缝合”文学历史的断裂带,重新对接80、90年代文学通道。如果不再局限于时间和年代的“细节”或人为割裂,而是从更宏观的叙事层面上寻找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文学表达方式,就能够从文学角度发掘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这样的历史脉络更容易让我们从内在视角来把握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也许,在80、90年代文学连续性研究中,更有利于实现对当代文学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并在连续性的时空中找到这种自我逻辑和内在规律。
[1] 金耀基. 中国社会与文化[M]. 香港: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2: 16.
[2]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8.
[3] 徐勇. “改革”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困境[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6): 123−133.
[4]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八年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N]. 人民日报, 1978−1−1(1).
[5] 王蒙. “面向现代化”与文学[C]// 王蒙文集(第6卷).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3: 492.
[6] 王蒙. 我们的责任[J]. 文艺报, 1979(11−12): 47−50.
[7] 杨义. 王蒙小说的哲学、数学与形式[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5): 5−15.
[8] 初清华. 新时期之初小说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想象[J]. 文学评论, 2005(6): 79−85.
[9] 傅崇兰, 白晨曦, 曹文明. 中国城市发展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5.
[10]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4.
[11] 汪晖.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C]// 汪晖自选集.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35.
[12] 郜元宝. 编选者序[C]// 尼采在中国.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1.
Modernity relevance of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LU Yanpeng
(College of Ar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63, China;Chinese Department, Zaozhuang College, Zaozhuang 277160, China)
In literature studies on chronology or dynastic history, there exist two opposing ideological trends. So if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it will be easier to find out the narrativ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he two, and that their innate continuity is greater than their superficial “rupture” and otherness. By seaming historical rupture, and by abutting literature passages from the 1980s to the 1990s from modern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essay hackles the literary expression for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nd experience, finds a clear historical context to grasp the self understanding and self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explores the aesthetic logic and internal rules in continuous space-time. Modernist novels represented Chinese imagin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1980s and expressed individual sensitive experience to the modern, from which actually started the dispute about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of the 1990s.
historical continuity; modernity; literary modernity; dating literature; modernity narrative
[编辑: 何彩章]
I022
A
1672-3104(2017)03−0149−06
2016−12−18;
2017−03−1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文学的‘历史连续性’研究”(13BZW126);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文明话语中的文学观念:从晚清到‘五四’”(1607463);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重点项目)“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女性婚姻及其文学书写研究”(ZD20161025)
卢衍鹏(1982−),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枣庄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