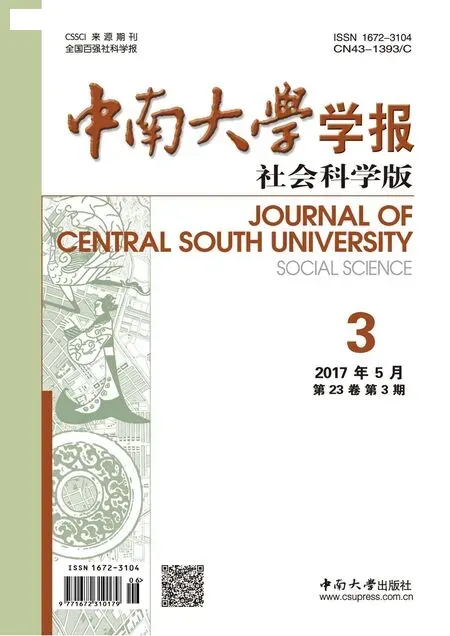论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2017-01-12孙保全
孙保全
论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孙保全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中国传统的疆域格局是异质性的,在“核心—边缘”二分视野下,边疆形态是碎片化的。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边疆治理的核心课题就是按照民族国家一体化特质,将这种碎片化边疆转换为整体性边疆。这种边疆整合工程在晚清以后逐步开启,并在民国时期得以推进。其中,主权体制建设导致边疆形态领土化,中华民族建构促使边疆归属一体化,地方制度变革推动边疆政治均质化。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总体完成,随着边疆领土属性的确立,政治制度的统一,以及社会文化的彻底改造,一种整体性的边疆形态由此基本成形。
民族国家;边疆治理;边疆整合;主权;中华民族
在缺乏主权体制的王朝时代,国家疆域经常随着王朝实力消长和统治者政治偏好转移而发生盈缩变动。其中,作为国家疆域边缘地带的边疆区域,在王朝版图中的流变显得更为频繁。即便作为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边疆区域与内地之间仍长期保持着二元性的格局,同时不同边疆区域之间也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个在政治生态、经济生业、社会结群和文化形态诸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空间版块,呈现出异质性和碎片化的形态。这表明,中国传统的疆域构造是异质性的,在“核心—边缘”二分视野下,边疆形态是碎片化的。这种碎片化的边疆现实,同王朝国家的国家形态和治理逻辑是相适应的。然而,近代以后,随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开启,这种碎片化的边疆形态日渐同民族国家的一体化特质难以兼容。传统碎片化和异质性的边疆架构不仅给国家形态转换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对民族国家主权体制的形成、中华民族建构、统一政治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制约作用。因此,中国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将这种碎片化边疆转变为整体性边疆,以实现国家疆域的整合。从历史过程来看,这种边疆整合工程在晚清以后逐步开启,在民国时期得以推进,并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得以基本完成。
一、主权体制建设中边疆形态的领土化
近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是迫于救亡图存压力而被动开启的。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属性和领土要素,因与挽救国家危亡直接攸关,而成为重塑国家形态的首要任务。在进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主权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外交关系以及划定疆域和边疆范围的主要依据。在这样的条件下,边疆逐渐处于国家主权的管控和保护之下,由此成为国家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边疆的范围变得更为稳固,边疆同内地之间的整体性也大大增强。
鸦片战争以降,当中国王朝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发生直接而激烈的碰撞之时,传统的朝贡体系不仅无法将列强纳入到既有秩序中来,反而被强行裹挟到民族国家所构成的更大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观念日渐“将至高无上的华夏文明世界降格为西方国际体系内的一个地方性邦国”[1],并且被迫将文明性的“天下”疆域转化为主权性与国家性的领土范畴。一方面,受王朝中央统治程度较深的“属部”的大片边疆区域被强行割让;另一方面,作为清朝属国的周边国家也相继被西方列强纳入殖民体系,而脱离了传统的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体系。在这种情势下,清王朝不得不以牺牲巨大利益为代价,逐步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确立疆界,从而初步形成了国家外沿断断续续的边界。
这些边界大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淫威下被迫划定的,因此具有突出的不平等性。然而,从实际层面来看,“缔约各国在确立边界过程中,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无意识地帮助了中国主权的定形。随着国际法成为国家关系的准则,对中国主权的不断侵犯就形成了对中国剩余领土的主权承认,而满清在中亚和北亚征服地域也就成为合法的并受到承认的中国国土了”[2]。这样一种主权机制对于整体性边疆的形塑是通过双重路径实现的:一是将边界之外的、国家控制最弱、碎片化最强的疆域排除在领土之外,通过这种消极的缩减方式增强边疆的整体性;二是确立了国家主权占有、控制和管辖的空间范围,加强了边疆的领土化,通过这种积极的建构方式增强边疆的整体性。
清朝祚灭,民国初建。南京临时政府由于存续的时间较短,因而对于边疆领土化的影响较多地停留在思想和理念层面,而在实践层面上的作用则较为有限。在北京政府成立之时,中国的边疆形势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危急。“西南、西北、东北边境出现严重危机,中国正面临被肢解的危险”[3]。此后,随着中国主权体制的进一步做实以及边疆领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样的边疆危机逐步得到缓解。
一战以后,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方,在外交关系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是针对以往不平等条约的“修约”及“废约”的外交行为,对中国主权体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明确提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4]。与此同时,北京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来强化中央对边疆的主权控制,力图将边疆地区维系在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一方面,北京政府极力断绝或削弱边疆地方的主权性权力,以强化中央政府主权权威。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政府采取权宜性的怀柔政策,以维系边疆地方同中央的关系,但在必要之时也采取了强硬手段来维护国家主权。这不仅使得辛亥革命后皇权体制解体带来的边疆危机得到缓解,而且在主权领土方面推进了边疆的整体化进程。在极为不利的大环境下,北京政府保证了中国边疆领土基本上维持了原状,这样的内政外交成就实属不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得到控制,国家能力和中央政府的权力都有所增强,由此加深了对边疆地方的主权管控。在这一历史时期,边疆区域的传统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被限定在地方政治层面,而对于军政、外交及其他关乎全局的重要权力,则逐步上收到国民政府手中[5]。这样的举措,实际上是对中央和边疆地方的权力进行了划分,使得国家的主权归属到中央层面。与民初的中央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更加强调对边疆地区的主权性管辖,并努力将国家权力更为深入地延展到边疆内部。以此削弱了边疆的分立和分离倾向与实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国外势力通过与边疆地方之间密谋勾结或私订协约以实现分裂中国版图的目的,使得边疆更加牢固地维系在完整性的国家领土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地位和声望有所提升。作为战胜国,中国收复了被日本侵占的大片边疆区域,排除了边疆地区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确立和巩固了边疆的主权归属。此外,随着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以及联合国的成立,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被重新塑造,主权国家大量涌现,主权体制得以在全世界普遍推行。至此,中国以主权独立的国家身份,真正融入到新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得到外部承认,进而获得了实质性内涵。在这一过程当中,虽然国家的疆域及边疆,仍旧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和差异性,但是就主权领土属性这一根本性的要素来说,其整体性大大增强了。
二、中华民族构建中边疆归属的一体化
作为与民族单位连为一体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近代以后,中国人逐步模仿西方国家中“民族”(nation)的基本样式,来重新定位中国的族际关系,同时打造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边疆属性由归属各个族体的“民族性”,逐渐转向由全国人民所共同拥有的“中华民族性”,由民族因素造成的边疆碎片化格局也不断向着一体化方向发展。
晚清时期,在民族国家和民族概念传入中国之初,对于如何认识中国民族结构的问题,“革命党”与“保皇派”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论战。前者坚持从种族主义出发,在“内地十八省”强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并对其他少数民族群体采取排斥态度。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则继承了“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主义传统,主张将业已接受华夏文明的满人等“外族”纳入“中华”范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主张,形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双重模式。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革命党人主张的将民族国家解读为“一国一族”,并且将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的观点占据了主流地位。
在民族国家构建之初,革命派精英分子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仅是要构建起一个作为“nation”的汉族共同体,而且要恢复汉人对中原故土的排他性统治,而那些作为“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连同其生活的边疆地带就成为了被驱除的对象。这种种族式的“一国一族”思潮对当时的国家统一产生了极大的解构作用,保存“中国本部”和放弃边疆的主张,使得原本就动荡不安的边疆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从而加剧了边疆的碎片化形态。
辛亥革命以后,在反思种族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五族共和”理念得到重视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之时,孙中山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6]随后,在各省代表会议上,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被拟定为中华民国的国旗,并最终被当时的临时参议院确定为国旗。这表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在这一理念的导向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一步明确:“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宪法的形式,将非汉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认定为国家的领土范畴。
从实际的政治效果上来看,“五族共和”话语在边疆地区也得到了各族民众和上层人士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发挥了边疆整合的作用。但这种多元主义的民族建构模式,所产生的边疆整合作用很快便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日渐式微。一战以后,在威尔逊和列宁的大力鼓吹之下,民族自决思想潮流开始在全世界传播蔓延。在这样的世界潮流下,英国、日本、苏俄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开始借由“民族自决”口号策动中国边疆的一些民族上层从事分裂活动。为有效规避“民族自决”带来的冲击,中华民族的构建理论和构建进路开始由多元主义转向了一元主义。
1920年代孙中山等人提出了一种“民族同化”的论调,主张以汉族为中心来同化其他民族,并以“大熔炉”政策来冶炼出一个一元化的中华民族[7]。这种建构模式并未得到当时北京政府的支持,却对后来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国内各民族间的命运共同体认同越来越得到强化。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理论构建也步入了新的阶段。与此前孙中山等人提出的“民族同化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构建话语以“民族同源论”为主导。在遭遇中国各族人民一致对外的抵抗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试图采取策划边疆分裂的手段来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为预防民族主义泛滥带来的国家危机,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直指滥用“民族”概念暗含的政治风险。受其启发,蒋介石在1940年代提出了“宗族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汉、满、蒙、回、藏均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下的宗支而非“民族”[8]。自此以后,“中华民族宗族论”逐渐取代了“五族共和”,成为官方论述国内民族问题的统一口径,也占据了当时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构建的主流地位。
随着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和理论构建的不断推进,内地和边疆之间因民族和文化要素而形成的鸿沟也逐步得到弥合。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下,唯有中华民族能够“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 家’”[9]。这样一来,边疆同内地共同构成了同一民族共同体的生活区域,打破了原有的因族体区隔而形成的内外分际的疆域格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已然由一种自在形态升华为一个自觉共同体,国家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增进,也使得领土认同日渐内化为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而这对于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维护又是不可或缺的。
三、地方制度转型中边疆政治的均质化
在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地方政治具有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自秦朝开始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主要体现在中原地区,而在边疆地带则表现得并不明显。长期以来,边疆地区在相对封闭的政治地理空间场域下,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地方政权体系。而中原王朝所采取的因俗而治和羁縻治策措施,使得这种边疆地方政治形态得以延续和强化。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边疆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松散,边疆治理更多时候是一种由地方政权主导的高度“自治”。
与传统国家形态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统一性和渗透性的特征。为了实现对“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10]以及形成“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11],并取代其他社会权威与一切组织成为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和独享者。国家治理达到了政权和治权上的高度统一,国家力量不仅深入到社会基层,而且延伸到边陲的各个角落。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边疆政治仍然可能存在较大的独特性,但是必须在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下组织和运行。边疆地区的政治生活,也不大可能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之外,而必须在国家制度框架中展开。这样的客观现实使得边疆地区在政治上的同质性与一体化水平被大大提升了。
晚清时期,中国就开始按照民族国家的政治特征来调整边疆地方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做法便是将施用于内地区域的行省制度,向边疆地区移植和推行。在此之前,清朝的边疆地方制度具有鲜明的羁縻性特征,如在维吾尔族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在北疆地区实施扎萨克制度,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等。而不断加深的边疆危机,使得羁縻统治下的边疆空虚问题空前凸显,从而迫使清朝“放弃固有的统治方式,通过对周边地区积极地行使权力,使其与内地一体化”[12]。有清一代,省制无论是在空间位置上还是在政治属性上,都具有突出的内地性特征。而晚清建省行为,则正是要改变边疆地方制度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状态,转而推动其向着内地化和一体化转变。这样的重大调整,被西方学者视为“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 碑”[13]。
民国建立以后,边疆地方制度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革。北京政府时期,颁布了整理全国地方制度的三道“统一令”,规范了省、道、县的三级行政区划。为实现边疆政治与全国形势趋于一致,北京政府在热河、绥远、察哈尔等边疆地区设置了特别行政区域,以此作为统一省制和县制的过渡性地方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统一省、县两个地方层级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内地化和一体化的边疆地方制度变革取向。在省级层面,先后推动实施了青海、宁夏和甘肃的分省设治,重划原内蒙辖地进而设置了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以及在西康地区建省;在县级层面,边疆地区广泛成立了“设治局”,以为此后统一县制做准备。
纵观近现代的历届政府对边疆地方政治制度的调整,大体上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实了边疆地区,并且在政治层面将边疆的范围由内向外推移,在地缘政治上抵御了国际势力在边疆地区的渗透和内侵;二是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方的实际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边疆地区的分裂主义与地方主义;三是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在行政管理上的整齐划一,从而推动了国家政令的统一与执行。由此来看,随着地方制度变革的深化,边疆政治一体化程度也得以大大增强。
四、民族国家建立与整体性边疆的重构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传统边疆形态逐渐被民族国家构建力量所解构、重组和整合。但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此条件下所推动的边疆整合总体上仍处于一个不断积累的量变阶段和过渡性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基本建立。此后,国家主权获得独立,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统一性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确立,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国家能力空前提升。在这一系列条件下,党和新中国政府开始能够真正按照民族国家的治理需要和政治逻辑,在多个维度上加深边疆整合。
首先,领土性边疆的整体构筑。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自觉运用主权领土原则来划分陆地边疆范围。但囿于国内外形势,在一定历史时期对领土争端采取了一种“维持现状”和“不承认主义”的态度。此后,受到中苏、中缅之间领土纠纷的刺激,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我们的对外关系中,有切身利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同周边国家都有边界纠葛,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14]与此同时,在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以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处理边界问题便被提上政治日程。在这样的情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着手同周边国家划定边界。截至60年代中期,中国已陆续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划定了边界,有近一半的陆地边界线得以标定。这样一来,中国陆地边疆的外部界线渐次廓清,“有边无界”的边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次,边疆政治的统一安排。人民民主政权在边疆地区的建立,为促进边疆政治的一体化,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控制和治理创造了最为基本的政治条件。边疆地区传统的政治体系和体制外权威逐渐被统一的国家政府体系和地方政治制度所取代。在边疆地区的地方政权建设方面,省级行政区层面统一设置了“省”和自治区政府;在县域层面,则废除了民国时期过渡性的“设治局”,统一推行了县制(包括自治县和自治旗)。在统一的地方政府体系和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上,边疆居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保障,由此也推动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上的整合。同时,由于统一政权和制度的建立,也使得国家宪法、法律和政策在边疆地区得到贯彻实施,国家权力和政党力量也得以延伸和扎根到边疆基层。
再次,边疆社会的全面改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边疆地区存在着极为复杂和多样的社会形态。面对这种情况,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慎重稳进”的基本方针下逐步开展了边疆社会的全面改造。从时间维度上来划分,边疆社会的改造大致可分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其中,民主改革以土地改革为核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入手,逐渐废除了边疆地区的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而社会主义改造则在民主改革基础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将边疆社会引向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改造的区域类型上划分,边疆社会改造可分为农业区、牧业区和城市的社会改造。其中,边疆农业区和城市的改造与内地大体上遵从了同样的社会改造模式。而对于边疆牧业区的社会,则因为其特殊的生产方式,经历了“步子更稳些、政策更宽些、时间更长些”的改造过程,其改造方式也更为特殊。经过这样的改造活动,大部分边疆区域的社会形态的异质性得以削弱,而同内地之间的同质性则大大提升了。
最后,边疆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改造,边疆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深刻转变。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开国元勋凭借其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在边疆地区形成了势能强大的魅力型权威,弱化或消解了边疆民众对于传统政治权威的认同和信仰,并以此为中介强化了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同时,边疆文化教育机制的形成和推广,起到了“改造旧的社会、旧的思想、旧的人,建立新的社会、新的思想,培养有社会主义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5]的作用。而边疆的统战工作,从另一个维度加深了对边疆上层人士的思想改造,增强了其对于执政党和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政治运动,通过政治动员途径在政治文化层面上也提升了边疆民众的现代政治认知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热情。
除此之外,建国初期针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扶持发展和规模空前的移民支边、屯垦戍边等举措,也进一步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形态、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这样一来,自晚清开启的边疆整合工程,随着民族国家的基本建立而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持续治理,边疆形态从总体上实现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的转型和重构,这对于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产生了基础性和决定性的 影响。
五、结语
从本质上来看,民族国家一体化与边疆异质性之间存在着固有张力。民族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强调政治形态上的一体化与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整合。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边疆天然就是一块异质性和差异性的区域。在前民族国家时代,国家统治和国家治理对一体化的要求并不突出,因此边疆地区的异质性并不一定构成一个“问题”。但是在民族国家语境下,这种“一体”与“异质”之间的矛盾就被凸显出来了。凡是疆域面积广袤,边疆多样性和异质性突出的现代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协调和平衡这种矛盾的任务,或者说都面临着如何实现边疆整合的问题。总体来看,克服“异质性”、实现“一体化”是晚清至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边疆治理的一个基本取向,但这种一体化进程也伴随着边疆区域多元化力量的抵制。在这个边疆形态“民族国家化”的过渡阶段中,这种抵制表现为传统对现代的反叛,以及地方利益对国家利益的抗争。实际上,时至今日中国的边疆整合工程也尚未彻底完成,特别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内地-边疆”整体化发展、持续推进边疆的认同整合与社会整合等方面的问题,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异常复杂。不能深刻认识这种“一体化”与“异质性”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理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边疆形态的演进轨迹和内在逻辑,也无法理解今天民族国家建设中边疆问题的症结所在。
[1] 刘仲敬.世界体系的演变与中国的国家塑造[J].文化纵横, 2014(4): 72−78.
[2]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4.
[3]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6.
[4]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C].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218.
[5] 张羽新, 张双志.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一卷[C].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5: 201.
[6]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
[7]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87.
[8]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M].南京: 正中书局, 1943: 2.
[9] 马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J].西北民族研究, 2010, 65(2): 6−13.
[10]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44.
[11] 宁骚.论民族国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28(6): 84−94.
[12] 薛小荣.对“海防”“塞防”之争的另一种解读[J].探索与争鸣, 2006(7): 57−60.
[13] 费正清, 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年·上卷[C].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18.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335.
[15] 张养吾. 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的伟大成就[J]. 民族研究, 1959(10): 27−35.
On the frontier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hina as a nation-state
SUN Baoqu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y pattern is heterogeneous in China. From the binary perspective of “core-periphery”, the traditional frontier form is fragment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nation-state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core issue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s to transform the fragmented frontier into integral frontier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nation-state integration. This kind of frontier integration project start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 is promo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mong them, the construction of sovereignty system leads to the territorial form of the frontier; Chinese nation building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frontier entitle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system reform to promote the homogenization of the frontier politics.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arks the overall completion of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frontier territorial attribute, the unified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ulture, the integrated form of frontier is basically formed.
nation-sate; frontier governance; frontier integration; sovereignty; Chinese nation
[编辑: 颜关明]
D032
A
1672-3104(2017)03−0129−06
2016−11−07;
2016−12−02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边疆社会问题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范式”(16BZZ037)
孙保全(1986−),男,河北沧州人,法学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