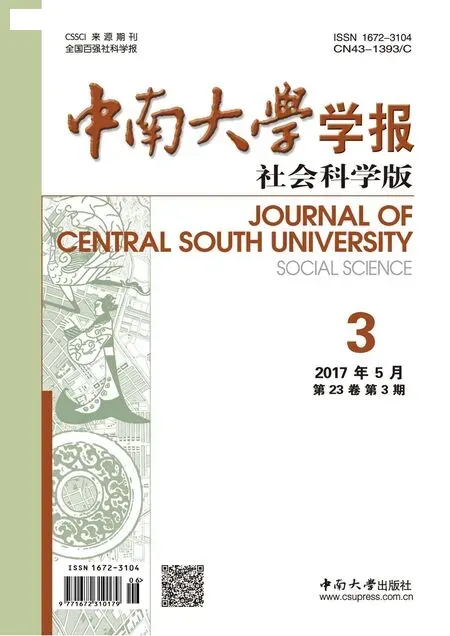走向“政治性公司法”——党组织如何参与公司治理
2017-01-12蒋大兴
蒋大兴
走向“政治性公司法”——党组织如何参与公司治理
蒋大兴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政治性公司法”是“重视国企”或“重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公司法模式的别称,该种公司法模式与Hansmann等谈及的“国家主义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有某种家族相似性。“政治性公司法”之提出,意味着处于西方公司法包围过程中的中国开始思考公司治理的民族特色/政治特色。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国企“公共财产”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国企应更多地凸显其公共性/人民性的一面。“重视国企”/“重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本身存在宪法和公司法上的依据,也是中国应对TPP等西方式“国企压制”,彰显“经济发展道路自信”的重要方式。当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仍应平衡好企业治理效率与治理安全的关系,公司治理之本质在于凸显“效率经营”。尤其在国企决策效率本身仍有待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设计,不应成为企业“效率化经营”的障碍,更不应因此无谓地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
政治性公司法;党组织;国企;公司治理
因最近之中央文件对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纷纷修改其章程,在公司治理部分嵌入党组织的地位与权力,保卫党组织先行决策的权力。由此,再度形成“党组织如何参与公司治理”,以及中国公司法是否会呈现出社会主义特色的转型或倒退的问题?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再被重视”,系因习近平同志在国资委的一次讲话而生,因此,笔者将“重视国企”及“重视党委作用”的公司法模式称为“政治性公司法”。
“政治性公司法”之提出,是否意味着中国公司法将从此脱离全球公司治理的“普适渠道”,如同中国政治制度一样,表现出更多的“中国特色”?此种“党委先决”的治理安排,是否会进一步孤立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国国企?笔者秉持“同情理解”政治决策的立场,试图梳理与解释“政治性公司法”的逻辑,并对党组织如何参与公司治理的问题表达个人见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种探讨纯基于学术立场,笔者对 该类问题不持任何“先定的”政治预设,亦非旨在对公司法的某种政治模式或政治主张予以“取舍性” 评价。
一、为什么有“政治性公司法”?
本文所谓“政治性公司法”,可能是不甚准确的提法,主要意指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密切的公司法,在中国则指“重视国企”“重视党委作用”的公司法模式,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集权型”或“国家主义”公司法模式的别称。就此而言,“政治性公司法”其实早在Hansmann, Kraakman[1]关于《公司法的历史终结》的宏文中就能找到影子。其国家主义的公司法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属于“政治性公司法”之范畴,虽然Hansmann和Kraakman并未对此种“国企友好主 义”的公司法模式如此命名。本文关心的是,此种含义上的“政治性公司法”在中国是如何衍生而来?该种表述是否有其政治性/法理上的局限?下文分别从《宪法》《公司法》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三个维度展开讨论,以透析“政治性公司法”可能的理论逻辑。
(一)宪法逻辑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改革,总体上一直在“自由主义路线”上前进,所谓“市场经济”基本是此种改革道路的描述。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中所提到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忽略该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个性,而喜欢褒扬其“市场主义/自由主义”的一面。对《宪法》确定的经济体制的此种“偏于一隅”的理解与解读,是相当不完整的。
笔者认为,《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一语,至少有两大表征:其一,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或者说公共企业/国企或集体企业在中国经济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对“主导地位”如何解释,仍然存在不同路径[2],但这至少意味着国企仍是组织国家市场经济运营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力量。其二,人民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在市场经济活动的组织、参与以及利润分享方面,都应居于主导地位。此种人的主导地位,往往容易被忽略。
可见,“政治性公司法”强调对国企的重视、强调要“做大做强”国企,是有其《宪法》基础的。那种动辄主张国企私有化或者消灭国企的观点,是不合现行《宪法》安排的[2]。
(二)公司法逻辑
同样,对公司治理中党组织功能的重视,也并非没有公司法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第19条明确规定了党组织在国企中的地位及活动规则:“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习近平同志在国资委的讲话提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
可见,有人认为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一种中国公司法上的倒退的观点,可能有失偏颇。从文义上来说,《公司法》第19条所提到的“在公司中设立党组织”,其中所谓“公司”并非仅指“国企”,而是泛指一切公司而言。相较“政治性公司法”仅对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的要求而言,《公司法》之要求其实更为激进。按照上述要求,非国有企业(包括私企与外企)也得设立党组织,并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条件。
因此,从参与主体来说,“政治性公司法”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要求可能是温柔的、局部的,甚至还不如《公司法》第19条要求的那么广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同志否定了《公司法》第19条之规定,他只是强调了该规定的部分内容——党组织在国企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参与国企治理的方式。
(三)反TPP制约
另一个可能有助于理解“政治性公司法”的政治逻辑的是关于类似于TPP之类“西式国企压制”对中国企业海外竞争的影响。中国国企的海外竞争一直遭受各种歧视,国企通常被认为在国内享受了特别待遇及资源,其参与海外竞争有悖“竞争中立”原则。TPP坚持了此种一贯逻辑。由此,按照TPP的规则逻辑,国企在海外竞争将处于整体劣势状态,而国企又恰好是中国企业海外竞争的主体。这无疑是有计划地将中国国企排除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之外。TPP所建立的“竞争中立”规则,实则是单向度地对中国国企参与海外竞争予以限制。可事实上,中国企业参与海外竞争,目前主要依托实力雄厚的国企进行。此种以“竞争中立”为名排挤国企的集体行动,将使中国国企开拓海外市场、从事海外竞争面临更大困难。
多年来,中国国企改革一直在“效仿美国”的自由市场道路上前进,“国企改制”就是践行此种道路的明证。中国曾经以为,只要将国企改造成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让其走向市场,国企就不会被视为政府的经济特权模式。相应地,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讲规则的”国际社会也会对中国国企予以公平对待,不会动辄实施反垄断、反倾销、反补贴……可事实证明,“国企平等竞争论”只是中国决策者的一厢情愿。一方面,在国际竞争环境中,无论中国如何将自己打扮成“市场经济家族”的一员,欧美的竞争政策制定者似乎并不买帐。例如,直到今天都不认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断以此作为在经济政策上“压制中国”的藉口。有意思的是,最近欧盟还因国资委同时控制若干央企,而将其共同控制的央企视为关联企业予以反垄断法规制,完全不顾《公司法》第216条的排除规定①。欧盟在这一问题上,强烈地表现了其对法治的傲慢,以及对中国立法主权的蔑视[3]。TPP所设定的竞争中立政策,无疑再次将国企的海外竞争打入冷宫,按照其所设定的竞争政策,中国国企无法展开海外平等的商事竞争。如同媒体报道的那样:“美国通过TPP谈判可以对中国东盟FTA(自由贸易协定)起到制衡作用,削弱中国经济在该区域的影响力,确保其东亚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一旦谈判达成,美国将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制定新的规则。另一方面,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在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降低的同时,对区外经济体则构成更高的壁垒,会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美国积极推进TPP的根本战略目标,就是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源版图,重新构建信用体系,继续保持美国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4]尽管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可能改变了对TPP的旧有立场,但中国仍需反思此前一贯坚持的“经济道路效仿西方”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其实,不仅中国国企的海外竞争受到制度性歧视,即使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其海外竞争也不断受到各种阻碍。例如,华为等民企海外收购困难重重,就是明证。
可见,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深刻的政治烙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很强的反作用力。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做大做强国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此前国企政策的重整,这是一种“不唯西方”的经济上的道路自信。中国有自己庞大的内部市场,如同我们在政治道路上独立自信一样,在经济道路上同样也应坚持自信。既然《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有制是中国主导的经济形式,我们何必遮遮掩掩,偏要将自己打扮成“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因此,中国应当大胆地坚持《宪法》设定的经济道路,坚定地“做大做强国企”,完全不必担心此种对《宪法》的坚持会影响我国国企的海外扩张。这是因为,在此种制度背景下,他国企业是否选择与中国或中国国企合作,是其自身的商业判断(business judgement)问题。换言之,认同中国经济道路的他国企业可选择参与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包括国企)合作;不认同此种经济道路或国企形式的他国企业,可以选择拒绝与中国国企合作。选择何种政治区域的何种企业进行交易/合作,这本身是企业的商业判断问题,应交给商主体自决。若某些国家因中国国企的立法模式和立法政策,选择放弃与中国国企进行交易,这也是其商业决断权,中国不必太在意——时间会改变或习惯一切。在商业与政治日益合体的现代,企业不仅是商业的工具,也是政治的工具。如果中国最好的企业是国企,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是国企,最安全的企业也是国企,那么,任何拒绝与中国国企进行交易的企业或国家,只会扩大其自身的商业风险,加大其交易损失的可能性。这是非理性的。
因此,在TPP等西式“反国企”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强调国企的核心地位,体现了经济道路上的充分自信,这也可视为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韬光养晦”经济外交政策的顺势微调。
二、党组织如何参与公司治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党组织如何参与公司治理?诸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政治参与”还是“经济参与”?是只把握政治方向,还是也参与经济/商事决策?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整体参与”还是“个体参与”,是“集中参与”还是“分散参与”,是“全部参与”还是“局部参与”?以及这种参与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是否会改变中国国企发展的“市场化”方向?
笔者认为,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其所理解或设计的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的模式,在具体实施/执行时,可能会存在以下争点。现结合《公司法》的规定,对有关争议问题,学理解释如下。
(一)政治参与Vs.经济参与
习近平同志认为,党组织参与国企的公司治理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原则”。所谓政治原则,是指政治活动的根本准则。但这是否如同学者理解的那样,意味着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只是把握其“政治方向”?从而延续此前党对国企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的安排?②对此,笔者认为,很难如此区分处理。而且,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简称《党章》)第32条的规定,党组织对企业治理的参与,不仅仅只是政治参与,其在发挥“政治核心”的作用时,需要参与企业的业务决策——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只有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党组织,才强调其不能参与领导本单位的业务工作——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监督,不领导本单位的业务工作。③实际上,只要党组织参与了公司治理,就很难区分其参与是“政治参与”,还是“经济参与”?即便是政治方向的把控,也需在经济决策中进行及实施。因此,很难将此种“参与权”仅仅局限在“政治参与”的范畴。尤其在国资委日益强调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而董事长又广泛参与公司经营之情形中,如何将党组织的行为限制在政治参与方面?确实很难实现。
学者主张将党组织的参与限定在政治参与方面,可能有试图保持公司治理纯粹性的考量。虽然将党组织的参与限制在“政治方向”把控方面,可能有助于国企保持“经营权的独立性”,有助于其在具体营业时,独立进行商事判断、提高商事决策的效率,尤其符合“自由主义公司法逻辑”,但却未必完全吻合“政治性公司法”之本意——通过经济参与实现政治领导。因此,在实务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否就“商业判断”事项发表意见,确实是一个核心问题。若党组织在参与过程中不对商业判断事项发表意见,则其参与公司治理只是为了接近并取得“政治监管”的信息,此种治理参与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若其参与具体的商业判断,则还会衍生出是否具备商业判断的能力以及应否承担判断失误的法律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企业治理事项的多维性而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很难不进行商业判断。事实上,党组织对经济决策的参与、判断可能会是多层次、多向度、综合性的过程,既包括判断的权利,也包括判断的义务。其中,政治性判断是义务,合规性和商业性判断是权利。这种判断大体至少包括以下层级/内容:
其一,业务决策的政治性判断。党组织在参与公司治理时,应当对业务决策是否符合国家以及党的方针政策,是否背离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直接判断。这是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的“判断义务”。例如,国家进行去产能的供给侧改革时,判断国企新增投资是否符合国家去产能的政策,是否存在扩大落后产能的投资问题?这是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通常所说的党组织对企业经营政治方向的把握。《党章》第32条也明确规定了此种参与的内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其二,业务决策的合规性判断。党组织在参与公司治理时,还有权对企业的业务决策是否违规提出意见。但此种合规性判断,应理解为权利而非义务。虽然党组织主要进行政治性判断,但不意味着党组织发现企业决策违规时,不能提出异议,予以制止。只是因为“合规判断”是专业性判断范畴,企业内部有专门机构从事合规判断事项,将合规判断视为党组织的义务,可能因党组织成员构成的特殊性,难以完全承担此种义务。因此,宜将此种判断理解为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的权利。《党章》第32条同样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那么,从《党章》的角度而言,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非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党组织应有权予以制止,这同样验证了合规性判断可能应配置为权利。当然,从法律公知的角度而言,法律一旦制定就推定为所有人知晓,党组织有义务维护法律的权威。因此,合规性判断中也可能包含了义务性因素,从而呈现出一定的复合特色。
其三,业务决策的商业价值判断。党组织对业务决策商业性之判断,也应理解为权利而非义务。一旦党组织发现公司某项业务决策对公司存在巨大的商业风险,有权对决策层提出建议,但最终业务决定应由决策层定夺。党委的此种商业判断,更像“建议权”。
由于党组织要参与公司治理机构的决策过程,因此,此种参与就不可能只是一种“事后监督”。有人认为党组织的参与只能是一种事后的监督参与,主张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构,以排除党组织对公司经营决策的不当干扰。这可能弱化了党组织对不当决策的事前规制。
此外,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原则”,是否等同于“法律原则”?是否意味着应修改《公司法》的相关立法,进一步明确党对国企领导的重要性?对此,尚可进一步讨论。
(二)集中嵌入Vs.分散嵌入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应以“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方式”进行,要落实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这就意味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一种“组织性参与”——党组织需要参与到公司治理机构之中,而非仅仅是“事件性参与”——党组织仅参与讨论公司内部经营决策事件,其本身并不进入公司内部治理机构。
当然,此处所谓“党组织”是何种含义,可能还会存在争议,是指企业内部党委成员/党委机构,还是市一级的党委组织?若属后者,显然存在参与困难,因此,宜限缩解释为“企业内部基层党组织”比较妥当,这也符合《党章》对企业基层党组织的界定。此外,此种“组织的参与”与“组织成员——党员的参与”有明显不同,当指“党组织”作为一个主体的“集体参与”,而非仅指其中个别成员个别性地兼任公司治理机构中的某些角色。当然,如何明确基层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定位,可能存在较大困难,甚至与《公司法》存在某种协调上的难题,尚需仔细斟酌。
通常而言,党组织对国企内部治理的“组织性参与”,可能存在两种供选方式:
其一,集中参与。党组织本身作为一个公司内部治理中的决策主体,在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传统法定机构外,对公司内部治理事项进行独立决策。简言之,在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决策之前,先由党委进行决策,经党委通过之后,方才提交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决议。此种参与方式独立、党委控制有效,但可能会影响公司治理机构的决策效率,也可能影响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成本。此种参与方式需要明确党委本身在公司内部的法定地位,当党委决定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决定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何者具有优先效力?而且,此种集中参与方式,能否理解为已经融入了公司治理,也会存在疑问。
其二,分散参与。党组织成员分散到公司内部各种治理机构中去,融入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分散地行使党组织对企业的领导。此种方式可以减少公司内部决策链条,从而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的效率。但分散参与,党员在各个公司内部治理机构中,可能未必能居于“多数地位”,难以确保党组织“领导权”的实现。因此,集中参与可能会是事实上的优选方案。
以上市公司章程修改为例,大多也采取了传统公司治理机构之外集中参与的方式,在其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党组织的地位和职权。当然,也还可能存在将党组织整体融入现存公司机关的“集中参与”方式。例如,有人主张将党委融入某一个公司内部监督机关,同时,赋予监事会类似于德国法上的人事任免权,以维持党委作为监督机关的权威地位④。这可能也是一种务实的策略,但其缺陷在于,监事会主要是事后监督,难以确保党组织事先就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如此操作,可能尚需修改《公司法》赋予监事会对重大问题的事先决策权。
(三)评价体系:有责任Vs.无责任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进行评价?众所周知,当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机构的一员、行使特定的治理权利时,必然需要承担特定的治理责任。习近平同志在其讲话中也初步建立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评价体系——强调要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这十六个字将事实上成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评价体系。简言之,要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组织定位、要充实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人员构成、要明确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职责、要严格规范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
就监督评价而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能面临双重评价的问题:其一,参与公司治理的党组织,要接受党组织系统内的评价。此种评价多为政治性评价,考核党组织的忠诚度可能是其核心内容。其二,参与公司治理的党组织,还要接受公司法上对公司治理机构的评价。此种评价多为商业性、合规性评价,重在考核党组织履职行为是否到位,监督是否严格。
(四)回归社会主义Vs.放弃市场化改革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否意味着中国回归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已经放弃国企改革的市场逻辑?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答案是否定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只是强化了党对国企的监管,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因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一以贯之。是故,不必担心中国在国企改革中会或已经完全放弃了“自由主义道路”,国企的市场化改革仍会在“党组织强力介入公司治理”的同时进一步深化。显然,按照“政治性公司法”的逻辑,此种市场化改革与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是并行不悖,且需继续一以贯之。可见,“政治性公司法”试图建立的国企模式是——内部党委监管集权、外部市场自行负责的模式。如同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联姻一样,党组织监管也可与市场经济模式联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能是大型国企/央企经常出现监管失控,酿成巨大治理风险所诱发的制度改进。虽然,此种改进的效果尚有待公司治理实践检验。
当然,对国企是否应当继续传统的“自由市场式”改革,仍存在较大的可探讨空间。中央的有关文件似乎是采取分类改革的策略,让商业类国企更市场,让公益类国企更公共,但这一改革逻辑仍不十分彻底。笔者主张国企改革应当坚持更彻底的“公法逻辑”,逐渐放弃“私法逻辑”,无论是公益类还是商业类国企,都应当适用“公法规制”,只是商业类国企在从事市场竞争行为时,要接受竞争法规管,受到“双重规制”。因此,“自由”不应是国企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规制”才是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
三、需要修改公司法吗?
当中央决定走向“政治性公司法”——强调国企的重要性以及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的重要性时,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修改公司法,以回应上述需求?笔者认为,长期来看,答案是肯定的。这不仅是因为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讲话,更主要是因为国企本身的特殊性——公共性。首先,国企的公共性要求国企在全部企业法领域应当被单独对待,国企应当撤出公司法的一般调整;其次,国企的公共性还意味着,在公司治理上,国企确实与其他企业形式存在差异,国企公司治理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烙印。这意味着公司法中有关党组织的普适条款也许需要微调。
(一)作为公共企业的国企:大修公司法?
国企是以国有资产/公共财产设立的企业形式,无论其是否从事商事营业,其功能或者财产的公共性都不同于一般私企。为此,各国立法大多对国企予以特别调整,多以公法的逻辑规制国企的设立、治理及外部行为,以提升国企的透明度,最终实现“为人民服务”(working for people)的目的。国有企业法因此成为一个特别法域,在美国公司法中,也属“特别公司法”范畴。虽然在某些规整领域,国企可能也适用普通公司法规则,但国企不同于普通公司,需要实行特别规制,要对公众负责而非仅对股东负责,这已属共识。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因国企长期效率低下,“效率改进”成为其首要追求目标,尤其是在现代企业制度转型过程中,国企一直被视为普通商事公司(common business corporation),立法者和国有资产监管者也习惯于用商事公司法的方式规制国企。因此,追求商业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国企的首要目标,这导致国企的公共功能未能完全开发并得到充分发挥。长远来看,国企应撤出公司法,予以单独调整[5,6]。所谓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因而给公司法造成无尽困扰的问题,也许可以迎刃而解。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国企没有必要单独立法调整。⑤
此外,有人主张对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进行分类对待——在不同类型以及不同行业企业中,党的领导的核心性应有所差别。例如,公益性国企与商业类国企应区别处理⑥,关键行业与非关键行业应区别处理。对此,笔者不敢完全认同。按照笔者主张的国企“统一规整”逻辑,无论是公益类,还是商业类国企,均系以公共财产设立,都应采取同样的规制方法予以对待。尤其在公共监管(党组织参与)方面,似应同样处理。至于关键类与非关键类行业,是否因为行业的重要性不同,党组织的地位和核心力也会有所差异?言下之意乃党组织是否参与治理以及如何参与治理与行业的“重要性”有关。此种理解似也欠缺足够的解释力,不符合笔者所谓国企“统一规制”的逻辑。
(二)非国企如何协调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微调公司法?
国企撤出公司法可以轻松解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给传统公司法带来的困扰,另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公司企业的党组织是否也应参与公司治理?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来看,主要强调了国企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并未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普遍扩展到所有类型的公司,但公司法实际上采取了“普适主义”的方式,《公司法》第19条对党组织的法律调整,并未局限于国企,但上述法条并未得到很好执行。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不设党组织,更毋言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条件。在很多私人公司,党组织可能存在,但基本居于不重要地位。因此,当国企撤出公司法后,《公司法》第19条是否仍有必要维持存在,确实值得讨论。
一种可行的学术主张是修改《公司法》,设计弹性条款,允许公司章程对党组织是否以及如何参与非国企治理进行自决——由非公司企业的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时根据每家公司的不同情况选择决定⑦。此种思路相较于《公司法》第19条来说,可能会使党组织对非国企内部治理的影响权实质被弱化,但不失为一种务实的设计。尤其是考量到党组织在外资企业普遍贫弱的现实,如果上层决策者不是试图改变此种因企业类型不同而事实上被区分对待的状况,则“由章程设计/选择”可能是可以接受的道路。而且,《公司法》第19条在论及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只提到了“根据党章”参与公司活动,未提到“根据章程”参与公司活动,未充分体现党组织在参与公司内部治理活动时对公司章程的尊重。因此,引入根据公司章程决定参与公司治理的规则,恰好体现了“党章规定”与“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机融合,是尊重公司章程的表现。
四、结论
当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党组织在国企治理中的重要性、强调国企本身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时,也许我们可以将“重视国企”的公司法模式称为“政治性公司法”。“政治性公司法”之提出,意味着处于西方公司法包围过程中的中国开始思考公司治理的民族特色/政治特色,意味着我们认可企业的发展不只有国际上的普适道路,如同政治、经济发展的道路可以多元化一样,公司治理虽有趋同,但仍存在多样性之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有权/都可以尝试“多元化”的公司治理路径。
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国企“公共财产”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国企甚至一般企业的治理,应呈现出更独特的特点——企业/国企应更多地凸显其公共性/人民性的一面。“重视国企”/“重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本身存在宪法和公司法上的依据,也是中国应对TPP类“西方式”的“国企压制”,彰显“经济发展道路自信”的重要方式。
当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仍应平衡好企业治理效率与治理安全的关系,公司治理之本质在于凸显“效率经营”。尤其在国企决策效率本身仍有待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设计,不应成为企业“效率化经营”的障碍,不应因此无谓地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
注释:
① 《公司法》第216条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② 华东政法大学顾功耘教授在2016年中南大学有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学术讨论会议上,坚持并阐释了这一观点。
③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2条规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领导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监督,不领导本单位的业务工作。”
④ 例如,湖南大学肖海军教授在2016年中南大学有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学术讨论会议上,持有此种观点。
⑤ 例如,四川社科院周友苏教授在2016年中南大学有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学术讨论会议上,坚持此种观点。他认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目标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核心是公司制度,不是对法人治理结构的取代,党组织可以以融入型和嵌入式为主要特点,必须要确保国企保值增值。并且,没有必要制定国有企业法,用公司章程解决问题足矣。
⑥ 例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朱慈蕴教授在2016年中南大学有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学术讨论会议上,持有此类观点。
⑦ 例如,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顾功耕教授、中南大学法学院蒋建湘教授在2016年中南大学有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学术讨论会议上都持此种观点。
[1] Hansmann H, Kraakman R. 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0, 89(2): 439−468.
[2] 蒋大兴. 合宪视角下混合所有制的法律途径[J]. 法学, 2015(5): 39−51.
[3] Amy Beckingham, Simon Cooke, 张清彦, 等. 欧洲委员会对涉及中国国企交易展开详查[EB/OL].http://opinion.caixin. com/2016-06-20/100956508.html, 2016−06−20.
[4] 中国被孤立!被“TPP”拒绝入局,怎么破?中国企业家[EB/J]. http://tech.163.com/15/1006/13/B58FLD3N00094ODU.html, 2015−10−06.
[5] 蒋大兴. 国企应从公司法中撤退——从“商事公司”向“公共企业”演进[J].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13, (12): 19−25.
[6] 蒋大兴. 国企为何需要行政化的治理——一种被忽略的效率性解释[J]. 现代法学, 2014, (5): 14−28.
Political company law: How party organization participat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JIANG Daxing
(School of Law,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Political company law” is a nickname of company law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arty organization to participat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share certain family resemblances with “statism-oriented”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s. The proposal of "political company law" means that China, a country influenced by western company laws, has begun to reflect on nation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ince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public properties”,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supposed to particularly highlight their public and people-oriented natures. In essence, some evidences may also be found from constitutions and company laws that “importance shall be attached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importance shall be attached to party organization to participat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respond to limits of TPP up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highlight “confidence about path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be sur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ts involved in the governance. The ess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highlighting “efficient operations”. It is more improper to hinder enterprises’ “efficient operations” because of the party’s involvement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since the decision-making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main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or needlessly increase companies’ operating costs.
political company law; party organization; state-owned business; company govern
[编辑: 苏慧]
D912.29
A
1672-3104(2017)03−0027−07
2017−01−10;
2017−04−06
蒋大兴(1971−),男,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