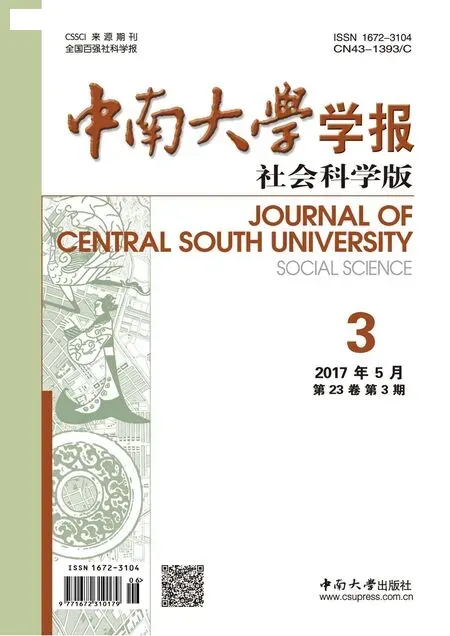论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及其困境
2017-01-12吴鹏
吴鹏
论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及其困境
吴鹏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青年黑格尔从古典经济学那里继承了“劳动”概念,并在劳动论题的理解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他把古典经济学中最为核心和基础的经济学概念“劳动”纳入哲学的理论视界,将其运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等问题的哲学思考,使劳动概念从形而下的经济学层面转换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对劳动的“物性”的单向度理解,凸显了劳动概念的“人性”内涵。但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作为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的物质生产活动也只是“绝对”彰显自己的一个环节,如此以来,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必然无法挣脱“绝对精神”的黑洞。马克思深刻地洞见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困境与局限,从立场、方法和观点这三个方面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展开了整体性的批判,成功地把“劳动”从绝对精神的笼罩中拯救出来,作为自己整个世界观和全部哲学的思想地平。
黑格尔;马克思;劳动;古典经济学;主奴关系;市民社会;异化
在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中,劳动概念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每当谈及黑格尔哲学,我们首先、经常和习惯重视的都是一些抽象宏大的哲学范畴,如“绝对精神”“辩证法”“逻辑学”等,劳动概念在现有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中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目前,学界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关注,要么淹没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宏大体系研究中,要么只是在研究马克思的劳动论题时进行比较并主要批评其缺陷。诚然,这两种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理解以及劳动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地位。但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于此,那么我们就还没有真正面对问题本身,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本身还缺乏一种整体、全面和深刻的把握,当然也就无法真实地切中劳动概念背后所牵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因此,深入探赜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是一项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理论工作,它既能够直接开显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本真面貌,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思考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劳动概念的出场契机
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劳动”第一次获得理论上的关注应该说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理论沉思、实践和制作。所谓的“制作”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亚里士多德对这三种活动形式的层次进行了划分:理论沉思居于人类活动的最高层次,实践活动居于中间位置,制作则处于人类活动的最低层次,是一种不自由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由卑贱的奴隶来从事的。可见,亚里士多德非常轻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在他看来,劳动是一种卑微的、低贱的、消极的人类活动。即使到了中世纪,“劳动”的地位也没有获得任何提升,在中古基督教的正统观念中,劳动就是对原罪的一种忏悔和救赎,没有任何的肯定意义和积极价值。虽然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对待劳动的态度有所转变,承认劳动的独立价值和正面意义,但是,劳动至此还没有获得学理意义上的指认和确证。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劳动的性质和特征的巨大改变,伴随着分工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逐渐摆脱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具体形式,在一般或抽象的意义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在这种转变发生后,劳动的重要意义就彻底凸显出来。劳动的社会意义的凸显必然要求其在理论层面获得一种价值确证,这项工作是由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探讨国民财富的本质问题中完成的①。亚当·斯密把抽象掉各种特殊规定性的“劳动一般”——“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1](21)——视为社会财富的本质规定。“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 西。”[1](22)可以说,当斯密把“劳动一般”或直接说是“劳动”规定为财富的根本特质时,“劳动”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才获得了真正的出场。
虽然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表面到处散发着抽象性和思辨性,但是理论背后却有着强大的历史现实作为支撑,恩格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1](42),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现出他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这种强烈的现实感表现为他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关切和思考,其中就包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及其理论形态即古典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指认,“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2](102)。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黑格尔为什么会关注国民经济学并站在它的立场上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回到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及其思想的发展历程之中。
虽然黑格尔生活的德国还处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中,但此时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相继发生,革命的火光和思想也传入了德国,黑格尔曾为纪念法国大革命在图宾根神学院种下“自由树”,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和憧憬。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及对“实证”基督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把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视为当前的社会和国家具体改造的一种永久的标本和楷模,希望通过重建伦理共同体以恢复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他认为古代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范例;古代固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应该恢复,而复兴伟大的古代,正是当代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任务”[3](80)。黑格尔把古代的复兴和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关联起来,希望这种政治理想能够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取得政权后转化为社会现实②。但是1794年的“热月政变”使法国大革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被摧毁,“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而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 治”[4]。法国大革命的转折推动了黑格尔思想的转变,此前他把罗马共和国灭亡到他当时的历史时期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存在都视为人类历史的没落阶段,寄希望于法国大革命来恢复古希腊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现在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基本的、无可改变的事实,开始认识到他必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分析处理这个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性”[3](88−89)。
当资产阶级社会成为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资产阶级社会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时,黑格尔就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事实相联系。此时,黑格尔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到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实证性”势力——经济力量,卢卡奇指出,“黑格尔是德国这个时期的唯一哲学家,曾经由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问题而认真地分析过经济问题”[3](84−85)。之所以关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问题,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包含着共同性和相互性的种子即“需要的体系”,能够为伦理共同体的重建提供可能性。通过阅读青年黑格尔早期的著作和手稿以及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叙述,我们能够基本确定,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就阅读过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到了耶拿时期,经济学在黑格尔那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黑格尔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个时期,他认真阅读并研究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卡奇认为,“对亚当·斯密的研究很可能是黑格尔思想进程中的转折点,对作为人类活动的核心模式、作为实现主客同一性的主要方法、作为取消客体的僵死性的活动的劳动问题的理解,能够显现出黑格尔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惊人的相似性”[5](172)。因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在耶拿时期获得了正式出场,并在以后的思想和著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劳动概念的哲学理解
根据黑格尔自己的哲学著作及其撰写历史以及后来洛维特的表述,我们可以确定,黑格尔一生主要开展过三次以劳动为主题的思考和讨论:第一次集中表现在耶拿时期的哲学讲演和哲学手稿中,具体包括《伦理体系》和《实在哲学》等,通过劳动概念展开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以及异化和目的论等问题的思考;第二次集中表现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劳动概念为中介展开了“主奴辩证法”的讨论;第三次集中表现在晚期著作《法哲学原理》中,以劳动概念为环节展开了市民社会辩证法的讨论[6]。在这三次讨论中,黑格尔通过劳动概念,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三个问题入手,对此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思想梳理和理论表达,基本上就可以构成黑格尔关于劳动概念的创造性理解的全貌。
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劳动能够得以开展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劳动主体和劳动对象,主体与对象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理解劳动概念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在《伦理体系》中,黑格尔就从主客体的关系上对劳动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劳动就是对“客体的毁坏”“直觉的毁坏”。但是,这种“毁坏”并不是纯粹否定意义上的毁灭,而是包含着肯定性的否定,是一种“塑造性的破坏”,即赋予客体另一种形式取代其原有的状态。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劳动的规定更加简单明了:“劳动进行塑造”,“对劳动者来说,对象具有独立性,正因如此,这种与对象之间的否定关联转变为对象的形式,转变为一个持久不变的东 西”[7](125)。简而言之,劳动就是人们采取行动给对象以定形,使对象获得独立存在的外观,具有“我”的规定性,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塑形”或“定形”活动。对劳动作“塑形”活动的理解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史渊源,其直接来源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事物做出了“形式”与“质料”的划分: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包含着质料,一切变化都需要一个基质,变化就在这个基质上进行,但质料只是潜能,是一种潜在性和可能性,单纯的质料并不能成为真实的存在,只有获得了形式才具有现实性,因此,质料能够成为真实的,要归功于形式。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形式的获得就来源于劳动,人们通过劳动赋予无限杂多的自然“质料”以“形式”,使其成为一种持久不变的作品,从而满足劳动主体自身的需要,这样一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了为我之物,与人无关的自在的世界转变为人在其中的人的世界。所以,劳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活动或中间环节,在这个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获得了重塑,实现了否定性的统一。
但是,在确立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中,劳动又促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这种分离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本能的、动物式的生活方式的摆脱。黑格尔认为,劳动造成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是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自然的、本能的、动物式的生活方式就是通过直接消灭对象、单纯否定对象来达到自然欲望的直接满足。而人类却能够将劳动置于欲望和满足欲望的中间,通过劳动塑造自然质料的形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满足需求的活动是一种间接性的活动。而且,“劳动是一种被遏制的欲望,是一种被阻止的飘逝”[7](125),在劳动过程中,人们(特别是“奴隶”)并不会无限地放任纵容自己的欲望,相反是获得了“欲望的节制”,劳动者从自然欲望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这样一来,劳动者在塑造物品的同时塑造了自己,在陶冶事物的同时陶冶了自己,在人化自然的同时教化了自己。在这个塑造过程中,劳动主体超出自身的自然性和特殊性,发展为一种精神性和普遍性的存在。
在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劳动引介出人与自我的关系问题,劳动不仅表现为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客观方式,更重要的是,劳动是主体理性获得自我形成、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活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对劳动与自我意识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指认,这个指认集中表现在“主奴辩证法”中。自我意识经过诸环节的运动——“自我意识本身→生命→自我意识与欲望”[7](111−117)——发展到“主人与奴隶”阶段。在“主奴关系”中,人们以往生活中的“需要——劳动——享受”的三段论,就具体化为“主人的需要——奴隶的劳动——主人的享受”。由于物的独立性,欲望自身不能够直接在享受中得到满足,但是主人却做到了欲望没能够做到的事情,即以享受为目的,通过对于物的纯粹否定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主人之所以能够做到,秘密就在于,他把奴隶置放于自己与外物之间,“但物同时也是独立于奴隶的,所以奴隶在他的否定活动中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将物消灭掉,换言之,他仅仅对物进行加工改造”,“通过这个中介活动,主人与物之间的关联转变为一个直接的关联,转变为对于物的纯粹否定,换言之,这个直接的关联是一种享受”[7](123)。因而,原本独立于主人的外物,就转变为满足主人欲望和供应主人享受的手段,这样一来,主人就仅仅与物的非独立性联系在一起,而物的独立性就让渡给奴隶了。
此时,一种新的情况就产生了:在奴隶方面,他直接与物的独立性打交道,并通过劳动来加工改造对象,使对象成为一个持久不变的东西,“在对物进行塑造时,仆从意识就认识到自为存在是它自己固有的自为存在,认识到它本身就是自在且自为的”[7](125),通过劳动,仆从意识由原来“不由自主的意向”转变为“自主的意向”,获得了一种独立于物的自我意识。相反,在主人方面,欲望的满足是以奴隶的劳动为中介的,他在欲望的追逐中不断把物的独立性让渡给奴隶,并依赖于奴隶的劳动及其产品,原本自为存在的意识现在变成了一种依赖意识。由此,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主人成为奴隶的奴隶,奴隶成为主人的主人,奴隶在劳动中获得了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成为一个自为存在着的意识。但是劳动并不止步于对个体自我意识的确证,它的目标是“一个已经得到承认的自我意识,它通过另一个自由的自我意识获得它的自身确定性”[7](216),因此,个体的自我意识就要积极地与另一个自我意识打交道,并在其中获得一种自我确证。在这里,个体的行动不仅仅具有特殊性,而且还具有普遍性,“一个个体的所作所为,作为全部个体的普遍技能和普遍伦常存在着”[7](217)。此时,个体的劳动也由原本具体的特殊性走向了抽象的普遍性,“个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中已经无意识地从事着一个普遍的劳动,同样,他又自觉地把这个普遍的劳动当作是他自己的工作”[7](217−218)。这时,黑格尔通过劳动潜移默化地将问题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拓展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开启了关于伦理实体特别是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论思考。
在前市民社会中,分工并没有获得普遍实现,劳动表现为主体单独完成对劳动对象的改造,这个过程从劳动者个人作用于对象开始,到劳动者制造出劳动产品时结束,劳动产品完全是劳动者个人的作品,虽然此时的劳动是一种比较原始和低级的创造活动,但是个人却在劳动产品中保留了自身的整体性、个体性和具体性。进入现代市民社会,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分工的加深,“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 单”[8](210),劳动从具体转变为抽象,从个体转变为一般,个人的具体劳动转化为人类的抽象劳动,抽象性构成为劳动的基本特质和一般规定。此时,个人已经无法通过个体单独的劳动来满足自己多样化的需要,他必须要与他人打交道,与他人进行交换。因此,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个体劳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普遍的意义,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交换体系,也就是“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 系”[8](203)。在这个“需要的体系”中,虽然个人出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但是他的劳动及其成果却构成了满足他人需要的手段,同样,他人的劳动及其成果也构成了满足他的需要的手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原本的莫不相干转变为现在的息息相关。“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8](210),亚当·斯密认为这种局面的背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而黑格尔则指出,这种局面是由劳动的抽象性所造成的市民社会的辩证运动,即市民社会的辩证法,由此,那只作为“自在之物”的“看不见的手”的秘密就解开了。而且,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劳动不仅中介了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提升了人类的教养。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劳动使人们产生了“一般的勤劳习惯”,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活动,使其顺应自然的规律和“物质的性质”,更主要的是,使其能够适应别人的任性,习得“普遍有效的技能”,从而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真正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指能做别人做的事而不表示自己特异性的人”[8](203),在劳动的“实践教育”中,个人的特殊性被打磨并上升为一种普遍性,从而使人作为人能够真正成为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劳动又将人的自我成长向前推进了一步。
总的来说,黑格尔在哲学层面上从一系列与“人”相关的重要问题出发,解读了劳动概念的内涵和实质,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对劳动的“物性”的单方面理解,凸显了劳动概念的“人性”内涵。在劳动中,主体首先和对象打交道,在对象上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赋予了周遭世界以人化的形式,以此将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且在对象中意识到自我的力量和能力,获得一种自我意识。当然,个体的自我意识必须与另一个自我意识打交道,在另一个自由的自我意识中获得自身的确定性,自我意识逐渐从个体上升到普遍。至此,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劳动中全部释放出来,构成了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总体性理解。
三、劳动概念的理论困境:从马克思的视角看
在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中,劳动概念获得了全新的“生命体验”,对劳动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劳动价值论中抽象掉具体规定性的作为国民财富之根本来源的“劳动一般”,而是拓展到与人的生存相关的诸领域中,劳动的“人性”展现出来,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这项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评价,“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101),这是黑格尔在劳动论题中做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但是,在肯定理论贡献的同时,马克思也理性地揭示了黑格尔劳动思想的困境和局限,并对此做出精确的判断,“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101)。在这里,马克思不仅直接指认了黑格尔劳动论题的理论立场,而且批驳了黑格尔劳动论题的思想方法和基本观点。其中,理论立场的批判是前提性和根本性的,而方法和观点的批判是阐释性和具体性的,三者相互支撑、互相融贯,共同构成了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整体性批判。因此,从马克思的视角来反观黑格尔的劳动论题,对于理解黑格尔劳动概念本身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既然“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在探寻他的劳动概念的理论立场时,首先就要追问什么是“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简单说来,国民经济学确立了劳动的核心地位,把国民财富的源泉从外在于人的存在物拉回到人自身,实现了经济学领域中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国民经济学所把握到的劳动是剥离掉具体规定性的抽象劳动,因而它对主体性的彰显和确立是流于表面的,其实质是通过抽象劳动对人进行新一轮的压制和奴役。“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2](18),把人之为人的基本特质仅仅看作是物的本质和源泉,在根本上消解了劳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对此,马克思进行了精妙的隐喻,“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1](136),这个英国人就是国民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由此看来,国民经济学家把人的劳动变成了帽子的本质,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纯粹从物的方面展开经济学研究,是一种抽象的实证科学的唯物论立场。受思想传统和文化特质的影响,黑格尔当然不可能直接继承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科学的唯物论立场,而是以德国哲学的观念论特质对国民经济学立场进行“形而上学地改装”,把作为物的抽象劳动神秘化为绝对精神的环节,“把帽子变成了观念”[1](136),以一种历史的观念论立场改装了科学的唯物论立场。但这种改装是有限和无力的,因为,无论是国民经济学还是黑格尔,无论是科学的唯物论立场还是历史的观念论立场,他们对人及其劳动的理解都是抽象的,在他们那里,个人总是受抽象所统治。因此,说“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是因为二者都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抽象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的基本事实,只不过国民经济学家站在科学的唯物论的立场上将其表达为“帽子”,黑格尔站在思辨的唯心论的立场上将其表达为“观念”,但“观念”也只是以神秘的形式表达着“帽子”所指代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立场都是非批判的,前者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后者是“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他对这种非批判的立场进行了批判,重新把“观念”变成了“帽子”,并且使“帽子”回到了“人”自身,克服了黑格尔的观念论,重新“返回”唯物论立场。但是这种唯物论不再是国民经济学家式的科学的唯物论,而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唯物论立场,站在这个立场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展开了批判,分析了作为商品的“帽子”所蕴含的双重属性——物的属性和人的属性,揭开了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划定了这种社会形态的历史界限,惊醒了国民经济学家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迷梦”。
与非批判的理论立场相适应的必然是一种保守的方法,古典经济学如此,黑格尔亦如此。古典经济学最大的特色就是运用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在经验科学的实证方法上获得关于社会经济事实的经验材料的整理和概括,这种方法“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9]。古典经济学以这些“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为平台,构筑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性逻辑,以经济学的形式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在此之中,劳动、分工、价值、价格、利润等概念变成了不动的、不发展的,一切矛盾性、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因素都被排除了,因而它在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保守性就不言自明了。与古典经济学的非批判的实证方法不同,劳动在黑格尔这里从属于思辨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思辨结构中,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它的身上承载着个体意识的成长和人类精神的发展——“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2](102),劳动作为人的活动,就被设定为精神(自我意识)的劳动,即“克服意识的对象的运动”;自我意识通过外化设定他物,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对象;自我意识通过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使他物又返回到自身之中。这里,劳动不是改造客观事物的现实活动,而是推动意识外化和扬弃外化的精神劳作,通过这种精神劳作,意识从抽象走向具体,从贫乏走向充盈。黑格尔构筑的这个自我展开过程遵循着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他“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1](19),作为精神劳作的劳动,就是思维的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它能够到达一种观念的具体。与古典经济学相比,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或“概念思维”的概念辩证法具有明显的批判外表。但是,由于这个概念辩证法背后的支配力量是作为唯一主体和实体的绝对精神,无论这种运动表现出多么丰富的环节,对自己展开多少次批判和否定,当意识经过诸环节发展至最后的“绝对知识”时,自我意识的历史性运动就变成了超历史性的存在,在此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实现了“合流”,辩证法真正的批判性不可能发挥出来。对于这种方法,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评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19)。马克思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直接切中这个“具体本身”,在这里,劳动成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得以实现的根基,而不再是“绝对”的一个注脚。因此,马克思也就无需对劳动进行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以服务于终极的、永恒的形上目标,他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异化劳动本身,并对其展开尖锐深刻的批判,通过对劳动的批判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限度。在这个过程中,非批判的思辨辩证法被马克思改造成为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让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真正发挥出来。
由于立场和方法上的非批判性,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基本观点也只能是非批判的和保守的,而且这种非批判的观点与古典经济学是分不开的。从表面上看,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劳动的经济学运用与黑格尔对劳动的哲学理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这种明显差别背后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一致性,这种一致表现为: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都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合理劳动”,只不过二者应用的领域不同罢了。所谓“合理劳动”,指的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和现实化,就是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的一般劳动,它在实质上是关于“异化劳动”的合理化解释。具体说来,黑格尔对“合理劳动”进行了形而上学的运用,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局限和困境。首先,站在思辨的观念论立场上,“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101)。作为一种精神劳作,劳动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构成了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一个环节,换言之,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变成了绝对精神自己开展的一种“游戏”和“消遣”,人与世界的关系以精神的自我运动表现出来,劳动的主体、过程及其结果都变得神秘化和抽象化了。其次,由于劳动被看作是一种精神劳作,劳动的异化(在这里就等于对象化)就是理性自我实现的中介环节,从而获得了合理性和肯定性的意义。在黑格尔那里,异化就等于外化、对象化,从而异化的克服也是理性在自身中能够轻易完成的事情,一旦理性意识到异化就意味着意识到对象在自身之中,就意味着异化的克服,因为“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2](102),“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2](103)。因此,黑格尔即使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劳动给人们的生存境况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他仍然肯定异化的合理性,并对此作出合理性的解释,把资产阶级社会视为一个按照自身内在规律进行运动的客观整体,异化的产生和克服都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进行自我展开和自我调节的必然环节。对此,卢卡奇做出深刻的评价:“唯心主义辩证法把人类的整个历史转变成一个庞大的哲学乌托邦:在这个哲学梦境中,异化可以在主体自身中被克服,物质可以被转变为主体。”[5](333)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站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论立场上,把劳动理解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使它从思辨天国重新返回到现实大地。在劳动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诉诸精神的自我运动过程来表现,而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活动表现为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待异化的态度与黑格尔大相庭径,黑格尔以一种温情脉脉的肯定态度看待异化劳动,马克思则是以尖锐严厉的批判态度来对待异化劳动。马克思看到了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法领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反而受到其支配的社会事实,以及异化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顽固性,指认了异化劳动的社会根源就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消除异化劳动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此来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和有 限性。
在劳动的概念史上,黑格尔理应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他把古典经济学中最为核心和基础的经济学概念“劳动”纳入哲学的理论视界之中,并以此为质点来研究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生存的理论问题,使劳动概念从形而下的经济学层面转换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确证了劳动概念的“人性”内涵,使之获得全新的“生命体验”。但究其实质来说,他并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是与古典经济学结成理论同盟,共同论证抽象资本作为统治力量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对异化劳动的合理化解释,他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本身。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古典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局限和理论界限,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超越。
注释:
① 虽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一观点,但他的目的是确立“劳动创造财产权”的自由主义观点,他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确认了劳动的价值,本文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讨论劳动概念,所以肯定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开创性。
② 在当时的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都是卢梭的直接学生,他们幻想在法国恢复古代的民主政治,追求财产的相对平等,黑格尔幻想着雅各宾派革命党人的幻想能够在法国大革命中实现。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揭露了雅各宾派的英雄幻想:“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 卡尔·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3] 格奥尔格·卢卡奇. 青年黑格尔[M]. 王玖兴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156−157.
[5] Geor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M].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6] 卡尔·洛维特. 从黑格尔到尼采[M]. 李秋零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358.
[7]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先刚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8]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9] 卡尔·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82.
On Hegel’s concept of labor and its dilemma
WU P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Young Hegel inherited the concept of “labor” from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opened up a whole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thesis of labor. He brought the most core and basic economic concept of “labor” from classical economics into the theoretical vision of philosophy. Hegel applied labor to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human and nature, human and self, human and society and other questions which made the concept of labor shift from the level of physics economy to the level of philosophical metaphysics. This surpasses the one-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ing” of labor in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highlights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 nature of labor concept. But in Hegel’s philosophical system, as the basis of settling down and living in peace,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is only a link that absoluteness demonstrates itself. In this sense, Hegel’s concept of labor will definitely be stuck in the black hole of “absolute spirit”. Marx had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of Hegel’s concept of labor, criticizing it from position, method and viewpoints, then putting the “labor” out of the shadow of “absolute spirit”, and making it the thinking horizon of his whole world outlook and philosophy.
Hegel; Marx; labor; classical economics;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civil society; alienation
[编辑: 颜关明]
B516.35
A
1672-3104(2017)03−0013−07
2016−10−11;
2017−01−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实践辩证法研究”(13JJD720009)
吴鹏(1991−),男,河南信阳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