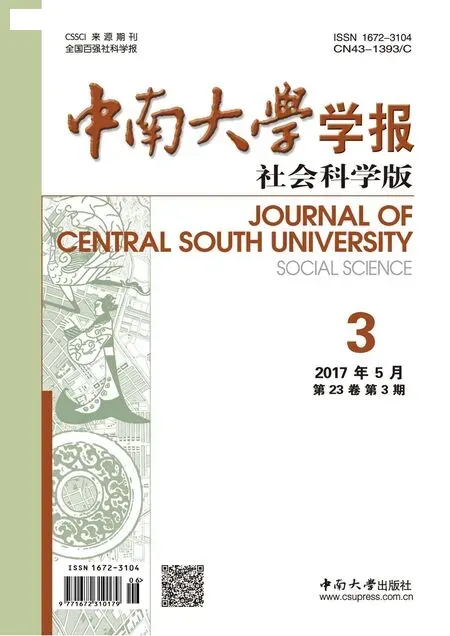现代德性幸福何以可能——兼论现代幸福观的哲学建构路径
2017-01-12张方玉
张方玉
现代德性幸福何以可能——兼论现代幸福观的哲学建构路径
张方玉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处于物欲化与世俗化的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对“何谓幸福、何种生活”的追问更为必要。三种建构幸福观的哲学方案具有深刻的代表性——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优雅生存”;生活哲学维度上的“可能生活”;人生哲学视域中的“德性幸福”。优雅生存、可能生活与德性幸福的内在精神相通,均是秉持了广义的德性论的思想内核,现代德性幸福将可能意味着中国幸福观的建构方向。
德性幸福;孔颜之乐;优雅生存;可能生活
在西方伦理思想上,雅典的梭伦通常被视为探讨幸福范畴的第一人,古希腊哲学中的“幸福论”由此诞生。而在古代中国,元典文献虽未将“幸”“福”二字连用,但却独特地形成了“福”“吉”“喜”“乐”等众多有关幸福的“字词族群”。幸福是个美好的词汇,同时也是一个涵义模糊的概念,人们仿佛并不需要来自学院派的理论与说教,就已经能够心领神会地各自追寻着自身的幸福。伴随着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物质文化产品日渐丰富,幸福概念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快乐的感觉、利益的获得、欲望的满足、社会的福利、成功的喜悦、奢侈的享受,如此种种的“幸福观”开始泛滥。于是在物欲化与世俗化的消费主义时代,对“何谓幸福、何种生活”的追问显得更为必要。
一、传统幸福观的表征符号:孔颜之乐
审视与反思当前社会中的幸福话题,构建新的幸福理论,为现代生活提供合理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审美趣味和生活境界,这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所应承担的神圣使命。新的理论建基于其社会现实条件与理论渊源,现代幸福观的建构自然不能割断其历史传统。当人们试图在历史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竟然难以找到“幸福”一词,更似乎缺乏一套系统完整的“幸福论”。与其形成鲜明反差的似乎是,西方幸福论的思想内容丰富、理论脉络完整。于是,在中国式幸福观的建构中,“言必称希腊”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在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体系下,众多研究者对于西方幸福观的论述如数家珍,诸如理性主义幸福观、感性主义幸福观、功利主义幸福观、基督教的幸福观、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作为最高善”、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阿奎那的天堂幸福、康德的“配享幸福”、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及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等西方伦理思想。当论及“传统语境中的幸福理解”时,有文章这样表述——“从英雄时代的幸福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再到基督教的来世幸福以及到启蒙以来的幸福观”,而对于中国传统幸福观只字未提,仿佛中国传统幸福观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在当下的研究文章中屡见不鲜。
那么,中国传统哲学中到底是否存在成熟形态的幸福观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孔颜之乐”即可视为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
幸福是人类生活的共同指向,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追求着属于自己的幸福。中华民族探寻幸福的历程是漫长而久远的。早在儒家的“孔颜之乐”之前,各种关涉幸福的语词已经相当丰富。在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经》中,卦辞和爻辞中大量出现的“元”“亨”“利”“贞”“吉”“喜”“福”等构成了相对独特的幸福概念;在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构成了相对系统的“五福”,这被视为中国最早有关“德福”关系的论述;在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福”“乐”“禄”“祜”“祉”等概念现实地展现了人们对于幸福的向往。儒家创设以后,孔子被尊奉为“圣人”,其思想与言行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论语·述而》篇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又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雍也》篇记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被视为儒者安贫乐道的基本生活旨趣,儒家“孔颜之乐”的德性幸福由此生发,并对后世影响深远。宋明理学对此大做文章,进而把“孔颜之乐”升格为“与天地同体”“与道合一”的高妙境界。
“孔颜之乐”构成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与榜样,此种人生之乐尽可能降低感性欲望的要求,摒弃世俗的功利幸福,从而成为儒者生活价值的精神导向。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此种人生幸福大约与苦行无甚差别,即便是儒家弟子也难以企及,但也正是这样一种纯粹的圣贤境界展现了儒家幸福观的核心所在。当然,“孔颜之乐”也并非孔子幸福观的唯一形态。《论语·先进》的记述中,孔子也对“曾点之志”大为推崇,这就是在暮春时节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向往。“曾点之志”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山水之乐内在相连,构成了儒家幸福观的另一种形态。后世所谓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调素琴,阅金经”,或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人生境界可以视为此种幸福观的精彩呈现。颜回、曾点是孔子门下德性出类拔萃的少数弟子,而“学干禄”大约代表着多数孔门弟子的追求。子张也是孔门的出色弟子,就曾直言不讳向夫子讨教做官得俸禄的途径,孔子对此种功利性的诉求也并不排斥,而是提出“禄在德中”,即要做到好学、谨言慎行、“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在这里,官职俸禄等世俗的功利幸福完全成为德性的副产品,所成就的是一种现实形态的德性幸福。因此,孔子的德性幸福既涵盖了理想层面的“孔颜之乐”和“曾点之志”,也包涵现实层面的“君子之禄”和“禄在德中”。到了孟子,以“孔颜之乐”为典范的德性幸福进一步衍化为“君子有三乐”,即父母兄弟的家庭之乐、无愧天地的内心之乐,以及教育英才的事业之乐。“君子之乐”可以视为“孔颜之乐”的更为大众化的版本。
在儒家传统文化的视域中,“孔颜之乐”是德性幸福的经典形态。在更加宽阔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视域中,儒家的“孔颜之乐”“君子之乐”,道家的“逍遥之乐”“至乐无乐”,以及佛教的“第一义乐”“极乐世界”,则分别代表了中国人严肃认真的德性幸福观、自然洒脱的浪漫幸福观和精神超越的宗教幸福观。在道家庄子的思想世界中,人生的逍遥境界构成了独特的美丽风景,“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展现出人生幸福的宏大气象。一边是坎井之蛙的快乐,一边是东海之鳖眼里的“大乐”,超然的心态、宽广的胸怀溢于言表。遨游于逍遥天地、混沌世界,庄子以“心斋”“坐忘”的神秘体验和精神修养方式,寻求达到宁静的心灵境界;而“达道”“体乐”“通神”则呈现出道家“真人”“至人”的理想人格形象,其理想人格经由“法天贵真”最终实现所谓的“天乐”与“至乐”。佛教幸福观的宗旨可以称为“与乐拔苦”,就是要使芸芸众生从苦海无边中解脱出来,实现“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或者进入所谓的“极乐世界”。佛教幸福观在实现的路径上既呈现为外在超越的路向,也呈现为内在超越的路向。无论是证得涅槃进入佛国,还是往生极乐世界,总是寄希望于终极的彼岸世界。而中国化佛教的典型——禅宗则表现出种种入世的精神,由不食人间烟火转向滚滚红尘,并强调依靠自我本心的觉悟获得解脱。
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中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幸福观的缺失。如果一定要选取一个语词与“幸福”相对应,那么“乐”大约是古典哲学的首选。在这个意义上,“孔颜之乐”“君子之乐”“逍遥之乐”“至乐无乐”“第一义乐”“极乐世界”构成了传统哲学语境中的幸福范畴,“乐观”即为传统哲学中的幸福观。鉴于儒家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又由于“孔颜之乐”的境界高妙且影响深远,人们自然很容易将“孔颜之乐”作为传统幸福观的表征符号。
二、社会哲学的视角:优雅生存
现代幸福观与古典幸福观所依赖的社会生活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宏观地表述为农业社会、农业文明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甚至是后工业文明的不同,也可以具体呈现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明显变化。孟子曾经设想“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的仁政蓝图,再联系颜回“箪食瓢饮”的贫苦生活,可见古代社会的生活条件何其艰苦,那么体现在幸福观的设计中,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抑制人的基本的感性欲望的要求,即中国古典幸福观展现出对于实际的生存状况、生活境遇的较低要求,而更加强调内在的心理体验和心灵境界。现代中国,经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推进,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大幅提升,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应运而生。据称,“你幸福吗”采访了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各个阶层,背后蕴含着普通中国人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感受与体会,并引发了人们对于幸福的深入思考。
新闻调查节目“你幸福吗”可以视为一种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于幸福的思考。而社会哲学则侧重于从国家理论、政治观点、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等方面探讨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它不是单纯地在科学、教育、文化、经济、政治上寻求方向,而是致力于认识人类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原则,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进行哲学的思考。在当代中国幸福观的哲学建构中,“走向优雅生存”正是出自一种社会哲学的视角。优雅生存的核心观念是:“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智慧是实现幸福的最佳途径,而优雅生存是当代人类智慧的应有选择。”[1]优雅生存理论批驳了两种常见的幸福定义——幸福即快乐和幸福即德性,认为幸福是人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获得适度满足后所产生的愉悦状态。尽管幸福概念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和模糊性,但优雅生存的这个幸福定义是当代中国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因为该定义考虑了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的统一、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优雅生存的体系包括四个方面:优雅生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优雅生存的内容,优雅生存的条件以及优雅生存的实现路径。整个体系的建构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式、人类的存在方式开始,论及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国家发展方式、本国国情;阐述了优雅生存的生存目标、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论及了价值体系、经济基础、政治管理、教育事业、文化生活、婚姻家庭及个人素质,基本上是一种面面俱到的社会幸福系统。
优雅生存的理论建构充满了社会理想主义色彩,诸如全面发展、自我实现、人格完善、体魄强健、心灵安宁、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环境美丽等令人羡慕、缤纷炫目的状态,自由、平等、公正、和谐、尊严、德性、智慧、格调、情趣、创意等无比美好的词汇。不仅如此,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公民自主的社会制度、人性化的教育、丰富的雅俗文化、舒适温情的家庭、乐生休闲的生活等等,美丽浪漫的幸福世界尽显眼前。这些幸福的情景与英国哲学家罗素“幸福之路”(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的期望非常接近。如《幸福之路》第十一章到十七章的标题“兴致”“情爱”“家庭”“工作”“闲情逸致”“努力与放弃”“快乐的人”就是很好的例证。罗素称十八世纪法国沙龙中的谈话艺术炉火纯青,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艺术,令人无限回味和向往,但现在却很少有人关心这样悠闲的事情。[2]在这个意义上说,优雅生存的理论满足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然而它又容易导致一种大众化的生活享受观念甚至生活奢侈观念的出现。优雅生存在一般意义上就是“优质”“雅致”地生存,就是“生存的质量高”,就是“生存的规格高”,这很容易被理解为高端、奢华的贵族生活,尽管优雅生存的本意是人的需要获得充分协调的满足,是人的各种才能获得自由充分的发挥。优雅生存的方式是对顺应人性、压抑人性和放纵人性的超越,但在无形中,优雅生存理论本身也存在着走向放纵恣肆的可能性。
在理论构建的逻辑上优雅生存理论提出,人类文明的形态与人类的生存方式相互规定,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依次更替规定了自然生存、奴役生存、自由生存和优雅生存。这样,优雅生存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理论认为,优雅生存意味着克服了现代文明弊端的后现代文明,同时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就名称而言,四种人类生存方式的划分极易造成人们的疑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吗?为何在自由生存的生存方式之后还会出现一种优雅生存的生存方式呢?《走向优雅生存》中指出,自由生存的根本特质在于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并且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最佳生存方式。自由生存的生存方式要求解放与张扬人的个性,释放人的潜能,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使人获得尽情的欲望满足与生活享受。另一方面,《走向优雅生存》又指出自由生存放纵人性、刺激人性,并由此派生出贪得无厌的疯狂性,而且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与环境的差异,各人按意愿行事的结果大相径庭。因此,自由生存的方式仍然是有缺陷的,最终必然以优雅生存取而代之。尽管自由生存和优雅生存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但是依照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文化背景,估计很少有人能把优雅置于自由之上。这大概是“优雅生存”理论所要直面的问题。
三、生活哲学的维度:可能生活
社会哲学的维度与生活哲学的维度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因为生活总是以社会的形式发生和存在着,而且公正的社会与幸福的生活具有天然的一致性。社会哲学更多地在科学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层面进行反思,在目标上往往指向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并经由公正的社会机制达到生活的幸福。而生活哲学则直接立足于人的生活世界,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当作哲学的主题。这样,哲学就由知识性的绝对真理走向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思考,哲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过程,最终意图是要创造和提供一种真正属人的幸福生活。[3]“人应该怎样生活”即成为生活哲学的经典问题。在生活哲学的维度上,社会只是生活的形式和条件,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才是最终的目的所在。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人们不假思索就接受了的“大道理”,比如“社会”意味着多数人的福利,而“生活”则是属于个人性的事,而实际上“生活”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再比如,“社会”总是自然而然服务于“生活”的,但实际上“社会”所制造的规范往往扭曲“生活”。生活中所谓“人性化设计”“人文关怀”之类的说法,仿佛是某种格外的恩赐,这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此种设计、关怀本来就是为人的生活服务的应有之意。
在社会哲学的视野中,现代社会提供了愈发雄厚的经济基础,21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琳琅满目的商品不断积累,各项社会制度越来越严密健全,文化的繁荣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了华丽的盛景,幸福生活的大门已经开启。而在生活哲学的维度上,商品、信息、娱乐甚至科技并非幸福本身,而只是幸福的现象,它们甚至误导了生活幸福的本义。面对“你幸福吗”的街头采访,多数受访者的感受与期望十分朴素,所谈论的大多是就业、收入、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现实话题,而生活哲学所要反思的显然更加深刻。生活哲学面向生活世界,但又超越日常生活,它可以把“孔颜之乐”“优雅生存”作为反思的对象,它也可以提出新的幸福理念。在当代中国幸福观的哲学建构中,“可能生活”无疑是在生活哲学的维度上引人注目的典范。可能生活理论是一种所谓“新目的论”伦理学的思路,其核心观念是:生活具有自成目的性,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而生活的意义是通过创造性的生活或者创造可能生活来实现的;有意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幸福来自于自成目的性的行为本身。[4](P26)“可能生活”理论肯定良好的社会条件是生活所必需的,压抑人的基本生理性需求显然是残忍的。但同时也指出,仅仅是良好的生活条件,譬如丰衣足食的饱暖生活也无法带来生活的真正乐趣。为此,可能生活理论区分了生活能力和生物功能,而代表着基础性需求满足的生物功能并不能构成生活的本质意义。进一步而言,作为利益的典型表现形式,财富与权力只是达到生活意义的手段,而不是生活意义本身。利益是可以交换、分配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公正的原理来解决。但这里的公正仅仅具有手段的意义,因为公正的利益分配并非最终目的,公正的利益分配仍然是为幸福生活提供社会物质条件,幸福才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利益的获得、生物需求的满足并不具有人性的光辉,可能生活自然是要发挥人的生活能力。可能生活理论提出人的每一种生活能力都意味着一种可能生活,尽可能实现各种可能生活就是目的论意义上的道德原则。这样,可能生活理论把幸福公理视为伦理学的第一原则,并将幸福公理表述为:假如一个人的某个行动本身是自成目的的,并且这一行动所试图达到的结果也是一个具有自足价值的事情,那么,这一行动必定使他幸福。[4](P162)简单地说,可能生活具有两个基本特质,即创造性和自成目的性。
可能生活理论将幸福视为全部伦理学的第一问题,试图提出一条在每个人身上普遍有效的“幸福公理”,充分显示出生活哲学的深刻性,同时也呈现出浓厚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色彩。从可能生活理论建构的思想渊源看,“可能生活”(possible lives)这个概念是以逻辑学上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而设计出来的。可能世界是一个逻辑学和哲学的经典概念,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基于逻辑性而提出的世界概念,它意味着只要自身不包含逻辑矛盾即可成立。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可能生活被定义为“与每一种人类生活能力相对应的生活”,于是多样化的可能生活便展现出生活的丰富性。由此,《论可能生活》中提出,人应当尽可能去实现各种有积极意义的可能生活,否则便会有遗憾和缺陷。然而实际上,可能世界的限制只有逻辑性,可能生活的实现却必须具有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可能生活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可能。因此,可能生活将必然遭遇更多的无奈,多数人在实现各种可能生活的道路上无疑会困难重重,这必然使可能生活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进一步而言,可能世界属于逻辑学的范畴,可能生活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也就是说可能生活内在地具有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因此,《论可能生活》将可能世界与可能生活相提并论,就很容易忽视两者之间在价值判断上的差异。可能世界概念无须考虑其价值性。很明显,《论可能生活》所主张的是实现具有正价值的可能生活。但是通过对可能生活的深入分析,人们又很容易得到这样的逻辑:可能生活=幸福。这就是说,《论可能生活》有意无意地把可能生活概念界定为“创造性的生活”,进而把“创造性的生活”理解为“有意义的生活”,而“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幸福生活。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事业满足,是人生所能获得的最大幸福之一,这需要具备强大的生活能力或人性能力,通常只有少数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在这个意义上,可能生活的理论建构具有明显的精英化取向。
四、人生哲学的境域:德性幸福
在人生哲学的境域中探讨幸福观的建构,显得中规中矩,是一种“正统”的思路。众所周知,人生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和态度等,这就极其自然地将“如何生活得更加幸福”作为落脚点。即便一些宗教人生观认为现世幸福并不可能,也会寄希望于彼岸世界的幸福。可以说,幸福主题是全部人生哲学的归宿。依照古希腊哲学家的划分,哲学包含物理学(physics)、伦理学(ethics)、论理学(logic),分别可以对应于现在常说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他们认为论理学好比果园的围墙、物理学好比果园的果树,而伦理学才是果树的果实。不难发现,在古希腊哲学中,伦理学直接地与人生论相对应,德性论与幸福论难解难分。
尽管知识界已经熟知古希腊哲学中的德性论与幸福论,但是“德性幸福”被提及时,许多人仍会觉得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持有几分抵触的心理。在人们的哲学常识中,整个世界二分为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习惯性地,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划分。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在富有诗意的人生哲学中,人既是一种感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一半是灵魂,一半是肉体。由此,物质幸福与自然属性、感性存在、魔鬼、肉体等内在关联,而精神幸福与社会属性、理性存在、天使、灵魂等内在关联。这种日常生活中貌似有理的通俗见解,其实在道德哲学中是虚妄的,它根本无法表征幸福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特质。因为就所谓的物质幸福而言,基础性生理需求的满足自然而然,天然正当,这是一种健康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而对正当的生理需求进行抑制则是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同时,就所谓的精神幸福而言,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精神生活也可能是空洞贫乏甚至是低俗趣味的。因此,我们更加愿意使用“德性幸福”这一概念。考察其理论渊源,《尚书·洪范》将“攸好德”作为“五福”之一,可以视为中国典籍最早论述德性幸福的材料。此后,原始儒家的“孔颜之乐”“君子之乐”等均可视为中国德性幸福的典范。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幸福是因为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事物,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就是最高善。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已经充分建构了古希腊德性幸福的典范。
在当代中国幸福观的哲学建构中,德性幸福应是人生哲学视域中的经典形态。这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伦理学内在贯通,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实践哲学。德性幸福的核心观念是:道德与幸福内在相通,惟有德性主体才能“获得幸福”且“配享幸福”;广义的德性完善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存在的完善才是人生幸福的真谛所在。德性幸福无疑是一种“德福一致”的理论,一个幸福的人必是一个道德的人,一个缺德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只有那些具有道德合理性的需要满足、理想实现、精神愉悦才是真正的人生幸福,不具备道德正当性的快乐和愉悦在本质上不可能构成幸福所在。”[5]这就是德性幸福首先必须遵循的原则,德性原则可以视为德性幸福观的第一个要点。德性主体是德性幸福观的第二个要点。康德区分了“获得幸福”与“配享幸福”,认为道德不是“获得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如何“配享幸福”的学说。“获得幸福”以幸福为追求的目标,而“配享幸福”则强调如何使主体达到德性的完善。在德性幸福观看来,无论是获得幸福还是配享幸福,均需要德性主体的前提性存在。西方哲学有个关于主体的经典故事,面对黄金与草料,恐怕所有的牛马选择的都是草料而非黄金。《孟子》首篇《梁惠王》对此也有精彩发挥:“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杨国荣先生认为:就幸福的实际境遇而言,幸福则同时体现为价值创造过程中人的精神形态的提升,后者构成了主体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6]德性幸福的第三个要点是德性境界。注重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这是中国哲学对于世界哲学的特殊贡献。中国传统的幸福观并不企慕彼岸世界的幸福,总是试图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寻求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理想的归宿。所谓理想人格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德性主体实现了理想的境界;所谓人生幸福的实现,实际上是幸福生活与幸福境界的统一,而幸福境界又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有人称现代社会是一个“喻以利”的小人社会,对于商品、服务、财富、权力、资源的无限制追求随处可见,而理想主义、德性境界几乎成为“贬义词”,于是真正的幸福成为一种稀罕物。而人一旦真正具有了这样的德性境界,即便是穿衣吃饭、即便是担水砍柴,人生的本真幸福自然溢出。
德性幸福是一种广义的德性与幸福的统一体。德性幸福所指称的德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品德,例如诚实、正直、友爱、勤劳、勇敢、敬业等等,广义的德性还意味着一种理智德性,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所谓的“美德即知识”,冯契先生所讲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进一步而言,德性幸福的理论中,德性的完善还意味着存在的完善、理想人格的健全、精神境界的实现,所有这些全部指向——人生的幸福。“这不是狭义的关于个人品格操守的德性,而是具有更为深厚内容的、对人的全面发展、潜能的充分发挥、人格完整的充分肯定的广义德性。”[7]在这个意义上说,德性幸福不仅把德性作为幸福的前提、保障、工具和条件,而且把德性完善视为幸福的内容和源泉,是一种“成己与成物”。广义的德性幸福关涉人的整体性存在,它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最高善”精神相通,也与马克思设想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精神相通,同时也是对儒家德性幸福的传承与发展。因此,在广义的语境中,优雅生存、可能生活与德性幸福的内在精神相通,均是秉持了广义的德性论的思想内核,优雅生存、可能生活自身也存有向德性幸福衍化的趋势。它们不仅为现代社会幸福观的哲学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能够在现实中引导健康、文明、和谐的现代生活方式。
[1] 江畅. 走向优雅生存——21世纪中国社会价值选择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65.
[2] 伯特兰·罗素. 幸福之路[M]. 吴默朗, 金剑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32.
[3] 李文阁. 生活哲学的复兴[J]. 哲学研究, 2008(10): 85−91.
[4] 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 张方玉. 追寻君子的幸福——当代视域中的先秦儒家幸福观研究[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4: 234.
[6] 杨国荣. 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71.
[7] 高兆明. 幸福论[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29.
How to make possible the modern virtue happiness: Also on the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about the view of modern happiness
ZHANG Fangyu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In a materialized and secular age of Consumerism, it is more vital for people to inquire what happiness is and how life should be led. There are three philosophical schemata of constructing happiness which are profoundly representative: “elegant existence” in the view of social philosophy, “possible life” in living philosophy, and “virtue happiness” in philosophy of life. These three are interlinked in spirit, all upholding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generalized virtue theory. And such modern virtue happiness will probably suggest the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Chinese concept of happiness.
virtue happiness; Confucius-Yan’s happiness; elegant existence; possible life
[编辑: 颜关明]
B82
A
1672-3104(2017)03−0001−06
2016−11−01;
2017−01−1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中西会通视野下的幸福观研究”(16CZXJ09)
张方玉(1977-),男,江苏句容人,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道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