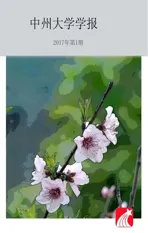“礼崩乐坏”与“涅槃重生”:论春秋礼乐文化的辩证发展
2017-01-12张书霞钱东晓
张书霞,钱东晓
(1.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图书馆,郑州 450044;2.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郑州 451100)
“礼崩乐坏”与“涅槃重生”:论春秋礼乐文化的辩证发展
张书霞1,钱东晓2
(1.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图书馆,郑州 450044;2.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郑州 451100)
从中华文明肇始,中经西周全盛和春秋的衰落,再到儒家重新阐释,华夏礼乐文化在先秦经历了由合而分,又由分到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本文以礼乐美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辩证发展为线索,分析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原因,指出礼乐美学经历的西周兴盛和东周创新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强调礼乐文化美学有其道德缺憾,但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利益,其合乎人性和人道的人文精神有益于当前中华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和谐与发展。
礼乐;春秋;辩证发展
礼与乐发生在农耕文明的中华大地,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得益于适宜的纬度位置、肥沃的黄土地、水量充沛的黄河水系和锦上添花的季风气候四个方面的天造地设,构成了精美绝伦的孕育和谐文化的温床。就历史文化线索来说,“礼”和“乐”与原始宗教与图腾密切关联。把礼乐两种美学形式结合在一起,更显中华先民的审美创造能力。经过上古三代的不断发展,礼乐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审美的核心概念和中国政治美学的标志性内容。和谐,也就成为中华文明几千年不变的特征。
众所周知,西周时代的礼乐逐渐脱离宗教而与政治统治相结合成为政治统治的手段,是礼乐美学的一个质变。在这一质变过程中,贯穿礼乐这一社会现象几千年的和谐文化精神没有变,礼乐相融的形式没有变。“周公制礼作乐”,造就了以礼为中心、以德为内在、以乐为形式的审美政治的雏形。
就像从中华文明肇始,中经西周全盛和春秋的衰落,再到儒家重新阐释,华夏礼乐文化经历了由合而分,又由分到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大的逻辑循环一样,事实上,在每一个相对独立的较短的历史时期,礼乐文化也经历着同样的范围相对较小的辩证逻辑过程。本研究以礼乐美学在春秋时期辩证发展为线索,强调礼乐美学经历的西周兴盛和东周创新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探讨春秋“礼崩乐坏”时期礼乐美学的“涅槃重生”。
一、“礼崩乐坏”的原因分析
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春秋时期的大变革和大动乱打乱了奴隶主统治次序,制度体系失去了约束力。西周礼乐赖以维系的社会根基动摇。另一方面,“郑卫之声”等新乐兴起,则反映当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社会文化生活需要的民间音乐文化形式迅速崛起。但这些都只是表象,“王室衰微”与“郑卫之声”背后的真正原因还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政治和经济都经历着大变革。礼崩乐坏作为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表象是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使然,究其根本原因是代表奴隶制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和代表封建制的新兴生产力因素的强大动力都在发生内在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表现在生产工具上,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铁器使用愈加广泛。铁器的使用和井田制的瓦解可以理解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而政治上的纷争也只不过是新旧生产关系的较量,而所有这些,都在为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思潮的到来准备着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东周“礼崩乐坏”不是人为因素,更不是历史倒退,而是社会大变革时代政治文化的表达方式。文化交流方式的更新只是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不能把新媒介带来的文化拓展作为“礼崩乐坏”的社会原因。
对于“礼崩乐坏”,文化研究者历来观点各异。李石根认为“礼崩乐坏”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政治局面,是儒家学派对礼乐文化时代变迁的一种误判,而事实上礼乐文化从来没有过崩坏局面,而且一直在发展。钟琛则认为“礼崩乐坏”是新媒介带来的文化拓展。
当然,和宗法制结合在一起的礼乐制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很明显,礼乐制度 “对劳动实践的道德意义”以及“知识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1]都非常漠视。可见,我们对礼乐文化的态度从来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地分析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
礼乐文化在很多历史境况下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体现了民族的审美精神,直到今天,礼乐文化中合乎人性和人道的人文精神仍然有益于中华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和谐与发展。经历过“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但礼乐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一分钟也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其对和谐的价值追求,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和其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组成伟大的民族文化基因。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之后,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基因必然更加富有生命力,这里所指的就是儒家礼乐美学的创新发展。
二、“礼崩乐坏”时期礼乐文化的辩证发展
东周时期的“礼崩乐坏”给多种文化发展以新的契机,同时也加速了礼乐美学的新生,儒家礼乐美学的创新发展只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东周时期“礼乐崩坏”,但礼乐审美理性成分增加,而正是孔子和他的继承者们对礼乐进行理性主义的思考,实现其德育与美育的统一,赋予礼乐美学以蓬勃生命力,才使之影响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而不衰。
首先,对礼乐文化的辩证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数孔子。学者大都认可“周公是礼乐的主要制定者,孔子是礼乐的坚定执行者”的说法。孔子在美学史上最早奠定礼乐相亲、善美相成的原则,使之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理念。孔子的礼乐思想源于周公,但又有很大创新。康德提出“善的快乐”“感觉的快乐”和“审美的快乐”,而孔子说欲仁、好仁和乐仁,两者异曲同工,很好地论证了审美、感觉和社会意义的关系:礼是乐的基础,乐是礼的升华,礼乐相通。对孔子来说,三者关系对应着对待仁的知性、物性和情性的态度,都是仁的“文”化。礼和乐均建立在仁的基础上。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出人格建造从感性始,经过理性的作用,再到感性,最后实现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统一的过程。
在《原儒墨》中,冯友兰指出孔子不是儒的创立者,但他却是儒家的创立者[2]。可以认为从儒者到儒家的转变是一次质的飞跃。儒家借助于西周礼乐制度,用理论充分论证礼乐制度并据此提出治理国家的方略,使礼乐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获得新生。当然,孔子能把儒者改造成为儒家,除了其礼乐教育途径培养出来的学生通过仕途参与政治的主观原因外,当时鲁国的礼乐制度破坏较小是其重要的社会现实基础,当然,进入仕途的儒家弟子,通过人格典范迅速扩大影响,是儒家思想成功的重要思想基础。
其次,孟子有诸多重大贡献。孟子继承和发挥了“仁”的思想,把伦理道德完善与精神情感的审美体验结合,提出用人格美体现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理论的核心主张。孟子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禽分际的规范性标志。
“以礼释仁”,礼通过内化的功夫,化作人的情感心理,成为人的先验本体和经验现象的概括;“乐与民通”,在强调礼乐美育作用的教化过程中,实现“德教”与“乐教”的最佳效果;“化育天下”,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完美社会关系角度论证伦理美的重要意义,指出和谐的伦理美的最高境界在于人格美,实现“仁义礼智”的社会美学,达到化育天下目的,是孟子礼乐思想的美学意义。直到今天,强调美学的社会功能对美好社会建构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由孔孟开始的对于礼乐的理性理解,在荀子《乐论》的美学阐释中达到高峰。荀子围绕礼乐重建,设计“宽猛相济”和“崇礼兴乐”,关切“王霸之途”和“理国之道”,奠基“天子之学”和“人性之论”,坚持人本主义与通权达变并举,认为审美应以礼乐为引导,促使人性由恶变善,宣扬审美要求与礼乐约束的完美统一。
礼乐是荀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美善相乐”是荀子对礼乐关系的主张。在这里,礼、善、乐达到了和谐统一,各自既是目的,又是途径和手段。强调礼的规范意义和作用的同时,关注礼的审美旨趣,通过礼的审美功能完成对礼的诗化阐释。而乐是心性从善的修养工具,给予乐伦理定位和道德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道德善与艺术美的统一。当然,荀子夸张了乐的政治功能,也损害了艺术自身的审美功能。
三、先秦诸子对礼乐美学的身体探讨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是政治制度使得原有社会文化元素分离的结果,其结果使得具有身体统一性的礼乐文化突然残缺不全。生活在过渡年代里如何用身体思维应对世道变故、挽救世道没落是摆在儒家诸子面前的问题。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都用自己的躬身践履给历史以完美回答。孔子在奔波游说中,在乡校、宫廷、村社不同场合身体力行,用身体语言复兴周道。事物的意义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借助于通感等整体感受,实现身体审美。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也正是这样实现礼乐美学的身体践行的。当然,这也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了身体美学中“意境”的含义了。王国维曾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3]”。
荀子在《正名》中分析了身体思维和概念思维的关系。今天,我们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分析,能够清晰地判断出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决定了身心合一、知行合一、唯象思维的身体思维模式,但对于哲学理论相对混沌的先秦时期来说,我们只能感叹先秦诸子对身体思维的历史贡献从实践上契合了哲学规律。在中国先秦诸子的身体思维中,具有极大身体涵容性,同时,理论逻辑充分,“理”文化特征明显,“名象交融”成为长期影响中国美学发展的思维方式。
“身体”两字的造字,可以说明中国先人对于身心关系的理解,对于知行合一的态度。许慎的《说文解字》对“身”的解释是,“躬也,象人之身”。身体的“体”字繁体字与礼仪的“礼”的繁体字是相通的,都是祀神和敬身的意思。可见,古人对于身体的解释就是躬身与崇敬。
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环境来说,农耕文明中,社会个体生活距离缩小,身体接近,交往密切而广泛。这种环境从物质基础上决定了礼仪互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荀子的礼仪观找到了合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中国美学和伦理学的身体性践行特征找到了理论依据。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礼法社会,合乎礼的就是正确的,就是合适的。这说明身体性审美是一种实践自觉。
从身体起念,是中国农业文明孕育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特征又造就了风骨、形神之类的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和中国传统审美意境。礼乐文化与身体思维和身体审美在较长历史时期的相互影响,又反过来加深了礼仪的模式化和典范化。身体演示通过体态、服饰、场景、氛围对礼的传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审美意识突出、通感联觉发达的中华民族的重要美学特征。正所谓民族的失望透顶和审美特征弥漫于我们的身心。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审美基因和文化基因,我们在身体力行传统文化遗产时,才会感受到中国优秀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四、礼乐文化美学批判
墨子以“非乐”为中心的美育思想是先秦美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墨子、韩非子等人的礼乐批判是西周礼乐美育观裂变中的重要声音,引起当时思想界强烈关注,尽管其对礼乐审美的批判过于片面和极端,但其对礼乐审美价值与社会功利矛盾的分析,尤其是对于上层社会奢侈享乐的批判,有益于礼乐美学的涅槃重生。正是百家争鸣促成儒家学派的全面创新。
墨子对上层社会礼乐的批判是系统和彻底的。从音乐演奏到音乐欣赏,从音乐制作到乐人供养等,最终结论是由“非乐”到“禁乐”。墨子对音乐的态度和他对儒家礼乐教化的态度是一致的:彻底批判直至全盘否定。墨子这种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全盘否定却显得滑稽可笑。但无论如何,墨子的呼声引起了当时思想界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正是墨子的初衷吧:正是全盘否定引起的强大的反响赚足了思想界重视和反思。从这个方面来说,墨子对礼乐美学的批判至少有以下功用和价值:第一,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其批判精神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下层人民正义的呐喊。第二,战国时期的社会动乱造成人民生活苦难,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礼乐审美的艺术表现与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现状严重不符,凸显了墨子批判的进步性和历史意义。第三,墨子对礼乐文化最大的贡献和价值在于,他的批判触及到了儒家一贯忽略的审美与社会功利问题。可以认为,荀子对审美和功利辩证关系的论述,孟子“与民同乐”的主张,都是墨子礼乐批判背景下的辩证思考。韩非等法家学派的礼乐批判及其美学观与墨子密切关联,一脉相承。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批判,促成儒家学派在继承和创新礼乐美学的过程中更加系统和全面,礼乐美学批判是春秋时期礼乐美学涅槃重生的重要环节和条件。
五、启示
研究礼乐美学的发展脉络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要求,对于建设和谐中国、文化中国和美丽中国,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从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的辩证发展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文化转型必须适应社会转型。春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动决定了礼乐文化从多方面的变化发展,“礼崩乐坏”是和“以礼释仁”“乐与民通”“美善相乐”“崇礼兴乐”“化育天下”等等同时存在的文化发展状况。“礼崩乐坏”过程与儒家诸子辩证发展礼乐美学的过程相伴而生,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礼崩乐坏”和儒家礼乐重构其实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
其次,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发展的唯一出路。礼乐文化在春秋时期的涅槃重生就是在传承与创新中辩证发展的例证。春秋时期,对待传统文化诸子百家大都采取了“述”与“作”相结合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传统文化问题时也强调继承与创新的方式和方法。
最后,文化辩证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重要性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往往体现在学术中的文化自觉精神。礼乐在春秋时期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担当起了历史责任,在社会转型冲击中表现出了足够的创新精神。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文化精神的确立,也标志着中国礼乐文化在东周时期涅槃重生而获得了新生,并在此后两千余年,在被世界公认为礼仪之邦的国家文明发展史中薪火相传。
[1]汤一介.中国文化与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0:338.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63.
[3]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18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alling”and“Rebirth”: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in the Dynasty of Spring and Autumn
ZHANG Shu-xia1, QIAN Dong-xiao2
(1.Library,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Zhengzhou 451100,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in China has witnessed the flourishing perio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fading perio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Dynasty, and the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combina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em and then the recombination in which the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in pre-Qin period as a clue, analyzes the social reasons of falling and rebirth, points out that the flourishing perio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fading perio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Dynasty are two aspects of innovation and related together.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ritual and music aesthetics culture of China being in line with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the human nature and humanity and humanistic spirit, even in harmon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mankind.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the Dynasty of Spring and Autumn;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2016-12-18
河南省教育厅2017年度人文社科项目“礼乐美学发展脉络研究”;河南省社科联2017年度项目“春秋礼乐文化创新发展经验研究”
张书霞(1969—),女,河南平舆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哲学。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9
B232
A
1008-3715(2017)01-009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