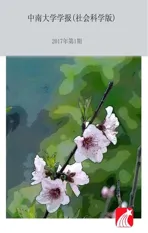汉大赋制作的图志化倾向
2017-01-12张朋兵
张朋兵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汉大赋制作的图志化倾向
张朋兵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汉大赋的图志化”,即汉大赋的制作常需从地图、方志中获取书写材料,图志成了大赋写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而且在叙事上还呈现出一定的立体空间感。辞赋图志化表征有二:一是重视知识的博物与知类,二是强调空间与方位叙事。汉代的许多著名大赋,皆有图志化的典型特征。汉大赋图志化是在汉帝国政治军事需求、图籍编纂之风盛行及图画辅助教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汉代“体国经野,义尚广大”的时代精神是其文化学术背景。大赋图志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本质属性,扩充了汉赋所要呈现的物态容量和空间维度,使辞赋由原来的文学语言艺术变成了“空间艺术”,但是过度追求图志化,也给辞赋革新带来了弊端。
汉大赋;图志化;博物和知类;空间与方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图志化”是文学书写的一种呈现方式,是文学独立于文献学之外的另一层存在空间和阐释领域。[1]但本文所谈及的“图志化”,是说汉大赋在制作过程中将地图、方志等材料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源泉,而且在叙事上还表现出重视空间方位的风格特征。汉大赋具备了图志资料本该有的史料价值和地理空间意识,无论是在材料筛选、叙述顺序上,还是谋篇布局、审美建构上,大赋的图志属性都更加明显。汉大赋所呈现出的图志化趋向,是一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试图以汉代文学的主流——大赋为中心,探析汉赋的图志化现象及相关问题。
一、图志:汉大赋创制的一个知识来源
汉大赋因其“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铺陈特征而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写制汉赋要罗列各种草木鸟兽之状,陈说山川河溯之原,比物连类,极尽穷奢漫衍之藻彩,这需要赋家具备深厚的才学功底。简单地讲,所谓“才学”就是各种文化与知识的储备,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写出一篇辞赋的重要保证,而“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2]。写制汉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经验,诸如历史地理沿革、典章制度、传闻逸事等,牵涉范围之广,无所不包。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作赋之法,已尽长卿之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3]辞赋所涵盖的知识范围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所以长期的学识积累和材料准备便成了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据说张衡写《二京赋》时“精思傅会,十年乃成”[4]。可见大赋的写作过程不仅要精思博览,还需向别人不断讨教、问询。至于扬雄作《甘泉赋》,更是“一首始成,卒暴倦卧,梦五脏出地,以手收内之,及觉,大少气,病一年。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5]。由此知作赋之辛劳,非同一般,它不仅是各种知识、材料的搜集、储备、消化过程,也牵涉到对材料的熟练运用与驾驭,更触及到很多写作技法与神思方面的问题。
汉大赋囊括天地、包举宇内的博物取向,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认知范围。除了长期的研习积累、亲身考察以外,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地图、方志等图籍资料是大赋写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这是因为图志资料涵盖了各地区丰富的地形、物产、医药、民俗、宗教等地理名物资源,对以擅长“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大赋而言最为适用。在作赋之前,出于征实的目的,要尽可能地参考各类地图、方志材料,大体以“《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6]。在汉代士人眼里,《离骚》“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7],《尔雅》多释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等动植物之名,《舆地志》载录各类地理人文风俗,因此它们常被当作地理博物类文献。而在诸多的图志典籍中,以《山海经》最为奇特。它最初是有图的,图上载录了大量关于古代山川、植物、矿产、巫术等的名物知识,具有备百物、知神奸的巫史博物图画属性,其性质类似于百科工具手册。这些辑录了数以千计的山川地形、物产风俗材料的图志文献,是汉代知识、观念与思想的重要载体。汉大赋所要呈现的山泽湖海、宫室苑囿、礼制风俗、人物百态等皆可在具体图志条目中找到出处,因此,从具有类书性质的地图、方志中查检、搜寻资料便成了制作大赋一条非常便捷的途径。
两汉是大赋创制的高潮时期。《子虚》《上林》《两都》《二京》之赋的创制无不从地图、方志资料中汲取知识和素材,这就使图志资料显得格外重要。以《鲁灵光殿赋》为例,王延寿对灵光殿的描绘虽有夸诞虚饰与不合情理之处,但赋中所描绘的草木鸟兽、亭台楼阁、风景形胜、名宿人物等基本是依据真实的实物场景和绘画图录撰写的。据《博物志》记载:“鲁作灵光殿初成,(王)逸语其子曰:‘汝写状归,吾欲为赋’。文考遂以韵写简其父,曰:‘此即好赋,吾故不及矣’。”[8]又《文选》卷一一《鲁灵光殿赋》下张铣注:“范晔《后汉书》云:‘王延寿父逸欲作辞赋,命文考往图其状,文考因韵之以简其父。’”[9](215)王逸欲写关于汉鲁灵光殿的辞赋作品,遂派其子亲往图摹其状,这体现出辞赋写作委实的一面。之后不久,其子王延寿所作《鲁灵光殿赋》,即是按照之前所见壁画内容据实摹写其貌,其辞曰: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讬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娲蛇躯。洪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列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10](515−516)
王延寿能写出如此鸿篇巨制,不能说不依赖于他先前对灵光殿在布局、雕刻、形制等方面的实地考察和图画实录。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汉灵光殿风貌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而且还开汉赋征实的先河。
当然,大赋写作中参考地图、方志的做法也影响到了汉以后的赋家。西晋左思花十年之功作《三都赋》,赋成后“洛阳纸贵”,可他在《三都赋序》中却说:“余既思摹《二京》而作《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9](91−92)左思认为作赋时要依据地理实情,不能夸大事实,山川城郭等地理名胜稽之地图,草木鸟兽等物产验之方志,歌舞谣谚则来源于乡土民俗,名人贤达则出自当地耆老故旧。而《三都赋》正是勘察了地图方志、物产风俗资料写制而成,因此皇甫谧在给《三都赋》写《序》时称赏说:“其物图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9](860)西晋卫权也夸赞道:“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特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11]他们正是注意到了左思赋“披图而校”“按记而验”的征实特点才这样推许的。大赋囊括天地、包举宇内的博物趋向,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所接触的知识范围,因此从具有类书性质的地图、方志中查检、翻阅资料就是一条非常便捷的途径。
汉大赋中的各种物态既可从图志文献中获得,那么,在塑造这一场景的过程中,载录了各地地理形貌、物产风俗的图志就成了赋体文学写作中必不可少的知识构成要素,而汲取图志素材撰作而成的汉大赋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知识由简至繁的演进过程。汉初辞赋具有楚辞化的风格,赋中也多有鸟兽草木等自然动、植物物象的出现。但赋作主要还是抒发情感的,图志知识只是起到描摹、记述作用。真正迎来汉赋图志化高潮的是司马相如、班固、扬雄、张衡等辞赋大家。首先是他们在大赋中不间断地再现汉帝国自然山川、地理形胜、风土人物、宫廷苑囿等宏大叙事图景,呈现出了类书、图志所具有的博物化、知识化趋向;其次是对空间叙事手法的重视。辞赋有意模仿地图、方志的叙事方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辞赋所要呈现的物态容量和视域范围,阅读一篇辞赋就像俯瞰一幅山川地图一样,从而使辞赋具有了可视性和画面感。此后,汉赋图志化继续发展,辞赋不断深化自身叙事技巧,并且还产生了一些固定的空间方位句型、句式,这进一步丰富了汉赋图志化的内涵。
二、博物与知类:汉赋图志化表征之一
汉代既是文学语言艺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图志资料空前膨胀与重新阐释的时代。面对如此烟波浩淼的人类图文典籍,汉代知识群体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如何将传统及当下社会存在的一切知识、经验、思想等囊括其中,进行分类整理,使之系统化和秩序化,为汉代政治建设、道德宣传和文化学术服务,这是横亘在赋家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汉赋创制中,赋家正是借鉴、吸收了图志类典籍在知识集成与分类上的逻辑思维方法,才使得辞赋图志化成为可能,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博物,二是知类。
先说博物。后世学者在谈及汉大赋写作时经常引用司马相如论赋的一段话表达汉赋的骋辞博物技巧。他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12]汉大赋铺采摛文,极尽穷侈漫衍之辞,以此与汉帝国“体国经野,义尚广大”的时代精神相匹配。因此,在最能代表汉代文学主流的文体——汉大赋中,要尽可能多地罗列物态、铺陈辞藻,这逐渐成为汉赋写作中的常态和一项重要的“潜规则”。古人在讨论汉赋时也是常以“多识博物”(班固《汉书·叙传》)、“极声貌以穷文”(刘勰《文心雕龙》)、“赋取穷物之变”(刘熙载《物概·赋概》)等来概括,无不将汉赋与名物传统相联系。虽然他们在描述手段和目的上各有侧重,但其要旨最终都落到了“博物”这一点上,“博物”成了汉赋写制当中最为重要的文化风尚。以《汉书·艺文志》所录的诸多辞赋作品为例,虽以“赋”体名之,但内容几乎完全博物化了,如《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等,内容上出现了全面博物化、知识化的倾向。而在其他非极端化的辞赋中,也日益呈现出博采知识的趋势。可以说,博物化是汉赋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时代痕迹。
而汉大赋的博物化,一定意义上也是辞赋具备“类书”性质的诱因[13]。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而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14]《三都》《两京》之赋,由于在写制过程中参照了大量的图籍、地志文献,故有一定的征实特征,在还没有博物之书的时代[15],它基本上充当了类书、志书的功能。
在编纂方式上,图志文献一般是以一定的地域空间为单位,对所辖区内的地理交通、物产风俗、历史人文等进行集中记载。而颇具类书性质的汉大赋,虽在编纂上以方位为序,没有像图志那样按照类别对名物进行集中分配,但在博采众物、辑录各门类知识方面,两者具有相通之处。后世许多学者对辞赋的兴趣,也并不是专注于它的骋辞体物技巧,而是多半将它当作博物文章来读[16],这种认知颇类似于我们今天对大百科全书的界定。
汉大赋的博物化特征,不仅表现于可以把它当作地志、类书来读,而且赋中很多内容皆可与后来的图籍、方志著作相印证,从而具有了某些志乘价值。以人们熟知的京都大赋为例,《西都赋》中描绘的长安京畿形胜、宫殿台阁、街衢集市等,可与《三辅黄图》的记载相吻合;《西京赋》中对长安八街九陌、通天台、建章宫等的描摹,也可与《三辅黄图》《三辅决录》相印证。[1](106)汉晋以后,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时还曾引录扬雄《河东赋》、张衡《二京赋》等来佐证江河的流向及相关城郭遗址的地理位置问题。[18]汉赋在历史地理沿革、宫殿布局等方面与图籍资料相佐证的志乘功能,是汉赋博物化、征实性最集中的体现。
次说知类。在汉赋创制过程中,赋家时常需要从图志中筛选材料以扩充汉大赋的物态容量。但是如何将这些品类繁多的知识、材料进行合理编排与分类,也是赋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汉赋制作中,赋家从方志资料的编纂方式中得到了某种启示——知类法,就是把名物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进行编排使之系统化,这来源于汉人的象数思维。“知类”法是汉人在逻辑思维领域里的一项重要发现,冯友兰在《新事论》中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时说:“汉人之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以五德、三统、三世等理论,说明历史或文化之变迁者,就其内容说,有些亦可说是荒谬绝伦。不过他们的看法,却系从类的观点,以观察事物者,就此方面说,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19]汉人在写作辞赋时,经常将象数思维带入到名物知识的分类当中。以汉代图文关系而论,辞赋以博采铺排见称,在总体上要尽可能多地罗列物态,以展示恢宏的汉帝国物质图景,但在具体条目上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积材料,而是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使之“类型化”,如社会之物就可划分为“宫室”“礼仪”“校猎”“百戏”“乐舞”等若干名物系统。曹丕所谓“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20],正是对汉赋知类手法的最好诠释。在汉代图籍资料中,图志所描摹的各种物态遵循着以类相从的排列原则,而在汉赋所罗列的名物当中,其实也遵循着这种聚类的象数思维。汉赋定型并蔚然大观的汉代,正是象数哲学日益发达的时代,可以说,汉赋文本形式上的“巨丽”之美与汉人的“知类”思维及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具体到汉赋所展示的图文物象而言,有横向集中罗列式的,如《上林赋》中对天子上林苑之“鸟兽鱼鳖”的叙述:“于是乎蛟龙赤螭,渐离,鳍,禺禺鳎。揵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欢声,万物众伙。明月珠子,的砾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汗,藂积乎其中。鸿鹔鹄鸨,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庸渠。箴疵䴔卢,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10](363−364)赋家对动物种类一一呈现,尤其是对鱼的不同种类的列举,仿佛一个活灵活现的动物综合“大观园”。还有一种是纵向分散连续性的,按照“事类化”的原则,如《西京赋》中对平乐观前“扛鼎”“钻圈”“缘干”“走索”“跳丸剑”“硬气功”“吞刀吐火”“化妆歌舞”等一系列百戏活动依时间顺序描摹,如同一张节目次序表。而在汉代图志资料中,乐舞图画所描绘的各种舞蹈动作,前后相继,也呈现出一定的程序化和类型化。汉赋所展示的舞蹈场景、种类完全可与图籍、图志资料相对应,真正使图文达到了相互配合的境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互文阐释系统。
而在汉代流传的许多图志文献资料中,其载录模式也遵循着这种“知类”逻辑。以《山海经》为例,它在叙事上基本呈现出“某处有某山,某山有何特产与神怪,其形状与功能若何”的三段论固定模式[21],结构形式完全服从于书中所介绍的名物内容。每段围绕一种名物展开,三段共同构成一个独立的名物阐释体系。同样地,另一种汉代天文地理知识的综合文献《汉书·地理志》,也有“知类”的三段论逻辑。它的内部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部分:先叙古九州地理轮廓与形貌,内容基本依据《禹贡》;次录汉代各郡国地理山川、关塞城郭、经济物产、户口赋税等,可能是依据各地区《图经》所成;最后叙述某地风俗人情、历史传说等。这种载录模式从先秦志、书体例而来,但又有所变化。而在两汉京都大赋的叙事当中,也大致遵循着三段论似的载录模式,在叙述每种建筑群落时,总是紧紧围绕某种体制分类延伸。如班固在《西都赋》中对帝京宫室建筑的描述:先从总体上叙述山川城郭走势,再分区位附之以具体的宫观、城池、楼阙、街市等繁华盛景,最后从形制、制度、文物、历史上分述不同功能与作用,形成了一个既复杂又详细的叙事系统。
三、空间与方位:汉赋图志化表征之二
由于汉大赋的描述内容主要涉及地理山川、宫殿苑囿、巡狩弋猎等宏大叙事场景,其摹写对象决定了叙述主体必须具备平面与立体的多维视域,在视觉上要呈现出恢宏的空间画面感与方位性。故此,从视觉维度出发形成的空间铺叙技巧逐渐被赋家运用在汉赋写作当中,并逐渐成为辞赋叙事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汉赋在叙事技巧上经常表现出重视空间方位的特点。朱光潜在讨论诗赋关系时就已提到,他说:“一般抒情诗较接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图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22]赋所具备的类似“空间艺术”,其实是说赋在谋篇布局、美学建构上与地图资料的记录、标示及描述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据现代学者研究,汉赋空间叙事的方式有十余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平面直线型叙事”“平面四方型叙事”和“立体直线型叙事”三种类型[23],而这些均能与图志资料的记载相吻合。地图需要在空间上标出山川河流、疆域城郭的所在,需要标记地理方位和山川走向,需要从东南西北不同角度画出道路交通、关隘形胜,这些都与汉赋的空间叙事艺术息息相关。以枚乘《七发》为例,其描摹对象(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因叙述空间从室内到室外的方位转换,故而呈现出平面直线型的铺写方式,叙事顺序也因叙事空间的变换而变化,形成了一个由近及远的叙事主线。
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叙事手法明显增多,对空间方位的重视也更进一步。“子虚先生”在夸耀楚国云梦泽“方九百里”时说“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其高燥则……,其埤湿则……,其西则……,其中则……,其北则……,其上则……,其下则……”等,赋文顺次从东、南、西、北、高、低、上、下不同时空和方位分层铺陈。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感的叙述模式,扩充了辞赋所要表现的时空维度,更能体现出汉大赋“义尚广大”的宏伟气势。其后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扬雄《蜀都赋》等进一步发展了空间方位叙事,并呈现出多元化和细密性的趋向。
班固在《西都赋》中展示了都城长安的地理形貌,“其阳则崇山隐天……,其阴则冠以九嵕……,下有郑白之沃……,东郊则有……,西郊则有……,其中乃有……。”张衡《西京赋》拟《两都赋》而成,叙事以秦都咸阳为中心而分方位依次排开,“左有崤函之固……,右有陇坻之隘……,于前终南太一……,于后则高陵平原……,其远则九嵕甘泉……”。叙事路径如同眼睛在观察地图时视线的来回游移一样,因此美国学者余定国认为《二京赋》“具有双重的地图学意义。首先是使用量度和测绘,常与地图学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政治隐喻,在描写汉高祖如何建都长安时,量度和测绘暗示了汉初的政治制度……张衡的赋也可能包含了有关地图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应用的证据。……除了可能是有关应用地图的描述,张衡赋中的一些用词也暗示它可能是根据地图撰写的。有些部分,可以说张衡等于是制作了一幅‘口头描述的地图’。他的赋读起来是有方向的,他的描述向左右移动,又向南北移动”[24]。余先生不仅看出了汉大赋的空间叙事与地图的记录方式有类似之处,而且还认识到汉大赋描绘的许多地理场景具有政治地理学的意义。
再看扬雄《蜀都赋》。它以“蜀都”为中心形成“东有……,南则……,西有……,北则……”的平面四方叙述模式,在叙事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方位属性。而到了左思《蜀都赋》,他对巴蜀地区空间方位的叙述则更加立体化、详细化了,“于前则……,于后则……,于东……,于西……”,以中央为参照系分不同方位、层次分别陈述,如同作者居高俯瞰一样,因而有身临其境之感。在空间内部,疆域之中又穿插“其园则……,其沃瀛则……”,一重空间套嵌多重空间,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辞赋因而具备了与诗相似的“错彩镂金”之美。
其实,汉大赋尤其是京都赋对空间方位叙事的重视,所折射出的乃是汉代帝京文化向外的不断延伸与渗透。两汉是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时代,汉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日益扩张,逐渐影响和浸润着它在文化与学术上的书写,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对京都乃至皇权文化的极力宣扬、称颂。譬如《上林赋》对上林苑的歌咏,《西都赋》对长安的夸饰,《西京赋》对咸阳的赞誉等等。具体到赋体叙事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先中心后周边的“中央−边缘”(也可称为“中心−四方”)模式:即先以京都为中心,再按照一定方位逻辑分述周边历史、地理、人文概况。而这种“中央−边缘”范式的建立也绝非赋体文学所仅有,在史书论著、朝堂礼仪的制定上也非常多见。《史记》就遵循着“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常”的书写秩序[25](3319);汉代明堂的设立取法天地,呈现出众星垂拱的宇宙图式;两汉墓葬形制以墓葬主人为中心建造,发展成为影响后世的横穴墓室,等等。汉代的京都和皇权文化,既形诸于外在的世俗空间,又植根于内在的仪式场域,“宫殿环绕的帝都象征着汉王朝制度化的国家机构,其中包括了宫殿、内阁各部、太子府、蛮夷邸与祭祀和商业中心。围绕着它的是附着于每个皇帝陵墓的一批卫星城。每一座皇陵构成一个二级的政治和社会中心,它们的周围又有一些高级官员或皇亲国戚的陪葬墓。这些陪葬墓也有自己的围墙和陪葬墓,反映出一种逐级递减的社会组织结构”[26]。从表面上看,汉大赋热衷于对京都宫室的刻绘与渲染,实则是文化归属问题上的一种礼仪展示。居于中央的帝京被看做是权力与政治的象征,它对周边的统御反映了文化空间上的主客身份差别、夷夏主次认同,因此对帝京的称颂和宣传就意味着在文化归属上的完全占有。
此外,汉大赋空间叙事还具有宗教与哲学上的双重意义。“中心−四方”的赋体书写模式已经初具宇宙中心论的意识,也就是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谓的“世界中心”。他认为:“完美的中华帝国的首都都是坐落在世界的中央的。因此在夏至那天,日晷仪不会在那里投下阴影。”[27](14)在这里,京都被当作连接尘世与上天的纽带,所以具有了神秘的神圣空间意义。另外,巴比伦的圣山、神庙、宫殿也同样被赋予了这层神圣属性,巫师借此可以“绝地天通”,以实现内在超越。而在汉大赋的描述当中,赋家对皇家宫殿苑囿的热情书写随处可见,那里不仅被描绘成一个“青龙蚴蟉于东箱,象舆婉僤于西清,灵圄燕于闲馆,偓佺之伦暴于南荣”式的“梦幻仙境”[10](367−368),而且更是一个宗教崇拜场所。武帝在云阳甘泉宫立泰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25](1388),并配享通天台,即如班固《东都赋》所言“建章甘泉,馆御列仙”[10](39)。此外,他还在各地分设其他畤、庙、祠以辅助祭祀,这样就形成了以甘泉宫为“神圣中心”、其他宗祠神庙环绕的帝国祭祀体系。这种富于宗教学意义的空间组合是原始巫术、宗教、仪式的混合产物,“从一个中心开始,在四个方位上形成了四方宇宙……它同时又是一幅宇宙的图式和人类居住地的一种范式”[27](19)。在空间上由宫殿、神山、宗庙组成的祭祀体系成了汉代天人秩序中最重要的一环,这就从宗教与哲学上进一步解释了汉大赋为何偏重空间方位叙事的原因。
四、汉赋图志化的意义及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文学特别是汉大赋的图志化倾向最为明显。汉大赋的“图志”化,使它具备了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首先,它所呈现的博物与知类特征,使原本仅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辞赋多了一层属性,它具有了与类书等资料性书籍相近的一些知识品格。尤其是地理场景上的某些征实描写,不仅避免了汉大赋铺采摛文的虚饰弊端,还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历史地理学资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其次,叙事艺术上对空间与方位的重视,扩充了辞赋所要展示的时空维度与物态容量,形成了“时间−空间−物质”三位一体的汉赋审美观,将原来只适合案头阅读的文学语言艺术转换成可供观赏的视觉“空间艺术”,趣味性和画面感有所提升。大赋在这两方面所表现出的功能与价值,是辞赋图志化最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思维逻辑和艺术呈现来看,辞赋与图志又存在明显的割裂与差别。前者属于文学创作范畴,后者属于知识工具范畴,分属两个不同的思维体系,因此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方面,辞赋“博物”化特征不断引导它朝着知识化、专精化的道路发展,许多赋家为了尽可能多地呈现“并存的物态”,专以语言艰深、辞藻晦涩作为大赋写作的风尚,辞赋沦为了类似辞典性质的工具手册,不免使汉大赋日益脱离了文学的本质属性,束缚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辞赋专注内在“空间”化的趋向,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学审美的视域维度,文学形象更加立体和多元,但在体志抒情上的表现日渐孱弱,辞赋逐渐成为模仿图画、地图等的空间表现艺术,辞赋本身的“情”“志”成分不同程度地下滑,叙事手段也日益繁复和僵化。因此,辞赋图志化是一体两面的,一旦处理不好辞赋与图志的关系,就会导致双方相互掣肘或排斥的问题出现。
东汉中后期,汉大赋博物技巧达到顶峰,而图画叙事能力又在减弱,图文关系不断疏离与分化,这导致汉大赋还没来得及转型就被抒情小赋取代。尽管两晋出现了诸如左思《三都赋》这样的大赋力作,卫权还称赞其赋能“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刘逵也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28],但他们对左思赋的着眼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博物与征实,而不是赋的情志抒发。这说明左思等人的努力继续朝着赋体文学知识性与空间化的方向发展,在最重要的情志方面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甚至一度走向了“摄其体统,归诸训诂焉”[10](174)的小学道路,文学写作纯粹成了语言文字游戏与名物知识的辑录与编纂,这就使辞赋过度图志化了。
需要注意的是,汉大赋图志化产生于汉帝国的定型与扩张时期。“体国经野,义尚广大”的时代精神以及图志编纂、图画风尚是汉大赋图志化产生的重要学术文化土壤。辞赋正逢其时,才有了博物知类与重视空间方位的艺术特征。如果这种文化环境一旦削弱甚至消失,辞赋图志化的地位就会大打折扣抑或跌落。从这个层面来看,汉大赋图志化的产生、兴盛,甚至走向中衰,是特殊历史时代下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我们应该理性对待。
[1] 杨义. 文学的文化学与图志学问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1): 83−86.
[2]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01.
[3] 王世贞. 艺苑卮言校注[M]. 罗仲鼎校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 32.
[4]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897.
[5] 桓谭. 新辑本桓谭新论[M]. 谦之校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2.
[6] 谢榛. 四溟诗话[M]. 宛平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62.
[7] 吕祖谦. 宋文鉴[M]. 齐治平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306.
[8] 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3645.
[9] 六臣注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0] 萧统. 文选[M]. 李善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1] 严可均辑. 全晋文[C]//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1958: 2064.
[12] 葛洪. 西京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2.
[13] 许结. 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J]. 社会科学研究, 2008(5): 168−171.
[14] 袁枚. 随园诗话[M]. 顾学颉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7.
[15] 徐公持. 汉代文学的知识化特征——以汉赋“博物”为取向的考察[J]. 文学遗产, 2014(1): 19−22.
[16] 程章灿. 魏晋南北朝赋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193.
[17]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8] 杨晓斌. 地图、方志的编纂与汉晋大赋的创作[J]. 文学评论, 2013(2): 64−67.
[19] 冯友兰. 贞元六书[C]// 三松堂全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243.
[20] 陈寿撰.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158.
[21] 傅修延. 先秦叙事研究[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140.
[22] 朱光潜. 诗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74.
[23] 李立. 论汉赋与汉画空间方位叙事艺术[J]. 文艺研究, 2008(2): 50−53.
[24] 余定国. 中国地图学史[M]. 姜道章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48−149.
[2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6] 巫鸿.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 李清泉, 郑岩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16.
[27] 伊利亚德. 神圣与世俗[M]. 王建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28]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376.
The trend of annals and maps in Han Fu Writing
ZHANG Pengb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The Trend of Chronicles and Maps in Han Fu Writing” refers 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which Han Fu often needs to draw writing materials from the maps and local chronicles. That is to say, maps and local chronicl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knowledge, showing a three-dimensional sense of space in the narrative. This tendency has two representations: the first one is nature history and clustering; the second is emphasis on narrative of space and orientation. And there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chronicles and maps in many well-known Fu. The formation of Han Fu is caus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Han Empir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eeds, the prevalence abou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graphic information and the pictures auxiliary function of enlightenment as well as the grand time spirit of Han Dynasty as its cultur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To some extent, it has changed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expanded the state capacity and spatial dimension of Han Fu, and transformed the literary language into “space art”, but overt pursuit of the trend of chronicles and maps of Han Fu has brought about some disadvantages.
Han Fu; the trend of annals and maps; nature history and clustering; space and orientation
I222.4
A
1672-3104(2017)01−0136−07
2016−04−13;
2016−10−19
张朋兵(1989−),男,甘肃天水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