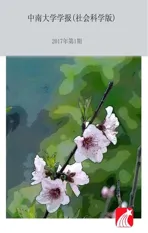对休谟的“道德情感”的两个基础性批判
2017-01-12刘少明
刘少明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对休谟的“道德情感”的两个基础性批判
刘少明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基于休谟的道德情感的情境性及道德情感对指涉对象的依赖性特征,来研判其道德情感论可知:道德情感本身的原发性是可疑的,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道德行为和判断的始发点;道德情感的指涉对象是需要提前被规定的,否则道德情感是十分盲目的。前者对情感作为道德基础的动力特点发出了挑战:要证明情感的原发性,需要排除的环境和背景因素太复杂,要实现理想化的操作几乎不可能。而证明情感的情境性却十分容易。后一个批判对道德情感的清晰性产生了怀疑,而休谟的解决方式是设定道德原则和理想化的人。这样的设定又不符合经验论的认识方法,基础十分薄弱。因此,这两个道德情感的隐含特点,构成了对休谟将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的理论极大的挑战。
情感;道德;情景;指涉
情感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占据着基础性的位置。继承其前辈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对理性道德论的批判,休谟在道德哲学中彻底将理性放置在情感之下,认为道德情感才是道德的唯一支点。那么休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休谟研究专家夏洛特R.布朗认为休谟对道德的基础问题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观念或者印象区分善与恶,或去宣称一个行为是值得赞扬的或应该被批评的。”[1](222)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追溯道德的起源。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休谟列举了四个方面的论据来证明理性不能单独作为道德的起源。布朗将这个四个方面归结为:关于动机的论据;关于真理与错误的论据;关于理性发现观念或事实之间联系的论据;关于“是与应该”关系的论据。[1](224)休谟证明了理性本身并没有驱动力;道德的对错不同于真理和谬误;理性对事物之间关系的发觉永远不会有善恶之分;“是与应该”关系的讨论证明道德感的直接性。既然理性最终不能作为道德的驱动力,就只能指望情感了。因为在休谟哲学中,意志是受情感驱动的,意志本身并不能作为最终的发动机。
休谟谈到的道德情感到底是什么?“从恶发生的印象是令人不快的,从美德发生的印象是令人愉快的”[2](304),这是道德情感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即道德行为使人产生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但也不是所有能产生快乐与不快乐的情感的行为都可以称为道德行为,因此必须对这种快乐与不快乐加上一定的限制。第一个限制就是行为所引起的情感不能涉及个人的特殊利益。“在我们不参照我们的特殊利益,只是在一般地考虑一种品格时,那个品格才引起那么一种感觉或者情绪,而让我们把道德上善的或恶的归于那个品格。”[2](303)第二个限制就是在产生快乐或痛苦的情绪的同时,必须产生休谟提到的骄傲、谦卑、爱和恨中的一种激情,以此来区分其他物体给人产生的情感,原因就在于“不论是骄傲与谦卑还是爱与恨的情感都是由与我们相关的性质所引起。因而,特殊的苦乐感和与我们无关的无生物所发生的苦乐感是不同的,特殊的苦乐感必然具备能够产生骄傲或谦卑、爱或恨的能力”[3]。这说明这种特殊的道德感总是与我们的或者他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品行相关。不仅如此,同情也是道德情感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同情是对别人的感觉的类比,我们通过想象能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情感和感觉。这对于道德的认知有很大的作用。
在对休谟这个理论的反驳中,大多数反对者是从驱动力这个核心部分着手的。如在《道德问题》一书中,澳大利亚学者麦克尔•史密斯就列举了几个重要人物对休谟动机论的反驳。其中托马斯•内格尔就认为情感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事情的理由:“欲望自身,来为当前对于那个对象的追求提供一个理由。”[4](97)(史密斯认为这种观点没有触碰到动机论本身)。麦克道威尔认为“心灵是各种各样的力量或压力……(通过各种信念)获得了一些特定方向上的通道,并最终联合制造了一种合成力量或压力(一个行为)”[4](100)。对于情感与情感对象之间关系的批判上,马克•普拉特认为情感之中总是包含着信念因素,“所有的欲望有牵涉到一些信念的因素”[4](111),以此来反对将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唐纳德•戴维森认为欲望本身是一种规范性的理由(一种理性的信念),“一种欲望适当地被表达为关于我们有规范性的理由去做的主张”[4](139)。总的来说,这些反驳还是对欲求与信念(作为理性的理由)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探讨,从而找出情感在道德行为上的非基础性。约翰•罗尔斯也对休谟提出过批评。“我们的道德情感总是包含了早期训练的痕迹,这个痕迹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的本性”[5],因此他认为休谟没有找出道德的规范性内容,以此认定休谟的道德情感论的失效(事实上笔者认为休谟预设了规范性内容。但是休谟并不承认这一点。
因为承认这一点将会导致其理论内部的矛盾。(对此后文中将会提到)国内研究休谟的著作中,对休谟将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的批判也集中在论证的严密程度上。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时工就认为“休谟的论证有一个很大的跳跃。我们确实不能对他所列举的关系和事实加以道德判断,但尚不能因此就推断从关系和事实中得不出道德判断”[6]。华南师范大学的罗伟玲和陈晓平认为道德评价主要靠理性来完成,情感是私人性的,“只有理性才能控制利己的感情,改变情感的方向”[7]。但是这些批评都不是从情感本身的特性出发来反对将情感作为道德基础的。而本文主要准备从道德情感本身所具有的两个特征(当然,这两个道德情感的特征是针对休谟的道德情感的论述的,其他人的道德情感的特点在这里不做考虑)出发,来论证休谟将情感当作道德基础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这种论证是一种弱的论证,并不期望给出道德行为的最终答案,并没能找出一种新的基础,目的仅仅在于找出休谟道德情感论的缺陷。
一、道德情感的情景性
情境性意味着一个事件的发生总是与一定的环境和背景有关,失去这样的环境,这个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杜威也持有一种道德情景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反省的德行要求对特定的境遇进行考察,而不是固守着某种先验原则”[8](281)。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反对道德先验原则,以利于创造新的道德原则。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阐明道德情感的情境性意味着一种道德情感的发生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之下的,它并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保持着一个人一贯的特征,或是让其他人在任何情况下对同样的行为倒向同样的评价,所以与杜威的主要目的是不同的,而且本文也并没有像他那样完全站在一种理性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待问题。这个论证主要是针对休谟提出的道德情感是对无关自己利害的行为的情感的一种反驳。更为重要的是,情景性将证明情感本身也有原发的动力因素。因为道德情感如果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话,是否说明了环境本身就包含着某种背后的利益去推动情感的发生呢?或者进一步说,环境的改变导致的人的道德情感的变化是否说明了道德情感本身并不是道德的原发点呢?对于此点的论证需要一定的可靠的材料作为依据。
日本学者山田正行在《自我认同感与战争》一书中引用了一个日本兵在经历失去战友之后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变化。“在洞庆作战中失去了赎买不回的战友之后,全部的中国人便成了憎恶的对象。对民间人士的虐杀也变得毫不犹豫。男人就不言而喻了,认为孩子是将来的中国兵,女人生出来将来的中国兵,我如同张牙舞爪的野兽。”[9]在经历失去战友的过程之后,所有的中国人在这个日本兵的眼里都蒙上了一层令人厌恶的色彩,从而在他眼里,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该杀的。而通常我们将这种随意的杀人事件或想法认为是不道德的。
但是在经历这种巨大的变化之后,这个人的意识的变化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道德感变化了,另外一种解释是道德意识被另外的情感和意识压抑住了。在第一种解释中,道德感的情境性就变得十分明显,因为道德感变化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带来的恐惧、愤怒,将不能随意杀人的道德行为的限令变得荡然无存。当这个人再次回忆往事时,他将自己评价为“野兽”,说明已经由战争期间的极端意识变成了另外一种在大部分的文明社会的文明状态下的普通意识了。但他这样做是因为这时候他已经身处另一个文明、和平的社会里面。如果是第二种解释,也就是他那时候只是“良知”被他仇恨和愤怒蒙蔽了住了,那么就必须要设置一种道德上的本体意识。也就是要将道德作为本来就存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动力,只不过会在一定的情况下被掩埋,但并没有被抹去。这样休谟就将面对更大的挑战,因为作为彻底经验论的休谟不能在道德上证明此本体的存在。这在讨论道德情感的原则设置的基础时会着重分析。
当然我们还有第三种解释方式,这种解释方式表面上是有利于休谟的。我们可以说人在某一刻的行为动力是单一的,被一种主要的情感所主导。那么这时候就既不需要掩埋道德感,也不需要道德感的转化。这时候他所有具有的就仅仅是愤怒和恐惧,并没有道德感在起作用。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恰恰证明了道德感的情境性。因为道德感只有在其他情感不参与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才会占据主导。那如何让其他情感不发生呢?那就需要设置一个理想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都心平气和地感受到某个行为带给我们的快乐与不快乐。更为重要的是,里面不能掺杂任何关于自己身份相关的认同感。也就是说,宗教、地域、文化、家庭、个人状态等因素都要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仍然可能导致产生与道德无关的情感或认知,来使道德情感不发生作用。这时候我们将会实现一种理想的道德感。但是这些因素往往是不能被排除的,只能通过理性来实现这一理想化的操作。结果就会导致对休谟理论的反对。
由此,日本兵道德感的变化是被情景所主导的。事实上,这种情景背后包含的是一些认知的背景。比如作为国籍和信仰上的对立等因素,都加强了这种情境性。而且,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出现在日本兵身上。成吉思汗手下乘其骏马、占其土地、掳其妻子的行为大量实施在其他民族的人民身上,但是却很少发生在己方阵营里面。不仅如此,同样的情感也会以同样的作用传递到相隔很远或很久的人。如主要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的中世界研究专家普拉茹就热情洋溢地说:“如果十二世纪拉丁人的远征完美地实现了目标,对于现代欧洲的智慧来说,东方不再是一个需要征服的世界,而是需要一份需要看管的遗产。”[10]显然,作为法国人的普拉茹更加赞赏法国前辈的丰功伟绩,而将东方看成是需要征服的世界。这不仅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伟大冲击和拿破仑对欧洲国家的征服),还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所以才能同情十字军所做的事情,大力提倡将十字军东征当作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材料。我们所看到的其同情也是情境性的,其背后的宗教、国籍、时代和作为历史专家的自豪感激发了他的这一观点。所以“同情只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只要满足类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任何人的任何情感都可以得到某些人的共鸣,甚至强奸犯的快乐也不例外……仅由个人同情心并不能构成道德评价的规范或标准”[7]。
尽管“休谟认为,一个行动、一种情绪、一种品格之所以被认为是善良的或恶劣的,那是因为人们一看到它,就发生一种特殊的快乐或痛苦……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德与不德归根到底都是由快乐与不快乐的感觉决定”[11],但是如果道德情感的情境性是对的话,休谟提到的道德是无关乎自己利益的行为所产生的快乐与不快的情感的说法就面临着挑战。更为重要的是,道德感本身并不是行为产生的出发点,而是情景的中介。道德感成为其自身的原因是可能是外在的、被限制的(内在的发动力成为主导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作为直接的道德情感还是同情产生的道德感都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此一来,道德情感不同于其他情感所具有的根本特征就被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做出道德判断除了有一定的偏向爱好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情景、背景在影响着我们的偏好。所以作为动力的道德感就是说不通的,作为道德判断标准的道德感也是说不通的。那这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情感是否是道德情感呢?或许只是掺杂了各种背景与情景因素的混合情感呢?这时候理性的强大作用就又会再次被想到。正如麦金太尔所说,“情感主义必然抹杀操纵性的(manipulative)与非操纵性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任何真正的区别”[12]。而从道德的情境性和背景性的特征的分析出发就可以避免这一巨大的缺陷。
二、道德情感与指涉对象的依赖性
一种情感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休谟也承认这一点。在道德情感产生之前,总会有理性对于事物之间联系的判断。“在道德判断中,所有的环境和联系必须被提前知晓;开始完整沉思的心灵就会感觉到一些爱与厌恶,尊重或鄙视,赞成或责备的印象。”[13](161)。没有这种对于事物之间的联系的充分认知,将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情感。休谟列举的是俄狄浦斯杀害其父拉伊俄斯的例子。他认为“他对于环境中的联系是无知的,无辜和非故意地形成了一种与其实施的行为相关的错误观念”[13](161)。尽管如此,休谟仍然认为理性本身对于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没有推动力和激发能力。因为不管我们从从事件中发现了什么,都仍然不能说它是道德的和非道德的。仅当我们作为观察者本身有某种情感上的偏好的时候,才能对其进行道德上的判定。正是愉快与不愉快就成了道德判定的基础。
可休谟在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道德情感本身的指向性问题。因为即使道德情感作为一种具有发动能力的出发点,但是这个出发点本身已经包含了对象的信息,否则快乐与不快乐本身就显得很盲目。“道德认知是道德情感形成的逻辑前提。”[14]。在俄狄浦斯杀害拉伊俄斯的例子中,休谟之所以认为他是无辜的、非自愿的,从而其杀父的罪行带来的道德的上的厌恶降低了不少,是因为他已经提前意识到自己的道德的谴责里指涉的是故意杀人的罪行,而非无辜的误杀或自卫的杀人。这种关系就如康德的知识论里面慨念与直观的关系。概念无直观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没有较为明确指向的道德情感将是十分盲目的。
这种解释如此明确,为什么休谟还一直强调道德的基础是情感而非理性呢?因为休谟对于感性和理性本身的关系的认识建立在十分强的概念区分上,情感就是情感,理性就是理性。所以他会认为即使在道德情感前面已经有了理性的判断,这些判断仍然需要道德情感做出最后的发动证明,否则将与道德无关。迈克尔•史密斯将这个教条归结为“信念与欲望是不同的存在”[4](120)。这个教条确实说出了休谟情感道德论的核心。我们上面谈到的情感对象必须具有指涉的对象的理论能否反驳休谟如此强的存在区分呢?在我们的情感必须带有指涉的理论中,情感与对象之间的存在关系是怎样的?史密斯进一步追溯这个问题,又将信念与欲望的存在问题归结为信念与欲望是否可以分离的问题。可分离就意味着休谟是对的,发动机只能是欲望(情感)。不可分离就意味着欲望本身也不能单独作为道德的基础,而是二者共同发生作用作为道德的基础。在《道德问题》一书中,史密斯提出的反休谟论者的论证方法始终围绕着信念是否必然导致欲望的问题,也就是认知的对象是否必然导致情感的问题。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太过复杂,需要对大脑的运作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我们这里最终的目的还是通过情感自身的特点来进行论证,不去讨论信念、知识或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因果联系问题。而只是通过证明情感如果没有恰当的指涉,休谟的情感理论将会陷入矛盾之中。
再回到休谟对道德情感所做的两个限制,第一个是强调道德情感是与自身无利害关系的一种快乐与不快乐的感受。另外一个是伴随骄傲与谦卑、爱与恨的情感。这两重限制本身就说明道德是包含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否则我们将会对任何道德感情都没有恰当的概念,道德情感就会被当成其他类型的情感。所以罗尔斯才会说“休谟只是纯粹给出了一个道德的心理学的解释,而没有给出道德的实际内容”[15](51)。当休谟说小树害死大树不等于谋杀的时候,不等于说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对于小树与大树的之间关系的爱好倾向(道德倾向)的排除。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小树杀害大树,那么我们如何第一次见到小树杀害大树的时候就清楚明白地认为这不是谋杀呢?这说明虽然我们不可能经历所有的具体的事件,从而去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倾向,但是,我们已经有了某些内心的道德原则(这个例子中明显的就是小树杀害大树已经被当成了自然物的生长,而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不在我们的道德倾向之中)。排除这个原则来进行道德判断是不可能的。当然,休谟还可以说我们有对某一类物的行为的情感倾向,有了这一类的倾向之后就会自然产生道德情感了。可事实是,对一类的物的倾向本身也是一个原则,一个更加确实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所谓的道德情感的指涉(严格说来这个原则应该是对某一类行为的归纳和对其他类行为的排除)。排除这个指涉对象,对俄狄浦斯杀害拉伊俄斯的观察将是不可能产生道德感的,因为这其中将涉及到对故意杀人的认知,涉及到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认知,更是涉及对其他关系的排除。没有这个指涉,道德情感将是无从发生的。因此,以上的论证有效地排除了所谓的苏格拉底魔咒:“事物是快乐的,所以才是善的,还是因为事物本身是善的,所以才是快乐的?”[16]也即是,道德情感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对一类行为的倾向,这种情感就可能是随意产生的。另一方面,站在道德观察者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对自身利益的排除,那么如何证明对于从中产生的骄傲感或恨的感觉这些情感就是道德感呢?因为它也可能是所谓的自然感觉。所以倾向都是有指涉内容的,没有指涉内容的的感觉无从谈道德与不道德。因此并不如史密斯认为的那样是“信念和欲望的偶然性共存”[4](120),反而信念和欲望是必然共存的。而且这种共存不是信念导致了情感,或者情感导致了信念(这里的欲望和情感是混用的,在休谟那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分),而是情感本身就是包含了信念的。
当然休谟的支持者也可以说道德情感完全是主观的,不需要任何规范性的内容。比如拉塞尔•哈丁就认为“他给予了我们一个论据,证明为什么没有道德的真理性内容,因为道德本身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15](51)。这样的说法表面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因为情感本身就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但是假如贯彻这个原则到底的话,任何对道德的限制就将成为多余的。也即是,如果道德完全是主观的话,休谟如何知道道德感本身是与个人利益无关呢?他如何知道一定会有骄傲与谦卑、爱与恨的情感伴随呢?他又如何知道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不能当做道德关系呢?所以,尽管道德情感本身是主观的,但是其指向的对象必定符合某些原则,才能被定性为道德关系。尽管这些原则本身是随着国家、宗教和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变化本身指的是道德情感指涉对象的变化。情感永远都是快乐与不快乐,赞成与不赞成。而且,原则本身变化之后,符合这个原则的关系是否还能称作道德关系,也是需要最终辨明的。“休谟在讨论道德时,认识到道德理论很容易使道德评价流于主观偏见,为了避免这一点,他也在暗中小心翼翼地借助理性的力量。”[17]。
所以我们现在来回答上面提出的那个疑问:情感与对象之间的存在关系是怎样的?答案是道德情感是包含了其对象的。所以二者本来就是一体的,说到情感,就不意味着单单谈情感,它已经谈到了其对象。所以,我们就可以反驳休谟的情感和信念是不同的存在这个教条:情感和信念是一同存在。而这个信念就是理论性的信念,是关于一类事物的认知上的信念。因此,从情感包含其指涉性内容的结论来看,休谟将情感当作道德的基础就是片面的。因为他一开始就将情感和理性分得如此清楚,以至于看成一种线性的关系。仿佛理性只是水管,而情绪是水龙头。如果水龙头不开,则水管里面的水流不出来。而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理性信念是水,情感是水龙头。二者从来都是一同发生作用。休谟看中的是情感的发动作用,而对于一杆大炮来说,没有炮弹,其发动作用根本就是无效的。大炮与炮弹不能分开。道德情感,即所谓的道德上的快乐与厌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认知基础上的。这个认知可能解释为对于对象的倾向,也可以解释为对于对象的信念。二者纠缠在一起,很难十分清楚地分开。“在道德生活中,只有基于情感体验的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否则,就是空洞的‘理念’,虚无的‘戒律’。同时理性也只有与情感一起,才能发挥制约人的行为的作用。”[18]所以情感不能单独作为道德的基础。
三、休谟道德原则的理论缺陷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道德情感是需要设定一些原则的,尽管这些原则是千变万化、富有弹性的。实际上休谟在进行论证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一些道德上的本体原则。而且在这个原则之外,为了能够对这些道德行为进行恰当的注意和评价,他还提出了“冷静的旁观者”的概念。这些最终将导致与其经验论的认识理论相违背,导致理论基础的薄弱。
首先来看他对道德原则的设置。“我们容易把因利益发生的情绪与因道德发生的情绪相互混淆,并且两者会自然地相互相交融。因此,我们极少认为一个敌人不是恶劣的,也很少能够区别他对我们的利益冲突和真正的个人卑劣。”[2](303−304)为了将个人利益与道德情感分开,休谟提出有一种真正的道德,所以他认为人身上有一种真正的卑劣。当然这种卑劣是针对个人的品行而言的。真正的卑劣是什么呢?休谟没有明说,但这种真正的卑劣就是在一种被设定的道德原则的评判下被鄙视的行为或品行。或者休谟可以说,对于在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来说,对某一类行为有一种天生的或后天的厌恶情绪,我们称这种行为是卑劣的行为。但是这一类本身又需要一种原则,否则何以称其为一类呢?但是若不设立这些原则,就会导致休谟提出的这些所谓的道德感情没法与其他情感区分开来的问题,所以他不得不认为有一种真正的卑劣来防止误认的卑劣。现在问题是休谟如何知道它呢?根据经验主义的原则,所有的道德原则应该都是根据经验印象而归纳出来的。那么休谟如何知道有一种真正的卑劣,而且这种卑劣与作为评价者的我们没有相关的利益呢?同时,这种卑劣带给我们的厌恶的情绪总是与我们自身的骄傲与谦卑、爱与恨结合在一起是如何可能的?也许休谟会说在伦理学里面,经验主义的法则不适用,但是他如何证明这些法则是推理出来而不是提前被设置的呢?如果休谟不知道这些原则的话,他又如何知道德情感是与其他情感不一样的呢?因此,将道德作为情感的基础最终还是要依赖于对情感自身的辨明,而辨明本身需要规则,规则又来源于设定。而这样的设定显然没有任何的基础。
休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提出了一种理想化的人的存在,就是所谓的冷静的旁观者。“这并未妨害这些情绪本身的独立,并且一个沉着并且有主见的人是可以摆脱这些幻觉的支配的。”[2](304)“道德内容——哪些特征是善,哪些特征是恶——是由认可了某种普遍观点的旁观者的反应决定的。”[19]但是很明显,这种人仍然接受了某种普遍化的道德观点。若不如此,如何会对谋杀生厌,对助人为乐赞扬?而且人类接受的普遍化的规则如此之多,哪种才是道德规则呢?这时候我们因为接受某种规则而对其他行为和品行产生的情感是道德情绪吗?很明显,除非我们一开始就认定某种行为是道德行为,否则,这时候产生的情感就不能称为道德情感。冷静的旁观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情感所指涉的对象已经被纳入了他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之中了。这时候反而规则作为了道德的基础,情感只是附属品了。“情绪主义者引入了一个无私的‘理想观察者’的概念,说明了他们需要把情绪根植于认知运算(如可逆性与公平)的土壤中,即那些导致原则的道德判断的运算。”[8](274)所以冷静的旁观者不能解决设立道德规则的无基础性问题。
上面的两个挑战都是建立在休谟的道德情感自身的特点(尽管这两个特点休谟自身并没有提到,但是我们通过我们仔细的思考就可以得出)基础上的。这两个批判也可看成是道德情感自身所具有的在理论上的不完整之处。总的来看,通过对休谟提到的道德情感的两个批判的分析可知:道德情感本身的原发性是可疑的,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道德行为和判断的始发点;道德情感的指涉对象是需要提前被规定的,否则道德情感是十分盲目的。前者对情感作为道德基础的动力特点发出了挑战:要证明情感的原发性,需要排除的环境和背景因素太复杂,要实现理想化的操作几乎不可能。而证明情感的情境性却十分容易。后一个批判对道德情感的清晰性产生了怀疑,而休谟的解决方式是设定道德原则和理想化的人。这样的设定又不符合经验论的认识方法,基础十分薄弱。所以这两个道德情感的隐含特点对休谟将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的理论产生极大的挑战。
[1] Elizabeth S, Radcliffe. A companion to Hume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2]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纹红涛. 论休谟−特殊的道德感[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8(1): 102−105.
[4] 迈克尔•史密斯. 道德问题[M]. 林航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5]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02.
[6] 刘时工. 休谟道德的基础[J]. 道德与文明, 2005(6): 20−24.
[7] 罗伟玲, 陈晓平.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J]. 现代哲学, 2011(6): 72−77.
[8] L•科尔伯格. 道德发展心理学——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9] 山田正行: 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M]. 刘燕子, 胡慧敏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4: 52.
[10] 米肖, 普拉茹. 十字军东征简史[M]. 杨小雪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5.
[11] 王传峰. 休谟的道德感刍议[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2(5): 21−81.
[12] 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M]. 宋继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29.
[13] 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 罗石, 郭敬和. 试析道德情感下的道德行为[J]. 伦理学研究, 2012(1): 14−19.
[15] Russell Hardin. David Hume: Moral & political theoris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 刘隽. 怪异的道德——“休谟问题”的缘起研究[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3: 41.
[17] 张钦. 休谟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47.
[18] 任德新, 张芊. 论道德情感对道德理性与道德意志的驱动[J].南京社会科学, 2016(12): 50−54.
[19] 伊丽莎白·S·拉德克利夫. 休谟[M]. 胡自信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02.
Two fundamental criticisms at Hume’s “moral sentiment”
LIU Shaom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Based on the two features of Hume’s moral sentiment, namely the emotional context and the dependence of moral sentiment on their referents, we can clarify that the primary of moral emotion is questionable in hi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 which in itself is not necessarily ethical behavior and starting point of moral judgment. The moral emotion of referent objects are to be specified in advance, otherwise the moral emotions are very blind. The former one has challenged the moral emotion as the basis of moral force.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testify the primary and to realize the idealized operation as the environment and background factors are too complicated. But it is fairly easy to find the proof that moral sentiments have some backgrounds. The second critic view casts doubt on the clarity of moral feeling. Hume’s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o set ethical principles and idealistic people. This presumption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method of empiricism, which prove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is solution is very weak. So these two implicit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 emotions have a great challenge at Hume’s theory which regards the sentiment as the basis of morality.
sentiment; morality; circumstance; reference
B561.291
A
1672-3104(2017)01−0012−06
[编辑: 颜关明]
2016−03−20;
2016−06−27
刘少明(1988−),男,重庆奉节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14级外国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