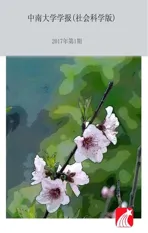“天籁”与“逍遥”
——庄子“听之以气”之审美关照探颐
2017-01-12史建成
史建成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天籁”与“逍遥”
——庄子“听之以气”之审美关照探颐
史建成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心斋”作为庄子提出的修持功夫,其实只是达到“听之以气”的逻辑前提,是为实现“游乎天地之一气”所作的主观否定。庄子继承了“气”字本义,并提升了“气”对于个体、社会、自然的功能意义,提出了“通天下一气”思想。“通天下一气”通过“物化”实现了“气”对于纵、横双向的贯通。在此基础上,庄子阐发了“听之以气”的思想,辩证统一了“听之以耳”和“听之以心”,并将“天籁”思想具体化。“听之以气”打通了人生在世与“道”本体的隔阂,使“逍遥游”的审美理想有章可循。“听之以气”的真人在逍遥游中与道合一,并以道面向世界。
庄子;听之以气;耳;心;道;真人
《庄子·人间世》主要以人间世事为探讨主题。本篇开头假借孔子、颜回问答试图寻求一种谏言暴君的最佳方式。作为儒家贤者的颜回秉持着“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庄子·人间世》①)的治世理想。但在庄子看来,假若谏者不首先安立己道而继续以“名”“知”这样的凶器来对暴君实行教化,结果只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庄子借孔子之口否定了“端虚勉一”“内直外曲”“成而上比”这三种谏言方式,转而寻求一种“存诸己”的向内方式作为安立己道的根本,这种功夫就是“心斋”。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专一你的心志,不要用感官的耳朵来听而是要用心去听,不要用心去听而是要用气去听!耳朵的限度在于它有限的听力,心的限度在于与之相合的情境。然而,气是一种虚空以待物的存在者。唯有道聚集于虚空之气,并且成为气的规定性。人如何达到虚并且听之以气,这就是心斋的功夫。《庄子》历代的注释者极为重视保持“虚而待物”对于主体修持“心斋”的重要意义。郭象认为“遗耳目,去心意,而符气性之自得,此虚而待物者也”[1](153)。明释德清亦认为“颜子多方,皆未离有心,凡有心之言,未忘机也。机不忘,则己不化。故教之以心斋,以虚为极”[2]。陈鼓应则直接认为“气即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灵明觉之心”[3]。当代庄学研究者也大都将修心作为庄子气论思想的核心指向,把“虚静”之心当作这一理论的完成。然而,通过《庄子》文本的整体考察我们发现,“听之以气”的阐发有着内在的理论铺垫,是庄子道论美学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通过“听之以气”,实现“游心”对于道的体察,最终达到“无待”的“逍遥游”。与此相对,“心斋”作为一种修持功夫仅仅只是达到“听之以气”的逻辑前提,是为实现“游乎天地之一气”所作的主观否定。因此,如何理解庄子哲学中“气”的本性以及“听之以气”如何发生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一、“气”字演化与庄子的拓展
在《庄子》的繁体文本中,“气”本作“氣”字。然而,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二者是有差异的。其中,对“气”的解释为“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说文解字》)。而“氣”则为“馈客刍米也,从米,气声”(《说文解字》)。“气”作为云气,属象形,而“氣”则是从“气”字的写法中演变而来,具体指赠予别人的刍米。“气”字作为象形字,其历史早于“氣”字这一点也可从甲骨文中得到印证,日本学者前川捷三认为甲骨文中“≡”字就是后来的“气”字是没有疑义的[4],这一形制表现了一种对于云气流动的模仿。后世虽然用“氣”字假借了“气”字的本义,但对其字形意义上的解读显然不能不归因于“气”字的本来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说文句读》中提到“氣,本或作气,同。是后汉犹用气字”[5]。也就是说汉代及以前还没有出现“氣”字对于“气”的假借,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为何《说文解字》中并没有涉及“氣”字同“气”字本义关系的说法。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先秦对于“气”字的使用与表达实际上是建立在“象云起之貌”的本义之上的。这种表达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中逐渐导向一种普遍性的哲学概念。李存山认为“气概念的原始意义是烟气、蒸汽、云气、雾气、风气、寒暖之气、呼吸之气等气体状态的物质”[6](30),并且“生理、心理、伦理乃至审美等意义的‘气’都由此衍生而来”[7]。在已确考的春秋时期著作中,“气”的概念已经具有了个体、社会、自然意义上的广泛内涵并且成为沟通三者的关键性因素。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国语·周语中》有:“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这里的血气分别表达了个体意义上生理之气和心理之气的意思,李存山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的‘血气’概念就是从呼吸之气和血液升华发展而来”[6](45),由此体现了“气”观念由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规律。同样,对于社会而言,“气”往往也被理解为礼仪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例如“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通过约束个人达到对于“气”所化成的“五味”“五色”和“五声”的合理接受,从而使社会秩序得以和谐。此外,西周时期三川发生地震,伯阳父用气的观念对这一自然现象进行解读:“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天地阴阳之气秩序的混乱造成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自然之气的内涵已经超越了自然云气的象征而成为一个具有功能属性的更为抽象的概念。这一具有功能属性的概念将个体、社会、自然统一于自身,成为它们变化的直接原因,并使三者得以沟通。《左传》中的“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就成为不仅关乎自然、社会变化同时也是人生理、心理产生以及相互关联的关键要素。
就庄子文本而言,其对“气”的阐述显然继承了商周以至春秋时期的观念。《齐物论》中的“大块噫气”,《在宥》中的“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缮性》中的“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众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分别体现了“气”对于自然、个体以及社会的构成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庄子哲学实现了“气”与个体、社会、自然相关联之功能属性的提升。《道德经》中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阴阳二气相激相荡化生世间万物,这种化生并未使“气”成为道之下构成万物的普遍材质。稷下道家的《管子》与《庄子》年代较为接近,其“精气”等同于道,中有“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管子·内业》)。“精气”为“气之精也者”,只有这种精微之气才可化生为世间的物质和精神。“精气”虽然是“生命和智慧的根源”[8],但其具体生成的万物之间却无法达到气化的沟通。庄子的“气论”思想与以上两个文本传达出的意旨有所不同,他不仅强调“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而且将气之聚散理解为万物生成与转化的根本原因,把“气”理解为构成世界的普遍材质,即“故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此外,这种“一气”的观念极为重视“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的功能属性,这里的“通”则具体表现为一种“物化”思想。《逍遥游》里的鲲化为鹏、《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以及“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均是“气”之具体形态间的沟通,这种物与物之间的“气化”使得“气”在纵向上生出万物之外,于横向上又使得具体有形的万物之间得以贯通。这种“气化”思想最终成为庄子寻求“听之以气”的宇宙观基础。
二、“听之以气”以落实“天籁观”
“无听之以耳”的原因在于“耳止于听”,俞樾注解曰:“言耳之为用止于听而已,故无听之以耳也。”[1](153)那么首先,何为“听之以耳”呢?《说文》曰“耳,主听者也”,耳作为主听的感官,其功能就在于聆听外部的声音。《说文》段注云:“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宫商角徵羽,声也。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声和音分别对应于五声音阶和八种人造乐器。《齐物论》中提到的“地籁”和“人籁”就是与二者相关联的表述。“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穴窍,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后者唱喁。”(《庄子·齐物论》)大树身上的许多窍穴形状各异,发出的声响也各有特点。风起,然后自然界的孔窍秉其形质自然而然地发出各自的声响。这便是“地籁”之声。“人籁”之音则与之不同,它是“比竹是已”,是萧管乐器所发出的声响。所以“听之以耳”就是对自然、人为的各种声音进行聆听。
声音的发出虽然率性而动,各称其所受,但作为接受主体的人则不能仅仅用耳朵这样的感官来听。正如《管子·心术上》所言:“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言之分也。”人的感官受心的统辖,感官所接收的信息也必然要为心所思虑。《说文解字》云:“心,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人间世》中“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体现了审美方式中“心”对于“耳”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一种整合的结果。成玄英疏曰:“耳根虚寂,不凝宫商,反听无声,凝神心符。”符即是符合之意,在庄子文本中则是指符合情境之意,这种情境就包含了对于声音的听觉体验。因而,人在审美活动中所把握到的就不仅仅是各种类型的声调及音响,而是有心知参与的情境。也正因为有心知的参与,《齐物论》中各种孔窍发出的声音才会体现出“激者,謞者,叱者,吸者,譹者”等不同情绪的感受。有境则自成一个世界,因而“听之以心”是对“听之以耳”的必然超越。
然而,心的思虑也为“听之以心”的关照方式划定了边界。“听之以心”正如成玄英所说:“心起缘虑,必与境合。”这种心与情境的结合将心知、心虑设定为一种关照世间万物的思维。这种思维使得人不能真正关照事物自身的本然状态,而将人自身种种精神的、心理的要素投射其中。《齐物论》中有“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意思就是人都将自己已有成见的心作为师法的对象,那么谁还需要师法什么呢?在这里,成心便是每个人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前见,所以“成心即被视为是非之分与是非之争发生的根源”[9]。正如《齐物论》中所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知心”最大的特点即在于以“彼是”划分界线并且“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所以,在庄子看来,“知心”是要被否定的,自然“听之以心”的关照方式也不可能得到庄子的赞同。那么为何要“听之以气”呢?就《人间世》来看,庄子提出了“气”可以作为关照世界之“感官”的两大属性:“虚”和“待物”。首先,气的词源是对云气的象形,以至后来生发出来的关于社会、个人身心的气都不可能是有形状的实体,气所具有“虚”的特性在庄子之前就已经成形;其次,“待物”意味着对于有形物体的承载,意味着对于物体运动轨迹的规定,这种“待物”思想实际上是从庄子开始被哲学化的。这两个特性将“气”与“耳”“心”区分开来,也即“耳”与“心”感官的实与“气”之虚形成对照,关照对象的有止与无止形成对照。
在讨论“听之以气”如何实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庄子文本中有关这一理论的铺垫进行考察。我们上文引用了《齐物论》中“人籁”“地籁”思想来论说“听之以耳”与“听之以心”。《齐物论》中,使孔窍发出声响的是“大块噫气”之风,这种风事实上也是气的一种。庄子在论述“人籁”“地籁”“天籁”思想的时候已经开始触发“听之以气”的审美关照。籁的本义是一种箫管,龠的一种,那么与之比附的地籁如何发出声响呢?庄子借子游之口道出:“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滈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庄子·齐物论》)山林中的不同孔窍形状各异,受到气的大小不同,发出的声响也不同。这就是子游所说的“地籁则众窍是已”,那么与之对应的人籁也就是人类的各种箫管乐器,即“比竹是已”。与子游进行对话的子綦道出了地籁、人籁之外的天籁,即“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子綦的回答耐人寻味,因为这种回答并非正面性的阐释,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描述。这种阐发为后世的解读造成了障碍,也因此形成了各种版本的天籁思想。有学者认为天籁就是无心之籁,只要是无心的,地籁、人籁都可以是天籁[10]。有的学者认为天籁是宇宙自然的本体,万物由此而呈现,它对万物是没有任何压力的[11]。将天籁观提升到宇宙自然的本体过于夸大了这一概念,反而忽略了它在整个庄子文本中的寓意。而将天籁设定为无心之籁,实际上是将一种主观修持客观化了。笔者认为,庄子天籁思想意在表明并无人籁、地籁的区分,人对万事万物的倾听都可以达到对于道的倾听,天籁意在消解所有的区分。庄子文本中,天籁思想的提出者子綦是“丧我”之人,事实上也是《逍遥游》中的“至人”。这一“至人”形象将万物视为一,强调透过万事万物表面差别看到内在统一。当子游详细地描述不同孔窍所发出的声音之后,子綦直接否定了这种划分,而将真正的关照方式,即对万物“自己”(自然)的体察提炼出来。这种解读也将天籁的寓言同其后所讨论的去除彼此、是非紧密关联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籁观事实上为“听之以气”的理论阐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听气”说成为进一步深化“天籁”思想的重要环节。
“听之以气”的审美关照方式继承了“天籁观”对于世界区分的取消,将其落实到“气”上。正如我们第一节所提到的,庄子的“气”已经实现了与个体、社会、自然相关联之功能属性的提升,这使“通天下一气”的解释成为可能。《人间世》中进一步落实“听之以气”的关照方式。庄子借孔子之口提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使耳朵、眼睛的感官内通于心,并将知心抛弃,这样子的话鬼神都来归附,何况是人呢!所以,“听之以气”的关照方式并不是单纯地否定耳、眼、心等官能,而是将他们内通于斋戒之心。由于心斋的功夫已经将“心”放空,成为“常心”,所以耳、眼、心对于世界的关照就成为了对世界本身的关照,也即是对自然与道的关照。但这种关照是流动的、充满活力的,因为常心之“气”同世间万物之“气”是沟通的。
三、“听之以气”以达逍遥之境
庄子的美学思想追求一种身心合一的自由,也就是逍遥,那么何为逍遥?《天运》中说:“逍遥,无为也”。“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在于“无事而为”,这同老子的“无为”思想一脉相承。“逍遥”一方面否定了人的“事功”之为,另一方面为人的本性之“为”做出进一步阐发。《逍遥游》中,鲲鹏之游与蜩、学鸠、斥鴳之游并非绝然对立,“小大之辩”才是阻碍逍遥的问题所在。要破除这种对立的辩解,人就应当做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无功”“无名”从而“无所待”于外物,也就能够真正成就本性之逍遥的境界。在庄子看来,贯通于天地的“气”,正是人从自身狭隘视野走向与道贯通并实现逍遥之境的关键环节。
《庄子》有言“通天下一气耳”,“气”成为庄子哲学美学贯通一切存在之物的根本要素。即便在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上,“气”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庄子的人生哲学根本目的在于“体道”并“同于大通”,“道”依然是“自本自根”的本源。“气”在庄子的道论哲学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呢?我们认为“气”可理解为连接存在者与道的根本方式。刘笑敢认为庄子在其哲学中使用“气”概念有三重原因:首先,以“气”作为无为无形的道与具体有形万物间的过渡状态;其次,“气”是庄子“齐物”思想的一个理论基石;再次,庄子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转化,这种转化恰好可以用“气”作为运动过程的中介。[12]其实,还有一个至为关键因素未被考虑到,即“气”是真正实现“道”本体与人生在世哲学贯通的根本方式。这也是庄子审美方式中极言“听之以气”重要性的根本原因。在庄子时代,“气”概念本身已经初步具有本体论倾向(例如管子),并且也有将“气”作为精神修养媒介的思想(例如孟子),但将“气”作为关照媒介同时关联起人与道的只有庄子。
关联起人与气内在关系的存在者是“真人”。《大宗师》详细讨论了“真人”的特点,“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真人”不欺凌弱小,不恃其功德,也不招徕谋士,这样的话,有过失也不悔恨,有成就也不得意,登高履危都不曾使其惊惧,真知之人可以达到道。这里表达的是对其外在特点的描述。另一方面,“真人”在用心方面是“守其宗”之人,其“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庄子·德充符》)。这里“真人”的“守宗”即是“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真人”将万物视为一,自然也就不会有得失痛苦、喜怒哀乐了,这就是他“心”的修持。在庄子文本中,“一”并不意味着一个完整、确定的整体,“一”就是“气”,是万事万物都相同的“宗”,但这个“宗”是不否认事物多样性的。相反,“一”正是在“气”的意义上表达了多样性的统一,正所谓“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庄子·天运》),“真人”“将旁礴万物以为一”,将分疏的万物视为“一”正是把握了多样性中的统一性。虽然在庄子文本中,气并没有参与到所有问题的探讨,但“气”与“一”内在意义上的沟通却把“气”的重要作用体现出来。庄子的“一”是对“气”之意涵的升华和进一步哲学化。这一观念的秉持者在庄子那里也就是“真人”。
“真人”与气的关联是通过“常心”与“游心”实现的。“真人”通过修心来达到与气的贯通。《德充符》中有“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这里的“知”已经不是分别了的“知”,而是心对于世界的“齐一”之“知”,“常心之知”达到的是“未始有物者”。在这种情况下所得之心也不再是与物境相合之心,而是不随物迁化的“常心”。“常心”要求“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庄子·德充符》)台湾学者娄世丽认为“‘自守其宗’是说:守其心,使心成为‘白’(虚气也、神也)的‘虚室’(心斋也),而如此之‘心’,才可能说是‘常心’(有‘道’集之,始能‘常’而不变也)”[13]。所以,真正的“常心”即为一种“虚心”,而“虚”本身即为气的重要特性以及存在形态。所以,“真人”通过修得“常心”而与“气”合为一体。《外物》中有“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磎。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意思是人的躯体是空旷的,所以可以容纳五脏六腑,人的心同样是空虚的,所以才能与天相交游。一方面,人之心同百骸九窍一样需要一定的物理空间;另一方面,心之空间却又是向外开放的,如若顺其自然则可以天游。如果顺从心的本性实现游心则“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游心于德之和”也即是“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庄子·达生》),这样人与世界的关联就不在于一此一彼,也就破除了知心的局限性。“常心”与“游心”是从“气”的的多样性统一中抽离出的两种状态,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它们是“真人”与“气”贯通的两个方面。正如庄子所云“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 (《庄子·天道》)。守宗之“常心”从静出发照见世间万事万物,从而使精神之“游心”能够无所依傍,无所不游,进而使“心”成为“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常心”立足于“守其宗”而不因世间外物变化,“游心”则着眼于天地一气的普遍性进而将游览于千变万化视为“一”中本有。因而,“常心”与“游心”互为两面,“常心”为“游心”奠定逍遥游的基础。
“真人”在与“一气”贯通的逍遥游中,与道合一。《庄子·至乐》曰:“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气”在“芒芴之间”生,“芒芴之间”也就是无,无即是“道”,无生有,这个有就是“一气”。“一气”作为虚而待物者是世间万物具体形态的共同本源,也是运动变化的规定者。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它是最终决定因素,但这种因素隐藏于背后并通过“一气”得以展现。“真人”通过“心”的修养视万物为一(将旁礴万物以为一),并消除彼此,视物我为一(物莫之伤),实现“齐一”。“真人”展现出的状态是“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大宗师》),他的喜怒通于春夏秋冬,与万事万物有所契合而没有终极,最终达到“天与人不相胜”的境界。“真人”在“一气”的贯通之中达到了与“道”的合一,并以“道”面向世界。那么“真人”如何面向世界并展现“道”的关照呢?他在面向世界的时候主要体现为“才全”与“德不形”。在孔子与哀公的问答中详细阐述了何为“才全”与“德不形”。孔子认为,“真人”在面对死生存亡、穷达富贵的世事之变的时候,“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郄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庄子·德充符》)。他使自己的心性不乱,并使日夜变化并无间隔,万事万物自为青春。这样的话,“真人”便以“道”的方式面向他人和世界,使世界的变化和万物发展遵循自己的本性。此外,“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的意义在于,事情的成功、万物的内在之和都离不开自在之德。使德不形,就在于使万物自然而然,而不刻意施予帮助。成玄英注解曰:“夫明齐日月而归明于昧,功侔造化而归功于物者,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天下乐推而不厌,斯物不离之者也。”[1](221)“不形之德”恰恰是以道面向世界的大德,“真人”之“德不形”正是使事物遵循自身由道所规定的德。“才全”与“德不形”一内一外,从两个方面诠释了“真人”如何以“道”面向世界。
四、结语
“听之以气”的审美关照对于庄子美学的贯通作用常常被人忽略,原因归结于学界将“修心”作为理论重点,错误地将庄学局限于一种内在精神超越。事实上,从《齐物论》倡导打破视角、辩说的局限开始,庄子就试图寻找一种如何理解“道枢”的方式。“气”学的发展与演化为这一探索提供了支撑,庄子用“听之以气”勾连了人与道。在这一的审美方式中,耳、目、心的官能统合于对“气”的关照,这是一种人生在世整体生命的关照,它使人与大化流行之气相贯通。在这一贯通之中,真人能够充分“体道”,以“常心”与“游心”的一体两面实现人之本性的逍遥。真人无疑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即启发人们如何成为一个与道合一的人,并以道面向世界。理论的归旨要求我们重视“听之以气”的关照方式,并从此处出发解开诸多问题的症结。
注释:
① 以下《庄子》文本均参见[清]郭庆藩《庄子集释》,2012年中华书局版。
[1]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 释德清. 庄子内篇注[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78.
[3]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18.
[4] 小泽精一, 福永光司, 山井涌. 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14.
[5] 王筠. 说文句读[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25.
[6] 李存山. 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7] 李存山. “气”概念几个层次意义的分殊[J]. 哲学研究, 2006, (9): 34−41.
[8]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65.
[9] 杨国荣. 庄子的思想世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14.
[10] 王博. 庄子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05.
[11] 刘坤生. 庄子九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33.
[12] 刘笑敢.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37.
[13] 娄世丽. 庄子气论探微[M]. 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0: 103.
Sounds of nature and free travel: Aesthetics of Chuang Tzu’s “hearing through Qi”
SHI Jianc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s Chuang Tzu’s cultivation effort, “xin zhai” is just the logical basis of hearing through Qi and the subjective negation to fulfill “the Tour of Qi within the Universe.” Chuang Tzu inherits Qi’s original meaning and upgrades its functions for the individual, the society and the nature. He puts forward “Overall Qi under Heaven” which realizes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connection of Qi. On this basis, Chuang Tzu elaborates “hearing through Qi,”which dialectically unites “hearing with ear” and “hearing with mind” and embodies the thought of sounds of nature. Hearing through Qi breaks down the barrier between being alive and Taoist ontology and offers rules for “free travel.”The authentic person who hears through Qi is integrated with Taoism with which to face the world.
Chuang Tzu; hearing through Qi; ear; mind; Tao; the authentic person
B223.5
A
1672-3104(2017)01−0006−06
[编辑: 颜关明]
2016−06−21;
2016−09−21
史建成(1990−),男,山东莒南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学原理,环境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