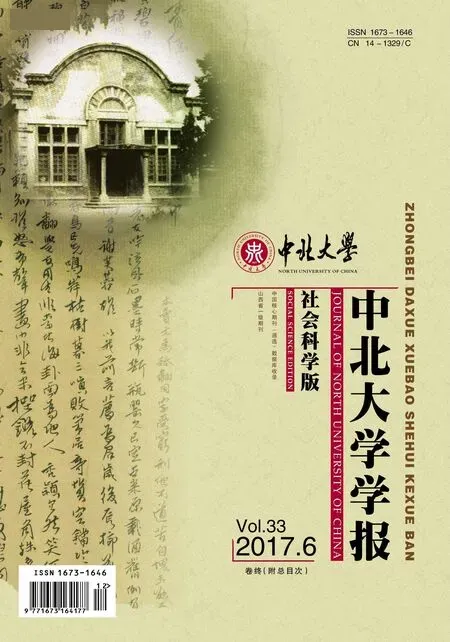论《大闪蝶尤金尼娅》中威廉的自我身份构建*
2017-01-12刘竹婷
刘竹婷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论《大闪蝶尤金尼娅》中威廉的自我身份构建*
刘竹婷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以安东尼亚·苏珊·拜厄特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天使与昆虫》中的第一篇《大闪蝶尤金尼娅》为基础, 着重从三个方面探索主人公威廉·亚当森的自我身份构建过程, 即威廉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对自身达尔文式认识偏颇的摆脱以及与马蒂·克朗普顿关系的改变, 还原了威廉作为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的精神成长历程, 也彰显出拜厄特对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自身情感以及精神价值追求的肯定, 体现出她深切的人文关怀。
《大闪蝶尤金尼娅》; 安东尼亚·苏珊·拜厄特; 威廉·亚当森; 达尔文主义
0 引 言
与对拜厄特成名作《占有》的大量研究相比, 学者们对《天使与昆虫》的关注略显不足。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自1999年以来, 以《天使与昆虫》或《大闪蝶尤金尼娅》为主题的国内外论文只有寥寥几十篇。 从内容上看, 有对小说中较明显的类比与隐喻和性别化建构进行的分析, 也有从新历史主义及后殖民主义角度对作者怀旧观和立场进行的阐释。 金冰从微观角度分析了这部作品中的变形与成长主题[1]、 达尔文主义与自然神学之争[2]及英国性元素[3]。 纵观这些研究, 尽管有学者提出了主人公威廉的成长问题, 但还没有具体系统地对他的身份构建过程进行过梳理。 本文通过对主人公威廉的自我身份建构过程进行分析, 探讨其成长的主题, 从而进一步阐释作家本人的人文生命观。
“我是谁”这个问题已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之一, 这在拜厄特的作品中表现地尤为明显。 从她的四部曲中一位女主人公弗莱德雷卡两次问到“谁能告诉我我是谁”[4], 到她的成名作《占有》中罗兰和毛德在对别人的身份追寻中发现了自己, 再到《传记作家的传记: 一部小说》中纳森在为被立传人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立传的过程中偶然形成了对自我的肯定, 这一切都昭示着拜厄特对其主人公的自我身份发现过程的关注。 《大闪蝶尤金尼娅》(又译《尤金尼娅蝴蝶》)的背景设置为19世纪60年代早期, 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对维多利亚人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自然神学”与达尔文主义的交锋使人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感, 达尔文的“本能即宿命”“自然选择”以及“适者生存”等理论使人的意志、 自由、 理性等主体性概念失去了它们曾经具有的重要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 作为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的青年科学家威廉在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 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
《大闪蝶尤金尼娅》是一部达尔文主义者的自我精神成长史。 主人公威廉·亚当森是19世纪一名生物学家, 他在亚马逊丛林中生活了十年之久, 研究及采集植物标本, 考察生物的形态和地理分布, 但在返回英国的途中突生变故, 导致大部分标本沉入海底。 之后, 他接受了贵族出身并且信奉自然神论的英国国教牧师哈罗德·奥兰巴斯特的邀请, 入住布雷德利庄园, 帮助他整理从世界各地搜罗到的珍奇标本。 在一次舞会上, 威廉被哈罗德的大女儿尤金尼娅所吸引, 很快坠入爱河并留了下来。 然而, 威廉逐渐发现布雷德利庄园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般平静, 这座庄园里其实隐藏着许多肮脏的秘密, 如尤金尼娅与其同父异母的长兄埃德加长期保持乱伦关系以及埃德加仗势强奸了女仆艾米, 而奥兰巴斯特夫人对这一切却熟视无睹。 庄园中的另一位女性人物——家庭教师马蒂·克朗普顿的出现对威廉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她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 热爱科学, 而且爱好观察蚂蚁与写作。 在她的鼓励下, 威廉重拾了对自然的探索及写作的热情, 并最终决定与马蒂一起回亚马逊丛林, 重新踏上科学考察的航程。
在这座貌似城堡的庄园的经历对威廉“王子”的自我身份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使威廉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纠正了威廉对于达尔文主义的认识偏差, 还通过马蒂发现了他自己的精神诉求及自我意愿, 最终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发现, 构建了自我的身份。
1 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初到庄园时, 威廉是感性的, 他被尤金尼娅的美貌所吸引。 “他内心的那只眼睛里只装着尤金尼娅·奥兰巴斯特, 她白皙的胸部从舞裙花边的海洋中缓缓升起, 犹如阿芙洛狄特从海水中的泡沫中升起。”[5]20他还“感觉这些舞蹈完全是专门为了唤醒他的欲望而设计”[5]20。 可以看出, 出于对外表美的迷恋以及对欲望的屈服, 威廉在初到庄园时已有了迷失自我的迹象。 受感性的驱使, 威廉最终用花房里破蛹成蝶的奇观赢得了尤金尼娅的芳心, 并与之喜结连理。 “拉康指出主体的判断必须通过他人来实现, ‘我’不是自我的产物, 而是他者的产物。 自我在他者中生存, 也只有在他者中才能发现自我, 被社会接纳。”[6]很明显, 威廉为了获得尤金尼娅这个“他者”的认同及爱, 忘记了自己的科学家身份及追求, 故他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构建是失败的。 尤金尼娅企图以与威廉的结合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秘密, 因此这个“他者”制约了威廉, 导致其个体发生异化。 “一般认为, 异化指的是, 主体丧失了自我, 成为了不是他自己的那个人。”[7]威廉无形中遭到的异化与他以青年科学家自居的客观冷静的态度形成了巨大反差, 也为他之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婚后的威廉刚开始一直沉浸在肉欲之中, 但在白天时与妻子的交流却近乎为零。 不久, 尤金尼娅怀孕, 她与威廉连见面的机会都变得甚少, 威廉最初为之疯狂迷恋的美也不复存在, 有的只是“那对比例失调、 抢眼的乳房的模样, 跟她的细腰和单薄的肩膀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样子让威廉的体内相应地膨胀开一种不适感”[5]77。 此时, 威廉在尤金尼娅这个“他者”中更加难以实现肉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 于是产生了一种不快乐感, 这标志着威廉开始用理性来思考发生的这一切。
克里斯汀·弗兰肯认为“审美享受、 感官享受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适合解释拜厄特小说的关键主题”[8]。 在经历过感官享受后, 威廉开始用一度失去的理性思考自己的人生。 寄人篱下、 与岳父在思想上的争论, 再加上受马蒂追求自我精神的感染使威廉开始真正反思自己的选择。 三年五个孩子让他感到自身的价值不应该只在于为哈罗德家族传宗接代, 妻子乱伦的事实又提醒他: 人并不和其他生物一样, 只是大自然的偶然产物, 只受生物本能支配, 人还应该受到道德的约束, 人生应当过得有意义。 这种醒悟使他在发现妻子乱伦时如释重负, 甚至觉得自己自由了, 这说明威廉逐渐发生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以至于他最后与妻子见面时异常平静, 并且发现他自己才是导致尤金尼娅不愉快的原因。 与尤金尼娅的分道扬镳标志着威廉脱离了“他者”的制约, 实现了自身的重生和蜕变。 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人生意义及价值所在, 这也是他重构自己身份的开始。
2 达尔文主义思想认识偏颇的自我修正
“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科学发展的时代, 是一个赖尔、 达尔文、 华莱士和赫胥黎的时代。”[2]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自然神学将一切神奇都归功于一位超验的造物主, 而达尔文学说中的“偶然性” “自然选择”以及“本能即宿命”等观点极大地颠覆了《圣经》中上帝创世等的天意设计。 维多利亚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及身份焦虑中。 作为一个在亚马逊丛林中生活了十年之久的科学家和观察家, 一方面威廉“觉得自己深受本人(威廉)的研究——我的观察——影响——相信我们都是物质行为、 变异和无情发展原理的产物, 这就是我的全部信仰”, 另一方面威廉又“说实话, 我同意, 宗教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现出的宗教感——是人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跟烹调知识或反对乱伦禁忌同等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 理智引导我信奉的东西常常又被自己的各种直觉修正过来”[5]37。
“直觉”即本能的作用在拜厄特的作品《占有》中曾有所彰显。 关于主人公罗兰对偶然发现的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艾什的私人信件的偷窃行为, 波·隆登(Bo Lundén)认为背后的动机就在于直觉。 这是一种神秘的、 本能的、 被现代人扼杀了的感情。 身处后现代的各种知识及批评理论的包围之中, 罗兰对理论及知识的信奉导致他只能用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批评术语去思考问题, 而无法用感情去体会。 莫名其妙的偷窃行为唤起了罗兰对自己压制已久的感情及直觉的重视, 他开始正视自己感情的作用。 这次事件“对罗兰和毛德(及读者)的(再)教育发生在情感方面, 在于它发现了理论装置所不能发现的, 那就是: 欲望, 感情和直觉”[9]。 对自己欲望、 感情及直觉的重新重视使罗兰摆脱了理论及理性的束缚, 最终发现了真正的自我。
同样, 威廉的这种理智上对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与其在直觉上对它的修正也恰恰是它思想矛盾的一个体现, 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纠结斗争之中威廉实现了对自我的身份构建。 换言之, 威廉出于直觉的行为以及他之后的经历使他彻底摆脱了这种认识偏见。 达尔文式思想要求个人进行冷静的、 客观的甚至麻木的分析, 要摒弃一切影响科学判断的情感因素。 然而, 威廉却“出于直觉地”对女仆艾米表示同情并对她进行帮助, 他对布雷德利庄园的观察是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 并非科学的。 对其妻子乱伦关系的发现使他无法将埃德加仅仅视为一个跟任何飞禽或者爬行动物都没有区别的动物而原谅他, 因为人不应完全屈从于生物本能, 而应该具有道德意识和社会的规范意识。
因此, 在写作手稿的最后, 他写道: “我曾提到过本能扮演着宿命的角色, 蕴藏在集体而非个体间的智慧的作用。 质问在那个忙碌的世界中蚂蚁是什么, 无异于在问我们是什么, ……”[5]126这段话很明显地表现出威廉已经对达尔文主义心生怀疑, 同时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既然“本能即是命运”, 那么威廉作为布雷德利庄园中的一只默默无闻的“蚂蚁”, 他的命运又是什么, 难道只是为奥兰巴斯特家族繁衍后代的工具吗?难道如蚁后般的奥兰巴斯特夫人的命运就只是履行自己生育的职责而对家里发生的一切都熟视无睹吗?直觉告诉威廉, 他虽然信奉达尔文主义, 但却不能完全赞同, 他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人虽然不是天意设计的, 但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受本能和不可预知规律所支配的动物, 人是具有个体意志和个体生命价值的, 对自我意志和自我精神价值的追求应该受到肯定。 “在对各种话语形式进行辩证思考的过程中, 威廉对自身的认识偏差有所察觉,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本能即命运’的生物决定论思想, 并在麦蒂(即马蒂)的帮助下通过自身的努力证明了人不是蚂蚁。”[10]从这个意义上讲, 威廉通过自身的经历逐渐摆脱了达尔文主义式的思想, 在构建自我身份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3 威廉与马蒂关系的改变
摆脱了对达尔文主义思想认识的偏颇使威廉重获个人主体及个人精神价值追求意识, 他开始踏上漫漫的自我身份追寻之旅。 而与家庭教师马蒂的接触使他进一步明白了“我是谁”以及“我要做什么”。 雷娜·斯蒂维克(Lena Steveker)曾指出, 拜厄特的主人公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他们却感觉到了自身的空虚并参与到填补空虚的活动中来, 从而努力地去构建他们的身份”[4]。 威廉感觉到了这种空虚, 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挣扎, 不过是一段沿着黑暗通道行走的匆匆旅程, 看不到光明的出口”[5]127, 并无意中受到了马蒂的帮助, 与其一起参与到了自我身份的构建之中。 “自我身份具体包括自我这个个体、 不同环境下的他者或者两者的互动”[11], 因此威廉在与马蒂这个“他者”互动的过程中构建了自己的身份。
一开始, 威廉被尤金尼娅的美所吸引, 以至于忘记了自己要献身于人生最重要的事业。 对于刚开始接触的马蒂, 他甚至有些偏见, 心里想着: “她还没有搞清自己的信仰。”[5]35对她的认识也只是: “她语调客观, 异常地客观……”[5]42但马蒂对于观察蚂蚁的执着以及对他的请教使得威廉“既感到快乐, 同时也觉得刺痛, 因为寻猎和搜索的本能再次苏醒过来”[5]41, 他的内心第一次产生了挣扎。 在如愿以偿得到尤金尼娅后, 威廉却不快乐。 虽然他们三年生了五个孩子, 但他们夫妻的日常交流却几乎为零。 这时, 马蒂一次随口的建议让他又投入到有着确切目标的行动中, 那就是设计实验观察蚂蚁。 当时的他“正要说‘你让我恢复了某种希望’, 但又立刻意识到这样说不合适, 甚至隐约有些不忠的味道”[5]84。 这说明此时的威廉已经重燃了自己的研究热情, 但尚未摆脱尤金尼娅的制约。 他与马蒂及其他人一起对蚂蚁的研究甚至实施了三年之久。 在威廉与哈罗德爆发了又一次巨大的关于达尔文主义与自然神学的争执后, 马蒂的建议又一次触动了威廉的心, 促使他完成长久以来不敢完成的事情——写一本实用的书。 马蒂愿意充当助手帮助他。 威廉认为这个提议已经改变了他的前程。 为了书籍的出版, 他们进行了有组织的观察蚂蚁的活动。 这是威廉发现自我的重要一步, 因为任何人都想让自己的成果公之于众, 得到大家的认可。 出于对马蒂的不了解, 此时的他甚至还怀疑马蒂的野心, 他认为马蒂会一直利用他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时, 他“偶然”发现了妻子乱伦的事实, 但他最强烈的感受是他自由了, 而不是震惊或者报复。 事实上, 此时的威廉在精神上已摆脱尤金尼娅的束缚, 正朝着身体上的自由走去。 马蒂适时提出重返亚马逊丛林, 并为威廉扫除了一切后顾之忧。 “马蒂对自身情感和精神价值的追求使威廉无法漠视她个性化自我的存在”[1], 因此在与马蒂这两年的互动交往中, 威廉被她对科学的勇敢追求所打动, 让他最终选择与她一起重返亚马逊丛林探索大自然, 实现其精神价值与物质追求的完美统一。
威廉的经历体现了拜厄特的主人公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 也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在科学与宗教中的一种挣扎。 同时, 他通过自己的经历为其他处于困境中的知识分子指出一条道路, 那就是人的个体生命应该具有自己本来的独特意义, 对精神价值及自我的追求应该受到肯定, 这样才能勇敢地发现自我。
4 结 语
《大闪蝶尤金尼娅》以丰富的内容与独特的拜厄特式“智性”手法描绘了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的精神成长历程。 威廉从最初的感性占主导, 到最后能理性分析自己的经历及计划自己的未来; 从最初对达尔文主义刻板教条的认识到最后摆脱了达尔文式的偏见肯定了个体生命的自我意愿及追求; 从最初对马蒂的无感到最后深受其鼓励勇敢走上了重回亚马逊丛林之旅, 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及身份重构。 这是拜厄特对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焦虑的一种回应, 通过威廉的故事, 她肯定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生命及个性化的自我追求, 也使他们摆脱了对达尔文主义的刻板认识, 体现出她深切的人文关怀。
[1] 金冰. 论“尤金尼娅蝴蝶”中的变形与成长[J]. 外国文学研究,2011, 31(1):61-65.
[2] 金冰. 天使还是昆虫?:拜厄特笔下的达尔文主义与自然神论之争[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3):107-119.
[3] 金冰. 英国庄园与亚马逊丛林——A.S.拜厄特对“英国性“的双重建构[J]. 外国文学,2009(6): 69-76.
[4] Steveker, Lena.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the Fiction of A.S. Byatt: Knitting the Net of Culture[M].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5] [英]A.S.拜厄特. 天使与昆虫[M]. 杨向荣, 译. 海南: 南海出版公司, 2012.
[6] 李畅, 陈连丰. 从拉康的镜像理论看保罗的自我身份建构[J]. 北方文学, 2016(2): 73.
[7] 黄汉平. 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8] Franken, Christien. A. S. Byatt: Art, Authorship, Creativity[M]. London: Palgrave, 2001.
[9] Bo Lundén. (Re)educating the Reader: Fictional Critiques of Poststructuralism in Banville’s Dr Copernicus, Coetzee’s Foe, and Byatt’s Possession[M]. Göteborg: 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1999.
[10] 金冰. 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 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 丁礼明. 论劳伦斯现代主义小说中自我身份的建构与重构[J]. 作家, 2012(6): 86-87.
StudyontheConstructionofWilliam’sSelf-IdentityofMorphoEugenia
LIUZhu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Based on the first novella of Antonia Susan Byatt’s Neo-Victorian novel Angels and Insects,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tagonist’s self-identity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William Adamson’s transformation from sensibility to rationality, William’s extrication of his partial understanding of Darwinism, and the change in his relationship with Matty Crompton, thus, restoring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William as a Darwinist. Besides, it also highlights Byatt’s support of the Victorian’s pursuit of their self-emotion and spiritual values, and shows her deep concern of humanities.
MorphoEugenia; Antonia Susan Byatt; William Adamson; Darwinism
1673-1646(2017)06-0053-04
2017-09-26
刘竹婷(1983-), 女, 讲师, 硕士, 从事专业: 英美文学。
I106.4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