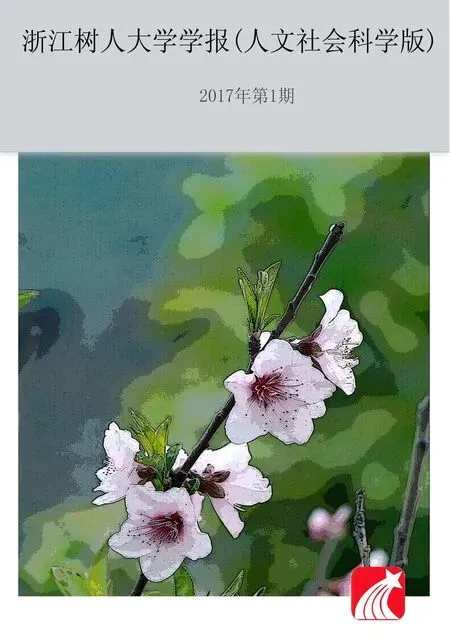“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及其对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启示
2017-01-11李敢
李敢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社会学研究
“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及其对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启示
李敢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在中国近代史与社会学史上,黄郛及其夫人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实践,足以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相媲美。但囿于诸种因素,相较之下,鲜为学界所深知。基于史实梳理、实地调研以及经由对与该活动存续同时期部分社会学家学术思想的重读,将“莫干乡村改进”实践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典型个案,去审视其对于促进新旧乡村建设的学理价值,并围绕新时期农村建设中“村庄转型向何处去”的议题,从“有形”与“无形”双向融合的视角切入,提供若干关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分析性概念暨命题。
黄郛;莫干山;乡村建设;大农业;村镇化
国内学界一旦提及中国近代史上乡村建设运动议题,皆论有晏阳初(1890—1990)和梁漱溟(1893—1988)等方家①晏阳初先生于1926年至1936年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后于1940年至1949年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1950年,晏阳初移居美国,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从事乡村建设活动。参阅宋恩荣:《晏阳初全集(1-4册)》,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3页。梁漱溟先生于1928年开始正式倡议乡治和村治,其乡村建设运动正式启动于1931年1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的建立,历时7年有余。参阅马勇:《思想奇人梁漱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3页。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从业者很多,包括黄炎培、陶行知、卢作孚、彭禹廷、江恒源以及陈翰笙等。,但对黄郛(1880—1936)及其夫人沈亦云(1894—1971)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实践(1928—1950)相对鲜为了解。实际上,莫干农村改良实践的社会影响力在民国时代足以媲美前两者,而其政治影响力甚至远高于前两者。虽然“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只是中国近代史上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片段,但本着发掘旧日乡建史实的诉求,基于实地考证,笔者对“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历史资料予以梳理,且将此案例置于今日新农村建设大环境中进行再审视,围绕“村庄转型向何处去”,提供关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历史与现实、经济产业与社会文化双向融合的分析视角。
不过,鉴于多重复杂因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黄郛一度被定格为“亲日派”软骨头,乃至“汉奸/卖国贼”的罪名,毁之者有,誉之者亦有,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于是,在文章结构上,首先,有必要对黄郛及其夫人的一生作个简要介绍;其次,对“莫干乡村改进”实践脉络予以整体性呈现;再次,探讨“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社会学学理意义;最后,探讨“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对于今日乡村建设的启迪,如当年莫干乡村改进活动原址德清县①“莫干乡村改进”活动主要发生于莫干山下的庾村,原来属于武康县,武康县在1958年并入德清县。当年庾村故地主要位于如今德清县莫干山镇庾村和燎原村。与浙江其他地方乡村建设实践的成绩和不足,以及其可能转化与提升空间等。
一、黄郛与其夫人沈亦云概介
黄郛,字膺白,江苏松江人(今属上海),民国时代风云人物之一,但终生郁郁不得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黄郛是同盟会最早期成员(“丈夫团”团长),与陈其美和蒋介石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其二,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任职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参与过上海光复,是劝退清皇室退位与维护保存故宫博物院最大的功臣之一;其三,1921年,黄郛出任华盛顿会议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又在1924年的冯玉祥“北京政变”时期任职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在此前后,还陆续参与过“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和国民党“清党”等事件;其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郛担任过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927)、外交部长(1928)以及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1933)等职位;其五,1928年5月,黄郛在“济南惨案”处置过程中被蒋介石免职顶罪,在1933年“塘沽协定”处置中再次替人受过。从此以后,身负“反共”“亲日派”乃至“卖国贼”等污名②沈亦云:《黄膺白先生家传(一卷)》,出自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6-67页。③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两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156-159页。④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132页。⑤杨天石:《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76-81页。⑥方可:《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第33页。⑦张学继:《黄郛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66-71页。⑧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第四十四卷人物)》2008年版,第81-87页。。
沈亦云,本名性真,浙江嘉兴人,黄郛第二任妻子。亦云一名为其1906年在天津女师学堂毕业时时任校长的傅增湘所赠,她还为自己取名“景英”。辛亥革命爆发后,沈亦云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1912年嫁给黄郛。1950年移居美国后,沈亦云于1961年写成《亦云回忆》⑨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该著述以史料丰富真实而著称于世。
“济南惨案”后,黄郛即开始退出政坛,隐居莫干山,从事乡村教育与改良事业。“塘沽协定”后则完全退隐,全身心投入“莫干乡村改进”活动,直至病殁。黄郛1936年辞世后,“莫干乡村改进”事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到1950年,离不开其夫人在这数年非常时期的操劳,谓之苦心孤诣以至于殚精竭虑,并不为过。以下按照黄、沈二人两个时期对“莫干乡村改进”事业脉络予以概要性介绍。
二、“莫干乡村改进”实践脉络(1928—1950)
(一)黄郛时期(1928—1936)
黄郛从事“莫干乡村改进”活动,一直奉行“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的信仰理念,倡导以“意远进渐”的温和方式从事乡村建设⑩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6-99页。。
1928年,黄郛与沈亦云在莫干山先购后修“白云山馆”,拟作为退隐之所。初始主要是埋首书籍、吃斋念佛和零星做些善事,其后悉心经营以“耕读并重、勤俭忠慎”为宗旨的莫干小学(1932),主张“以学校为中心,谋农村之改进”。随之依托小学开办农业种养场,以场养校,执行教育与生产实践双结合方式,既可以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学习乡村实践知识,也有助于小学自力更生⑪“以农村教育促农村改进”是当年黄郛办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1932年6月1日,莫干小学举行开学典礼时,黄郛致辞说:“我夫妇二人将来即以学校为家,愿乡村父老予以合作,使莫干小学成为我们农村改进的先声,莫干小学的学生,各个能成为地方上有用的人才。”按照德清籍黄郛研究者朱武的考证,无论是师资、设施还是规模,莫干小学在当时中国都属一流。参阅朱武:《黄郛的教育实践研究》,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23页。。之后,在当地开始乡村公益设施建造,例如“膺白图书馆”以及白云池水库⑫白云池水库兴建于1934年庾村大旱之际,命名取自膺白和亦云各一字。等农田水利设施⑬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黄郛余生以学校教育作为改进农村事业的中心,并试图不再过问“窗外事”。依据沈亦云的记录,黄郛经营莫干小学的动机有三:其一为报德,即“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其二为育才,黄郛目睹当时莫干农村儿童基本目不识丁,痛心于此;其三为帮扶农民,与莫干小学成立同时,莫干农村改进会和莫干农事试验场等从事具体乡村改进工作的机构也相继成立①1934年江南大旱时(甲戌大旱),还在“莫干农村改进会”下面设立了“旱灾救济委员会”,因其组织有方、工作有序,对救助莫干山村灾民、恢复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功用。,它们主要执行自治、自教、自养和自卫四大职责功能②莫干乡村改进之“自治”包括订立山林公约、调解纠纷等;“自教”包括儿童教育、农民夜校、农民教育馆、健身场等;“自养”包括推广改良蚕种、推广改良麦种、提倡造林、水利交通建设、提倡副业等;“自卫”包括壮丁训练、建立消防队、设置医诊室等。,旨在帮助农民举办福利项目与增产增收,改进生活,从而“使得农村自有其乐趣所在”③沈亦云:《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不分卷)》,出自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5-51页。④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23页。。在黄郛看来,乡村改进实践是推进农村改良与改变农民“贫愚弱私”⑤中国农民有“贫、愚、弱、私”四大病为晏阳初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所提出。面貌的不二法则。
在黄郛心目中,农村事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数千年来养国家者农村,而国家尚无暇谋所以养农村者”;从事局部农村志愿工作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乡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身心健康的国民;理想的农村当有“习于农村、了解农村”的基本人才,这些从事农村工作的人才宜渐进知晓农村最需要什么、最厌烦什么,努力做到“上应政府法令,下合地方需要”;农村改进工作可以围绕农民体质、农民技术以及农村市场销路拓展等方面展开。为此,有必要采用现代合作方式和科学技术。农村问题的解决,既须考虑农业机械的使用,也须同时兼营工业;农村建设最终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农村居民种种需要,也可以吸引城市居民长期居住而不只是短期休闲度假,且“自治自卫自教养,相友相助相扶持”的农村不只应在莫干山出现,而应遍布全国⑥沈亦云:《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不分卷)》,出自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3-61页。⑦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133页。。
(二)沈亦云时期(1936—1950)
1.1936—1945。1936年底及以后,夫君赍志而殁,江浙随之相继沦陷,对于沈亦云而言,“莫干乡村改进”事业何去何从,自然是极大考验。例如,在日军数次侵犯莫干山和庾村期间,黄郛生前悉心经营的莫干小学、文治藏书楼以及教学设备器材、宿卧用具和饲养场的家畜屡屡被日军劫掠吞噬。“断炊”是常有之事。
在将位于杭州的唯一住宅捐献给国家用于抗战经费之后⑧卢沟桥事变之后,沈亦云立即将他们夫妇位于今杭州市南山路105号唯一住宅及附属财物捐献给国家,“以供抗敌之用”。参阅:项文惠:《寻访黄郛别墅》,《浙江档案》2001年第3期。,驻留于莫干山的沈亦云首先接手了黄郛生前主持的改进会之“庾村公共仓库”,为地方农民融资与生活提供帮助,这是黄郛隐居莫干山期间从事的多项乡村建设活动之一。1937年底,因时局骤变以及出于对沈家人身安全的考虑,政府力劝沈亦云去上海避难。到上海后,沈亦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信给留守在莫干小学的时任校长郑性白,了解小学情况,继续出资维系小学运营。在郑性白及其夫人李雪钧以及其他亲友同仁的鼎力支持下,莫干小学全体教职工历经艰辛,在时时警戒和日军侵略的战火中顽强生存,还因时制宜地开设了“临时中学”,每个学期都不存在完全停课情形,直至抗战胜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体校董事会示范与支持之下,当时莫干小学全体师生不仅维系了战时义务教育的秩序,还以铺修道路、节食捐粮和担架救护等方式协助政府军抗战。与此同时,沈亦云等人继续从事救济灾民与其他相关乡村农事改进工作⑨罗永昌:《黄郛与莫干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199页。,以知行合一的实践,落实了“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的理念。在这期间,莫干乡村教育与改良工作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培养了一种患难不屈的精神、为国家与乡村建设全身心投入的志趣,即以“对农村之热心报以对国家之贡献”⑩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91-592页。。
2.1945 —1950。抗战胜利之后,对于沈亦云等热衷乡村事业的人士而言,除了莫干小学的复建之外,亟待开展的还是既有农村改进事业的推进,因为庾村公益事业是黄郛退隐政坛后的最大志愿。在亲友同事的共同努力之下,沈亦云确立了庾村改进事业当奉行“以生产之力,扩充教育,以教育之功,改良农村”的复建方针①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庾村教育和农事工作再度得以紧密结合。庾村复兴计划执行后,主要有两件工作值得肯定:其一,一度名扬江浙的莫干蚕种场即发展于此阶段,蚕场培养的“天竺牌”蚕种在当时业界口碑极佳,该品牌延续至今;其二,在沈亦云等周旋之下,受益于联合国救济总署资助以及宋美龄赠送的50头乳牛和2头种牛,“莫干农场”得以快速建立。让当地人喝上牛羊奶也是黄郛生前的一大夙愿。
浙江和上海相继解放后,出于综合权衡,沈亦云同意将莫干小学以及庾村蚕种场、奶牛场、农场、林场等资产悉数捐给当时的政府管理,仅保留墓地、藏书楼等用作“纪念”。沈亦云随后在1950年经我国香港地区去了美国,直至去世,未曾再返回莫干山。
概而言之,在黄氏夫妇等人的精心呵护下,历经20多年的努力,莫干乡村改进工作稳步发展,并初显成效,当地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进和提升;而在1934年江南大旱时,相较于周遭饿殍遍野的情形,庾村无灾民饿死;庾村无失学儿童,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是莫干小学毕业生,乃至有父子叔侄同校同呼先生的佳话②罗永昌:《黄郛与莫干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219页。。这期间莫干小学的毕业生中,既有从军抗战捐躯者,也有其他以不同专业知识服务地方和社会者,一些毕业生至今尚健在③参阅《黄郛与莫干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6页)著述中附录的系列访谈。2015年8月31日与9月1日实访时,作者罗永昌与德清县莫干山镇工作人员对此也有介绍。。
当时的浙江人民政府对于黄氏夫妇等人的奉献予以了充分肯定,曾复函沈亦云:“台端在莫干山所做生产教育事业,已有相当成绩,请本为人民服务意愿继续努力。”④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62页。
三、“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学理意义
关于“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本文侧重从与其存续同期的部分社会学家(尤其是专长于农村研究与社会调查者)学术思想评议着手。这个写作思路多少启发自本议题主角缘故,即黄郛先生的连襟、中国社会学最重要奠基者之一陶孟和先生(1887—1960)。另外,从社会学及其运用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两大特色:一是包括农业实验主义、农村合作运动和乡村教育等板块在内的“乡村复兴”运动风行一时;二是在那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发展,除陶孟和外,还有陈达(1892—1975)、孙本文(1892—1979)、陈翰笙(1894—2004)、李景汉(1895—1986)、言心哲(1898—1984)和杨开道(1899—1981)等一批学界翘楚,他们在国际社会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尤以系列社会调查与乡村建设议题成果最为突出。
本文之所以一时埋首于“故纸堆”,也是找回濒临“丢失”的民国时期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尝试⑤田毅鹏:《找回“丢失的传统”》,《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2页。。用陶孟和先生的话来概括,是因为历史的功用在于明白现在的情形和思想,而要明白现在,需要对过去有充分认知,需要先知其如何经过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68页。。以“莫干乡村改进”实践所处时代社会学家的学术思想去反思这场改良活动学理的研究方式,也许具有一定的拓展价值。
(一)民国时代“乡村建设”与“莫干乡村改进”灵魂为何物
关于“乡村建设”一词何时进入理论界“大雅之堂”,学界有一个共识肇始于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对此也有关于乡村建设是什么、由来、意义、关键以及救济乡村和创造新文化对于乡村建设价值功用一类相关论述⑦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共8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在那个时代,相近主张在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卢作孚、彭禹廷、江恒源以及陈翰笙等先贤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欲以局部渐进的乡村改进和农村复兴方式去救治和振兴中国。孙本文曾明确指出,农村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建设的四大类问题之一,其中尤以土地问题为甚①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1页。。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家国离乱的非常时期,其中尤以乡村破鄙为甚,包括乡村教育、农村实验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改良救国”呼声不绝于耳。因而,“莫干乡村改进”实践正是当时国内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产物或者缩影②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考证,参阅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第22-38页;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页;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9页;何建华、于建嵘:《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第33-39页;徐秀丽:《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第20-26页;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第13-18页;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32-37页;李金铮:《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江海学刊》2013年第2期,第42-46页;李金铮:《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文史哲》2014年第10期,第21-26页。以上文献是改革开放后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相对“有分量”的文献,但对“莫干乡村改进”都未提及。。
黄郛认为,乡村事业是中国的根本。他隐居莫干山之初所目睹的农村种种困苦,正是其萌生兴资办学、从事帮扶农村事业的一大动力源。关于“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第一点价值意义即在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陶孟和那样的研究者,还是黄郛那样的实干家,对于乡村建设都有着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一种敢于担当的执着坚韧。这种担当尤其体现于当年莫干小学整体教职工团队在抗战非常时期的努力。在他们身上,可以见到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风采与品格。因此,莫干山乡村改造活动最大成果之一在于对秉持家国一致专业性乡建精神的培育,对成为陶孟和所言“有责任心的人”③陶孟和:《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的肯定。在再度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这种执着与担当的乡村建设精神尤其值得继承与发扬。
(二)“莫干乡村改进”何以存续——多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④“多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为钱理群先生针对问题百出的教育现状,依据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提出,参阅钱理群:《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随笔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本文借此语去论证可行性乡村改良思路逻辑,其中“主义”在本文指的是,在乡村建设议题中,轻田野考证,重数字推演,为了理论(模型)而理论(模型)的研究取向以及那类只见到乡村“土地”重要性,而未能有效关注“土地上的人”限定性因素的“纯理论性”命题假设的构建和检验类的操作理念与方式,其忽视历史与现实的多元综合,试图得出某种普遍性、可复制性的结论。
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背景着手,“莫干乡村改进”无疑是一场地方化的社会进步实践,尽管相对于当时整个武康县乡村建设而言,黄郛从事的莫干小学乡村教育及其附属农业试验只是一种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但改良工作也只能循序渐进才能得以运作和持续。或正如李景汉所言,农村社区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于调查而言,应用具有首要位置,为此,一要发现事实,二要说明事实⑤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星云堂书店(1933);《民国丛书第三编03017-4》,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1-22页。。而孙本文也认为,乡村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其地方性和时代性予以充分估计⑥孙本文:《孙本文文集第一卷之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于是,乡村改造适宜以技术、经济和科学为主,而以宣传为辅⑦杨开道:《农村问题》,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21页。。杨开道此语,或可用作对“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秉性的一个不错注脚。倘若抛开其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纵览“莫干乡村改进”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农村生活三大块,即自治、经济和教育⑧杨开道:《农村政策》,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9页。,均具有明显的专注于实践而远离空论的风格。
就“莫干乡村改进”实践整体而言,这种“多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的务实风格具体是指,反对空谈、不求“根本解决”,只求“逐步解决”,主张面向实际问题的探究与求解,经由不断的实践和实证,奉行实干兴村与科学兴村之准则。关于实干兴村,借用杨开道的论述,农村问题不是单靠喊口号或“理论研究”即可以解决,乡村改良第一步是了解真实的农村,应如诊病一般去弄清楚病症的诱因与病理,然后才可能找到解决之道①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9-11页。。比如,务必先弄清楚农村建设的主体问题,而只有具有自己意志、能力和工作的“村民自己”才是乡村建设的主体②杨开道:《农村自治》,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7-10页。。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动性,聆听农民的声音,深入农村,细心考察特定地域乡村社会特定需求的实际情形(如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竞争优势、自然条件和文化底蕴等),实地田野研究农村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继续摆出“为农民做主”的官学精英高姿态。科学兴村指的是农业生产需要及时吸纳新科技,乡村改进事业的持续推进离不开技术与理念的与时俱进。黄郛不但重视一般农业发展,还倡导农村市场拓展、新技术与机械的使用,以及与工业一道发展的乡村经济复兴之路。陶孟和曾指出,“新农业”倡导离不开基于农业机械化与科学化的农业技术革命。于是,不论是论及农民增收,还是论及农业增效,抑或是农村发展,科学作为与理性决策均不可或缺③陶孟和:《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页。。
民国时期,包括“莫干乡村改进”在内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指导意见纷繁复杂,但民国社会学人一般都在扎实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给出自己的见解。李景汉曾指出,关于农村问题症结及其解决办法的争执一直处于胶着状态④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21-123页。。李景汉认为,乡村最缺乏基于自立自强的公民训练以及基于团结合作的道德陶冶⑤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第785-786页。。陈达认为,人口数量与人口品质不匹配为农村问题的主要病根。⑥陈达:《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9-49页。言心哲则将农村病因归纳为赋税、人口、农村组织涣散等九个方面⑦言心哲:《民国丛书第四编04012册-2-农村社会学概论》,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355-359页。,陈翰笙则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地主阶级压迫才是农村建设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⑧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1931),汪熙等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5页。。
尽管在政权性质与乡村社会问题种类与层次等方面,今日中国与民国时期并无多少可比之处,但在新一轮乡村建设中,国内理论界倾向于“坐而论道”状态,至今也无多少实质性改观,“仰望星空”者多而坐言起行者少。例如,走马观花式调查后,过多依赖于“理论或模型”去揣度乡村建设,而不是身体力行,以力所能及的行动去改变乡村现实,远逊于民国先贤对于乡村建设的专一和执着。
因此,对于新时期乡村建设全体利益相关者而言,“多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脚踏实地的作风在今日乡村建设中尤为可贵。也只有如此持续前行,方能孕育出有效解决各地乡村建设实际问题的能力、情怀与智慧。
(三)“莫干乡村改进”的后续理论求索——社会与国家力量如何更好合作
不同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普遍具有救亡图存之诉求,如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关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这一世纪难题的破解,同样面临着诸多压力与挑战⑨自温铁军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三农问题”后,2000年李昌平寄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关于三农问题的呼吁而广为人知。从1982年到1986年,再从2004年到2015年,中央一共发布了17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三农问题重要性可见一斑。而“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前进目标则明确写进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在转型新时期,国家与乡村的各自权力与权利基础的构建都还处于某种程度的磨合之中,即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在各自形态呈现及其角色扮演、功能发挥和互动关系等方面,均处于变动不居的形塑过程中。
近十年来,始于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新农村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莫干乡村改进”一类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涅槃再生⑩本文将“美丽乡村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范畴。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正式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出台《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十二五”期间,受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影响,浙江省制定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广东、海南等省市陆续有跟进。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如今,“美丽乡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代名词。。但这种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新农村建设”,在乡村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与乡村社会发展空间提升等方面衍生出很多问题。譬如,部分地方新农村建设有沦为新农村建筑(外观)建设之嫌,多局限于基础设施层面的造村或并村,而“建新村”运动背后的乡村经济产业、乡村组织结构、乡村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内容鲜有新进展。再如,农村适宜劳动力流失加剧问题,即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浙北浙东地区也并未有实质性减缓,越来越多的农村适宜劳动力流向城市,至少流入附近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镇务工或定居①从浙北、浙东多地的调研来观察,即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留在村中谋生存的劳动力,其教育水准一般在高中以下,这个比例往往占全村人口的80%~90%,有的更高。换言之,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与其留乡村意愿或事实成反比。。其中的利弊得失,不宜简而化之,需要辅之以分门别类、审慎细致的调研与考察。因为其中涉及“村庄转型向何处去”变迁过程中类型、趋势和功能发挥等多重维度,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域乡村的历史文化特色、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既有产业形态以及其他物质性或物质性资产遗存等差异性村庄特质。于是,“村将不村,庄不再庄”既可能是一种遭遇工业化、城镇化大面积“侵蚀”之后村庄的全面衰败或“沦陷”,也可能是一种从传统“农业”型农村向现代服务型农村转变后的升华,在后一类新型现代化乡村中,不仅可以见到传统“乡愁”的点点滴滴再次在萌芽,也可以见到过去一直以城市为载体的便捷舒适现代生活的乡村转移。
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疏而不是堵,例如,可以遵循“一不越位,二不错位”的原则。一方面,国家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乡村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与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空间的改良提升,其中需要由乡村自己完成的事项,尽可能经由乡村自治,借助市场与社会力量去完成,国家力量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宜管得过多、过细②国内目前已经有了一些试点,例如传媒人士陈统奎在海口市古村落“博学里”生态创业,海归艺术家渠岩在山西和顺县许村“以艺术激活乡村”实验,浙江德清“新村落”五四村借力土地流转推动产业升级等,在借力市场和社会力量方面各有特色,但不宜照搬照抄。。另一方面,循序渐进地推进城乡体制改革,促进公共服务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均等化与共享化,有序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新空间。为此,户籍、土地和金融等配套改革措施需要及时跟进。简而言之,今日乡村活力的维系与提升依赖于城乡互动之上既有体制机制藩篱的循序突破,乡村建设诸种问题的解决将更多取决于特定地域内城乡一体化的水准、成本与效果。
四、对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启示
囿于多重因素,“莫干乡村改进”活动的史实与学理价值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状态,亟待进一步发掘。而在其所在地德清县,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则颇为显著③参阅德清城乡体改办〔2015〕4号文件、县体改办2014年城乡体改总体性评估报告和提交于省直机构报告,以及县委书记张晓强(全国“百优书记”之一)于2014年11月13-14日在浙江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美丽乡村”现场会上的发言。。这也许多少惠泽于当年“莫干乡村改进”事业的遗风。关于“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对于今日乡村建设的启示,结合历史和浙北、浙东的调研,得出以下三点总结。
(一)复兴之路,从农村起步,重建乡村社会文化生活
中国目前依然处在复杂的多重转型期,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而言,“复兴之路从农村起步”实为一个重要的抉择。杨开道认为,农村生活是改造农村目标所在,而谋求“全体农民的生活幸福”是其最终归宿④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2-19页。。从农村起步,重建乡村生活,需要细细讨论乡村生活的灵魂是什么,对应象征符号与价值信仰体系在哪里,新时期乡村建设中需要怎样的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两者之间如何结合才合宜等。
与此同时,鉴于文化主要体现于人们的社会性行为⑤孙本文:《孙本文文集第一卷之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仅从日常生活方式完善去观察,今日乡村建设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浙江乡村建设,尽管在“口袋充实”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在“脑袋充实”方面尚有待探索和丰富。比如,基于风俗移易基础上的健康生活方式如何更有效地推广等事宜。黄郛当年在莫干山推进乡村改进实验时就非常看重移风易俗的功用,择其善者而从之,提倡不吸烟、不赌博、讲卫生、守秩序等有益的生活方式。
以乡村精神文化如何重建为例去审视乡村生活议题。在这方面,浙江以“文化礼堂”作为突破口。虽说“文化礼堂”建设目前在浙江蔚为风尚,其出发点也不错,但纵观多地实践,依然较多体现出急功近利“做工程”的政绩观,而非脚踏实地“以进为文”的人文关怀,结果多的是“礼堂”,少的是“文化”①在浙江,有的文化礼堂是将过去庙宇祠堂加以改头换面,且美其名曰反对封建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文化礼堂的主墙上孔子、雷锋和锤头镰刀旗共放,不伦不类;有的文化礼堂连传统拱手礼姿势与汉服穿戴基本要求都没有搞清楚即开始大肆宣扬。政府力量过多参与“思想主旨指导”,约莫为此种现象的一大动因。实际上,政府对于这类文化建设更多应提供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余下事务可由民间力量完成。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按照基层干部解释,依据省里有关文件精神,每一处新建的文化礼堂在占地面积和长宽高等方面必须达到相应规格方可“验收过关”,如此看重硬件标准的“文化礼堂”建设,未免令人生疑。。目前,从杭州、浙北和浙东多地的调研得知,绝大多数“文化礼堂”有沦为“聋子的耳朵”之嫌,其对应的文化惠民活动也大多停留在器物层面的配置上②李敢:《“文化兴国”之悖论:我们的“文化”在哪里?》,《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22页。。除了偶尔有村民办酒席借用场地以及有人员来参观访问时,“文化礼堂”的大门会临时打开,此外基本无人问津。
究竟何为“文化礼堂”,能否在实际中做到因地、因村、因时而制宜,“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有无虑及特定村庄“集体记忆”的复建诉求③集体记忆又称集体回忆或群体记忆,这一概念由涂尔干的学生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首次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从广义来看,集体记忆指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从狭义来看,集体记忆专指非历史学的对历史的记忆。研究层面主要有建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范式,还有两种的“混合式”。?如果有,拟将打造何种“集体记忆”?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又虑及不同乡土社会都具有延续自身文化实践层面与物质形式集体记忆的双重必要性和必然性?在这一方面,历史经验或值得咀嚼品味,陶孟和曾论证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祭祖风俗和佛教等民间信仰对于乡村生活的黏合聚集有着重大功用,重建乡村信仰非常重要④陶孟和:《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2页。。由此观之,传统文化中以家谱和祠堂为标志的祖宗观在“文化礼堂”建设中是否值得倡导,还是只能宣扬那些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人好事?现今浙江新农村建设中开始倡导家风家训复建,但是否家家户户必须都要有自己的家风家训?在这其中,有无注意到现今家庭多为以“核心家庭”面貌出现的“小家庭”,而过去家庭多为以“家族”面貌出现的“大家庭”这一基础性社会事实?
新中国成立已有67年,时移俗易,中华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亟待梳理归位,哪些是“封建文化”,哪些不是“封建文化”,国家宜及早明确,而不宜含糊其辞。
(二)新思维与“大农业”,助推复苏乡村经济活力
如果说重建乡村生活第一步是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建设,第二步则为乡村经济产业建设。陶孟和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振兴中国不仅在于改造农村文化与生活,还要关注农村的社会经济建设,他还亲自组织了一系列县域乡村的经济社会调查⑤陶孟和:《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6页。。依据浙江的调研实际,笔者认为还可从“异业整合”与产业融合等角度出发,对农村经济产业或转型或升级等内容展开研究。
首先,还是以“莫干乡村改进”原址德清县莫干山镇为例⑥莫干山镇,因莫干山在其境内而得名,先后获得全国环境优美乡镇、浙江东海文化明珠、市级新农村实验示范镇和浙江省首批风情小镇等称号。目前已确立“建设特色风情小镇和全省一流的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的目标,致力于建成惠及全镇人民的小康社会。。近年来,以“土洋一体”和“新旧一家”为特色的“洋家乐”⑦按照德清县文创办李姓工作人员介绍,“洋家乐”这个名词是当年他“奉旨作文”的产物,当时需要写一篇关于洋人开设农家乐的报道,直接启发于“洋人+农家乐”这一组合,即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农家乐,包括国际化服务、管理、餐饮、休闲与运动等。群落化发展以及其他类别文创产业的集聚化发展,已成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文创共生已经成为莫干乡村经济产业升级的一条可行路径。伴随文化旅游的发展,以生态农业为标志的现代农业也在莫干山镇快速成长。概而言之,农村经济在莫干山镇既有“生态化”体现,更有“文创化”体现,“软硬”与“新旧”产业融合特色日趋明显。关于新时期“莫干乡村改进下一步可以做什么”的后续关注,最重要的莫过于因地、因时而制宜。比如,能否给各个村庄更多的自主空间由其自主发展①调研发现,传统社会时代“乡贤参事会”正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兴,但在选拔标准、组织结构和功能发挥等方面亟待改善。。基于莫干山实践,一个可能的路径为: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一方面,以文化融合携手产业整合,这是有鉴于文化元素再创造可以为乡村带来不同寻常的生命延续力,而“大农业”②调研发现,在德清部分乡村,原本属于“异质性”的产业已经开始融合发展,此处借用陶孟和先生“新农业”的术语提出“大农业”概念。之间多元、有效的产业整合,则可以成为乡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与源泉。另一方面,支持城乡互动联合发展,从理念价值到技术行为以及空间布局等规划设计均可涵盖在内,采取以“过去(乡村)记忆加现代(城市)印象相结合”的乡村改进方法,努力做到既尊重和保留原有形态(例如民间礼俗的复活),又能容纳新鲜悦动的现代生活(例如新式消费方式的迭代),而要实现这类发展规划愿景,除却知识与技能之外,更需要全体利益相关者的智慧与情怀。
其次,德清县域内一些农村在经济产业发展转型方面也具有此种“软硬(新旧)产业复合化”特色。例如,县城中部五四村以“花花世界”为代表的文化旅游群落,以及位于县城东部东衡村和雁塘村等村落的“中国钢琴音乐谷”文化产业园③德清县多数有影响力的文创园均处于乡镇之中。2015上半年,德清县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0.75%,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9.55亿元,增速为27.9%。而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一个主要标志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或以上。浙江省规定,参评文化产业十强县认定指标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须超10亿元(含10亿元)或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以上。由此看来,德清在文化产业指标层面早已经“超标”。目前,德清县入选浙江省文化产业十强县,为湖州市唯一入选县市(参阅浙文改办〔2015〕2号)。“莫干民国风情小镇”从属于“莫干山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整体的规划与建设,因具有万国别墅和黄郛乡村改进活动遗迹等较为丰富的民国文化元素,以及对当下“民国热”消费的捕捉开发而得名。其理想定位为:突出发掘潜在文化资源,提升既有主题特色,整合产业融合要素。庾村文创园区主要是对黄郛时代蚕种场的改造与开发利用,目前有初步建成的中国首个乡村文创园“清境·庾村1932”与正在建设的“清境上物”和“清境农园”,其中包括全国最大的自行车主题餐厅“乡食”、乡村文化艺术展厅、莫干山艺术邮票馆、光合作用创意邮局、茧咖啡、茧舍、“蚕宝宝乐园”萱草书屋,以及黄郛莫干农村改良展示馆等文创单元。“中国钢琴音乐谷”已经被列入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122工程”中20个重点培育文化产业园区名录(参阅浙宣〔2012〕55号)。。基于地域化乡村产业发展特色,此类乡村产业转型或可涉及对既有“农业”概念的某种另类理解。比如,农业或许不只是第一产业,还可以包括更为广义的农村产业,涵盖第一、二、三类产业,只要有助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产业,都可以纳入其中。这种综合化“大农业”发展思路及其转化,或许可以更好地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改良目的之实现。
再次,此种主打生态牌脱贫致富的“大农业”乡村发展模式在浙江省内多有出现。除德清之外,还存在于安吉县余村、湖州南浔区荻港村、杭州桐庐荻浦村以及宁波奉化滕头村等地。其类似之处均在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一体化,大致包括农地规模化、农业企业化与科技化以及农村生态化三大环节。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提出的“大农业”概念,旨在探讨服务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经济产业发展转型的某一种可能路径。当然,也由于此“大农业”概念提法有违于传统产业划分标准,并不适于统计层面用途。至于是否有利于乡村经济产业整合式发展、是否有后续研讨价值,有待于学界批评指正。
(三)“村镇化”: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在旧式城镇化扩张过程中,多的是社会问题丛生的“城中村”与“镇中村”。相较之下,在浙江部分地区,在新式乡村建设中却已开始浮现出“村中镇”。此处的“村中镇”不是指乡村简单地被城镇吞噬同质化或孤立化,而是指乡村生活质量的现代化与城镇化。在这类乡村,不仅可以大致均等地享受到以往以城镇为载体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还可以享受到城市中难得的生态资源。在这种“村庄里的城市”的发展模式范畴内,“城”在村中,村在景中,构建了一幅“乡城一体化”图景,从而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另类标杆。因此,这类“村中镇”同样属于一种新型城镇化的乡村建设产物,尽管往往有“城市”之实而无“城市”之名。本文姑且将此现象命名为“村镇化”。如果从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④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31-35页。角度去观察,此种“村镇化”实际为正向“逆城镇化”的一个体现,体现了别具一格的乡村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路径以及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或可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种特定类型与阶段。
The Practice of“Mogan Village Improvement”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urrent Village Construction
LI G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8,China)
In the modern history and sociology history of China,the practice of“Mogan Village Improvement”,led by Huang Fu and his wife,is comparable to the rural construction advocated by Liang Shuming and Yan Yangchu.However,in comparison,due to various factors,it has rarely been understoo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field research,as well as re-examining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some sociologists in the same period,this paper treats the“Mogan Village Improvement”practice as a typical case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chang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o examine its academic value in promoting new and old rural construction.It also provides a number of analytical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on the theme of“how to maintain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he villag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tangible”and“invisible”in the context of“where the village transforms”in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Huang Fu;Mogan Mountain;village construction;big agriculture;village and town
10.3969/j.issn.1671-2714.2016.00.016
(责任编辑:陈汉轮)
2016-09-27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6-12-28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840016);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1150XJ3515009)
李敢,男,江苏睢宁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