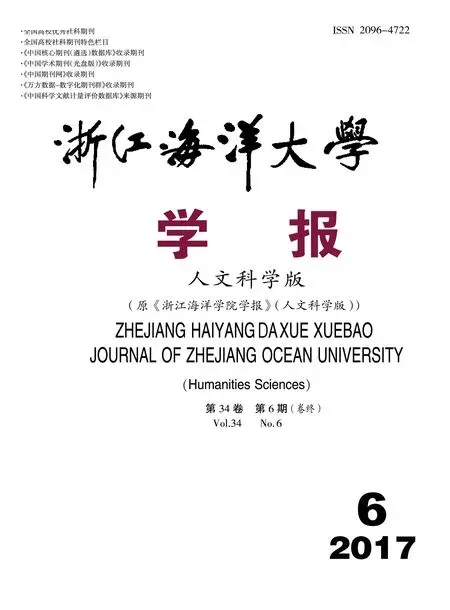后殖民语境中的《重访加勒比》旅行写作
2017-01-11赖丹琪
赖丹琪
(浙江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1100)
国内奈保尔研究中,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长期没能获得其虚构作品同等的研究关注度。近年来,以张德明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奈保尔的旅行写作展开了更多研究。①作为奈保尔第一部成书的旅行文学作品,《重访加勒比》值得更深入关注。本文选取这部作品作为讨论对象,意欲解决如下问题:《重访加勒比》的旅行写作究竟是否包含了宗主国的殖民话语策略,仅仅模仿了维多利亚时期旅行作家的民族志式选择性凝视,还是具有表述的原创性与客观性?
一、维多利亚旅行写作传统的影响
在《重访加勒比》中,奈保尔频繁引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加勒比地区旅行文学作品如J.A.弗劳德的《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1887)、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西印度群岛与西班牙大陆》(1859)、查尔斯·金斯利的《终于:西印度群岛的圣诞节》(1871)。在第一章开篇,奈保尔在引用了J.A.弗劳德的《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里的一段叙述之后,才开始叙述自己的观察所见:“滑铁卢的港口联运列车站台上挤满了移民模样的西印度人,我不禁庆幸自己是坐头等舱去西印度群岛。”[1]5可以发现,在整部作品中,奈保尔时常使用这种方式,即引用前述维多利亚旅行作家的作品来对照自己所观察到的加勒比社会。如在叙述去特立尼达赛马会的经历时,奈保尔在引用了金斯利和特罗洛普对赛马会和当地人服饰的描绘后,便以与文本参照的口吻写道:“在如今的特立尼达赛马场,你不会看到……”的确,奈保尔揭示出民族特色的消失和文化的融合,批判了加勒比社会“所有标准都近似于……欧洲人的标准。”[1]57-58这说明他并不是完全以文本代替现实,而是观察到了现实的变化。然而,在引入与现实对照的历史时,奈保尔仍然依赖于维多利亚旅行作家的参照系。因而,奈保尔被批评“着迷于确认维多利亚时期对于西印度群岛的断言”[2]45,也即持有萨义德所批评的那种东方主义“文本式”态度:将文本中读到的世界当作真实的世界。观点和分析先于写作产生,写作不过是为了印证这种观点。黄运特曾论述过这种“书本式(bookish)”先入之见,认为它“即便不是预先决定我们所观看到的内容和观看事物的方式,也会和其产生互动。”[3]3对奈保尔的批评还源于奈保尔的旅行写作批判的都是第三世界。在《抵达之谜》和《南方的转折》之前,奈保尔很少批判英国、美国。即便《抵达之谜》和《南方的转折》也少有奈保尔对第三世界那种毫不留情的批判。有论者如罗伯·尼克森认为奈保尔实际上继承了维多利亚时期旅行写作居高临下的殖民话语:“奈保尔从来没有从维多利亚英国的幻想(chimera)里恢复。”[2]46他认为奈保尔“模仿维多利亚旅行作家权威性的、具有优越感的语调、来自世界之巅的最高帝国的自信”[2]51,“奈保尔的旅行路线遵循着从欧洲到所谓传统的或原始的前殖民地的陈腐的人类学路线”。[2]66
的确,一方面,奈保尔对加勒比地区所受的历史创伤有所同情,看到了奴隶制的罪恶,认为西印度作家的种族偏见是他们的局限所在。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旅行写作中所包含的种族偏见,《重访加勒比》似乎也没能完全避免。如在作品中,奈保尔直言不讳地表示无法对印第安人这个整体产生兴趣,无法和他们交流。他写道:“他们是情感的寄生虫,靠吸干你好容易积攒起来的生命力而自肥。印第安人对我就有这样的效力。”[1]1211958年,英国对西印度移民的政治排斥加大(就在此年英国诺丁山爆发了种族骚乱),奈保尔语带嘲讽的言论显示他加入了这种排外的种族主义情绪中:“很快就会有两百万牙买加人。很难看到(英国)任何人能做什么,除了多吃牙买加香蕉,而且不要抱怨。可能——谁知道呢?——一天吃一根香蕉,把牙买加人赶跑(A banana a day will keep the Jamaican away)。”[2]50此处对英语谚语“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所做的文字游戏是否暴露了接受殖民教育体系的奈保尔向标准英语靠拢和归属英国文学传统的焦虑?奈保尔曾说:“来自于特立尼达这样一个地方,我总是觉得特立尼达存在于世界的边缘,不仅在物理上也在文化上,远离其他一切事物,我觉得我必须非常努力才能重新加入旧大陆。”[2]47
某种意义上,奈保尔的确对宗主国文化传统有归属与模仿的焦虑,其旅行写作也包含了这种“加入旧大陆”的旅行文学传统的努力。苏里南民族主义者希望用黑人英语取代荷兰语。《重访加勒比》中讲述了奈保尔的一段旅行经历:奈保尔按回忆写下英国诗人托马斯·华埃特的诗句,而后一个叫艾尔瑟尔的人用黑人英语进行了翻译。然而,奈保尔并不将之视为创造。他写道:“英语成分在艾尔瑟尔先生的翻译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主要是由于他发音太差导致的。”奈保尔并未真正去展望黑人英语创造的可能性,而是以标准英语的尺寸,嘲讽着模拟者的努力:“Ah dee day day we。这句话几乎都是英语,很难相信吧”,“对拙劣语法的热爱是荷属地区自豪感的一种极为古怪的特色。”[1]204-205奈保尔一方面批判西印度缺乏历史,另一方面却选择性地忽视这些溢出标准的英语本来就是殖民的产物。正如《米格尔街》中儿童叙述者的口语是不标准的英语,到了成人叙述者则转变成标准英语,奈保尔自身是否也遭受过这种分裂?1961年,奈保尔站在英属圭亚那一个阳台上和一个年老的印度女人聊天时,闻到一阵花香,便问这花的名字。女人告诉他花名叫“jasmine(茉莉)”。奈保尔之前在外国书本里经常看到这名字,却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花。因而,奈保尔感受到一种语言与实物之间被延迟的联系:“Jasmine,jasmine。这个单词和花在我的思想里分离得太久了。它们没有连在一起。”[2]130单词和实物之间的分离实际上是奈保尔“经验和身份的错置”[4]1。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在成书之前,主要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纽约书评》《哈泼斯》《星期日时报》(伦敦)《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文学增刊》。[2]7这些刊物在奈保尔的旅行写作的叙述权力策略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尼克森提醒我们注意这种“表征权力的分配”:“奈保尔用英语写作,并且他的新殖民主义倾向很容易被伦敦—纽约媒体轴心同化。”[2]80奈保尔曾经说自己和帝国旅行作家的区别是他“没有世界性读者可以报告东西”[5]。然而,这恰恰说明奈保尔的旅行写作已经有预期的“读者”。实际上,奈保尔在这些代表着文化、话语权力中心的刊物上发表非虚构作品,已然说明他的观察具有“回到中心”的倾向。
旅行写作总是经历了一个从经验到文本的过程。在经验过程中,旅行作家有一系列随机而不可预测的遭遇。作家叙述时选择了哪些形象和事件来定义所观察的社会?这些选择又是如何形成的?纵观整部《重访加勒比》,占据其中最大篇幅的还是对加勒比社会种族问题的着墨。十九世纪种族理论的出现为当时的旅行写作注入了许多种族刻板印象成分。铃木·杰·吉川曾提出“不同文化间的相遇和交流的四种模式”:种族中心主义的、控制式的、辩证的和对话的。在种族中心主义的模式里,A文化中的个体以A文化的框架来审视B文化,B文化的文化整体性、独特性和差异性被忽略。交流是单向的,反馈是无效的。因为A文化中的个体“选择性地注意、选择性地感知、选择性地记忆”[4]14。奈保尔对加勒比社会的观察中对种族问题的过度“关切”,包含了这种“选择性”凝视,因而缺失了对加勒比文化全局性的理解,亦是对维多利亚时期旅行写作传统的一种趋附。奈保尔明确地写道:“实际上只有我们的英国性,都属于大英帝国这一点,才使我们有了些身份认同。”[1]47奈保尔的加勒比旅行写作也包含了对英国旅行文学传统中殖民话语某种程度上的认同。
二、传统民族志式观察角度和叙述方式
詹姆斯·克利福德称旅行写作是一种“类民族志的类型”[2]66。可以发现,奈保尔加勒比社会的旅行写作具有传统民族志的特点,对加勒比社会的历史、种族、语言、风俗、服饰、风景等各方面都有叙述。《重访加勒比》中,奈保尔的重要叙述策略之一是频繁引用维多利亚时期旅行作品、当地报纸、《加勒比季刊》等文本。这类似于传统民族志的“互文的策略”:“吸收其他文本,将这些文本转化为符合民族志学者对一种文化的先入之见的叙述。”[3]4然而,这些文本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奈保尔在其中旅行的当时的加勒比社会?对历史的关注固然本就可能是旅行写作的动机之一,但如果把维多利亚时期旅行作家对加勒比社会的观察当作现实则是危险的。正如克利福德指出:“‘文化’并非为了他们的描绘而静止不动。试图使文化保持静态,必然包含了简化和排除,选择暂时的焦点,建构特定的自我-他者关系,以及一种权力关系的强加或讨价还价。”[6]39
虽然旅行写作与传统民族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后殖民民族志引入了对话的维度,更加注重其他文化与民族的差异性。《重访加勒比》是一种类民族志的旅行写作,那么它是否与本土民族志展开了对话?苏里南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应该抛弃荷兰语,用一种叫作“塔基-塔基”的黑人英语来代替。然而,奈保尔虽然认同苏里南民族主义者对“模拟”的批判,对于他们的语言实践,他却并无欣赏的态度。对于艾尔瑟尔先生将英国诗人诗句翻译成黑人英语,奈保尔的点评是:“语言的甜美和节奏还在。我很想看他如何翻译更抽象的东西,可惜我的记性不太争气。”[1]204这段叙述表明奈保尔潜在的一个假定,即“这种语言能否表达细腻微妙的含义”、“能否用来写诗”,其评判的标准依然是它能否“翻译”出标准英语产出的文学作品。[1]203然而,正如琼·波·鲁比埃斯在《旅行写作与民族志》一文中指出,“很多不识字的土著人的语言具有巨大复杂性,其语言之复杂,甚至抗拒欧洲语言的那种分门别类。”[7]众所周知,克里奥尔语具有鲜明的口语修辞特点,而如果忽略其差异和特色,只以是否能“翻译”标准英语来判定这种语言,则有可能重新落入殖民话语的强权逻辑。从“民族志”(ethnography)一词的词源学来看,其内在含义即为“写文化”(the writing /-graphy of culture/ethno-)。尼克森提醒我们注意这其中包含的文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传统民族志式的旅行写作总是存在一个观察者与一个被观察的文化,总是经历了从“俯视(looking down the society)”到“书写(writing it up)”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所运用的修辞策略需要进行审视。[2]68《重访加勒比》部分继承了传统民族志中那种地理-动物园学(geo-zoology)式的分门别类式思维。当黑人英语和其他殖民地英语的混乱打破了这种标准,奈保尔便回到了“中心”、“权威”与“标准”的俯瞰式嘲讽。
虽然,到了《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旅行写作,奈保尔成为“聆听者、对话者和记录者”,力图建构一部印度当代口述史,作品充满着“众声喧哗”[8],《重访加勒比》的旅行写作的叙述方式,依然主要是一种单声部的权威语调。这也符合传统民族志的特点:“通过给一个声音以压倒性的权威功能,而把其他人当作可以引用或转写其言语的信息来源,‘被访人’,复调性受到限制和整编”。[6]44
在《重访加勒比》中有许多自传性因素。这也和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志类型产生联系。按照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说法,民族志写作本来就包含了非个人性叙述(impersonal narrative)和个人性叙述(personal narrative)。[6]57个人性叙述是民族志常规的组成部分,为民族志文本的主体进行最初定位。只不过,在传统民族志中,个人性叙述是边缘性的。[6]61《重访加勒比》既通过频繁引用各类文本完成非个人性叙述,又加入了作者的个人性叙述。并且,这种“个人性叙述”不再边缘化,而是全程参与叙述。作品中不仅“我”与“被观察”的对象相遇、交流,对“被观察者”给出评价,“我”的感受、回忆等也融入了旅行写作的叙述中。“我”的选择性凝视构成了整部作品的观察视角。然而,对话性却遭到忽略。由于被翻译并流传到话语权力中心的本土民族志本就在少数,它们能否具有足够代表性已然值得商榷。如果缺乏和本土民族志的比较语境和对话,《重访加勒比》中民族志式的旅行写作便容易包含作者的偏见。
三、表述的原创性与客观性
前文讨论了《重访加勒比》对英国旅行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模仿,指出了其传统民族志式的包含偏见的写作方式。然而,《重访加勒比》是否仅仅是殖民话语逻辑的回归?从奈保尔的旅行写作动机和对象来看,作品依然有其表述的原创性与客观性。
虽然作品的副标题写着是对特立尼达、英属圭亚那、苏里南、马提尼克、牙买加五个殖民地社会的“印象”,《重访加勒比》的观察深度与写作动机实际上都超出了“印象”。奈保尔曾经强调自己和其他旅行者的不同:“他们是帝国为其保证安全的世界里的旅行者。……我的旅行和他们的旅行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旅行是为了如画风景,我却极其关切我在其中旅行的国家。”[2]55这种“关切”在《重访加勒比》中便体现为奈保尔对加勒比社会缺乏创造、没有历史感、“模拟(mimicry)”的批判。在加勒比社会,故事总是关于失败而非创造,“自命不凡”是骂人的话。任何逃离、超越的努力都被贬低,因为人们满足于既定的生活模式。奈保尔讽刺了殖民地人的“模拟”性格,指责他们品位低下。比如,特立尼达人只喜欢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模式。这种肤浅的精神食粮,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西印度富家子弟经常游学英伦,但也只是皮毛的游学,而非真正地接受教育。奈保尔毫不客气地称殖民地人进行的是“毫无灵魂的模仿”,批判他们没有能力创造真正的文化成就。奈保尔如此描绘特立尼达人对美国好莱坞电影趋之若鹜的形象:“几乎所有影院都在上演美国片。”“特立尼达人……只能对好莱坞模式的电影产生反应。除了这种模式,其他的都理解不了,哪怕同样是美国拍的。”“各种族、各阶层的特立尼达人都按好莱坞二流电影中完美男人的形象重塑自身。特立尼达现代主义的全部意义不过如此。”[1]66-68奈保尔在《米格尔街》里早已塑造过类似的模仿者,如模仿美国电影中的人物和美国口音的博加特。《重访加勒比》中引用的苏里南民族主义者扬·乌尔霍夫的讲话尖锐地讽刺了这些模仿者:“那些人陷入毫无灵魂的模仿中,从没有实现自我。他们学会鄙视自我,却又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取代旧的自我。于是,战争结束后,苏里南有很多人自以为凌驾于普通人之上,因为他们吸收了荷兰的语言和文化。有时候,他们会模仿克洛斯写首漂亮的小诗,或者画幅漂亮的小画,或不无技巧地弹奏一曲莫扎特的奏鸣曲;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创造任何真正的文化成就。”[1]199
对殖民地社会“模拟”的批判当然不是奈保尔的首创。1961年,即奈保尔创作《重访加勒比》前一年,弗兰兹·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就指出过欠发达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令人厌恶的模拟”:在欠发达国家不存在真正的资产阶级,这些暴富的中产阶级贪婪、残忍、缺乏创造和伟大的思想。然而,奈保尔和法农对“模拟”的原因追溯是不同的。法农认为中产阶级的派生与仿制是脱离大众的症状,奈保尔却认为“模拟”源于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真实世界”产生了距离。[2]137对于奈保尔来说,“模拟”正是加勒比社会缺乏创造、品位低下的标志。“现代性在特立尼达就成了一个缺乏自信、没有自己品位或格调、急于接受指导的民族极度敏感的问题。”[1]51-52霍米·巴巴在《关于模拟与人:殖民话语的矛盾心态》一文中曾指出“模拟”也可能是殖民地或前殖民地颠覆权威的一种方法。[9]詹姆斯·克利福德也认为“模拟”可以转变为汇合(syncretism),变成新的身份建构。[4]74奈保尔在贬低“模拟”时,也许忽略了“模拟”有可能来源于弱小民族类生物学拟态的生存需要。然而,加勒比社会若要获得表达的话语权力,表述建构自己的历史,的确不能停留在鹦鹉学舌(parroting)的层面,不能够只是袭用者/复制者(borrowers/copiers),而要成为生产者(producers)。在这一层面上,奈保尔批判加勒比社会是“借来的文化”富有警醒意义。
对于加勒比社会的缺乏历史感,奈保尔也不遗余力地给予批评。奈保尔引用特罗洛普的话“如果能做到,我们宁愿完全忘记牙买加”[1]283,其目的是为了揭示实际上“忘记”已经开始。他还引用了《加勒比季刊》上经济学教授肯尼斯·鲍尔丁博士的“小社会理论”,即小社会即将走上“毁灭之路”:如出境移民增加,社会精英流失;人口激增,人潮涌向大城市贫民区;外国投资、援助干涸;军事独裁政权建立等等。[1]282-283奈保尔所忧虑的正是殖民地人遗忘历史并且丧失危机意识,对现存的问题熟视无睹,从而走向更加黯淡的未来。奈保尔清楚地认识到殖民话语体系的强大不是没有原因的:“历史是围绕成就和创造而建构的,而西印度群岛却毫无创造可言。”[1]26正如德瑞克·沃尔科特曾经说新大陆的真实历史就是“健忘症(amnesia)”[2]20,奈保尔批判加勒比社会缺乏历史感,乃是为了避免对历史的遗忘。
必须承认,奈保尔的旅行如他所说的那样超越了观看风景的层面而具有深度的关切。游客们参观的是牙买加中产阶级的世界,奈保尔却去观察金斯敦的贫民区。[1]263“观看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和建构。”[4]16《重访加勒比》里,奈保尔观察的对象最集中的莫过于加勒比社会的种族偏见、“模拟”、缺乏创造这三大问题。在此,蒂莫西·韦斯提出的问题值得思考:“一个作家能否诊断殖民社会的疾病、清除自己身上那些疾病的痕迹,却不采取贬低的态度、附和欧洲殖民话语的贬义语调?”[4]75
奈保尔加勒比之旅的特立尼达一站无疑是进入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特立尼达是传统意义上奈保尔的“故乡”。然而在“特立尼达”一章开头,奈保尔就写道:船一触到码头,“特立尼达原有的恐惧”便又涌上心头。这种“恐惧”是什么?奈保尔驱车穿过西班牙港时的感受可以帮助揭示这种恐惧:“在海外度过的岁月消失了,我拿不准自己生活中哪些是真实的:在特立尼达生活的前十八年还是之后在英国度过的那些岁月?我从来都不想在特立尼达生活。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在肯尼迪编的《拉丁语入门》修订版书后环衬上写下豪言壮语,发誓在五年内离开。六年后我离开祖国;到达英国几年之后,睡在开着电暖炉的坐卧两用房间,我仍会被噩梦惊醒,梦见我又回到了酷热难耐的特立尼达。”[1]44奈保尔已经在《米格尔街》《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里涉及过逃离的主题,而从上面这段论述也可以看出逃离殖民地狭窄、限制的环境也是他从小就有的渴望。但回到特立尼达对于奈保尔既然是“噩梦”,为什么他还是要进行这趟加勒比之旅?在《幽黯国度》中,奈保尔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异乡人”[10]。保罗·索鲁指明奈保尔旅行的深层原因:“他们旅行,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地方;他们无法定居,他们总是在移动——某种意义上他们从未抵达——他们的旅行很大程度上是逃离。……无家可归者并不平静;他们的无家可归是特殊痛苦的来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没有过去,没有祖先’,……对于奈保尔来说,没有可以返回的过去或地方……没有传统,没有家。”[2]29
如果说《重访加勒比》的旅行写作表述实践具有超越模仿之处,正是由于奥尔巴赫意义上的“有意的无家可归(willed homelessness)”[11]。奈保尔主动而非被动的“无家可归”与流亡(exile)虽然导致了他身份的错置和分裂,却赋予他一种边缘的观察角度。作为流散(diaspora)知识分子,奈保尔获得了蒂莫西·韦斯所说的双重声音(double-voicedness)、内外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s):流亡者既属于两种文化却又不完全认同于其中任一种文化,因而具有双重外位性(double exteriority),可以从一种文化的透镜观察另一种文化。[4]13-24一方面,奈保尔的旅行写作依附于英国旅行写作传统。因而他观察的角度与目光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殖民话语的“文本式”态度。另一方面,奈保尔所处的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处境又使得作家个人的身份参与到了旅行写作中,作家同时成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其旅行写作脱离了单纯的殖民者话语的高空俯瞰的观察角度。《重访加勒比》中对卡里普索的思考即体现了奈保尔的内外双重视角。奈保尔认为:卡里普索是特立尼达人唯一一种触及现实的方式,并且是一种“地道的本地艺术形式”。“卡里普索涉及本地事件、本地人的态度,运用的语言也是本地方言。纯粹的卡里普索,最好的卡里普索,外来人是听不懂的。”[1]80在《米格尔街》等作品里,人物灵活地运用这一民间口头艺术形式,也成为奈保尔叙事艺术特色之一。可见,奈保尔对于这一本土艺术形式是肯定与偏爱的。然而,奈保尔在《重访加勒比》中却讽刺了游记作家“特意”记录为他们演唱的打油诗,认为这糟蹋了卡里普索艺术。这和奈保尔对旅游业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奈保尔之所以将旅游业视为新的奴隶制,正在于本土文化由于迎合新的权力话语而成为一种“表演性”文化:“美国人期望看到土著服装和土著舞蹈,特立尼达人便要探寻这两样。”[1]81由此,奈保尔审视了特立尼达缺乏真正的文化创造的原因。正是这种兼具本土与外围、局内与局外的双重视角,赋予奈保尔的旅行写作观察一定的客观性。
奈保尔《重访加勒比》的旅行写作可以清晰地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旅行写作传统。然而,奈保尔归属旅行写作“中心”传统的努力并不意味着他对帝国旅行写作仅仅停留在亦步亦趋和模仿的阶段。他认同于英国旅行文化传统,并且也采取了类民族志的旅行写作方式,但他自身的独特文化身份和双重视角,让《重访加勒比》得以摆脱完全的主观性和种族中心主义,而是具有清醒的批判立场。奈保尔将其所擅长的讽刺和加勒比社会的旅行写作这一特殊观察视角相结合。他对加勒比社会弊病尤其是“模拟”、缺乏历史感和文化创造等问题的“诊断”,构成了其旅行写作超越模仿、获得原创性的所在。即便这些“诊断”包含偏见,至少为当时的加勒比社会思考如何创造自己的文化、构建自己的历史提供了契机。
注释:
①如张德明从后殖民与文化身份理论出发,认为“印度三部曲”的旅行写作体现了奈保尔对母国文化既想认同又想保持距离的矛盾心态,三部曲中身份认同与叙事策略具有辩证运动的过程:奈保尔从客观、冷静的观察者转变成聆听者、对话者和记录者。详见张德明:《后殖民旅行写作与身份认同——V.S.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51-57页。赵飒飒从传达“真实”的视角考察了“印度三部曲”在体裁选择、叙事层面上从“讲述”到“展示”的变化过程。详见赵飒飒:《讲述与展示——V.S.奈保尔旅行写作中“真实”的印度》,《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4期,第171-182页。
[1]V.S.奈保尔.重访加勒比[M].王爱燕,译.海口:南海出版社公司,2015.
[2]Nixon R London calling:V.S.Naipaul,postcolonial Mandarin[M].New York: Oxford U P,Inc.,1992:45.
[3]Huang Y.Transpacific displacement: ethnography,translation, and intertextual travel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M].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 U of California P,2002.
[4]Weiss T F.On the margins: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M].Amherst:U of Massachusetts P,1992.
[5]Naipaul V S.The Enigma of Arrival[M].New York:Knopf,1987:153.
[6]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Rubiés J P.Travel writing and ethnography[C]//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 P,2002:254.
[8]张德明.后殖民旅行写作与身份认同——V.S.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解读[J].外国文学评论,2005(2):56.
[9]Bhabha H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85-92.
[10]V.S.奈保尔.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M].李永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03.
[11]Said E.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M].Cambridge,Mass:Harvard U P,19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