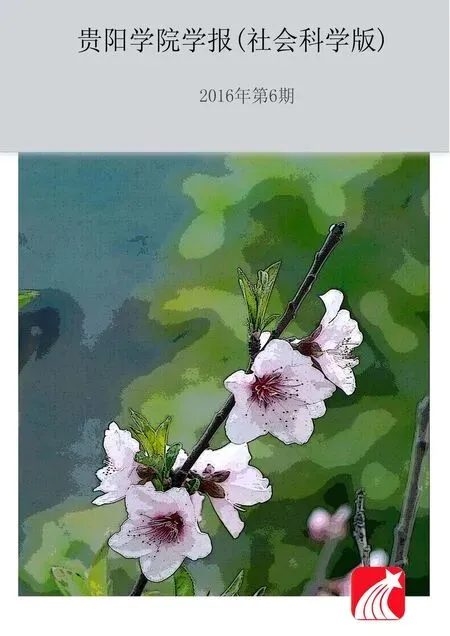王船山对王学良知说的批评
2017-01-10彭传华
彭传华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王船山对王学良知说的批评
彭传华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王学受到来自明末清初诸多思想家不同方面的广泛批评,王船山即是其中著名的代表。王船山对王学的“尊知贱能”说、“舍能而孤言知”说,对王学所言之“良知”是不修而至、不学而知的观点,对王学中的“无善无恶是良知”的说法,对王学以空、虚、寂、无等内在性质来规定良知,对王学近于禅的总体特征等五个方面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总体来讲,王船山对王学良知说的批评有得有失,理性和偏激并存,其中的内在原因包括王船山与王学诸家基于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差别而导致的学术主旨不同、学术立场各异、学术方法有别等等。
王船山;王学;良知说;批评
王学*王学主要指阳明学及阳明后学,牟宗三的《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杨国荣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蔡仁厚的《王学流衍》均使用“王学”这一概念。在明末清初受到广泛的批判。顾宪成、高攀龙、张履祥、陆陇其、张烈、陆世仪、顾炎武、张伯行等对王学的无善无恶说、心即理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阳儒阴释的思想实质等方面展开了猛烈的批评。王船山也是明末清初批评王学②*②王学包括阳明学和阳明后学,船山有些批评是直接针对阳明本人的,有些是针对阳明后学的,对于阳明后学船山并不是整体地反对,而主要是针对阳明后学中讲虚无、重情识的派别。参见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9.的一位著名代表,正如唐君毅所言:“船山之哲学,重矫王学之弊,故于阳明攻击最烈。于程、朱、康节,皆有所弹正,而独契于横渠。”[1]关于王船山对阳明的批评,学界大都从整体出发讨论王船山对阳明的整体批评,如曾昭旭[2]、张祥浩[3]、张昭炜[4]、徐孙铭[5],也有讨论王船山批评阳明的其中一个重要观念者,如刘梁剑[6]讨论了王船山对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命题的批评;谷继明[7]专门论述了王船山对王阳明知行观的批评,等等。鉴于王船山对王学的批评有诸多面向,笔者主要选择一个为学界关注不多的方面,即王船山批评王学良知说这个重要的角度展开讨论,期待方家不吝赐教。
良知的观念源出自《孟子》,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者。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根据这个说法,良知是指人的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不学”表示其先验性,“不虑”表示其直觉性,“良”即兼此二者而言。[8]154关于王阳明的良知说遭到后世的批评这个问题,学界讨论颇多,如陈来指出:“儒家内部对于良知的批评主要从先验论和普遍论两个角度展开的,如王廷相《雅述》对于良知的批评属于前者,而湛若水对于良知的批评属于后者。”[8]176但学界鲜有讨论王船山对王学良知说所持批评者,愚以为王船山批评王学的良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现分述之。
一、舍能而孤言知,宜其疾入于异端也
孟子首言良知良能,在孟子那里,知能是并提的。在王船山的视域里,“知”和“能”是认识主体的心所固有而尚待展开、实现出来的两种潜在的能动性:“知”是人潜在的认识能力,“能”是人的潜在的实践能力,并说“合知能而载之一心也”,认为二者皆统摄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心”中。船山强调“知能同功而成德业”[9]989,认为只有同时把人的“知”与“能”这两种潜在的能力同时发挥出来,才能成就人的德业,实现人之为人的目的。所以船山强调:“夫天下之大用二,知能是也;而成乎体,则德业相因而一,”[9]983也即一切德业都是主体的“知”与“能”共同发挥出来的,是“知”与“能”在认识和实践的活动中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知”与“能”的作用又不是相同的,实践能动性(“能”)比认识的能动性(“知”)更为重要。因此,王船山对于王学的“尊知贱能”“舍能而孤言知”的说法大为不满。
船山曰:“体天之神化,存诚尽性,则可备万物于我。有我者,以心从小体,而执功利声色为己得,则迷而丧之尔。孟子言良知良能,而张子重言良能。盖天地以神化运行为德,非但恃其空晶之体;圣人以尽伦成物为道,抑非但恃其虚灵之悟。故知虽良而能不逮,犹之乎弗知。近世王氏之学,舍能而孤言知,宜其疾入于异端也。”[10]121王船山在此明确批评王学的良知学舍能而孤言知,导致误入异端之途。王船山认为良知和良能之间应有辩证的连结,否则会导致“知虽良而能不逮,犹之乎弗知”的结果。在船山看来,一个人有了某方面的知识,固然标志着他具有相应的认识能力,然而不一定就具备了与知识相应的实践能力,“或有知而不能”[11]494,实践能力的提高有待于进行实践活动,而能知不能行无异于不知。[12]169因此王学知能观的问题在于:“以知为首,尊知而贱能,则能废。……废其能,则知非其知,而知亦废。于是异端者欲并废之。”[9]989-990从认识的起源来看,离开了实践能动性的发挥,认识的能动性也就失去了其发挥的途径;从认识的检验来看,离开了实践能动性的发挥,认识能力究竟如何又从何得到确证?因此,陆王心学表面上“尊知而贱能”,实际上取消了“能”也否定了“知”,是知能并废。[12]166-167船山知能同举,乾坤并建,以易知简能替代良知良能,将心之所生归结于自然之良能。从道体论来看,将良能看作阴阳二气的变化,从客体化、物化的世界返回自我。其曰:“乾以易知,惟其健也。坤以简能,惟其顺也。健则可大,顺则可久。可大则贤人之德,可久则贤人之业。久大者,贤人之以尽其健顺也。易简者,天地之道,非人之能也。”[13]430因此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二气氤氲,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13]420、“知能同功而成德业”[9]989。也就是说,在船山看来,“知”与“能”与“知”与“行”一样是“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关系。
在王船山看来,作为人的认识和活动能力的“知能”是人心所固有的,但同时又是在后天不断充实和发展的。其曰:“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人心固有之知能,得学而适遇之者也。若性无此知能,则应如梦,不相接续。”[11]565“人心固有之知能”是先天因素,“得学而适遇”是后天因素。很明显,在王船山看来,知能是在先天的“固有知能”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有效学习和适当的境遇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王船山认为,在实践过程中,可以通过“学”“虑”的学问思辨之功,使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相互转化,共同提高,此即是“学虑之充其知能”[13]414。因此王船山非常强调“学”“虑”对于“知能”的充实增益作用,批评王学对“不学不虑”的误解。
二、屈孟子不学不虑之说以附会己见
王学良知说中有大量以“不学不虑”一词来说明良知是先验性、自然性的说法,如龙溪在《答楚侗耿子问》中说道:“良知原是不学不虑,原是平常,原是无声无臭,原是不为不欲。才涉安排放散等病,皆非本色。”(《全集》卷四)在与聂豹辩论的《致知议辨》中,龙溪进一步指出:“先师良知之说,仿于孟子。不学不虑,乃天所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学虑,故爱亲敬兄,触机而发,神感神应。惟其触机而发,神感神应,然后为不学不虑、自然之良也。”[14]12又龙溪将“无是无非”来形容良知的无执不滞,以揭示良知的“自然性”,所谓“良知者,无所思为,自然之明觉”[14]2。
王船山对王学这种以孟子的不学不虑之说附会己见的做法持严厉批评态度:“于德言明,于民言新,经文固自有差等。陆、王乱禅,只在此处,而屈孟子不学不虑之说以附会己见,其实则佛氏呴呴呕呕之大慈大悲而已。圣贤之道,理一分殊,断不以乳媪推干就湿、哺乳嚼粒之恩为天地之大德。故朱子预防其弊,而言识、言推,显出家国殊等来。家国且有分别,而况于君德之与民俗,直是万仞壁立,分疆画界。比而同之,乱天下之道也。”[11]431指出陆王言爱其实与佛家讲的大慈大悲无异,并对王阳明所言的“不学不虑”的先验性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提出质疑:“孩提之童之爱其亲,亲死而他人字之,则爱他人矣。孟子言不学不虑之中,尚有此存,则学虑之充其知能者可知。断章取此以为真,而他皆妄,洵夏虫之于冰也。质以忠信为美,德以好学为极。绝学而游心于虚,吾不知之矣。导天下以弃其忠信,陆子静倡之也。”[13]414他以小孩受他人领养而对他人产生爱为例说明学虑可以充其知能,以此质疑良知的先验性,并指出人的良知与动物的本能是不同的。船山通过区分人之性与禽之性来说明这一点,船山认为人之性与禽之性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禽之性是指动物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会增益的本能:“其所知能即夙具焉,终身用之而无待于益,是其不学不虑之得于气化者也。”而人之性是能学、知虑的,是禽所不具备的,他说:“夫人则不能夙矣,而岂无不学之能、不虑之知乎?学而能之,能学者即其能也,则能先于学矣。虑而知之,知虑者即其知也,则知先于虑矣。能学知虑,禽之所不得与也,是人之性也。学虑者以尽仁义之用焉,而始著之能、始发之知,非禽之所与,则岂非固有其良焉者乎?”[15]675-676“能学知虑,禽之所不得与也,是人之性也。”此句深刻地揭示了人禽之别,认为“能学知虑”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从中可见船山以“能学知虑”反对王学的“不学不虑”。
王船山说:“夫但以不学为能,不虑为知也,则色而能悦,斗而能克,得而能取,人皆能之于习尚之余,而不如禽之胜任也蚤;利而知趋,害而知避,土而知怀,人皆知之于筹度之后,而不如禽之自然而觉。以此思之,人之不学不虑而自有知能者,非其良焉者乎?孩提而始发其端,既长而益呈其效,则爱其亲敬其长者,人所独也,天下之所同也,知禽之不知、能禽之不能也,故曰良也。是故君子以仁义言性,于此决矣。”[15]676王船山在此指出,如果撇开道德意识不讲,单纯以“不学为能、不虑为知”,那么诸如色而能悦、斗而能克、得而能取之类的知能,人类甚至不如禽类。就自然而觉的本能而言,禽在利而知趋、害而知避、土而知怀等方面也远在人类之上。但人禽之别显然不在自然本性上,关键在人的知能是“良”的,这个良的实质内容即是“仁义”。良知良能之所以言“良”,是因为人能“知禽之不知、能禽之不能”,这个知能的内容就是以仁义为实质的道德意识。因此船山告诫人类道:“勿以禽兽之知为良知,禽兽之能为良能。”他说:“大矣哉,其立人以事天;严矣哉,其贵人以治物也。私淑君子而承其将斩之泽者,舍此奚事哉!以言乎道,不敢侈言天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匪形之是践,而几乱乎鬼神。以言乎性,不忍滥乎物也。人无有不善者也;以命为无殊,则必同乎牛犬。抑功利,崇仁义,绍帝王之治教以抑强食之兽心;辨杨墨,存君父,继春秋以距争鸣之禽语,其在斯乎!后有作者,勿以禽兽之知为良知,禽兽之能为良能,尚有幸哉!”[15]678-679
王船山认为王学之所以持“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10]370的观点是因为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其曰:“近世王氏良知之说正若此,一以浮屠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迥脱根尘、不立知见为宗。”[10]370批评阳明良知说受释氏“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的直观方法的影响,对王阳明所言之良知是不修而至、不学而知的观点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在船山看来,王阳明误认为良知是不修而至、不学而知的关键在于对“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产生了严重的误解。王船山借用“习”“践”等实践性很强的概念来解释良知、良能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即性之谓也。学、虑,习也。学者学此,虑者虑此,而未学则已能,未虑则已知,故学之、虑之,皆以践其所与知、与能之实,而充其已知、已能之理耳。”[11]1125指出学虑的关键在于“践其所与知、与能之实,而充其已知、已能之理”,并尖锐指出王阳明对良知为不学不虑的理解之所以错误的关键在于对于“不”字的理解存在严重的误区:“乃此未学而已知、未虑而已能(“不”字只可作“未” 字解。)者,则既非不良之知、不良之能也,抑非或良或不良、能良能不良之知能也。皆良也。良即善也。良者何也?仁也,义也。能仁而不能不仁,能义而不能不义;知仁而不知不仁,知义而不知不义:人之性则然也。”[11]1125认为良知之良即是仁义等善性,以此批评王阳明以“无善无恶”界定良知,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待破而自明矣。
王船山对于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作出如下解释:“爱之几动,生之理渐以不忘,理有所未安而不忍,于是而学矣,故能学也。敬之情伸,天之则不可复隐,则有所未宜而不慊,于是而虑矣,故知虑也。学虑者,爱敬之所生也;爱敬者,仁义之所显也。不学之能,不虑之知,所以首出庶物而立人极者,惟其良故也。”[15]676-677在王船山看来,能是可学的、知是可虑的。在理有所未安而不忍和敬有所未宜而不慊的情况下需要学、虑。脱离学、虑则爱敬无所生,离开爱敬则仁义无所显,而之所以说不学之能、不虑之知是因为其能其知是良善的缘故。
而阳明之徒不知性之真义,竟然认为“学虑之知能”只会汩灭良知良能之“良”,唯有无善无恶才为良知,在船山看来,这是阳明等人“舞孟子之文以惑天下”[15]677的荒谬逻辑而已,因此对“无善无恶是良知”的说法进行猛烈的批评。
三、以无善无恶为良知者,其妄亦不待辨而自辟
王船山对王学中的“无善无恶是良知”的说法持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这是“直以诬道”的[11]1125。
王船山首先分析了“无善无恶”的良知说兴起的背景,其曰:“盖《易》《诗》《书》《乐》《春秋》皆著其理,而《礼》则实见于事,则《五经》者《礼》之精意,而《礼》者《五经》之法象也。故不通于《五经》之微言,不知《礼》之所自起;而非秉《礼》以为实,则虽达于性情之旨,审于治乱之故,而高者驰于玄虚,卑者趋于功利,此过不及者所以鲜能知味而道不行也。后世唯横渠张子能深得此理以立教,而学者惮其难为,无有能继之者,于是而‘良知’之说起焉,决裂藩维以恣其无忌惮之跛行,而圣教泯。学者诚有志于修己治人之道,不可不于此而加之意也。”[16]1171指出张载能深得“《礼》则实见于事”之理而创立了关学,然而遗憾的是,后世之人担心张载之学难以践履而出现后继无人的局面,于是不修而至、不虑而知的良知说趁机兴起。其次,王船山分析了导致“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良知说出现理论失误的原因:其一,王学误以为善恶的根源是无善无恶。船山曰:“至于不可谓之为‘无’,而后果无矣。既可曰‘无’矣,则是有而无之也。因耳目不可得而见闻,遂躁言之曰‘无’,从其小体而蔽也。善恶可得而见闻也,善恶之所自生,不可得而见闻也。是以躁言之曰‘无善无恶’也。”[13]415有者变化为无,才是无,无不是自本自根的。有者变为无以后,耳目不可得而见闻,于是人称之为无,以为实无所有,其实这只是感官能力的界限,由于看不到、听不到,就以为真是无。善恶是大家所能见闻的,而善恶的根源人们往往无所知,于是以为善恶的根源是无善无恶。[8]275其二,王学舍弃节文条理而以无善无恶作为心之归趋。船山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循乎地中,相其所归,即以泛滥之水为我用,以效濬涤之功。若欲别凿一空洞之壑以置水,而冀中国之长无水患,则势必不能,徒妄而已,所谓凿也。言性者舍固有之节文条理,凿一无善无恶之区以为此心之归,讵不谓之凿乎?凿者必不能成,迨其狂决奰发,舍善而趋恶如崩,自然之势也。”[13]413以大禹治水为例说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理论失误在于舍弃节文条理而以无善无恶作为心之归趋。船山把无善无恶说称为“凿”,指立此说者要人的心离开了本性固有的理,而进入一个本性之外的无善无恶的空间。他特别指出,这不仅不能使人心在本性上得以安顿,而势必离善趋恶,造成情欲的横流。[8]276

最后,船山总结道:“其(指张载,引者注)视程子以率性之道为人物之偕焉者,得失自晓然易见;而抉性之藏,该之以诚明,为良知之实,则近世窃释氏之沈,以无善无恶为良知者,其妄亦不待辨而自辟。学者欲知性以存养,所宜服膺也。”[10]112明确指出以无善无恶为良知者受到释氏的影响,其妄亦不待辨而自辟!
四、谓之空洞而以虚室触物之影为良知,可乎
阳明常以空、虚、寂、无等内在性质规定良知。如王阳明在《答陆元静》中说道:“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物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9]79阳明并不隐讳自己那些关于“无”的生存智慧吸收了《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及《坛经》的“无念、无相、无住”的思想。甚至当有人问起阳明是否要兼取吸纳佛老二氏关于身心修养的思想资源时,阳明是这样回答的:“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一厅,儒者不知皆吾之用,见佛氏则割左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其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9]1289在阳明看来,“虚”与“无”本来也是儒学中固有的一些思想内容,不能将虚无之说说成是佛老的专利①*①薛侃也持相同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后儒谓:‘释空老无为异。’非也。二氏之蔽在遗伦,不在虚无。著空沦无,二氏且以为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圣人亦曰虚明,曰以虚受人,亦曰无极,曰无声无臭,虽至玄妙,不外彝伦日用,即圣学也,安可以虚无二字归之二氏?以是归之二氏,则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义,此圣学所以不明也。”(《研几录》)。阳明高足王龙溪也有类似的表达:“吾儒未尝不说虚不说寂不说微不说密,此是千圣相传之秘藏,从此悟入乃是范围三教之宗”。(《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本此观念,龙溪在阐发自己的良知说时随处可见以“空”“虚”“无”规定良知。龙溪有云:“空空者,道之体也。口惟空,故能辨甘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清浊;心惟空,故能辨是非。”(《全集》卷六)心体和良知在阳明学中是异名同实的关系,以“空”说心,也就是以“空”说良知。后在《宛陵会语》中以“虚”释良知:“夫目之能备五色,耳之能备五声,良知之能备万物,以其虚也。”(《全集》卷二)在龙溪看来“不虚则无以周流而适变;不无则无以致虚而通感;不虚不无,则无以入微而成德业。”(《全集卷二》《白鹿洞讲义》)甚至直接以“无”来形容良知:“夫良知之于万物,犹目之于色、耳之于声。目惟无色,始能辨五色;耳惟无声,始能辨五声;良知惟无物,始能尽万物之变。”(《全集》卷九《答季彭山龙镜书》)龙溪的良知说是良知现成说中“虚无派”的重要代表。
明代后期,王门别派的良知现成说(分为“虚无派”和“日用派”两派)严重偏离王学本旨而风靡天下。其中“虚无派”从“四无说”出发,标榜妄念所发皆是良知妙用,笃信谨守皆是犯手做作,把一切道德礼法都视为人生束缚而不屑一顾,其说使人日陷于恣情纵欲而不能自拔。“虚无派”导致上层社会的纵欲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膨胀。[20]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21]其中原因,也即刘宗周所言:“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22]刘宗周明确指出“荡之以玄虚”是王学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与阳明同时期的儒者既已注意到阳明以空、虚、寂、灭等内在性质规定良知可能导致的流弊,因而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湛甘泉。他说:“昨叔贤到山间,道及老兄,颇讶不疑佛老,以为一致,且云到底是空,以为极致之论。若然,则不肖之惑滋甚。此必一时之见耶?抑权以为救弊之言耶?不然,则不肖之惑滋甚,不然,则不肖平日所以明辨之功未至也。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与道为体,何莫非有?何空之云?虽天地弊坏人物消尽,而此气此道亦未尝亡,则未尝空也。道也者,先天地而无始,后天地而无终者也。”[23]这是甘泉祭阳明文中所说的关于空的辩论,甘泉指出:宇宙间此气此理无始无终,充塞无余,所谓“空”根本不存在。王船山在甘泉的基础上提出类似的质疑:“上天下地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虽然,莫为之郛郭也。惟有郛郭者,则旁有质而中无实,谓之空洞可矣,宇宙其如是哉!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气缊,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二气缊而健顺章,诚也。知能不舍而变合禅,诚之者也。谓之空洞而以虚室触物之影为良知,可乎?”[13]420船山从宇宙具有时间、空间的二维角度批评以空、虚来规定良知。船山认为,宇宙积气之后有既久且大的特征(久指时间性,大指空间性)。宇宙之所以成其久大,乃二气缊和知能不舍的结果。二气缊即阴阳二气本体和合的状态,知能不舍即变合的神化功能不息,所以说二气缊是“诚者”,知能不舍是“诚之者”,前者是本然实体,后者是变合功能。船山认为,如果不讲气本论和变合论,把二气缊和知能不舍当做空洞的理论,反而把知觉当成良知加以鼓吹,这是不对的。[8]254船山又曰:“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幽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 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13]411也就是说,一般人所说的“无”是针对特定的“有”而言的,从而这些“无”是特定的、有规定的“无”,船山以龟无毛、兔无角来说明“无”都不是普遍的抽象的“无”,而是针对特定的“有”加以解构和破除。船山认为宇宙间根本没有规定性的普遍的“无”*当然,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道家所言的“无”即是普遍的无规定性的“无”,这种“无”是形而上的实体,不是宇宙的某一存在。,而阳明学派及其后学并不知道这个道理:“寻求而不得,则将应之曰无,姚江之徒以之。天下寻求而不得者众矣,宜其乐从之也”[13]411。
在分析王学以“无”规定良知的思想缘由时,王船山认为王学受佛家思想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他说:“释氏缘见闻之所不及而遂谓之无,故以真空为圆成实性,乃于物理之必感者,无理以处之而欲灭之;灭之而终不可灭,又为‘化身无碍’之遁辞,乃至云‘淫坊酒肆皆菩提道场’,其穷见矣。性不可率之以为道,其为幻诞可知;而近世王畿之流,中其邪而不寤,悲夫!”[10]182-183王船山认为,王畿之流正是受释氏“见闻之所不及即是无”观点的影响而以“无”规定良知的。因此王船山集中火力攻击王学近于禅的思想特征。
五、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
王船山对于王学特征的总体评价是王学近于禅,甚至认为王学之罪通于天,这是对王学最为严厉的批评:“近世之名为儒者,且欲诬圣人之言与彼合而杂乱之,皆不百年而▯▯▯,则陆九渊、王守仁之罪通于天矣。圣人之徒,其膺惩之当如何邪!”[24]足见船山对于王学近于禅的思想特征之深恶痛绝。王船山认为王学近于禅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他说:“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申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沉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10]序论10此处王船山追溯了阳明学阳儒阴释、诬圣邪说的思想来源。在王船山看来,由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太极阴阳、静一诚敬等内容有歧出而趋于浮屠的可能性*其说周子始发明圣道所由,即谓周子功在立天道之大本也。其说二程子之静一诚敬,即谓程子已下贯于人道,然而只落实在主观道德生活之上而不足与言道德事业之间开展,使一贯之旨只重在逆求,而失其至正,故一传即不免混于佛老也。参见曾昭旭.王船山哲学[M].台湾:远景出版社,1995:319.,再加上双峰、勿轩诸儒沉溺于训诂,最终开启了阳明近于禅的思想学说。而在船山看来,阳明于儒家经典中,主要援引《中庸》与佛家学说相附会:“姚江王氏出焉,则以其所得于佛、老者强攀是篇(《中庸》)以为证据,其为妄也既莫之容诘,而其失之皎然易见者,则但取经中片句只字与彼相似者以为文过之媒,至于全书之义,详略相因,巨细毕举,一以贯之而为天德王道之全者,则芒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钱、罗之流,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16]1246王船山在此严厉批评了王阳明凭借儒家重要经典《中庸》中的思想资源以附会佛老的危害。阳明之后,又有王畿、李贽之流沿着阳明的歧途越走越远:“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肤发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蒙古兴,其流祸一也。”[10]371王船山认为阳明学存在“阳明-王畿-李贽”这样一个道统,这个无忌惮的道统一旦确立,就直接导致了“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的结局。然后王船山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王学近于禅的思想实质进行批评:
第一,批评王学在成圣的工夫上近于禅。王船山曰:“今之学者(姚江之徒)。速期一悟之获,幸而获其所获,遂恣以佚乐。”[13]422直接批评阳明学“速期一悟”的顿悟说。又曰:“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学》复乱,盖其学所从入,以释氏不立文字之宗为虚妄悟入之本,故以《章句》八条目归重格物为非,而不知以格物为本始者经也,非独传也,尤非独朱子之意也。既不揣而以此与《章句》为难,乃挟郑氏旧本以为口实,顾其立说又未尝与郑氏之言合,卤莽灭裂,首尾不恤,而百年以来,天下翕然宗之,道几而不丧,世亦恶得而不乱乎?……夫道之必有序,学之必有渐,古今之不能违也。特所谓先后者,初非终一事而后及其次,则经、传、章句本末相生之旨亦无往而不著,王氏之徒未之察耳。若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则释氏之诞者固优为之,奚必假圣贤之经传以为盗竽乎?”[16]1467-1468在此,王船山揭示了“道之必有序,学之必有渐”是“古今不能违”的深刻道理,尖锐批评阳明学受禅宗顿悟之说的影响而倡导成圣的“躐等”工夫的工夫论*关于躐等工夫、密室传心,龙溪《天泉证道纪》的表述中非常明显:“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王畿.天泉证道纪[M].苏州:凤凰出版社,2007:2.;又批评王学忽视了《大学》中的格物工夫,从而“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结果趋入于无忌惮之域。王船山在其另一部著作《读四书大全说》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孟子于疾徐先后之际,精审孝弟之则而慎其微,则以尧、舜之道为即在是,乃敬、肆之分,天理、人欲之充塞无间,亦非如姚江之躐等而沦于佛也。”[11]1099批评阳明忽视了孟子所言成圣所应注重的疾徐先后之际的要求,追求“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式的躐等,最终沦于佛。船山除了批评王学在追求成圣上因躐等而沦于佛外,船山还批评王学不加操持严密之功而息心以静的工夫论,认为这将导致或流入于释老之虚寂、或成乎无忌惮之小人的后果。[10]252
第二,批评王学在认识路线上堕于“乱禅”。王船山曰:“以圣人无所不知而谓之有知,此正堕释氏家言,及陆子静顿悟之说。盖人疑圣为有知者,谓无所不知者其枝叶,而必有知为之本也。异端行无本而知有本,故举一废百。圣人行有本而知无本,诚则明矣。固有此理,则因是见知;而一切物理现前者,又因天下之诚有是事,则诚有此理,而无不可见:所谓叩两端而竭也。若古今名物象数,虽圣人亦只是畜积得日新富有耳。此与帝王之富,但因天下之财,自无与敌一例。”[11]730王船山认为圣学与王学存在根本区别:在知行观上,王学持行无本而知有本(神秘妙悟)的观点,圣学则持知无本而行有本的观点。圣贤重实行,坚持即物穷理的认识路线,轻于内省、思辨和心灵的冥悟工夫;王学则轻实行,重于沉思冥想、神秘妙悟的认识路线,正是在此意义上,船山批评王学堕于“乱禅”,背弃儒家“由诚而明”、即物穷理、蓄积而日新的认识路线。
第三,批评王学从方法论上窜入禅宗。船山曰:“自苏明允以斗筲之识,将孟子支分条合,附会其雕虫之技;孙月峰于《国风》《考工记》《檀弓》《公羊》《谷梁》效其尤,而以纤巧拈弄之:皆所谓侮圣人之言也。然侮其词,犹不敢侮其义。至姚江之学出,更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25]船山认为陆王心学堕于禅的方法论上的根源在于: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对待圣人之言,肆意比附附会曲解圣人之言,从而窜入禅宗,到了肆无忌惮地侮圣人之言的地步。
总之,王船山对王学良知说最严厉的批评即是良知说近于禅这一点,嵇文甫曾明确地表达过这种观点:“船山宗旨在激烈底排除佛老,辟陆王为其近佛老,修正程朱亦因其有些地方还沾染佛老,只有横渠‘无丝毫沾染’,所以认为圣学正宗。”[26]王船山甚至认为王学简直就是“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10]12,这样的批评可见船山对于王学良知说近于禅的思想特征的痛恨了。
城如前述,王船山从五个方面对王学良知说进行批评的思想内容和内在逻辑已然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总体来讲,王船山对王学的良知说的批评有得有失,理性和偏激并存,其中的内在原因包括王船山与王学诸家基于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差别而导致的学术主旨不同、学术立场各异、学术方法有别等等,限于篇幅,有俟来日另作专文再论了。
[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2004:515.
[2]曾昭旭.王船山哲学[M].台湾:远景出版社,1995:299-303.
[3]张祥浩.王守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505-506.
[4]张昭炜.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J].衡阳学院学报,2012(10).
[5]徐孙铭.船山对阳明心学的批驳和误读[M].阳明学研究(创刊号).北京:中华书局,2015:112.
[6]刘梁剑.“无善无恶心之体”:船山与阳明关于心学的智性对话[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7]谷继明.对于船山批评阳明的再检讨[C].杭州:阳明学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92.
[8]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M]//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0]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2]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3]王夫之.思问录内篇[M]//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4]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M].道光二年[会稽莫晋刻本].
[15]王夫之.船山经义[M]//船山全书: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6]王夫之.礼记章句[M]//船山全书: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M]//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639.
[18]王夫之.尚书引义[M]//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260.
[19]王阳明全集:卷二[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0]徐儒宗.江右王学通论·自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1]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703.
[22]刘宗周.证学杂解[M]//刘宗周全集.吴光,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278.
[23]湛甘泉先生文集:外篇第七卷[M].明嘉靖十五年刻本:5.
[24]王夫之.四书训义(下)[M]//船山全书:第8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397.
[25]王夫之.俟解[M]//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489.
[26]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116.
[责任编辑 何志玉]
Wang Chuanshan's Criticism of the Wang School's Conscience Theory
PENG Chuan-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Zhejiang, China)
The Wang School was widely criticized by thinker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from different aspects,one famous representative of which was Wang Chuanshan. Wang Chuanshan was highly critical of the Wang School's point of view that "knowing is prior to actual doing", "knowing can be discussed without talking about doing", "conscience can be achieved simply by intuitive knowledge without learning and practice" and "conscience is a state between good and evil". He also held the critical opinion of the fact that Wang School defined conscience with the properties of KONG, XU, JI and WU, and that Wang School was similar to Zen. Generally speaking,there were both merits and demerits in Wang Chuanshan's criticism of the Conscience Theory of Wang School, and his criticism was both rational and radical.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Wang chuanshan's academic purport, standpoint and methods differed from Wang School,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social backgrounds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Wang Chuanshan; learning of the Wang School; Conscience Theory; criticism
2016-11-0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王船山与中国政治思想的近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1CZX036);“王船山与中国近代实践观的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4BZX034);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王船山与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015T80633)阶段性成果。
彭传华(1975-),男,江西遂川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儒家伦理思想及明清政治哲学研究。
B222.6
A
1673-6133(2016)06-0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