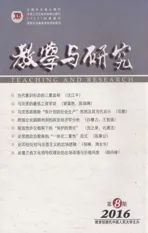同质性与异质性:英国学派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
2017-01-05张强,吴勇
张 强,吴 勇
同质性与异质性:英国学派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
张 强,吴 勇
英国学派;全球国际社会;地区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的核心议题之一。迄今为止,英国学派已经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上对国际社会展开了颇具特色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英国学派两波地区国际社会的研究成果,归纳出英国学派内部存在的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即全球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和地区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前者强调国际社会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的同质性;后者则强调国际社会两个层次的异质性。英国学派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描绘了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国际社会图景。
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的主要概念和独特标志,因此,英国学派也被称为国际社会学派。[1](P1)[2](P112)尽管英国学派的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社会展开了富有见地的研究*第一代英国学派代表人物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和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将“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混用,奠定了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研究的“话语”基础;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则对“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进行了区分,并就“国际社会”的构成要素、秩序和正义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第二代英国学派代表人物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对国际社会的研究旨趣开始从多元主义转向社会连带主义。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和蒂姆·邓恩(Tim Dunne)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英国学派学者则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关于三代英国学派学者的划分,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第117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但是,在巴里·布赞(Barry Buzan)看来,“英国学派对于国际社会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全球或者体系层次,鲜有关于地区层面的讨论。”[3](P105)实际上,对于英国学派来说,国际社会的地区层面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英国学派内部已经出现了“两波地区研究”。[4](P6-9)本文主要从国际社会的界定、构成国际社会的制度以及国际社会全球和地区层次三个维度对英国学派的这两波地区研究进行考察,以两波地区研究的共性和差异为出发点,归纳出了英国学派内部存在的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即以国际社会全球和地区层次的同质性为核心的全球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和以两个层次异质性为核心的地区国际社会生成逻辑。
一、英国学派的两波地区研究的共性与差异性
英国学派的两波地区研究分别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和本世纪头十年。英国学派第一波地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亚当·沃森(Adam Watson)、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江文汉(Gerrit W. Gong)等人,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分析全球国际社会出现以前的各地区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第二波地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巴里·布赞和张勇进(Yongjin Zhang)等人*巴里·布赞认为阿尤布(Ayoob)、迪兹和惠特曼( Diez and Whitman)、斯蒂瓦施蒂斯和恰普托维奇 (Stivachtis and Czaputowicz)等人对国际社会结构的地区层面的探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参见Barry Buzan,Ana Gonzalez-Pelaez (eds.),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Middle East English School Theory at the Regional Level,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2009,p.27.,其研究特点是主要通过案例研究来分析国际社会中是否存在与全球国际社会并存的次全球或地区国际社会。英国学派两波地区研究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共性主要表现在两波地区研究都是在英国学派的话语体系中进行的;差异性则主要表现在英国学派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并未囿于国际社会的全球层次,而是进一步推进了英国学派的地区研究。
第一,英国学派地区研究中的共同“话语”。英国学派之所以成为英国学派,并不是因为研究者都具有英国国籍,而恰恰是因为英国学派学者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话语”。这在英国学派的地区研究中也不例外。首先,国际社会作为第一波地区研究的英国学派学者所提出的核心概念之一,被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所继承。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最为经典的界定是由赫德利·布尔做出的,即“当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之间有某些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并构成为一个社会时,即当它们自己相信彼此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并且彼此在共同制度的运行中分担责任时,就存在着一个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5](P13)英国学派学者,不论是在全球层次还是在地区层次讨论国际社会,都把这一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第二波英国学派的地区研究学者认为布尔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界定,可以应用到地区层次,成为其所讨论的国际社会的一部分。[4](P13)其次,两波地区研究的英国学派学者都注重国际社会的制度研究。在布尔看来,国家之间存在交往就存在国际体系,但这并不能构成国际社会。只有当国家受到共同制度的支配时,才存在国际社会。这就是布尔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做出的重要界分。布尔认为:“15—19世纪期间的欧洲扩张促生了一个将各大地区性体系连为一体的国际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社会”;“一个世界性国际社会及其各个维度,只有等到欧洲国家以及他们所交往的、共存于一个相同的国际体系的许多独立政治实体最终在共处与合作结构方面形成共同利益,心照不宣地或公开地承认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之时,才算是真正出现。”[6](P113、116)布尔认为象征着国际社会之存在的制度包括主权、均势、国际法、外交机制、大国管理体系和战争。[5](P71)第二波地区研究代表人物巴里·布赞也认为制度是英国学派思想的核心,因为制度展现出了国际社会的本质内容;制度也支撑着英国学派所说的国家关系中的秩序;制度还是英国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7](P161)再次,两波地区研究的英国学派学者都认为当代全球国际社会是从欧洲国际社会扩展而来的。亚当·沃森将欧洲扩张的历史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世纪时期对伊比利亚和波罗的海周围地区的十字军远征;第二个阶段长达3个世纪之久,包括你争我夺的海上探险和扩张以及并行不悖的欧洲国际社会的演进;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工业革命使得欧洲协调扩大到全球范围并统治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最后一个阶段则是20世纪,欧洲统治的浪潮日益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欧洲模式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社会,欧洲只在其中起着有限的作用。”[6](P27)如前文所述,布尔也认为世界性的国际社会(即全球国际社会)始于15—19世纪欧洲性的国际社会在地理范围的扩展。同样地,巴里·布赞也认为“英国学派的经典假设是可以接受的,即当代全球国际社会主要是从欧洲发展中演化出来的。”[7](P241)
第二,英国学派地区研究中的发展。英国学派地区研究的第二波学者在继承学术传统的同时,还有所突破。首先,英国学派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对国际社会的认识有所突破。巴里·布赞认为经典英国学派的学者所说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国家间社会(interstate society),除此之外,国际社会还应该包括人际社会(interhuman society)和跨国社会(transnational society)。人际社会是基于个人之间互动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共有认同(shared identity)形态;跨国社会则指全体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社会结构。国家间社会、人际社会和跨国社会三者一起在国际社会中起作用。[7](P xvii-xviii、128-138)其次,第二波学者丰富了国际社会中制度的内容。根据巴里·布赞的观点,布尔所说的国际社会制度属于国际社会制度中的主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主要制度是演进而来的,而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制度,是构成性制度而不是工具性制度。主要制度包括多元主义者所说的主权、不干涉、外交、国际法、战争、均势和大国管理;也包括晚近的民族主义和市场,还包括社会连带主义者正在推动,但尚未成功的人权和主权制度。除了主要制度之外,国际社会制度中还包含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次级制度则是被设计出来的工具性的实体,包括国家间领域的政府间组织;也包括跨国领域的联邦式的(federative)实体。[8](P27)再次,第二波学者在看待非欧洲地区在欧洲国际社会扩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上与之前的学者有所不同。如前文所述,两波英国学派地区研究学者都认为当代全球国际社会是由欧洲国际社会扩展而来的。但是,第一波学者认为在欧洲国际社会向全球扩展的过程当中,非欧洲或非西方国家发挥作用甚小,最终被“同化”成为国际社会成员,进而形成了以欧洲性为中心的全球国际社会。然而,第二波学者则更加注重各个地区的特性,进而探讨是否存在与欧洲国际社会扩展而来的全球国际社会异质的地区性国际社会。实际上,这就形成了英国学派在国际社会研究中的两种逻辑。简单地说,第一种逻辑是全球国际社会生成逻辑;第二种逻辑则是地区国际社会生成逻辑。
二、国际社会地区层次的同质性与全球国际社会生成
在英国学派第一波地区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欧洲国际社会形成之前,就存在与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并立而存的几个重要的地区国际体系,如阿拉伯—伊斯兰体系、印度体系、蒙古人—鞑靼人体系和中华体系;[6](P2)而在全球国际社会形成之前,除了存在欧洲国际社会之外,还存在着不同“文明标准”的非欧洲地区社会。在东亚、穆斯林世界和非洲都存在着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实践的“文明标准”,以此规范着各自的社会。[9](P7)这两种观点共同揭示了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即在全球国际社会形成之前,包括欧洲国际社会在内的所有地区国际社会都遵循着各自的规则和制度。然而,在全球国际社会形成的进程中,非欧洲地区国际社会不得不放弃或调整原有的规则和制度,并与欧洲国际社会共享共同的规则和制度,进而形成了彼此同质的全球国际社会。
第一,国际社会的构成要素及现代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在英国学派学者看来,国际社会是由国际体系演进而来,国际体系之所以演进成为一个国际社会,其核心要素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存在共同制度。当然,共同制度仅仅是构成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它实际上维护着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规则,而共同规则又体现了共同利益和价值。因此,共同制度、共同利益和价值以及共同规则三者共同成为国际社会的构成要素。由此可见,讨论一个国际社会是否存在,主要观察是否存在共同制度,当共同的制度在一个国际体系中间出现并起作用时,国际社会也就出现了。布尔认为欧洲国际社会形成于18到19世纪,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象征着国际社会的制度在欧洲各国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并起作用。主权原则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得以确立,这为欧洲国际社会设定了“门槛”,即欧洲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主权本身是一种制度,所有其他的制度又是主权国家维护国际社会秩序的工具;均势在1713年签订的《乌得勒支条约》中正式确立;实证国际法在18—19世纪,完全取代自然法和神权法成为国家间共处的规则;常驻使节制度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并在16世纪传播到整个欧洲;战争则始终是欧洲国际社会维持均势、执行以及变更国际法的手段;大国管理体系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协调”之中得到体现。同样地,亚当·沃森也认为到17世纪中叶时,拥有绝对主权和法律上平等的各国形成了新的欧洲社会,这个欧洲社会运用均势、国际法、定期国际会议和外交对话四个机制来维持秩序。[6](P10-21)随着布尔和亚当·沃森所说的国际社会制度在欧洲国家间得到普遍承认,欧洲国家间的共同规则就得到了维护,进而共同利益和价值也得到体现,因此,欧洲地区也便从基督教国际体系演进成为了欧洲国际社会。
第二,欧洲之外的地区社会及其特点。在欧洲之外,还存在着与欧洲社会并不相同的地区社会。亚当·沃森认为在非欧洲地区存在着同欧洲体系一样的高度文明的社会,譬如欧洲东方的穆斯林体系以及穆斯林东方的亚洲体系。他认为亚洲体系存在着宗藩体制,这个体制是一种中心—外围的等级体制,中心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宗主国,而外围则是承认宗主国霸权地位并向宗主国纳贡的藩属国,这些藩属国享有自治权。在宗藩体制内部,宗藩交往以及藩属国之间交往受到具体条约和传统的行为规则约束。[10](P215-216)这与现代欧洲国际社会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反对霸权、外交对话和遵守国际法等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同时,亚当·沃森还认为在非欧洲地区还存在着很少被文明世界了解的更为原始的人类社会,譬如广大的美洲地区。这些“新世界”(The New World)被欧洲国家殖民形成了殖民体系。随着欧洲对“新世界”的殖民,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得到传播并不断加强。[10](P220)然而,江文汉则认为欧洲国际社会才是文明的象征,因为在欧洲地区存在着所谓的“文明标准”,而非欧洲地区不存在同样的“文明标准”,属于非文明的地区。总而言之,在全球国际社会生成之前,欧洲和非欧洲地区并不存在共同的制度,欧洲国际社会代表着“现代性”,而非欧洲地区尽管存在着各自的特点,但是仍被认为是传统的甚或是原始的社会。
第三,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展与非欧洲地区的融入。既然欧洲国际社会与非欧洲地区之间存在差异,那么当欧洲国际社会向非欧洲地区扩展时,就会引起欧洲国际社会与非欧洲地区之间的冲突。正如江文汉所说,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在欧洲向非欧地区扩张进程中,不仅仅存在着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冲突,而且存在着最为根本的冲突是文明和各自文化体系的冲突。[9](P3)面对这些互动过程中的冲突,互动的主体就有可能做出必要的调整以相互适应。一方面是欧洲国际社会在扩张过程中做出了某些调整。亚当·沃森就认为“欧洲性国际社会演变成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漫长过程,至少开始于欧洲列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达到巅峰以前的一个世纪。这个演变过程,主要呈现出两种形式。一是欧洲体系在扩展过程中做出一系列调整,旨在更有效地处理欧洲列强与亚洲国家(以及不那么重要的非亚洲国家)的关系。二是欧洲体系对欧洲海外殖民地之独立做出的各种调整。”[6](P121)另一方面是极力维护传统文化的非欧洲地区所做出的调整。非欧洲地区为了得到“文明”国家的保护和特权,根据欧洲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进行了改革,并最终利用“文明标准”得到“文明”国家的认可。[9](P2-9)尽管互动双方都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但是毕竟欧洲国际社会和非欧洲地区在规则、利益和价值以及制度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异,因此,在欧洲国际社会向全球扩展过程中,“暴力(violence)、强迫(coercion)和去殖民化起到了重要作用。”[7](P223)总体来看,欧洲国际社会向外扩展与非欧洲地区融入的进程中包含着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其一,主动模式,即欧洲与非欧洲地区相互适应,主动调整;其二,被动模式,即非欧洲地区被迫接受欧洲的“文明标准”以及欧洲国际社会被迫承认那些接受了其“文明标准”的非欧洲地区。在这两种模式的相互作用下,欧洲国际社会扩展成为了全球国际社会。
第四,全球国际社会形成与地区国际社会的同质性。英国学派第一波地区研究学者,将国家视为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把国际社会的制度作为构成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以欧洲地区国际社会形成与扩展为起点,形成了英国学派的全球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即欧洲国际社会形成——欧洲国际社会扩展——非欧洲国家认同“欧洲标准”,并融入欧洲国际社会——全球国际社会形成。全球国际社会形成意味着,一方面非欧洲地区成员变得与欧洲国际社会成员相似或者同质;另一方面欧洲国际社会接受了这些相似或同质的非欧洲地区成员。如布尔所说:“数量巨大而迥然不同的政治实体共同构建一个统一的国际社会,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这些实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相似。”[6](P117)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有学者认为在英国学派第一波地区研究学者的著述当中,全球国际社会形成之时,地区的重要性降到了最低点。[4](P6)尽管布尔认为非欧洲国家加入欧洲国家俱乐部,从而构成世界性国家社会的正统观点是荒谬的,但是他终究还是认为非欧洲地区接受了欧洲国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6](P118-119)实际上,在英国学派第一波地区研究学者的分析中,全球国际社会形成以后,不仅仅是非欧洲地区放弃传统的规则和制度,融入到全球国际社会;欧洲国际社会在与非欧洲地区互动过程中也做出了调整,成为全球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从整体来看,全球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确实在制约着各地区国际社会的交往,也没有一个地区国际社会在丝毫不做出调整的情况下主导全球国际社会。可以说,英国学派第一波地区研究学者更为关注全球层面的同质性,而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在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同时,探索并逐渐呈现出了一幅具有地区特性的国际社会图景。
三、国际社会地区层次的异质性 与地区国际社会的生成
无论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都认同当代全球国际社会是由欧洲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地区国际社会)扩展而来。不同的是,在第一波学者的论述中全球国际社会最终取代了包括欧洲国际社会在内的所有地区国际社会;而第二波学者则认为全球国际社会和地区国际社会并存,地区国际社会与全球国际社会在国际社会的构成主体、构成要素和一般特征等方面存在异质性。英国学派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在继承全球国际社会的生成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反思。他们将非国家行为体纳入分析框架,扩大了国际社会构成主体;同时还明确了主要制度和次级制度在构成全球与地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种全球国际社会改进逻辑,即欧洲国际社会形成——欧洲国际社会扩展——欧洲地区与非欧地区共享制度/次全球或地区行为体存在各自的制度——全球国际社会生成/地区国际社会(可能)生成。
第一,国际社会的再定义。赫德利·布尔从构成主体和构成要素两个方面对国际社会做出了经典的界定,即国际社会的主要构成主体是主权国家,核心构成要素是象征着国际社会的制度,这一经典的界定对英国学派两波地区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毋庸置疑,在第一波地区研究中,布尔关于国际社会的界定是判别地区和全球层次是否存在着国际社会的基本标准。虽然英国学派的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延续了布尔界定国际社会的主要思路,但是他们还是在此基础上对国际社会做出了重要的发展。首先,在构成主体方面,国际社会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巴里·布赞认为布尔所说的国际社会仅仅是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社会,除此之外,国际社会还包括前文提到的人际社会和跨国社会。国家间社会、人际社会和跨国社会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社会结构的三个领域。其次,从地理范围上看,国际社会的三个领域可能存在于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上,也就是说,全球和地区层次是否存在国际社会,应该从国家间社会、人际社会和跨国社会这三个领域进行考察。这样就克服了英国学派既往研究中只关注全球层次的缺陷。再次,在核心构成要素方面,除了布尔所说的主要制度,还包括次级制度,这些制度是区分国际社会的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的核心标准。总而言之,英国学派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在第一波地区研究学者的基础上,大大扩展了国际社会的内涵和外延。
第二,地区国际社会的一般特征。[11](P207)地区国际社会之所以成为地区国际社会,是因为它存在不同于全球国际社会的一般特征,主要表现在地区国际社会在其核心构成要素方面存在的外部差异性和内部同质性上。首先,地区国际社会与全球国际社会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有些主要制度在地区国际社会存在,但是在全球国际社会却不存在;而有些主要制度在地区国际社会不存在,但是在全球国际社会中却存在;还有些主要制度由地区国际社会和全球国际社会共享,但是地区国际社会在践行这些主要制度时却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特征。同样地,次级制度也在国际社会的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其次,地区国际社会与其他地区国际社会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一方面,不同的地区国际社会存在不同的主要制度和次级制度;另一方面,地区间普遍存在的主要制度,在实践中也会存在某些地区特性。显著的差异性自然能够有力地证明地区国际社会的存在。再次,地区国际社会的同质化和一体化程度。地区国际社会的同质化和一体化,在对规范、规则和制度的认同中得到体现。这种认同可能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即强制(coercion)、算计(calculation)和信仰(belief),与此相对应的是规范、规则和制度内化程度由低到高排列。[7](P128-138)最后,地区国际社会的一般类型。根据地区国际社会的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倾向,可以将地区国际社会归类为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al)、共存(co-existence)、合作(co-operation)与聚合(convergence)四种类型。[7](P159-160)

其次,与主要制度相较而言,国际社会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在次级制度方面存在着更为显著的差异性。国际社会的全球层次、地区层次以及地区层次之间都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次级制度。国际社会的全球层次存在着以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B)等世界性国际组织为代表的次级制度;而国际社会的地区层次则存在着更为多样的次级制度,主要代表有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联盟(LAS)、东亚地区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以及南美洲的安第斯国家共同体(CAN)等等。基于主要制度和次级制度在全球和地区层次的密集程度,还可以从国际社会体系的三个领域(即国家间社会、人际社会和跨国社会)对国际社会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的差异性进行考察。换言之,主要制度和次级制度密度较高/较低的领域,则存在较厚(thick)/较薄(thin)的国际社会。[7](P207-217)
总而言之,英国学派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通过重新界定国际社会、探索地区国际社会的一般特征、聚焦于国际社会全球和地区层次异质性,逐渐形成了前文提到的地区国际社会的生成逻辑,其核心要义是地区行为体认同有别于全球层次的国际社会制度,进而形成(或可能形成)地区国际社会。这与聚焦于国际社会全球和地区层次同质性的学者所提出的全球国际社会生成逻辑有十分巨大的差异。
四、结 语
英国学派两波地区研究蕴含了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它们共同描述了全球国际社会和地区国际社会如何成为可能。首先,全球国际社会生成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同质性逻辑”。它更加强调,在地区国际社会演进成为全球国际社会进程当中,国际社会地区层次异质性的减弱和同质性的增强。这部分地反映了现代主权国家社会确立的历史进程,因为构成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在此进程中得到了各个地区的普遍认可,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国际社会中存在较强的同质性。但是,全球国际社会的生成并不能泯灭国际社会地区层次的特殊性。其次,地区国际社会生成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异质性逻辑”。它更加强调地区国际社会构成主体和构成要素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揭示了国际社会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再次,英国学派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并存,本质上要求将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并存的国际社会中,既要看到全球国际社会的同质性,又不能忽视地区国际社会的异质性。总之,英国学派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共同描绘了一幅相对清晰完整的国际社会图景。
英国学派两波地区研究也从客观上揭示了英国学派自身发展的特点。首先,共同的学术旨趣是英国学派发展的根基。英国学派历代学者对国际社会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使英国学派具备了共同的学术“话语”和学术传统。从这一角度来看,英国学派内部是具有一定程度“同质性”的。其次,自觉的反思和对话是英国学派发展的重要动力。英国学派第二波地区研究学者在继承学派内部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部分地借鉴了当代国际关系其他理论流派(如,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智识,基于不同地区的案例,对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研究做出了创造性反思,不仅挖掘出了国际社会地区层次的“异质性”,也在学术贡献中展现出了“异质性”。
英国学派两波地区研究仍然存在许多缺陷,但是两波研究对国际社会两个层次的探索,不仅在进一步完善英国学派理论方面作用良多,而且也为学界探讨国际社会秩序相关问题提供了一种具有英国学派理论色彩的进路。既然国际社会需要从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进行考察,那么关于国际社会秩序问题自然也不能简单地做“同质化”或者全然“异质化”的处理。因此,从国际社会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出发,讨论国际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持和转型等相关问题则是本文未能涵盖,但却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Cornelia Navari and Daniel M. Green (eds.).Guide to the English School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C].London: Wiley Blackwell,2014.
[2]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巴里·布赞.英国学派及其当下发展[J].李晨译,张小明校.国际政治研究,2007,(2).
[4] Aleš Karmazin.Introduction: English School Investigations at the Regional Level[A]. In Aleš Karmazin, Filippo Costa-Buranelli, Yongjin Zhang, Federico Merke (eds.). Reg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English School at the Sub-Global [C]. Brno: Masary-kova Univerzita,2014.
[5]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M]. England: Palgrave,2002.
[6] (英)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扩展[M].周桂银,储召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7]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8] Barry Buzan.The Middle East through English School Theory [A].in Barry Buzan, Ana Gonzalez-Pelaez(eds).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Middle East English School Theory at the Regional Level[C].England:Palgrave Macmillan,2009.
[9] Gerrit W. 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a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0]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M].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1992.
[11] Barry Buzan and Yongjin Zhang (eds.). Contes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East Asia[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责任编辑 刘蔚然]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the Dual Generated Log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Englsih School
Zhang Qiang1,Wu Yong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English School;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g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one of core issues in English School. Hitherto, English School has already conducted a quite characteristic study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s. Reviewing the study of two waves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nglish School,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ual generated log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which exist within English School. The logics refer to the generated logics of global and reg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homogeneity betwee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latter highlights the heterogeneity in the two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dual generated log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English School describe a more clear and integrated imag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中欧学术对话”(项目号:13JJD810013)的阶段性成果。
张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吴勇,燕山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河北 秦皇岛066004),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