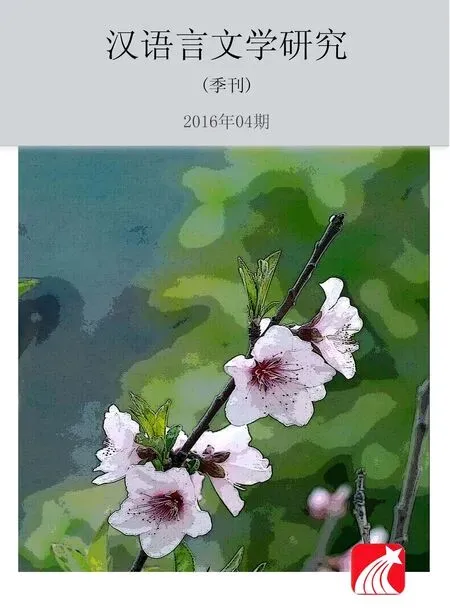认知“装置”与语言的间隙
2016-12-29徐刚
徐刚
认知“装置”与语言的间隙
徐刚
李松睿博士的著作《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讨论“地方性”这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中极为重要的论题,并试图以此为据提供中国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中所特有的历史风貌。在此,30年代与40年代的文学转折,战争对于国土的强行分割所形成的地区性差异,以及以此为背景,对“地方性”这一问题不同层面的历史的具体的阐释,构成了整部著作的主体部分。为了深入而清晰地阐明这一论题,作者在作出一种总体的历史梳理与理论辨析(即吴晓东教授所指出的“理论的历史性”分析)之后,其“地方性”的具体展开是以个案的形式向理论总体性背后的不同侧面切入的。在此,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甚至上海孤岛的具体历史场景在“地方性”的讨论框架之下被详尽打开,所涉及的作家则分别包括老舍、赵树理、梁山丁、师陀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无不令人耳目一新。而在这中间,最为精彩的当属涉及赵树理的相关讨论。
在《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一章中,李松睿的论述焦点是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最具大众化特征的赵树理小说。彼时的赵树理作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其“被发现”的过程与意义曾被研究者不断阐述,再加之“赵树理方向”在解放区的建立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性命运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也使之早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焦点。在问题的呈现中,李松睿独辟蹊径,从赵树理小说浓郁的“地域民俗色彩”和地方性特征在40年代接受中的被忽视入手,考察这一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已是常识的认识方式,却在当年的接受中被完全“忽视”的独特“认知装置”。“地方性”的“发现”与“忽视”的认知“装置”背后,引而不发的问题则在于“赵树理方向”为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走向破产。
众所周知,在1942年延安的《讲话》之后,赵树理一举成为解放区具有示范意义的 “明星作家”。在当时的批评接受中,人们更多倾向于从政治化和大众化的角度予以理解,将其视为“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讴歌新社会的胜利的代表”。在他们看来,赵树理的最大意义在于,他将自觉的政治性融化到具体的语言实践之中,这使得30年代以来便孜孜以求的文艺大众化目标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在研究者看来,赵树理的最大成就在于语言,即生动鲜活的农民口语,显示其向农民学习的态势。作为“农民作家”和“农民代言人”,他被认为克服了“五四”新文学的知识分子腔调,这与毛泽东所提倡的文艺发展方向相契合,因此被赋予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一点通过将其小说与周立波等人作品的比较便可清楚看出。同样是瞩目于方言土语,赵树理的作品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运用,而周立波则更多是用方言土语来“装饰自己的作品”,他对方言土语的刻意追求常被理解为“炫耀自己需要的知识”和“还没有完全脱却洋气”。
在具体的分析中,李松睿敏锐地发现了赵树理语言的“翻译”特征,即赵树理语言的某种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的反映方式,是作家在充分了解其潜在读者的阅读习惯后,在语言层面上进行的“翻译”。这突出表现在他把知识分子的语言“翻译”为农民语言的过程直接暴露给读者。在李松睿看来,赵树理的文学语言所具有的口语化特征,既不是对“群众的语言”的学习,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农民实际使用的口语,它直接生发于两种语言的“翻译”行为中,是“翻译”所实现的某种特殊效果。这一特点构成了他和其他解放区作家在语言上的主要区别。相对于赵树理小说语言的“翻译性”,周立波语言的“炫耀性”显得极为明显。李松睿正是通过分析赵树理和周立波小说注释的不同,来提示后者作品中那些客观、平板的注释语言,以及作为知识出现的方言土语的“炫耀性”。正是这种差别主导了此后评论者理解地方性问题的认知“装置”的特点。在阶级性价值准则的主导下,赵树理的小说被轻易指认为“学习群众的语言”,克服知识分子欧化文风,改造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以获得“无产阶级立场”的样本,这也使得人们对其政治性与阶级性之外的“地方性”与“地域特征”视而不见。
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另一特点在于叙述语言与人物对话之间没有区别,表现出某种同一性。他是用地地道道的农民语言来创作并贯穿始终,甚至在小说中也以不同的方式对书面语的装腔作势给予厌弃与鄙夷,这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于“五四”以来书面语写作的批判。比如小说《李有才板话》便选择了以两种语言的差异来表征章工作员和老杨同志的不同态度。小说中,坏干部不切实际脱离群众的重要表现就在于一味操持毫不及物的书面语,而不能运用生动简明的民间语言。现在看来,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农村地区有效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将这一政治的思考转化为文学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书面语无疑代表了某种脱离农村地方实际,总是以“国际国内形势”的角度出发的好高骛远的工作态度;而让普通农民喜闻乐见的口语则代表了值得赞赏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李松睿看来,这种文学语言与政治态度之间水乳交融的状态,或许是40年代左翼批评家特别看重赵树理语言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与此相反,周立波则竭力呈现并不断强化作品中的语言分裂倾向。他一方面在小说中不断追求标准化的叙述语言,一方面却总用截然相反的标准来书写作品中的人物对话,认为对话中必须加入方言土语才能达到真切、传神的效果。因此,在周立波作品中,叙述语言与对话语言便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分裂状态。
如果说正是语言的一致与纯粹所显示的新颖,是解放区选择赵树理作为明星作家的示范意义,那么周立波的这种“分裂”背后所蕴含的丰富与复杂则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对于“地方性”的认知“装置”发生改变之后才能体会得到。在著作中,李松睿多次引述语言学家邢公畹的文章《谈“方言文学”》,由此暗示方言土语在知识分子改造之外所具有的某种 “引导我们向后看”和“走向分裂的东西”的复杂性因素。而对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松睿有着更为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小说中的萧队长绝大部分时间都与元茂屯的农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召开会议宣传土改政策、布置斗争地主的策略、领导民兵抵御土匪的骚扰,只有在偶尔的片刻时间里他才能从元茂屯的事务中暂时脱身出来,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也正是在这种语言的间隙,李松睿读出了赵树理与周立波的巨大差异。
在李松睿看来,使用何种语言进行表达,与言说者能够站在多高的层次上思考问题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当萧队长必须从元茂屯的实际情况出发处理问题时,他只能运用地方性的方言土语进行表述;而当他开始在中华民族改变命运的层面上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时,他就必须转而使用标准书面语进行相应的思考。由此可以看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土语,亦即普通农民口中活生生的语言,在解放区的这批小说中与地方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群众路线等处在结构性的对应关系中。而知识分子所使用的书面语,则在小说中意味着以宏观的视野思考问题,这一点正是《暴风骤雨》对主人公萧队长的描写最有意味的地方。
现在看来,也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认知“装置”的出现,才使得原本被认为具有极大语言缺憾的周立波,恰恰显示了其在全国或全民族的范畴下思考问题的宏阔视野,而赵树理小说则因始终局限于对农村地方的表现而逐渐蜕变为仅仅只是“山西味道晋阳风味”,就此结合文学批评则是其创作“缺陷”的逐渐“暴露”。确实如此,在赵树理那里,那些宏大的事物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细枝末节的“地方性”、乡土气息和地域特征。诸如“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其作品对于农村生活的变化进行描绘时,“没有结合整个历史的动向来写出合理的解决过程”等批评意见也被逐渐发现。批评家逐渐可以感知到,在赵树理身上,其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由不可见变为可见。总之,如李松睿所发现的,当解放区的批评家在40年代由衷赞美赵树理所创造的小说人物时,存在着一系列因素让他们这样判断,这些因素包括文艺大众化思潮、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思想、赵树理的写作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共产党在地方工作中对赵树理作品的应用等;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位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再被当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农民的集体的形象”,只能在真实地表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人物形象的意义上予以理解。
在这认知“装置”转换的背后,其实是赵树理创作本身所蕴藏的“新颖”与“陈旧”的辩证关系。李松睿在其论述中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为了清楚地说明,他将赵树理小说与鲁迅的《伤逝》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作了比较。在鲁迅的《伤逝》中,作家直接为读者呈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赵树理的小说并不表现内心世界;而相较于《暴风骤雨》中个人的命运、爱情以及革命事业的相同结构关系,赵树理的小说又缺少私人生活。不仅如此,赵树理甚至从来没有把诸如人物形象、主题意蕴以及情节编织等文学创作中的常规范畴看作是不容置疑的铁律。他更愿意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党的文艺工作者,让其文字事业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写作永远面对的是现实革命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甚至到了1959年,赵树理更是明确地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问题小说”,表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①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号。。正是因为赵树理的小说始终是为了回应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才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永远不是作为鲜活的个体出现,而总是以农民的集体命运、集体经验的形式呈现出来,即似乎从来不是某个单独的个体,而只是他们所在村落“新生力量的集体命运的具象化”。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日本学者竹内好对赵树理小说“新颖性”的发现。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新文学》第7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一文中,竹内好从“现代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差异入手,分析赵树理小说的“新颖”与“陈旧”。在他看来,赵树理小说看似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却体现出十足的“新颖性”,这种“新颖性”使之从“现代文学”中超拔出来,又超越了“现代文学”与“人民文学”。竹内好以赵树理的小说 《李家庄的变迁》为例,认为主人公小常和铁锁,不再仅仅是“非凡”和“卓越”这种意义上的英雄人物,这与现代文学的个人英雄截然不同。相对于典型人物的核心地位,他们的位置是“侧面”的和“消极”的,甚至最后是“背景化”的,作品中的人物完成典型的同时与背景融为一体。这便使其完成了“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个人,又无疑超越了这种典型的塑造方式,却不完全如大部分“人民文学”所做的那样消弭个性,这就顺利实现了他所说的,“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正是赵树理文学的新颖之处。
现在看来,赵树理小说叙事中被压抑的内心描写和私人生活等因素,固然是4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需要被否定的内容,这也是其作品的“新颖”之处,但这种“新颖”之中暗藏的“陈旧”又会在新的时代被重新指认。这种“新颖”与“陈旧”的辩证,既让时代“发现”了赵树理,又让新的时代毫不留情地将他抛弃。这也正是李杨教授在近期的论文中所指出的《讲话》所包含的“历史的辩证法”的重要意义。在《“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的历史辩证法》一文中,李杨的问题意识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赵树理“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他的“黄金时代”刚刚开始便宣告结束。在他看来,赵树理的作品政治性强,符合《讲话》“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这也是“赵树理方向”得以在解放区奠定的重要原因。但他同时提出,赵树理之所以终其一生都主动服务于政治,但始终未能写出同时代的周立波、丁玲那样的“伟大”作品,不是因为艺术功力的差距,而在于作品表现的是不同的“政治”以及作家对“政治”的理解和认知的不同。这就涉及郭沫若所评价的毛泽东 《讲话》的“经常的道理”与“权宜之计”的差异。在此,“政治”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不能等同于赵树理所理解的一时一地的“政策”。李杨指出:“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一方面,新民主主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政治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政治的地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并最终以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目标。前者为‘权’,后者为‘经’;前者是民族解放,后者是阶级解放。这种关系决定了延安时期的所有新民主主义政策,包括土地政策、乡村政治等等其实都是过渡性的,赵树理的作品如果只是停留于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就不可能表现出两种政治之间的相互协商与相互否定,由此,他永不可能触摸到《讲话》真实的灵魂。”①李杨:《“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的历史辩证法》,《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因此,尽管对应于《讲话》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深入论述以及对文艺工作者要把思想、感情和立场转移到人民大众这边来的要求,立志告别“五四”作家梦,做“文摊”作家,为老百姓——农民服务的赵树理经由周扬、郭沫若、茅盾等文艺权威反复撰文推介,被推到了“五四”文艺的对立面,成为了实践《讲话》精神的典型代表,但在建国之后更为宏大的历史氛围之中,原本奠定的“赵树理方向”还是很快难以为继。这不仅仅是《讲话》所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的差异,即李杨所指出的,赵树理看到了《讲话》对“普及”的强调,并以实践文艺的“普及”功能为己任,却没有意识到《讲话》对“普及”的强调和论述是在与“提高”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展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所要求的历史目标的具体与抽象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李松睿所论述的认知“装置”背后希望展开的论题,而二者的研究也恰恰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共同构成对于赵树理接受难题的别开生面的解答。
【责任编辑 穆海亮】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