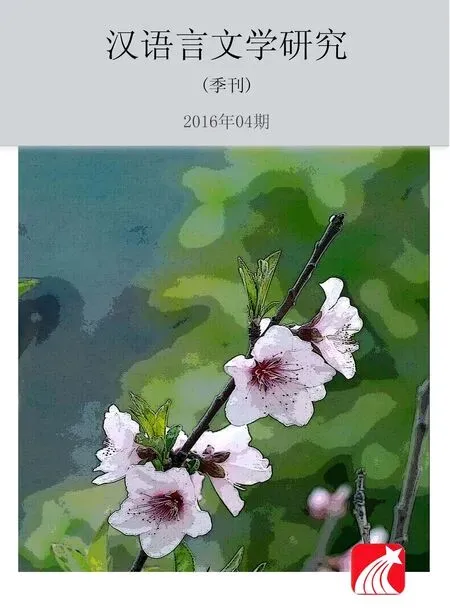郁达夫诗词情感探幽
2016-12-29王文金
王文金
郁达夫诗词情感探幽
王文金
郁达夫创作的旧体诗词是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视了郁达夫诗词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及形成这些情感的个人的、时代的原因,对我们更深地了解他,了解他其他形式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郁达夫;诗词;郁闷;感伤
郁达夫虽然以小说家、散文家著称,但人们评价最高的还是他的旧体诗词。他的好友刘海粟曾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第四。”①刘海粟:《漫论郁达夫》,《文汇月刊》1985年8月号。郁达夫本人也承认,他“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②郁达夫:《骸骨迷恋者的独语》,《郁达夫文集》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23页。。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他一生的经历行迹,可分为四个时期:1896年12月至1913年8月,是在家乡和国内生活、读书的时期;1913年9月至1922年4月,是在日本留学的时期;1922年5月至1938年底,是在国内为生计东奔西走的时期;1938年底至1945年9月,是漂泊旅寓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时期。第一时期,现存旧体诗词不多,包括写欲离乡赴日之作,也只有6首。其他500多首,都是后三个时期创作的。他的诗词基本上都是他心灵的呼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诗人的精神的图像,同时也展现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梁启超曾说,“诗是歌的笑的好呀还是哭的叫的好?换一句话说:诗的任务在赞美自然之美呀抑在呼诉人生之苦?再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为做诗而做诗呀?抑或应该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而做诗?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见……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像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③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4页。。郁达夫的诗词,即属“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而且也“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下面从三个方面来探视他 “哭叫人生”的情感世界。
一、羁旅飘零的郁闷感伤情结
郁达夫的家庭原本为乡绅书香世家,在他出生时已沦为“中产之家”。他三岁丧父,母亲“身兼父职”,支撑着家庭。孤儿寡母,免不了常常“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每在这时,母亲“就只是在父亲像前的一场痛哭”。他看母亲哭了,自己“当然也只有哭”。再加上两个哥哥,因与他年龄相差太大,且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了,所以在郁达夫童年的记忆里,只有“孤独”,而且还有着“饥饿的恐怖”。④以上断续引文,均见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3-356页。在这种生活土壤里所埋下的孤独寂寞的种子,便在他日后羁旅飘零的生活中生根发芽,遂形成了他诗中郁闷感伤的情结。
1913年9月,郁达夫离开家乡,去日本留学。郁达夫初到日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学语初”的困难,这还不算最苦,“最难安置是乡愁”(《秋宿品川驿》)“只身去国三千里,一日思乡十二回。寄语界宵休早睡,五更魂梦欲归来。”(《有寄》)思念家乡亲人,白日未曾间断,夜逼“界宵”仍不能入睡,至“五更魂梦”还是“欲归来”,真乃无时不思乡了。“悔驾天风出帝乡”(《金丝雀》五首之二),诗人真的似对赴日留学有些后悔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乡之情日显浓烈,尤其是每逢佳节,其乡愁更是无处安置。“逆旅逢新岁,飘蓬笑故吾。百年原是客,半世悔为儒。细雨家山隐,长天雁影孤。乡思无着处,掩醉倒屠苏。”(《丙辰元日感赋》)类似这些抒发乡愁的情思,在郁达夫诗中随处可见,如丝结网般包裹着他。
这是不是郁达夫自我矫情,或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呢?不是的,这是他生活乃至于生命的真切体验。其体验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如前所述,他自幼的生活环境,使他尝尽了孤独的滋味。他害怕孤独,又无法驱遣孤独,只得以诗呼诉。即如他在诗中写道:“离家少小谁能惯,一发青山唤不应。昨夜梦中逢母别,可怜枕上有红冰。”(《自述诗》之十六)二是因在日本选学什么科目的问题,曾使他产生过痛苦的纠结。按郁达夫本人的志趣,欲选学文科,而他长兄则认为学医科日后较能适应社会需要。郁达夫当时接受了长兄好意,并在他所住的旅馆里题写“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话来明志。但学了一年之后,他深感医难救国,又萌生了弃医从文之念。他将此一愿望写信告知长兄,因长兄与他的意见相左,在未得到长兄答复的情况下,遂自行决定改学文科。这样就与长兄发生过一段不愉快的龃龉。兄弟情深,又都出于好意,因此,兄弟“二人龃龉”很快冰释。但是,郁达夫改学文科一年之后,回望国事衰微,前途茫茫,心中的愁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愁上加愁:
良医良相愿续非,邯郸客梦料应稀。
危巢日覆家安在,愁煞江南旧布衣。
作“良医”的愿望既难实现,作“良相”的愿望也如“邯郸客梦”,愿望相续而“非”,自称“江南旧布衣”的郁达夫,也只剩下一个“愁”字了。
以上两个方面生命体验所带来的郁闷感伤,虽然在郁达夫心中已近饱和,但还在他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最使他难以忍受的生命体验,就是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处处受到日本某些人的轻视和欺凌。郁达夫在《日本思想的中心》一文中说,“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民族,从头脑的简单、顽固,思想的保守、荒诞的两方面来说,总要以日本民族为第一”,日本民族的某些人,自认为“是神的子孙”,他们有“仇视其他各种人的心理”,尤其对弱国中国的子民。①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8卷,第324页。郁达夫还在《雪夜——自传之一章》一文中,这样诉述他的体验:“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语言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去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②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93页。作为生性自尊、敏感的郁达夫,在这种生活体验下,何不更加产生念国思乡、孤独飘零的郁闷感伤呢?
处于受民族歧视氛围中的郁达夫,为了排解心中所压抑的苦闷,曾“自甘潦倒作情囚”,走入烟花柳巷。但事后又后悔,并将这一后悔的心情告诉曾劝诫过他的长兄长嫂:“垂教殷殷意味长,从今泥絮不多狂。春风廿四桥边路,悔作烟花梦一场。”(《奉答长嫂并呈曼兄四首》之三)看来诗人似乎真的如杜牧一样“梦醒繁华”了,而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他常常又故态重萌。痛悔、重犯、又痛悔,这在他郁闷苦恼心灵中无异于雪上加霜,因而使得他感到“生太飘零死也难”,并期望别人“莫与多情一例看”(《懊恼两首》之一)。郁达夫就是这样:“十年海外苦羁留,不为无家更泪流。鬼蜮乘轩公碌碌,杜陵诗句只牢愁。”(《寄和荃君原韵四首》之三)
1922年4月,郁达夫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归国后的情景又是怎样呢?依然是羁旅飘零:“回国来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①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71页。他又自述,“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②郁达夫:《忏余独白》,《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251页。。郁达夫自谓似“人海中间一点萍”,漂泊到上海、北京、武昌、广州、杭州、福建和山东等地。由于奔波劳碌心情郁闷,又染上了肺病,郁达夫于是陷入了“天涯歌哭”“秋雨秋风遍地愁”境地。写于1926年的《和冯白华〈重至五羊城〉原韵》一诗,最能反映他这一时期的心境:
侏儒处处乘肥马,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惊海内,竟无饮亶粥润诗肠。
敢夸邻女三秋望,忝受涪翁一瓣香。
升斗微名成底事,词人身世太凄凉。
“侏儒”,在这里指无能无德的当权者,他们肥马轻车,高官厚禄,而有志的文人只能“年年伴瘦羊”,自己则更为清苦“竟无饮亶粥润诗肠”。观社会不平,诗人愤从胸起,又感无奈,只好叹曰,“词人身世太凄凉”。
1938年底,诗人应星洲日报社之邀,怀着凄苦,又远走天涯——新加坡。至新加坡之后,复如去日本一样,又泛起“乡愁”:“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窗外乐舞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后来,又因家庭发生变故,他一人寓居新加坡,如孤鸿独雁,更是“满怀羁思涕横流”(《〈温陵探古录〉题词》)。思乡之愁还在其次,更愁的是,随着日寇的铁蹄踏进新加坡,诗人的生活乃至生命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1942年2月初,诗人乘难民船,撤离新加坡赴苏门答腊。诗人本打算“愿随南雁侣,以此赋刀环”(《星洲既陷,厄苏岛,困孤舟中,赋此见志》),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谁料中途受阻,只好暂栖身于苏门答腊。他当时为排遣心中的苦闷,日赋一诗,名《乱离杂诗》,现存诗12首。其诗有曰:“镇日临流怀祖逖,中宵舞剑学专诸”;“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细雨蒲帆游子泪,春风杨柳故园情”;“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读着这些诗句,不禁使我们想起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潦倒寂寞的苦况,也更使我们感到,非经漂泊乱离之人,是难以道出这复杂、深沉、真切的内心体验的。
郁达夫说:“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③郁达夫:《〈茑萝集〉自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53页。诗人这段话,不仅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小说有启示意义,更对于我们窥探他的诗所包蕴的内心的幽情,有着解开密码似的作用。
二、“虚负凌云万丈才”的心有不甘情结
郁达夫在《自述诗十八首并序》之二中写道:“风雪四山花落夜,窦家丛桂一枝开。”“窦家”,指后周窦禹钧家,其家五子相继登科。冯道给窦禹钧的诗中赞曰:“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郁达夫借此寓自己三兄弟。“丛桂”,即指三兄弟,“一枝开”说他自己。三桂争芳,“名扬浙水滨”(《自述诗》之三),而郁达夫的才气更是不凡——“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生小便聪明”(《自述诗》之六)。郁达夫所言,并非是自我矜夸之词,他不但有诗才,而且胸怀“风云奇气”(《自述诗》之十一)。可是“谁知早慧终非福”(《自述诗》之六),社会现实却使他难施抱负。于是他遂心灰意冷,愁思百结:
不羡神仙况一官,觚棱那复梦长安。
脱樊野鹤冲天易,铩羽山鸡对镜难。
黄叶欲凋闻敕勒,苍生回顾足悲酸。
秋来百事仍依旧,只觉罗衫日渐单。
——《初秋客舍二首》之二
这首诗于1915年秋作于日本。诗人去日留学,本欲如脱却樊笼的野鹤,青云而上,展翅高翔,但现在却似“铩羽山鸡”,对镜不堪自照。秋来黄叶欲凋,罗衣单衫,心中充满了“悲酸”。现实与愿望差距太大,日本也并非成才之地。“事到无成愿转平,从今梦自冷春明。若能阳羡终耕读,何必崎岖上玉京。”(《村居杂诗五首》之二)“书生风骨太寒酸,只称渔樵不称官。我欲乘风归去也,严滩重理钓鱼竿。”(《无题三首》之三)诗人由愿望不能实现的意冷,进而产生了归国隐居耕读之念。当然,诗人这样写,也只是他苦闷心情的一种抒发,并非真的要付诸行动,不然既与长兄无法交待,同时自己也难以在将来解决“衣饭难”的问题。在此后不久(1919年秋),他有了一个消解郁闷、施展长才、实现抱负的好机会:国内举行招收外交官和高等文官的考试。诗人急急由日本回国,趁考试前回老家富阳小住,借以备考。经过备考之后,他觉得此次赴京应试应是有把握的,所以他在别家赴京前,以打叠愁苦之心态,赋诗曰:
匆匆临别更登楼,打叠行装打叠愁。
江上青峰江下水,不应齐向夜郎流。
——《题春江第一楼壁》
诗中抒发了打叠愁闷、志在必得的心情。然而谁知这次考试却遭落败。其原因非是诗人才能不及,而是他不谙社会黑暗,事先未行“关说”疏通之故也!他愤懑地在日记中写道:“庸人之碌碌者,反登台省;品学兼优者,被黜而亡。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余闻此次之失败,因试前无人之关说之故。夫考试而必欲人之关说,是无人关说之应试者无可为力矣,取士之谓何?”(见1919年9月26日日记)
这次考试失利,对郁达夫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由此,他的诗风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时期的诗,虽充满了郁闷感伤,但并非是痛入骨髓的哀怨,故词采清丽,情感飘逸。而考试失利后所写的诗,却于郁闷感伤中夹带着一种心有不甘的悲慨之情,带血带泪,深沉顿挫。如《己未秋,应外交官试被斥,仓卒东行,返国不知当在何日》一诗,即是他诗风转变开始的明证:
江上芙蓉惨遭霜,有人兰佩祝东皇。
狱中钝剑光千丈,垓下雄歌泣数行。
燕雀岂知鸿鹄志,凤凰终惜羽毛伤!
明朝挂席扶桑去,回首中原事渺茫。
这是一首豪情悲歌。首联自比荷花与兰芷,虽惨遭严霜摧落,但依然“有人兰佩祝东皇”。意谓有人赞扬他有如荷花、兰芷的高洁,有如屈原的气节。颔联以宝剑和项羽自喻,抒发被斥的处境和英雄失利的悲愤。颈联又以鸿鹄和凤凰作比,直斥主考当局昏庸俗眼,不识志大才高的人才。尾联笔锋一转,诉述“明朝”将怀着遗憾和不平,“挂席”东去“扶桑”。回首故国,渺渺茫茫,“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诗人悲怆愤懑之情可见一斑。后又以《己未出都口占》为题,再次抒发不甘落败的情怀:
芦沟立马怕摇鞭,默看城南尺五天。
此去愿戕千里足,再来不值半分钱。
塞翁得失原难定,贫士生涯总可怜。
寄语诸公深致意,凉风近在殿西边。
这首诗的抒情、议论大开大合,尤其是“贫士生涯总可怜”一语,不仅读来令人鼻酸,而且也会勾起同病相怜“贫士”们的共鸣。结尾“凉风近在殿西边”,是取李商隐《宫辞》的诗意。李商隐的诗为:“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李诗借宫嫔之口,道出自己的仕途遭际,郁达夫则借典抒怀,言当局之无道,令文人志士绝望心寒。但是诗人还怀抱着对未来的一线希望:“塞翁得失原难定”,也许仍有翻身的日子。
郁达夫考试失利返日继续学业后,仍难解开这一复杂的不甘示弱的悲慨情结,于是他连连写诗,抒发他怀才不遇、求仕无门的不平景况:“纵裁千尺素,难尽九回肠”(《偶感》);“天津桥上鹃啼日,痛哭长沙陋贾生”(《和某君》);“老夫亦是奇男子,潦倒如今百事空”(《客舍偶成》)。由此可见,他因考试被斥的挫败感有多么深!具有贾谊之才的“奇男子”,为何“潦倒如今百事空”呢?志如鸿鹄的有识之士,为何今日“翼未张”呢?诗人通过这次考试的亲身体验,找到了原因——统治当局不分良莠、压制人才之故也:
俊逸灵奇宰相才,卞和抱璞古今哀。
士生乱世空弹铗,客到新亭漫举杯。
一死拼题鹦鹉赋,百年几上凤凰台。
问他白玉楼未成?欲向天公泣诉来。
郁达夫观古今社会现实,进一步证实了压制人才的祸根在当权者,古时具有“俊逸灵奇”的宰相和“抱璞”进献的卞和都不为当权者所识,如今“士生乱世空弹铗”,也就觉得不奇怪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一死拼题鹦鹉赋”,学狂士祢衡写诗文痛斥权奸。
郭沫若在《郁达夫诗词抄·序》中,以郁达夫名郁文评价说:“古人说‘多文为富’,他叫郁文,真可谓名实相副,‘郁乎文哉’了。”然而,即使如此,也避免不了如李商隐一样:“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钰《哭李商隐》)于是,他心中就结下了心有不甘而又难以释解的情结。
三、国破家毁的愤懑无奈情结
爱国主义是郁达夫的思想核心。他13岁时开始萌生出国家的意识和概念,16岁即写 《咏史三首》:
楚虽三户竟亡秦,万世雄图一夕湮。
聚富咸阳终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贫。
大度高皇自有真,入关妇女几曾亲。
虞歌声里天亡楚,毕竟倾城是美人。
马上琵琶出塞吟,和戎端的爱君深?
当年若赂毛延寿,那得诗人说到今。
第一首咏评项羽灭秦,第二首咏评刘邦亡楚(灭项羽),第三首咏评昭君出塞和亲。不唯文笔清健飘逸,且一位16岁少年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如此深切的见解,可见他关注古今“天下大事”的爱国情怀。
郁达夫去国留日之后,爱国思想日渐成熟,由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而转入对整个国家的关心,所以他在留日期间所写的诗,一直是思乡之苦伴着忧国之愁。如《秋兴四首》之一:
桐飞一叶海天秋,戎马江关客自愁。
五载干戈初定局,几人旗鼓又争侯。
须知国破家安在,岂有舟沉橹独浮?
旧事厓山殷鉴在,诸公努力救神州。
又如《席间口占》:
醉拍栏杆酒意寒,江湖牢落又冬残。
剧冷鹦鹉中洲骨,未拜长沙太傅官。
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几辈出关难。
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两首诗所抒发的都是思乡忧国之情。前一首的“五载干戈初定局,几人旗鼓又争侯”,指国内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初定局”之后,又起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之间的“争侯”之斗。客居日本的诗人郁达夫,面对如此混乱的时局,不觉“自愁”,于是呼吁“诸公努力救神州”。后一首,诗人自谓是“慷慨悲歌,觉有老杜哀愁之风”。确实,诗人“醉拍栏杆”,既有“未拜长沙太傅官”之叹,又有为神州争侯“泪暗弹”之忧。诗人忧思萦绕,又以《送文伯西归》一诗,继续抒发他欲“救神州”的情怀:
相逢客馆只悲歌,太息神州事奈何!
夜静星光摇北斗,楼空人语逼天河。
问谁堪作中流柱,痛尔难清浊海波。
此去若从燕赵过,为侬千万觅荆轲。
文伯,即作者友人王文伯。文伯西归,诗人为其送行,共话神州,悲歌太息,又无可“奈何”。“为侬千万觅荆轲”这一神来之笔,既是诗人对国人的呼唤,也是诗人自己欲“救神州”的义士精神的真切表达。
郁达夫欲“救神州”的忧国之思,于1931年日寇侵华之后,变成了国破之恨,于是他便将笔锋转而刺向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投降主义者。写于“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题剑诗》和《过岳坟有感时事》,即是抒发这一情思的代表之作:
秋风一夜起榆关,寂寞江城万仞山。
九月霜鼙摧木叶,十年书屋误刀环。
梦从长剑驱流豹,醉向遥天食海蛮。
襟袖几时寒露重,天涯歌哭一身闲。
——《题剑诗》
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
权臣自欲成和议,金虏何尝要汴州。
屠狗犹拼弦上命,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立马吴山志竟酬。
——《过岳坟有感时事》
前一首的 “榆关”,即山海关。此指日寇于1931年9月18日,突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寇相继占领了我东北全境。“秋风一夜”,山河变色,诗人“梦从长剑驱流豹”,随我勇猛战士,长驱直入,英勇杀敌,不仅如此,还要剥敌之皮食敌之肉(“食海蛮”)。笔锋犀利,来敌朝食的心情,溢于满纸。后一首直斥采取不抵抗政策的投降主义者。这些“小儿耽逸乐”,惜头颅,不知弦上拼命,反而欲与敌“成和议”,岂不知“金虏何尝要汴州”,他要的是整个中国。如果“饶他关外(指日本)童男女”,其后果不堪设想。诗人史笔抒情,于对投降主义者的耳提面命中,深刻地揭露出了日寇的狼子野心。郁达夫一方面为国破而忧心如焚,一方面又为自己天涯闲旅、“十年书屋误刀环”而悔恨。于是常在这样焦虑矛盾的心境下,表达出一种恨而无奈的“歌哭”情怀。
上面所说的是郁达夫所写的“国破之恨”,下面再说说郁达夫所写的“家毁之愁”。1933年,郁达夫于“冷雨埋春四月初”(《迁杭有感》)的日子里,将在上海的家迁到杭州。这一迁,便埋下了毁家的祸根。破坏他与王映霞婚姻家庭的人,就是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流氓党棍许绍棣。许趁郁达夫行踪不定之机,采用各种手段诱骗了王映霞的感情,二人有染,终至王映霞与郁达夫夫妻感情产生了裂痕。为此郁达夫自1936年春至1938年冬陆续写成《毁家诗纪》20首(诗19首,词一阕),诗情凄惋,令人难以卒读。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毁家诗纪》之四
“鸠占凤巢”之辱,谁堪忍受,而郁达夫一介儒生,手无权柄,又加国难当头,不忍也得忍,所以他在《贺新郎》一词中无可奈何地写道:
忧患余生矣!
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
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
耻说与,衡门墙茨。
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
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持?
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
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
歼小丑,自然容易。
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
先逐寇,再驱雉。
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读着这首词及词后之注,不禁令人扼腕。个人事小,民族复仇事大,更见诗人掂量轻重的大义情怀。
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怀着“张禄有心逃魏辱”(《抵星洲感赋》)的心情,“离愁戚戚走天涯”,带着王映霞避居新加坡。但“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残心篆看全灰”(《毁家诗纪》之十二),二人终至劳燕分飞,协议离婚。
郁达夫于1935年40岁生日时曾写诗抒怀曰:“卜筑城东事偶然,种瓜敢咏应龙篇。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赵龙文录于右任并己作诗题扇贻余,始就原韵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诗》)十年后的现实却是:“相看无复旧家庭,剩有残书拥画屏。异国飘零妻又去,十年恨事几番经。”(《自叹》)诗人叹声未了,却不料被残忍的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
郁达夫带着羁旅飘零郁闷感伤、空负高才的心有不甘和国破家毁的愤懑无奈纠集而成的复杂情结走了,真是令人惜哉!痛哉!因此,当郭沫若闻知郁达夫失踪而凶讯未确的情况下,便奋笔疾书道:“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日本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①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年第3期。
【责任编辑 穆海亮】
王文金,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