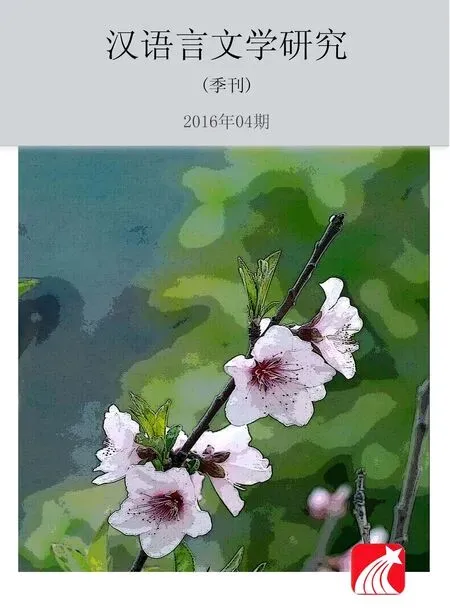流动的“地方性”与“乡土文学”
2016-12-29李斌
李斌
流动的“地方性”与“乡土文学”
李斌
有关现代文学中的“地方性”和“乡土文学”的研究其实已有不少,比如对“民族形式”等相关理论的探讨,对现代文学和“区域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但与以往研究不同,李松睿的《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既不是从文学题材和主题学的角度探讨“地方性”问题,也不是将这类作品“看作是一个按照某种逻辑不断发展的特殊文类”。本书所讨论的“地方性”,源自作者独特的问题意识:“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对地方性问题如此念兹在兹,并在文学表达中将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在加强其作品的地方特征时,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地方性特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这样的问题意识,意味着松睿不是将“地方性”当成一种自然生长的文学现象,去描述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育过程,而是将它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放置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探讨它在特殊时代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又如何在理论和创作之间回旋;以及提出“地方性”的理论家、在文学中去表现和落实的作家,他们通过这一概念意欲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对当时的文学和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对特殊文学现象的历史化的处理方式,体现了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新的研究思路:即借助于文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从以前那种将文学作为一种自足性的现象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不再将文学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形式等作为一种自然生长的现象,而是将文学放在特定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等网络中去考察。这样,跟文学相关的一些概念就变得更为流动、更具结构性。最近讨论较多的“民国机制”“大文学史观念”等,都是这方面的最新思考。
由于将“地方性”放置在特殊的时代社会背景和作家的独特处境下考察,松睿感觉到不可能去对这一时期的小说进行全盘性的讨论,“而是选择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从解放区、国统区以及沦陷区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他们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变化,特别是对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因素的呈现进行考察,探究这些作家在怎样的价值尺度中理解文学的地方性特征,他们为什么在创作中努力加强作品的地方性特征,他们的这种尝试又对小说的形式产生了什么影响”。由于松睿的方法是对特殊文学现象进行历史化处理,所以个案研究对于他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样最有可能呈现出具体历史语境中“地方性”的多样复杂性。
事实也是如此。当松睿选择了国统区的老舍、解放区的赵树理、沦陷区的梁山丁和师陀这四位作家作为典型,考察其作品中的“地方性”时,他发现,尽管同样是强调作品的“地方性”,四位作家的初衷和其作品的表达效果竟然相去甚远。从放弃“地方性”再到回归“地方性”,老舍考虑的始终是如何在作品中加强民族特色,发挥民众动员功能。在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中,他将自己“最为熟悉的北京故事,作为负载民族、国家象征的手段”。赵树理代表了解放区文学的方向,他不像老舍那样将“地方性”视作普遍性的有机因素,而是将其作为检验自己是否成功地改造思想,是否为工农兵服务的标准。而在沦陷区的梁山丁那里,“地方性”则既有反思现代性,也有表达殖民地普通百姓情感的功能,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在师陀那样身处沦陷区“因苦闷贫病变得意志消沉的作家”那里,“地方性”成为一种苦闷的心灵的投影。通过这四个个案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同样重视“地方性”的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其背后却有不同的思想状态、言说方式和功能期待。松睿这些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本质性概念,比如“乡土文学”等。这些本质性概念在某一时期凝固下来,概念的凝固的过程中也凝固了研究者特定的倾向和情感。如今,松睿让概念重新流动起来,那些先前的情感和倾向也随着概念的重新打开和流动而逐渐稀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一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把握历史的独特的位置和立场。当然,松睿是客观的,他按捺住自己的倾向,尽量冷静地、不动声色地、如实地去展开“地方性”在20世纪40年代的多种形态。
松睿的雄心是使“地方性”和“乡土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所补充和推动,所以,他不会只满足于横剖面的个案研究,他要将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地方性”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去考察。于是,他明确提出,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的“地方性”特征源自对新文学的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严酷的现实,来自不同区域,处于不同政权之下的作家和批评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对‘五四’新文学感到不满,开始自觉地构想更能为中国的普通读者所接受的,并与战争环境相适应的文学表达方式”。所以,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的“地方性”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时代问题,而是新文学自我调适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同时,40年代对于“地方性”的不同“构想”,跟30年代新文学关于“地方性”的思考,有很多延续之处,但在战争状态下,在不同政权统治区域,又有了各自特殊的表现形态。在《结语》部分,松睿还探讨了文学中的 “地方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所面临的一个紧要任务,就是如何在这片幅员辽阔,各地差异性极大的土地上,行之有效地建立起全体人民对这个新政权的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性特征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的方言土语受到压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如此一来,松睿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史叙述,这种以小说中的“地方性”为核心的历史叙述,无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有所推进。
松睿的个案研究是精彩的,将个案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能够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但将个案作为典型,强调它的代表性,可能会遮蔽历史的丰富性。将“地方性”作为民族象征的《四世同堂》,究竟在国统区的小说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沙汀表现四川“地方性”的《淘金记》,沈从文表现湘西“地方性”的《雪晴》等国统区小说,是否也都是以“地方性”作为民族象征呢?萧红的《呼兰河传》,表现了东北的“地方性”,跟同样表现东北“地方性”的梁山丁的《绿色的谷》,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区域,但它们有没有一定的共性呢?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是否也可以算作“地方性”呢?如果算,跟梁山丁和师陀小说中“地方性”,区别何在呢?如果能带进这些问题,作更为详尽的考察和区分,就可能部分地避免个案研究对于历史丰富性的遮蔽。
在松睿的设计中,“地方性”和“乡土文学”是流动的,也许会出现跟惯常理解相悖的地方甚或暧昧不明之处,但本书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十分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表达。从这些表达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松睿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反复提炼以及文字上的仔细打磨,这体现的是一位有着良好学术训练的青年学者的可贵品质。但是,过于清晰的表述可能也隐藏着危险:容易以偏概全,容易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从松睿的其他成果来看,他对此是有所觉悟的,此处的明晰或许只是受制于博士论文这一体裁的规训而已。
在讨论“地方性”和“乡土文学”时,松睿的对话对象是丁帆、汪晖、李泽厚、杜赞奇等有着广泛影响的权威学者。松睿在肯定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这部著作“忽视了对赵树理、孙犁是在怎样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强地方性描写的探讨,也就没有通过细部的文本分析告诉读者地方风景的刻画究竟对小说作品的形式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汪晖和李泽厚的相关研究,松睿批评说:“两位研究者在对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更愿意将研究对象纳入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框架,因而往往会得出一些偏离史实的结论。”对于杜赞奇有关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问题的研究,松睿认为:“在对中国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话语所做的出色研究中,他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依据启蒙主义和线性时间观来进行的话语建构,它遮蔽的是那些更为本真、自然的关于民族的话语。”在我看来,松睿对这些权威学者相关研究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学术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不断的对话中丰富和发展的。松睿这种大胆挑战的精神,使得他的“地方性”和“乡土文学”的研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松睿的研究领域逐渐开阔起来,正如吴晓东老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近来,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也开始丰富多彩,影视批评、艺术评论、外国文学研究,都正在成为他关注的领域。”在影视批评和当代文学研究等领域中,松睿都有不俗的表现,他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正成为我们80后学人中的佼佼者。从《书写“我乡我土”》出发,松睿迈向的是广阔的学术天地。
【责任编辑 穆海亮】
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