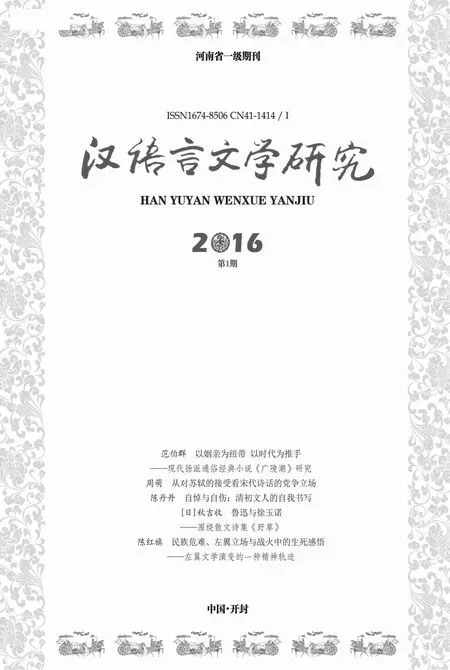试论严歌苓《白蛇》中的身体叙事
2016-12-28郭一
郭一
试论严歌苓《白蛇》中的身体叙事
郭一
摘要:严歌苓在中篇小说《白蛇》中通过对舞蹈家孙丽坤在不同时期身体之美变化的描写,讲述了一个女性丧失自我又重获自我的故事。小说中孙丽坤对身体之美的重视和追求,体现了她的自我意识。她的身体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社会关系变化的一种投射。自我借身体之美表达,经过身体的颓败而丧失,最终又通过身体之美找回,这一精妙而完整的构思体现了身体叙事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也打破了长久以来性格描写中灵与肉相割裂的惯习。
关键词:严歌苓;《白蛇》;女性;身体叙事;自我意识
一
严歌苓的《白蛇》讲述了舞蹈家孙丽坤在被关押期间与女扮男装的调查员徐群山(珊)之间的感情。在这段感情中,孙丽坤就如同美丽却落魄的“白蛇”,而徐群珊则是默默陪伴努力拯救她的“青蛇”。在这段同性之爱中,孙丽坤重拾了生活的信心﹑找回了一度被丢失掉的自我。面对这段不被人接受的同性之爱,孙、徐虽迫于社会压力不能相守,却用她们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彼此间这份情谊。严歌苓在谈及此时曾说:“我能写的没有任何人能感觉到我是在写一段不正常的感情,我写的就是像男人和女人的感情一样,里面照样有非常高尚和非常神圣的东西。”①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上海文学》2005年第6期,第33页。孙丽坤舞者的身份暗示了她的身体之美。正如舞者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内心,生活中的孙丽坤也通过她的行为举止表达了她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她的骄傲和自我正是通过她的身体之美展露无遗。在被关押期间,孙丽坤身体之美的变化,体现了她内心自我意识的变化:“女主人公身体消失后,紧接着代替它的是一个更加精神化的灵魂。”②Helena Michie.The Flesh Made Word:Female Figures and Women Bod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86.因此,《白蛇》中孙丽坤的身体之美的表面背后有着更大的阐释空间。
作家在文学中对身体的描写,使得身体成为一种隐喻,身体因此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与作为第一位的精神不同的是,身体一直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作是第二位的。与精神的理性相对,身体意味着非理性的欲望和激情。“身体不仅是生理性的,更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政治性的……如果理智被认是主宰的﹑自律的(和男性的),那么与其相对的身体就会被认为与欲望﹑非理性﹑无法控制的激情和颠覆性的欲望相关,身体就是一个被殖民的﹑偶然的﹑或许是女性的。”③Sarah Sceats.Food,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63.因此,身体的隐喻意味着人潜意识中个人欲望的表达。关于女性身体在文学中的表达,Helena Michie曾说:“对于这些女性主义批评和其他人,身体是表现女性体验的最具文学性的土壤,也是表达女性体验文学性的一个隐喻。”④Helena Michie.The Flesh Made Word:Female Figures and Women Bodies,p.128.第二位的身体和第二性的女性决定了女性的身体叙事具有双重的非理性,因此,文学中女性的身体叙事有着极为复杂的阐释方式。
二
《白蛇》中的女主人公孙丽坤是“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舞剧《白蛇》是她的代表作。孙丽坤的身体之美是她骄傲的资本:“她漂亮就漂亮在那个下巴和颈子上。那样一转,这样一绕,谁都不在她眼里。”①严歌苓:《白蛇》,《严歌苓作品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文中《白蛇》引文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标注)。孙丽坤的身体之美也体现了她的审美价值:“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的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舞动的胸脯,爱她的长颈子尖下巴流水一样的肩膀。”
除了那些男人,还有一位小舞迷徐群珊,她被“白蛇”之美所折服,更被“白蛇”的身体之美深深吸引。与那些男人不同的是,徐群珊眼中孙丽坤的身体不是肉欲的,而是美得像个“受难的女英雄”。凝视着这具美丽的身体时,徐群珊手中的烟如庙堂里的香火一般,供奉的是神圣的孙丽坤。由这种虔诚之爱生发出的是徐群珊对孙丽坤的敬爱:“徐群山(珊)爱这肉体,他不去追究它的暗示,因为那种最基本的准确言语就在这暗示中,不可被追究。”孙丽坤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种超越语言的准确语言,她“不意识到她已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物质存在,她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那直觉和暗示形成了这个舞蹈的肉体。一具无论怎样走形﹑歪曲都含有准确表白的肉体”。
孙丽坤身体之美在平日里得到的赞美和称赞,在被关押期间则变成了被猛烈恶毒地羞辱和调侃之源。这种尖锐地转变,源于强烈情感未得到满足而导致的挫败感。男人们爱着孙丽坤的美丽,但是“他们的爱对于它太具体笨重了。它的不具体使他们从来不可掌握它,爱便成了复仇”。与男人们的爱不同,舞蹈队的小女娃对孙丽坤的地位十分恭敬,她们把孙丽坤当成“祖师爷”,甚至进她单独的练功房和化妆室都像进祖宗祠,而“如此的恭敬,自然是要变成仇恨的”。男人的“复仇”和女娃们的“仇恨”,导致了他们在孙丽坤被关押期间对其身体之美的扭曲解读,即“被看作是一个怪异的他者”。②Hsiu-chih Tsai,abstract of“Female Sexuality:Its Allurement and Repression in Geling Yan’s“White Snak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Vol 23,2007,p.123-146.因此,与之前美丽高雅的舞者不同,此时的孙丽坤是一个有着“水蛇腰”和“一百二十节脊椎骨”的“国际大破鞋”。
在被关押期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丽坤褪去了她作为一个舞者的美丽,成了一个身材走形的女人:“一个茧蛹腰,两个瓠子奶,屁股也是大大方方撅起来上面能开一桌饭。脸还是美人脸,就是横过来了;眼睫毛扫来扫去扫得人心痒,两个眼珠子已经黑的不黑白的不白。”虽然因其身体之美而被诟病,但丧失了身体之美的孙丽坤依旧受到了审美和道德上的双重批判。文学作品中的“肥胖”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意味着形态上的丑陋,更意味着道德上的缺陷:“肥胖被普遍认为是令人厌恶的;研究显示肥胖者被污名化,被认为需要为他们的状况负道德层面的责任。”③Sarah Sceats.Food,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p.90.而人们对“肥胖的女性”则更为苛刻:“据Edwin Schur所说,肥胖的女性尤其容易遭受吹毛求疵,或许是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服装永久地将她们的身材展示出来,因此肥胖被认为是对符合常规体型尺寸的失败(或拒绝)。”④Sarah Sceats,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p.91.这种对“肥胖”、尤其是对女性“肥胖”的憎恶,源自于社会对女性纤瘦柔弱之美的审美要求:“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存在一种文化上(和商业上)赞同的理想苗条(甚至瘦削)的女性身体。对于苗条身体典范的起源并不容易确定,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趋势。”⑤同上,p.65.而对于身体的控制,尤其是女性身体的控制,实则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个人的控制:“福柯在身体规训的微观政治和人口调节的宏观政治之间的对比,与身体意象(和节食)的问题极为相关,往大处考虑,可是说是一种社会控制。”①Sarah Sceats,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p.62.
因此,孙丽坤的身体之美除了生理层面的美与丑,还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隐喻了她的道德水平。和苏联舞蹈家之间的风流韵事使得孙丽坤成为了“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国际特务嫌疑﹑反革命美女蛇”。其实,在别人眼中她的美貌就是她的罪行,因此,对她最恰当的惩罚就是剥夺她的美。
在被关押期间,孙丽坤这只有着“粉蒸肉”似白膀子的“胖胖的美女蛇”已经失去了别人对她的距离感和敬畏之心。老少爷们失望着,因为他们“看清她头发好久没洗,起了饼,脸巴子上留着枕席压出的一大片麻印。大家还看清她穿件普通的淡蓝衬衫,又窄又旧,在她发了胖的身子上裹粽子。”
发了胖的孙丽坤是“罪恶的”﹑是“羞耻的”。她的“肥胖”是社会对她的羞辱,也隐喻着她对自我的放弃。关于身体与内心和社会的关系,Russo罗列出“怪诞身体”的两种作用方式:其一是对内心状态的投射,并且多与可怕的心理状态相关。其二是怪诞身体的社会作用,它与所有“低级”相关——屈辱的身体部位,过程和物质。一个肥胖女人的形象或许包含了个人的和社会的屈辱:一方面作为个人“羞耻与被压抑的欲望”的仓库,一方面作为社会过度消耗的文学屈辱。Russo称其为“生产的负面”和“过度生产的危险”,简而言之,肥胖的妇女只是“一个替罪羊”。②同上,p.90.
因此,孙丽坤失去的身体之美,实际上是她已经失去了的自我。她的舞蹈﹑美丽,以前支撑她如女英雄﹑女神般自我的特质,在“一颗烟锅巴”面前消失殆尽。为了“一颗烟锅巴”,孙丽坤向监牢外的男人们毫无顾忌地展示着她那条“有着太多太暧昧的意味”的腿:“那么一条笔直粗壮如白蟒的腿,众目之下赫赫然竖将起来。”此时,她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更是她作为舞者的自我。此时的她再也不是舞台上那条备受观众喜爱的“白蛇”,而是马戏团里供人娱乐的猴子:“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笼子般的铁栅栏内,成了一只马戏团的猴子,当着满身淫汗的老少男人玩起两条曾经著名的腿;两条美丽绝伦,已变得茁壮丰肥的大腿,就这样轮番展示了它们无尽﹑深长的意味。”美丽、高雅﹑性感——这双腿曾经的内涵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暧昧不明的色情﹑欲望和卑贱。
三
舞者孙丽坤是美丽且骄傲的:“她比其他演员高,背挺得都有点向后仰了。”是她的美赋予了她强烈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她就是看上去高;她那个尖下颏子一抬就把她抬高两寸。大会小会斗争她,她也不放下那个下巴颏。”放不下的“下巴颏”,是她放不下的自我。但孙丽坤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她的自我:“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了舞蹈,她有没有自身?”她的生活里只有舞蹈,或者说,她把舞蹈过成了一种生活:“她用舞蹈去活着。活着,而不去思考‘活着’。她的手指尖足趾尖眉毛丝头发梢都灌满感觉,而脑子却是空的,远远跟在感觉后面。”孙丽坤的舞蹈与她的身体之美密不可分,而她的身体之美与她的自我意识也息息相关,因此,当她被剥夺了舞蹈和美的时刻,她真正失去的是内心的自我。
情势所迫,孙丽坤不得已放弃了她的自尊,她“学会若无其事地跟女娃们脸对脸蹲茅坑”。放弃自尊,也就意味着对自我的放弃,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习惯了,不再为一大串不好听的罪名羞惭得活不下去”。
然而孙丽坤并没有完全丧失自我。在她忘却了之前的美好时,最后忘却的是小女孩眼里的失望:“小女孩如同眼看一尊佛像在面前坍塌那样,眼睛里充满坍塌的虔诚。”小女孩的出现暗示着美与舞对身处泥淖中的孙丽坤的救赎,即“尽管你什么都没了”,“但还永远是舞台上那个白蛇”。
孙丽坤对丑陋自我的不满,是她自我觉醒的开始。真正被派来救赎孙丽坤的,是她曾经的一个小舞迷。他(她)的出现,使得孙丽坤意识到自己现状的窘迫。面对着被派来调查她的青年调查员的嫌弃和怜惜,孙丽坤意识到了自己的丑陋和窘迫:“她顿时感到自己这三十四岁的脸从未像此刻这样赤裸。”她做出了“一个意外的下台动作”:“转身走进了另一块布景搁置的小角落。”在舞台上,孙丽坤的“下台动作”是为了避免身体“赤裸”,而在监狱里,她的“下台动作”是为了避免精神“赤裸”。她习惯了被人宠爱﹑崇拜,而不是惹人嫌弃﹑怜惜。“下台”之后,孙丽坤期望着调整自己的内心状态:“她进了一个他目光不能所及的角落,不是为了更衣修发,而是要更彻底换一番精神容貌。她知道自己的精神容貌是丑陋不堪的,如同一具裸露的丑陋不堪的肉体。”孙丽坤在黑暗中的调整,使得她的自我又开始萌芽:“她走出角落重新登场时非常的不同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视的更换就在那片阴暗中完成……她却与猝然下台前不是一个人了。她那个已宽厚起来的下巴颏再次游动起来,画出优美的弧度。她的脸仍是那种潮湿阴暗里沤出的白色,神情中却出现了她固有的美丽。她原有的美丽像一种疼痛那样再次出现在她修长的脖颈上,她躲闪着疼痛而小心举着头颅。她肌肤之下,形骸深部,都蛇似的柔软和缠绵,蛇一般的冷艳孤傲已复苏。”“黑暗”,往往象征着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孙丽坤进入“黑暗”之中,正是她进入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当中。在这片“黑暗”中,她积极探索着自我,直到她触碰到自我的萌芽时,她得有勇气走出这片“黑暗”,去面对外界对她的审判。
这条已经逐渐复苏的“美女蛇”已经有了自我的意识和想法:“她把身子重心移到一条腿的支点上,伸出另一条腿,绷紧脚尖。腿在他眼前升高,一时间不再像腿。它似乎在无限延伸,长而柔韧。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那腿上苏醒舒展。这有灵有肉的腿使那不成形状的裤子蓦然消逝了一般。”而孙丽坤腿部美的恢复,暗示着她自我意识在逐渐觉醒:“她的另一条腿。它有了它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弹动几下,又绕动几下,出现了一个哑语般的暗示。”腿在这里是提喻的用法,它的“想法和意愿”,就是孙丽坤自己的想法和意愿。这“哑语般的暗示”,就是孙丽坤自我的复萌和对爱情的渴望:“活到三十四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
爱情重燃孙丽坤对自我和美的追求,她努力找回那个曾经的自我﹑那个美丽的舞者孙丽坤:“没有镜子,她只能用灯光投影来端详自己。她这样做已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的身体细下去,轮廓清晰起来。又是苗条超拔的她了。每天半夜她偷摸起床,偷摸地练习舞蹈。这时她从投影上看见舞蹈完全地回到了她的身上。所有的冗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
“镜子”的意象与女性之美密不可分。“镜子”对女性容貌的如实反映暗示着对女性的审美凝视,因而也被认为是女性虚荣的载体:“镜子,因其复制和失真的无限潜力,极其相反的关于虚荣和自省的内涵,成为可以反映女性身体十分贴切的象征。”①Helena Michie.The Flesh Made Word:Female Figures and Women Bodies.P.88.沉溺于“镜”中的女性多被认为是自恋的,而孙丽坤用以审视自我的并非是有着“复制和失真”可能的“镜子”,而是灯光下的剪影。继孙丽坤为避免灵魂“赤裸”而躲进阴影之后,阴影的再次出现暗示着孙丽坤在塑造身体之美的背后,是对灵魂之美的塑造。她寻找美的意志坚定得如刀雕刻了她的自身一般。她的意志之坚,是她对找回自我的坚定的信念。面对逐渐热烈的爱情,这条冷傲的“春蛇”“舒展出了新鲜和生命”,孙丽坤对自我的无意识复萌已经转为努力的追求。这种对重塑自我的追求,体现在孙丽坤对身体之美和对舞蹈之美的追求上。
孙丽坤被动地被牢房隔离于外界,而她复萌的自我则主动地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她不再与窗外的男人们打闹调侃,重新变回“一个紧闭着窗子和又变得望尘莫及的女人”。她紧闭的内心里爱着的是这位前来搭救她的青年:“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而其实这“无法看透的手段”,就是唤起曾被她一度忘却的舞蹈﹑美丽和自我。
这条“美人蛇”的苏醒过程是沉重且暧昧的:“室内所有的布景在冬季霉潮中发出气息来。绘景前涂在帆布上的猪血渐被潮湿溶解,从尘封的历史,从忘却和遗弃的阴暗里游出腥味。徐群山和孙丽坤都唤着这股复苏的血腥,并不想追究它的来源。气味不止这些,还有温热发黏的体温的气息,以及舞蹈者的脚汗气味。这些浓浑的气味使盘环的肉体逐渐演变,化为逼真的美人蛇。”
爱情支撑着孙丽坤的自我,正如曾经的美丽和舞蹈一样。因此,当她得知即将与青年分离时,“她收住了姿态,浑身坍塌地站立着”。徐群山对她的爱慕,唤醒了她对自我的追求,而现在他即将离开,孙丽坤再次面临失去自我的危险。孙丽坤绝不愿再次失去,因此,面对徐群山告别时抬起的手,“直觉让她把自己整个肉体送上去”,她“给出去她肉铸的舞蹈者雕塑”。
“脱衣是女性展示自我的一种行为,是对身体试图做出描绘。随着语言和‘壁垒’的坍塌,揭示的是身体本身和对身体的否定;只要脱衣的行为是‘为了他’,是性爱之眼中的性爱语言的产物,完全的赤裸就不能与完全的存在联系起来。”①Helena Michie.The Flesh Made Word:Female Figures and Women Bodies,P.129.然而孙丽坤的行为,在其“性爱”的表面,潜藏的是她重拾自我、以一个完整的自我奉献爱的行为。她“没有意识到那英俊的青年其实是位女性,舞者陷入爱情中,并找回了曾经的自己”。②Carol Anne Douglas,“White snakes and secret fans:Chinese women in fiction(Book Review)”,Off Our Backs,Vol.36,2006,p.86-88.自此,孙丽坤有了自我,有了爱,她的身体不再仅仅被当作审美的对象,而是她的自我的载体。
孙丽坤重回的自我,在她决定为爱追随徐群山离开时得到真正地显露:“最后的这天下午,她照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只有十九岁。影子不像五官和脸容,会褪色。在这个灰色潮湿的冬季的下午,她要好好收拾一番自己,好好度这个末日。她在这一个月里消瘦了。她消瘦得连看守她的女娃们也不安起来,开始嘀嘀咕咕地议论,她一天天蜕变,一天天恢复原形,连她自己在看着这个完美的投影时也有些惊惧:它是她十九岁留下的投影,高高束起的发髻,与她昂起的下巴形成工整的对称。”此时,阴影的第三次出现,暗示着阴影中孙丽坤身体之美与她内心的紧密关联。阴影中,34岁的孙丽坤和19岁的孙丽坤的完全一样,意味着34岁的孙丽坤已经找回了19岁的她——那个美丽的骄傲的自我。
孙丽坤在感情中的地位,也通过她的身体姿态体现出来。面对徐群山,“她身子向前倾,两个支在膝盖上的手捧住她尖削的下巴。她把自己弄得很低,向他仰起脸。那姿态是个女奴。她上仰的小小秀丽的脑袋像一颗雌蛇的头……”她女奴般的姿态意味着她在这段感情中被俘虏﹑被拯救的地位。但她的自我和自尊不允许她放任自己的情感,她对自我的竭力保持,同样体现在她的身体姿态中:“她坐下去,却没有把分量沉下去。她两条腿强有力地控制着她的下陷。它们绷直,呈出每块肌肉的形状。”就像舞者竭力控制住自己的肌肉和身体以维持体态的平衡,孙丽坤竭力维持住她的下陷,意味着她在努力把握着自己即将崩溃的情感。而这种对自我情感的把握能力,正体现了她的自我和自尊。
四
在《白蛇》中,严歌苓通过对舞者孙丽坤身体之美变化的描写,讲述了孙丽坤丧失自我又重拾自我的心路历程。孙丽坤的身体之美是她自我意识的隐喻,因此身体之美的失去,即意味着她自我的失去。女性的身体之美多被认为是激情的,肉欲的。在小说中,孙丽坤正是因为对自己身体之美缺乏反思,导致她陷入了道德的泥淖之中。随着身体之美的失去,孙丽坤无意间也失去了曾经的支撑她骄傲的自我。徐群山的出现,唤醒了她对自我的追求。在重新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孙丽坤开始反思并重塑自我,最终得以找回那个曾经美丽而骄傲的自我。追寻过程也是孙丽坤获得更加完整,更加真实自我的过程。在整篇小说中,孙丽坤的自我意识与身体之美紧密相关。自我借身体之美表达,又通过身体之美找回,体现了身体叙事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也很好地体现了灵与肉在文学作品中的融合。
【责任编辑郑慧霞】
作者简介:郭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美国诗歌和海外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