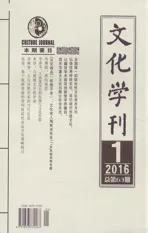孟称舜《娇红记》的三重悲剧
2016-12-23杨婧
杨 婧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文史论苑】
孟称舜《娇红记》的三重悲剧
杨 婧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娇红记》被王季思先生归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中,其悲剧性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将从心理、社会和哲理三个层面,对《娇红记》所体现的爱情悲剧、社会悲剧、人生悲剧作初步探讨。这三重悲剧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悲剧意蕴。
《娇红记》;悲剧意蕴;爱情;社会;人生
《娇红记》是明朝剧作家孟称舜(约1599-1684年)的一部沉博绝丽、独出机杼的传奇剧作,又名《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世人多有对明代传奇“十部传奇九相思”的评论,《娇红记》可谓是继《牡丹亭》之后的又一部至情之作。它摆脱了以往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窠臼,摒弃了倾心悦慕后便修成正果的大团圆结局,慷慨高歌一曲“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爱情挽歌。王季思先生将其收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其所含的悲剧意蕴颇发人深思。
一、《娇红记》内容简述
剧作讲述了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1年前后)申生和娇娘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两人一见倾心,再见钟情,经过互探试情、和诗明意,最终私定终身。情定之后,申生遣媒求婚,王父却以内兄妹不得成婚为由而拒婚。无奈之下,申生赶考应试,科举登第,使得矛盾缓和,王父授意结亲申生。两人深情缱绻之时,却突遇帅府提亲,王父改口许婚,富贵的世家豪权最终压倒了寒门士子,娇娘忧郁成疾,绝食而亡。申生痛贯心膂,不顾双亲之命,随娇娘于地下,毅然履行与娇娘“死同穴”的誓言。申生与娇娘两情相悦,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却最终在封建制度的打压下毁灭,爱情的悲剧性昭然若揭。王文瑞嫌贫爱富,攀附权要,以封建家长制的独裁,拆散申生娇娘,却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其中的社会悲剧发人深省。申生娇娘两人死后仙圆,却终究不能逃离与亲人相隔的悲剧命运,追求理想爱情却不可实现,最终酿成了人生悲剧。爱情、社会、人生这三重悲剧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悲剧意蕴,其深刻性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二、爱情悲剧
申娇二人的爱情悲剧是贯穿全剧的线索,两人至死不渝的爱情无不使读者潸然泪下。其爱情的悲剧固然离不开外部封建势力的打压,但其自身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娇娘这个人物身上散发着这个时代特有的人性光辉。王娇娘虽是封建大家庭里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小姐,但她却不拘泥于封建礼教,更不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她追求的乃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爱情。在《会娇》中,娇娘第一次见到申生,便对他的一表人才倾尽芳心,流露出“不争他显峥嵘,珠宫画廊,也不狂巧温存,锦帷绣床”[1]的感慨。这种大胆的爱情宣言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理学兴盛的时代里,是绝不允许的。但娇娘认为“古来才子佳人共携姻眷,人生大幸,无过于斯”,[2](《晚绣》)对申生更是有托付终身之愿。她“死同穴,生同舍”的爱情观更是在这个时代空谷绝响。“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3]娇娘虽抱有美好的爱情理想,并能大胆与申生暗约偷期,但娇娘的这种行为终究还是不能暴露于光天之下,既避嫌于飞红,又受制于王父。在面对其父的拒媒和反婚时,娇娘始终未能据理力争,认为婚姻大事,不是女孩子家所能说的出口的,只是坐等机会,直到希望落空,万念俱灰,卧病在床,无所为的情况下,以绝食相抗,香消玉损。娇娘至死也未能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她对婚姻大事,父母之命不敢逾越,盛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却不曾有卓文君私奔当垆的勇气。正由于缺乏这种冲破封建制度的自信与魄力,因此娇娘美好的爱情也只能在夹缝中夭折。
“一往情深”是申生爱情观的显著特点。他将婚姻与仕途并重,而不是像以往书生那样把婚姻当作其功名的牺牲品或垫脚石。申生大胆追求娇娘,一次又一次地表白自己的心意,以求得娇娘的真心。申生的爱情炽热激烈,但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他对爱情的追求又不得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封建家长制下,他不敢违背父母之意。因番兵近逼,家书遣归,不得不泪别娇娘。《求医》一出“喜番兵以去,地方安妥,欲往见小姐,未得爹娘之命,不敢遽行。”[4]申生想再会小姐,却因没征得父母同意,不得不抑制住思念,忧郁成病。对于自己的情感,申生始终未能向父母表露。甚至对遣媒一事,申生都处于被动的地位。二十一出《遣媒》中,申生得知父母要派人说媒时,不禁喜上心来,独自旁白:“如此早则喜也”,[5]甚至要感谢天意,称这是“天上青鸾应有托。”[6]谁知情路坎坷,求婚被拒。无奈之下,做出装神弄鬼,得以辟邪舅家的荒唐之举。性格带有迂腐性,对封建家长唯命是从。甚至在将要失去所爱之人的情况下,申生顾忌的也仍是:“既迫严父己命,便暂从他氏罢了。”[7]第二,以封建旧方式追求爱情。在人性复苏,张扬真情和爱情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申生追求的是一种相互平等、志同道合的爱情,但在追求理想爱情的过程中,他试图以科举高中这种旧方式来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实现自己的爱情。这种方式虽然得到王父的暂时认可,但当位高权重的帅少爷出现时,科举这一举动就显得软弱无力。申生虽能以情胜理,但却终究未能冲破封建壁垒。第三,爱情受阻,一味逃避。面对帅公子的横刀夺爱,娇娘改许他人,申生却怯懦地称,“这不足小生缘悭也”“离合悲欢,皆天所定”“今生缘分从此决矣,你去勉事新君”。[8]他完全抱着一种消极不抵抗的态度,甚至产生懊悔:“思量懊悔天公,争似当初休把两情通。”[9]面对申生的这一软弱和逃避,娇娘也忍不住厉声指责:“兄丈夫也,堂堂六尺之躯,乃不能谋一妇人。事以至此,而更委之他人,兄其忍之乎?”[10](《生离》)正是申生对父命唯唯诺诺,畏首畏尾,最终导致娇娘毁灭,爱情以悲剧落幕。
三、社会悲剧
明嘉靖以来,封建制度弊病百出,社会矛盾尖锐,而这片凋敝的封建土壤上却滋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经济在明代政权日益衰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新兴地主阶级由此不断积聚财富,但受根深蒂固的封建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财富并没有转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是重新流向土地,致使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负担加重,社会矛盾更加激烈,整个社会除了金钱上的欲望,更有权力欲求的膨胀。他们靠财势不断向官府靠拢,一些高官富户与朝廷官员结合,贪贿公行,士风败坏。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被彻底颠覆。《赴试》一出,考生对科场之路的评论一语中的(生甲云):“自来戴纱帽的,不晓文章,只晓势利。依小弟看来,势又不如利。有了利,势也有了。如今父兄要子弟做官,不消教他读书,只自家挣银子。银子挣得多,举人进士也就好世袭了”“昭文馆闭门,便长沙哭倒,谁偢谁问?凤凰池上,立着一对不识字猢狲。奶腥胎发犹尚存,说地谈天胡论文。登高弟,居要津,几曾都是读书人?才学真,到头终老做刘蕡。”[11]由此可见当时社会追名逐利之风盛行,官场腐败且都是一群无能之辈。管理制度任人唯亲,加剧了内政腐败,整个社会走向灭亡已不可阻挡。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的小官员王文瑞的命运,成了这种社会悲剧的缩影。王文瑞以表兄妹不得成婚为由,严词拒绝了白衣女婿申生,朝廷不允许只是王文瑞嫌贫爱富的一个幌子,更何况朝廷明令禁止的是同姓堂兄妹结婚,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还是“亲上加亲”之说。王文瑞的这种托辞足见其油滑。等到申生高中,前程万里,王文瑞才稍作和颜,勉强答应了这门亲事。帅府豪门出现,一方面迫于权势压迫,另一面则是受求荣求贵心理的影响。权衡之下,寒门士子科举高中已变得微不足道,“正是那帅府威福,一省中谁不畏他?况兼公子年少风流,女儿许他,也不辱没于我。”[12](《帅媾》)足见王文瑞追权逐势之心。于是棒打鸳鸯,为一己之私,攀求权贵,王文瑞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娇娘之死,直接使王文瑞的官场追求成空,不仅如此,还落得晚景凄凉,家破人亡的结局。这种悲剧结局,不仅是封建家长制的失败,也是社会世风日下的最终恶果,更是封建大厦将倾,岌岌可危的信号。
对于天生富贵的帅少爷,一门亲事作罢,重新再找一个又有何妨,可悲的是走了娇娘和申生,又有多少有情人要遭遇不幸,多少趋炎附势之人飞蛾扑火。
四、人生悲剧
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有自由发挥情感的理想和追求,却又无法超越自身和历史的特定局限。这种高雅的追求与现实中的无可奈何相互纠缠,最终形成人生苦闷的状态。为寻找人生出路,或以死相抗,或屈节变志。但“归根到底,是历史的个人性爱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屈服”。[13]理想和现实相互抵牾,妥协是他们走出这种困境的选择。申生娇娘二人惺惺相惜,不顾封建礼教,大胆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他们抛开封建礼教之大防,私定终身。但强大的封建制度始终是横在两人面前不可逾越的鸿沟,理想与现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意识到,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而炽热的情感又使他们难以割舍对方,他们深陷焦灼与矛盾的囹圄,无所适从。这时,相较于科举,死亡对于感情的解脱或许成为一种最好的方式。悲剧的时代产生悲剧的人生,申生二人的人生悲剧归根结底是因情爱自由不可得造成。
除申娇外,飞红也具有人性觉醒意识。孟称舜以娇娘、飞红之名将剧作命名为《娇红记》,足见作者是有意为之。二八侍女飞红“也知一种伤情思”,虽然身份低微,但她对申生的感情并不亚于小姐娇娘。“休道小姐爱他,便我见了,也自留情《和诗》”[14]俊书生,我为你逗真情,几次花前陪笑迎。”[15]《红搆》不仅如此,飞红还敢与小姐比肩,当娇娘指责其游春的行为时,飞红乃以”难道女人家不是人那”[16](《诟红》)相驳。当她意识到申生对娇娘一片痴心而于己无意时,她便抱着得不到则毁之的心态,故意在夫人面前提起丢鞋一事,试图揭穿两人的私情,甚至有意将夫人引入花园,使申娇二人相会被撞,直接导致申生被逐,但亲眼目睹了申娇二人爱情的不幸后,飞红慑服于封建礼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情追求,转而以一种同情的心态关照申娇二人。她以求得庇护的心理渐渐向封建制度靠拢,解放的情感重新凝聚成理性,她对娇娘感到惋惜,并开始劝说:“今帅家富贵极矣,帅官人端方峻拔,殆过申生。”[17](《芳殒》)申生、娇娘、飞红三人面对这种苦闷的人生境遇,纷纷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无法脱离封建社会的茧缚,最后都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作者在结尾处加上《仙圆》这一凤尾,有情人在仙界得以团圆,使情感上的永恒超越了肉体上的毁灭,虽弥补了现实生活中的缺憾,但人仙殊途,他们又始终摆脱不了与亲人分离的苦痛。孟称舜将美好的东西毁灭,又以这样一个诗意的结尾告诫人们:人生就是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悲剧。悲哀之余,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1][2][4][5][6][7][8][9][10][11][12][14][15][16][17]叶桂刚,王贵元.中国古代十大悲剧赏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691.699.767.788.789.928.914.914.914.881.909.717.857.835.939.
[3]司马迁.史记[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541.
[13]王季思.从《凤求凰》到《西厢记》——兼谈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中的爱情作品[J].文学遗产,1980,(1):14-26.
【责任编辑:王 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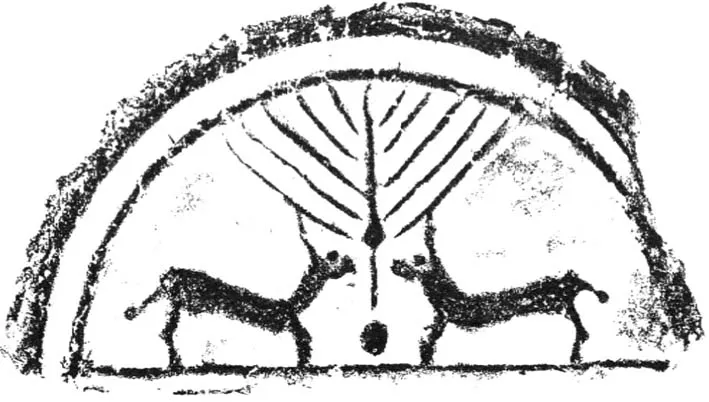
战国 树双马纹2
I207.411
A
1673-7725(2016)01-0195-04
2015-10-15
杨婧(1991-),女,山西运城人,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