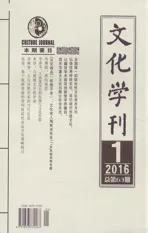记周有光先生
2016-12-23周素子
周素子
【文化视点】
记周有光先生
周素子
我于1957年夏结识周有光先生,至今58年,超过了半个世纪,将近一个花甲子。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已是漫长的了,我从青年学子到了晚年,他从壮年最有为的岁月到了111岁。但在近六十年的岁月中,我们甚少居住在同一个城市,而且都是相距甚远的,可是人生就有这样的奇迹,不论相隔多远,我们始终彼此关怀,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后。只要彼此有著作问世,就互相寄赠。1995年后,我移居海外,在不多的中文藏书中,竟有周有光夫妇相赠的若干本书,扉页上都有亲笔签名,爱称我这个比他年少三十多岁的后辈为“姐”。

图一 赠书题字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随陈朗发配到西北甘肃边境,一去二十载,“生还玉门关”后,又只许陈朗一人返京,我们流落江南。上世纪80年代后全家陆续又移居岛国,至今已是又一个二十载。
有许多的“共同”,将我们联络在一起,息息相关,彼此关怀,理念的共同,使我们对周先生的前卫思想顶礼不已,将他看成指路的明灯,有疑难,有追求,都想获得他的认可,方才安心。他的智慧识见并不因年老而背晦,他的渊博,真知灼见在世少有,这是我的看法。
2005年,我有幸任新西兰汉学会会长,我立刻想到要请周有光先生为本会顾问,有他的顾问我才不会偏离方向,我才会步步走稳,我在聘任书上如此写:“周有光先生博学多闻,著作等身,先生于文字学,经济学等范畴的研究卓有成就。对汉学有杰出贡献。先生作为本会顾问,是本会最大荣幸。纽西兰汉学会,在先生指导下,将更有利于汉学的深入研究与宏扬,兹聘请周有光先生为纽西兰汉学会顾问。”

图二 聘请周有光先生为
我随信寄去一些照片包括新西兰的大自然风光,另外,我还随信寄出数份我们创办于1996年的中文报刊《新报》。
先生收信后很快为我寄来了复信,信写得活力四射,毫无老态,(周先生2005年12月25日来信如下:)
朗兄、素子姐:
2005年圣诞节前三天,我家关起大门,准备午睡。忽然门铃响,邮差送来你们“双十二”发出的大邮包。打开细看,有热情的书信,有优美的照片,有开朗的报刊,使我喜出望外!特别感谢你们给我荣誉,邀请我当汉学会的顾问。谢谢!谢谢!
你们是尘世不俗的仙侣,被中原浊浪冲出人寰,遨游于茫茫仙岛,居然落地生根,蔚然成林。真是,天涯何处无桃园!
允和生前出版物有《最后的闺秀》《张家旧事》《多情人不老》等;生后遗稿已经出版的有《浪花集》《昆曲日记》。这里寄上她的《浪花集》和我的《百岁新稿》,请指正。
不久前,上海复旦大学纪念建校100周年,其中一个项目是纪念九位健在的百岁老教授,最老的107岁,我是其中的小弟弟。今年春天,教育部举行座谈会,纪念我100岁。我糊里糊涂活到今天,真是蹉跎岁月!
中国正在演变中,这两天的香港新闻,你们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多。
敬祝
新年快乐!
周有光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五

图三 与周有光先生来往信件
2008年,我的《右派情踪》一书在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余英时先生为我写了序言,我深感荣幸。2010年我的《老家的回忆》再由田园书屋出版,即使先生年事已高,我还是恳请周先生为我作序,蒙先生不弃,慨然承诺,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现转录于此地,与大家分享,他还为我相请张充和女士为我的书题签,这本书,有先生序文,充和女士题签,以及我哥周昌穀为我作的画像作为封面装饰,这些都比我的文字本身珍贵多多。

图四 《老家的回忆》封面
现附上周有光先生为我作的序文:
海燕其归来乎?
——序周素子《老家的回忆》
几年前,素姐自奥克兰致函邀任我为其“纽西兰汉学会”荣誉顾问,使我深感荣幸,曾向她表示谢忱。今复以其所著《老家的回忆》书稿征序于我,更因感荣幸而义不容辞。
我与素子伉俪相交已有半个世纪,初见素子时,她还是个大学生,当允和等在俞平伯先生出面组织北京昆曲研习社期间,彼此夤缘而相识。二人当时还不是曲社的正式社员,未像允和那样的“投入”,像我一样只是曲社的“边缘”人,后二人离京,中间隔断有20年之久,他们长期处于颠沛流离中。朗兄原是京城“戏剧圈”中人,曾任《戏剧报》编辑,允和所作记叙昆曲“全福班”的《奇妙的江湖船队》,首先是他拿去发表于他所执编的《戏剧论丛》上,这是“文革”后他返京“复职”时。但只要他俩在京期间,则为我家的“常客”,堪称“莫逆”。但命运使他们远遣他乡,我们不相闻问的时日漫长。素子作为她个人,她的经历更为艰难。难处存言,本书是也。作为回忆,自叙平生,不曾出于凄楚之情,相反,却是一片美好,具有人性的至善至美。虽则零章断篇,却如昆曲的每支曲,其间离合之情,风云际会,也是一本“传奇”,也是一种“奇妙”。
处于20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子,无不经受严重的考验,经受到精神与肉体的磨炼。1957年,素子这个大学未毕业学生也不例外。朗兄也是个不谙“世事”的书生,虽比她大十岁,自身不保,焉能保护她?不像二姐允和,尚叨身为家属身份,以之“安身立命”。素子先随朗兄播迁塞外,当朗兄被投入遐荒,她随即被遣出兰州市,挈带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先而踯躅于古秦川道上,再而流徙到江南农村,与朗兄被迫劳燕分飞。我们的宗先辈北宋词人自称“憔悴江南倦客”的钱塘周邦彦,在其《满庭芳》词中有句云:“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素子一天也没从过政,但她确也到过瀚海之边(见书中《户口的故事》《西域探夫记》等篇),最后于杭州近郊的村店当“伙计”,以不“憔悴”之身谋生,然不忘读书,钻研学问,苦心孤诣,追求不懈,艰辛地抚养女儿成长。这只生命“小舟”竟不破不灭。等到“落实政策”“改正”,已到中年,然犹壮心未泯。过去为学生时,学的是洋乐,走的是“白专道路”,然二十年来虽挣扎于社会底层,学业早经荒疏,幸赖有家学并自学的根柢,于是能胜任大专的汉语教师并杂志编辑。其间还以“业余”身份受聘于首都“昆曲艺术研究学会”的副秘书长,以遂年轻时即热爱而欲拯挽的正声之失坠,为之尽绵力之心,又投身徽学、民居学的研究,深入古徽州若干次,走访全国传统民居百十次,因从事风景名胜事业,走遍了名山大川,处处留有足迹。如今身居海外,犹从事华文报刊的文事,并致力“汉学会”事业,系情于故国未止。
书称“老家”,实包涵故园、故国之意。举凡家人父子,亲友故交,师长前辈,并向之所接的村民船户,卖浆者流,山川草木,无不在追忆之中。结念之深,给人以“归来”之感。前些年,我曾给素子伉俪的复信中说过:“你们是尘世不容的仙侣,被中原的浊浪冲出人寰,遨游於茫茫神空,降落於海外仙岛,居然落地生根,蔚然成林。真是,天涯何处无桃园!”这几句话,今天有新的诠释:浊浪若非久长,大禹的子孙终能学治水,顺从世界的潮流,趋於完善。桑梓之地,人文渊薮,故园何尝非桃园,布帆无恙,生命之舟犹能旋,海燕其归来乎?
在这里,还必须一提允和等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先生之间的“不须曲”故事。1968年,充和在哈佛大学演出昆曲《思凡》和《游园惊梦》,余先生观后曾感赋一绝,后二句云“不须更写还乡曲,故国如今无此音”。盖当时大陆“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也。相隔十年,此诗经充和寄与在大陆的允和,当时充和未提作者名,只说“有人”,得到允和并北京昆曲曲社诸友的相和,允和和了二首,其第一首第二句为“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盖允和正于是年春在南京观看了由江苏昆剧院演出的《牡丹亭》之后,因诸和诗均用了“不须”两字,故充和称之为“不须曲”。后来当然得知首唱者即是余英时先生,且于该年11月在北京机场,允和同我与余先生有了一面之缘。此一事,直至大前年2006年,余先生为我的《百岁口述》一书作序,竟将之作为序题《不须曲的故事》,于序文中作了回顾,且谓“无巧不成书”,说“2006年5月忽收到纽西兰周素子女士的一封信,附有她最近写的《记当代才女张允和女士》一篇文稿,文稿记述‘不须曲’发生前后过程,籍以证明1978年春天《牡丹亭》在南京演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是‘不须曲’的缘起及其具体的语境和事境”。因而认为:“‘不须曲’的唱和发生在太平洋两岸极小的文化社群之间,既不为局外人所知,更谈不上什么影响。然而作为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件,它未尝没有一点发人深思的启示。时隔十年,地去万里,唱者和者初互不相识,却在顷刻之间共跻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世界,这似乎显示: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确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永恒的人性,没有任何强大的外力能把它长期压下去。”于是余先生将这则“文字因缘”作为他为我书所作序文的“曲终雅奏”。我今援此“不须曲”这段小小的文事,将我与余先生、素子又融合其中,真是“无巧不成书”。今为素子书作序,亦正处于太平洋两岸,地去万里,时隔十年或更十年、二十年,而彼此心迹相同,亦将之作为我写序文的“雅奏”。
周有光
二零零九年元月
他在序文中提及我和余英时先生,与他本人张二姐之间的一段“正处于太平洋两岸,地去万里,时隔十年或更十年、二十年而彼此心迹相同的小小文化事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世界一事。在此说明以与读者分享,数十年前,我国正处风雨如磐的上世纪60年代,余英时先生在美国观看张充和的昆曲表演后,写了一首七律寄充和,诗曰“一曲思凡百感生,京华旧梦已沉沉,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无此音”,文革结束后,充和才敢将此诗寄给国内的二姐允和。1982年,南京昆曲院首次恢复公演牡丹亭,允和二姐特从北京奔赴南京观剧,她写了一首七律和余英时先生:“十载连天霜雪侵,回春箫鼓起消沉,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当时北京一大批老先生都纷纷奉和余英时先生,当充和将一卷和诗交给余英时先生时,使他“受宠若惊”,因诗中均有“不须”二字,故这些均称“不须曲”。2008年香港田园书屋因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祭,出版了我的《右派情踪》,我恳请余英时先生为我作序文,在去信中我寄了我写的《记当代才女张允和女士》一文,并附了一首“不须曲”,诗曰:“感念平生百事侵,人琴消息几低沉,不须惆怅阳春曲,犹盼高云赐好音。”余先生收信读我诗后,很快为我的书写了序言,他说,我的《记现代才女张允和女士》一文和他唱和《不须曲》的往事,引起了他的一点回忆,即关于允和在1968年在哈佛大学演出《思凡》和《游园惊梦》,那时大陆还正是“文革”进行的如火如荼时,这使他很感慨,故写下了那首“不须曲”。“文革”结束,充和才敢把这首诗和海外相关唱和诸诗寄给二姐,1977年秋充和才交给余先生一叠诗稿,是大陆不少人和他的原作,且墨迹出自许姬传先生之手,琳琅满目,使他受宠若惊,所以当他读到我的《记当代才女》后,才确知和诗的写作年月为1978年春,我的这首“不须曲”使他回忆往事,是值得珍惜的文字因缘,他说我“委婉陈词”,才以短文以报其诚”。
又若干年后,余英时先生撰文将这段“不须曲”文字因缘发表于《南方周末》,美国友人为我寄来该期报纸,使我备受感动。文中将我、周有光、张允和、张充和与他本人之间这段文字因缘说正处于太平洋两岸,地去万里,时隔十年或更十年,二十年,而彼此心迹相同的小小文化事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世界。素子何幸竟能混迹在诸大家之间,成就小小的文化事件,幸矣!足矣!
2000年我曾返国,陪我多年挚友,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赴京专谒周先生,因周先生曾任教杭州大众教育学院,为丰富地方文献,图书馆为留存周先生著作目录,而专访。那时二姐尚健在,我们摄影留念。
2011年2月,我再次返国,仍与褚树青同赴北京拜谒周先生,周先生虽105岁,但仍头脑清晰,识见前卫。我们请教了许多问题,事后我写成“周有光访谈录”,因篇幅过长不能转录于此,他的真知灼见、忧国忧民和乐观精神,永远激励我们。
现在,先生即将进入111岁,能如此长寿,只有秉承庄子的达生、达观,方能呈现,而庄子是蝴蝶的化身,周先生是一只不老的玉蝴蝶,蘧蘧然是蝴蝶?是周先生?
戏作一首“不须曲”,以为此文之殿:
四姐思凡二姐梦,隔海原本是一俦。
人天同爱不须曲,相看百岁同白头。
【责任编辑:刘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