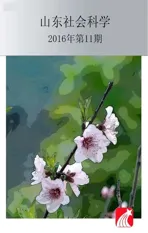小说信仰:皈依阅读、计算建模及现代小说①——特奥多尔·冯塔纳《混乱与迷惘》
2016-12-20加拿大安德鲁派博撰陈先梅译
[加拿大]安德鲁·派博撰 陈先梅译
(麦克吉尔大学,加拿大 蒙特利尔 H1K 2E3)
小说信仰:皈依阅读、计算建模及现代小说①
——特奥多尔·冯塔纳《混乱与迷惘》
[加拿大]安德鲁·派博撰 陈先梅译
(麦克吉尔大学,加拿大 蒙特利尔 H1K 2E3)
“最终,我们其实总是要掉转方向。”
我们在翻动一部小说的书页的同时也被其翻动,这意味着什么?在小说的指示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双重指引下,我们是如何不仅被简单地感动,而是被改造——被扭转?换言之,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的小说在深刻的个人层面上能够对我们具有意义,我们应该如何据此来思考小说所使用的技巧和修辞之间的关系。
小说的历史,正如汉斯·布卢门贝格(Hans Blumenberg)所言,常被理解为一种扩大化的表决,针对的则是柏拉图所持的诗人说谎的观点。*Hans Blumenberg, “Wirklichkeitsbegriff und Möglichkeit des Romans,” Nachahmung und Illusion, Hg. Hans Robert Jauss (München: Fink, 1969) 9-27. 1 Hans Blumenberg, “Wirklichkeitsbegriff und Möglichkeit des Romans,” Nachahmung und Illusion, Hg. Hans Robert Jauss (München: Fink, 1969),p 9-27.小说的各种主要研究方法——从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论(mimesis)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真实效果(reality effect),再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以及其他理论——无一例外始于小说对陌生化现实的表现:这种表现被视为小说首要的内在特征。*托马斯·帕维尔在他关于小说史的文章中有很好的总结:“通过在角色与他们身处的环境之间强加一个裂口,小说成为第一个反思个人的起源以及公共道德的建立问题的文学类别。” Thomas Pavel, “The Novel in Search of Itself: A Historical Morphology,” The Novel, vol. 2, ed. Franco Moretti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6) 3。还可参见一些小说家新近的意见——他们强调小说的现实主义诉求。这些小说家包括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 “Why bother?” How To Be Alone: Essays, New York: Picador, 2002)和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The Na”ïve and Sentimental Novelist, New York: Vintage, 2011)。在小说里,我们体会到疏离,从而感知我们对社会化世界合宜的政治或批评方向。但是,更近的研究开始强调我们与小说阅读之间的情感关系。*参见 Deidre Shauna Lynch, Loving Literature: A Cultural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Rita Felski, “Enchantment,” The Uses of Litera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8) 51-76、Helen Deutsch, Loving Dr. John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和 Rüdiger Campe, Affekt und Ausdruck. Zur Umwandlung der literarischen Rede im 17. und 18. Jahrundert (Tübingen: Niemeyer, 1990)。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写道:“我们解释喜爱之谜的方式是着眼于隐藏的确定性及社会兴趣,却很少注意到文本可能引发我们的好感,讨好我们的感情,满足我们的迷恋的方式。”*Rita Felski, “Context Stinks,” New Literary History, 42 (2011): 573-591; 582.小说还是非常有效的载体,引发个人喜爱,而不是仅表达社会疏离。从这一点来说,小说的历史不应被视为是研究已知性(das Gegebene),即卢卡奇(Georg Lukacs)所谓“世界之立即的不可打碎的已知性”。*Georg Lukacs, Die Theorie des Romans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4) 51.它还意味着我们对小说在可被我们称作投入性(或Ergebenheit)——即其让我们投入其中的方式——方面的表现历史的理解。在此意义上,小说变成了一种可以让我们体验到深刻内在差异的文学类别——并非疏离于世界(卢卡奇所称的一种原始的思乡病[Heimweh]),而是一种与某个世界之间已完成的认同体验。这种关于小说的皈依力量的历史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在探究计算模型的发展,以求了解小说与深层次转变叙事的关系是如何引发个人的情感依附的,也就是小说表现以及让我们投入感情的方式。我也曾问过我自己及其他相同研究领域的同仁:小说是否有什么内在的特质使得我们如此投入。如果有的话,是否跟它内部较大的语言流有关——不是某一个单一的行、段,或角色,也不是诸如“文体”之类——而是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较大的语言转变所能引起的情感状态,例如忠诚、信念或信仰?换句话说,语言转变可以成为令读者投入的有效载体吗?
从其历史渊源来说,思考文本的改造性力量当然是有浓浓的奥古斯丁式意味。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被认为是在叙事技巧、抄本技术及个人皈依之间建立连接的奠基之作——形式和媒质互相作用以产生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关于奥古斯丁与书籍的关系,参见Andrew Piper, “Take it and read,” Book Was There: Reading in Electronic Ti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根据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和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等理论家的说法,在更基本的连续性叙事结构中,叙事的目的是表现事件之间的因果序连关系(首先如此,接着如此如此)。*关于叙事与因果之间的关系,参见Gé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Ithaca: Cornell UP, 1980) 26, and Tzvetan Todorov, Introduction to Poetic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P, 1981) 41。皈依说则与此不同:在它引入的结构中,叙事具有一种明显的先后特征,但这仅仅是因为时间上的差异感。*关于奥古斯丁式皈依,参见 Dong Young Kim,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Conversion: The Case of Saint Augustine (Eugene, Oreg.: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2).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皈依叙述就违背了格雷马斯关于叙事均衡是一切叙事的基础的理论。参见A.J. Greimas, “Narrative Grammar,” MLN 86 (1971): 793-806. 关于叙述的功能在于标记差异的观点,参见Tzvetan Todorov, Genres in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30. 据此皈依将被理解为叙事的极端化,而非叙事的消解。据一种奥古斯丁式的皈依理论,生命不再被理解为由一连串有限的、一件接着另一件的事件组成,而是被视为一个整体,以某一个转折为特点,这个转折点既是离开(从原来的自我出发),也是回归(到真正的自我)。决裂不仅是回归的媒介,是“皈依”(conversio)的“皈”(con-),也是信仰和承诺的媒介,是要朝着一个终点的转折。文本强烈的二元形式,即其先后特征,是奥古斯丁设计的让主角和读者双方产生某种信仰姿态的方式。
我在这些问题上所做研究的最初定位是探讨奥古斯丁对卢梭以后的现代自传体的影响。我很想知道,在现代日益商业化的传记写作环境中,这种自白的原型还剩下多少痕迹?尽管文学学者们为卢梭的《忏悔录》之后奥古斯丁对现代自传体还有多大影响争论不休,我们还未超出几个经常探讨的作品范围,还未将这一问题置于更广泛的作品范围内来考察,也未在更广的语言学范畴内探讨过影响的概念——我们仅仅讨论过少数精选的文本相似性案例。再者,我们也未曾探寻奥古斯丁式皈依还有没有别的源泉。然而,让我惊讶的是,我在建的模型揭示:奥古斯丁式皈依并非主要依赖自传体裁——在这方面更多只是名义上的——而是主要依赖于小说体裁。看起来,小说才是19世纪以来读者们为获取这种不断的“掉转”(“turning around”)体验而作出的选择。我所说的“掉转”指的是语言学上先前和然后的鲜明的对比,以及伴随的一种强烈的投入感——将自己与某种事物融为一体(com-mitto)之感。
这种观点与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学说对比强烈:后者认为小说身为媒介,它的定性是规范化、中庸,以及平凡。用弗兰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话说,小说就是“资产阶级生活的规范化”*Franco Moretti, The Bourgeois: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London: Verso, 2013) 81. 关于小说和平庸的问题,参见Paul Fleming, Exemplarity and Mediocrity: The Art of the Average from Bourgeois Tragedy to Re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9)。的一面镜子。相反地,小说(以及这种体裁中的某个次范畴)在19世纪即以一种极不规范的形式出现,其标志便是明显的二元性以及语言变化。在莫雷蒂提出“小说的节奏充满了理性化的逻辑”的同时(同书82页),我的模型显示起作用的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节奏。19世纪小说远非要让读者适应现代生活的繁重不堪与一成不变——即文本上的韦伯式理性化。相反,它看上去更专注于让深层次的语言转变得以实现,从而为个人参与感奠定基础。此类转变刚好发生于小说被体制化为民族之声和深刻教导工具的时间框架之内,这在此种情境下也是合乎情理的。小说具有使我们疏离于世界已知性的批判性力量,也有让我们接受超理性化的现代性的能力,但我们不应将这两点视为其历久不衰的合理性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看到小说的这类情感维度使之变成了一种有效的体制化媒介,使之能够在爱国和教化这两种背景下都能被成功利用。
此项目因而着眼于追溯某一特定的、可以作为引发读者投入的重要载体的奥古斯丁式叙事转变模型的谱系。*大量对皈依的研究都将之视为主要是一种宗教现象。要了解皈依研究领域的概况,参见Karl Frederick Morrison, Understanding Conversion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P, 1992) and Lewis R. Rambo,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Conversion (New Haven: Yale UP, 1993). 要了解最近在更广泛的文化范畴和心理学范畴对皈依进行的思考工作,参见Matthew William Maguire, The Conversion of Imagination: From Pascal through Rousseau to Tocquevil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06) and Dana Anderson, Identity's Strategy: Rhetorical Selves in Conversio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7)。它假定也许有别的方式思考奥古斯丁与叙事的关系,或者叙事与皈依的关系。对我的目的至关重要的不是对某单一对象的多种模型展示,这一对象指的是我们可以思考如何捕捉奥古斯丁式皈依这一复杂现象,或者就是广义上的皈依的多种方式——它们即使不比奥古斯丁式的皈依可靠,但是却能起到补充的作用。我的目的是去理解某一特定的文本模型是怎样历经时间的洗礼,且在此过程中获得新的意义和社会目的。研究某种特定的、历时的皈依模型就是研究连续性内的差异性以及差异性内的连续性,这是对历史谱系性理解的基础。*关于尼采式的将历史视为谱系学的研究,参见Michel Foucault, “Nieztsche, Genealogy, History,”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P, 1977) 139-164. 关于情感和文学史跨时间段模型之间的关系,参见Rita Felski, “Enchantment” 51-76.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写道:“它必须对[事件的]再现敏感,不是意图画出其进化的曲线,而是要分离出它扮演不同角色时的不同场景。”*Michel Foucault, “Nieztsche, Genealogy, History” 140.
以这种方式思考皈依,且坚持认为即使在面对世俗文学体裁时我们仍然是在谈论某种形式的皈依,使得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概念变化以及文化过程,其实就是将文化理解为一个谱系性过程。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寻找一个字面上鲜明的叫作宗教皈依的种类,不如说是试图发现细微的语义和叙述上的循环建构。这种结构已经不再是它原始的意思,而是在新的使用目的环境下,获得了新的形式和地位。这样寻找文化残留就是将文化理解为被历史掩埋的形式重新开始起作用了。
以这种方式来研究小说的历史问题,让我们可以全局理解这一文学体裁,最终提出一段历史时间之内各种文类成型之前的作品、新文类形式之间的混杂,以及新文类的功能。我们同时也能洞察小说体裁内部的类属,以不同于我们已接受的批评叙事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归类。写给儿童的成长小说、讲星际逃离的科幻小说、双重婚姻情节、卡夫卡的不可能完成的求索——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典型地体现了奥古斯丁的叙事皈依模式的小说。但是这些小说通常都不会被归到一类,在课程表上也不会被放到一起。计算机阅读将一些我们不曾注意到的小说之间的相似性呈现出来。这种相似性有赖于大规模的语言转换。这在过去我们的批判阅读模式中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可能对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阅读体验非常重要。
我们将看到,量化特征的统一性为探究现代小说的皈依问题——即何为在阅读中被扭转——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语义学和形式方法支持。量化模型为主题多样化提供了语言学基础。就我们传统的文本归类的方法而言,这些小说也许大相径庭。但是每一部小说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结果为深度转换这一问题提供了参照。因此,计算机阅读为我们思考“皈依”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既在较大的结构模式方面,也包括它所带来的多样化的体验方面。综合起来,这些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后奥古斯丁式的皈依阅读的基本分类,将告诉我们什么才使读者被感动。这不是一张模板,而是颜色丰富的画布,包含了多种刺激个人转变的方式,同时还包含着读者投入感,即小说让读者沉浸其中的不同方式。
在调查转变式的阅读历史时,本项目还有一种对支撑今天阅读行为媒介的当代转型的自觉。我的目的是开启早应出现的对计算机模型的思考过程——将之视为一种调节我们与文本之间关系的假想结构的构建过程——并对这些模型本身何以具有循环和转化性质进行考察。*关于科学建模的文献非常多,但是仍应被视为今后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参考。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性著作,参见Mary S. Morgan and Margaret Morrison, eds., Models as Mediators: Perspectives o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Roman Frigg, “Models and Fiction,” Synthese 172.2 (2010): 251-268; and Matthew C. Hunter, “Experiment, Theory, Representation: Robery Hooke’s Material Models,” Beyond Mimesis and Nominalism: Representation in Art and Science, eds. Roman Frigg and Matthew Hunter (Berlin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0) 97-138。一个模型的应用始于这样的假设,即语言及其意义的量化维度之间并非等同的关系。在有些情况下也许可以合理假设单个的词或短语可以代表它们所指的那个事物(如地名之于“地方”,日期之于“时间”)。在其他情况下,比如“皈依”,在指称和意义之间我们就需要一种介质。为了解决模型的这个问题,我会在“细读”与“远读”之间游移,结合这两种方法而不是将它们对立(见图1)。我要识别的是模型化和意义生成之间的往复过程,这是由于“细读”和“远读”的相互作用方式是螺旋式的,接近于某一分析目标(在此即“皈依小说”),但它们的分析目标不会完全一致。

图1 计算解释学。此表显示了计算机阅读的不同阶段以及每一阶段所需要进行的操作。传统的“细读”法(close reading)包含第一个阶段“相信”(belief)。当下对“远读”(distant reading)的理解则将我们带往“量度”(measurement)。这一模型要求处理过程以振荡的方式持续,在细读与远读之间游移,以求接近想象中的概念中心。初始样本(这里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选择和理解都以更大的类别(这里指“小说”)为参照。根据模型找到的具有显著量化意义的新文本样本也同样如此(即sample 2[“样本2”])。“样本2”还受其所来自的更大的样本影响(即“整体”,这里指我选取的、包含450篇小说的子集,用以作为“小说”的代表)。阐释“样本2”的过程既是一个实证过程(模型是否有效?),也是一个完善过程(我们还可以用其他何种方式来理解并进而量度这组文本?)。总体的过程呈螺旋状,不会回到初始样本,而是逐渐地,尽管并不完全地,聚合于一个想象的类别中心
下一节,我会从计算机模型的建立入手。模型本身基于对某一特定文本模式(奥古斯丁)的理解。接着,我会描述模型的应用:方法是对450部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的德语、法语及英语小说和150部同时期的德语自传文本进行比较。这些文本共计包含60,094,905个单词。*数据集的完整清单参见: http://txtlab.org/?page_id=369我在这一节的目的是了解这些来源广泛的叙事体裁在何种程度上呈现出与奥古斯丁式模型相关的不同趋势。自传与小说在各自叙事过程中与语言的二元分布、与对皈依前后的戏剧化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显著的不同吗?在第三节里,我将通过“验证”模型来得出结论。这是计算机研究的传统步骤,其中包含对小说特征明显的特定小说子集进行仔细分析,以求确认模型是否捕捉到了我认为自己在寻找的东西的性质。这些小说是“皈依性”的吗?如果是,那何以如此?
我将提出,“验证”一词在这里不应理解为计算机科学意义上的建立某种形式的“基础事实”,不是模型有效性的证据,而是某种形式上在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发现。由于模型提供了一个能让文本获得新意义的阐释视野,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此模型识别的文本子集。此外,通过详细地分析模型识别的文本,我们对这一计算模型本身的深入了解也不断增多。“细读”不能作为证实——另一尺度上的重复计算——的工具,也不能被当作是反对的方法,用以说明计算是会有所疏漏的。相反,它本身就被理解为一种模型建构,内嵌于一个更大尺度的循环发现过程之中,这一循环过程的目的在于祛除计算之后的猜测范围(这些大规模结果向我们透露了特定文本的哪些信息?),也在于祛除细读之前的猜测范围(某个文本样本想当然地所具有的可以完美代替一个想象的、从未具体化的整体的能力)。远读之后的细读只是进一步进行远读和细读的开端。
我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向“要么/或者”阵营提出一种方法论上的挑战。这些阵营认为我们必须在细读和远读中二选其一,必须在浅读和深读中二选其一。这种态度今天在我们的批判话语内部已经流播开来。我希望我们能认识到,在试图构建适用于一定规模的文学论题时,在这几种极端的方法论之间选择其中一种往返回复,而不是只选择其中一种,这是怎样地不可避免(尽管何时发生这种方法论上变化的时间尚不清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尤其想让我们看到:定性的和定量的分析有必要合二为一。正如我将展示的,这种整合基本上是循环的,因而带有解释学的性质。当我们从少量的文本样本转向更多、更有代表性的文本样本,然后再回到少量但此时已产生关键性差异的文本样本时,这种循环能够带来新的知识、新的洞见。它将一种皈依式阅读付诸实践。其目的(telos)不是一个单一的、极端化的洞见,而是一个重复性的、循环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作为概念转换的载体。正如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言,朝圣之行的循环特点大体上总是呈椭圆形。*Edith Turner and Victor Turner,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8).我们回来的路和出发时不同。这就是计算机阅读的皈依本质(conversional nature)。
我认为,在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这一皈依过程的核心)之间移动的过程中,我们将越来越清晰地发现一种批判疏离(critical estrangement)也在起作用。这种疏离与书目附录或“怀疑解释学”不同,后二者长期以来伴随着我们与文本之间的职业和私人关系。*Rita Felski, “Suspicious Minds.”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我们在对文本分析的过程中产生了与文本的关系,我们需要对此作出解释,这与对我们文本产生的直接的情感和怀疑的解释同等重要(这是因为,模型在解释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准主体[quasi-subject])。我怀疑:阅读的革命——即奥古斯丁所展示的、与书本这一介质紧密相关的顿悟式洞察,将不可避免地被阅读的解析所取代。所谓阅读解析,就是一种重复性的计算过程。我们通过它无限接近某个文本组成的整体——无论是以细读还是远读的方式。这个过程永无终结。计算环境对文本的引入和转译可以产生出新的和未曾料想到的文本分类想象方式,也可以产生出那些我们极为熟悉的方式——它们的奇异性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如此的寻常可见。这就是我所谓的计算机阅读的“奇特解释学”(strange hermeneutics)。我们并非用计算机揭示了秘密——更多时候是要么想不明白量化事实的意义,要么因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新东西而变得厌倦。对这一奇特和寻常的混合物的思考将成为我们在学术机构内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学术机构已经越来越需要一个以“新知识”和“可重复的知识”为必要前提的科学体系。然而,这也将向一个职业立场发出挑战。这一立场往往未能将其未明示的、却深深感受到的依恋投入书本之中,因而逼迫我们重新思考读者式投入的技术条件——既包括过去的也包括现在的。
模型建构(远读)
此模式以一种信念开始。读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以后,我感到皈依这一经历需要不同的语体来捕捉皈依前后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皈依所带来的新生活需要一套新的词汇,或一种基于现有词汇的强度变化。根据我在生平叙事(life narratives)的历史语境中对奥古斯丁进行的阅读,语言和形式密切相关。
为了验证这种信念, 我使用了在思考文档间大规模关系时最普遍使用的技巧之一——向量空间模型(vector-space model)。这种方法将文本表现为多维度客体,每一维度对应于文档内某词的出现频率。向量空间模型不把文本看作句子的线性排列,也不把句子看作词语的线性排列。相反,这种模型认为文本是由词语的相对重复所定义的,继而利用这些数值来对文本进行空间定位。根据这种观点,文本含义就是语言重复的一种功能。*如需更全面地了解这种思考文本的方式,参见Andrew Piper, “Reading’s Refrain: From Bibliography to Topology,” ELH. 80.2 Special Issue on “Reading.” Ed. Joseph Slaughter (Summer 2013): 373-399。假如我们只考虑某一词乃至某两个词,这种模型将不可避免地显得琐细和过于简化,因为我们牺牲了许多关于这些词语的上下文提供的信息(即文本的大部分内容)。然而,当我们开始思考上百个词,甚至成千上万的词的时候,我们对文本的语言布置方式的理解就会复杂得多。这就是计算解释学(computational hermeneutics)的第一法则:简化是在较大尺度上理解复杂性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不应把这点视作失去语言的结构体维度——即一个词的含义的一部分是它的句法上下文的功能——的方式,而是应当把向量空间模型看作重建一种新句法的途径——只不过是在贯穿整部著作这一更大尺度上的句法。一个词的上下文不再指那些与之紧邻、发生了句法变形的词,而是指整部著作中发生了量化变形的那些词。这种模型能将让更多文档中只基于人力就无法处理的大量语言变得彼此相关,以至于文本间的空间联系变得近似于语言学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互文性的传统模型要么适用于仅仅几个基于语言上的复杂联系的文本,要么适用于大量基于非常简单的联系——比如某一引用或关键词——的文本。向量空间模型则可以在大量文本间建立基于大量词汇的联系。对这些模型适用或偏离互文性文学理论历史的程度的理解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而且急需进一步的研究。两个文本相似的词语越多,这些词语的频率(即它们的“坐标”)越相近,它们在这种多维度文本空间中就会更接近。
为了验证《忏悔录》是否真的具有组成部分之间的大规模语言转换这一特征,我首先将整本书分为不同章节(奥古斯丁将之称为“卷”[book]],然后建立一个章节间关系的向量空间模型。*这一过程通过使用R中的TM包来完成。我去掉了无用功能词(stopwords,指在自然语言中出现频率非常高,但是对文章或页面的意义没有实质影响的那类词,因而在处理自然语言数据之前或之后被过滤的字或词。如英文中的“the”“and”“of” 等,中文中的“的”“也”“啊”等——译者注),用欧式距离测量法。更多信息参看Ingo Feinerer and Kurt Hornik, “tm: Text Mining Package. R package version 0.5-9.1 (2013): http://CRAN.R-project.org/package=tm and Ingo Feinerer, Kurt Hornik, and David Meyer, “Text Mining Infrastructure in R,”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25.5 (2008): 1-54。你们在下面看到的这个图表中,它用多维尺度(MDS)再现了《忏悔录》的13卷相互之间的词汇相似性(见图2)。多维尺度(MDS)类似于主要成分分析法,它尝试将多维数据的维度尽可能减少(在这里是减少到两个),同时保留数据内部尽可能多的信息。*关于多维尺度(MDS)的介绍,参见Ingwer Borg, Patrick J.F. Groenen, and Patrick Mair, Applied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Berlin: Springer 2013)。两个章节具有相似频率的词越多,它们在图上就更接近。那些相近的文本共同拥有这种大尺度的句法——我们可能将之称之为“话语”,因为找不到更恰当的名称。“话语”指的是对某一特殊类型或子集的语言的反复使用,即福柯所谓“规则性场域”(field of regularity)。*Michel Foucault, The Archea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55. 这些计算方法向文学分析语言的转化本身就是个难题,有待进一步探索。这些语言的多维配置的本性如何,以及它们怎样与我们现有的分析框架相关,都有许多尚需要理解的地方。

图2 奥古斯丁《忏悔录》,总共13卷。此图使用多维尺度,表现了奥古斯丁《忏悔录》的13卷之间的语言相似性。两卷彼此越靠近,就越倾向于以相似的强度共同使用一种语言
此图使我注意到两个特征,我随后将它们加入了我的模型。第一是《忏悔录》中奥古斯丁本人皈依前与皈依后文本间的距离。奥古斯丁的皈依发生在第8卷的末尾。我们可以看到1-10卷的聚类与11-13卷的聚类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我很清楚关于奥古斯丁作品完整性的争议,尤其是关于10-13卷是应该被当作对皈依前诸卷的“补充”,还是全书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关于《忏悔录》统一性的关键不确定性恰恰反映了属于皈依叙事并由多维模型测量得出的语义发散性和多样性。对于我的目标而言更重要的是,这本著作在历史上从来都是被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读者的。正如詹姆斯·奥唐奈在他对此书全面的评论中写道:“没有证据表明这部著作曾以我们所见形式以外的形式流通过。”参见James O’Donnell, The Confessions of Augustine: An Electronic Edition(1992): http://www.stoa.org/hippo/comm.html. 因此,考虑到手抄和印刷这两种复制方式,《忏悔录》的复制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整体进行的,也因此一直以来就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关于《忏悔录》文本的完整性的争论,可特别参考J.J. O'Meara, The Young Augustine (London, 1954) and Pierre Courcelle, Les Confessions de Saint Augustin dans la tradition littéraire (Paris, 1963)。11-13卷似乎从其他各卷中脱离了出来,尽管在第13卷又出现了某种有趣的转折——它似乎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回归到最初10卷的群集当中(类似k-均值的标准聚类测试表明:11-12卷自成一组,而13卷归入1-10卷那一组。)研究奥古斯丁的学者詹姆斯·奥唐奈(James O’Donnell)在论述皈依后的诸卷时写道:“奥古斯丁在写作这篇文本时将他在奥斯提亚所领悟到的付诸实践。这不再是一篇对从前某个时间发生在别的某处的事情的记述;文本自身就成为了上升的过程。它不再讲述神秘的经验,而是变成了神秘经验本身。”*James O’Donnell, The Confessions of Augustine: An Electronic Edition (1992): http://www.stoa.org/hippo/comm10.html#CB10C1S1.根据这张图,皈依前和皈依后的叙述之间存在语言上的显著不同。这种差异在叙述结束之际又开始与它自身汇聚。
此图让我注意到的第二个特征是聚类内部各卷之间的相对距离较短。我们可以看出,皈依前各卷的聚类比皈依后各卷的聚类要紧密得多。后期数卷不仅距离前期数卷较远,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比较大。事实上,把11—13卷称为一个聚类甚至有点不合适,不如将之视为从前10卷发散出去的一系列独立点。在对皈依前后的生活叙事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内部-话语(intra-discursive)差异。换言之,皈依后的语言比皈依前远为异质化。奥古斯丁在皈依前和皈依后所使用的语汇不仅非常不同,而且越来越不同。根据这张图,皈依成为奥古斯丁语言高度离散性的开端。

当我使用此模型来处理我的数据时,发现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奥古斯丁在两种测量表上比大多数小说得分都高,并在半内得分表上超越了所有被测小说。*奥古斯丁的得分结果:半间距离(cross-half)= 0.021597377, z得分(z-score)= 2.5899149785, 半内距离(in-half)= 0.0067916874, z得分z-score = 5.162108633. 通常具有统计意义的界点为距离平均值有1.96个标准方差。鉴于半间得分对长度的敏感(见下一条注释),这些得分尤其显著,因为奥古斯丁的文本在5个总体长度最大的组中排第3位。换句话说,此模型非常擅长于识别它赖以建立的文本范例。这不奇怪,但是也很重要。接下来我用此模型比较了我的两个样本组。我的目标是弄清楚这两种不同的叙事体裁——自传和小说——在漫长的19世纪(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它们各自数量的和形式的巩固,在与这两种语言转换的关系上是否呈现出显著的不同。

3a:奥古斯丁《忏悔录》全13卷的半间距离

3b:奥古斯丁《忏悔录》全13卷的半内距离图3a和3b 半间距离(a)采集《忏悔录》皈依前和皈依后的部分之间的平均距离。半内距离(b)采集皈依前各卷间距和皈依后各卷间距之间的差异(即半内1-半内2)。在以下讨论的模型中,这些测量将对每一部小说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距离进行采集
我发现,在所有三种语言中,小说在两个量表上的得分都远高于自传(见图4)。*以下结果基于小说和自传的比较。我纳入了t测试结果和威尔卡森等级总和检定的结果。后者修正了数据内的非正态分布。两个结果都低于p < 0.05这个通常的临界点。半间距离 小说平均 自传平均 p值(t测试) p值(威尔卡森) 0.013847732 0.009992367 2.2e-16 2.2e-16半内距离 小说平均 自传平均 p值(t测试) p值(威尔卡森) 0.001141110 0.000797757 4.03e-05 0.0003017这些结果表明语言、性别或视角(第一人称叙事对第三人称叙事)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结论基于对方差检验的分析,其结果没有在此展示)。然而,长度必定是半间距离测量中的一个因素(但在半内距离中则并非如此)。较长作品在这项数据上(半间距离)得到高分的机会明显较低。总而言之,测量结果对长度敏感,得高分的几率偏向较短的小说或者至少不那么长的小说。根据此模型,自传叙事的极化或断裂程度较低,这表明了自传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或一致性,甚至是连续性。在对这一体裁在19世纪的崛起以及它与小说的关系的思考中,这一点相当有趣(假如我们从卢曼(Niklas Luhmann)的形式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forms]这个角度来思考)。自传具有一种对一个人的连续性的关注,与小说的散漫型变化特征显著不同,这向我们暗示了两种题材在这一时期起到的不同社会功能。*这些发现应该让我们放慢脚步,不要太轻易地接受一些关于自传研究的老生常谈,认为这是一个为变化而生的体裁。如卡罗琳·巴罗斯写道:“自传是关于变化的,它讲述一系列转变。这是我们对任何自传性文本的期望。”Carolyn A. Barros, Autobiography: Narrative of Transform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1。 詹姆斯·奥尔尼在他关于从奥古斯丁到卢梭的自传与记忆的著作中也有相似的主张:James Olney, Memory and Narrative: The Weave of Life-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图4 皈依模型,根据两种皈依得分得到德语中自传和小说双变量图。尽管有重叠的地方,但是大体来说小说的分布呈现出向上和向右的趋势,表明小说在两种量度上的得分都更高
为在任何给定作品内部找到聚类的最大数量而进行进一步测试,我们将之称为“轮廓测试”(silhouette test),这为小说的普遍二元性提供了新的证据。如我们在表中所见,超过三分之二的德语小说的最佳归类仅有两个聚类(见图5)。*轮廓测试(silhouette test)度量的是在一个任意可能大小的给定聚类中,任何给定点到其他所有点之间的平均距离,并将此结果与它和所有其他给定聚类中任意点的关系相比较。理想的场景是每个点到同聚类中其他点的距离最近,且与另一聚类中的所有点距离最远。这项测试结果来自在R语言包中使用pam()聚类方法操作。进一步阅读,参见P.J. Rousseeuw, “Silhouettes: A graphical aid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cluster analysis,” Computational Applied Mathematics 20 (1987): 53-65。与之相反,自传中可归入两个聚类的百分比要低得多(更接近50%),而且拥有更大数量聚类的自传作品要比小说更多。这表明生平叙事中二元性的缺乏为作品在更高的程度上表达微小差异留出了余地。为进一步检验这一发现的显著性,我将我的小说样本与一系列由散文和哲学文献组成的非叙述性文本进行了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在两种测量表里都没有得到显著的高分,表明此模型仅适用于叙事体裁内部的差异。这可能与叙事体裁具有较强的语言连续性有关。当然这一点需要进一步验证。*以下结果基于对小说和自传的比较:半间距离 小说平均 非叙事平均 p值(t测试) p值(威尔卡森) 0.013847732 0.01458604 0.158 0.2824半内距离 小说平均 非叙事平均 p值(t测试) p值(威尔卡森) 0.001141110 0.002164255 0.0003465 2.572e-05所以,此模型不仅能够识别体裁间的显著差异,也能识别此种差异的极限情况——即它们何时不再有效。

图5 对不同体裁的聚类最大数量进行的轮廓测试结果。最常见的聚类数量是两类,在两种体裁中都常见,但在小说中比在自传中明显地更常见。此外,我们能看到在可以分为更多聚类的作品中,自传比小说的数量要多。只有21部小说可以被分为3个以上的聚类,而可分为7个或更多聚类的自传就有21部。我在比较中只使用了德语小说,以求保持语料库的对等
当今的远读实践通常就在这里结束了(见图1)。有了一个统计性显著的大范围结果后,实行远读分析的研究者会花一点时间来设想这个结果的文化意义(正如我刚刚做的),然后就谈别的。然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回到定性方法的时候。定性方法本身不是目的,但它是优化我们的量化模型的方式,可以降低所谓的猜想程度(正如图1中指向图表想象中心“小说”的那些虚线所示)。
如此一来问题可能就会是:这些量化尺度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叙事内容?如果我们不是在群体之间进行泛泛的观察(如将小说与自传或别的叙事体裁进行对比),而是对那些在测量表上得到显著高分的小说进行体裁内部的审视呢?假设一部小说被识别为“皈依性”的,它一定跟皈依有关吗?如果是,以何种方式有关?小说进程中以量化方式显示的明显语言转换与皈依的语义学概念是否对应?
这就是计算机科学中所说的验证过程,即证明所使用的测量方法与其所测量的主题内容相符合。而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发现的过程。识别小说表现“皈依性”的不同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定性方向上理解小说中皈依叙事的本质。此外,它还能帮助我们识别那些可以加入模型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进一步验证可以让我们对皈依叙事的本质有更多了解(见图1中的“模型2”)。假如我从一个事先已被贴上“皈依”标签的小说子集开始这个过程,以检验模型的精确度,即:这个模型能在何种程度上捕捉到我已知的事实?那么我很不可能把我的小说样本进行这样的归类(更别提这样做是多么的不现实——我得从哪里开始?)。事实上,100多年来的小说研究从未以这样的方式成功过。同时,一旦我创建了这个模型且付诸实践,那么我极有可能在细读时发现自己寻找的目标。这就是细读确认我们的想法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验证过程不应该被视为目的本身,而是一个提出进一步假设进行验证的过程。这是计算解释学的第二条法则:验证并非证实,而是为进一步检验提供手段。正如细读可以检验远读的可靠性,远读也应该能检验细读的可靠性。在下一节里我将从“验证-发现”这一过程开始,进行二次建模。
发现(验证)
首先,我根据以上两组皈依数据对我的小说样本进行了排序,结果以降序排列如下,并仅保留了那些至少在一项得分中有统计意义的作品(见表1)。这些小说在这两项特征中的至少一项上显示出明显高的得分。根据我的模型,这种现象应该说明某种类型的皈依体验的存在,也就表明了深层次的语言和/或时间转变的存在。与奥古斯丁的作品一样,这里应该有一种清楚的二元性(皈依前后的自我),还要有合并的过程——将自我纳入某种自我之外的存在。接下来,我会提供一个初步的小说皈依分类法(taxonomy of novelistic conversion),以及一份需要进一步检验的假设清单。阅读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让我们得以识别和描述那些能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特殊子体裁(sub-genre)性质的可能性特征。

作品半间距离z得分排名半内距离Z得分排名综合得分德语保罗·施尔巴特《勒撒本迪欧》(1913)0.0183+3.0720.0030+2.1553.5约翰娜·斯比里《海蒂学以致用》(1881)0.0193+3.4910.0029+2.0184.5特奥多尔·冯塔纳《混乱与迷惘》(1887)∗0.0152+1.59110.0047+3.9516约翰娜·斯比里《海蒂的学徒和旅行年代》(1880)∗0.0183+3.0630.0022+1.341710弗兰兹·卡夫卡《城堡》(1922)∗∗0.0150+1.48130.0027+1.84911法语儒勒·列那尔《胡萝卜须》(1894)0.0251+3.7210.0047+3.4032古斯塔夫·福楼拜《斯玛》(1839)0.0242+3.3820.0055+4.1522伊莎贝尔·夏何耶《三个女人》(1795)0.0212+2.2340.0040+2.7344儒勒·凡尔纳《从地球到月球》(1865)∗0.0174+0.79270.0058+4.46114苏菲·塞居尔《苏菲的烦恼》(1864)∗0.0233+3.0130.0018+0.632614.5英语托马斯·洛夫·皮考克《梦魇寺》(1818)0.0224+2.7820.0051+3.4632.5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彭布罗克》(1894)0.0209+2.2960.0042+2.6566杰克·伦敦《白牙》(1906)0.0198+1.9080.0042+2.6656.5托马斯·洛夫·皮考克《黑德朗大厅》(1815)∗0.0186+1.47120.0054+3.7416.5玛利亚·埃奇沃思《拉克伦特堡》1800∗0.0198+1.8890.0034+2.01109.5H·G·维尔斯《时间机器》(1895)∗0.0168+0.85230.0051+3.46413.5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1920)∗0.0151+0.27480.0053+3.61225
表1此表列出了各种语言中每一测量里得分最高的小说。这里只考虑了那些在至少一项测量中表现出统计显著性的小说。它们的排序根据各自在两种测量中的综合评分。星标表示该小说只在一项测量中呈现出统计显著性。其中一部——卡夫卡的《城堡》——有两个星标,在两种测量中都分别低于阈值,尽管它的综合排位仍进入了前五。某些小说——比如施尔巴特和列那尔的作品——在两种测量中得分都相当高。其余小说的两种结果之间则呈现明显不同,如菲茨杰拉德或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所示:两人作品的半内得分都很高,但是半间得分则低得多
自然—文化,或神性的回归
高度皈依性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它对自然/文化的二元性的强烈关注。这一点并非是结构主义的,并非等于将自然/文化二元视为小说(或者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的现代文化)的决定性二元。反之,它是一种让与宗教相关的经验变得戏剧化的有用模型。斯比里(Johanna Spyri)的海蒂系列小说(Heidinovels)、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白牙》(WhiteFang),以及福楼拜(Gustav Flaubert)的《斯玛》(Smarh)基本是关于世界二分结构的小说,宗教和自然则是这种二分结构的编码语言。在斯比里的小说中,住在阿尔卑斯山高处的祖父在故事结尾将经历向基督教的皈依(在这位瑞士野蛮人被拯救之时);在杰克·伦敦的小说中,离开野外世界的半狼将人类视为“诸神”,而它将再度进入的世界正是人类的世界;在福楼拜的《斯玛》里,对皈依的渴望就是对其后来的哲理作品《圣安东尼的诱惑》的预演——这种渴望被描述为从无限开始,坠落到怪异文明的可怕深渊(书中的恶魔化身“于克”[Yuk]正是这一深渊的象征)。正如斯玛在与撒旦对话时的宣言:“哦!我的心变大,我的灵魂打开了,我的头脑开始不清楚了;我感觉我要变了,”然而仅仅过了几页他就改变了决定:“哦,不!将我带回人间,让我回到我的陋室。”*Gustav Flaubert, Smar. Vieux mystère. Oeuvres complètes, ed. Claudine GothotMersch et Guy Sagnes, vol. 1 (Paris: Gallimard, 2013) 548; 559.或如艾默里·布莱恩——菲茨杰拉德晚期关于幻灭的成长小说的主人公,该小说也是半内距离测量表上得分第二高的作品——所言:“我们想要相信。年轻的学生们试着相信老一辈的作家,选民们试着相信他们的议员……但是他们没法相信。太多的声音,太多分散、不合逻辑、欠缺考虑的批评。”*F. Scott Fitzgerald, This Side of Paradise (New York: Scribner, 1920) 215.对信仰无法完成的追求是皈依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斯比里的小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这些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影响深远,很少有小说能像它们一样将宗教皈依表达得如此清晰。*如贝蒂娜·胡热曼写道:“宗教导向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无论是写给儿童的还是写给成人的。” Bettina Hurrelman, “Mignons erlöste Schwester: Johanna Spyris ‘Heidi.’” Klassiker der Kinder- und Jugendliteratur, ed. Bettina Hurrelmann (Frankfurt/Main: Fischer, 1995) 192. See also Regine Schindler, “Form und Funktion religiöser Elemente in Johanna Spyris Werken,” Nebenan: Der Anteil der Schweiz an der deutschsprachigen Kinder- und Jugendliteratur (Zürich: Chronos, 1999) 173-199.她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题为《海蒂的学徒和旅行年代》(Heidi’sApprenticeshipandJourneymanYears),借取了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系列的成长教育小说原型,讲述一个年轻的瑞士孤女海蒂的故事。海蒂被她的姑姑交给她的祖父,因为姑姑已无力照顾她。*胡热曼认为歌德对海蒂系列小说产生了许多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威廉·麦斯特小说在两项测试中得分都是中低水平(半间距离得分137/140,半内距离得分57/76)。这表明模仿作品可以比原型具有更强的特征。我们会看到,借来的模板通常看起来像皈依小说的背景,有着突出的二元性(如皮考克[Peacock]的哥特戏仿小说、福楼拜的浮士德式改写,或者成长小说体裁的诸多蹩脚模仿作品所示)。在她避世僻居的祖父那座位于阿尔卑斯山高处的小屋里,海蒂度过了三年田园牧歌式的时光。三年以后她被姑姑带走,寄放在法兰克福一个有钱人家里。将一个瑞士野蛮人引入德国文化的家庭空间,这即是从神性空间“堕落”(descent)一词的精准注释。海蒂越来越讨厌她身处的这个文明新环境。在憔悴将死的边缘,她突然又被送回了阿尔卑斯山区。小说的戏剧性就在于她的祖父母是否还健在,以及她从文明世界带回了两种突出经验的事实:她学会了读书和祈祷(尽管搞反了顺序)。在小说结尾,她的祖父皈依了基督教,放弃了先前对神的弃绝态度。海蒂曾被要求顺服于法兰克福的社会习俗。这种顺服在小说的结尾又被表现为向上帝以及圣经投降。
正如这一简述所示,奥古斯丁式的皈依模板和海蒂故事的主题内容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对应。实际上,在一项针对奥古斯丁式的词汇在一般小说中的残留度的单独测试中,海蒂系列是得分最高的两部作品。*为创建我的词典(仅限于德语小说部分),我从《忏悔录》第8卷第12节皈依场景中提取了一套词汇,且仅保留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5个德语译本中都出现了的词语。这个时间线正对应了我的主要语料库的时间线。因此,我使用的这套词汇由46个词组成。它们无一例外,都出现在两个多世纪期间对奥古斯丁皈依的德语翻译中文本中。有意思的是,小说在这项测试中的平均得分同样较高,而且10部得分最高的小说中有7部的作者是女性,表明女性小说家与皈依词汇之间也许存在某种相关性。在这一测试中,海蒂小说表现出了它的时代特征:不仅平均而言奥古斯丁式的词汇在小说中的存留更显著,而且这种现象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似乎还有稍微的增长(见图6)。*比较小说和自传的词汇得到结果如下:自传平均值 = 0.01435336, 小说平均值 = 0.01661757, p值 = 6.628e-13。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如下:调整后的R平方值为0.03762,p值斜率0.00992。至少在德语中,小说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奥古斯丁化,而不是相反。此外,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奥古斯丁式的词汇。这意味着关于女性小说在德语中的发展的一项重大发现。*用方差测试分析,F统计量是4.589,p值为0.0338。此外,10部得分最高的小说中有7部作者为女性。

图6 《忏悔录》第8卷第12节的皈依场景中,奥古斯丁所使用词汇的出现频率及其在德语小说中出现频率的对比。此词汇表来自5种跨度为一个半世纪的、不同的奥古斯丁作品德语译本,且仅保留在所有5种译文里都出现的词语,一共44个
《海蒂的学徒和旅行年代》不仅明显地讲述了一次宗教皈依的经历——这次皈依发生在祖父身上,带有清晰的奥古斯丁意味——还充满了一系列二元结构,如瑞士和法兰克福之间的自然/文化分界、祖父与孙女之间的代际分界,以及阅读与不阅读之间的发展分界。最后一点对于这部小说似乎最为重要。事实上,就整个德语小说的语料库而言,“阅读”一词在这部小说中的显著性排在第6位。*我为小说中每一个在全部小说的至少60%中出现的词(共计3141个)算出z得分,然后以降序排列。目的是寻找那些在所有小说中经常出现,且在某一部小说中使用频率高出正常水平的词。海蒂学会阅读标志着她回家和回归上帝的开端。当被问到海蒂是否可以保留她的第一本书的时候,她的祖母回答:“当然,当然,现在它属于你了。”“永远吗?即使当我回家的时候?”海蒂问。“当然是永远了!……明天我们就开始读书,”祖母说。*Johanna Spyri, Heidis Lehr- und Wanderjahre (Zürich: Diogenes, 2000) 154. 除非特别注明,本文中所有的译文(德-英)都是我自己翻译的。拥有这本书并可以抓握住它成为皈依链的前提条件,而小说正是以皈依结尾的。在小说结尾,这是一天晚上,在小海蒂睡着的时候,祖父盯着孩子交叠的双手,随后就发生了他自身的皈依,相当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书和孩子的身体姿势共同作用,带来了精神上的转化。这一场景明显是奥古斯丁自己的触觉皈依理论(haptic theory of conversion)的回响,既有其最为重要的叠句重复,又有其作为手册指南的迫切:“拿走它,去读。拿走它,去读。”
如果说海蒂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将文化引入自然使之成为根本变化的前提,杰克·伦敦的《白牙》——一个关于一只驯化的狼的流行故事——中,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从这个用动物视角讲述的故事中得到的教益是如何掌握社会生存的铁律。正如叙述者在小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用自由间接引语所表达的:“对[白牙]而言,对人的效忠似乎是比对自由和同胞的爱更重要的存在法则。”*Jack London, The Call of the Wild, White Fang, and To Build a Fire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1998) 169.白牙的母亲是半狗半狼,小说讲述的就是它渐渐融入社会的故事。与海蒂的故事一样,这部小说也充斥着二元结构,如南方和北方之间、人和动物之间、野蛮和文明之间、野外世界和其他一切之间。白牙最后将拯救它的收养者及其家人的性命,这种交换式的报答在小说里被称为“正义”。“对于白牙而言,这是开始也是结束——结束了它原来的生活,结束了仇恨在生命中的统治地位。一种新的、无法言喻的更美好生活正在拉开序幕”(214页)。白牙的皈依在小说的结尾处实现了——它与当地狗柯丽生下了小狗。柯丽是牧羊犬,在所有地方都是狼群的大敌,现在却是白牙孩子的母亲。
假设1:皈依小说由自然/文化的二分法定义,其中自然是神性的代表。我们基于这些小说创建两份词汇表(一份是代表“文化”的词,如文明、正义、阅读等,另一份是代表“自然”的词,如阿尔卑斯山、树木、荒野等),并测量这些词语的使用强度。这两份词汇表的强度越高,就可以认为小说的皈依性越强。
外太空,或无法沟通
如果在19世纪晚期的成长小说里,自然是外部因素而文化是内部因素的话,在新兴的科幻小说体裁中,“空间”将提供另一个更极端的二元对立。*Wolfgang Braunart, Gotthart Fuchs, Manfred Koch, sthetische und religiöse Erfahrungen der Jahrhundertwende, II: Um 1900 (München; Schöningh, 1998).H. G. 韦尔斯的(H. G. Wells)《时间机器》(TimeMachine,1895)、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从地球到月球》(DelaTerreálaLune,1865),及保罗·施尔巴特(Paul Scheerbart)的《勒撒本迪欧》(Lesabéndio)(1913)都代表了科幻小说依赖于强烈对立模型的方式,就好像成长小说中的自然-文化对立被转引进入一个文化-科技坐标系。外太空和科技成为与地球生活和日常生活相对立的极端,超越地球成了它们的首要叙事推动力。《从地球到月球》从本质上是一个弹道学故事,椭圆弧代表人类逃离自身的欲望。在小说中,巴尔的摩有一个“大炮俱乐部”,从事对理想中的大炮和抛射体进行完善的工作,作者对这些进行了大量描述——这些完善工作旨在确定实现逃逸速度的地球技术条件(从炮弹的合适厚度,到大炮的长度,到需要的火药量)。随后,当一个(来自法国的)愿意乘坐炮弹前往月球的人类志愿者出现时,小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这名志愿者最终说服大炮的发明者——他的主要对手——与他一起出发。小说的弧线不是自然融入文化——比如那只被驯化的半狼半狗身上发生的故事——而是人在物理意义上被技术封装。
保罗·施尔巴特的《勒撒本迪欧》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最喜爱的小说之一。它同样在过程上花费了大量篇幅。然而,它关注的不是上一故事中的完美抛射物,而是一座星际高塔的建造,讲述了一个带有现代色彩的巴别塔故事。建塔的目的是与那个被称为拥有“大个子”(德语:das Größere)这个含混代号的星体结为一体。再一次,与另一类的全面结合(德语:Ergebenheit )清晰地成为小说的目标:“勒撒本迪欧一心思索着他的归附理论(德语:Ergebenheitstheorie),同时沿螺旋线旋转,慢慢消失在宇宙深处。”*Paul Scheerbart, Lesábendio. Ein Asteroiden-Roman (Hamburg: tredition, 2006) 86.小说以勒撒本迪欧升入外太空结束,这一上升显然是浮士德式的。与浮士德一样,勒撒本迪欧一路盲目探索,听见了各种隐喻的话语。他的旅程以大笑开场,却以极度的痛苦结束。这种经验被描述为一种激烈的对感官的重新定位。对行星的超越被表现为一种深刻的生理断裂,然而它在最后也被描述为一种沉默。“但是勒撒什么都没说”(195页;斜体出自原文——作者注)。与此类似,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中也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火箭没能在月球上着陆,因此与留在后面的人或已经出发的人进行交流的梦想无法实现。这些科幻小说表现出的皈依难题是沟通问题:怎样才能把这新发现的知识传回给予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怎样才能与那些留在原星球的人实现沟通?
对于奥古斯丁,皈依是更广阔的交流形式的前提。与语言进入了丰满话语境地的奥古斯丁不同,在施尔巴特那里,皈依被表现为交流的极限,是不可言说之物。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两半部之间的半内距离为明显的负数,意味着小说的前半部比后半部表现出了更大的语言变化幅度(见图7)。奥古斯丁的皈依被看作是向丰满话语的转折,勒撒本迪欧的皈依却被看作是一种语言限制、一种话语的窄化。相应地,小说最后一句中的“新生”——皈依的终极比喻——将以假设句的形式出现:“绿色的太阳如此闪耀——似乎它上面也有一个新生命在苏生。”(199页,德语:Und die grüne Sonne strahlte so hell auf - als wäre auch auf ihr ein neues Leben erwacht)。皈依的沟通和新生的联结——即皈依体验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或者从一个行星体传到另一个行星体的可能性——最终被标记为一种诠释过程,为补完小说的开篇假设而做的总结性假设。这一点将由凡尔纳笔下那趟没有归程的月球之旅开启。皈依是局外人的解读,而非局内人所表达。这就是现代皈依的“外太空”,是它不可言说的残留。

图7 关于施尔巴特的《勒撒本迪欧》的多维尺度(MDS)测量表。图中的点分属小说的两半,因此用不同的符号标记
假设2:皈依小说的定义来自不可沟通性这一传统主题。它会创造一些语句来表达交流中的无路可走,比如:a)虚拟语气语句如德语中的als ware或“即使+动词”;或者b)说过+否定(如“什么都没说”、“没有说”、“说不出口”等等)。较高的条件性和否定性应该与更强的皈依性和皈依的不可沟通性相关联。
双重婚姻,或多义现象
如果说我迄今描述的小说都有很强的地理差异标记,比如月亮、双行星、阿尔卑斯山和荒野,那么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Mary Wilkins Freeman)的《彭布罗克》(Pembroke),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混乱与迷惘》(Irrungen,Wirrungen),或是儒勒·列那尔(Jules Renard)的《胡萝卜须》(PoildeCarrotte)在尺度上则要微观得多。它们中每一部作品都有关不幸的婚姻、二元结构的社会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压迫限制。冯塔纳关心的是贵族博托男爵和工人阶级的莱娜之间的恋爱。两人在小说大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将会分手,之后分别与社会地位更相配的对象结婚,从而保存了威廉时期柏林的阶级分层。弗里曼关心的是巴纳巴斯·塞耶和夏洛特·巴纳德失败的婚姻(我们可以看出巴纳巴斯-巴纳德[Barnabas-Barnard])这样的取名习惯本身就包含着小说暗含的轨迹)。纵观我们在此研究的150年中出现在小说中的婚姻情节,这两部小说看起来最全面地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我们没有纳入英国作家简·奥斯丁,原因不言自明:评论家对奥斯丁认可的前提就是她的叙事模式从不基于大幅情感波动,而是基于语言的连续性,以及因而产生的某种需要阐释的微妙感。奥斯丁小说的正统性、经典性也使得她的几部小说之间较为统一,在显著的特点方面较为模糊。
我们先来看弗里曼。这部小说的中心事件是巴纳巴斯在一次与未来岳父的争吵之后无心“回归”。小说对某人明确的不愿“掉转”(turning around)进行了抨击。对于弗里曼,这部小说是一项关于人类意志以及意志需要用爱来治愈的研究。“我写作《彭布罗克》的原本意图是,”弗里曼写道,“通过研究几个新英格兰的人物,他们历经疾病和非健康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研究人类意志,以此证明——尤其是在最显著的情况下——下面这一理论的真实性:那就是,人类意志的治愈良方完全在于个人的爱的能力——它可以高于一切对自身的考虑。”*Mary Wilkins Freeman, Pembroke (New York: Bibliobazaar, 2007) 7.一次又一次,巴纳巴斯会说出“我不能”。这是那个名字与他的名字押韵的前辈巴特比*指美国19世纪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发表于1853年的中篇小说《巴特比抄写员:华尔街故事一则》中的主人公。——译者注常用的“我宁愿不”的回响。与其说这部小说是关于抵抗,不如说它是关于人的无能——即一个人想做自己从情感上无法接受的事时会是什么样。这部小说里许多其他失败的关系也将与巴纳巴斯和夏洛特的问题形成映射,如丽贝卡·塞耶的未婚先孕及她与威廉·巴里的结合、理查德·阿尔杰将老处女西尔维娅·克雷因抛弃,还有巴纳巴斯病怏怏的弟弟伊弗雷姆那令人揪心的死。伊弗雷姆的死既由于他在一天晚上乘着月光偷偷地坐雪橇(“他一生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到快乐”[184页]),也由于随后遭到母亲殴打。从19世纪末的眼光看来,19世纪中叶的新英格兰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爱存在。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巴纳巴斯会变得越来越驼背,这是一个竖直方向上的隐喻,他生活在两个家庭房子之间一座未完工的小屋里,这则是这个隐喻在水平方向上的映射。最终,在小说结尾处,在两人最初分手10年以后,身患重病的巴纳巴斯醒悟了,回到夏洛特身边。“他在走,他像任何人一样挺直了走!……夏洛特走上前。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然后越过她的头顶看着她父亲说:‘我回来了,’他说。”(257页)巴纳巴斯在身体、动作、和精神上的皈依由此完成。
冯塔纳的小说在情节上也是惊人的相似,也有两个家庭的二元结构,也有一个关于接受的更大主题。正如博托在小说的决定性转折使用主题词“放弃”(Ergebung)时所说的那样:“放弃毫无疑问是最佳方案(德语:Ergebung ist überhaupt das Beste)。”*Theodor Fontane, Irrungen, Wirrungen (Stuttgart: Suhrkamp, 2006) 101.空间上的双重性伴随着——或者不如说成为其背景——的是为某种比自身更伟大的事物而放弃自我的个人经历。冯塔纳的小说——以及他的普遍作品——常以其高度的对话性(即对话优先于叙事)和因对话性产生的语言多样性(他的小说在方言和阶层上投入甚多)而为人留意。批评家们认为,《混乱与迷惘》是19世纪最能代表巴赫金众声喧哗理论(heteroglossia)的作品之一。*关于这部小说的复调,参见Ingrid Mittenzwei, Die Sprache als Thema: Untersuchungen zu Fontanes Gesellschaftsromanen (Bad Homburg: Gehlen, 1970);Horst Schmidt-Brümmer, Formen des perspektivischen Erzählens: Fontanes Irrungen, Wirrungen (München: Fink, 1971);Norbert Mecklenburg, Theodor Fontane: Romankunst der Vielstimmigkeit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98);更新的研究参见Gerhard Neumann, Theodor Fontane: Romankunst als Gespräch (Freiburg: Rombach 2011)。
然而,我在此希望证明的是:这样的复调在这部小说中不是静态的,而是沿着一条轨迹前进。这条轨迹对于我们理解这部小说致力产生的各种语言皈依至关重要。关于冯塔纳的小说,皈依性测试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几点之一就是:在我的德语小说库里,这部小说因其前后两半之间的语言差异(半内距离)最大而被标记出来(见图8)。这并非因为冯塔纳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显著地改变了他的词汇,而是因为这部小说在走向结尾时发生了语言窄化(linguistic narrowing)——这一点比德语传统中的其他作品更显著。婚姻和阶级的社会限制都通过说话时的词汇限制反映了出来。小说前半部分中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复调——阶级和方言的复调正是冯塔纳所著名的地方,也启发了许许多多研究冯塔纳的学者——然而这种复调的存在不过是为它在后来的丧失作铺垫。

图8 冯塔纳的《混乱与迷惘》多维尺度(MDS)表。此表说明小说前半部的大规模离散如何在后半部缩减到一个局促得多的空间
然而,这种词汇限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为语义上的开放性所弥补。小说在空间上显著的二重性成为思考语言本质的背景。此小说最怪诞的特征之一是将博托的新妻子凯特变成了滑稽和大笑的代名词。“简直太可笑了(Es ist doch zu komisch)”(174页),凯特又一次说道。这一说法又被经常重复:“啊,那太好笑了(Ach, das ist zu komisch)”(183页);“你能想到比那更好笑的事情吗?(Kannst du dir was Komischeres denken)”(187页);或者“情书,太好笑了(Liebesbriefe, zu komisch)”(184页)。“情书”当然没什么好笑的,更别说这部小说了。在德语里“好笑”(“Komisch”)一词也可以是“奇怪”的意思,而我认为冯塔纳想要捕捉的正是这种好笑的奇怪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交流有其非字面的一面,即意义的内化。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扩张弥补了小说整体上的词汇缩减特征——多义性,而非复调,变成了小说的目的。
这种二重性将在阳台一幕找到理想的场景关联——博托和凯特之间的最终对话大部分发生在阳台上。阳台被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性边缘受限空间,这一点在画家马奈的作品中尤为重要。*Jonathan Crary, 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这部小说对非人介词(impersonal preposition)的使用具有统计上的独特性。而这种二重性正是在这些介词中得到了词汇表达。这些介词包括“在那边”,“在……后面”,“在……之间”,及“在……之外”(德语:“drüben”、“dahinter”、“dazwischen”或“draußen”)等等,构成对符号学上别处的众多重复表达。对于冯塔纳来说,皈依不是一种身体上或精神上远离或朝向某个目标的运动。小说的皈依更应被理解为一种语义的内化过程,是语言内部意义强度的增加。
假设3a:皈依小说在结构上有着强烈的地理二元性,以不同的说话方式为标志。我们是否能用对命名实体的识别来找到将名字纳入不同的词汇群的归集方法?一部小说中二者之间的对立越强烈(区别越明显),就可以说是更具有皈依性。
假说3b:皈依小说以小说发展过程中多义性的增加为标志。词汇的缩减对应的是语义的复杂化。我们能否创造一个量表来解释一个文本在语义上的模糊性?即确定一个词的特定意义何以变得越来越难?我们可以使用一系列工具,如词性标识(speech tagging)、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并观察它们的失败程度。模糊性应该与自动化处理的难度增大正相关,而且这些数值应该随着小说的进展而相应地增加。
卡夫卡,或递归性
我的最后一个例子既是最明显的,同时也是最让人迷惑的情况。一方面,从神学角度讨论卡夫卡进入了文学学者最熟悉的领域之一。很少有现代作家在超越超验问题方面受到的解读比卡夫卡更多。这些关注也的确经常与皈依的问题挂钩,不论是将之理解为身体的变化(如《变形记》)还是深度信仰(如《在流放地》)。*卡夫卡作品的这种皈依性的核心是一个基本的二元结构,那是他的许多小说的基础,而我们在这部分的其他小说里也明显地看到了。关于卡夫卡的空间二元性,参见Manuela Günter, “Tierische T/Räume. Zu Kafkas Heterotopien,” Raumkonstruktionen in der Moderne. Kultur-Literatur-Film, ed. Sigrid Lange (Bielefeld: Aesthesis, 2001) 49-74.寻找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与某种极为难以把握的东西的共融,是卡夫卡小说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然而,他未发表的小说初看上去似乎排斥这样的联系,这不同于卡夫卡那些生前发表的、明确围绕着皈依问题的故事。既作为小说也作为小说中物理存在的“城堡”能让我们皈依何物?奥古斯丁相信他接近了上帝,这种接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语言世界,也开启了全新的知识范畴——比如时间和永恒。卡夫卡《城堡》中的K.,与奥古斯丁不同,他相信城堡是可以进入的,这种信仰将他带往比城堡更远的地方——而且应当加一句——带向一个不断消减的词汇世界(如同冯塔纳和施尔巴特的小说,《城堡》具有强烈的语言窄化特征)。因此,宣称卡夫卡的《城堡》是德语文学历史上最奥古斯丁式的,也就是最具皈依性的小说之一,是一种相当奇怪的主张。*与我的数据集相符合的卡夫卡《城堡》版本是Franz Kafka, Das Schloβ (Frankfurt/Main: Fischer, 1967)。关于卡夫卡作品版本的作者意图还有很大争议。我的目的不是参与到这些争议中,而是对最主流的通行读者版本进行处理。本文讨论的分层聚类分析为采用这个版本提供了进一步支持:该分析表明《城堡》中词汇聚类为两组,与其两半部分的划分正相一致,是德语小说样本库中呈现这种特色的3部小说之一。
但是,我们越看得仔细,就越能从《城堡》中看到一种对奥古斯丁主义的模仿在起作用。这一点据我所知之前还没有学者提出过。在德语小说样本库中,有三部小说的前后两半与其各部分的词汇聚类几乎完全重合,而卡夫卡的《城堡》仅是其中之一(见图9)。就一部小说的词汇分界线正好与其量化分割相匹配这种理想情况而言,《城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范例。这为马科斯·布洛德(Max Brod)*马科斯·布洛德(1884—1968),德语犹太作家,卡夫卡的密友。卡夫卡生前留下遗嘱,要布洛德在他死后将他的全部作品烧毁,但布洛德没有执行这一遗嘱。相反,他将卡夫卡的作品一一作序出版,并写了不少卡夫卡的评传,还将卡夫卡的作品改变为戏剧。——译者注对卡夫卡死后留下的残篇所做的安排提供了大量逻辑支撑。

图9 使用沃德(Joe H. Ward Jr.)的分层聚类法(Ward’s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为卡夫卡的《城堡》绘制树状图。这张图将小说的前后两半归成两个不同的分枝。德语小说样本库里仅有3部小说的聚类间词汇分界与小说前后两半分割完美匹配(没有任何第二部分的片段出现在第一部分的聚类里,反之亦然),《城堡》即是其中之一。另两部小说之一就是施尔巴特的《勒撒本迪欧》
第二点,这部小说有一种可辨识的词汇纵向定位特征——通过在那些具有统计重要性的词中使用“auf”这个前缀(如Auftrag, aufnehmen, Aufrecht, Aufmerksam, aufgeben, aufgeschoben),小说隐隐有了一种超越意味。然而,小说中也明显存在对奥古斯丁式经验的象征性共鸣,比如村庄和城堡之间第一次通电话那个著名场景:
从听筒(Hörmuschel)里传来一阵嗡嗡声(ein Summen),这种声音K.以前打电话的时候从未听到过。在嗡嗡声中似乎可以听出无数童稚的声音——可这嗡嗡声甚至都不是嗡嗡的,而是遥远的,最遥远的声音的合唱——,好像从这个嗡嗡声中不可思议地组合出一个单一的强烈高音。这声音在耳朵里猛烈震动,仿佛只要它想,就能钻入更深之处,穿透那可怜的听觉器官(das armselige Gehör)。(32页)
唱歌儿童的声音在《忏悔录》中是奥古斯丁皈依的序曲,在《城堡》中却通过电话的媒介出现(但电话也隐喻着贝壳(Muschel)——当你把贝壳拿到耳旁,可以制造出一种与远方通话的幻觉,听到一种似乎具有重要象征性的嗡嗡声)。奥古斯丁那里无法区分性别的儿童在卡夫卡这里被复制为声音在量上的无法辨别(“无数童稚的声音”),以量上的复多替换了性别的二元。相似的是,奥古斯丁描述了从未听过的童谣的重复吟唱(这些吟唱最终引出了那一句“拿走它,去读。拿走它,去读。”),在卡夫卡这里无法辨识的嗡嗡声(Summen)变成了一首歌(Gesang),后者是对前者模式上的复制。最后,在奥古斯丁那里,神性的间接存在贯穿于幼童的口头表达和成人的书籍中,到卡夫卡这里变成了电话中那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出的单一、高昂和强烈的声音。这声音超越了“可怜的耳朵”的承受限度,要求进入听者身体的更深处。超越感官以寻找一种更深刻的东西,以寻找一种亚感官知识(sub-sensory)是一种明显的卡夫卡式关切。它将奥古斯丁对神性向外和向上的追寻变成了面向自身的追寻。
奥古斯丁的皈依体验基于一种信念:一种单一的、超越的声音仍能通过媒介、机会和意志的结合找到我们。这一模板很可能在卡夫卡这里抵达了它的讽刺性结局。那个超验的电话里的声音(或众多声音)实际上可能只是噪音——只是贝壳状的听筒引起的幻觉,是自然耍的花招。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卡夫卡来想象这些皈依阅读的经历,但是我们所经历的不是这种经历的完成,而是对它们的想象性的认识。在这些意义上,卡夫卡将会是奥古斯丁式皈依的否定形式——他将我们引入一个后皈依的(post-conversional)阅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仍有希望,却不是给我们的。
许多关于卡夫卡的早期评论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神学追求,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却与他们针锋相对——他谈到了卡夫卡的“反神学”(inverse theology)。*Theodor W. Adorno, “Aufzeichnungen zu Kafka,”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olf Tiedemann, vol. 10.1 (Darmstadt, 1998) 254-287.卡夫卡之所以重要,其秘密不在于奥古斯丁式的语义充足,不在于某种更高或更深的东西的可能性,而在于字面,在于对意义的绝对限制。然而,如果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卡夫卡的散文体中的限制性和幽闭恐惧,就忽视了他的文字的强度和其中内嵌的运动类型。卡夫卡的小说宇宙最主要关注的是工作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对皈依小说中用以取代上帝的宏大能指(master-signifiers)——自然、外太空和婚姻——的一个补充。工作的存在即卡夫卡所谓的Arbeitersein,其特征并非意义的缺失,并非阿多诺认为的纯粹否定,而是一种抽空、撤离的经验,是一种回归式的(regressive)否定,关于纯粹意义上的运动崩塌于其自身之上的否定。*这也是为了区别于许多用介入(mediation)和沟通(Verkehr)强调卡夫卡小说两大最主要的关切的学术研究。对卡夫卡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某一媒介甚或媒介性(mediality),而是这样的现代体系让真实性的退场在无限递归中成为可能。关于卡夫卡的媒介性有两部著作的观点最为鲜明,参见Wolf Kittler, ed., Franz Kafka: Schriftverkehr (Freiburg: Rombach, 1990) 和Stanley Corngold and Benno Wagner, Franz Kafka: The Ghosts in the Machine (Evanston: Northwestern, 2011) 109-132。《城堡》没有推进,而是一直重演对角色彼此之间联系的讲述,以致每一次对于小说的社会宇宙的叙述都包含在前一次叙述之内。《城堡》不会回归或者打开——那是奥古斯丁开启的皈依体验的两种可能性。相反,它会进行重述。*参见 Stanley Corngold, “Kafka’s Double Helix,” Franz Kafka: The Necessity of Form (Ithaca: Cornell UP, 1988) 134。《城堡》以一种无限的螺旋形态朝向自身内部开放。正如芝诺的悖论,小说越长,就越难抵达任何地方。我们看不到行动,只有一份长长的、关于何为递归体验的讲述,即面向自身展开的重复。卡夫卡认为,没有运动性的运动是阅读停滞的悖论性承诺。这就是卡夫卡宇宙的皈依信仰状态,是对限制的无限依恋。
假设4:皈依小说是递归的。它们在推进的过程中重述自身,在向内扩张的同时放慢节奏。这是一种重叠式的皈依(我们无法从中逃离)。因此,叙事层次——即叙事中的叙事——应该随着小说的发展而增加。此处还有一个社会网络分析角度:对新角色的介绍会延缓而非推进叙事的发展。角色的增加和内故事叙事层(intra-diegeticnarration)的增长与情节变缓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呢?
重新建模(结语)
本文尝试为我们对小说作为体裁的重要性的思考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这个角度较少依赖某种形式的批评陌生化,更多依赖于某种明显的转变经验。它通过显著地改变分析的规模和范围来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对三种语言的几百部小说进行考察,随后对这些小说中超出我们的传统细读方法规模的语言转换进行检视。这种大规模语言转换看起来的确像是一种词汇基础建设构造——不同种类的皈依叙事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这种方式,在这样的多重价值层面上进行阅读,可以揭示出一幅迄今一直未能为我们的批评叙事所捕捉到的小说这种文体的肖像。在词汇变化、语义限制、地理对立、主题极化,甚至叙事的重复(如卡夫卡作品所示)等层次上,小说以及小说文体下的某个类别似乎都倾向于某些明显的分离模式。尽管“皈依小说”不属于传统文学史所接受的批评范畴,但本文使用的计算模型及定性阅读都表明它应该属于这一范畴。无论对这些小说的归类初看上去多么随意——海蒂、勒撒本迪欧、白牙、安佩·巴比康、巴纳巴斯·索耶、胡萝卜须以及K.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但是这些小说的关注点确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在于它们都关注深层变化的问题,还在于它们似乎都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奥古斯丁式关切。别的不论,这些小说至少应该让我们停下来重新思索卢卡奇(Lukacs)的论文——他认为小说是关心“被上帝抛弃的世界”的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小说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通过其语言和形式使人产生信仰的体裁,我们现在应该能看得更清楚了。
在更加理论化的层次上,本文还尝试对最近围绕远读模型与细读模型以及我们的批评实践的显著二元性发生的争论作出回应。我试图说明这两种阅读方法能通过一种重复性更高的“建模”过程被结合起来,可以被用来证实和拓展彼此的洞见。我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表明计算机辅助阅读本身所具有的皈依性程度。这种阅读方法涉及一个环形或是螺旋状的、经由一种在疏离与依附之间的振荡朝向一个无法抵达的终结目标(“小说本身”)的永恒接近过程。我希望指出的是,这些方法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作为读者的虔诚姿态,并代替掉那种被文献书目激发出来的、关于确认或揭露的强烈信念。这些信念已经在我们这一行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体验:它们由那些越来越更临时性的系列工作义务所确定,也同样地涉及世界的建构和世界的消解。我们关于小说的信念将会发生改变。这不是简单地由于这种新技术产生的新事实,而是因为新技术对我们的情感的新的影响方式。这也许是计算解释学的第三法则:技术影响论题,不仅仅在于它产生的新事实,更在于它改变我们与我们阅读的文本间的情感联系的方式。
附录: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安德鲁·派博副教授访谈*本文系栏目主持人戴安德、姜文涛对安德鲁·派博所作本刊独家访谈,由原新华社英文编辑曾毅翻译。
问题:您能给我们讲一下您的学术背景吗?您是怎么进入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您在这个过程之中面临过什么样的挑战?或者说,您本来的学术背景在您进入数字人文的时候给了您什么样的优势?
回答:我本来的学术训练是德语文学和欧洲文学,尤其在书籍史这方面。我之前的工作是关于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过程里,书籍如何影响了它的读者。所以,现在来理解计算机如何影响了我们的阅读,也可以算是我之前工作的一个自然的延伸。最大的挑战是适应作量化分析的要求,这样的工作远远比写程序复杂得多,我发现快速使用量化的数据很有挑战性,而同时也很激动人心。我们能从其他学科已经做过的事情那里学习到许多,我们也可以带着自己的价值参与到这些讨论中。对于人文研究来说,历史偏向的和主观偏向的学术更有价值。我看到这样的人文研究理想可以影响到目前正在发展的、用于学习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分析模型类型,很激动。
问题:最近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大多依赖新形式的合作模式,或者是某种“实验室”的形式,或者是不同学者之间的远程协作。您能谈谈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学术研究方面的经历吗?您与其他学者合作吗?
回答:我现在的大多数工作都是与人合作展开的。我还有一些项目主要由自己来完成,但越来越多的工作是与其他同事一起完成的,也涉及和学生们的合作。有时候,我与计算机科学的人合作,许多情况下也跟其他人文研究者合作。这跟所谈研究的社会属性有关系,如果是要理解大规模的人类社会行为,就会与其他人合作展开。如果研究的是形式方面和美学方面的问题,我就倾向于以较为个人的形式开展。看起来是所研究问题的属性使得我有兴趣与别人合作。
我发现跟学生一起工作最让人享受。我现在跟学生合作更密切了。我们一起展开某些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做研究。他们其实更能说拥有这些研究。我发现这样做给了学生许多力量,对作为导师的我也很有启发。这样也并不总是利他性质的,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比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展开更多的研究项目。
问题:您能跟我们的中国读者讲一讲“小说文本数据库挖掘”(NovelTM)这个项目吗?这个项目涉及许多学者间的合作,这有什么意义?它在宽泛意义上的学科内是如何定位自身的?而且,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数字人文的新期刊《文化分析学》(CA:JournalofCulturalAnalytics)吗?
回答:NovelTM涉及北美14位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者,还有3位合作者并无学院的背景。这项研究的目标是产生出历史上第一部大规模的、涉及多个文化的、量化的小说史。与非学院背景人员合作,是因为这会迫使我们思考我们的工作如何能在学院之外产生更大的影响;与其他学院派研究人员合作则会带来真正多元的思考模式,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重新理解小说史。我们主要的贡献会是开启一场如何从计算角度思考复杂文学文本的谈话。我们该更努力一些,发展出一个跨文化的方法。
《文化分析学》是一个致力于以计算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的期刊,它是开源的,以网络为主。我们的目标是推出这样新类型的学术:认真思考文化研究的问题,但是使用计算来产生关于文化的新的认识。我曾经写过一篇简单的介绍,题为《这里会有数字》(“There will be numbers”)*参见http://culturalanalytics.org/2016/05/there-will-be-numbers/,那里的描述更有深度一些。我谈了为什么我觉得计算可以对文化研究有许多的贡献,以及为什么文化研究也会影响计算模型的发展。这个期刊并不仅仅只对计算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有用,而是优先考虑那些针对人文研究的论题。
问题:我们来谈谈刊登在本期的您的一篇新作《小说信仰:皈依阅读、计算建模及现代小说》,在这篇文章中,您谈到“细读”和“远读”之间的辩证方案,可以让我们以新的更有生产性的方法,来思考技术是如何促使某些新的阅读方法产生的。您是如何想到这个方案的?您觉得,在我们目前日益多媒体的环境中,这个方案是在如何变化着的?
回答:“阐释学的循环”这个观念非常古老。将其应用于计算分析,这看起来很合适。这个辩论目前为止也很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模式并不存在于我自己的方法之中,我的方法本质上是很循环式的。我们不能只赋予某一类别的阅读特权,相反,我们应该欢迎不同的、互为补充的观察。阅读这项活动总是比学院派倾向于认为得更多元。您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不同类型的媒体决定不同的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如此,但是,更重要的是集中在“实践”这个方面,即我阅读的时候我究竟是在做什么,这与所阅读材料的媒介材料无关。最后,我们需要在“发生效果”(“validation”)方面作更多的研究,我们需要努力理解我们建立的模型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您所谈到的这篇我写的文章中,建立了那个图表,我那样做的动力就在这里。我觉得那是一个新的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希望看到有人会在这方面作更多探索。
(责任编辑:陆晓芳)
2016-09-25
安德鲁·派博(Andrew Pip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加拿大麦克吉尔(McGill)大学德语及欧洲文学副教授,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以量化的方法研究小说史的学术项目“小说文本数据库挖掘”(NovelTM,网址:http://novel-tm.ca/)的主任和数字人文研究期刊《文化分析刊物》(CA:JournalofCulturalAnalytics,网址:http://culturalanalytics.org/)的主任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是自18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及其阅读技术,集中于文学拓扑学与网络的历史、文本流传及跨文本实践、文学量化分析。
I0-05
A
1003-4145[2016]11-0054-19
译者简介:陈先梅(1980—),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学理论。
①Andrew Piper, “Novel Devotions: Conversional Reading,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the Modern Novel.”NewLiteraryHistory46:1 (2015), 63-98. © 2015NewLiterary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